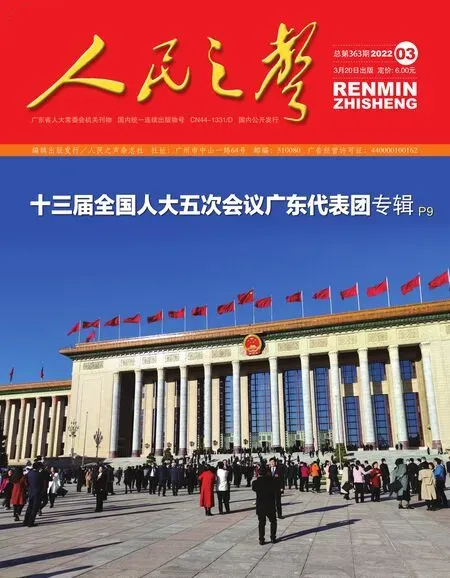后冬奥时代 体育立法如何提速
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冬奥会上,除了精彩纷呈的赛事,“冰墩墩”等冬奥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俄罗斯“花滑天才少女”身陷兴奋剂争议风波,韩国代表团不满裁判而诉诸国际体育仲裁庭等等,也留下了令人难忘的插曲,直观呈现了体育与“规则”“法治”之间的内在联系。
无独有偶,就在三个多月前,体育法修订草案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历一审,正式启动了实施26年来的首次大修。在迎接冬奥会的时代语境下,体育法的修法之举,不应仅仅视为体育领域基本法的一次更新换代,更应成为体育立法全面提速的起点。其深层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体育立法体系虽然已初成规模,但在关涉重要社会生活的立法版图中,相较于近年来文化、卫生、教育等领域立法的迅猛进展,体育立法的增长却明显落后。其突出表征是,在中央立法层面,仅有1部体育法和7部行政法规,体育领域的制度规范,实际上更多依赖于数百件部门规章、地方法规与规章,乃至政策性文件与行业内部规则。高位阶立法的供应不足,不仅拉低了体育立法的权威性,更难以回应体育领域的法制需求。
因而,梳理当下体育发展和改革进程中的立法短板,全力加快核心制度的法律法规化,理应成为后冬奥时代的紧迫议题。更应看到,体育立法牵扯多维的价值诉求和冲突,如何作出合理平衡或取舍,决定了立法的观念底色和制度重心,也是未来推进体育立法的深层追求和终极意义之所在。
至为关键的是,体育立法应当坚守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定位。从本质而言,体育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人权事业,体育立法的最高价值是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然而因传统体育体制惯性等影响,我国当下的体育立法,秩序优先的行政管理色彩依然十分浓厚,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制度设计则相对薄弱。近期亮相的体育法修订草案,已在我国法律中首次确认了“公民体育权利”,但这一原则性的立法进步,仍然有待具体法制开辟落实权利的通途。未来的体育立法,不仅需要设计满足公民多元化体育需求的普适性权利机制,也需要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村居民等弱势群体的体育权益予以特别关怀,还需要大力强化对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体育从业者的权利保护。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向体育权利保障法的全面转型。
此外,体育立法应当合理规划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与树立国家形象、振奋民族精神的竞技体育相比,大众体育具有提升国民素质的普惠价值,也更契合体育的初心,两者的共生共荣、不可偏废,才是体育应有的良性生态。因而在填补竞技体育立法盲区的同时,应当将立法资源更多地投向大众体育,以扭转当下大众体育立法弱于竞技体育立法的失衡状态,为全民健身、学校体育、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等等提供更有力的法制支持。
还有,体育立法应当妥善调谐体育公益与体育产业的利益冲突。近年来,竞赛表演、健身休闲、体育用品、体育培训、体育彩票等新业态的兴旺,以及竞技体育职业化等改革措施的推行,创造了日益壮大的体育产业,也为体育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因而体育立法的一大重心,乃是构建目前极为欠缺的体育产业立法,对体育市场准入、体育产权界定、体育无形资产保护等关键议题作出法制安排。尤其是,立法在扶助体育产业的同时,也须对体育过度商业化抱有足够警惕,因为这将侵蚀体育的公益属性,甚至滋生假球、黑哨等恶果。这就要求立法明确政府的监管权力和公共责任,厘清产业的市场权利和社会义务,最终在法治的轨道上实现体育公益和体育经济的双赢。
再有,体育立法应当大力推进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的深度融合。正所谓“体育无国界”,体育高度的专业性、跨国性等特质,意味着世界各体育组织的自治规范已构成国际体育法则,也催生了国际体育仲裁庭等全球性体育争议解决机制,这就要求我国体育立法具备国际视野,注入更多的开放性和融合度。比如,正在进行中的体育法修订,已经增设了“体育仲裁”章节,为我国摆脱长期缺失专业化体育仲裁的制度困境奠定了立法依据。在此基础上,有必要以单行立法的形式加以细化,真正建立起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世界接轨的体育仲裁机制。同样,在反兴奋剂、体育知识产权保护、职业体育等纬度,我国体育立法也需高度尊重国际体育公约、规则和惯例,进而实现立法实施效益的最大化。
正如奥运精神所昭示的,后冬奥时代的体育立法,理应秉持“公平、公正、权利”的立场,向“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演进。而经由法治力量加持的体育事业,也终将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助推我国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