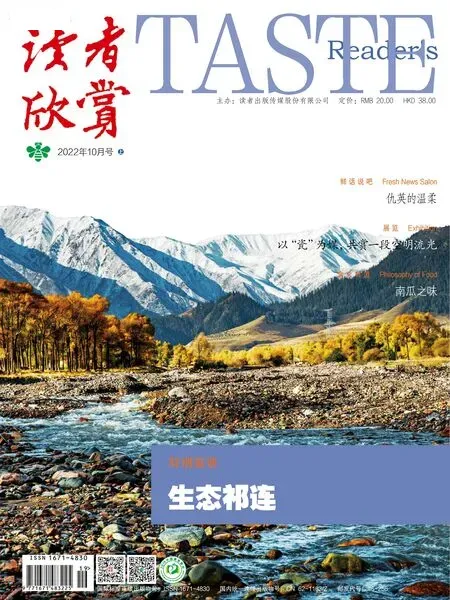仇英的温柔
文吃畫人
从小缺失了传统诗书的洗礼,仇英没有沈周、文徵明、唐寅的满腹文采,他从不向当时的文人一样在画上题诗作记,大多时候连落款也不写。他把自己隐没在作画之中,为画而生,因画得名,最后又湮没在浩如烟海、不记年款的画作里。
阁中帝子
提起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或许你脑海里会马上浮现出接踵摩肩的行人商贾、目不暇接的店铺酒家、街头巷尾的牛羊猪马……为了凸显京师的繁华,画家把“热闹”二字做到了极致。
要比热闹,后来者仇英毫不逊色。两者同名画作中精彩丰富的细节早已被无数人叹赏。那人山人海的集会,可以说是对张择端画中市井元素的新时代演绎。但若是仅仅如此,也只能说是小有变化。

清明上河图(局部)绢本设色 全幅30.5cm×987cm 明 仇英 辽宁省博物馆藏
如果非要说仇画有什么天然的优势,或许是那明亮多彩的设色—是它让热闹不再深藏在随时光流逝越发深沉的绢色之下,变得明明白白、直入眼眸。除此之外,同样以“清明上河”为题,要怎么在“热闹”上下功夫才能超过前人珠玉?又或者,至少是在某些方面自出新意,不落母题的窠臼?对于后来的模仿者来说,即使做到和原作一模一样,也无法在任何意义上称作胜利。这种始终被压过一头的感觉,直至看到仇英《清明上河图》的最后1/12处才得以释怀。
在一处曲折宫墙的阻隔下,市井的繁华景象戛然而止。然而,只要继续往后看,你就会发现它只是看上去戛然而止罢了。宽阔的江面上,女眷们划着龙舟驶归江畔的亭台楼阁。那里雕栏玉砌、金碧辉煌,却空荡荡的,只画有两位举头凝望的宫人。她们的视线落在一处江景最胜、金瓦朱栏的阁楼中一把空荡荡的座椅上。

宫乐图 绢本设色 48.7cm×69.5cm 唐 佚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时,少即是多,无言却似有万语,人山人海不敌一把空椅。仇英不画平地,而是将宫殿楼阁置于大江之上,又在有意无意间唤起观者对于那首著名的《滕王阁序》的记忆:“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借着脍炙人口的唐诗,我们仿佛听见仇英隔着由宋至明300多年的时空,向他摹写的前辈张择端发出一声无言的回应:美人歌舞已罢,阁中帝子何在?300年间几度物换星移,当年汴京的繁华早已和唐人的诗句一样成为回忆,只有槛外江水,还在不舍昼夜地奔流入海。仇英写不出比王勃更好的诗句,但他还有画笔。
“C位”是猫咪
一场热闹酒局中,有人用力碰杯后大口豪饮,有人旁若无人地引吭高歌,夹在中间的小辈却无处可逃,只能皱着眉忍到曲终人散……对于观画人来说,《宫乐图》里有妖娆的唐代仕女、精致的乐器酒盏。但对于画中处于“C位”的宠物犬来说,上一段的描述或许才是它的真实体验。
并排合奏古筝、琵琶、胡琴的三姐妹,整张脸都在用力的吹笙女,手持拍板伴奏的侍婢,构成了饭桌上的主旋律。已有如此声响,需要发出多大的分贝,才能隔着老远行酒令?除此之外,还有更强的画外音浪。从左侧跑进画内的侍婢扶住不胜酒力还要逞强的主人。而另一名女子手持大碗转身盯向画外,暗示了我们看到的有可能只是盛大宴会中的一桌而已。
逃无可逃的宠物犬蜷缩在桌底,铺天盖地的嘈杂声传进它耷拉的双耳,邻桌的景象也让它无助皱眉。很难相信仇英没有见过这幅《宫乐图》。如果说唐人画中处于“C位”的黑狗还不够抓人眼球的话,仇英笔下的猫咪则不偏不倚地趴在了《汉宫春晓图》的中央。
对于观画者来说,这里有太多扑面而来、入目即难忘的场面。捣练及熨烫的宫人、好动的婴孩、乐器三人组、闻乐而舞的观众、围坐斗草的众人、窃窃私语的闺密……擅长摹古的仇英为前代画作中的经典细节穿上新衣,毫无违和地重新布置、组合,令人目不暇接,但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连下棋、画像、读书这样原本没有什么声响的活动,也在众人的围观下显得聒噪起来。
相比之下,那只趴在藤椅上、还没有某些宫女头大的小猫就太不惹人注意了。说它微不足道吧,工匠出身、对谋篇布局极为讲究的仇英又怎么会以“ C位”相予?他大胆地将一只猫塞进画心,又小心翼翼到不想留下痕迹。
不同于《宫乐图》里愁眉苦脸的黑犬,仇英笔下的猫咪则睡得浑然忘我。其中有动物习性的差异,绝非脱离现实的刻意安排,但选择不同的对象本身就反映出画家的心意。
当同时代的吴门才子们纷纷落笔扬名,以诗书画三绝为至高追求,埋首画图的仇英用数年的光阴才磨砺出一件鸿篇巨制。屈子说“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不善言辞的仇英和他笔下的这只猫咪,却以另一种方式在说:“任世人再吵闹,我自睡我的觉。”
落单的穿水竹
《独乐园图》是我认为最能反映仇英身上矛盾特质的一幅画。不满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从朝中隐退,来到洛阳买田置地,并亲自设计新家,取名“独乐园”,在那里度过了13年“辛苦著书却无世俗之累的悠悠岁月”。因为园主人自己写的《独乐园记》和歌咏其中七处亭台楼阁的《独乐园七咏》,“独乐园”建成之初就已声名远播。而司马光在独乐园中那段“宁守幽独”的岁月,更是让其在后世升华为无数文人的精神家园,以至于很多人常常忽略了历史上独乐园真实的样貌。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写道:“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

汉宫春晓图(局部) 绢本重彩 全幅30.6cm×574.1cm 明 仇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汉宫春晓图(局部)
相比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司马光风流潇洒的诗文无疑流传更广,也更具感染力。且一个亘古不变的现象是,当某地成了只存在于诗文中的“精神家园”,往往会经历一代代人想象的美化:一个前代大贤设计、居住,还留下了不朽之作的地方,必然在历史记忆中变得更为优雅、宜居。

独乐园图 绢本设色 28cm×519.8cm 明 仇英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独乐园图(局部)
在《独乐园图》的前六景里,仇英都在满足人们关于这座名园的美好想象。直到那条通向第七景“见山台”之“路”的出现。那是一处《独乐园记》与《独乐园七咏》中并没有的存在。
按司马光的描述,“见山台”本在一片树林之中,但仇英改变了原来的方位,将它安置在江面。最直接来看,这可能是因为江边视野辽阔,在图画表现中更适合与见山台相连。但若仅仅出于这一考虑,直接在第六景“浇花亭”后面跟上“见山台”即可,即使要添加一段过渡,也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仔细看“通向见山台之路”与“见山台”的景致,跟前六景有不小的差别。这里没有“采药圃”内秩序井然的草药、精心搭建的竹庐,而是错置的怪石、自在饮水的麋鹿、水际荒疏的灌木、扭曲光秃的枝干……
当想象中典雅、有序的独乐园已大体具备优雅调性的前提下,加入一丝原始、野性的气息并不足以倾覆整体的氛围,反而可以使园子更具一种亲近自然的文人趣味。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汉宫春晓图》等大多数仇英宫廷画风的作品中没有的粗犷或者说“野性”的那一面。而在《清明上河图》里,自然景致只是市民生活的点缀,那种粗放也是与这里全然不同的。只有在设定中极具文人气质的《独乐园图》里,仇英必须要在精确和粗犷、优雅与野性之间做到某种调和。
长卷前3/4部分仇英太擅长了,但当他在结尾试图让自己陷入某种“失控”,画风一贯严谨精确、优美有序的仇英能否突破自己?

通往“见山台”的路上,一竿绿竹被大风吹得弯折入水,然而梢头又穿水而出,形成一个大“S”。在这幅画里,竹子总是以竹林的形式出现,只有这一竿落了单,从一株老树后冒了出来。
竹子自古以来便是文人精神品质的象征,扎实、坚韧、不畏风霜。独乐园七景中就有一处“种竹斋”,另一处“采药圃”里也有一座竹庐。只是相比于前两处用来烘托文人雅致的“花瓶竹”,通往“见山台”路上的“穿水竹”才更像是园主人精神的映射—宁守幽独,且在风霜摧折下倔强向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里仇英也在试图唤起观者对历史上真实的独乐园和身处其中的司马光的记忆。
一根竹子需要经受多大的摧折,才能弯曲成如今的样子?可画中的它枝叶不乱,身姿妖娆,就像是刻意摆出的造型。这里不是沈周、文徵明、唐寅画中常常出现的野外,工匠出身的仇英一丝不苟,拒绝放任任何设定之外的不确定因素。而当“失控”成为需要小心控制的状态,它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那正是所有艺术创作中最能带来惊喜的部分。
在《独乐园图》的结尾,仇英似乎要努力突破瓶颈,却并不能尽意。事实上若是真的尽了意,可能只会显得更加突兀。一笔一画都认真掌控的他太渴望做到完美了,殊不知真正让完美变得完美的,反而是那一点儿意料之外的不完美。
这是仇英的不完美,却也是他作为真实的人的可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