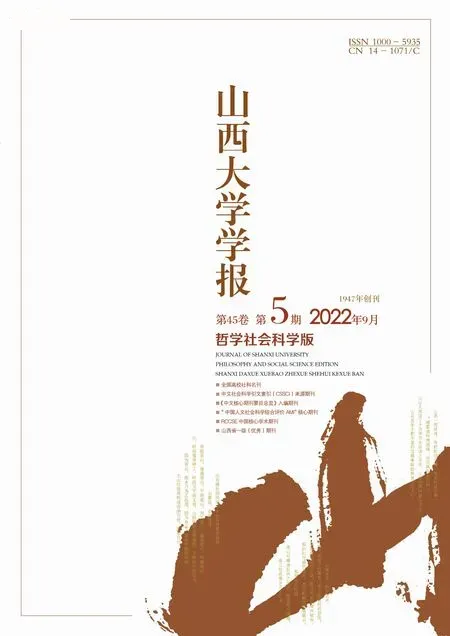“恩师”及其现代困境
郭 华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恩师”是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有现象,我国尤甚。直至今天,被称作“恩师”,仍是教师的至高荣誉。但现代学校的大规模、标准化、统一化,却侵蚀着“恩师”发挥作用的空间、存在的土壤。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教师地位很高,与“天地君亲”并列。“尊师重道”是植根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基因,尊重、信任教师几乎是传统中国人的本能。即便在现代学校,教师依然受人尊重,教师职业是教育事业的关键,所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专业发展、教师队伍建设历来是我国教育政策文件的重点。“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表达着对教师专业自主权及教学能力的无条件信任与依赖,是理所当然无须反省的口头禅,但从各地历年的“减负”文件中,从学校管理中却又能看出对教师能力和职业品格的不信任、对教师专业活动的干预。例如,“一刀切”地强行规定作业的时长、类型等,教学常规管理的细碎、繁琐以及全景课堂监控设施的使用等。在家长那里,也反映出同样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希望教师能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学生,倾心付出、不计成本、无私奉献;另一方面,却又希望以法律条目来要求、约束教师的基本行为,以保障学生的基本权利和教育公平。
这就是现代学校教师面临的困境。一方面,现代学校的高效运行需要尽可能地摒除个人因素而主要依赖和突出制度的作用,教师必须服从制度、受制度支配;另一方面,即便是标准化的现代学校,想要有生动、温暖的教育活动,也必须依赖教师个人的主动性。这个困境,既是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的困境,也是教育活动、师生关系的特殊性在现代学校的突出困境。
一、“恩师”的社会心理基础
“恩师”频出的社会,通常知识经验少、教育资源稀缺、教育不普及。有一技之长的工匠、艺人、识字人、僧侣、官吏、乡绅,都可能是“师”,相对数量却少之又少。能够拜师门下、“登堂入室”是求学者极大的幸运。“拜师”这个词彰显着古代社会教师无上的权威地位,同时也表达了学生放下自己、以师为上、以师为尊的意味。“亲其师而信其道”,只有尊重、信任教师,才能信他所传授的“道”、得到他的“道”。师道一体,不可分割,“师”就是“道”,用现代语言即可表达为“教师即课程”“教师即教育”。教师有什么便教什么,想教什么便教什么,能教什么便教什么。学生所求之“道”与教师所传之“道”同一。教师所传之“道”,既包括他关于世间万物的知识经验,也包括他对待自己、他人以及学生的态度、方式,不能分而析之,也不能与教师分离,是与“师”同在的一体,是他的经验、本事,也是他的人格、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是他之所以为“师”的根本。因此,教师的经验(即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专业判断就是权威本身,他人无能力质疑也无权力质疑。这是恩师(当然也有恶师)及其专业权威的社会基础。
在传统社会,“尊师”“重道”是一体两面。“尊师”才能“重道”,“重道”必然“尊师”。“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学记》)。“严师”是“道尊”的前提与表现,是核心、关键。《学记》讲“君之所以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尊师既是为学之道,也是学习的结果。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教师是“师父”,意指对学生有再造之恩,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论语·先进》)视师为父,是对学生提出的伦理要求。学生尊师如“父”,教师便要“爱生如子”。师生关系,因“传道授业解惑”而结成,却不因“传道授业解惑”结束而瓦解,而是转化升华为更为浓烈的父子亲情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教师的职责并不限于“传道授业解惑”,其角色行为并非全是职业行为,而是“亦师亦父”“师、父一体”。教师要像对待自己的后代那样全身心地为学生着想,尽心尽力去成就学生。教师的地位高,责任也同样高。
这是尊师的深层心理基础,并由此发展出一套尊师重道的传统观念及行为方式。我国著名的文化典籍《论语》的记录方式便是这种观念及行为的反映。虽然《论语》也有弟子与孔子相互启发的对话,但这些文字,在相互启发的背后,彰显的是孔子作为至圣先师的高德大品、教育风格。如: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论语》里最典型的对话是“问答”——弟子“问”孔子“答”。问仁、问政、问知、问友、问行、问耻、问君子、问事君、问为仁、问为邦、问事鬼神……几乎无所不问。或许问答现场也有议论、有争辩,但记录者并不重视争辩的过程而只关注孔子的教诲和教导,只呈现“子曰”的内容。如《里仁》: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
“子曰”是学生需要牢记并践行的圣人教诲,是“道”。
颜回是孔子弟子的典范。“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颜回之不“愚”,是因为他能够“退而省其私”,过后再自行反思、生发,有自己的想法、见解。而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贤者”精神,大约是颜回被后世奉为榜样的重要原因。也正因其“贤”,他面对孔子时“如愚”的“无违”,便成为传统中国师生关系样态的原型。
《论语》也有记录孔子幽默风趣、率真自然的篇章。他和学生开玩笑,也会承认自己不严谨。跟学生在一起,是很“平等”的。如: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甚至子路对他去见南子表达“不说”时,孔子要对天发誓,“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可见,孔子与弟子的关系并非后世所描绘的那样等级森严,孔子个人也非那样干瘪无趣。但在后世的普遍想象中,孔子却是不苟言笑的上位者,他与学生的关系被塑造为等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或父子关系。孔子形象成为尊师重道所需要的至圣先师的抽象概念。随着时间的延移,尊师重道渐被化约为了“不违”,教师由“道”而具有的专业权威则演化成了教师的人格特征。“尊师重道”成为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也成为中国人普遍的日常理念与行为方式。虽然它形成于现代学校出现以前,却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学校的师生关系及行为方式。
二、“恩师”的魅力与作为
古往今来被尊为恩师的人,都有共同的特点:学识广博、人品高洁,受学生尊敬、爱戴、仰慕。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不只是他的弟子的恩师,更是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在弟子心里,孔夫子如日月,至高至明,得其门而入者寡矣。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类,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得其门而入者,就能发现最高的美好,令人“欲罢不能”。颜渊的名句是对恩师的最高赞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论语·子罕》)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是当时希腊年轻人的崇拜对象,若从东方的观念来看,也是“恩师”。在柏拉图创作的有关苏格拉底的对话中,苏格拉底虽不似孔子那般万事皆通,但读者依然能体会到苏格拉底学识的宽广、人品的高度,以及人们对他的崇敬和赞美。但苏格拉底本人却对他人的仰慕有嘲讽之意。《会饮篇》中苏格拉底与诗人阿伽通的对话非常典型:
苏格拉底坐下来说:“阿伽通啊,要是智慧能像满满一杯水,通过一根毛线,就可以引到一只空杯里去,只要两个人挨着坐,智慧就从充满的人那里流进空虚的人心里,那该多好啊!如果智慧是这样的,我该把坐在你旁边这件事看得非常珍贵,因为我想这样一来你的许多智慧就会倾注到我身上。我的智慧很浮浅,有如梦幻,是真是假还说不定”。[1]9
苏格拉底的说法,与中国人常说的“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观念截然不同。他不认为智慧可以传输,更不认为教师一定有智慧。苏格拉底并不强调“师”的地位,而在乎通过对话达成真理。例如,阿伽通说:“苏格拉底啊,我没有办法驳斥你,就承认你的说法吧。”苏格拉底则说:“亲爱的阿伽通啊,你不能驳斥的是真理,驳斥苏格拉底并不是难事。”[1]51无论是苏格拉底本人还是那些奉苏格拉底为智慧者的人,不仅把当面驳斥看作正常,更看作是追求真理的一种路径。这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思想基础,与中国传统的“师道”不同。
相同的是年轻人的仰慕和追随。《会饮篇》中有大段文字描述苏格拉底的学生阿尔基弼亚德对他的由衷崇拜,有着类似颜渊一样的“欲罢不能”的喟叹。
这个人的言论对我影响很大……我一听到他的讲话就心跳不已,眼泪夺眶而出……不能把握自己,有如处在奴隶状态之中。[1]77
当他认真地推心置腹的时候谁都看见他肚子里的那些神像。这些神像……非常神圣地、金光闪闪地、无比美好地、奇妙地向我走来,使我感到必须五体投地去遵照苏格拉底的愿望做。[1]79
令学生“神魂颠倒,有如处在奴隶状态之中”“五体投地”“随它摆布”的,正是苏格拉底的学识和人格魅力,“他肚子里的那些神像”“非常神圣、金光闪闪、无比美好、奇妙”。苏格拉底之让人欲罢不能、能够抓住别人的灵魂,是因为他拥有美好的品质,有令人景仰的人格魅力。和孔子一样,苏格拉底也“循循然善诱人”。
苏格拉底对年轻人的教导,不是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智慧告诉年轻人,而是通过谈话,像“产婆”一样,帮助年轻人自己将原本有的东西引发出来、“生育”下来。当然,没有产婆,“生育”会极为困难,甚至“胎死腹中”。因而,教师的主动引导就极为关键。苏格拉底遇到年轻人(美少年)总要去主动谈话,“苏格拉底……总是围着他们转,向他们献殷勤。”[1]78在《会饮篇》中,苏格拉底引用女巫狄欧蒂玛的话说:爱就是共同“生育”美,爱者与被爱者(或者年长者与他所爱的年轻人,或教师与学生)在一起,是为了共同去“生育”美本身。推而广之,教育是师生双方共同的努力,是追求智慧的“同行者”。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语境有所不同。中国讲究“求学”,是弟子(学生)向先生求、向先生学。相比于教师,学生更要有主动的意愿。“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学生若是达不到愤悱的状态,没有积极的状态,教师便不予启发。《论语》里记述了“宰予昼寝”事件。“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孔子更强调学生的主动。对学问的敬畏本身也是弟子需要修习的内容。
孔子与苏格拉底各自开启了东西方不同的师生关系传统。16世纪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园》(1)《雅典学园》是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桑西于1510—1511年创作的一幅油画。、我国明代画家吴彬的《孔子杏坛讲学图》描绘了各自想像的先贤圣师形象。《雅典学园》最醒目的中心是并排前行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其体态、表情和动作,无疑都在表达这是正在争论的两个人。这与中国人对孔子师徒关系的描绘显然不同。无论是吴彬笔下的《孔子杏坛讲学图》还是当代的孔子讲学图,都表达着共同的想象:孔子独居高位,弟子们在下静听。无论是面部表情还是行为样态,弟子们都是凝神恭敬的——这样的态度正是对待恩师的态度。
在中学语文课本里,有鲁迅记述自己先生的两个名篇——《藤野先生》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三味书屋”写的是鲁迅儿时的授业恩师寿镜吾先生。这位先生是典型的中国教师形象,表面严肃古板,内心却对学生宽和宽松,质朴博学,极具魅力。
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这段话直白地说出了年幼学生的真实心理:对先生的恭敬是因为先生有获得尊重的前提——品格和学识,不见有分毫“师道尊严”的影响。
这位先生之所以令鲁迅难忘,大约与他古板教师角色之外的长辈般宽厚的品格分不开。鲁迅先是记录了他少时的调皮: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绝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
这一段刻画的是先生的古板严厉,有着“先生”应有的刻板风格,似乎不宽容、不温和。
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哪里去了!”
先生的宽容和可爱,一点点在鲁迅的笔下生出来。及至鲁迅写道:
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先生的宽容和可爱越发清晰可见。他既有先生的规矩,更有对孩子们如长辈一样的关心,“总不过瞪几眼”,用自己的方式督促孩子们好好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一定是先生的可爱可敬令鲁迅记忆犹新。因为有这样的先生,才会有学生像对长辈一样的恭敬,又能发现教师如同行者一样的可亲可爱。
鲁迅《三味书屋》里的“先生”,是中国人内心对教师的形象定位,师的严肃严谨、父的严厉慈让、友的宽容坦然,集于一身。
三、恩师的专业自主权
在传统语境下,“师父”一词本就意味着教师于学生有如父母般的再造之恩。“恩师”(2)恩师有时也作敬语用,这种情况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恩则比“师父”更进一层。“恩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创造奇迹、化腐朽为神奇的人。恩师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除了他在知识或技艺上有超于常人的神奇之处,还有他全心全意、全身心付出、想尽一切办法去成就学生的品格。严厉或者温和,暴风骤雨或和风细雨,并不重要,只是其内在品质的个性表达。人们把教师比作蜡烛、春蚕,正是对这种全心全意、竭尽所能、鞠躬尽瘁为学生的精神和品格的赞誉。这样的教师,比父母更用心,配得上“师父”,是成就学生的“恩师”。
“恩师”对学生的成就,决定了“恩师”是一个结果性而非过程性概念,是教育过程结束后学生感激教师时的称谓。教师能否被称为恩师,要看他能否培养出超出一般预期的、有成就而且有感恩心的学生。换言之,“恩师”是由学生在“未来”定义的。处于“现在”的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但都期待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也都明白“未来”是“现在”的延长和展开。中国人相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没有努力就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因此,以“未来”来评判、定义“现在”既是教育的一大特征,也赋予了教师当下活动以极大的弹性空间,一切可能有利于“未来”的行为方式都被赋予了合理合法化的根据。“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笨办法,“恨铁不成钢”的强硬干预,皆因未来可期,便合理了。换言之,正因为人们对“未来”有期待,才赋予“现在”以意义,也恰恰是因为对“未来”的期待,“现在”本身没有了意义,只有它作为“未来”的准备和基础时才有意义。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未来比现在重要、结果比过程重要,这当然抓住了教育的根本和核心,因为教育是面向未来的,若无未来,便不需要教育。但是,完全用“未来”来定义“现在”,就会忽视师生双方尤其是学生当下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以及情感需求,忽视教育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在这样的情形下,“恩师”与“恶师”(3)“恶师”是笔者的自创,意在与“恩”相对。并不严谨,只能意会。可能只是一念之差、一步之遥,甚至是一体两面,在表现形式上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对教师的信任,给了“恶师”的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以理由和空间,但对“恩师”而言,则是给了他们探索更好地提升学生发展的空间,给了他们充分发挥专业自主权的空间。
“恩师”总是某个学生的恩师。学生千差万别,只有心里装着学生的老师,才能“看得见”每个学生的不同需要;能“看见”,还得有能帮得上学生的专业措施,也就是说,尽心尽力为学生发展着想的品格和境界,得通过高超的专业能力才能显现。因材施教,能够让每个学生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关心关注”,也是教师专业能力和专业自主权的重要体现。即便在古代的个别教学背景下,因材施教也难以实现,遑论现代学校的班级授课制。一方面,班级授课的统一要求,难以实现因材施教;另一方面,难以判断教师“因材施教”的做法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这样,就涉及现代学校是否允许教师行使专业自主权,换言之,教师专业自主权的发挥是有条件的。
《恩师的条件》(中译名《全世界都想上的课》)一书记述了日本传奇国语教师桥本武的传奇教学[2]。这本书之风靡日本,在我看来,除了桥本老师的神奇教学之外,还在于他所教的学生几乎个个成名。桥本武“中学三年只带学生精读一本薄薄的文库本(口袋书)小说,就把近三分之二的学生送进了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他任教的那所原本默默无闻的私立中学也因此一跃成为‘东京大学升学率’全日本第一的顶级名校……多年以后,他的学生遍地开花,成长为日本政经文教各界的领军人物”[3]。可以说,桥本武之为“恩师”,正是因为他教出了众多有成就的学生,他的教学法之神奇,也是在多年后的“未来”才被更多的人认可。
桥本武教学的神奇之处,首先是初中三年只带学生读一本薄薄的小说。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当然是因为他有胆识、有担当,但也因为他所在的学校有相当宽松的教育氛围,几无约束。桥本武就职于日本一家私立学校,学校独有的学制以及校长对教师的极大信任,赋予了教师行使专业自主权以极大空间。桥本武回忆:“一科目一教师,学生一入学就要带足6年,即一直带到他们毕业。……这一独有学制下,教师责任重大。尽管如此,对如我一样的新任教师也并无半句指示性的话,一切就都交给我了。”[2]168一门学科由一位教师教六年,教什么,如何教,完全由老师自己决定。正是这种宽松的情形,才使桥本武有可能弃文部省的官定教材不用而自主选择《银汤匙》作为学生初中三年的国语教材[2]168。当然,自选教材是因战后日本的官定教材实在“不成样子”“没办法教”[2]168。官定教材的“不成样子”,客观上为桥本武自主决定教学内容提供了自由空间。桥本武教学的另一独特神奇之处,是故意的“绕远”和“跑题”。
曾有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特意前来听桥本先生的国语课,但他的感想却不怎么正面:“跑题太过严重。”桥本先生……提及此事时这样写道:“跑题?这正是我想要的。这一评语,就当是教授认同了自己的特色吧。”……跑题真就是无处不在。他的课本就总是沿着与《银汤匙》本文无关的岔路不断开掘下去的,甚至于《〈银汤匙〉研究笔记》中的有些地方就像是要探一探究竟能跑题多远一样![2]45
桥本武自选教材、教学“绕远”“跑题”,这样的做法与现代学校的统一要求、标准化管理格格不入。他之所以能够存在,当然与学校的信任、他自己的品质与能力有关,但最根本的,是与东方世界关于教育的深层思想观念有关。好教师就是好课程,好教师强过好课程,有了好教师,差课程也会变成好课程,教师才是教学活动的核心和灵魂……,类似这样的观念,正是东方世界人们内心深处对教师能力和品行高度信任的反映。有了这样的观念,才会有对教师的信任。在相当大程度上,教师专业自主权的行使,反而来自人们对教师作为教师之品格的信任。
桥本武的“恩师”形象,还表现在他待学生的严格严厉。《恩师的条件》作者(桥本武曾经的学生)用“毫不留情”“强制”“严格”“魔鬼教师”这些词语来描写他。
无论是什么样的时刻,先生一直是毫不留情地给我们下达作文任务。这一任务是强制的,不完成是绝对混不过去的。……享有大名的魔鬼教师的身影,到我们入读时也依然浓墨重彩地保留着。[2]129
他对纪律的要求非常严格。若有礼仪不到位、上课迟到等违纪学生,用出勤簿敲他们头的情景,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2]序3
但他的严厉严格,不仅没有招致学生的仇恨,多年之后竟成为学生回忆的趣事[2]106-107。当年的“拳头”成为后来的“趣事”,这正是“恩师”的行为与形象。之所以能够成为恩师,其根据就在于对学生的全情关注,与那些对学生漠不关心、例行公事的教师不同。教师的严格要求,既是教育的手段,也是教育的重要内容。赫尔巴特曾批评过对学生的迁就。他说:“事情被一些老教育家搞糟了,他们迁就学生,通过各种各样的谈话与游戏,而不是通过唤起持久与增长着的兴趣来使应当进行的学习为学生所接受。假如这样地把学习意图看成一件必然的坏事,并把那种使学生尝到甜头的做法视为使学习可以接受的手段,那么一切观念都混淆了,而青少年在这种松松垮垮的活动中得不到他们本来能够得到的收获。”[4]基于专业判断,对学生提出严格严厉的要求,是教师的重要责任,也是成为恩师的重要前提。
对学生的“严厉”“严格”,是教师信任学生、尊重学生、平等对待学生的表现。当教师不再对一个学生有要求时,就表明不再相信他有向上的能力,也放弃了对他的教育。正如马卡连柯所言:“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也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5]严格要求与尊重学生是一致的。但是,在现代学校,教师对学生的态度,究竟应该严格还是应该宽容,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教师个人能够决定的。
四、现代学校还会有恩师吗?
如前所述,恩师主要是东方的传统观念。“恩师”,不仅需要教师个人有集于一身的渊博的学识、超凡的人格魅力,更需要有能够发挥其专业权威的宽松的制度环境。这样的条件,与现代学校致力于普及教育的设计及运行机制是矛盾的。
教育普及、人人受教育的理想,在现代社会,通过班级授课制成为了现实。班级授课制的分年级、分学科教学,不仅扩大了教育规模,提高了教学效率,还降低了教师职业的门槛,弱化了教师个人的重要性。在现代学校,成就学生的不再是某个教师,而是学校的所有教师。一个优秀的教师未必能成就学生,但一个蠢坏的教师却可以毁掉整个教师团队的努力。现代学校的运行并不依靠和突出某个教师的独特才能,但要防止团队中最弱的教师拖团队的后腿。在这个意义上,加强教师团队建设并不是要突出个别教师的优秀,而是把较弱水平的教师拉到正常水平,形成有机配合的团队。强化制度规范,依靠法律、制度、规则、规范来约束教师的言行,划出合格教师的底线,而非依靠教师个人的人品、修养,是现代学校教育教学运行的基本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学校与标准化的工厂一样,主要依靠制度而不是个别的“恩师”来运行。即便教育教学活动离不开教师,也要尽可能去除教师个人的情感和观念,教师个人要服从学校整体安排,要像精密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一样,发挥该有的作用,使学校能像夸美纽斯所说的如一座精密的钟表那样顺畅地运转。
现代学校的大多数课程是由外部规定的,即课程与教师是分离的,再也不是古代社会的教师即课程的同一状态,也不再是教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的情形。现代学校的教师,必先被教育、被培训,并经评估合格后才能进入教学过程。将规定的内容教给学生并且力保其达到规定的水平,是教师的基本任务。这意味着,现代教师也许并不需要多高的学识,但必须有完成统一任务的能力。而教师教学工作是否合格,是否完成了教学任务,也并不由教师自己说了算,而要由相应的指标来衡量。课前的教案、课上的环节、课后的作业布置等,都有各自独立又相互参照的评估标准。有的学校甚至装有课堂视频监测系统,可以随时查看每一位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教师必须遵从统一的规范,而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节奏来工作。如此规范的好处,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证所有教师的言行都能达到规定的合格基线,避免出现不顾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蛮干”,防止反教育行为的发生。
与教师个人的超凡魅力相比,现代学校更强调统一的言行规范,这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教师个人风格的形成,几无个人专业自主权发挥的空间。当然,即便在如此强大的统一规范之下,也有能够“带着镣铐跳舞”的教师脱颖而出,既合规范,又有个性。但总体而言,现代学校的教师主要是社会的代言人,是达成教育目标、帮助学生实现成长的中介手段,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学校并不需要“恩师”,若说有,也是学校——“母校”。所以,在现代社会,“母校”替代了“师父”,成为影响学生的人格化组织,而教师个体则被匿名了。
被匿名了的现代学校教师,如何在内心真切感受“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的崇高感和神圣感还需研究,但教师被他律、被监管却是生活常态。如果教师只能感受到这份职业的谋生价值而难以体会职业的崇高感,他还愿意投入额外的精力吗?还愿意做春蚕、红烛,为学生的成长呕心沥血吗?当教师的精神高度被拉低时,还能指望他培养出高境界的学生吗?还能要求教师无私奉献吗?
说到底,统一的规范和制度并不是教育本身,统一的规范和制度也无法替代师生面对面的精神交流。学生的个别需要、每个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次心理变化、动荡,必须由教师个别对待——教师必须付出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来投入工作。马卡连柯曾说过,一个教师要“学会用十五种至二十种声调来说‘到这里来’”[6]。换言之,教师说话的声调都在表达教育意图,更别提他的思想、精神和情感。现代学校虽然与大工业相伴而生,但学校教育毕竟与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不同,它是师生共同经历的生命历程。师生共在的时间、空间,相互间的一个眼神、互道的一句话语,都可能在学生内心产生奇妙的反应,成为学生成长的宝贵财富。承认教育是科学,但不能否认教育是艺术。科学有规律可循,可细分为规则、程序,但艺术却承担着那些无法细分的情感、想象力、创造性。广义的教育规律,本身就包含着艺术的部分。只有这样,才能说,好的教育是打动人心的教育,是能激励人自我教育、自我努力的教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便在讲求规范、制度的现代学校,依然要有愿意而且能够关心学生的教师,需要有超凡魅力的教师来感染和感动学生;需要有教师愿意投入情感、爱和希望;需要有教师愿意打破常规探索新路;需要有教师愿意承担责任,运用自己的专业自主权为学生的个别需要制定出有针对性的个别方案……如何看待教师,如何对待现代学校中的教师,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根本理解。是培养千篇一律的标准件,还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有灵魂的个体?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即便是在智能机器可以根据规则来替代教师工作的条件下,教师也不可替代。即便在现代社会,也依然需要“恩师”。
多年以后,当你回想你的教育时光时,也许已经忘记了教师曾经教过你什么,那些都已经化为你的思想、血肉,但你会记得老师投过来的那道目光,记得曾经微不足道的一句鼓励,记得那一刹那的感动。这正是教育的力量,是教师不可替代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