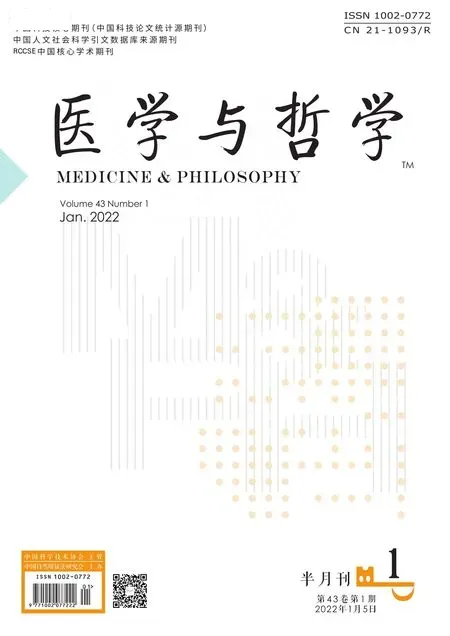应对癌:需要的不仅仅是科技,更是智慧*
何裕民
1 几个巨大反差案例之反思
2021年7月,杭州患友张某来看笔者,他是13年前的晚期肝癌患者,这些年患难与共,医患早已相交至深。2008年10月,他因乏力消瘦被确证肝癌,手术切除后病理是肝细胞癌,做了二次介入后恢复工作。2009年7月查体发现复发,但其无法承受介入治疗,只能改用当时欧洲刚被批准用于肝癌的靶药索拉非尼(Sorafenib),但副作用巨大。他当时任某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无奈中找到该省中医药大学校长求助,校长是笔者老友,建议他来找笔者。因身份特殊(老友介绍)而印象深刻。当时,虚弱至极的他无法行走,夫人搀扶着才能坐在笔者诊桌前,灰暗夹带黧黑的面容,折射出严重肝损态。问诊后得知,他每天用索拉非尼4片,是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的。他反复跟笔者强调,不想再用此药了,实在受不了……笔者看其体态,120斤上下,遂好言相劝,是剂量大了些,减量即可,此药不赖(其实当时他没更好的治疗办法),中西医结合,有把握可消解副作用。遂疏以中医药方案,同时叮嘱相关注意事宜;并告知其靶药是救急的,眼下可减量服用;一旦稳定,可逐渐抽去,因为靶药早晚会耐药。他信且应诺了。当时笔者即指示他索拉非尼减至3片,2周后复诊,症状明显减轻。2月余,检查结果很好,遂改成2天5片。半年余,一切皆好,已恢复全天工作,再次减量。就此循序递减,他依旧信且诺。坚信在综合调控下,自己定能走出来。约2013年前后,他停用所有靶药,只是以中医药为主,生活方式调整为辅。2014年,他荣升另所大学党委书记,升正厅级,主持工作。这些年,一切都好。这是他每年2次的例行公事,借复诊来看看我,并告知年龄到了,退居二线了,轻松多了。夫人则旁边唠叨说:早就该退了。他却不无自我得意地说,善始善终么……!
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就在一周前,天津某银行退休的李行长复诊,他于2012年5月确诊为肺腺癌,手术后3年整发现多处转移(切缘、胸膜及右肺尖部),行化疗、放疗,有的病灶见小、变薄,有的增厚,遂用生物扩增疗法多次,无效。因配对发现能用靶药,遂开始用凯美纳(Conmana),每日3粒(标准量),有些副作用,能够承受,怕耐药而要求中医配合。笔者也晓之以理,告诉他靶药短期会有效,长期定会耐药,积极配合中医药,控制剂量可延长使用时间,争取逐步减去靶药。他愉快应允了。2019年5月是他第10次来门诊(一年两次),此时凯美纳用量已改为2天1粒,属安慰剂性质。考虑其多次CT等复查均无恙,遂建议他可停药。又隔了两年多,近期复诊一切皆好。患者心情特别愉悦,因为靶药能抽去,且抽去后两年查体无恙,也算是巨大的成功。
笔者的靶药使用并非随意的,而是建立在长期经验及理性分析基础上。笔者根据20年来运用各种靶药治疗数以万例患者的经验,总结出以下规律:靶药应从小剂量用起;同时配合中医药,但时间宜岔开服用;见效剂量即可;稳定后(3个月~5个月)逐渐递减;并佐以相对密集的追踪检查(初期2个月~3个月一查,稳定后5个月~6个月一查)等的规律,屡试不爽。没比较就没深刻认识。靶药的比较似乎没太大意义,因为个体差异太大,且能抽去靶药者似乎很少,上述案例已能说明问题。
试以高科技之代表的免疫疗法,再行分析:
近期临床试用免疫疗法(PD-1、PD-L1等)不在少数,有些患者效果不错,但也有很多需思考检讨的。一位著名军旅作家,女性,2008年因肺腺癌手术,术后发现脑可疑转移而做放疗。第一时间就用中医药,一直控制不错。她原本是高产作家,曾因病而低迷一段时间。因控制良好,在笔者鼓励下2011年起又接连推出许多脍炙人口作品。她夏天住在北京,冬天住在海南,创作稿约不断。2019年3月,接到她从海南打来的电话,告知要来上海看笔者,但准备做一次PD-1后再来。我追问她为什么?她说希望好的更彻底点,也因为不差钱,结果不久便传来噩耗,一次PD-1就走了……
西部某省有位领导,嗜烟,先后发现前列腺癌、肾癌等,又因重大变故,查体确诊有胰腺癌,因笔者治此癌有点影响力,故求助。他人缘很好,其他癌同事们没瞒他,却隐瞒了胰腺癌,这是2015年的事。一年、二年、三年……都很好。2020年上半年因疫情,我们没法见面(原本一年能见四五次),结果2020年底笔者再去西部该省,他来机场接笔者,拽着笔者的手动情地说:差一点见不到了……。原来,我们没法见面后同事们关心他,也有权威医师建议他试试新的免疫疗法——PD-1(K药),拗不过,试了一次,有点轻微不适;21天后再用一次,用下去旋即转急诊抢救,昏迷近1个月方苏醒过来,原来,诱发了免疫风暴。他感慨万千地说:也许,稍有怠慢今天就不在了,再也不敢如此莽撞了。
也许,这些只是极端案例,因极端才记忆深刻。但这类事件并非罕见,故有资深肿瘤专家以“神药不神,精准不准”来定位当今癌症治疗之困境[1]。这些案例也引申出一个问题:靶药、免疫疗法等高科技手段对控制癌来说确实是重要的;但仅凭医药高科技,似乎又少了点什么,也许,缺少的,同样是重要的。
2 神药不神,精准不准——治癌究竟困在何处
防治癌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投入最多,也是期望值最高的领域。笔者从事癌防治开始,一直看到乐观派说人们将很快有效征服癌症。一查历史,原来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把治愈癌定为国家目标,如肿瘤权威贾伯1968年出版了《治愈癌症:国家目标》。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恩迪克特(K·Endicott)在1963年强调“下一步:完全的治愈,势不可挡”[2]。即使今天,虽治癌捷报频传,新疗法层出不穷,攻克癌之成果几乎天天见诸报端;且进入21世纪后美国部分癌的发病率/死亡率确有明显下降。但业内权威分析后认为,“美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的真正原因得益于美国人生活习惯的改变和减少对癌症的过度诊断”[1],而不是癌治疗上的根本性突破。中国国家癌症中心赖少清主任医师[1]认为:人们依然没有走出癌治疗尴尬境地,并概括出“神药不神,精准不准”之困境。如靶药一度给人们带来战胜癌之希望,被认为是神药,但其实并没那么神奇。原因在于:(1)靶药不能治疗所有癌;(2)靶药不能彻底治愈癌,只是延长生存期;(3)靶药也有不小副作用,且不能精准地选择癌细胞。故他在《癌症的现状与困境、希望与出路》一文中指出:癌症问题陷入泥淖是因为“癌症理论的困境”,“生物医学模式的基因突变理论不能解释癌症的全部现象,不具备成为理论假说的条件”。“战胜癌症的出路”在于“癌症认识的理论突破”,并提出“强烈的应激负荷是癌症的重要病因”等[1]。对此笔者完全赞同,但似乎意犹未尽,还没完全触及癌症困境的真正痛点。
防治癌症究竟困在哪里?这也许是没法寻求一致之认识,各有各的解答。根据认知常识,越是难解之题,越是首先需“知己知彼”。这是2 500年前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不刊之论。这一破解谜团之智慧,一直指引世人(包括国人、欧美等多国贤士)获得洞悉之光,破解迷雾,以寻得案底之举。
这里,“知己”是对自我能力之认知。对此需检讨:人们或自视过高(如上述的癌“完全治愈,势不可挡”);或自我蔑视(如“十个癌症九个埋,还有一个不是癌”)。但现在多少有了点“度”——虽有了进步,却远不够!各种神药、精准药不神、不准就是其典型体现。就本质而言,关键是“知彼”很差;没达到通透“癌症”之境地。对癌(彼)之认识,太过受制于旧说窠臼或习惯趋势了。
近300年来,经典物理之进展催生了大工业化,后者的巨大魅力又在潜移默化中滋生出“科学=简洁”之坚定信念——万事都需寻求最简洁答案。而简洁的往往也是最本质的。因此,人们在探寻癌的过程中前仆后继,奋勇探究,提出了数十种解说。这些解说,有些契合这类现象,但不符合那种临床表现;或仅在一定条件下有所契合,甚或都不契合。可以说,尚没有一种能“解释癌症的全部现象”。用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血液病(血癌)专家格里夫斯(Mel Greaves)[3]形象的话而言,对于癌,人们现在只是“蒙着双眼的射手”。因此,陷于迷茫中“不神”“不准”是再正常不过之事了。这,才是癌应对中人类遭遇的真正困境。
笔者丝毫没有嘲讽肿瘤学界付出巨大努力之意。因为已有共识:癌是有史以来人类遇到的“真正的对手”——这个对手太多样化、太狡猾、太强大且太有智慧了!一点都不输给近期正在肆虐、已导致2亿人感染、400万人丢失性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其不断变异之新病株,虽后者打得整个世界人仰马翻,慌乱不堪;欧美等发达国家也黔驴技穷,纷纷尴尬地按下社会的“暂停键”。但新型冠状病毒总有消解之时,而癌则不然,它注定会与每个人(至少半数人)打交道,因为有资料认为,现在活着的人,半数以上会在一生中某个时候遭遇到它。故亟需分析治癌究竟困在何处,如何破解,以便让芸芸众生能够更从容地应对它。
3 常规科学陷入困境时,哲思也许可帮助指点迷津
很显然,借助生物科学视野对癌症想获得一统之认知,此努力已陷入困境。“知彼/癌症”又是必须的。在常规科学陷入无解之时后退一步,就其更宽泛性质做些哲理分析,不失为有价值的举措。换言之,科学探索遭遇困境,借助哲学思维未尝不是一条路。笔者临床诊治癌40年,亲历5万余例患者,有些患者反复诊疗多次,诊疗约30万人次,现在看来,今天临床常见之癌,其实根本不是一种病(或一大类病),其背后机制错综复杂,并不存在共性之处!要说共性,充其量只是原先没有(或不应有)而新近发现的,也就是通常说的异常增生;再加上组织形态上的不契合,遂定义为“蜕变”或“癌变”等,这就是“彼”之本质。在生物模式窠臼下,人们太想把“彼/癌症”纳入某类“病”(disease)的现成框架之下,遂有了人们拼命努力而不太成功,却越挫越勇之尴尬。
笔者喜欢隐喻:体内被发现有癌,类似于社会有坏小子;坏小子可以是偷鸡摸狗的、好吃懒做的,或为非作歹的,甚或杀人越货的……差异巨大,一同于癌;如此宽泛地寻找其统一之共性,客观上存在吗?可能吗?有意义吗?众所周知,辩证法核心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对癌研究来说同样重要。因此,笔者认为第一要义是需区别对待,不奢求癌之共性机理及要点;别试图给癌作出划一且清晰之定义,并试图以划一模式应对之。而应借临床悉心观察追踪,理解其基本特点后,逐步深化对其细节及异同等的具体认识,即善于因人、因病、因时、因景(境地/场景)而异,作出应对,以求患者长期效益最佳化。
本文开篇的两肺癌都是腺癌,都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突变,都已复发,女患者无吸烟史,患病11年;男患者吸烟30余年,患病9年;都用靶药[男患者用凯美纳(Conmanm),女患者先用易瑞沙(Iressa)、后接泰瑞沙(TaiRuiSha)],都配合中医治疗后无特殊症状;但女患者因左肺手术导致左胸塌陷,身体略左倾,阴雨天左胸隐隐作痛。客观地说,男患者病情更重,因有多年吸烟史;但他更从容自得些,积极想抽去靶药;女患者则感性、细腻多了,且不时担心复发,始终不愿减药,即心理始终处在应激状态,故更愿频试新药,尽管笔者不主张她用PD-1(一般她对笔者建议都会言听计从),但有些情况下她更愿意赌一把,结果导致不测。这里,有太多的旨趣值得深究。
至少,拷贝常规疾病研究范例,试图对癌作出清晰划一之界定不足取,也绝无可能。每个癌都是个案。即使同样患肺癌,基因雷同,仍因人而异,甚至差异很大。对此,40年前张孝骞就“肠伤寒”之教诲,一直回响在笔者耳边。1982年,笔者在北京聆听了内科大师张孝骞的一堂课,受益良多:他说他一辈子看了2 000多例肠伤寒患者,没有两例完全相同。很像黑格尔说的“天下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传染性的肠伤寒尚且如此,更何况远较肠伤寒复杂得多的癌症呢?因为肠伤寒是伤寒杆菌引起的,病因明确,单纯得多了。而癌症呢?癌症临床表现之差异,就十分鲜明。更不消说其内在的本质差异。人类应对癌之困境,正是以往模式成功后的作茧自缚,希望按图索骥,硬套在千差万别的癌症中,典型的削足适履。
4 癌症:人类碰到的真正对手
已有学者指出,癌是人类碰到的真正的对手。不是说以前没有癌,而是说以前癌并没成为人类急迫需面对并解决的对健康巨大威胁。过去的健康威胁很多,像感染、传染病、器斗伤、流行病、代谢病、自体免疫性疾病等,但性质大都与癌截然不同。这不同体现在多方面。下列特点就很鲜明。
(1)癌是自体细胞之变异,或说自身细胞之“异化”。癌与自身细胞同根、同源、同种。可杀死癌的,往往也伤及正常;“补益”正常的,一不小心可能补癌。故有专家形容说:化疗之难,就像用同种药要烂掉右耳,却需保全左耳那么困难。
(2)癌变起因或诱因复杂。可以说所有影响生命过程之因素,都可能起着某种作用。笔者意识到,前述女军旅作家的感性细腻、多虑,有挥之不去的担忧,容易处在应激状态等,就是潜在的促其癌变不消停之因,成为阻遏康复的拦路虎。
(3)作为活泼的生命体,癌等同于病毒,顽强生存下去是其本能。不断适应、变异、逃逸、迭代等,目标是顽强延续下去,这是共性特点。遂在癌细胞中表现出耐药、暂时潜伏、变异、转移、逃窜、复发等特征。癌与病毒都有“智慧”,人类必须承认这点。有智慧的癌碰上“蒙着双眼”之莽夫,结局不难预料。
(4)从中医学视野出发,几乎所有的病都呈邪正两势力之争斗态势,相互消长中决定了该病之转归。尽管中医学仍恪守此睿见,但它却没能登堂入室,成为主导性的现代认知。主流医学依然聚焦于某一具体“邪”,并视其为病本——如冠心病核心在于斑块阻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关键是病毒肆虐,癌则是癌细胞失控……故对策就是着眼于发明种种对抗性措施:消斑块、抗病毒、抗癌等,不一而足。然而,既然是种复杂的互动,涉及双方,只抓一极,难免顾此失彼,春风吹又生,永无消停。这就是癌临床困境哲思之果。
5 癌细胞有智慧,且有一定的自愈倾向
临床事实可以开导人。20多年前,一位胰腺癌手术失败者的康复历程,犹如醍醐灌顶,令笔者醒悟其趣。自那以后,一旦条件许可,癌之诊疗即需借互动视野,兼顾双方消长,而不是一味地滥杀。由于“所有影响生命过程之因素”都可能影响癌及双方之消长;相对说来,癌又较强势,生命力更旺盛,故需着重消解可能助癌之危险因素,哪怕只是潜在的。这就是笔者20年来防治癌的一孔之见,亦即传统理论“扶正抑邪”之旨趣。笔者认为“扶正抑邪”之现代含义,需借助手段,细化,深化而令其登堂入室。
在上述意义上,癌,构成了人类真正的对手。
徐某,女,2000年1月初因确诊胰腺癌在上海中山医院剖腹探查,胰腺头见5.0cm×5.5cm灰白色硬块,包裹大血管,发硬,没法切除,只能放弃,主刀的主任医生是其亲戚,建议其中医善后,遂找到笔者。当时她伴有严重胆结石、胆囊炎,但患者不太知情。中医药治疗后,徐某于当年10月恢复上班。她在龙华寺附近工作,有人走漏风声,她知道自己是胰腺癌,无法手术,但性格乐观,大大咧咧,认为既然治疗后症状没有了,应该是好了,就快乐地活着。2003年秋,她心窝下又疼痛,一查,胆囊炎、胆结石发作。这时,查体其胰腺头部已正常,胆囊里一大把结石,她还想保守,笔者说治不了,手术才是根治性的。劝其还是找亲戚手术治疗吧。该主任最初不同意,因为不可能开两次刀。但检查后,看了CT,愿意一试。开腹后傻眼了,因为她的胰腺与两年多前见的完全不一样,已完全光洁、柔软、呈现正常暗红色,遂切了胆囊。因此事震动颇大,故中央媒体专门做了采访报道(2004年7月17日中央电视台《科技之光》)。21年过去了,患者现已退休,一切都很好,常来看笔者,无任何不适。
此事的提示是:癌是生物细胞,是在变异中发展的,既可往前走,也可往后退。诸多不利因素消解后,可退回来,甚至回到正常状态,故癌某种程度是“可逆”的。
笔者经验,当患者还处于痛苦时,进行综合治疗有点为时过早。只有症状稳定、基本危险消除了,再采取综合措施,他才可能积极配合。因为前面阶段对他来说,消除症状、获得安全感才是最重要的。
6 “我”正在对抗的癌细胞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个卵巢癌患者,余姓,2010年4月46岁时发现卵巢浆液性囊腺癌四期,有腹水,化疗、手术都做了,复发了多次,前后已化疗30余次,2018年下半年她辗转找到了笔者,因为她移居英国的亲姑姑是笔者研究生时期的同学。当时她又复发了,正在再次化疗中。她接连问了笔者两个问题“我在对抗的癌细胞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化疗究竟什么时候才是终点?”这两个问题都带有哲思性质,且有着较为普遍的意义,遂在回答她的同时,也促使笔者的深入思考及追问。
余某是个知识分子,多次复诊中逐渐接受理解笔者阐述之理。她所对抗的是“乳头状浆液性囊腺癌”,一种常见的卵巢恶性肿瘤,发现时已属晚期;虽如此,但此癌性质缠绵,并非难以控制的:早期化疗常有效,但易反复复发。按通常做法,指标高了只知化疗,那她的化疗没有终点,活着就要化疗;最终此癌都死于化疗。但换一个思路,拉长化疗间歇时间,同时努力消解可能影响癌进展之因素,包括饮食、睡眠、性格、处事方式等,釜底抽薪,自有可能走出化疗囚徒困境。余某当时指标(CA-125)500U/ml多,须化疗,但血象不支持(化疗医生不敢上);也因姑姑极力推荐,遂破釜沉舟,化疗暂搁置。她偏胖,苔腻厚,肠胃与排便一直不好,湿热很重,性格刚烈,睡眠差,虽体力尚可,却浑身不舒服。我们约法三章,两个月内不查指标,转移注意焦点,适当加些安眠药,重点全身调整,内服外敷;她腹部不适,配合外敷后症状很快消解。两个月后CA-125仍500U/ml多,继续坚持,又两个月,CA-125不升反降,350U/ml多;再两个月,CA-125仅30U/ml多,她与化疗医生都很高兴,总算半年后指标下降得比化疗还要理想。现3年多了,CA-125仅12U/ml,无特别不适。她对两个问题追问及解析,也帮自己走出了卵巢癌的囚徒困境。
“活着就要化疗”,这几乎已是妇科治卵巢浆液性囊腺癌医师的经典口头禅了。坦率地说,这类困境之走出,依赖的不仅是技术,更是智慧与正确理念。以余某的卵巢癌控制为例,15年前笔者与前辈蔡树膜教授因卵巢癌中西医结合治疗而神交频频,他就认为卵巢癌“须大中医小化疗”[4]。这是知己知彼的结晶。
面对今天癌之飙升及防控困境,笔者认为,技术可改进,方法可不断调整及提升,但缺乏智慧或理念落后,则无以走出困境,只能在泥潭中打转。
7 治癌:既需向前探究,也需不时向后“回溯”
科技是日夜更新的,需不断向前探索并更新,第三代靶药一般好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但智慧是积淀的,常源自深厚的传统文化及历史等,故需时不时地“回溯”。
人们素有医家如兵家之说,治病与打仗有相似之理。西医治疗学的指导思想与西方军事思想同源,癌治疗中鲜明体现这一点。试着疏理《众病之王·癌症传》归纳的治疗演变:从始自19世纪末的外科,到稍后的扩大根治(霍尔斯特),到20世纪60年代的超级根治;从20世纪50年代放疗,到不断强调扩大视野以求根治;及始自20世纪中叶的化疗,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多种毒药组合,厉害时甚至同时用6种~8种毒药(平克尔);患者之恐惧化疗,犹如进入“全面地狱”;直到2000年贝兹沃达承认临床数据造假,才给根治性化疗沉重一击。这里,并不是指责医生,而是认定有意识在主导并操控着他们:这就是西方的军事思想。众所周知,影响近现代西方的军事家首推克劳塞维茨(K.G.Clausewitz),他号称“西方兵圣”,认为战争目的就是消灭对手,必须借武力决战,原则是最大限度使用全部力量;尽可能集中兵力于主突方向;打击需突然、快速、坚决和彻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争不正是体现出这些吗?上述癌治疗演变,也折射出其清晰理路。
1993年美国打伊拉克,柯林·鲍威尔任三军联席会主席,曾参与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他是有哲学头脑的。回忆录里他认为越战时美军受克氏军事思想影响,美国用的是“破城锤战术”——以绝对优势兵力,快速压进,充分利用现代化武器,争取第一时间击垮对手,结果却惨败。199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他已升至美军联席会主席,遂力排众议,抛弃欧美传统战术,用另类“四两拨千斤”的中国人战略[5]。其结果,重写了国际军事思想史[6]。
反观当今主流的癌治疗,不正是上述“破城锤战术”的简单复制吗?
癌症应对中亟需智慧早已引起贤哲的重视。工程院院士、著名肝外科大师汤钊猷[7-9]耄耋之年写了三本著作:分别是《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控癌战,而非抗癌战——〈论持久战〉与癌症防控方略》,体现了资深医生多年沉思之精髓,充满了“四两拨千斤”机巧,可借鉴处甚多。
汤老[7]之《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重点谈的是肝癌,明确指出令人谈之色变之肝癌,有时需消灭(彻底抑杀),有时改造(容许存在,逐步调教)可能更好,且强调“改造机体,治本之道”。他主张肝癌“有时不治疗是最好的治疗”。并以自身为典型案例,说明“上街买菜和游泳”等,都是治肝癌的好“处方”。
2014年4月,笔者与汤院士以“中西医对话:抗癌需要中国式智慧”为题,进行对话。整个上海图书馆大会议厅座无虚席,挤得满满的。汤老[10]的主题是“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笔者则探讨癌治疗中的“‘将军思维’与‘士兵情结’”[11]。汤老说他搞了这么多年肿瘤,是到了“现代科技和中国文明精髓相结合”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破解癌防治中的困境,创造新的可能。他明确提出孙子思想至少有四点非常重要:(1)不战取胜,这对抗癌非常重要;(2)慎战,创伤性治疗需非常谨慎;(3)一旦决定了,强调速战速决;(4)争取全面胜利。不久前,他又借持久战、游击战思想,讨论癌症防控方略。强调不应该是“抗癌”,而应追求“控癌”。并借毛泽东的持久战、游击战思想,详细论述了其对今天癌症防控的指导意义,读来令人时不时有掩卷深思之旨趣。
总之,防控癌需硬科技和软思维有机结合,向前探究与向后回溯均有意义。
8 有时,不治疗是最好的治疗
《孙子兵法》中,不战而胜是兵家最高境界。这里的“不战”有两层含义:一是无需创伤性治疗(无需征伐),一般调理、改造即可;二是本质上就无需多管它。先介绍几个案例。
(1)笔者1978年治疗了一位家乡来的肺癌患者,他还患有冠心病,没人愿收治,当时肺癌并无腺鳞之分,结果用中医药活到了1989年,活了11年。这对笔者医学观影响至深[12]。这也是促使笔者萌生出惰性癌概念的最早萌芽。
(2)大连市某领导,已退休,右肾原本已萎缩(可能是先天性的),9年前左肾确诊为透明细胞癌。不敢手术,找到笔者,用中医药调整,笔者曾建议他用靶药或微创疗法,他都谢绝了,这9年多来非常好,除肿块稍微大一点儿外,无任何不适,疫情前还到处旅游,包括出国周游多次。
(3)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某领导,确诊系膀胱癌晚期,会诊多次结论一致,需膀胱全切后再化疗。他不想成为废人,希望保住膀胱。笔者治疗两年多,最近系统检查结果提示已完全正常。他现逢人就说“你们别小看了中医药”,包括积极鼓励自己医院的医生,需重新认识中医药重要的价值。
(4)上海市某老领导,7年前见尿血,一查,尿残渣有移行细胞癌,一时没法确定具体来源。当时两派意见:一派建议深入探查,进行手术;一派主张保守。他选择了后者,因为当时已80岁了,不想吃苦,不想折腾,且他女儿是死于乳腺癌化疗控制不住的。遂找到笔者,以中医药治疗,约1年血尿消退,2年后尿残渣正常。现在7年多了,一切都很好,没有什么不适。
临床40余年,笔者的最大满足是遵循《孙子兵法》之意,让数百例甲状腺癌、乳腺癌、肺磨玻璃样结节患者逃脱手术之殇,不战而胜。故“有时,不治疗是最好的治疗”。
9 观察,未尝不是积极的诊疗措施
人们现已开始重视惰性癌,笔者刚发表的研究论文,提出惰性癌的确较普遍存在[13]。惰性癌自是应强调稳着点,别大动干戈,具体可参见上文。然惰性癌与进展癌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惰性可加速度为进展;进展有所控制,也可转为惰性。临床怎么取舍决定?何时该“不战”“慎战”?何时又该全面开战?尺度如何把握?这,既是专业性很强的难题,其中也浸透着智慧;非一篇短文所能涉略。在此不想就专业问题全面展开。仅想谈谈当属性并非十分明确之时,该怎么应对之智慧。
首先,需确立这一思想——“观察,未尝不是积极的诊疗措施”。
须知,癌早治疗不见得都是正确的[13]。有时,积极观察更重要。观察不是鸵鸟政策,不是消极回避,更不是拖延,而是资深医师指导下的悉心分析,并可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努力消解症状;同时静观其变,以便采取更合理的对策。
其次,需确立几个原则,如患者并无特异性症状;非高危人群(如肺有结节但不吸烟);情绪尚稳定,并非焦躁不安(或能控制焦躁);年事相对已高,综合评估创伤性治疗得不偿失;通过说理能够坦然接受(就像余女士)等。此时,积极观察也许最正确的选择。此外,医师比较有把握加以控制的,也以积极观察为宜。
再次,明确设定观察时间、方法、目标等,如肺磨玻璃密度影连续观察,400天倍增不到1倍,按照现有的研究标准,就算稳定[13],诸如此类。
最后,举个案例:湖南娄底邹某,2013年确诊为肺黏液表皮样癌,有吸烟史,已72岁,伴心脏病、高血压、阻塞性肺气肿等,无手术机会。此癌没靶药,本人拒绝化疗,女儿陪同找到笔者。当时咳嗽厉害,遂约法三章,戒烟、注意环境湿度、避免辛辣,先调其肺,定期复诊,整8年了,一切都好。其实,当缺乏针对性措施时,积极观察,同时中医药调整,未尝不是有智慧之积极疗法。
笔者信奉“从容面对老而死,尽量避免未老先死,力戒过度、不当治疗而死”。癌,既要积极诊疗,也须避免过度及不当之治,才算是优雅而有智慧之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