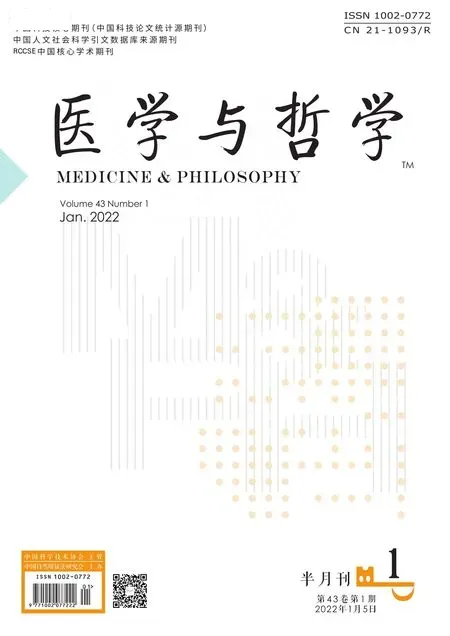ICU治疗实践的伦理问题辨析
郑洪君 李 涛
重症医学是现代医学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伴随着科学技术水平和相关制度的不断进步与完善,产生了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逐渐发展为重症医学科以及现在的重症医学专业临床基地。ICU作为一个独立的医疗单元,已然成为了医院现代化建设和规模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在ICU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和争议。随着近年来各种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重症医学专业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不再是只针对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场所。越来越多的患者家属期望可以给予患者更好、更加全面的监护和治疗,最大程度地延长患者生命,但这对于本就紧张的ICU医疗资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让一线的ICU医疗工作者面临很大的伦理风险。ICU治疗的伦理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已经成为ICU治疗规范化和良性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就当前一线ICU医生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主要面临的伦理问题,从实际接触的典型案例出发,对以下几方面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
1 患者收治过程中面临的伦理问题
ICU相较于其他科室而言存在其特殊性,主要以综合性重症患者救治为重点,独立设置,面向全院开放,加之设备、人员的配备要求,床位较其他科室而言相对紧张,因此,根据原卫生部办公厅印发的《重症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版)》通知完善的《重症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2020版)》,结合各地区、各医院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收治标准,主要收治以下患者:(1)急性、可逆、已经危及生命的器官或者系统功能衰竭,经过严密监护和加强治疗短期内可能得到恢复的患者;(2)存在各种高危因素,具有潜在生命危险,经过严密的监护和有效治疗可能减少死亡风险的患者;(3)在慢性器官或者系统功能不全的基础上,出现急性加重且危及生命,经过严密监护和治疗可能恢复到原来或者接近原来状态的患者;(4)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症患者;(5)其他适合在重症医学科进行监护和诊疗的患者。对于慢性消耗性疾病、不可逆性疾病和不能从加强监护治疗中获得益处的患者,一般不是重症医学科的收治范围[1]。但是,ICU医师在实际的工作中,很难完全按照上述标准收治患者,主要原因通过以下两个案例进行阐述。
1.1 病情可逆的危重症患者
案例1:患者,男,49岁,农民,因恶心呕吐4天,言语不清1天至急诊就诊。患者神志清楚,言语含糊,消瘦,脱水貌,急诊诊断:休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离子紊乱(高钾血症、低钠血症)。由于患者病情危重,面临猝死风险,急诊医生建议患者入住ICU治疗,并请ICU医师会诊。经ICU医师与患者本人及家属沟通后发现,患者本人对进入ICU治疗表现十分抗拒,并向医生询问自己是否已进入病情终末期,无法治疗,即将面临死亡。家属情绪激动,并表示患者发病前身体状态良好,已经多年未曾就医,对病情突然加重至此无法理解。当得知入住ICU每日治疗费用后,抵触情绪更加明显,并表示家庭经济条件差,无法承受医疗费用,拒绝进入ICU治疗,要求入住专科病区。反复向患者及家属说明患者病情、拒绝ICU治疗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ICU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后,患者及家属仍坚持原决定不变,并签署相关告知书,收入内分泌病区。于次日凌晨,患者昏迷,继而呼吸心跳骤停,经心肺复苏抢救无效,临床死亡。
案例1中,患者的诊断明确,经过及时有效的治疗后完全可以逆转病情,属于病情可逆的重症患者。此类患者符合ICU入住标准,并且很大概率会从ICU的监护治疗中获益。但患者本人或其家属,对疾病本身认识不足和对病程发展结局的茫然,以及大多数非专业人士对ICU的错误认知和误导,认为进入ICU就是生命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出于对死亡和未知的恐惧,部分危重患者更希望的是家人的关怀和陪伴,更希望得到提高生命质量、减轻自身痛苦的治疗。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疾病为家人造成经济和心理上的负担,对于自身疾病的救治往往处于一种极其消极的状态,而拒绝、放弃了ICU治疗,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也是ICU医生在急诊及其他科室会诊接收患者的过程中时常会面临的问题。
那么,作为ICU医生面临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针对病情可逆的重症患者,医学伦理中提出的有利原则要求医生尽最大的可能来拯救和延续生命。作为ICU医生也有义务向患者及其家属详细说明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ICU存在的意义和进入ICU治疗的必要性和存在问题,充分了解自身状况,消除误解。但是患者作为一个意识主体,有自主选择是否接受的权利。虽然放弃治疗不能得到道德上的支持,但如果患者或其家属可以明确理解继续治疗的意义和目的、拒绝或放弃治疗可能带来的各种结局,并且可以接受,作为医生就应该遵守自主性原则,满足他们的心理诉求,尊重患者及其家属的决定,这是作为医生同情心最好的表现。与此同时,尽可能地在ICU外给予患者最大限度的治疗,挽救患者生命,恢复患者健康,提高生命质量,维护患者生命尊严,尽最大努力减少悲剧的发生。
1.2 病情不可逆的危重症患者
案例2:患者,男,95岁,离退休人员,脑梗死后遗症,气管切开,长期住院卧床,无自主活动能力,自主睁眼,对外界刺激有反应。反复并发肺部感染、尿路感染,持续低热,体温波动在37.5℃~38.0℃,长期抗生素治疗。此次住院期间经胃管内引出褐色胃内容物,约200ml,消化道出血,体温最高达39.0℃,呼吸急促,痰液量明显增加,色黄绿且粘稠,血压明显下降,尿量减少,完善各项检查后评估,感染情况加重,心肺功能、肾功能均呈衰竭表现。主管医师向患者家属说明患者病情危重,多脏器功能衰竭,已至病程终末期,或将面临死亡,家属得知后表示要尽一切可能延长患者生命,于是主管医师请ICU医师会诊。ICU医师查看患者后与家属沟通,表示患者高龄,各脏器储备功能消耗殆尽,已经不可逆转,ICU与普通病房治疗并无特殊差异,且无法探视,单纯延长患者生命会增加患者痛苦,最后面临人财两空的结局,建议继续维持目前治疗方案。患者的多位子女经商议后决定继续目前治疗方案,并租用家庭用呼吸机维持患者呼吸,于半个月后,患者因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
伴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如案例2中高龄患者的比例逐年增加,各种生命支持技术和设备被不断引进。一部分患者就算经过ICU内积极治疗后,疾病的进程仍无法逆转,结局往往就是死亡。通过这些生命支持设备能做到的只是单纯延续生命,对于生命终末期或者临终期的患者来说,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丧失人格尊严,也让家属共同承受着生理和心理上的煎熬。面临这种情况,作为ICU医生,是应该运用一切手段延长患者生命?还是应该劝导和帮助患者家属理性地面对即将到来的结局?这是每一个ICU医生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依据社会医疗资源分配的效用原则,ICU作为稀缺医疗资源,在社会层面上要求医院把维护重症患者的最佳利益放在首位,合理利用ICU资源,病情可逆患者接受ICU治疗增加的健康价值明显高于生命终末期或临终患者,会优先考虑把ICU治疗的机会分配给治愈成功可能性高的患者,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但是,医院如若以效用性原则作为导向而收治患者,就会造成道德上的滑坡[2]。
疾病发展不可逆的重症患者,部分患者家属出于道德压力、家庭压力和社会压力等多方面因素,要求尽量去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哪怕只是依赖于各种医疗设备,形成生物学上生命的延续,要求入住ICU,但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
对于病情不可逆的重症患者来说,虽然尊重患者生存权利是医疗专业人员的责任和义务,是绝对的命令和法则,各种医疗设备的支持可以延长此类患者的生命,使得患者生命能得以暂时的延续,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但是病程发展的终点已经不可改变,死亡已经成为必然的结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患者施加各种额外的治疗手段和设备,患者身体负担日益加重,没有家人的陪伴,毫无生命质量可言,给患者及其家属造成巨大的身心痛苦和经济负担。就患者自身而言,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舒适、关怀和尊严。因此,针对病情发展不可逆的重症患者,应该在ICU下设置次一级治疗单元,有家属的陪伴,以维持生命、减轻痛苦和基础疾病的延续性治疗为主,不再进行ICU内的特殊手段支持,让患者的生命尊严得到保障,并且让家属形成心理缓冲,缓解道德压力,进行心理疏导,理智对待,逐渐坦然接受即将到来的结局,同时也避免了ICU医疗资源的浪费。
2 患者在ICU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伦理问题
ICU作为一个独立的医疗单元,患者进入ICU后恍如与世隔绝,初次进入陌生的环境,远离家人,难免会产生诸多负面情绪。家属在ICU门外不能直接接触患者的治疗过程也会担惊受怕,不可避免地焦虑、担忧。由此,患者在ICU住院期间就会产生诸多治疗之外的问题。
2.1 ICU综合征、ICU后综合征的产生
案例3:患者,男,36岁,教师,因腹胀、腹痛伴恶心呕吐10小时入院。患者发病前曾饮酒并进食大量油腻食物,急诊诊断急性胰腺炎收入普外科病区,予以保守治疗。入院1天后,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少尿、血压下降症状,腹胀、腹痛未见缓解,普外科医师考虑患者出现感染性休克、多脏器功能损害,病情危重,于是联系ICU,经ICU医师会诊,家属及患者本人同意后转入ICU治疗。
患者入ICU后呼吸困难症状进行性加重,血气分析示I型呼吸衰竭表现,无尿,复查肾功肌酐呈进行性升高,诊断为脓毒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给予经口气管插管、机械辅助通气、连续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联合血液灌流、腹腔灌洗治疗。治疗6天后,患者呼吸衰竭症状缓解,予以拔除气管插管。拔管后第3天,即患者入住ICU第9天,患者出现睡眠倒错症状,白天嗜睡,夜间清醒,情绪不稳定,并大喊大叫,辱骂医护人员,具有攻击性,不配合治疗,家属规劝效果不佳,并辱骂其家属。结合患者各项化验指标,考虑不除外并发胰性脑病(pancreatic encephalopathy,PE)可能,予以针对性治疗后,症状未见缓解,患者情绪愈发不稳定,愈发不配合治疗。综合考虑,患者可能出现了ICU综合征(intensive care syndrome,ICS)的表现,结合患者各项化验指标及生命体征,目前患者原发病趋于好转,与家属商议后决定将患者转回原病区继续治疗,家属陪伴行心理疏导,观察患者情况,若病情反复,随时再行转入ICU。于是患者在ICU第15天后转出ICU,于普外科病区继续治疗。
患者转出ICU一周后,再行探视,患者情绪稳定,睡眠倒错改善,恢复良好。患者自述,在ICU治疗期间,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受,特别是插管的时候,被绑在床上不能自由活动,全身上下各种不适,无法形容也不能缓解。身边没有亲人陪伴,晚上睡不好,经常被各种噪音吵醒,尤其是有患者进行抢救,总感觉自己将会和他们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再也醒不过来,因为害怕,也不敢睡觉。时间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心里越发地烦躁,就想不治了,反正家里人也不管我了,不如死了,一了百了,这种心思一发不可收拾,心里闷得厉害,只想发泄。家属也表示,患者刚从ICU出来的几天,情绪很不稳定,经常不配合治疗,不吃饭、拔针等情况时有发生,时常表示不治了,ICU都去了也治不好,对后续治疗没有信心。回原病区治疗几天后,经过家属的沟通,随着病情逐渐改善,情绪上慢慢也就缓和了。但是,患者对ICU仍存在明显抵触情绪,明确表示之后无论如何也不再进入ICU治疗。
案例3中的情况在ICU日常工作中并不少见,特别是对于清醒的患者更为常见。 ICS是指ICU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以精神障碍为主的、并伴有其他临床表现的一组临床综合征[3]。ICU后综合征(post-intensive care syndrome,PICS)是患者离开ICU后远期存活的生活中,广泛存在的躯体、认知和心理功能障碍的统称[4]。这两种综合征的发生均与患者在ICU中的治疗经历密切相关,严重影响着患者的预后。究其原因,既有疾病本身对于患者的折磨,更多的则是ICU特殊的环境和治疗过程中对患者身心造成的痛苦体验。
ICU患者病情复杂,疾病加身让患者本就痛苦不堪,为了挽救患者生命,各种医疗和护理的操作、遍布周身的导管,更让患者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疼痛和不适感。为了避免不良事件的发生,常常需要对患者进行保护性约束,极大地限制患者的肢体活动。以上措施,对于ICU患者,特别是意识清醒的患者心理上会产生无助、惊恐、愤怒等情绪,气管插管、镇静、身体约束的情况下,自主意愿的表达可能会被误解、忽略或者拒绝,精神上处于一种敏感、脆弱、恐慌的高度应激状态。同时,ICU多采取全封闭或半封闭的管理,谢绝家属陪护或者探视;昼夜不熄的灯光让患者失去了时间的概念;身体的不适、频繁的翻身打乱了患者正常的生理节律;其他患者的抢救、离世场景,各种仪器设备突然响起的刺耳警报声,种种情况,使患者孤独、无助、恐惧的情绪放大,甚至感到震惊、绝望。这时可能医护人员下意识的一个行为,就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患者本就脆弱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彻底崩溃,继而发生谵妄、焦虑、抑郁、自我伤害等情况。在转出ICU后,这种情况仍会存在,甚至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表现,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且抑郁和PTSD会增加患者死亡的风险,影响之后的康复进程,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负担[5]。
那么,应该如何尽量减少或者避免ICS及PICS的发生?目前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完善科室的建设和管理制度,推广人文关怀的理念,从法律、伦理、人性化三个层面上给予患者全方位的人文关怀,大力提倡全人医疗和整体医疗[6]。关心病,更要关心患者,认真实践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全面、深入地实现整体治疗、身心统一的治疗观念。(2)在技术层面上,应该严格评估各种治疗的应用指征,为患者提供适宜和最佳的诊疗方案,杜绝高新技术的滥用,力求避免过度诊疗情况的发生。发展微创技术,尽量减少有创操作。主张对进入ICU的重症患者给予以镇痛为主的镇静治疗,在无深镇静指征的前提下,采用早期充分镇痛,使用最小化镇静药物的剂量。让患者可以自主表达主观感受,同时辅以最大化的人文关怀,使ICU患者达到最优化的舒适度。合理的镇痛、镇静策略可以很大程度减轻患者的不适感,淡忘ICU经历,达到顺行性遗忘的效果,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肢体约束,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4]。(3)优化ICU环境,减少声光干扰,完善远程探视功能,方便清醒的患者与家属沟通。尽量让清醒的患者远离需要频繁抢救或临终的患者,避免其受到不利影响。(4)早期活动和康复治疗。虽然ICU患者病情和医疗环境比较特殊,对于ICU内患者早期康复治疗存在着许多困难和争议,但多项研究均表明,ICU患者早期活动康复治疗的安全性是可以得到保障的[7-8],并且2012年美国重症护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ritical-care Nurses,AACN)基于循证医学基础提出了ABCDE镇痛镇静集束化措施(ABCDE Bundle)[9],规范了ICU早期活动的实施。近年来,对于病情好转的重症患者,更是提倡家庭成员的早期介入,帮助参与ICU的日常护理工作。尽管目前ICU床旁早期活动在国内尚未普遍开展,但是早期活动的顺利实施,有助于患者迅速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帮助达到良好的预后效果。
2.2 沟通的桥梁
案例4:患者,女,55岁,农民,突发昏迷3小时入院,既往高血压病史,急诊颅脑CT示右侧基底节出血破入脑室,出血量约90ml,神经外科收治入院后急诊手术治疗,术后转入ICU,给予机械辅助通气、脑出血术后各项对症支持治疗及护理措施。于入ICU第5天,患者可见自主睁眼,对疼痛刺激有反应,无意识内容,自主呼吸良好,但咳嗽反射弱,基本无自主气道廓清能力,整体生命体征平稳,病情向恢复方向发展,呼吸机参数逐渐下调,有脱机希望。
于是综合患者病情,ICU医师与患者家属沟通,介于目前患者情况,建议行气管切开术,以方便后期气道护理,并可行自主呼吸功能锻炼,帮助早日脱离呼吸机,转出ICU。但与患者家属沟通过程中发现,患者娘家人态度积极,同意医生建议,要积极救治,但并不帮助患者支付任何医疗费用。患者丈夫态度不明朗,表示孩子还在上大学,家里经济条件差,自己一人无法负担后续的医疗费用,无法照护,如继续在医院治疗,自己及孩子生活都成问题,要求患者娘家帮助支付后续医疗费用,否则出院回到当地医院继续维持治疗。患者儿子并未发表意见。因此,双方发生争执,后续几日未缴纳住院费用,几次催缴未果。经过多次与双方沟通后,ICU医师表示,目前患者病情整体呈好转趋势,经后期康复治疗后未必不能恢复部分自理能力,若中断治疗可能前功尽弃,最后落下人财两空的结局,更加得不偿失,而且经过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结算后未必如想象中花费那么多,先将所欠医疗费用补缴,而后医院帮助办理一次结算,先报销部分费用应急,继续维持患者正常治疗,后续再行商议,家属同意。最终双方商议后决定,同意气管切开,待患者脱离呼吸机后,转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治疗费用由娘家人支付,其丈夫、儿子负责照护。患者出院后一月随访,患者意识恢复,尚无自理能力,可坐轮椅推行。
再次与患者儿子的沟通过程中,患者儿子表示,当时在ICU住院期间也很无奈,一方面是自己的母亲,不能说因为自己或某个人的原因而不治了,一方面是自己的父亲,不是说父母感情不好,但家里经济条件确实困难,也不能过度反驳,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所幸过程虽有波折,但结局还算好,至少人醒过来了,再之后尽力而为。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对于在ICU治疗的患者,医生和患者并不是仅有的参与者,患者的家庭和整个社会也是其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基于孝道的传统理念,中国的医患关系模式大多是以整个家庭为基础。特别是对于失去行为能力的患者,如深度昏迷的患者,无法对接下来的治疗进行自主决策,当其家属需要代表患者做出医疗决定时,难免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在传统道德观念里,个人利益往往要服从家庭的整体利益。患者家属代表患者做出医疗决定时,除了要考虑患者利益的同时,还要满足家庭的整体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这是最为现实的问题。伴随着我国医保制度的完善,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仍未能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特别是ICU住院期间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对于多数工薪阶层家庭和非正式就业人员而言仍然是不小的花费,可能面临着患者在ICU住院治疗的同时,家庭负担着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甚至严重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出于传统观念、社会压力、道德压力和理智,从而出现许多与患者治疗不相关的矛盾,转嫁到家庭成员、ICU一线医护人员、医院和社会之上,对患者接下来的治疗以及医患关系的和谐产生诸多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ICU医护人员与患者家属的沟通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在政策的层面上,作为一线医护人员应该了解当前的医保政策、各种药物和治疗措施的报销比例、是否是自费项目、治疗药物和手段使用的必要性及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向患者家属就每日的住院治疗费用做一个详尽的说明,在住院期间制定合理、完善的治疗方案,保障接下来的治疗和随时的调整做到及时、有效的沟通,让患者家属体会到一线医护人员对患者的负责态度。其次,在心理层面上,在与患者家属沟通的过程中,使用非医疗专业人员可以理解的语言,用尽可能简练的方式让家属理解患者当前的状态、疾病发展的进程,以及接下来可能面临的诸多问题,也为之后可能需要的决策做好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建立科学的心理预期。用平等的态度去沟通、交流,减少潜在的矛盾与纠纷。最后,在人文关怀层面上,ICU医护人员要做好患者与家属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可以向患者表达家属的关爱,医护人员对其的关心,减少患者的孤独感、恐惧感和被遗弃感;另一方面让患者家属也能体会到医护人员的同情,缓解其在ICU外担心和焦虑的情绪,为患者接下来的治疗共同努力。
3 治疗终末期面临的伦理问题
患者来到ICU的目的是为了抢救生命,争取生存的希望。但并不是每一个进入ICU的患者都会得到满意的结局。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在治疗走向终点,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如何能让患者尽量安详地离去,如何能让家属坦然地面对患者死亡,是每个ICU医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3.1 缓和医疗的实施
案例5:患者,男,76岁,离退休人员,车祸后致颅脑及全身多脏器损伤,入院后急诊手术治疗,术中失血约1 800ml,术后转入ICU。由于患者车祸致颅脑损伤伤及脑干,并且失血性休克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严重,经ICU内积极抢救治疗后生命体征尚可,但治疗20天后,患者仍处于深昏迷状态,无自主呼吸,呼吸靠呼吸机支持,产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各项生命体征靠药物调节,并且出现了肝肾功能不同程度的衰竭表现,间断行CRRT治疗,以保障脏器功能可维系。换言之,患者处于靠药物与生命支持手段维系生命的情况,一旦撤离机器、感染加重或某一脏器功能衰竭恶化,机体平衡打破,患者就将面临死亡。
ICU医师综合考虑患者病情,并详细向患者家属说明情况,由于患者高龄,此次车祸创伤严重,经过多日积极抢救治疗后,目前只能依靠生命支持手段维持基本生命体征,且颅脑损伤已经不可逆转,各脏器均呈现衰竭趋势,预后极差,建议家属放弃治疗。患者多位子女商议后向医生表示,可以理解医生的建议,也明白继续治疗下去不能挽回患者生命,但是现在患者毕竟还活着,可以继续延续生命,作为儿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去世,情感上无法接受,仍然希望全力救治。ICU医师综合考虑患者家属意见后,再次建议,既然家属了解患者目前情况已经不可逆转,处于临终状态,那么就继续目前生命维持治疗不变,但若发生其他情况,如肝肾功能衰竭、心跳骤停等情况,不再行CRRT、心肺复苏等措施,以药物治疗为主,一方面为减轻患者痛苦,另一方面也让家属们有一个心理安慰和接受的过程。家属商议后同意医生建议,最终患者在维持治疗一周后去世。
上述案例中,患者颅脑损伤已不可逆,且多脏器功能衰竭,尽管对患者采取了各种治疗手段干涉,最后仍然无法避免死亡,ICU医师应及时作出无效医疗的判断,即医务人员依靠现有的医疗技术或条件对患者疾病的预后、恢复所采用的没有促进作用的治疗措施或行为[10],使医疗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减轻家属经济负担。
在ICU,医生首要目的应当竭尽全力挽救患者生命,当患者病情不可逆转,逐步恶化至临终状态时,应当如实与患者家属沟通,并建议其接受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缓和医疗也称舒缓医疗,既往还称姑息治疗,涵盖支持治疗和临终关怀。2019年,国际安宁缓和医疗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spital and Palliative Care,IAHPC)给出了一个新的定义:“缓和医疗是针对全年龄段遭受严重健康相关痛苦个体的主动的全人照护,这些痛苦常由严重疾病引发,尤其是当患者临近生命终点时。缓和医疗的目的是提升患者、家属及其照护者(care giver,包括医护人员、护工和家政人员)的生命质量。”并且有研究者总结了缓和医疗的数条原则如下:(1)缓和医疗重视生命,并将死亡视为正常的过程;(2)缓和医疗既不有意加速也不过度延缓死亡;(3)提供解除疼痛和其他痛苦症状的干预;(4)为家属提供丧亲辅导;(5)可与以治愈为目标的治疗并行;(6)尊重患者的偏好和价值,满足患者和家属的合理需求[11]。
医学的目的是为受伤的躯体减轻痛苦,以仁为本,以术为用。对于生命终末期或者临终期患者,作为重症医学科医生,建议患者家属放弃ICU治疗,接受缓和医疗是合理的,缓和医疗的原则也是符合伦理学原则的。放弃治疗并不等同于放弃患者,放弃的是给患者造成痛苦的过度治疗,取而代之的是医护和家属对患者的关心和生命尊严的维护,对残余不多生命质量的追求。帮助患者疏导面临死亡的恐惧,帮助家属坦然地接受死亡,更是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3.2 器官捐献过程的参与
近年来,我国器官获取组织相继成立,国内器官移植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ICU作为器官捐献潜在者信息的主要来源地,ICU一线医护人员必然会参与到患者从急危重症患者到潜在捐献者及器官捐献者的转变,再到死亡判断、实现捐献及临终照护的全部过程,也必将面临复杂的伦理问题。因此,作为本身并不从事移植工作的ICU医护人员来说,理解并掌握器官捐献相关的临床和伦理原则就显得很必要[12]。其中主要的原则有以下几点:(1)只有供者死亡后,才能获取器官。在我国“脑死亡”尚未明确立法的前提下,只要心脏保持搏动,供者就可视为一直存活。(2)不能为了受者手术质量而伤害供者利益。也就是在供者死亡前不允许对其做任何与移植相关的医疗干预,更不能为了促成供者死亡而进行任何不利于患者本身病情的医疗干预。在其心脏停搏前,必须遵守供者利益至上的原则。(3)在切取器官前,必须告知家属并征得其同意。必须严格遵守避免与家属探讨器官的捐献,甚至诱导家属进行器官捐献的原则[13]。
4 结语
ICU作为“医院的第一道防线”,为到来的急危重症患者争取进一步治疗的希望,作为“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所守护的是患者最后的生命尊严。ICU医生所做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在治病,更是在救人,所拯救的不单单是患者,也包括他们的亲属。关注ICU医护工作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不仅能让患者身心得到救治,同时也能安抚患者亲属的心灵。即便最后患者不可避免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活着的人在心中缅怀的也是逝者临终前的安详,而不是对死亡痛苦的抵抗。尊重生命,敬畏死亡,为生者带来希望,守护逝者最后的尊严,是每一个ICU医护人员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