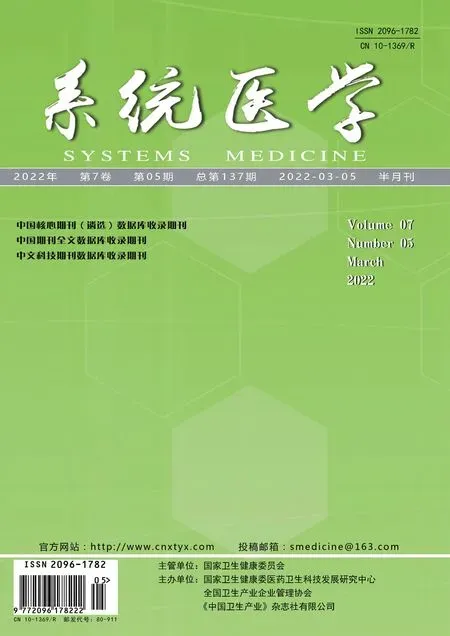ICD-11的修订对综合医院诊断躯体化及相关障碍的影响
张思睿,郭毅
1.暨南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广东深圳 518020;2.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广东深圳 518020
躯体症状不适广泛存在于各种精神障碍疾病之中,是其重要的临床表现,如躯体症状障碍、抑郁症、焦虑症、神经衰弱等[1]。躯体化症状在综合医院中相当普遍,这类患者长期被躯体症状所困扰,如睡眠障碍、躯体疼痛、头晕、乏力、感觉异常及呼吸、消化、心血管、泌尿系统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但通过完善检查也没检出器质性病变[2]。还有部分患者虽明确诊断有躯体疾病,但躯体不适的痛苦程度超过躯体疾病发展的限度。这些患者常就诊于综合医院各专科科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诊治,最后病情迁延,这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还损害了患者个人社会功能,甚至加剧了医患关系恶化[3-4]。
1 躯体症状及相关障碍的诊治现状
最新数据表明,精神疾病和成瘾性疾病影响了全球超过10亿人。按DALYs的数据,它们造成了全球疾病负担的7%,并且有19%的残疾人生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质量[5]。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快速的社会变化可能会导致心理压力和压力的普遍增加,我国人民面临着情绪、认知和行为障碍及相关问题的挑战。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精神障碍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普遍。根据ICD和DSM标准,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达16.6%[6]。可见精神疾病可严重损害人们的生活、社会功能,影响社会的发展。
据数据统计,面对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问题,有44%的受访者愿意在综合医院看精神专科,约24%的人愿意在综合医院看内科医生,而只有17%的受访者会在精神病医院就诊。47%的受访者会说服患有神经疾病的人去看心理医生[7-8]。综合各方资料,该现象有以下原因:①精神障碍以躯体症状(躯体化)为主或是首发症状;②躯体疾病与精神障碍共病;③躯体疾病导致自身状况改变,患者难以接受从而引发的应激反应;④躯体疾病继发精神障碍,如卒中后抑郁、帕金森病合并抑郁、甲状腺功能异常继发的焦虑或抑郁症状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报告结果显示,精神障碍疾病的发生率在持续增长,是世界上负担最重的疾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政策、规划和服务中心放在精神卫生保健的非机构化、精神卫生纳入一般卫生保健及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发展[9]。中国对精神障碍的认识不断提高,与世界保持一致,在过去的20年中,对包括神经系统疾病在内的精神疾病的意识有所提高。中国精神卫生法对综合医院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加强对精神障碍的诊治。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综合医院对精神障碍的识别度远不如精神专科医院,WHO曾发起一项涉及15个地区的多中心研究,其结果显示我国(上海地区)综合医院内科对心理障碍的平均识别率仅为15.9%,识别率列倒数第2位[10]。诊断率低很有可能与的诊断标准的不恰当相关。
越来越多的调查数据证明,精神障碍疾病患者躯体症状表现突出[1],许多患者因疼痛、头晕、乏力、睡眠障碍、食欲欠佳、心慌胸闷、呼吸困难等躯体不适就诊于各级综合医院,90.22%被诊断为神经症的患者到过各级综合医院非精神科诊治,做过多种特殊检查[11-12]。而这些患者的检查结果往往是阴性的,可见,精神障碍疾病常伴随着明显的躯体症状,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与精神障碍的数量呈线性关系[13-14]。精神障碍疾病中共病现象并不少见,可能会出现被诊断患有一种精神障碍的个体满足至少一种其他疾病的标准的情况,并且许多个体可以满足3种或更多种疾病的诊断标准,有两种疾病的共病率可达20%以上[15-17]。有9.3%的患者同时被诊断为应激障碍、躯体形式障碍、焦虑症及抑郁症[14]。当前许多研究报告一致发现,抑郁症、焦虑症与躯体形式障碍之间合并症出现率高[18],在精神病专科医院中,抑郁症、焦虑症是诊断最多的精神障碍;而在综合医院中,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常合并抑郁及焦虑[19-20],至少占有其中的1/3[15,21],躯体症状是促使患者就诊于综合医院的重要原因,与大量精神障碍的患者就诊于综合医院的现象是相符合的。除此之外,曾有学者做了一项研究,在1 700例器质性疾病的患者中,有12.7%的患者合并有重症焦虑症,其中有25%患有至少一种合并症(尤其焦虑症),而且更多地表现为身心症状如躯体化、易激惹等[22]。中国一项多中心、大样本、横断面研究调查8 487例综合医院门诊患者,MINI诊断的抑郁障碍、焦虑障碍、抑郁和焦虑共病的校正患病率分别为12.0%、8.6%和4.1%,其中任一诊断的患病率为16.5%,而以神经科的患病率最高。无论精神障碍疾病是以躯体症状为主还是精神障碍为主,不同疾病本可以相互影响,相互继发,如不及时诊治甚至会彼此恶化,如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并发焦虑、抑郁、恐怖,致使躯体症状更加明显,增加患者的易损性。综合医院常忽视器质性疾病患者的心理状况,而仅仅着眼于治疗器质性疾病,患者由于得不到充分的诊治,导致精神疾病的症状与器质性疾病的症状互相叠加,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在综合医院中,当患者躯体的不适时,除了关注器质性疾病之外,也要警惕患者是否疾患精神疾病,才能完成更好的诊治[18]。正确的评估手段成为了其中的关键。
2019年,ICD-11已正式发布,旨在成为减轻精神疾病疾病负担的更好的工具,新系统将需要在全世界有精神健康需求的人最有可能接触护理机会的地方变得有用和可用。因此,世卫组织在制订修订版时特别关注临床效用和全球适用性问题,ICD-11对综合医院常见的躯体症状及相关障碍进行了修订,以提高疾病分类的临床实用性。下面就对该修正进行一个相关解读。
2 ICD-11中躯体症状及相关障碍修正解读
在ICD-11中,躯体形式障碍将更改为躯体不适障碍,其定义为:明显的躯体症状为主要特征,该症状引发了患者的过度关注,从而反复就诊。或是对原本疾病的关注超过了疾病的本身及发展。过度关注的心理特征无法被适宜的临床检查手段或医生诊断确认所消除。明显的躯体症状及过度关注持续存在数月以上,对患者的社会功能造成严重损害。躯体症状表现为多元性、波动性。与DSM-V相比,这两套国际通用的诊断系统在躯体症状及相关障碍的章节归属方面虽然存在差异,但在对躯体障碍(躯体症状障碍/躯体不适障碍)的诊断定义上基本保持一致,且对于该类疾病诊断定义基本相同[23]。在ICD-10中,躯体形式障碍在精神病学中饱受争议与挑战,其中它对躯体形式障碍的诊断受到质疑[24],其受质疑之处如下:①躯体形式障碍的诊断基础为无法找到躯体病因,而不是有明确的社会心理及行为学特征的改变,这一点在临床诊断上有着巨大的影响。从诊断证据来看,躯体症状是否真的属于“医学上难以解释”,这一判断有着许多的变数,且缺乏效度。这种内在的二元论未免太过简单,让误诊、漏诊的可能性增大,对于临床诊断并无益处。②躯体化障碍的患病率与临床实践中这一诊断所使用的频率在很多地区或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可能的原因是,这些诊断分类标准容易受医生诊断习惯的影响,如医师倾向于诊断“抑郁/焦虑状态”,而非“躯体形式障碍”,这也提示躯体形式障碍的定义可能不够准确,才出现在不同地区患病率存在差异。③就定义而言,DSM-Ⅳ及ICD-10中,躯体形式障碍内部的分类并不十分合理;躯体化障碍与未分化躯体形式障碍的诊断阈值相差甚远,致绝大部分躯体形式障碍被诊断为未分化躯体形式障碍。使用不同诊断分类标准对患者做出诊断时,躯体化障碍患病率的差异可达20~150倍,由此看来,诊断标准有架空于临床的可能性,忽视医生和患者的理解。④由于躯体形式障碍与抑郁焦虑障碍均可有显著的躯体症状,它们之间的诊断界线存在交叉重叠,导致临床医师难以对它们的界限有着清晰的了解,这会导致诊断的混乱,从而产生不适合的诊断。⑤患者对躯体形式障碍这个诊断的接受度亦值得被关注,在患者试图去理解症状再归因时,患者难以接受“医学难以解释”或“身心性”之类的解释,从而对诊断产生质疑和抵触,对该诊断未予应有度重视,延误诊治。因此,ICD-11为提高临床适用性,将躯体不适障碍选为了新的诊断名称“躯体不适障碍”(bodily distress disorder,BDD),并大大简化了其下的诊断分类。躯体不适障碍较之前的躯体形式障碍相比,拥有以下优点:①躯体不适的定义削弱了精神、身体的不够准确的二元论,适用于那些存在或不存在确切器质性疾病的患者,也因此更可能同时被患者及医务工作者所重视和接受,更具有临床适用性;②该名字更为形象,即躯体的痛苦、不适给患者带来的一系列心理及行为变化,或未被患者所察觉的心理变化引起躯体的不适应,从而影响了日常社会功能,这个概念可引起多个学科的关注,从而推动多学科合作,例如综合医院中躯体疾病科及心理科的合作诊治;③该名字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具有相似的理解,中性描述,使得该分类诊断在不同地区、国家或不同的临床情景中避免过多的差异性[25]。当然,这些潜在的优势都需要进一步的临床实践及研究来证实。
3 小结
在我国,不少精神障碍的患者倾向于选择综合医院就诊,除了大多数患者以躯体症状为主要表现加之其对精神疾病知识缺乏了解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污名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人对于精神疾病都处于回避状态,以避免来自家人朋友及社会的压力和歧视[26]。公众的偏见和对精神疾病的社会污名带来的病耻感延误了早期治疗,并延迟了心理健康服务的最优利用。综合医院作为多数患者求助的第一线,应具备精神障碍疾病一定的识别力,才能真正帮助患者。作为非精神科医生,要对精神疾病有一定的识别力,除了主动了解精神疾病之外,还需要依靠临床使用度高的诊断分类标准。ICD-11的发布极大影响了精神障碍这种极度依靠诊断分类标准而尚缺乏客观指标的疾病诊断的分类及对精神障碍的重新理解。但这种诊断分类亦有学者认为是不必要的[27-28]。Allsopp K等[29]对DSM-5中的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抑郁症、焦虑障碍及创伤和压力相关的疾病进行了主题分析,发现:①精神疾病的诊断依赖于多个诊断分类系统的标准;②不同的诊断名称下,所包含的症状却多有重叠;③诊断忽视了负性事件的作用;④诊断名称无法一目了然地提示患者的情况与需求。诊断类别之间更广泛的考察了不同类别之间的症状重叠及创伤的作用。实用的标准和诊断困难在多个诊断类别中反复出现,这对病因的概念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基于疾病的特殊性,实用的精神病学评估方法是允许个体经验性识别的,了解患者的困惑与痛苦比单纯的参照疾病分类系统的诊断标准更为有效[28-29]。例如就诊于综合医院以躯体症状为主的精神疾病患者,主观感受在于躯体症状,从前习惯于诊断为神经衰弱,接着由于DSM-Ⅲ的修订又倾向于诊断为抑郁症的躯体症状,而后又因诊断分类的修订可诊断为躯体形式障碍,至今ICD-11的发布也许诊断为躯体不适障碍更为合适。在我国,因其特殊的社会文化因素,神经衰弱更容易被广大患者接受,降低其不应有的病耻感,提高患者的诊治质量及预后[30-31]。
综上所述,目前的精神障碍分类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演变,依然是建立在主观评价的“正常”与“异常”基础之上。因此,需要更客观、更实用的精神病学评估方法。ICD-11的发布虽然没有达到这种美好的愿望,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精神障碍分类史上的一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