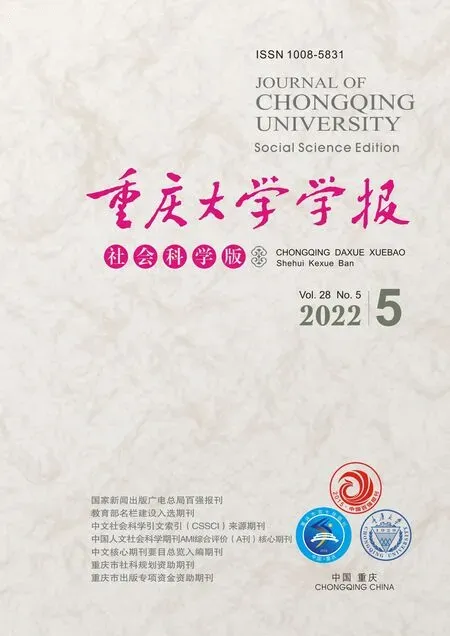讽喻与昭雪:《步辇图》李德裕题跋考论
摘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步辇图》手卷,是记录初唐贞观年间禄东赞入朝为松赞干布请婚事件的一件美术作品。该图卷旧传为阎立本手笔,后流传至晚唐,大和年间李德裕重予裱褙,并题跋于画心左侧。既往的研究,多集中在画作为唐真迹还是宋摹本、作者为谁、所呈现的具体历史场景为何以及递藏等方面,李德裕重装褙并题跋的动机、功能及影响,则鲜有学者论及。文章从跋文的格式、《册府元龟》的录文两个方面,为原跋文出于李德裕之手提供了新的佐证;通过对重装褙背景及跋文的分析,发现此事隐射了晚唐与吐蕃关系的一桩旧事——吐蕃维州城守将悉怛谋受降事。由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的打击报复,李德裕在该事件中经历了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失败,其所遭受的“幽枉”或羞辱,乃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故始终在寻找辩白和昭雪的机会。2年后,他主持中枢,恰逢宫廷书画整理与收藏活动,此时他新伤未平、恨意难抒,遂以宰相之尊亲自主持《步辇图》的重装褙工作,并不厌其烦、喋喋为之题跋。该题跋,与其说是对约200年前太宗接见禄东赞事件的追忆,毋宁是对2年前他本人所受的政治羞辱的咀嚼;同时,该题跋也可索解李德裕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职时的遭遇、他所倡导的边疆政策及二者与题跋内容之间隐喻性的关联。具体地说,其题跋所表现的内容,或不仅引发了李德裕的身世之痛,也可赋予其所主张的边疆政策以历史的正当性。跋文对《步辇图》所表现的事件进行了重构,似是为暗示他对维州受降事件的处理,乃是遵循太宗皇帝的原则和遒谟;而文宗皇帝与牛李出卖向化者致其遭虐杀,则违背了太宗所确立的对帝国藩属的执驭之道。换言之,李德裕对《步辇图》的题跋,当是以对太宗朝贞观旧事以及吐蕃政策的征引为隐喻,暗讽维州城悉怛谋受降事,并为自己辩白。重装褙、题跋及“追论悉怛谋”等一系列事件,不仅解慰了12年来所遭受的良心之痛与道德折磨,反映了当时牛李两党对于吐蕃政策的不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中晚唐朝廷对于回鹘、黠戛斯等边疆民族割据政权的立场及策略。文章可作为探讨古人如何以书画收藏及题跋活动作为政治“动源”,来隐晦地表达其施政策略的美术史个案。
关键词:李德裕;步辇图;晚唐边疆政策;牛李党争;吐蕃;悉怛谋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22)05-0151-11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步辇图》手卷,旧传初唐阎立本手笔,对此学界虽不尽认可,但称其祖本乃唐作、今本为宋人所摹,则大体是一致的徐邦达在《古书画伪讹考辨1》中对《步辇图》的画风、笔法、收藏印玺等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该画卷具有临摹特征,原作可能是唐人真本;杨仁凯在《中国书画》一书中也认为该图或是北宋摹本;傅漩琮、周建国在《<步辇图>题跋为李德裕作考述》中认为小篆文由李德裕作,后由章伯益过录到这个宋初摹本上。。除所用绢有宋绢的特征外,卷后的宋人题跋与印鉴,亦可印证此说。既有的《步辇图》研究,多围绕画作本身展开;争论的焦点,也多集中在唐真迹还是宋摹本、作者为谁、所呈现的具体历史场景为何等问题。至于画心左侧的李德裕题跋,则鲜有学者论及。今细读李德裕题跋,并与晚唐边疆民族关系及其所主张的吐蕃方略互证,不仅可进一步证明此画的祖本为唐本,也可考见李氏如何以宫内旧藏为“讽喻”,来正当化所主张的吐蕃政策;同时,对于以绘画收藏为政治“动源”(agency)的历史考察而言,也可获得一个案性的理解。
一、过录与原跋
李德裕在《步辇图》上的题跋,并非原迹,而是章伯益在宋摹《步辇图》上的过录。其文作:
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装褙。
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禄东赞是吐蕃之相也,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于吐蕃,其赞普遣禄东赞来逆,召见顾问,进对皆合旨,诏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妻之。禄东赞辞曰,“臣本国有婦,少小夫妻,虽至尊殊恩,奴不愿弃旧妇。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安敢辄取?”太宗嘉之,欲抚以厚恩,虽奇其答,而不遂其请。
唐相阎立本笔。章伯益篆。
其中“太子洗马……而不遂其请”,是宋人章伯益过录的李德裕原跋;“唐相阎立本笔 章伯益篆”,则是章伯益为过录李氏之跋所加的说明。关于章伯益所过录的题跋确出于李德裕之手,傅璇琮、周建国从书法质量、宫苑摹本的习惯称法、跋文中的历史信息等九个方面做过细密考证[1]。其说持之有故,学界未见异辞。对傅、周二人的结论,本文再提供两个佐证。
其一,跋文的格式。按跋文中有三处空格:两处见于“太宗”之前,一处见于“旨”之前。以抬头或空格表示敬意,乃古人提及本朝君主时习用的“书仪”,唐代也是如此。倘非亦步亦趋地摹写唐人题跋,这些格式原不必保留;尤其是“旨”之上的空格太过细微,仅有义于唐朝,尤不必保留。
其二,《册府元龟》的录文。按《册府元龟962卷外臣部·贤行》中,有一则唐太宗接见禄东赞的记载。其文作: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8卷第5期
李钦曾讽喻与昭雪:《步辇图》李德裕题跋考论
吐蕃相禄东赞,贞观十五年来朝。先是,许以文成公主出降,赞普遣禄东赞来迓。召见顾问,进对合旨,诏以琅琊公主外孙女妻之。禄东赞辞曰:“臣本国有妇,少小夫妇,虽复至尊殊恩,奴身不愿违弃旧妇。且赞府未谒公主,陪臣安敢辄娶?”太宗嘉之,欲抚以厚恩,虽奇其答,而不遂其请,乃以为右卫大将军[2]。
其中“召见顾问”至“不遂其请”一段,文字几乎与李德裕在《步辇图》上的题跋悉同,与《旧唐书》《唐会要》《新唐书》《资治通鉴》所记太宗接见禄东赞的文字却存在差异《旧唐书》(成书于945年)卷196上,“初,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赞普使禄东赞来迎,召见顾问,进对合旨,太宗礼之,有异诸蕃,乃拜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又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段氏妻之。禄东赞辞曰:‘臣本国有妇,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安敢辄娶。’太宗嘉之,欲抚以厚恩,虽奇其答而不遂其请”。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553页。《唐会要》(成书于961年)卷97,“初,太宗许降文成公主,东赞来迎,召见顾问,进对合旨,乃拜为右卫大将军,又以琅邪公主孙女妻之。东赞辞曰:‘臣本国有妇,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安敢妄婚?’上嘉之”。见[宋]王溥撰.唐会要:全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31页。《新唐书》(成书于1060年)卷216上“始入朝,占对合旨,太宗擢拜右卫大将军,以琅邪公主外孙妻之。禄东赞自言:‘先臣为聘妇,不敢奉诏。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敢辞!’帝异其言,然欲怀以恩,不听也”。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624页。《资治通鉴》(成书于1084年)卷196,“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上嘉禄东赞善应对,以琅邪公主外孙段氏妻之;辞曰:‘臣国中自有妇,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且赞普未得谒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贤之,然欲抚以厚恩,竞不从其志”。见[宋]司马光编撰.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8140页。。这说明《册府元龟》中的这一段文字,可能源自《步辇图》上的李德裕题跋。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王冀公家褚遂良书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见禄东赞步辇图》……以上皆录见者。”按“王冀公”,即王钦若(962—1025),乃《册府元龟》的主编修。宋敏求(1019—1076)略后于王钦若,则所谓“以上皆录见者”,当是宋敏求所见的《步辇图》卷上,有王钦若的印章或题跋等鉴藏信息,即该画上留有被王钦若收藏的证据。按《春明退朝录》所记的史料,多翔实可信,历来为史家所重视和采撷,乃至所记的“民情风俗、官场应酬、书画题记、诗话词评等……亦颇具文学史研究价值”[3]。其关于《步辇图》曾藏于王钦若家的记载,若所记属实,则上引《册府元龟》中的录文,或便是王钦若从所藏的唐真迹《步辇图》题跋中誊录的。章伯益(1005—1062)生活的年代,约与宋敏求同时[4]。故综合以上信息推测,北京故宫博物院本可能摹于藏于王钦若家期间或之后的一段时间。总之,所谓的李德裕题跋,虽由宋人过录,但原文出于李德裕之手,是基本可信的。
李德裕的题跋,乃是为重裱褙《步辇图》所加的,时间为唐文宗“大和七年十一月”。据两唐书,李德裕重裱《步辇图》的11个月前,始授兵部尚书;重裱前的9个月,又加授同平章事。从此,李德裕便位列宰相,可入中书门下(即政事堂)共议国事了。重裱前的5个月,李德裕又加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5]3076,进入朝廷的最中枢。然则以宰相之尊、职务之繁、政事之重,李德裕何以自轻其身,竟亲自主持一件微不足道的旧画装裱,又不厌其烦,喋喋为其作题跋呢?这背后的动机,我想可索解于李德裕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上的遭遇、他所倡导的边疆政策及二者与题跋内容之间或可建立起隐喻性的关联。具体地说,《步辇图》题跋所表现的内容,或不仅引发了李德裕的身世之痛,也可赋予其所主张的边疆政策以历史的正当性。
二、题跋的背景
安史之乱之后,初唐所建立的“中央—边缘”的帝国结构便逐渐崩溃。原归顺大唐帝国的边疆民族,在脱离其统治的同时,不断挑起边衅、侵扰内地,其中威胁最大的,便是唐初以来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可以说,宪宗(778—820)之后,唐与吐蕃的关系已成为中晚唐朝廷政治的核心。
文宗大和四年(830)十月,也就是重装褙《步辇图》的4年之前,李德裕受宰相牛僧儒及其党李宗闵排挤,以“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西山八国云南招抚”[5]3075等职务,外放四川。这个原是帝国腹地、在安史之乱时曾庇护过玄宗的地区,由于南临南诏、西接吐蕃,至李德裕驻节的时代,已沦为帝国的西南边疆了。不难想见的是,作为兼民政、军事长官于一身的地方首长,李德裕的首要工作,便是在防止南诏、吐蕃入侵的同时,相机收复帝国失土。到任后,李德裕恩威并施,一时为南诏、吐蕃所惧服。驻节仅约1年后,便“两边浸惧,南诏请还所俘掠四千人”[6]4120。大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城守将悉怛谋又以城请降。今按维州是唐与吐蕃交界处的边城,乃当时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该城原属唐朝,后来吐蕃以计取之,并加固城防,称为“无忧城”,为吐蕃突入唐地的桥头堡。宪宗贞元(785—805)中时,唐倾锐师万人、攻其数年,欲收复该城,但吐蕃派大兵增援,唐军终劳而无获。如今不加兵刃,便可收复此城,在李德裕看来,这无疑是有功于帝国的好事,也是其西南剑川节度使生涯的重大成就。因此,他在接到悉怛谋请降的消息之后,便作了细致的安排。一方面,在接纳悉怛谋及其兵众进入成都的同时,派手下将领迅速占据了维州;另一方面,又“飞章以闻”,快速把消息上奏给朝廷。但朝廷接到上奏后的反应及处理方式,却令李德裕大失所望。
据李德裕后来在《论大和五年八月将故维州城归降准诏却执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谋状》(843年3月)中回忆,唐文宗接获李德裕的奏章后,曾大为“惊喜”[7]251。惟当时主持中枢的牛僧儒、李宗闵等人,却称这会破坏唐与吐蕃之间的盟约,所谓“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今一朝失信,戎丑得以为词”[5]3043,并认为此举会激恼吐蕃,对京师长安作侵扰性报复。从表面看,牛僧儒的立场,乃是维护朝廷的信用;实则吐蕃之所谓“盟”,都只是权宜而已,罕有其信。这一点,在玄宗朝已成朝廷共识。如林冠群总结云:
吐蕃对唐每遇不利情势,辄遣使赴唐,声称蕃唐甥舅关系亲密,和睦有若一家;但待时局转变为有利于吐蕃之时,则即刻发兵攻打唐境……唐蕃“舅甥关系”已沦为吐蕃操控和战的工具[8]。
玄宗之后,随着吐蕃力量的崛起,其破盟的行为,又益形加剧。如长庆元年至三年,吐蕃与唐之会盟即达三次之多,但每次都旋盟旋破。其中长庆三年(823)的会盟,乃是牛僧孺亲自参与的;会盟之后,又分别于吐蕃及唐之都城,各立碑为证(立于吐蕃者现称为“唐蕃会盟碑”,仍立于拉萨大昭寺前),牛本人的名字,也列于碑中。但立碑不过3年(826),即维州受降的前1年,吐蕃竟出兵攻打鲁州[7]252。然则吐蕃何尝有“信”?这一点,牛僧孺显然心知肚明。其所谓“守信”,当只是说辞。其真正的动机,应是打击李德裕后代有学者根据有限的史料,称牛党的内外政策偏于“怀柔”,但Michael T. Dalby有反驳,见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651-652.。按早在宪宗朝时,李德裕的父亲、时任宰相的李吉甫,便与牛僧儒、李宗闵一党结下了怨隙。李吉甫去世后,这怨隙便迁移到了李德裕身上。事经两代,怨隙越结越深,最终恶化为仇恨。李德裕被调离中枢,外放剑南西川,以及“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便是这仇恨的表现之一。因此,牛僧儒在维州受降事上所秉持的立场,是——至少在李德裕看来——不可谓公义的,而是借机发泄对其家族及个人的私愤关于牛李党争及中外研究综述,参看Michael T. Dalby为《剑桥中国史》撰写的专门章节,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pp.639-654.。尤有甚的是,牛僧儒不仅不录其功,还建议软弱无见的文宗令德裕“却送悉怛谋一部之人还维州”[5]3075。这无异是对李德裕作公开的政治羞辱了。因为在受降之初,李德裕曾与悉怛谋“指天为誓”,约言互不背叛。文宗的詔书,则把李德裕置于个人道德的两难:不奉诏,乃谋逆;奉诏,则为“弃信偷安”。故奉接诏书后,李德裕大感为难,于是“累表陈论,乞垂矜舍”,意谓维州固可归还,至于悉怛谋及其部众,则请求留于成都。这一要求,无论是对“向化者”所宜施加的仁慈,还是存大臣之体,都是最合宜的。这也是汉朝以来帝国朝廷处理类似事件时所遵循的基本策略。但牛、李却坚欲羞辱李德裕,故怂恿文宗“答诏严切,竟令执还,加以体披三木,舆於竹畚,及将即路,冤叫呜呼”[7]252。牛僧儒的动机,颇为吐蕃朝廷所觑破。故在李德裕被迫归还维州城及降人之后,便在唐与吐蕃的边境上,对悉怛谋及其部众数百人,作了公开地展示性虐杀,所谓“将此降人戮於汉界之上。恣行残忍,用固携离,至乃掷其婴孩,承以枪槊”[7]252。对李德裕而言,这已经不仅仅是政治的羞辱,而是对其个人良心和道德的折磨了。可想见的是,这场政治、道德的双重失败,必然会给李德裕留下终身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新唐书·李德裕传》称“德裕终身以为恨”,便是言此。明此背景,我们便可理解2年之后,李德裕何以宰相之尊,竟然亲自主持《步辇图》的重装褙,并喋喋为之作跋文了。
按维州受降1年之后,与李德裕同派往四川的剑南西川监军使、太监王践言返回朝廷,向文宗详细讲述了悉怛谋归降与被“出卖”及虐杀的经过,称此事的处理,是颇沮“拒远人向化意”的。文宗的性格,原本优柔寡断,又宠信太监,闻听之后,便恼恨于牛僧儒当年给他的划策,于是便罢其相,逐其出朝廷。与此同时,又“以兵部尚书召(按李德裕),俄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赞皇县伯”欧阳修、宋祁撰[M].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120页。按李德裕与剑南西川监军使宦官王践言交好,王离川入朝知枢密使前,李德裕曾向其行贿,《册府元龟》卷669《内臣部·贪货》记载:“王践言为西川监军。节度使李德裕加征疲人三十万贯缗,因践言赴阙,尽以饯行。及践言为枢密使,德裕果为宰相。”见[宋]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M].中华书局,1989年,第2257页下。。因此,李德裕便离开四川,回到了朝廷中枢;不数月,即大和七年六月,又“代(按李宗闵)为中书侍郎、集贤大学士”[5]3076,从而荣登文宗的“首席宰相”。《步辇图》的重装褙与题跋,便发生于李德裕拜相5个月之后。细味其遭遇及题跋内容,其主持重装褙并题跋的动机,是不难推想的。
三、题跋的内容
李德裕在《步辇图》上的题跋,与其说是对约200年前太宗接见禄东赞事件的追忆,毋宁是对2年前他本人所受的政治羞辱的咀嚼。按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八月,吐蕃攻松州,太宗派遣侯君集、执失思力等四道行军,击溃了吐蕃的进犯。吐蕃国王松赞干布慑于唐威,遣其相禄东赞入朝请婚[9]8112。《步辇图》画面所呈现的,便是禄东赞入朝请婚、受太宗召见的一幕。图中太宗位于画心右侧,被九位宫女所簇拥,神情自若,富有威仪;禄东赞在典礼官、内官的引导下,处于画面左侧,作揖拜状。他体态拘谨、态度恭谦,颇见藩臣向化之意。
今按禄东赞入朝为赞普请婚,是初唐政治史上的大事,对此两唐书皆有记载。唯叙事的重点,乃集中于既慑于唐之国威,又欣慕唐之文化的吐蕃,即都将吐蕃作为叙述的主角。所谓遣禄东赞入朝“致礼,献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百事”[5]3552,赞普本人“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5]3553等内容,都是言此的。也就是说,史官叙事所呈现的,乃是吐蕃的主动向化。这种叙事策略,其实是古代官修史书的通例,《汉书》以来即如此。这主要缘于古代“中华帝国”的边疆策略,原不主张“力征”,而更倾向于“德化”。李德裕于会昌三年(843)撰写的《黠戛斯朝贡图传序》,也采用了同样的叙事策略。
但李氏撰写的《步辇图》题跋的叙事策略,却颇异于此。细味其跋文,可知其叙述的重点乃是太宗对向化者的嘉赏,具体来说,就是对吐蕃权臣禄东赞的嘉赏。如跋文劈头便称:“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在两唐书中,此事只是“畏威—向化”敘事结构中的一个寻常细节,但李的题跋却首举此事,仿佛这是太宗许降赞普以文成公主事件中最重要的内容。与此同时,原是两唐书所呈现的主角——既惧唐威、亦慕唐化的吐蕃,此处也易为嘉赏向化者的太宗了。此后,跋文又称“(太宗)召见顾问,进对皆合旨,诏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妻之”,这不仅再次强化了太宗的主角身份,也把一场重大的国事,降为太宗对禄东赞的个人嘉赏了。今按以宗室女妻吐蕃赞普,是帝国中央与藩属间的正礼,可定义两个政治体间以“子婿”为比喻的主属关系。以宗室女妻吐蕃之臣体现的,则是唐君主与外臣之间的私礼,不具有定义两个政体之间关系的意义和功能。李德裕所属的赞皇李家,乃唐代最显赫的士族之一,向来以礼名家。又据史书记载,李德裕少有宰相之器,凡事识大体,持大节。但其题跋在回忆吐蕃向化时,何以把叙事的重点,转移为太宗对向化者的个人嘉赏;不仅此,又何以遗帝国政治之大、取琐琐封赏之小呢?这背后的原因,必是画面所记载的事件触碰到了其内心的创伤。如前文介绍的,李德裕驻节剑南西川时,由于恩威并施、举措得当,最终赢得悉怛谋归诚向化。按太宗的原则,这必是应给予重赏的大功。但文宗惑于牛僧儒的谗言,不仅不嘉赏,反令李德裕归还。在李德裕看来,这未尝不是将向化者“出卖”给吐蕃,最后导致向化者惨遭虐杀。这不仅是对李德裕本人的羞辱,也颇沮“拒远人向化意”[6]4120(监军王践言语)。
总之,李德裕题跋对画面所呈现事件的重构,似是为暗示他对维州受降事件的处理,乃是遵循太宗的原则和遒谟;而文宗与牛李出卖向化者致其遭虐杀,则违背了太宗所确立的对帝国藩属的执驭之道。换言之,李德裕对《步辇图》的题跋,当是以对太宗吐蕃政策的征引为比喻,为2年前的维州受降事作辩白。
四、讽喻
或问李德裕重装褙并题跋的动机,若果在于为自己的吐蕃政策辩白,那么谁是他期望的目标读者?这便涉及《步辇图》的收藏者,以及李德裕作为集贤殿大学士的职掌了。
按大和五年(831),朝廷斥李德裕受降为悖举、并令他归还维州城及悉怛谋兵众,这背后的主使,固然是牛僧儒,但命令却是以文宗诏书的形式公开下达的[5]3076。1年后,由于监军王践言的暗中进言,文宗心悔其非,于是罢去牛僧儒,召李德裕回朝,并授予他一系列荣誉与官职,但授予的理由,却颇讳言之。原因是当初的命令,毕竟是以文宗而非中枢的名义下达的;明言其受拔擢的理由,便等于曝文宗之短。另外,当时牛僧儒虽被罢相,其党徒犹盘踞朝廷,如当初与牛僧孺共同排斥李德裕的李宗閔仍在朝为相,地位犹在李德裕之上。大和七年(833)七月李宗闵被罢相后,文宗才把其所担任的中书侍郎、集贤大学士等官职加诸李德裕身上。但即便如此,牛党在朝廷的势力也只是暂伏而已。也就是说,李德裕受羞辱的理由是公开过的,但受拔擢的理由,却因文宗方面的原因需要隐讳。对李德裕而言,这纵然不是不公平(为君讳乃臣义),也是令他气闷的。因此,如何以隐讳的方式,向文宗与朝臣作“自我昭雪”,必是李德裕内心的追求。《步辇图》的重裱,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前举章伯益过录的跋文之首,有以下字样:“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 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 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装褙”,可知署名的方式是甚为礼仪化的。故合理的推测为:二李的重装褙乃公务性行为,所装褙的画作当为朝廷的公藏。按唐代史料中,未见“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其人,但由姓名、官职、爵衔来推测,他或出自以陇西为郡望的李唐宗室。李德裕的名字列于其后,当是以伐阅和爵位来论,而非以官职大小为序。从伐阅来说,赞皇李当不及陇西李;以爵位来论,“赞皇伯”也低于“武都公”。
又据《新唐书·百官志》“东宫……左春坊……总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六局……司经局,洗马二人,从五品下。掌经籍,出入侍从。图书上东宫者,皆受而藏之”[6]847-848,可知李道志所担任的官职太子洗马,乃是东宫左春坊司经局的主官,其主要职责,即是掌管东宫的经籍与书画收藏。李德裕的官职,当时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中书侍郎兼集贤大学士。前三个官衔,都与书画装褙事无关。最后的兼领“集贤大学士”,则为集贤殿书院名义上的长官。唐代的集贤殿书院,兼有朝廷图书馆及博物馆的功能,除收藏国家图书外,也负责收藏、装褙、临摹历代所传的重要书画作品,其中尤以纪念性的作品为重,所谓“国朝内府、翰林、集贤、秘阁,搨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10]128。
故综合上述信息推测,李德裕兼领集贤大学士这一官职之后,对东宫与集贤院两家机构的书画收藏,曾有过一次重新整理、著录与装裱的活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装背裱轴”条称,字画的装裱“候阴阳之气以调适,秋为上时,春为中时,夏为下时,暑湿之时不可用”[10]195。《步辇图》可能就装裱于这一年的秋天,而题跋可能是重裱褙工作完成后所加。可想见的是,在这次大规模的重裱之后,还应有一件盛大的文化活动——“曝画会”吸引大批朝臣乃至皇帝前来观赏《宋朝事实类苑·蓬山志》记载过秘书省组织的曝书画会制度,“秘书省所藏书画,岁一暴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罢。是月,召尚书、侍郎、学士、待制、御史中丞、开封尹、殿中监、大司成两省官暨馆职,宴于阁下,陈图书古器纵阅之,题名于榜而去。凡酒醴膳羞之事,有司共之,仍赐钱百缗,以佐其费”。见[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399-400页。李德裕生活的中晚唐时期,可能已有曝书画会活动,但成熟的曝书画会制度尚未形成。——这些人恰是前文所推测的李德裕的目标读者,而这也是李德裕重装裱并题跋的直接动机。作为挂衔的集贤院长官,李德裕自不必躬亲此事,但作为当时最谙熟先代掌故、同时也最具绘画知识与修养的人之一李德裕曾撰写《代高平公进书画二状》《进玄宗马射图状》等疏状,《黠戛斯朝贡图传序》等纪功文集以及《画桐华凤扇赋并序》等文;《太平广记》《剧谈录》也记载过不少李德裕收藏古书名画的轶事。, 李德裕必定熟悉或至少了解这幅记录太宗会见吐蕃使臣的纪念性作品,故命主此事者特为取出、亲撰题跋并传观于廷臣,以作为自我辩诬或自我昭雪之计,乃是可想见的。换句话说,李德裕以宰相之尊,亲自主持《步辇图》的重装褙、并在题跋中重提禄东赞之事,目的似以这件贞观旧事为隐喻,暗讽维州城悉怛谋受降事。
如前文所说,由于政治、道德的双重失败,李德裕在维州城受降事件中所遭受的羞辱与创伤,是至为深痛的,远非一则婉讽性的题跋可疗愈。但碍于“臣为君讳”之义,也限于他与文宗之间脆弱的信任关系,他所能做的也只有如此,故其心底的愤懑,自然不问可知。《步辇图》重装褙的翌年,即大和八年(834),李德裕果然又失文宗意,被外放为元兴节度使;其宿敌李宗闵则返回朝廷,复拜宰相李德裕被罢相的原因,《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有记载,“及德裕秉政,群邪不悦,而郑注、李训深恶之,文宗乃复召宗闵于兴元,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命德裕代宗闵为兴元尹”。此处的“群邪”指的是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集团和以郑注、李训为首的朝官集团。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098页。。由于受牛李二人的排斥,至武宗继位的6年间,李德裕一直沉浮于地方,备受压抑;辩白其污的机会,尤渺不可得。开成五年(840),文宗去世,武宗继位,李德裕自辩清白的机会,才终于到来。
五、追论与昭雪
武宗甫继位,便召李德裕由淮南节度使回到朝廷,授“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兼门下侍郎”[5]398,李德裕再次拜相。翌年,即会昌元年(841),朝廷中枢为回纥事集议。集议的起因,据《旧唐书·李德裕传》:
开成末,回纥为黠戛斯所攻,战败,部族离散,乌介可汗奉大和公主南来。会昌二年二月,牙于塞上,遣使求助兵粮,收复本国,权借天德军以安公主。时天德军使田牟,请以沙陀、退浑诸部落兵击之。上意未决,下百僚商议,议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曰:‘顷者国家艰难之际,回纥继立大功。今国破家亡,窜投无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穷来归,遽行杀伐,非汉宣待呼韩邪之道也。不如聊济资粮,徐观其变。’……帝以为然,许借米三万石[5]3077-3078。
引文中李德裕所谓的“顷者国家艰难之际,回纥继立大功”,是指安史之乱中回纥勤王戡乱事;“以穷来归,遽行杀伐,非汉宣待呼韩邪之道”,则指如今回纥势穷,前来归化,朝廷竟欲借他人之手杀之,这与当年汉宣帝扶持、嘉赏归诚向化的呼韩邪单于,是迥然有别的。则知如李德裕题在《步辇图》上的跋文一样,此处的话,虽然克制、隐讳,但12年前朝廷借吐蕃之手杀害向化者留给他的心理創伤,似仍在隐隐作痛。
翌年,即会昌三年(843),黠戛斯进攻安西、北庭都护府。由于唐兵自安史之乱后,已撤离西域,此时统治安西、北庭的,乃是忠于唐朝的回纥。朝廷在救与不救之间,再次发生争议。原诸李德裕的道德感,或对向化者的一贯立场,本应主张救的,但是这次他却主张不救。不救的理由,是“河、陇尽陷吐蕃”[5]3077,若从内地去救,绕路太远、军储不供,“纵令救得,便须却置都护,须以汉兵镇守。每处不下万人,万人从何征发?馈运取何道路?……纵令得之,实无用也”[5]3078。这个选择,战略上固然得宜,道德上却有瑕疵,因为这等于向黠戛斯出卖了向化者。对于经历了维州城受降事的李德裕而言,这自会再次揭起心头的旧伤。尤有甚者,黠戛斯在攻陷安西、北庭之后,立即派大臣请求册封[5]405,以合法化其在西域的统治。对唐廷而言,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因回纥是唐的“传统盟友”,黠戛斯则是唐之劲敌吐蕃的爪牙。人灭其友,不能救之,今反加封册,以合法化其行为——这与12年前悉怛谋向化归诚时朝廷不加封赏反戮之,尽管一奖一惩,处置不同,但俱为悖戾,则无甚差异。对于亲历了维州城受降事的李德裕而言,除觉其悖戾外,则会再次激起心中的耻辱感。故在其主持下,朝廷虽然认可了黠戛斯灭回纥的事实,但对册封之请求,则含混了事[11]。为了挽回颜面,李德裕又上奏武宗,称太宗贞观初“中书侍郎颜师古上言:‘昔周武王天下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今万国来朝,蛮夷率服,实可图写,请撰为《王会图》。’”[7]26故建议武宗效法太宗,命画工写黠戛斯使臣之貌,并据此做《黠戛斯朝贡图》,以此呈现唐与黠戛斯的主属关系。图卷完成之后,李德裕又以宰相之尊,亲自撰写了《黠戛斯朝贡图传序》,并冠于图卷之首。在记述了黠戛斯的向化之举后,李德裕又回顾了太宗时代“万国来朝”的盛况,并借题发挥、赞美武宗是继踵太宗的“中兴之主”。今按“职贡图”或“王会图”,乃始于汉代的绘画主题类型,主要内容是记录“德化夷狄”[12] ,以呈现“中央—四方”的帝国结构。李德裕所题跋的《步辇图》上的“步辇”二字,未知是否由宋人所题,但依照唐代绘画的分类,其属于李德裕所称的“王会图”或“职贡图”之列,是断无疑议的。尽管在大和七年的题跋中,李德裕为浇心中块垒,琐琐以太宗封赏禄东赞为言,未免降低了图画的政治—礼仪性。但可想见的是,李德裕在回忆太宗朝的《王会图》时,必然想到了他当年重装褙并题跋过的《步辇图》。
由上文介绍可知,从会昌元年至三年初这短短的3年间,由于西北边疆频有事态,作为中枢宰相的李德裕,不得不左支右拒,以谋求帝国之安宁。其用心的大处,固然是非个人性的国家策略,但每一个事件的处理,都未尝不激发他个人的身世之痛。不仅此,由于黠戛斯之祸乃是吐蕃怂恿、支持的结果,而吐蕃得以支持、怂恿黠戛斯,又未尝不是12年前朝廷处理维州城受降事“一失良图,千古不复”[7]450(李德裕语)所导致。这样,个人的身世之痛便转化为家国之悲了。或由于频繁的心理刺激,他久郁心底的愤懑便爆发了:处理完黠戛斯事件后不久,他忽然上书武宗,请求“追论”12年前的维州受降事:
臣在先朝,出镇西蜀。其时吐蕃维州首领悉怛谋,虽是杂虏,久乐皇风,将彼坚城,降臣本道。臣寻差兵马,入据其城,飞章以闻,先帝惊叹[5]3079。
末句的“先帝惊叹”云云,盖指文宗最初是诧异于其举、并以为奇功的。这自然是“臣为君讳”义。但是:
其时与臣不足者,望风嫉臣,遽献疑言,上罔宸听,以为与吐蕃盟约,不可背之,必恐将此为辞,侵犯郊境。诏臣还却此城,兼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复降中使,迫促送还。昔白起杀降,终于杜邮致祸;陈汤见徙,是为郅支报仇。感叹前事,愧心终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备台司,辄敢追论,伏希省察[5]3079。
这便把“一失良图,前古不复”的罪责,一股脑推到了“与臣不足者”——即牛、李二人的头上。这样说,自然也是为了保存文宗的颜面,并无太多意义。但末句的“幸逢英主”“辄敢追论”,却颇值得玩味:这等于说在文宗时代,此事原不可“追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武宗对于文宗的所为本多不值;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武宗对李德裕的信任,可谓达到了古代君臣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如按《旧唐书》总结:“德裕特承武宗恩顾,委以枢衡。”又称:“自开成五年冬回纥至天德,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尾五年,其(按李德裕)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武宗与李德裕之间信任的牢固程度,在我国古代史中是极为罕见的。乃至李德裕老病乞休,武宗也不允许:
以功兼守太尉,进封卫国公,三千户。五年,武宗上徽号后,累表乞骸,不许。德裕病月余,坚请解机务,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数月追还,复知政事[5]3081。
信任既如此胶固,李德裕自然可以放下心来,一抒其愤,故这篇奏章继续写道:
臣受降之时,指天为誓,宁忍将三百余人性命,弃信偷安。累表上陈,乞垂矜赦。答诏严切,竟令执还,加以体披桎梏,舁于竹畚。及将就路,冤叫呼天。将吏对臣,无不流涕。其部送者,便遭蕃帅讥诮曰:“既已降彼,何须送来?”乃却将此降人,戮于汉界之上,恣行残害,用固携离。乃至掷其婴孩,承以枪槊。臣闻楚灵诱杀蛮子,春秋明讥;周文外送邓叔,简册深鄙。况乎大国,负此异类,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从古以来,未有此事[5]3081。
这便把12年来所遭受的冤屈、羞辱以及道德与良心的折磨,一股脑地倾泻了出来,不复文宗时代《步辇图》题跋中的婉讽与隐喻了。则知悉怛谋请降事,虽然已经过去了12年,李德裕讲来仍然痛心疾首,乃至有“泪尽泣之以血”之感。由此可见维州受降事给他留下的心理创伤之深痛,也可体会《步辇图》题跋那冷静、超然的文字背后,有着怎样的隐忍与悲愤了。为解慰他12年来所遭受的良心之痛与道德折磨,李德裕在奏章结尾建议说:“臣实痛悉怛谋举城受酷,由臣陷此无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赠。”武宗览奏后:“意伤之,寻赐赠官。”[5]3080唯碍于体例,《旧唐书》此处的记载颇为简略。据《李德裕文集》,武宗“伤之”的后果,乃是以“敕令”的形式,命赠官悉怛谋。敕文说:
故蕃维州城副使悉怛谋,尝解辫发,献其垒垣。议臣托以和盟,沮其诚款,寻令束缚,归戮虏庭,彼获甘心,且无噍类。昔常山临代,为全赵之宝符,河西绝羌,断西戎之右臂,弃兹要害,用长寇仇,至今蜀人,言必流涕。岂陈汤之专命,由匡衡之废忠。言念始谋,久罹幽枉,爰加宠赠,用慰贞魂[7]61。
虽曰赠官悉怛谋,但用今天的话来讲,其实是为李德裕“平反昭雪”的。又从《李德裕文集》可知,武宗的敕文,其實是由李德裕代为执笔的;后又将其收入自己的文集,可知他对此文的重视程度。12年沉冤,一朝洗雪,李德裕自然感沁五内,于是立即上表武宗,以示感谢云:
况受降之时,臣与其盟诅,力不能捄,心实怀慙。运属圣明,合申幽枉,辄敢论奏,岂望听从。陛下用周文之心,已同葬骨;念汧城之枉,仍赐策书。臣忝补钧衡,尝居戎师,仰感玄造,倍百群情。臣不任云云[7]450。
则知正如前文所说,李德裕被迫“出卖”悉怛谋,良心是备受折磨的。所谓“幽枉”、所谓“敢”者,则是暗示12年来,由于害怕触文宗之讳、撄政敌之锋,自己一直隐忍于心,未敢辩白。执此复读大和七年的《步辇图》题跋,其背后所压抑的隐痛,便畅然大白了。
由唐中枢的行政模式来推测,武宗的敕令下达之后,廷臣即当集议追赠的官衔。可想见的是,主持讨论的人,必是当年亲历该事、今掌中枢的李德裕。据两唐书,廷议的结果乃是追赠悉怛谋为“右卫将军”。这个官职,也颇堪玩味。回忆大和七年李德裕《步辇图》跋文中的第一句“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两个赠官的区别,不过一“正”一“从”而已。可知李德裕建议追赠悉怛谋为“右卫将军”,乃在暗引太宗赠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的先例;也可知自大和五年以來,李德裕一直将太宗对禄东赞的嘉赏作为参照来回忆、咀嚼其维州城之辱的。
余说
上文以唐与吐蕃关系为背景,以维州城守将悉怛谋受降事中李德裕的遭遇,以及此后一系列事件的反应与处理为中心,探讨了李德裕重装褙并撰写《步辇图》跋文的动机、功能及影响。李德裕在维州城受降中所遭受的“幽枉”或羞辱,乃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事件,故始终在寻找辩白的机会。这些机会,虽然以12年后(按武宗会昌三年)发生的“追论悉怛谋事”为最大,但文宗大和七年距离此事仅2年有余,李德裕新伤未平、恨意难抒,此时的宫廷书画整理与收藏活动,无疑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明乎此,便可理解跋文的潜义,“讽喻”之功能,以及李氏何以宰相之尊,竟亲自主持《步辇图》的重裱褙并琐琐撰写题跋了。
最后可论的是,沈从文从《步辇图》人物的服饰出发,认为《步辇图》当作于开元、天宝之后,或非唐初之物[13]。今按唐宋宫藏的绘画,出于维护或保存计,往往制作摹本——尤以事关国家重大纪念性事件者为甚。纪念性的题材,当以存内容之大略为主,不同于以美学品质为胜者的摹本制作,故制作時加入后代画工所熟悉的次要母题,固可想见。这类摹本,唐宋人也往往视其为真本。因此,今所亡佚之《步辇图》祖本(即李德裕所跋之本),即使如沈从文所言,乃作于开元、天宝之后,也殊不足以说明由章伯益所过录的李德裕题跋为伪。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周建国.《步辇图》题跋为李德裕作考述[J].文献,2004(2):60-69.
[2]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中华书局,1960:11325.
[3]宋敏求,等.春明退朝录:外四种[M].尚成,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
[4]陈志平.章友直与张友正书史考辨[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6(3):68-71.
[5]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李德裕.李德裕文集校笺[M].傅璇琮,周建国,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8.
[8]林冠群.唐蕃舅甥关系释义[J].中国藏学,2016(2):12-21.
[9]司马光.资治通鉴[M].沈志华,张宏儒,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9:8112.
[10]张彦远.许逸民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21.
[11]岑仲勉.《会昌伐叛集》编证上[M]//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434-435.
[12]缪哲.从灵光殿到武梁祠:两汉之交帝国艺术的遗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260-261.
[13]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276.
Allegory and exoneration: On Li Deyu’s postscript attached to
Emperor Taizong Receiving the Tibetan Envoy
LI Qinzeng1,2
(1.School of Art and Archae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P. R.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0, P. R. China)
Abstract: Emperor Taizong Receiving the Tibetan Envoy, a hand-scroll traditionally attributed to Yan Liben(601—673), is a contemporary visual documentation of the diplomatic encounter between Tang and the kingdom of Tibet,immediately after the later was defeated and accepted tributary status in 641 AD. In 833, nearly two centuries after the encounter, Li Deyu(787—849), the chief minister of the court, ordered the hand-scroll to be remounted and wrote a postscript at the end of it, which recounted the encounter in a new perspective. Previous studies have mostly focused on whether the painting is an authentic work of the Tang Dynasty or a copy of the Song Dynasty, who the author is, what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scenes it presents, and its collection history, but few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the motivation, function and influence of Li Deyu’s remounting and postscript. This paper provides new evidence that the original postscript was written by Li Deyu from two aspects: the format of the postscript and the book of Prime Tortoise of the Record Bureau;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and new postscript, it reflects a border incident between Tang and the kingdom of Tibet that Xidamou who was the defender of Weizhou City, a general of the kingdom of Tibet, surrendering to the Tang Dynasty. Due to the revenge of Niu Sengru, Li Zongmin and others, Li Deyu experienced the failure of politics and morality in this event. The injustice or humiliation he suffered was the most unforgettable memory in his political career, so he was always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to plead and defend himself. Two years later, when he came to power, he met the sorting and collection activity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n the court. At this time, he did not recover from the new injury or expresse his hatred yet, so, he presided over the remounting of the Emperor Taizong Receiving the Tibetan Envoy and did not tire of making postscripts. The postscripts are not a memory of the Taizong meeting with Lu Dongzan about 200 years ago, but an expression of the political humiliation he suffered two years ago; meanwhile, the postscripts also indicated Li Deyu’s experience when he served as the Jiannan Xichuan Jiedushi, and the frontier policy he advocated. To be specific, the content of his postscripts may not only cause his pain for his fate, but also give historical legitimacy to his frontier policy. The postscripts reconstructed the events shown in the Emperor Taizong Receiving the Tibetan Envoy seems to imply that his handling of the surrender of Weizhou followed th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Taizong; However, emperor Wenzong, Niu Sengru and Li Zongmin betrayed those who surrendered and caused them to be tortured and killed, which violated the strategy how the empire controlled tributary states established by Taizong. In other words, Li Deyu’s postscripts to the Taizong Receiving the Tibetan Envoy took advantage of the past events in the Taizong Dynasty and the policy to the kingdom of Tibet as a metaphor, secretly satirized the surrender of Weizhou city, and defend himself. A series of events, such as remounting the scroll, writing down postscripts, and asking emperor Wuzong to grant Xidamou an official post, not only relieved the pain of conscience and moral torture suffered in the past 12 years, but also revealed the different opinions of the Niu and Li parties on the policy to the kingdom of Tibet at that time. To a certain extent, it also reflected the position and strategy of the mid and late Tang court on the separatist regimes of Uyghurs, Xiajiasi, and other frontier nationalities. This paper is an art history case to explore how the ancients used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llections as well as inscriptions as political agency to implicitly convey their administrative strategies.
Key words: Li Deyu; Emperor Taizong Receiving the Tibetan Envoy; Late Tang frontier policy; Niu-Li controversy; Tibet; Xidamou
(责任编辑傅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