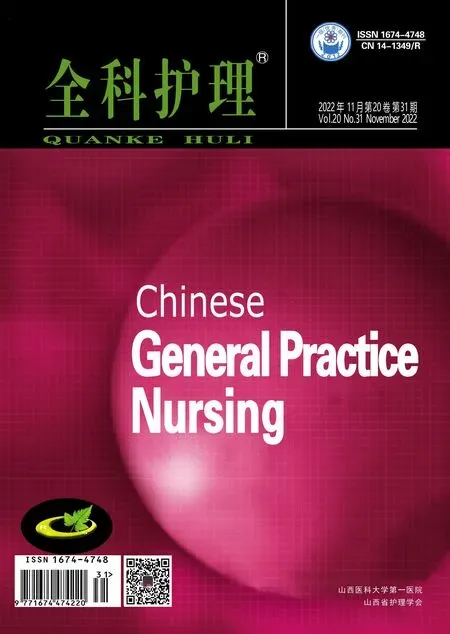夫妻间二元应对概念整合和实证研究进展
于 蕾,邓文卿,陈 娟
近几十年来,压力和应对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仅限于压力大的个体以及伴侣的支持在减轻他或她的压力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然而在过去的20年学者提出了更加系统的观点,他们将压力源影响从仅影响一个伴侣转变为影响伴侣双方,当伴侣面临同样的压力事件时,例如医疗问题,压力源最初可能与一个伴侣有关,但随后蔓延到关系中,最终也影响到另一个伴侣。换句话说,夫妻间的压力不再被概念化为个人现象,而是一种二元关系。这种压力的二元概念化不仅强调了伴侣压力经历的相互依赖性,且还将应对外部压力(源于夫妻关系之外的压力情境)的过程置于一种关系背景下,在这种背景下伴侣不仅对各自的压力做出反应,而且对彼此的压力做出反应。伴侣对由关系之外的环境造成的对方压力的应对通常被称为二元应对(dyadic coping,DC)。根据这种夫妻间压力和应对的人际观转变,发展了各种DC模型,最初主要包括一致性模型(the congruence model,CM)、以关系为中心模型(the relationship-focused model,RFM)、公共应对模型(the communal coping model,CCM)和系统交互模型(the systemic-transactional model,STM),考虑到发展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关系文化应对模型(the relational-cultural coping model,RCCM)和发展-背景应对模型(the developmental-contextual coping model,DCCM)。这些模型在概念上存在一定的重叠和交叉[1],本研究详细阐述每个模型的异同、应用领域以及用于测量的结构工具,最后对概念进行总结归纳。
1 CM及其研究
1.1 CM 20世纪80年代,不同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伴侣个体应对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感兴趣,他们研究了这些应对方式之间的相似和不同对个体和关系结果的影响。考虑到一方的压力和应对与另一方的压力和应对的关系,承认夫妻间压力和应对过程的人际背景。Cronkite等[2]研究了伴侣应对方式的相似性是否减轻了疾病相关压力,研究结果显示每个伴侣的个人应对资源和应对反应可以改变压力的影响和应对的有效性。Revenson[3]超越了伴侣应对策略之间的相似或相异之处,转而关注伴侣应对方式之间的一致性或契合度,即伴侣应对反应的协调和相互支持程度,进而创造了“一致性”应对这一术语,并提出了协调应对努力或相互加强的应对策略可以带来积极的心理、社会结果。CM主要应用于夫妻应对一般压力的研究(例如癌症、多发性硬化症等)。这些研究通常通过评估每个伴侣的个人应对方式和应对措施,常用的测量工具为修订的应对方式量表或应对策略清单。与其他DC模型不同,CM侧重于伴侣应对自身压力的个体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应对共同压力或一方应对另一方压力的联合策略。在这方面,这是唯一一个研究个人应对策略对夫妻功能的人际影响的DC模型。
1.2 实证研究 检索相关文献发现,对伴侣个体应对策略相似性的研究大都与医疗压力源有关。例如,伴侣在以情绪和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上的相似性帮助患有非转移性癌症的女性在10个月后适应[4]。在Kraemer等[4]的研究中,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方式的相似性预测了乳腺癌妇女更好的适应能力,但在Benzur等[5]的研究中没有预测到这一点。简而言之,即使是在聚焦相同的压力源时,对伴侣个人应对方式相似性的研究提供了不一致的观点。
2 RFM及其研究
2.1 RFM RFM主要由两组研究人员提出,一组为科因和史密斯领导[6],另一组为德隆吉斯和奥布莱恩领导[7],他们是第一个除了以个人情绪和问题为中心的应对压力的策略外考虑以关系为中心的策略来应对。两组分别关注RFM的不同层面,科因和史密斯的模型主要应用于夫妻应对医疗状况的研究,例如癌症、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等。他确定了主动参与和保护性缓冲两种具有关系聚焦功能的应对机制。在主动参与的过程中,一个人通过让他或她参与关于他或她如何思考及感觉,或者参与关于医疗状况的其他问题,来为患病的伴侣提供支持。保护性缓冲是指合作伙伴努力隐藏或否认担忧,并向另一方让步以尽量减少冲突。尽管这种应对方式可能是由积极的意图引发的,但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它通常会对压力大的个人和夫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随后通过与菲斯克的合作,科因和史密斯又确定了另一个应对策略:过度保护,即当伴侣低估了对方的能力,因此提供了不必要的支持(实际的或情感的)或限制了对方伴侣的活动时,就会出现这种应对方式。过度保护可以从概念上被视为一种消极的双向应对形式。为了直观的测量,科因和史密斯开发了关系聚焦应对量表,该量表带有评估积极参与和保护缓冲的子量表,并与菲斯克等人合作开发了过度保护量表。
德隆吉斯和奥布赖恩没有定义3个不同的具体层面,而是区分了积极和消极的RFM战略。积极策略包括同理心、提供支持和妥协,类似于系统交互模型的支持DC,而消极策略包括退缩和敌意,概念上类似于系统交互模型的矛盾/敌意消极DC。奥布赖恩等人特别关注一种积极关系应对方式的使用;移情反应,即无压力伴侣努力从另一伴的角度看待世界,体验压力情境为另一伴唤起的情感和认知联系,理解伴侣在他或她的交流中的心理状态。常用的测量工具为结构化日记和移情反应量表。
与CM不同,RFM将注意力从伴侣应对自身压力的方式转移到了识别帮助对方应对自身压力的成功和不成功策略上。通过这样做,RFM通过将保护性缓冲和过度保护描述为人们倾向于使用的个体机制。相比之下移情反应,也就是RFM描述的另一个积极的DC维度,与系统交互模型中以情感为中心的应对策略有相似之处。但它不包括伴侣共同应对压力的方式,也不承认背景因素(如文化)在塑造夫妻应对压力的方式中的作用。
2.2 实证研究 大多数关于积极参与的研究是在荷兰进行的,在不同的医疗条件下,一些研究发现积极参与对夫妻关系有积极的影响,对个人没有影响或有积极的影响。当伴侣变得积极参与时,病人和伴侣都报告了更好的关系满意度[8]、更好的个人应对和生活质量、更低的痛苦、更高的自我效能。研究还发现,伴侣的积极参与可以缓和糖尿病病人保护性缓冲和关系满意度之间的负面关联。也有研究发现积极参与与个人结果无关。Hinnen等[9]研究结果显示,伴侣的积极参与与他们的痛苦无关。
过度保护以及保护性缓冲作为一种消极的双向应对方式往往对病人产生消极影响。伴侣的过度保护与荷兰冠心病病人自我效能改善较少、癌症病人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DP)病人[10]控制感较弱和心理压力较大有关。Bodenmann等[11]还发现,当意大利夫妇的伴侣过度保护心脏病病人时,病人较少参与治疗。
在医疗应激源的情况下病人和他/她的伴侣可以通过保护性缓冲来相互帮助。然而,关于谁更依赖这种应对策略,调查结果并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照顾者往往比他们生病的伴侣使用更多的保护性缓冲,而其他研究则报告了相反的情况。不管哪一方提供保护性缓冲,保护性缓冲对西方夫妇治疗疾病时的提供者和接受者的个人和关系福祉都有负面影响。
3 CCM及其研究
3.1 CCM 由莱昂斯首先提出,主要包括3个组成部分。首先,关系中至少有一个人必须有共同的应对取向,也就是说,相信共同应对是有益的、必要的和/或有望解决问题的。第二,共同应对的过程需要交流压力,也就是说,个人必须分享情况的细节和意义。第三,个人通过合作来应对压力,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合作制定策略来减少这种情况的负面影响,并解决压力情况。许多学者认为这是理解夫妻应对医疗压力的一个很好的模型[12]。此类研究通常使用语言查询字数统计程序来统计伴侣在夫妻对话中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的情况,如我们或我们的,也称为我们交谈。一些研究也使用了两个自我报告式问题,一个是询问一方在多大程度上将另一方的健康状况视为“我们的问题”,另一个是询问双方合作解决该问题的程度。与其他DC模型相比,CCM的关注范围更窄,因为它几乎只关注医疗问题或个人压力。此外,CCM没有包括夫妻应对压力时的其他DC进程。例如:一方为压力大的另一方提供以情感或问题为中心的支持,而压力并不被视为“我们的”问题。
3.2 实证研究 基于每日日记数据的结果,患有前列腺癌男性[13]病人合作的DC与夫妻双方更积极、更少消极的情绪和个人应对效率有关。根据伴侣在交流中使用“我们”或“我们的”语言标准进行衡量,一项与患有乳腺癌的美国女性研究结果显示其抑郁程度较低,另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其对美国夫妇在治疗期间和随访期间戒酒情况改善[14]有关。
4 STM及其研究
4.1 STM 与起源于对夫妻一方有严重健康状况的研究的RFM或CM不同,STM侧重于检查夫妻应对日常麻烦或轻微慢性压力的过程。STM是一个全面的DC模型,因为它涉及积极和消极DC的各个方面。积极的DC形式包括支持、委托和共同的DC。支持性DC指的是一方试图通过以问题为中心(如提供建议或帮助寻找解决方案)或以情感为中心的策略(如表现理解)来帮助另一方应对。委派DC包括通过接管他/她的一些职责来帮助伴侣减轻压力。共同DC指的是双方或多或少对称或互补参与的应对策略,既可以以问题为中心(例如一起寻找解决方案),也可以以情感为中心(例如一起调节情绪)。与CCM相似,常见的DC可能发生在影响双方的情况下,并且被认为是双重压力或“我们的经历”(例如,孩子的出生或死亡、经济问题、儿童行为问题等)。但与CCM不同的是,它也被视为一种应对策略,也可能发生在最初可能与一方有关的情况下(例如失业、疾病),但被视为影响双方的情况,因此被视为“我们的压力”或“我们的疾病”[15]。STM消极的DC形式包括敌对、矛盾和形式上的努力来帮助压力大的伴侣。敌对的DC包括疏远、嘲笑、表现出不感兴趣。矛盾的DC指的是不情愿地提供支持或者表示不需要支持。(表面的)形式上的DC指的是不真诚的支持压力大的伴侣。夫妻双方的应对过程被认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背景、压力源的类型、双方的关心程度、压力原因的归因、个人因素、动机因素和关系因素。相关研究均使用博登曼开发的工具来评估DC即双向应对量表(DCI),该量表最初由55个条目组成,但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最常见的37个条目版本。DCI已经在35个国家使用过,并且在10多个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得到验证,国内由Xu等[16]进行汉化,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该模型指导了大部分DC研究,鉴于RFM将重点放在一方如何帮助另一方应对其压力上,而CCM将压力评估作为一个“我们”问题和合作应对策略来关注,STM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框架,其中包括压力评估(“我们的”问题与“你的”或“我的”问题”),并提供了帮助一方应对压力或让另一方共同应对压力的合作和个人机制。除了它的全面性,STM是唯一一个强调压力沟通这一维度的。
4.2 实证研究 压力沟通有益于夫妻关系,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压力沟通可以提高伴侣提供支持的可能性,针对日本人、拉丁美洲人和西欧和美国夫妇的研究也显示压力沟通与关系满意度提高有关。对一方患有抑郁症或癌症[17]的西方夫妇进行的研究表明,病人往往比他们的伴侣更少交流他们的压力。与医疗条件的压力沟通对个体具有积极影响,提高了COPD病人的生活质量[18],并促使健康伙伴提供支持。委托应对通常是在身体或心理条件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可能是因为在慢性病的背景下,人们期望伴侣能够支持患病伴侣的方法之一是接管他们的一些任务。从逻辑上讲,在患病的情况下非患病伴侣比患病一方提供更多的委托DC。例如,针对COPD或癌症病人的研究显示,与他们的伴侣相比,其参与委托DC的频率较低。然而,这种不平衡可能不一定有益,一项对COPD病人研究结果表明,当伴侣委托DC的不平衡程度较高时生活质量较低[18]。这些发现表明,在夫妻间处理委托DC的疾病不平衡可能是有益的,但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
5 RCCM及其研究
5.1 RCCM Kayser等[19]将STM理论应用于夫妻应对癌症的研究,不仅关注夫妻的应对策略,还关注影响这些行为的因素。因此,他们发展了RCCM,通过增加关系和文化成分来扩展STM。首先,在关系方面,他们确定了有助于相互反应的3个关键因素,即关系意识、真实性和相互性。关系意识是指考虑疾病对每一个伴侣和其关系的影响以及在疾病带来额外需求的情况下如何维持两个人的关系。真实性包括揭示真实的感情而不是隐藏它们,而相互性指的是要有同理心,伴侣的每一方都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和分享。在文化方面,Kayser等[19]首先通过承认文化在塑造夫妻适应压力环境的方式中的作用来扩展STM,但后来在对美国、中国和印度夫妇进行研究后,他们提出了可能影响应对的4个具体文化维度,即家庭边界(从开放到封闭)、性别角色(从差异到灵活)、个人控制(从接受到掌握)和独立(从依赖到独立)。RCCM是从定性研究发展而来的,因而还没有相关的测量工具。RCCM确定了有助于相互反应或回避的关键因素,此外RCCM是第一个研究文化因素在影响夫妻双方压力和应对过程的模型,因其仅考虑到对医疗状况的因素,尚不清楚RCCM确定的文化和相关因素是否适用于其他压力状况。
5.2 实证研究 在许多西方文化中DC对女性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也比男性更大。此外,在西方夫妇中女性比男性更经常地表达自己的压力。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提供消极的DC形式,例如保护性缓冲和敌对/矛盾的DC。一项关于中国夫妇的研究[16]报告称,男性比女性更频繁地交流压力,这与西方大量研究形成鲜明对比。一些研究发现年龄婚姻长度对整个DC[20]、压力沟通、积极参与、保护缓冲没有影响。相比之下,其他研究报告称,年轻夫妇比年长夫妇更频繁地以积极的DC形式参与,而较少以消极的DC形式参与。
6 DCCM与实证研究
6.1 DCCM DCCM是由Berg等[21]开发的,旨在了解夫妻应对慢性病的过程,主要包括无涉、支持、协作和控制4种应对策略。无涉应对指的是伴侣没有提供支持来帮助另一方应对压力,而支持性应对指的是伴侣在情感上和/或工具上提供这种支持的感觉。合作应对描述了双方共同应对压力的情况。控制应对描述了无压力的伴侣通过控制和告诉对方该做什么来控制另一方的行为。与STM、CCM和RCCM相似,DCCM强调压力评估过程在实际应对策略之前的重要性。与其他DC模型不同,DCCM不关注压力沟通,而是关注伴侣的反应,DCCM强调发展和背景因素在评估压力和应对措施中的作用。DCCM认为文化差异、性别差异、夫妻关系质量和疾病类型会影响压力评估和伴侣的应对。与其他模型相比,这一模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建议,即夫妇的应对策略可能因疾病的阶段而异。在这方面,这是唯一一个表明夫妇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即使是在应对相同的压力时。这种应对的动态观点在其他方法或研究中似乎是不存在的。
6.2 实证研究 共同协作的DC与更好地解决个人问题和减少个人及其伴侣抑郁的负面情绪表达有关。在关系层面,共同协作的DC对夫妻应对医疗状况有积极影响。作为公共应对的一个指标,我们交谈与美国夫妇应对乳腺癌的关系调整相关联。在肯尼亚夫妇中,社区应对帮助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阴性夫妇努力避免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帮助零不和谐夫妇预防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传播,并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呈阳性反应[17]。与这些发现相一致的是,报告相互反应的DC应对乳腺癌的夫妇也报告了更牢固的关系。
7 小结
综上所述,DC进程涉及伴侣关于他们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应的沟通,这些反应可以是积极的或消极的,概述起来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压力沟通:指伴侣对压力的沟通。②积极DC:个人积极应对即一方积极回应,帮助另一方应对压力(支持DC、移情、委托DC、积极参与);联合DC指伴侣共同应对压力(共同、协作)。③消极DC:个人消极应对指一方对另一方压力的消极反应(如保护性缓冲、过度保护、敌对/矛盾的DC和控制DC);消极联合DC指双方应对压力的联合消极反应(共同消极的DC、脱离回避)。与DCCM相似,发展变量、关系变量和情境变量也包含在模型中,作为影响压力和应对过程的因素。纳入发展因素,压力评估和DC策略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压力状况的变化或发展而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压力的变化可能导致采用不同的应对机制。例如,伴侣最初可能会用支持性的DC来应对一方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可能会将这种情况视为“我们”问题,并积极参与DC的联合行动。关系变量是影响压力评估和应对过程的关系特征。RCCM已经提出了一些关系特征,如关系意识、真实性和相互性,这些特征增加了伴侣将问题视为共有问题并参与合作应对形式的可能性。其他关系特征,如亲密程度、满意度和建设性地解决冲突的能力也会影响压力评估和应对过程。背景因素是指可能影响资源可用性(如失业、收入水平)、文化价值观(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和/或可能影响夫妻压力评估和应对的宗教信仰的社会经济条件。
综合起来或分开来看,各项结果表明,当夫妻报告使用DC时,移情反应、 积极参与、支持DC、委托DC、压力沟通或共同或协作的DC,在应对压力时会更好地使用有效的个人应对策略、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更低的心理压力和抑郁,以及在应对心理健康或医疗状况时更好的疾病管理和身心健康。在关系层面上,这些夫妇在应对压力、心理健康和医疗压力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具建设性的沟通和关系满意度。与DC的积极形式相反,DC的消极3种形式都与消极的个人和关系功能有关。在疾病的背景下,无论哪一方是提供者还是接受者,过度保护、保护性缓冲和敌对/矛盾的DC与较低的自我效能、控制感、身体和情感健康以及关系满意度相关。在伤害或保护个人和关系福祉方面,一些DC维度可能比其他维度更关键。例如,在医疗和非医疗压力方面,共同协作的DC往往比其他积极的DC层面更有利,而委派的DC似乎最不利。并非所有DC战略在不同背景下都是同样有利或不利的。然而,进一步的研究是必要的,以检查所有DC策略的不同影响和不同压力源之间的差异。此外,应该在不同的压力环境下研究DC形式。例如,大多数关于医疗应激源的研究都是针对夫妻应对癌症的,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集中在DC及其各个层面在夫妻应对其他医疗条件中的作用。同样,还可研究DC夫妇应对其他非医疗压力的情况,如经济问题、移民相关问题、抚养残疾儿童、情感和/或行为困难、照顾老年家庭成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