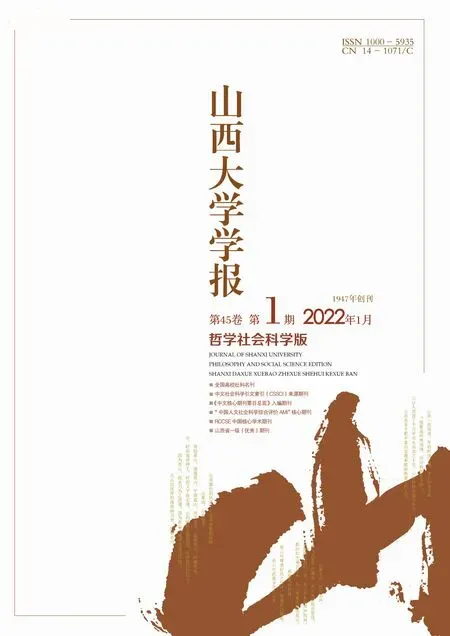论帝国的兴衰
俞可平
(北京大学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91)
帝国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这一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崩溃而一直被严重忽视。21世纪以来,帝国研究再度成为政治学的关注热点。帝国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是分析和探索帝国产生和兴亡的一般规律。本文将在简要分析20世纪晚期以来帝国研究回归的理论与现实原因后,着重分析影响和决定帝国产生和兴亡的主要因素,以期推动国内对帝国理论的深入研究。
一、帝国研究的回归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它不仅使人类的和平力量最终战胜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侵略力量,结束了数个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引发了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在战后纷纷挣脱殖民宗主国的束缚,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从而彻底摧毁了统治人类历史数个世纪之久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主角。正如马丁·托马斯(Martin Thomas)和安德鲁·汤普逊(Andrew S. Thompson)所说:“过去的20世纪,正式的殖民统治的崩溃、帝国的终结,或如专家们通常所说的非殖民,已经重新塑造了世界的政治地理”(1)THOMAS M,ANDREW S.Rethinking decolonization:a new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nds of Empir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1.。昔日视为政治荣耀的帝国体制,成为人类所不齿的政治压迫机器,而帝国主义则被当作是对外侵略和殖民的政治符号。随着帝国日益淡出人们的视野,对帝国的研究也日益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对民族国家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国家理论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帝国,而是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
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人类的历史进程再次发生重大的转轨,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得以重新调整,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世界政治两极时代宣告结束,人类政治进入了多极化时代。特别是全球化进程深刻地冲击了传统的主权国家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这一人类政治历史进程的转变相适应,国家理论的关注重点也再次发生变化。一个能够预见的变化是,更多的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另一个多少出乎许多政治学者意外的是,帝国问题又再度受到重视。
正如《千年帝国史》的作者克里尚·库马尔所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界,二战后,帝国的热潮渐退。政治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欧洲帝国的解体,包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新的国家由此诞生。因为帝国被视作过去的遗留物,人们对历史的具体情节缺乏兴趣,包括帝国的治理原则、帝国的目标愿景以及帝国代表的这种特殊政治实体。于是,人们对帝国既反感,又漠视。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人们对于帝国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最近几十年来,无视帝国的态度发生了改观。帝国研究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大批分量极重的著作、研讨会以及大众媒体宣传都说明了这一点”[1]。
关于帝国研究的重要著作,我们不妨在此随便举些例子:迈克·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thepoliticalorderofglobalizatio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新帝国主义》(Thenewimperialism)、尼尔·弗格森(Nial Ferguson)的《帝国:大英世界秩序的兴衰与全球霸权的教训》(Empire:theriseanddemiseoftheBritishworldorderandthelessonsforglobalpower)、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的《帖木尔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AfterTamerlane:theglobalhistoryofempiresince1405)、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的《千年帝国史》(Visionsofempire:howfiveimperialregimesshapedtheworld)、简·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库柏(Frederick Cooper)的《世界历史上的帝国:权力与差异政治》(Empiresinworldhistory:powerandthepoliticsofdifference)、勒波维克斯(H.Lebovics)的《将帝国带回家:全球化时代的法兰西》(Bringingtheempirebackhome:Franceintheglobalage)、列文(D.C.B Lieven)的《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Empire:Russianempireanditsrivals)、默顿(J. Muldoon)的《帝国与秩序:帝国的概念》(Empireandorder:theconceptofempire, 800-1800)、珍妮弗·皮茨(J. Pitts)的《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Aturntoempire:theriseofimperialliberalisminBritainandFrance)、萨伊德(E.W.Said)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andimperialism)、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帝国的迷思》(Mythsofempire:domesticpoliticsandinternationalambition)、马丁·托马斯(Martin Thomas)和安德鲁·汤普逊(Andrew S. Thompson)主编的《牛津帝国终结手册》(TheOxfordhandbookoftheendsofempires),以及彼得·F. 邦(Peter Fibiger Bang)、C.A.贝里(C.A. Bayly)和W.谢德尔(Walter Scheidel)合编的两卷本《牛津世界帝国史》(TheOxfordworldhistoryofempire)(2)关于“帝国研究的回归”,英文文献可集中参阅:BANG P,BAYLY C,SCHEIDEL W.The Oxford World History of Empir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PITTS J.Political Theory of Empire and Imperialism:an Appendix[A]∥MUTHU S.Empire and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351-389. 中文文献亦可参阅:饶淑莹.转型时代的帝国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客观地说,帝国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帝国主义在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中,仍然被排除在人类政治进步的范畴之外。但我们不能因之而否认,在人类漫长的政治历史进程中,帝国曾经是人类的主要政治生存环境。正如约翰·达尔文在《未终结的帝国》中说,“帝国由某个民族或种族的统治者通过影响或政治统治得以掌控其他人而建立,它长久以来一直是世界大多数地区在大多数时期的政治统治方式,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默认模式”“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是由诸多帝国共同缔造的。事实上,无论是殖民地还是在曾经的殖民地,非洲、亚洲、欧洲还是美洲,这些帝国的遗迹在现代世界随处可见。现代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充斥着这些帝国留下的记忆、抱负、制度和不满”[2]。或者如库马尔在《千年帝国史》的扉页中所指出的,“世界史就是一部帝国史。在留有记录的大部分历史中,人类生活在帝国之中”[1]1。因此,若要全面了解人类自己所发明的基本政治制度,不能不研究帝国。尽管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各国政治学者重新关注帝国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当全球化从根本上动摇人类的民族国家认同时,人们对帝国的热情再度高涨不只是历史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者的单纯学术兴趣,而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在的理论逻辑。
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认同的巨大冲击,促使人们思考全球化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在人类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帝国体系曾经是人类遏制国家间的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秩序的最主要结构性安排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结构性安排被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所取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人类造成的最深刻冲击之一,便是开始从根本上动摇基于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体系。全球化对主权国家体系的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组织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跨国公司在相当程度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于分层化和中空化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国家的传统政治职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国内政治的基本变量;大量的全球问题使得国家权力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民族国家的认同遇到了新的危机;全球化正在重塑国家的自主性[3]。既然全球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用以取代帝国体系的民族国家体系,那么,人类接下去将用什么的结构安排来维系基本的全球秩序?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些人便自然想到了传统的帝国体系。例如,麦克·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那本风靡学界的《帝国》,其副标题就是“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内格里自己也明确说过,他们研究帝国理论主要有三种分析视角,其中两种都与全球化相关:“在对帝国进行界定时,我们使用三种基本的分析手段:第一,我们考察全球化现象;第二,我们分析民族国家的危机;第三,我们追溯本体论层面的社会变化,即,在物质劳动、生产合作和由此产生的生命政治等方面的变化”[4]。
一方面,全球化正在从根本上动摇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体系;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没有带来人们所期待的新世界秩序。不仅如此,全球化时代虽然结束了以美苏冷战为主导的世界范围内的北约国家集团与华沙国家集团之间的对峙,但并未终结世界范围的冲突与战争。旧的冲突与战争威胁消失了,但大国之间和地区之间新的冲突产生了,人类依然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中。全球化有利于人类有限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便利的流动和合理的配置,从而在根本上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繁荣,也因而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但全球化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全球风险,以及民族文化与全球价值之间的新冲突。联合国竭力倡导和推动的全球治理,对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却远没有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人类仍然需要探寻一种后民族国家时代的新世界秩序,以最大限度地遏制国家间的战争、减少国家间的冲突、增强国际合作与信任,达到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存。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有些人便重新回想起“帝国治下的和平”,并希望从过去的伟大帝国中吸取某些经验。例如,促使库马尔开始系统研究《千年帝国史》的主要动因,其实也是全球化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挑战。他自己在书中明确表示:帝国已经重新回到了政治思考的中心,维护帝国运转的许多要素正是我们今天所急需的。人们在全球化时代期待“多元文化主义”,让不同信仰与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可以和谐相处。帝国从定义上就包含了多元文化因素;帝国不仅是“多民族的”,而且是“超越民族的”。最后,库马尔甚至公开期待,“帝国出现在民族国家之前,或许在将来会再次取代民族国家”[1]3。
作为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秩序体系中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也激发了不少人新的“帝国想象”。20世纪90年代后,苏联解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宣告结束,国际政治中美苏之间的对峙与平衡也不复存在,美国成为独霸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202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近30万亿美元,人均GDP为6.3万美元,在过去数十年中稳居世界第一。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成为世界唯一的通用货币,美国因而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美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和教育水平也稳居世界第一,无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与其匹敌。除此之外,美国也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军事大事,国防经费支出一直居全球之首,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海外军事基地,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也公认是世界之最。虽然自从21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目前为止,它仍然是唯一有实力充任“世界警察”的国家。鉴于过去曾经有过的“雅典治下的和平”“罗马治下的和平”和“英国治下的和平”的历史记忆,不少学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美国视为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麦克·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的《帝国》立论依据如此,帕特城里斯·格尼费和蒂埃里·伦茨的《帝国的终结》的逻辑其实也同样如此:“是的,美国正在衰落;不,它仍居群首”。在他看来,美国毫无疑问仍居世界首位,这首先是它的军事实力。美国的军备投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却占世界各国军费总和近一半。技术先进的武器、装备与海外700个基地所组成的“帝国”网络进一步加强了其霸权地位。这些军事基地分布于世界70多个国家,而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一共只拥有30多个海外基地[5]。所不同的只是,肯定者充分赞扬美国的新帝国地位,并期待它对世界秩序带来美好的前景;而否定者一则质疑美国的这种霸权能力是否足以形成一个新的帝国体系,二则批判美国的新帝国角色,认为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动荡和不安。
全球化时代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同样召唤着帝国研究的回归。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许多当代世界的重大政治事件在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这被许多思想家称为人类历史的周期性。历史发展也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在相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某些社会现象便会重复发生。因此,历史研究始终成为人类自身吸取经验教训的重要途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总是为人类的前进起着镜鉴的作用。帝国的文明曾经在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中占据过核心的地位,帝国的体制也曾经是人类长期生活于其内的政治结构,历史研究如果缺失了帝国研究,那就不成其为真正的人类史。无论是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塔西佗的《编年史》,还是近代英国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直到现代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和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不仅仅是帝国研究的名著,更是历史研究的名著。它们揭示的既是帝国兴亡的规律,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人类进入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后,具体的政治法律、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条件不同了,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依然存在,昔日帝国的兴亡依然对今日大国的起落有着警示作用。无论人类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如果要最大限度地降低进步的代价,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人类就需要不断进行历史的反思;对于全人类而言,只要进行历史的反思,就离不开反思历史上那些帝国兴亡的经验和教训。
最后,帝国研究的回归,也与左翼学者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后殖民主义的反思密切相关。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西方左翼学者和激进学者,对帝国主义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美国为代表的新霸权主义开展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不少左翼学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与批判,不仅仅只针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政治霸权和经济侵略,而且也试图深刻地揭露帝国主义在被殖民地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流毒,唤醒被殖民地国家广大民众的自主意识。因而,众多的左翼学者纷纷成为新一轮帝国和帝国主义研究的急先锋。无论是哈特和内格里的新《帝国》理论,还是哈维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或者萨伊德和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现象之本质的揭露,都可以看作是左翼学者对当代帝国研究的新贡献。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看到的那样,“当代帝国研究的学术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为例,它是当代帝国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东方学》关注的是现代学科和知识体系(比如人类学、语文学)与欧洲帝国(大英帝国以及法国)的殖民扩张之间的密切联系”[6]。在这位学者看来,这些左翼学者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的批判性分析,直接推动了当代的帝国研究。“帝国研究不是传统的对殖民地的研究,因为很早就有对殖民地的研究,研究殖民统治者怎样统治那里的人民。那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先从制度上给殖民地一个界定,然后讨论殖民管理,也就是殖民官员如何统治当地人民,这是一种相当狭窄的殖民地研究。当代帝国研究由于后殖民思路的引入,强调文化意义上的殖民。谈到文化殖民,你就不能简单地说他的民族被殖民过,我的民族没有被殖民过,当你把帝国研究扩展到文化这个领域,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有没有殖民地官僚体制的问题”[6]。
21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帝国研究回归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更加重视“中华帝国”的研究。传统的帝国研究,主要局限于欧洲历史,很少关注亚洲和非洲的帝国经验。新一轮帝国研究大大拓宽了视野,多半是从全球史或世界史的角度对帝国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其中,所谓的“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s)更成为各种帝国研究的重点。在所有重要的帝国研究著作中,“中华帝国”几乎都成了不可缺少的内容。有些著作把“中华帝国”作为一个整体国家加以论述,有些著作则选择“秦帝国”“汉帝国”“元帝国”“清帝国”等个别强盛王朝作为帝国的案例加以分析。除西方帝国研究专家关注“中华帝国”外,一些西方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也开始从“帝国”的视角重新反思中国历史。例如,哈佛大学的欧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系统地梳理了中文语境中的“帝国”概念(3)参阅: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J].读书,2014(1):29-40.该文详细而清晰地梳理了“帝国”概念在中国近代的引入与演变,追溯了“大清帝国”和“中华帝国”的概念与想象的源流与定型。,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则从帝国的视角分析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大国”概念[7]。西方最新的“帝国研究”之所以重视“中华帝国”,主要原因不外三个方面。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挣脱“欧洲中心主义”传统的束缚,拓展了帝国史研究的视野,从欧洲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正如彼得·F.邦所说:“大多数帝国理论墨守成规,局限于欧洲统治世界的经验。显而易见,这种视角和模板必须扩大和调整,将其放到世界统治史和征服史的适当背景之中。毕竟在欧洲声称主导世界历史进程之前,人类已经走过了很长时间:我们的知识视野必须做相应调整”[8]。因此,他主编的洋洋两卷本《牛津世界帝国史》涵盖了从公元前3000年的远古帝国,直到21世纪为止的全球各种帝国形态,包括多个中国王朝。约翰·达尔文也说:欧洲的诸帝国瓦解后,新兴的后殖民国家取而代之,欧洲本身则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因此,他在《帖木尔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一书中,“将欧洲(和西方)放在更大的范畴里,放在欧亚世界其他地区建造帝国、建造国家、建造文化的宏大工程之间来探讨。个人认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欧洲扩张的进程、本质、规模和范围,并且稍微厘清当下世界复杂性的源头”[9];其次,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重要角度,这使得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凸显,从而引起更多西方世界史专家的关注;最后,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日益强大,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度前所未有地增强,大量研究成果发表,客观上也为西方学者的帝国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素材。
二、帝国的产生
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帝国是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征服、占领或统治。因此,帝国是一种国家权力结构和国家秩序体系,是国家产生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其前提就是国家权力的存在。人们常说,国家是人类自身的伟大创造,它是为了避免人类自身陷于相互残杀的丛林法则而产生的。换言之,从积极的角度看,国家的产生是为了维护人类生活所需的基本公共秩序。至少从法理上和形式上而言,国家代表着社会的公共利益,它为人类的公共生活所必需。即使国家给人类自身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国家也是一个必要的祸害,人类迄今还离不开国家。那么,建立在国家权力基础之上的帝国体系呢?人类为什么会有帝国,它也像国家一样是人类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吗?
从其直观的后果来看,所有帝国几乎都与征服、掠夺和占领有关,这是因为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就是夺取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物质利益。人类的正常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的物质财富,对于人类整体而言,获取和增进物质财富的根本途径是生产劳动。但对于单独的个体或群体而言,获得财富最简单和直接的手段,就是对别人财富的野蛮掠夺。人类早期的原始暴力和原始权力,本质上不过就是获取物质利益的工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使是现代国家,本质上也是夺取和维护阶级利益的工具。这一点对于帝国权力的产生,也同样适用。古代的帝国几乎毫不隐瞒对外军事征服和扩张的目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土地,夺取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土地、更多的食物、更多的奴隶、更多的妻妾、更多的金银、更大的宫殿、更大的城池、更奢侈的生活,对于古代帝国几乎是赤裸裸的目的,像波斯帝国、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都毫不掩饰帝国扩张的这些动因。对于近现代的帝国,即使表面上多了一层遮羞布,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对物质利益的掠夺和攫取。正如霍布森在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时所指出的:“每一种生产方法的改进,每一次所有权的集中和控制似乎都加剧了帝国主义扩张的趋势。一个接一个国家进入机器经济时代并采用先进的工业方法,制造商、商人和金融家愈来愈难以使经济资源转换成利润。到处是生产能力过剩、寻求利润的资本过剩。所有的生意人都承认,本国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生产的商品过多,以致不能正常销售出去以赚取利润;现在资本过多,超出能带来盈利的投资量。上述经济状况是形成帝国主义的根源”[10]。
既然帝国产生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获取土地、人口和产品等人类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财富,那么,衡量和评价帝国的基本标准自然就是物质利益。土地面积、人口数量、财政税收、物质产品、大型工程、楼宇建筑、金银财富、稀世珍宝等等,通常都是帝国强大的表征,也是帝国的辉煌所在。在漫长的传统社会,土地和人口是生产的两个核心要素,从而也是财富的主要象征。有了土地,就有种植粮食的耕地、放牧牛马的草原、冶炼金属的矿藏和进退自如的空间;有了人口,就有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作战打仗的兵源、征收赋税的人丁和侍候权贵的奴仆。因此,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曾是帝国成就的主要标志。只是到了近现代之后,除了领土和人口之外,诸如生产、贸易、交通、金融等其他形式的财富也开始成为帝国荣耀的来源。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一世全盛时期,不仅征服了几十个国家,帝国版图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岁入丰盈。例如,“1526年至1550年期间,苏莱曼大帝的岁入总额达600万达卡银币,岁出总额则为450万达卡银币”[11]。又如,被称为第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在其全盛时期不仅是欧洲的霸主,而且其影响力遍及美洲和东南亚。西班牙从美洲夺取的白银,一度成为最硬的国际通货、世界经济的血液。16世纪末,西班牙统治的秘鲁和墨西哥两个地区就生产白银达27万公斤,而罗马帝国控制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250年至公元350年的600年间,总共生产白银只有5~6万吨[12]。到了大英帝国就更是如此,不仅帝国的面积前所未有的广阔,而且经济实力和财富总量都无与伦比:在1860年前后的大英帝国鼎盛时期,英国的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消费的原棉占世界原棉产量的50%。占世界人口2%的联合王国,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工业生产潜力的40%~45%[13]。
获取土地和劳动力等物质利益,这是就帝国产生的一般动因和主要动因而言的。就历史上各个帝国产生的具体动因和直接动因而言,则往往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帝国建立和扩张的直接动因是为了推广自己信奉的价值,有些是为了皈依异教,有些是出于报国家或民族之仇,有些是出于征服带来的荣耀,有些则是出于国家领土安全的考虑。
帝国是人类追求所谓“文明”“理性”和“公理”的结果。“帝国主义者如何解释自己的行动?主要来说有两条基本的理由:一是帝国主义者所谓的‘文明使命’,二是他们在本质上具有自然优势的理论。上述两个理由相互交叉,互为引证”[14]。亚历山大在建立马其顿帝国时,一直处于不停的征战之中,似乎从来没有“班师回朝”的计划。相反,要不是士兵集体罢战,他可能还会继续前进。当征服波斯帝国,占领巴比伦王朝时,他把帝国的首都也迁至巴比伦;当马其顿军队占领埃及后,他又在埃及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亚历山大的内心世界深刻地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他建立帝国的主要目的,是拯救他心目中的“野蛮人”,将“先进的”希腊文明带给“落后的”非希腊城邦。亚里士多德认为,唯有希腊人才是文明理性的民族,其他外邦人都是野蛮人,至少不能与希腊人相提并论。他对人类德性和理性的赞美,事实上只限于希腊人。他明确说,希腊人本性上是自由人,而外邦人本性上是野蛮人,他们是天然的奴隶。他还用理性征服野蛮的正义,去论证希腊人征服异族人。在他看来,如果说自由人统治奴隶是合乎自然正义的,那么希腊人统治野蛮人也是合乎自然的。不能不说,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希腊种族优越论,对后世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欧洲的种族优越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或许是受其种族优越论影响最早的人,他把对亚洲和非洲的大规模军事征服都看作是文明对野蛮的战胜[15]。亚里士多德曾告诉过亚历山大大帝,要待希腊人如自由人,待“野蛮人”如奴隶。所以,“每一次离希腊更远,亚历山大就越来越不像是个希腊人,倒是越来越像是个野蛮民族的国王了”[16]。亚历山大的这种帝国逻辑,在后来的罗马帝国扩张中再次发生作用。著名诗人但丁公开宣扬:“最高贵的民族理应高居其他民族之上;罗马民族就是最高贵的民族;因此,它应该高居其他民族之上”“罗马人建立帝国”就是“合乎公理的”。[17]
宗教信仰也是历史上不少统治者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重要原因。绝大多数西方的帝国扩张与宗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传播宗教真理,消灭或征服异教徒成为帝国对外征战的重要借口;另一方面,捍卫宗教真理,维护教徒利益,也成为反击外国侵略的响亮口号。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较量和博弈,与历史上多数西方伟大帝国的兴亡直接相关。著名的十字军东征,最早就起源于基督教国家进犯伊斯兰国家,先后9次十字军东征的时间跨度达200年之长,东征的主要对象就是试图夺回被伊斯兰教占领的广大地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拜占庭帝国为了收复被伊斯兰教占领的中东和小亚细亚领土,第二次和第三次东征都是由神圣罗马帝国发动的。传播伊斯兰教也同样成为伊斯兰统治者进行对外扩张和征服的重要原因,一时无可匹敌的奥斯曼帝国在其崛起的过程中,伊斯兰教就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来说,“帝国的领土便是伊斯兰的领土,帝国的君主便是伊斯兰的巴底沙赫国王,帝国的军队便是伊斯兰的士兵,帝国的宗教首领便是伊斯兰的谢伊赫教长,帝国的人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自己是穆斯林。”[18]总之,“奥斯曼帝国,由奠定直到灭亡始终是一个致力于促进或保卫伊斯兰教权力与信仰的国家”[18]21。
近代以后,一些帝国狂热分子把地缘政治学中的“生存空间”(living space)理论用作扩张和征服别国领土的理由。按照这种理论,国家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有一个生长发展过程,只有到达某一个特定的空间值,国家这个有机体就进入最安全和最有活力的阶段。简言之,建立强大的帝国,对外进行殖民和扩张,是国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国家需要拥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才能使自己处于安全和繁荣的状态。这种“生存空间”理论,在近代以后成为一些西方列强走向帝国之路的重要原因,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希特勒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一般认为,“生存空间”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被称为“政治地理学之父”的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Ratzel Friedrich),他提出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被公认是“德国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理论来源”。拉采尔认为,国家有机体处于不断生长的过程中。它与其他生物一样也具有幼年、青年、壮年、老年等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生长在空间上有三种表现:一是国家的边界,其变化是多个国家相互竞争形成的几何空间;二是领土的稳定性,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领土稳定性越强;三是空间的生长,民族集体不断寻求边界的外移与空间的扩大。拉采尔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生存空间”理论在德国和日本受到了法西斯统治者的追捧,成为德国和日本进行军国主义扩张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德国,这种循序渐进的帝国主义实践通过两步展开,首先是人口转移和民族清洗,然后是农业殖民化以及重建真正的德国生存空间。纳粹德国通过对外战争积极扩展空间实体,同时通过驱逐、奴役和杀戮其他种族霸占空间资源”[19]。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正如国家产生是人类作为“政治动物”的必然结果一样,帝国的产生也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倾向。例如,约翰·达尔文认为,人类社会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交换和分工;另一种倾向就是组成帝国的权力体系:“人类社会的第二个倾向,乃是大规模积聚权力,亦即建造帝国。事实上,以民族为基础建立自治国度,要克服文化或经济吸引力的强力拉扯,殊为不易,因此,将不同民族族群统归一人统治的帝国,一直是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会自然发展出的政治组织模式”[9]24。显而易见,帝国与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国家作为一种公共秩序体系和阶级统治的工具,确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避免人类陷于自相残杀的必要工具,因而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帝国本质上是掠夺和征服的产物,是外部强制的结果,而不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倾向。其实,达尔文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接着说,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就是掠夺和征服:“欧洲帝国主义的最大特色,是征用和剥夺。他们征用土地来满足长途贸易催生出的对种植园和矿场的需求。基于同一理由,殖民者从数千英里外贩运奴隶以满足新增的劳动力需求。殖民者称原住民不懂得善用手中的土地,将他们驱离家园,剥夺他们的财产权”[9]24。
杰克·施奈德对帝国扩张的动因和理由有过系统的研究。他把历史上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帝国建立和拓展的原因分为三类:“现实主义”的解释,强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的迫切要求;认知(cognitive)解释,强调在战略评估中所发生的纯粹思维方式的错误;以及国内政治方面的解释,强调利益集团、统治阶级以及它们所提出的战略意识形态。他自己认为国家对外扩张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他称为三种“帝国的迷思”:第一类帝国迷思是累积性收益。根据这种观点,征服可以增加权力,因为征服可以增加人力和物质资源,而这些资源在与其他大国所展开的进一步竞争中,可以被加以利用。第二类帝国迷思认为,最好的防御便是不断进攻。通过采取进攻性行动,可以在帝国的边缘地带获取累积性的收益,而被动则会带来累积性的失败。第三种帝国迷思是,施加威胁以使其他国家屈从。在这些“帝国迷思”中,核心的迷思是认为“国家的安全只有通过扩张才可得以维护”。但他自己最后的结论是,“大量证据表明,实际上正是一国的侵略政策才损害该国的安全”。[20]
三、帝国的兴衰
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发达还是落后,世界各国的许多统治者和民众都有拓展国家领土,进行对外征服,称霸地区和世界的“帝国梦想”或“帝国迷思”。但要使统治者和民众的帝国梦想变成帝国现实,仅有开拓疆土、征服他国的主观动因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进行扩张殖民和征服敌国的实际能力。没有这种实际能力,贸然进行对外战争,不仅难以实现帝国梦想,很可能国破人亡。如果实力不足,即使帝国建立起来了,很可能也是短命的。“理论上,各种帝国都不可避免会遭遇过度的压力、负担,以及突发的危机,并最终垮台。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帝国能永久不灭”[9]487。因此,研究帝国的兴衰,特别是影响帝国兴亡的因素,是帝国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人们通常所说的以史为鉴,其实主要就是找到国家崛起和衰落的原因,探寻国家兴衰的一般规律,从而给今天或未来的统治者作为鉴戒。
毫无疑问,每一个帝国的兴亡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具体原因,因此,对特定帝国的兴亡必须做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然而,个性背后有共性,帝国的兴亡同样也有着共同的要素,也要遵循普遍的规律。约翰·霍尔(John A. Hall)说:“特定的帝国都有其特定的终结。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帝国的衰落有着某种确定的模式”[8]530。从历史上那些强大帝国的兴亡中概括出普遍性的因素和规律性的现象,正是帝国研究者们的一个关注重点。霍尔自己认为,道德的腐败堕落、经济的衰退、僵化的制度、国家与社会的分裂、民族主义的兴起、过度的对外扩张等,是导致帝国衰亡的普遍因素。约翰·达尔文从帝国本土核心地区民心的丧失、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帝国统治合法性的流失、经济和环境的灾难性风险、统治机器的臃肿无效、财富和技术优势的丧失、帝国权贵的派系争斗,以及外部战争等更广阔的视野概括了决定帝国兴衰的共同因素。
总结已有的大量关于帝国兴衰的研究成果,反思历史上诸多强大帝国的兴亡经验,不难发现决定性影响帝国兴衰的若干普遍因素。
古往今来,所有帝国崛起和扩展的首要的和直接的因素,几乎毫无例外地要归功于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除了哈布斯堡帝国等极个别的例外,帝国崛起的基本途径就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武装占领和军事征服,这就首先要求母国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作战技术和指挥体制,以及相当规模的战斗人员和后勤保障设施。吉尔平说:“帝国的建立和政治统一的显赫年代总是同这样一些军事革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使这个或那个社会拥有超过防御国的大规模进攻优势。”[21]古代的亚述帝国是这样,近代的大英帝国也同样如此。古代亚述帝国不仅拥有当时最先进的骑兵,而且已经建立了常备军,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军队是古代帝国实现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服的基础与核心。亚述国家依靠着一支勇敢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在种族混杂、强国林立的西亚地区生存并崛起。在其最辉煌的3个世纪中,亚述军队在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所向披靡、战无不胜。”[22]紧跟其后的波斯帝国也一样,在大流士一世的改革后,波斯的军队已无敌于周边国家,从而成为“波斯帝国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和对外扩张的最主要的支柱”[23]。罗马帝国的崛起,也同样得益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罗马不仅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且建立了先进的兵役制,有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职业化军队。罗马人正是依靠威名远播的罗马军团进行武力扩张,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24]。近代大英帝国的兴起同样依靠其强大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其强大的海军。在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海战中,英国海军战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此后英国的海军替代西班牙,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从而助其建成了“日不落帝国”。
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帝国扩张和兴起的首要原因,但一个国家之所以拥有先进和强大的武装力量,背后通常还有其他更加深层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先进的经济和科技。因而,从根本上说,帝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崛起并得以长期繁荣的决定性原因,是一个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经济和科技对帝国兴起的决定性作用,到了近代以后便日益明显。科技的水平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武器装备和战争保障的水平,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水平。显而易见,长矛大刀敌不过机枪大炮,战马推车敌不过坦克飞机,而不同的武器装备代表的是不同的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水平直接相关的则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越高,生产力水平也越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就越强大。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制造更多的武器装备,供养更多的职业士兵,提供更好的后勤保障,从而拥有更强的军事实力。因此,许多学者更加看重经济力量对于国家强大和帝国霸权的决定性作用。英国帝国主义者利奥·艾默里曾警告说:“取得成功的大国将是那些拥有最强大的工业基础的国家”“那些拥有工业实力和科学创造能力的民族将能战胜所有其他民族”。[13]255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最后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明确地把科技水平和经济力量置于军事力量之上。他说,其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尔后它影响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各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其二,经济增长速度不平衡对于世界各国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具有长期重大的影响。“经济繁荣并不总是或立即转化为军事战斗力,因为这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从地理条件、民族精神到指挥才干和战术能力。然而事实表明,一切世界军事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都是生产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后的必然结果。而且国际体系中各个帝国和国家的兴衰无不取决于主要大国战争的结局,胜利永远属于拥有最大物质资源的一方”[13]538。
比起军事力量、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来,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对于帝国崛起的影响则更为深刻。一方面,纵使一个国家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没有先进的兵役制度、军事指挥体系和后勤保障体系,同样逃脱不了战败的命运。另一方面,即使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时占领或征服了其他国家,如果没有合适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制度,这样的帝国也不会长久。更进一步说,只有当一个国家拥有先进的精英选拔制度、政治决策制度、权力分配与制约制度、生产和交换制度、贸易和税收制度,一个国家才会涌现大量杰出的政治、科技和经济精英,才能防止帝国最高权力被庸人滥用和误用,才能避免最高决策者对帝国犯下灾难性的错误。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罗马帝国不仅有先进的军事制度,而且也拥有行之有效的行省制度、总督制度、宗教制度、税收制度和分配制度。罗马帝国早期的元首制度和元老院制度,能够保证帝国的最高统治权掌握在素质较高的元首手中,而且其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所以出现了“五贤帝”和帝国的长期辉煌。近代的大英帝国率先在世界上建立君主立宪制、代议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极大地有助于大英帝国的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使英国成为世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先驱者。
相反,马其顿帝国、蒙古帝国和拿破仑帝国,虽然曾经异军突起,一时无敌于天下。但是,它们都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先进的精英选拔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随着帝国创建者的消逝,整个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成为短命的帝国。以马其顿帝国为例,亚历山大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建立起了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其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均雄踞欧亚大陆。按照历史上帝国衰亡的周期,如此强大的帝国即使开始衰落通常也会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少则一二百年,多则几百年。但亚历山大帝国的历史却只有短短的13年,是历史上最短命的伟大帝国。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最高权力产生制度。正如一位专家所分析指出的:由于马其顿继承制度的不完善,在亚历山大去世后,王位继承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这逐渐加大了继承者之间的离心力。虽然依据马其顿的继承传统把亚历山大四世和腓力三世推上了当时的政治舞台,立为国王,但因他们缺乏执政能力反而更加速了王室的衰落。王室的衰落使其对继承者的约束力和向心力一点点地减弱,以致他们相互征战,最终导致帝国的分裂。亚历山大帝国毕竟是突然崛起的帝国,对帝国的统一与管理从自身统治制度和民众心理上都缺乏必要的准备,因此,对于如此庞大的帝国,在缺少凝聚力和向心力时,帝国的分裂也就不可避免[25]。
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素质与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历史上常有一些弱小的国家突然令人惊讶地崛起成为帝国,另一些强大的帝国则令人意想不到地轰然崩塌。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往往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品性和能力直接相关。马其顿帝国、蒙古帝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常常又被称为亚历山大帝国、成吉思汗帝国和拿破仑帝国,之所以用帝国创立者的名字命名,主要是因为这些帝国的崛起,与这几位最高统治者个人的雄才大略密不可分。亚历山大、拿破仑和成吉思汗都被公认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这些帝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天才统帅,帝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系于他们个人的命运。当他们死亡或失败后,帝国也随之衰落。古罗马由共和国转为帝国,并且创造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罗马帝国辉煌,与帝国创始人屋大维个人非凡的领导才能紧密相连。屋大维通过大刀阔斧的政治和行政改革,从根本上重组了罗马的政治秩序,创立了确保“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长治久安的各项制度,不仅将帝国的全部权力集于一身,而且赢得了贵族精英的充分信任,使“罗马迎来了它长期稳定的统治期”,屋大维自己也因此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这一至高无上的称号[26]。
重大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极大地改变帝国的命运。国家的战略决策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重大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配置,一旦国家的发展目标定位错误,或者重大资源配置失误,那么,对内就会导致经济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综合国力薄弱;对外就可能误判国家的战略盟友或战略对手,甚至发动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错误战争。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先于英国而崛起的全球性帝国,但很快就被大英帝国取代了。有些学者通过比较分析后得出结论说,正是因为不同的殖民战略、产业战略、贸易战略、人才战略和技术战略,才导致了西班牙的衰落和英国的崛起[27]。在帝国的对外战略中,“过度延伸”和误判战略对手也经常导致命运的转折。吉本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讨论了“过度延伸”(overstretch)的问题,他认为一味地进行领土扩张,最后必定导致帝国政权鞭长莫及和尾大不掉的统治失效。对于传统帝国而言,“帝国过度延伸,意味着补给线的延长;补给线越长,越容易遭受攻击。帝国在疆域上将触角伸得越远,留给反抗者以小股力量即可攻破的靶子也就越多。通过不断对这些薄弱点进行攻击,日削月割,也可最终重创帝国”[26]175。由于误判战略对手而贸然发动战争,也是帝国崩溃的原因。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错误地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就大大加速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彻底崩溃;而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迅速失败,也与其误判美国的力量而偷袭珍珠港直接相关。
地缘政治也是影响帝国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地缘政治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对国民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的影响。地缘政治一般通过三种方式对帝国的命运产生影响。一是帝国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二是周边国家的状况,三是同一时期其他霸权国家的实力。帝国的霸权意味着对其他国家的征服和统治,所以,一个地区以内通常难以共存两个以上的霸权国家。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其实也是一个地缘政治引发的帝国霸权问题。如果一个区域内已经存在一个帝国霸权,同一区域其他国家的崛起通常意味着与原先帝国的战争。因而,有些专家认为,人类最早的帝国之间战争,就源于地缘政治的因素:“在公元前1286年5月,在如今叙利亚的奥伦提斯(Orontes)河畔发生了一件大事,堪称是古代世界最波澜壮阔的事件之一。如果要控制北黎凡特,卡叠什(Kadesh)城堡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于是乎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两个帝国之间在此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其中一方是埃及,当时正处于新王国时期第十九王朝统治下,其军事力量正处于崛起中。……他的诉求受到了来自一个强大的安那托利亚帝国的挑战,这个帝国是建立在哈梯(Hatti)王国的基础之上的”[28]。
历史上不少帝国的崛起和衰亡,表面上看通常与某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或某个统治者的生死相关联,具有某种偶然性。事实上,所有这些偶然性的背后,都是一系列必然因素的综合。换言之,帝国的兴亡和衰落有其必然的规律,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当某些条件具备时,帝国就会产生和崛起,当某些条件不复存在时,帝国就将无可奈何地衰败。对于所有帝国的兴衰而言,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军事力量,而最根本的因素则是国家科技和经济实力。除此之外,地缘政治环境、国家的战略决策、最高统治者的素质、国民的精神状态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帝国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保罗·肯尼迪的分析是对的:“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力绝非仅在于它的武装部队,而且还在于它的经济和技术资源,在于执行对外政策时的灵活性、预见性和决心,在于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效率。这种力量尤其在于其民族本身,在于它的人民,他们的技能、精力、志气、纪律性、创新精神,他们的信念、信仰和幻想。而且,还在于将所有这些因素相互联系起来的方法。此外,对一国的国力还不能仅从它本身孤立地去考虑,还要联系该国的对外或帝国义务,联系到别国的国力来考虑”[13]255。
概而言之,20世纪晚期国际学术界对帝国研究的重新关注,既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又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深化对帝国的研究,不仅对于探索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探索全球化时代重建基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对帝国的产生和兴亡规律的研究,是帝国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帝国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结构,帝国的本质是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征服、占领或统治,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就是夺取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物质利益,但所谓“文明”的扩张、宗教信仰的传播和对“生存空间”的追求,也在帝国的产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影响和决定帝国兴衰有众多的因素,其中最主要因素是国家的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综合国力、政治制度、战略决策、领袖品性、国民素质和地缘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帝国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崩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虽然民族国家体系并没有带来理想的国际秩序,而且全球化又对主权国家体系造成了重大挑战,但帝国本质上是对他国的征服和剥夺,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帝国作为一种国际性的等级秩序体系,建立在民族不平等的基础之上,与人类自由平等的普遍价值和民主进步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此外,在政治多极化的当今世界,任何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也没有能力单独构建一个新的帝国体系,即使美国也不例外。因此,帝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把人类和平与全球秩序的希望寄托在梦幻的“帝国想象”中是完全不切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