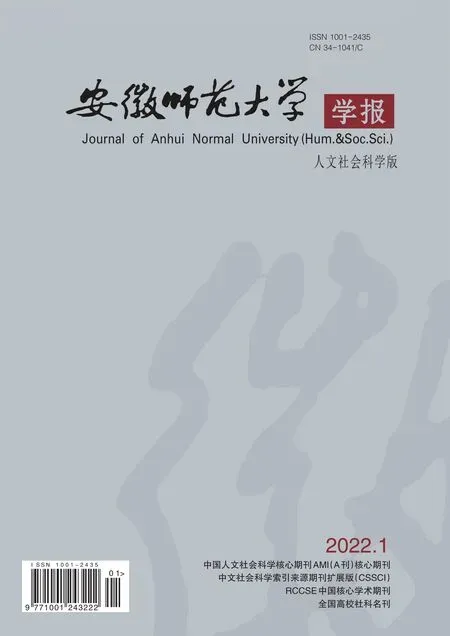民国时期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述论*
黄华平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民国时期的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自清末开始萌发至北洋政府交通部召开铁路运输会议之时始成风气,全面抗战爆发后被迫中止,是近代中国政府治理铁路运价的基本政策,也是铁路运价管制的初次尝试。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这一时期“运价统一”政策的内容既包括统一国有各路纷乱的运价规制和运价标准,也牵涉到如何将国有各路分散的运价管理权集中于中央铁路主管机构。其中,控制国有铁路运价权是这一政策的核心和关键。目前学界关于中国铁路运价管制问题的研究,较为关注的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铁路运价管制体制的改革,使之走向市场化;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欧国立:《运输市场变迁与中国铁路市场化改革》,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年版;魏际刚:《新时期深化铁路体制改革思路研究》,《发展研究》2016年第3期,等等。关于近代中国政府的铁路运价管制问题却鲜有探讨,涉及到该问题的一些研究且多持批判的和否定的态度,与客观不符。②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欧国立:《探究铁路经济问题》第2 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宋希斌、熊亚平:《近代中国铁路货等运价制度变迁初探(1915-1937)》,《兰州学刊》2012年第7期;黄华平:《论国民政府时期的铁路运价治理》,《历史教学》2012年第9期,等等。基于此,论文拟从主要动机、施行过程和影响三个层面对民国时期的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进行考察,以期对其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的主要动机
运价不仅是铁路“运输事业经营好坏与否之重要媒介与因素”,③张蒪:《铁路运输学理论与实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8页。更影响到“国家之经济、民生之繁荣、实业之进展、文化之发扬。”④马廷燮:《我国各路制定运价之史的分析》,《交通杂志·铁路运价问题专号》1934年第2卷第2-3期,1934年1月。这就决定了在制定铁路运价政策时需要兼顾多方面的因素。民国时期,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的产生,既包含了经济和民生的问题,也牵涉到政治问题。
首先,扩充铁路业务,发展国民经济,国有铁路实行“运价统一”势在必行。清末民初,由于受制外国资本的控制,中国国有各路不仅货物分等、运价权度不同,及“各路基本运价既各不同,而各等间之比率,全线段落之划分,递远递减之比率,与夫整车与零担间之比例,亦均彼此互异。”⑤沈奏廷:《吾国铁路运价之现状》,《铁道》1934年第5卷第18期,1934年6月21日。货物分等方面,京奉、道清和粤汉三路分为三等,京绥、沪宁、津浦、吉长和沪杭甬分为四等,株萍和1910年后的京绥铁路分为五等,而法国资本所涉及的京汉和汴洛两路则为六等,正太为唯一不分等的铁路;运价计量方面,里程的计量单位有英里、法里和华里,使用英里者包括京奉、津浦、沪宁、沪杭甬、道清、广九和吉长等路,使用法里者包括京汉、汴洛和正太等路,而株萍和京绥等路则使用华里。货物重量的计量单位也比较混乱,京汉、汴洛、正太等路使用法吨和启罗(法斤),而京奉、京绥、津浦、沪宁、沪杭甬、道清等路则使用英吨和英镑。各路的基本运价率更是差异甚大,1918年之前,京汉路最低货等每50公斤每公里基本运价率为0.002033元,津浦路为0.0012元,京奉路为0.0025元,而沪宁仅为0.001元,沪杭甬更低,只有0.00048元。⑥马廷燮:《我国各路制定运价之史的分析》,《交通杂志·铁路运价问题专号》1934年第2卷第2-3期,1934年1月。正太铁路1908年客运基本运价率为0.016元/每人每公里,⑦王懋功:《正太铁路运价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交通杂志·铁路运价问题专号》1934年第2卷第2-3期,1934年1月。同期的南浔、株萍两路客运基本运价率则分别为0.0095元/每人每公里⑧范致远:《南浔铁路运价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交通杂志·铁路运价问题专号》1934年第2卷第2-3期,1934年1月。和0.004元/每人每公里,⑨江西省地方编纂委员会:《江西省铁路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比正太铁路低很多,其中株萍路只相当于正太路的1/4。近代中国铁路用“何国款项建筑即采用何国制度,(铁路运价——引者注)既无全国一定之标准,更无各路划之一政策,枝枝节节自为风气,至国计民生实业文化,以及地理之通塞,客货之多寡,固均未曾计及也。”⑩马廷燮:《我国各路制定运价之史的分析》,《交通杂志·铁路运价问题专号》1934年第2卷第2-3期,1934年1月。
运价规制和运价标准的纷歧,在中国铁路没有形成彼此相连的路网之时,没有给各路运输业务以及商旅带来不便或其他直接影响。但随着铁路运输网络的逐渐联结,各路运输业务彼此延伸和扩展,特别是铁路联运业务的产生,各路纷歧的运价就成了问题。因为铁路联运至少是经过两路以上的运输,这就使得旅客及货物经过两路或两路以上者,不仅要在衔接站重新换票、卸货、换车,费时费力,而且“货运等级各路悬殊,全程运费究需若干,能否获利,均难预计……”11沈钟钰:《中国铁道联运事业》,《铁道公报》1929年第7期,1929年6月。铁路联运业务发展的举步维艰,进而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无论从扩充铁路自身的运输业务,还是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来说,国有铁路实行“运价统一”势在必行。正如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车务处课员樊正渠所言:“利用铁路交通以发展国民经济,寰瀛皆然。划一铁路运价以便利商旅,各国无异。此交通政策中必然之趋势,国计民生之首要问题也。世界各国铁路运价无论为国有抑为民有概行划一,而中国各路运价高下不一,各自为政,其扰民病商,为业务发展之最大阻碍也。欲谋善后补救之策,舍全国铁路运价统一不为功也。”①樊正渠:《铁路运价论》,《经济学季刊》1933年第4卷第1期,1933年3月。
其次,救济社会民生,国有铁路实行“运价统一”是重要手段。20 世纪20-30 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国内政治动荡和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影响,出现空前大萧条。因土地高度集中,生产力低下,金融枯竭,农产品缺乏市场和竞争力,价格大跌。据国定税则委员会报告,“上海各种粮食的价格近二年比1931年平均降落了26%,1934年的粮价还在继续跌落。”②钱俊瑞:《中国目下的农业恐慌》,《中国农村》第1卷第3期,1934年3月。工矿业方面,发展更是异常艰难,工矿业龙头国煤业在这一时期受日本煤的排挤,煤价不断下跌,据统计1932年1月至1933年初,在上海市场的中兴统煤由每吨13.50元跌至11.50元,贾汪统煤从每吨10.50元跌至6.70元,贾汪筛块由12.50元跌至7.50元,短短一年时间两矿三种煤价跌幅分别达14.81%、36.19%和40.00%。③李紫翔:《外煤倾销与我国煤工业之前途》,《申报月刊》第2 卷第11 期,1933年11月15日。工农矿业发展的困境,引发了严重的民生危机,许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业生产力衰落,农民生活无着,许多农民由此变成流民。
为摆脱困局,社会各界均寄希望于国有铁路给予工农矿业以运价支持。国民政府铁道部联运处秘书刘传书主张:“为积极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以渡此非常时期起见,对于铁路运价似应抱定使铁路与其他各种实业交相促进,同时开拓之政策,因之对于铁路全体运价高度,主张以全国国有各路为单位,而采用成本主义;对于铁路各个运价,主张打破各路界限,而采用担负力主义。前者所以使铁路运价水准减至较其净利不加限制时为低,以促进其他各种实业之充分发展;后者所以使货畅其流,内可以调剂各地生产之有无,外可以抵制舶来之货物。”④刘传书:《非常时期之中国铁路运价问题》,《铁道半月刊》1936年第1卷第12期,1936年11月1日。地方实力派也加入呼吁国有铁路减价的行列,1929年5月,由山西军阀阎锡山出资的晋北矿务局在大同成立。为疏通晋北煤运通道,以及减轻平绥铁路煤运费用,晋北矿务局多次派代表向铁道部呈文,呼吁减低煤运价格。1929年,阎锡山亲自出面向铁道部游说,希望平绥铁路按照1921年旧交通部所定的运价核收,之后阎锡山又动用私人关系,请动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进行斡旋。⑤佚名:《铁道部减轻晋煤运价经过》,《铁道公报》1930年第34期,1930年1月22日。国民政府也寄希望于铁路减价救济农工商矿各业,1933年11月由实业部召集的国煤救济委员会达成5项救济国煤方案,其中减低铁路运费列为首要。⑥佚名:《国煤救济会拟具救济具体方案》,《中央银行月报》1934年第3卷第1期,1934年1月。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国有各路均奉行“营利主义”运价政策,认为“所有客货运价之厘定,完全以获得最大利率为标准,使铁路每年所获净利,愈多愈好”。⑦刘传书:《铁路运价问题》,《大公报:上海》1936年10月2日,第1张第2版。至于客货能否负担、实业经济发展如何等则并非其所关心。加之国有各路背负巨额偿债压力,并不情愿施以援手,主动减低运价以救济工农矿业。因此,要使国有各路减低运价救济民生,政府当局就必须掌控国有各路的运价管理权,实行集中统一的运价管制,只有这样才能扭转国有铁路原先的“营利主义”运价政策,施行与政府经济政策相向而行的“民生主义”运价。
第三,国有铁路实行“运价统一”,还体现了强化中央集权的意图。民国时期,中国各铁路虽名为国有,但中央对于各路的治理之权却受制于地方势力,非常有限,包括铁路运价定价权在内的铁路管理、经营之权多落入地方势力及其代理人之手。比如,20世纪20年代初,京汉铁路先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失败后,该路管理权随之沦入奉系军阀手中。⑧佚名:《北京杂讯》,《申报》1927年5月5日,第8版。中原大战期间该路管理权一分为三,铁道部仅能管理南段(武胜关以南),中段和北段则为冯玉祥和阎锡山分别控制,1930年该路北段的管理权又遭张学良抢得。①平汉铁路管理委员会:《平汉年鉴》,编者印行1932年版,第26页。京绥铁路这一时期也曾先后被冯玉祥、吴佩孚和张作霖等地方势力所操控,广九和广三两路为广东省政府控制,东北各铁路则为奉系所管辖。这些地方势力,通常会利用操控的铁路运价定价权调高运价,以获得财源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京汉铁路货物运价仅在20世纪20年代内就有4次上调,②胡国本:《平汉铁路运价之史的叙述》,《交通建设》1943年第1卷第11期,1943年11月。京绥路也有2次上调。③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路政编》第9册,编者印行1935年版,第1959-1967页。除此,他们还在运价上加征各色名目的捐税,实为变相加价。因此,国有铁路实行“运价统一”政策,有利于消解地方势力利用铁路同中央对抗,从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由此可见,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是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政治需要。
二、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推行的两个阶段
自清末民初④早在1911年,清政府邮传部就曾谋求对国有各路运价的监管,在其草拟的《路律·车务篇》中规定,国有各路“凡定运费不得逾法令所限之率”、“凡定运费应遵邮传部所颁表式填报核行”,但《路律·车务篇》未及资政院审核,因革命而夭折。参见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路政编》第2册,编者印行1935年版,第1394页。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经历了北洋政府交通部和国民政府铁道部两个阶段。北洋政府交通部时期,召开全国铁路运输会议,注重于运价规制和运价标准的统一;国民政府铁道部时期则以货等运价委员会为主导,重点在于控制铁路运价权和推行“民生主义”运价。
(一)北洋政府交通部时期的“运价统一”
民元以后,随着铁路运输业务的发展,铁路运价问题逐渐受到重视。1914年10月,北洋政府交通部路政司营业科科长黄赞熙向时任交通部长曹汝霖呈文,指出:“(中国铁路—引者注)货物之等级,运价之额率胥由客卿审定,任意高低,倘不力谋统一实行监督,必至路自为政,不但主权旁落,至各(帝国主义列强——引者注)袒其本国商货箝制中国之土货,直以中国铁路专为彼国工商运用之机关,更为其工商之附属品也。将来路线增长,营业日广,此因循不特无形损失甚巨,即是时再行整顿必且著手更难。况货物等级运价高低不能不一。为各国之通例,本部直辖各路局同属国有,所有分等运价,实未便任其自为风气,以妨碍营业之前途。”由此,他向交通部力主:“自应及时改张,以谋(国有铁路运价—引者注)统一实行监督”,并向交通部提议设立铁路运输会为特别机关,集中部、路运输管理人才,谋划对国有铁路运价的管控。⑤佚名:《路政司科长黄赞熙君请设铁路运输会详文》,《铁路协会会报》1914年第25期,1914年10月20日。黄赞熙的提议最初并没有得到回应,直至1917年交通部才采纳了他的意见,同意在部内设立铁路运输会议,作为一个临时性的机构,负责筹划包括统一运价在内的铁路运输业务。⑥《运输会议章程》,《交通月刊》1918年第13期,1918年1月1日。1917年10月28日,交通部颁布《运输会议章程》,规定运输会议由部召集,成员由部内高级职员及国有各路具有运输经验者组成,专事讨论铁路运输各业务之改良及统一。⑦佚名:《本埠新闻·运输会议章程之公布》,《申报》1917年11月8日,第10版。
1918年6月24日,第一届全国铁路运输会议在北京召开,共有64人参会,关赓麟任会议主席,共收到议案46件。⑧交通部:《全国铁路运输会议纪录》(一),国民政府铁道部1936年印行,第13-28页。交通部抓住机会,在会上提出了多项关于统一国有铁路运价制度的议案,要者包括《划一普通旅客运价标准案》《统一各路货物普通运价标准案》《统一货物分等办法案》《划一普通货物运价递减办法案》及《铁路施行法定权度办法案》,足见交通部对统一国有铁路运价的迫切之情。其中,《划一普通旅客运价标准案》,提议客票分为三等,以三等客票为本位,定为每公里一分四厘,以十公里或一角起码;二等客票按三等票价加半倍,以每公里二分一厘为标准;头等客票,以每公里四分二厘为标准;“至如地当冲要,客商往来众多,则酌开通车或特别快车,于原定票价之外量予酌加;如系水运竞争之区域,为招徕客运计则于原定票价之内酌予核减,自可察酌各该路情形,以为增减之标准。”⑨交通部:《全国铁路运输会议纪录》(一),第29-31页。各路代表则以各路情形不同,“一律定价,不无窒碍”为由,反对统一旅客运价,致该案未获通过。《统一各路货物普通运价标准案》主张统一普通货物运价率,六等每吨每公里一分五,五等二分,四等二分五,三等三分,二等四分,头等五分,“倘遇各路有水道竞争、脚力竞争或大宗货物,或新增运输种种特别情形,亦可随时规定专价,以为招徕。”①交通部:《全国铁路运输会议纪录》(一),第71-75页。该案因货物分等标准尚未确定,被延至下次运输会议讨论,此后一直没能形成定论。《统一货物分等办法案》《划一普通货物运价递减办法案》和《铁路施行法定权度办法案》,由于得到了各路局的普遍支持,最终形成决议案获得通过。
第一次全国铁路运输会议后,交通部加紧落实第一次会议所达成的决议案,于1920年2月召开第二次全国铁路运输会议,通过《国有铁路客车运输通则》《国有铁路货车运输通则》和《国有铁路普通货物分类表》,实现旅客运价和货物分等制度的统一,并于1921年由交通部公布施行。国有各路的法定权度公里、公吨制也于同年施行。普通货物运价递减办法,虽经第一次铁路运输会议讨论通过,但只是达成运价递减的原则,各路在递减的计算方式上分歧较大,始未统一。②交通部:《全国铁路运输会议纪录》(二),国民政府铁道部1936年印行,第21页。此后,交通部又先后召开第三次至第七次全国铁路运输会议,交通部也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提出了“设立运价研究委员会”③交通部:《全国铁路运输会议纪录》(二),第97页。、“修订各路货运专价”④交通部:《全国铁路运输会议纪录》(二),第268-269页。、“区分中外货物标准”和“划一各路装卸费用”⑤交通部:《全国铁路运输会议纪录》(三),国民政府铁道部1936年印行,第18-20页。等议案。
(二)国民政府铁道部时期的“运价统一”
国民政府铁道部时期,强化了对国有铁路运价的治理。一是加强了对运价的控制。国民政府建立后,在路政管理上实现了飞跃。1928年10月23日,国民政府通告将原交通部路政司所管的铁道行政事务,单独划出,设立铁道部。⑥佚名:《铁道行政移交铁道部》,《大公报》1928年10月24日,第2版。其下设的管理司(后改称业务司)负责国有各路“客货运价之规定及审核,并修改(运价、货等—引者注)增减各事项”,各路凡涉及货物等级变更、分等表更新以及客货基本运价调整等均须履行法定程序,经业务司备案或批准。⑦铁道部铁道法规编订委员会:《铁道法规类编:上编第一次追加册》,京华印书馆1931年版,第12页。铁道部业务司成为拥有最高铁路运价管理权的行政机构。1932 年7 月,中国历史第一部铁路立法——《铁道法》颁布,该法不仅确立铁道部对全国铁路的管理全权,针对铁路运输与运价,其第11条规定:“铁道运价等第、联络运输或交互通车,除依法律规定外,应依铁道部所定之规章办理。”⑧行政院:《铁道法》,《立法院公报》1932年第40期,1932年8月。由此,铁道部在部、路运价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在法律上得到确立。
二是筹组货等运价委员会。1928年12月13日,铁道部鉴于“货物等级与货运价率,关系尤巨,更不能不详细研究审订”,⑨货等运价委员会:《货等运价委员会案卷:第1卷》,编者印行,出版年份不详,第1页。决定集中铁路系统人才,筹组货等运价委员会。货等运价委员会由理财(财务)、建设(工务)、管理(业务)三司、联运处代表和国有各路车务处处长组成,管理司司长蔡增基担任主席,主要负责对“旅客行李包裹等件之运费、运价及客车运输章程之制度”、“货物产销及市价情形、货物运价、货物分等及货车运输章程之制度”及“铁路运输项下应订运输法之立法根本主义”进行“调查”和“审订”,并向铁道部提出具体建议。⑩铁道部铁道法规编订委员会:《铁道法规类编 上第一次追加册》,国民政府铁道部1931年印行,第8页。1936年,铁道部修订货等运价委员会组织规程,专设货等与运价两个小组。11国民政府铁道部:《修正铁道部货等运价委员会组织规程》,《铁道公报》1936年第1407期,1936年2月27日。铁道部为推动各路进行货等和运价的统一,还要求各路设立货等运价委员会分会。1933年6月,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成立两路货等运价研究委员会,制定《两路货等运价研究委员会组织规程》;12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两路货等运价研究委员会组织规程》,《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3年第685期,1933年2月7日。津浦铁路管理局则于1936年初也设立货等运价委员会。13佚名:《津浦路设立货等运价委员会》,《铁道公报》1936年第1390期,1936年2月7日。
货等运价委员会虽不是铁道部常设机构,但由于该会委员多为部、路管理铁路运输业务的高级职员,部分委员业务经验丰富,诸如铁道部业务司专员许传音、广九铁路管理局副局长郑宝照、①货等运价委员会:《货等运价委员会案卷》第5卷,编者印行,出版年份不详,第27页。铁道部业务司运输科科长刘传书和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吴绍曾②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铁道部令第550号》,《铁道公报》1932年第274期,1932年6月15日。等均列名其中。他们所提的建议对铁道部的运价决策至关重要,且该委员会存续时间长达8年之久,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推行“运价统一”的主要机构。经货等运价委员会提议,1929年铁道部决定废除过去“五十公斤”“公吨”和“整车”三种货物运价,统一为“整车”和“不满整车”两种;③货等运价委员会:《货等运价委员会案卷》第5卷,编者印行,出版年份不详,第27页。并要求各路“不满整车”运价率照“整车”运价率加价标准统一为30%。④吴绍曾:《铁路货等运价之研究》,新业印书馆1936年版,第264页。1929年11月,由货等运价委员会拟定的货物特价专价适用原则6条,经铁道部公布在国有铁路统一施行。⑤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铁道部训令第2167号》,《铁道公报》1929年第12期,1929年11月。1930年,经过货等运价委员会调查,北方的陇海、平绥、平汉和津浦4路客运基本运价率相差不大,铁道部遂规定自1930年3月统一上述四路客运基本运价率为0.017元每人每公里。⑥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铁道部训令第3247号》,《铁道公报》1930年36期,1930年1月27日。1933年之后,铁道部又将京沪、北宁、道清、浙赣、津浦和平绥等路的旅客基本运价率统一减低为0.015元每人每公里。
三是搭建其他运价治理平台,推进“民生主义”运价。除筹组货等运价委员会外,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铁道部还陆续召集多次关涉国有铁路运价治理问题的会议。1931年3月1日,铁道部筹组发起全国铁路商运会议,出席会议代表约160 人,铁道部、国有各路和各商会代表就各路客货运价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改良运价议案76件,占议案总数的42%,各方达成5项改良运价原则,并重新修订货物特价专价原则7 条,强调货物特价专价应与国民经济政策相一致。⑦铁道部铁路商运会议办事处:《全国铁路商运会议丛刊》,编者印行1931年版,第281-282页。铁道部还延续前交通部旧制,于1931 年和1935年分别召开第8次和第9次全国铁路运输会议,在第8次会议上又新增货物特价专价原则4条,“扶值实业”“提倡国货”成为这一时期货物特价专价的主要原则;⑧章静斋:《我国铁路特价专价研究》上篇,《铁路月刊-津浦线》1935年第5卷第4期,1935年4月31日。在第9次会议上则通过两项决议案,一是货物由六等扩充为十等,一是“各路客票基价,改为每公里最高以一分五厘为限”。⑨魏榕:《第九次全国铁路运输会议述要》,《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月刊》1935年第3卷第6期,1935年6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有各路先后沦陷,国民政府铁道部也于1938年初裁并,从民初开始推行的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被迫画上句号。
三、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的影响分析
经过北洋政府交通部和国民政府铁道部数年的推行,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的影响直接或间接的有所显现,包括对铁路自身,也包括对社会经济和民生。首先,在一定程度扭转中国铁路运价混乱的局面。一是铁路运价权在法律上或形式上集中统一于铁道部;二是包括客货分等,铁路公里、公吨制度,货物特价专价适用原则等运价规制实现统一,货物“递远递减”原则得到确立;三是部分国有铁路旅客运价率也趋于一致。当然,这与政府当局所期待的控制国有铁路运价尚有距离,因为国有各路还牢牢掌控着客货基本运价率的自主权,货运“递远递减”率和特价专价优惠办法也由各路自定,铁道部拥有的铁路运价管理权实质上落空,客货基本运价率、客货优惠运价类别及减价办法等均无法统一。因此,客观上来讲,“一些国家的侵占以及其他政治、经济等原因造成期间的历届政府从未有过对铁路完全意义上的拥有和管理,在运价体制上也从未有过统一”。⑩欧国立:《探究铁路经济问题》第2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其次,促进了国有铁路运输业务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初期,随着铁路货物分等和运价权度等运价规制的统一,铁路运输业务特别是货物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统计数据显示,1919年国有各路货物运量为386 310万延吨公里,进款48 727 508元,1920年分别增加至454 094万延吨公里和52 450 092元,1923年货物运量和进款达这一时期最高峰,分别为513 674万延吨公里和73 429 787元。①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07-210页。其中,国有各路货物联运业务增长尤为明显,1921年,国有各路货物联运业务进款从1920年的545 047元,增至1 261 232元,增长231.4%,1922年和1923年又分别增加至5 595 932元和9 010 165元。②沈钟钰:《中国铁道联运事业(续上期)》,《铁道杂志》1929年第8期,1929年7月。此后由于军阀混战不断,路政混乱,铁路运输业务逐渐衰落。③麦莱:《中国铁道联运事业的回顾与前瞻》,《中华月报》1935年第3卷第7期,1935年7月。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铁道部在加强对铁路运价控制的同时,注重于推行“民生主义”运价。为恢复、发展铁路联运业务,制定国有各路统一的《联运货物运价递远递减办法》,规定除原各路的递远递减减价外,联运货物还另外享受1%至20%减价,即501-600 公里减收1%,以后每增加100公里递减1%,至2 500公里以上递减20%。④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铁道部训令第6732号》,《铁道公报》1933年第679期,1933年10月6日。次年12月,铁道部再次调减联运货物递减率,将起点公里数由501调至301公里,递减率至多增加至22%;⑤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联运处:《铁道部联运处通令运价类一号》,《铁道公报》1936年第1448期,1936年4月16日。为挽救国内工农矿业,扶植实业,调整了货物特价专价原则,并实行各类农工商矿业大规模减价措施。叠加这一时期其他铁路运输制度的改良,⑥佚名:《实行铁路货物负责运输经过》,《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3年第741号,933年8月8日。包括铁路客、货运输业务在内的铁路运输业务均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国有各路客运人数由1931 年的43 499 000人,增加至1936年的46 920 000人,延人公里数由4 340 047 370增长至4 348 850 000;国有各路载运货物量由1931年的25 225 000吨,增加至1936年的34 364 000吨,延吨公里数也由4 457 467 000增加至6 488 798 000。⑦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事业公司1948年版,第281-284页。
再次,推动了工农矿业的复苏。20世纪30年代,针对国民经济的衰落,铁道部围绕减低工农矿业货品的运价,强化对国有铁路运价监督,推动铁路运营政策由“营利主义”向“民生主义”⑧所谓“民生主义”运价政策,即主张铁路运价应以社会经济和民生问题为主旨,实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运价。参见韦以黻:《民生主义的铁路运价政策》,《交通杂志·铁路运价问题专号》1933年第2卷第2-3期合刊,1933年1月。转变。国有各铁路管理局也逐渐认识到振兴农工商矿各业的重要性,纷纷加入“救济国煤”和“复兴农村”的行列,推出诸多工农商矿业优惠运价,以重振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其减价措施主要有:一是根据铁道部1931年修订的特价专价适用原则,广泛施行铁路特价专价。津浦铁路管理局1933 年推出的特价货物达60 余种,专价亦有20余种,涉及中兴煤矿公司、开滦矿务局、山东丰华制针厂及利华铁矿公司等。⑨津浦铁路管理委员会车务处:《津浦铁路货车运输价目表》,编者印行1933年版,第43-51页。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1934年推行的特价货物也达60余种,诸如绍兴酒、高阳土布及沿线的蚕茧均在列,获得专价的公司或商户则包括永利制硷公司、开成造酸公司、利生铁工厂和东亚毛呢公司等;⑩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车务处营业课:《京沪沪杭甬铁路货车运输价目表》,编者印行1934年版。二是降低工农矿业产品的货等。货等之高低决定运价之高低,以1934年为例,约有30余种农产品获得降等,其中鲜桑叶由二等改为五等,冬瓜、黄瓜、芝麻饼、花生饼、玉米、各种豆类由四等降为五等,棉花子由5等减为6等。津浦路运潼关面粉、平绥路向东运输之国产机制面粉、小麦、荞面等由四等减为五等。11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一年来复兴农村政策之实施状况·一年来中央对农村复兴之计划及实施》,《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4年第2卷第3期,1934年8月26日。诸多工矿企业生产的货品也获得降等,山东丰华和青岛冀鲁制针厂所出之针由二等减为三等,天原电化厂所出之盐酸、烧碱、漂白粉3项均按原定等级减低一等收费。12俞棪:《最近三年铁路减低运价述略》,《铁路杂志》1935年第1卷第2期,1935年10月31日。经过系列运价优惠,农工矿业产品的铁路运输成本有了明显下降。据铁道部业务司司长俞棪所述,1932年中国国有各路货物基本运价率平均为0.0171元/每吨每公里,1934年则显著下降至0.0148元/每吨每公里。13俞棪:《最近三年铁路减低运价述略》,《铁路杂志》1935年第1卷第2期,1935年10月31日。运输成本的下降,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和销量,自1930年代中后期国民经济开始呈现阶段性的复苏迹象,社会经济渐趋活跃。①《交通银行史》编委会:《交通银行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6页。
最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民生。这主要表现在交通和铁道两部利用运价管理权,针对涉及社会民生、赈灾救济等客货运价给予格外优惠。比如,20世纪20-30年代为使贫苦、受灾被难的人口前往边疆开垦、谋生,交通和铁道两部先后实行廉价的移民票。1925年,交通部制订京奉、京绥两路移民特价票临时办法,对于前往满蒙殖边移民及其家属,铁路运费酌减四成或五成,幼童在12岁以下者免费,其农用器具及行李之运费则概行免收。②佚名:《国内要闻·交部优待移民办法》,《申报》1925年4月2日,第6版。次年4月,交通部又联合京奉、津浦、京汉和京绥四路,发行移民减价联运票,规定凡各省区运输人数达二十以上的大宗垦民,经行上述四路,前赴塞北和关东,成人车票一律减免四成。③佚名:《本埠新闻·垦民实边四路减费之厅令》,《申报》1926年4月4日,第14版。1931年,铁道部重新修订四路移民减价联运票办法,并调减运价。④《津浦、北宁、平汉、平绥铁路发售移民减价票规则》,《津浦铁路月刊》1931年第1卷第8期,1931年5月31日。通过国有铁路的运输疏解,大量贫苦人口得以前往东北和西北等地,缓解内地贫苦、受灾被难人口的生存压力,对迁出地社会稳定产生积极作用。为救济各地水灾及旱灾,铁路当局对运送赈济的粮食给予减价优惠。1920年11月,北洋政府交通部颁布《国有铁路运送赈济平粜粮食减免车价条例》,规定京奉、京汉、正太、道清、津浦和京绥等路灾区沿线各车站:“凡运送振济整车物品、粮食前赴灾区,经行国有各铁路,所有该路普通运价全行免收。”⑤佚名:《国有铁路运送振济平粜粮食减免车价条例》,《救灾周刊》1920年第4期,1920年11月14日。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颁布《铁路运输赈济物品条例》,规定赈济物品减价标准则按经行各路之普通货物运价五折核收现款。⑥交通部:《国民政府交通部铁路运输赈济物品条例》,《汉平新语》1928年第1卷第4期,1928年10月1日。这对缓解灾区粮食和物资紧缺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灾区社会的安定。
四、结语
近代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作为彼时国家治理铁路运价的基本政策,无论是其动机,还是其推进措施,均体现政府当局试图控制、统一铁路运价,发展国民经济和维护社会民生的初衷。从实际的结果来看,“运价统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当时中国铁路运价混乱的局面,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保障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近代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客观要求是相契合的,尤其是其实行的大规模“民生主义”运价充分体现了铁路公共产品的属性,具有进步意义。但这种进步意义是有限的,其主要的制约因素即是民国政府的政权势微。近代时期,受制于帝国主义势力及各色地方势力的束缚,民国政府政权处于衰势,这使得国家无法建立运转高效的国有铁路运价管理体制,运价治理政策也就无法有效贯彻。正是由于缺乏国家政权的强有力支持,铁路当局在运价治理方略上,只能进行局部的铁路运价整理,无法实行彻底的、根本性的方法。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要实现“运价统一”最可行的方案是在铁路统制之下控制铁路运价权。《交通杂志》编辑洪瑞涛就曾主张:“欲求我国铁道彻底的整理,非仅需要着人事上的努力,更有赖乎组织的改革,是很显然的事实。管见所及,以为只有采铁道统制的制度,吾国铁道的各项困难问题,才能迎刃而解。”⑦洪瑞涛:《铁道整理与铁道统制》,《湘鄂铁路旬刊》1933年第33期,1933年7月30日。但铁路统制的国家政权基础并不坚实,实际上也根本无实行的可能。
总而言之,近代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是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但在近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注定无法有效实现对铁路运价的管制,也就不可能使铁路运输效益得到充分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