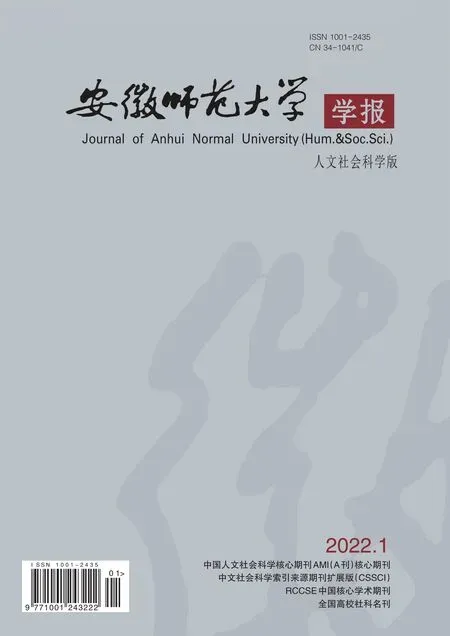“激发忠义,惩创叛逆”
——明代历史小说隐含作者的济世情怀*
江守义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97)
按照布斯《小说修辞学》中的说法,隐含作者是隐含在文本中的作者:“一部伟大的作品确立起它的隐含作者的‘忠实性’,不管创造了那个作者的真人在他的其他行为方式中,如何完全不符合他的作品中体现的价值”①[美]韦恩·布斯著,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这意味着,隐含作者是通过文本建构起来的,离开文本,隐含作者的形象就不存在,这也是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区别所在。真实作者有没有文本,都是生活中的那个人,同一个真实作者,可以在诸多作品中表现出不同的隐含作者面貌。
隐含作者虽然和真实作者区别明显,但真实作者的生活际遇、情感状态和伦理动机,一般会很自然地带到创作之中,从而影响到小说面貌,进而影响到小说面貌背后的隐含作者。由于史传对明代历史小说的影响,真实作者在创作小说时有强烈的慕史情结,形成一种“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①李康:《运命论》,载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页。的创作动机。此处需要说明的有三点:一是真实作者的动机和隐含作者意图的关系。真实作者的动机决定了小说面貌,隐含作者的意图隐含在小说之中,从根本上看,它受到真实作者动机的影响,但隐含作者的意图是从小说文本探寻出来的,与真实作者的动机没有直接关系,当我们不知道真实作者的动机时,仍然可以通过小说文本来探寻隐含作者的意图。二是真实作者的动机和小说文本所体现出来的隐含作者的意图之间未必一致,本文专论隐含作者,一切从小说文本来寻觅隐含作者的意图,不考虑真实作者的实际动机;三是就不同的明代历史小说而言,隐含作者的具体意图有很多,如《英烈传》的歌颂明君、《隋史遗文》的赞扬江湖侠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抨击奸恶,但总体上看,真实作者慕史情结对明代历史小说面貌的影响,导致隐含作者流露出一种“激发忠义,惩创叛逆”②无竞氏:《剿闯小说叙》,载《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懒道人口授:《古本小说集成剿闯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的济世情怀,歌颂明君、赞扬侠义等具体意图也可纳入到这一情怀之中。
一、激发忠义
明代历史小说中,隐含作者往往借助历史人事来激发“忠义”,或以明君贤臣来追怀盛世,或写属下对主人的忠心耿耿、朋友之间的忠肝义胆,或写忠义丧失带来的负面效应。
其一,通过明君贤臣来激发忠义,以示忠义于盛世之重要。历史小说明君贤臣之“忠义”大致可分三类:一是侧重渴望英明君主,二是侧重褒扬贤臣良将,三是侧重明君和贤臣良将的相得益彰。
通过渴望明君来激发“忠义”,往往是借助“忠义”来表达隐含作者渴望盛世的情怀,这体现了明代历史小说的一个特点,很少直接写太平盛世中的帝王,而是写乱世中的明君如何借助“忠义”来走向太平盛世,《三国演义》可为代表。《三国演义》将刘备奉为乱世中的明君,将曹操化成时势中的奸雄,塑造出“拥刘反曹”的隐含作者倾向。就刘备这一明君而言,其“忠”表现为对大汉王朝的尊崇和对大汉子民的爱护(即“仁”),其“义”表现为对待贤臣良将时的儒家风范。刘备对兄弟、对贤臣、对百姓的态度处处体现出一个明君的道德情怀。《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其说是一方君王,不如说是汉中人民的守护神,蜀汉政权也成为隐含作者想象中的乌托邦。作为君王,刘备的“忠义”在尊崇大汉之余,主要表现为“仁义”。“仁义”的结果是:他开创的蜀汉政权虽然谈不上真正的太平盛世,但丝毫不影响他的“明君”形象;他缺乏君主必要的冷静和果断,被复仇冲昏了头脑,为蜀汉政权带来灭顶之灾,也依然不影响他的“明君”形象。隐含作者推崇的是刘备恪守孟子所主张的君民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③杨伯骏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1页。这是刘备被推崇为明君的儒家思想根基。在这种伦理观念下,刘备即使因过失而死,隐含作者表达出来的,也不是对他的责难,而是天妒明君、大厦将倾的悲愤。
通过褒扬贤臣良将来激发忠义,侧重“忠义”在贤臣良将身上的具体表现,以示“忠义”对于盛世之重要。《于少保萃忠全传》可为代表。《于少保萃忠全传》塑造了于谦这样一个“忠义”形象。无论就国家大事还是个人气节来看,于谦都无愧于“忠义”的化身。在国家大事上,他秉公执法、廉洁无私、为百姓消灾弭难;尤其是“土木之变”后,于谦不顾个人利益,力排众议,反对南迁,且日理万机、宵衣旰食,在面对侵略时身先士卒、保国安民。在个人气节上,他洁身自好,生活清苦,即使和同僚结怨,也坚持以民众利益为先。隐含作者对于谦的“忠义”充满敬仰,对于谦的含冤而死充满同情,对于谦的平反昭雪感到慰藉。隐含作者站在儒家“为尊者讳”的立场上把矛头指向了乱臣贼子,认为奸佞为祸致使主上蒙尘,把于谦的不得善终归咎为奸佞构陷,对君王自身没有揭露和抨击,反而通过于谦的平反来间接维护君王。于谦之死在隐含作者看来,并非忠义的穷途,而是对忠义的成全,朝廷的平反谥封最终成为于谦忠义的见证。隐含作者表达的忠义是儒家“君为臣纲”观念下的忠义,通过于谦的忠义来反省激发,表明心志,感奋有识之士,希望以臣之忠义来感获君之仁义,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封建仕途的想象和向往。
借助明君和贤臣良将的相得益彰来激发忠义。由于明君乃天命所归,小说往往以贤臣良将为主,写君臣之间因忠义而互相成全,隐含作者由此表达出对君臣共同开辟盛世的礼赞。《隋史遗文》可为代表。《隋史遗文》主要通过秦叔宝等个体形象的塑造,表达了良将得遇明主、明主依赖贤臣的重要性。秦叔宝初为隋将,先后在来护儿、张须陀、裴仁基手下任职,虽凭借勇力闻名,但并无多大作为,反而多次遭宇文氏陷害,后投奔瓦岗李密,开始君臣合作时期。到瓦岗之后,秦叔宝虽得到李密重用,但李密并非明主,终无法实现明君贤臣的价值伦理;瓦岗之后,几经辗转,秦叔宝投奔李世民,良将遇明主,明主得贤臣,终于成就后来的大唐盛世。小说虽然主要写秦叔宝、尉迟恭等良将事迹,但也强调明主的重要性,否则像秦叔宝这样的英雄空有本领而无用武之地,无法成就一番事业。隐含作者的意图很明显:只有明主和贤臣都讲求忠义,二者相得益彰才能缔造盛世。任何一方不讲忠义,都难成大事。
其二,通过忠义行为和人格品质来激发忠义,以示忠义于为人之重要。忠义不仅存在于明君贤臣之间,也存在于下属和主人之间,甚至朋友之间。就下属和主人而言,这个主人可以是君王,也可以不是君王。隐含作者往往通过下属的忠义行为,来显示忠义对做人的重要性。《三国志后传》中的张宾,作为蜀汉后人,本是“大汉”刘渊的谋士,后奉命辅佐石勒,当石勒渐成气候后,即对石勒忠心耿耿。张宾的人格品质谈不上高尚,但其行为并不卑劣,反而体现出对主人一贯的忠心。隐含作者对张宾的人格品质不置褒贬,但对其具体行为却多有赞扬,借叙述者之口称其“谦虚敬慎,关怀下士,屏绝私恶,以身率物”。①酉阳野史编次,孔祥义校点:《三国志后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52页。张宾总体上仍是一个忠义之人,不首鼠两端。石勒作为刘渊倚重的大将,在拥兵自重后,基本上仍恪守一个臣子的本分,靳准叛乱后,石勒认为自己身为汉臣,“当仗义勠力,以报大仇,讨灭国贼”②酉阳野史编次,孔祥义校点:《三国志后传》,第832页。,在平定叛乱后,得知刘曜“改汉为赵”③酉阳野史编次,孔祥义校点:《三国志后传》,第835页。,才在张宾等人的劝说下,决定“即皇帝位”④酉阳野史编次,孔祥义校点:《三国志后传》,第852页。。他虽有异心,但一直克制到刘曜改汉之后才称帝,此前一直以汉臣自居,说明他总体上仍有对“大汉”的忠心。和他并不纯粹的忠心相比,他的“义”则是一以贯之的。不仅助刘曜灭靳准是“仗义”,他对张宾的敬重,已超出主帅对下属的听从,几乎是以师礼待之:“勒性极悍,惟宾言不敢拂……终宾之世,石勒无过误失败。”⑤酉阳野史编次,孔祥义校点:《三国志后传》,第852页。这也可看作是石勒之“义”。张宾、石勒对“大汉”谈不上忠心耿耿,但没有背叛“大汉”,不失忠义之本;同时,张宾对石勒始终是“忠诚”的,石勒对张宾也始终是“义气”的,在他们身上,忠义主要不是表现在对“大汉”的忠心上,而是表现在做人的道理上。
以忠义行为和人格品质来激发忠义,也可以发生于朋友之间,朋友之间的忠义更能见出忠义对做人的重要性。朋友之间不需要上下级之间所需要的下级对上级的单方面的忠心,需要的是推心置腹的平等的赤诚相待,此时所谓的“忠”基本让位于“义”。《梼杌闲评》中颇具活力的一个人物是侯秋鸿,她原是客印月的侍女,对主人忠心,当客印月和魏忠贤沆瀣一气时,她劝客印月收手,遭到拒绝后自己退出。后来客印月遭诛,侯秋鸿冒死为其收尸,此时的侯秋鸿已成为客印月妯娌,与客印月已无主仆关系。但多年的主仆情分让侯秋鸿甘冒风险,“仗义赎尸”①刘文忠校点:《梼杌闲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43页。,其行为固然有奴仆对故主的忠心,主要则是多年来形影相随的朋友之间的情义。侯秋鸿是小说中与魏党有牵连的幸存之人,或许也是隐含作者对其“义”予以褒扬的结果。
其三,通过丧失忠义带来不良后果,以示忠义缺失之危害。历史往往存在偶然性,一个人的成败与否与其道德水准并无必然关系,忠义者即使道德高尚,也可能下场凄惨,如岳飞;不忠义者即使道德卑劣,也可能一时风光无限,如梁冀。历史小说由于隐含作者的道德倾向,更容易借助人物道德品质和人物结局的张力来激发忠义。丧失忠义者在小说中固然是谴责的对象,但其功业有成,从世俗的层面看他获得了成功。在隐含作者看来,不忠义者即使事业成功,也要受到道德谴责。《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和司马氏均如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在不是人臣所当为,尤其是第六十六回为称“魏王”事,乱棒打死伏皇后,飞扬跋扈之极。李贽在此回总评道:“操贼上弑伏后,神人共愤,今古同嗟。”②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24页。李贽总评从隐含作者意图而来,一个最终事业成功的曹操,被隐含作者和评点者视为人神共愤之“贼”,事业成功也难逃道德审判。当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后,曹氏篡汉得到报应,所谓:“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③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第1441页。毛宗岗一百一十九回回前评说得更加详细:“魏之亡,非晋亡之,而魏自亡之也。何也?炎之逼主,一则曰:我何如曹丕?再则曰:父何如曹操?是其篡也,魏教之也。魏教之,则谓之魏之亡魏可矣。”④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第1432页。司马氏统一天下后,在秉承大汉为宗的儒家信徒看来,对统一的西晋也应该予以谴责。《三国志后传》为“泄万世苍生之大愤”,将本为胡人的刘渊虚构为蜀汉后人,以刘渊灭晋来报西晋灭蜀之仇,这虽然于史实不符,但隐含作者明言,如此做法是为了“解颐世间一时之通畅”⑤《三国志后传·引》,载酉阳野史编次,孔祥义校点:《三国志后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所谓“一时之通畅”,主要即伦理忠义之通畅。第一百六回刘曜破长安虏愍帝,司马氏灭蜀得到报应。曹操和司马氏最终都取得了成功,但由于他们于忠义大节有亏,隐含作者将他们后人的败亡与他们的不够忠义联系起来,以此来激发忠义。
就个人层面看,忠义缺失可以表现为奸诈,也可以表现为貌似忠义而实不忠义。奸诈者在小说中一般是反面角色,隐含作者对之持明显的贬斥态度,忠义缺失往往会带来灭顶之灾。《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有一些无关大局之人行事奸诈,他们没有远大的眼光,为个人得失做出不忠不义之事。第二十回黄巢势败,其侄黄勉想杀之“将功赎罪”,后黄巢自刎,黄勉将其首级献给晋王,并称黄巢是自己所杀,晋王斥其为“不忠、不孝、无恩、无义之徒,败坏人伦”,将其斩首⑥王述校点:《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宝文堂书店1983年版,第75页。。黄勉在黄巢那里是“一字并肩王”,却只顾自己安危,毫无忠心可言,死有余辜。和黄勉不同,历史小说中的有些人物,貌似忠厚,但实际上并不忠义,隐含作者并无明显贬斥,但通过人物行为可显示出隐含作者的不满。《西汉演义》中的项伯,身为项羽叔父,被项羽认为是“为人忠诚”⑦甄伟:《西汉演义》,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却为个人友情,在鸿门宴之前,向张良通风报信,并在鸿门宴中项庄舞剑时在张良示意下保护刘邦,又为一己私情,完全不顾大局,坏了范增大计。此时他虽有与张良之“义”,却无对项羽之“忠”。后又让张良得见韩信所献之策,开韩信归汉之端,可谓因“义”忘“忠”,实是项羽一方罪人。范增死后,项羽“遂立项伯为军师,凡一应大小国务,皆伯管理”⑧甄伟:《西汉演义》,第214页。,但他不识大体,劝项羽放太公归汉,让刘邦无所顾忌;又推荐李左车给项羽,让项羽最终中垓下之围,虽是无心之过,但实乃不“忠”之举。项羽大势已去,项伯即考虑自身,寻求张良庇护。叙述者虽对项伯行为不置可否,但和周兰、桓楚忠心护主相比,此时的项伯显然已是贪图个人安逸之小人,毫无忠义可言,隐含作者的不满也跃然纸上。
二、惩创叛逆
惩创叛逆往往和激发忠义联系在一起,叛逆和忠义可以形成对比,在对比中表现隐含作者的伦理意图。需要说明的是,无竞氏《剿闯小说叙》所说的“惩创叛逆”,是站在“君父之仇”立场上对“闯贼”叛乱所下的断语,但明代历史小说很多是写乱世的历史故事,乱世之中群雄逐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一统天下的理由,每个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都可以认为自己是在“惩创叛逆”。像《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晋王李克用奉皇命平定叛乱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惩创叛逆”;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和刘备所谓的“兴复汉室”,都认为自己的征伐是为国家谋太平,可以说是宽泛意义上的“惩创叛逆”;像《开辟演义》那样以天下大治为旨归,不分君王或臣下,凡有德者之行为即获得褒扬,君王“逆天”行道就合该被臣下推翻,可谓另类的“惩创叛逆”。就隐含作者的伦理意图而言,“惩创叛逆”最终目的仍是为了“激发忠义”,但和直接“激发忠义”不同的是,“惩创叛逆”主要关注的是惩创过程,以此显示隐含作者的伦理意图。
其一,叛逆之危害。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惩创叛逆”,都无法遮掩“叛逆”带来的危害。严格意义上的“惩创叛逆”,一般是王朝末世帝王统治无力的结果,但帝王仍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竭尽全力来戡乱。《东西晋演义》中,五胡十六国乱晋,五胡之间、五胡和晋之间,关系交错,形势复杂,但对晋王朝而言,要维护自身的统治,就必须戡乱。戡乱过程中显示出各方为私利而不择手段,也显示出有人希望在乱世之中浑水摸鱼成就自己的伟业,还显示出世风浇薄、人伦废弛的伦理情形。“西晋卷之三”有李雄夺成都、张方杀长沙王、多人讨伐司马颖、刘渊称汉王、李雄称成都王等事件,各方为一己之利,无所不用其极。“东晋卷之一”有“王敦举兵逆谋反”,想趁乱谋取大位,最终败亡。小说中人伦废弛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西晋卷之一”的“八王相图害”、“西晋卷之三”的“刘聪杀兄”、“东晋卷之二”的“石虎杀刘后石堪”、“东晋卷之三”的“闵冉弑鉴”,兄弟宗族之间,相互谋害,层出不穷;至于刘聪同时立三个皇后①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桓温追求的“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②杨尔曾:《东西晋演义》,第341页。,苻坚同时宠爱慕容冲姐弟③杨尔曾:《东西晋演义》,第385页。等有悖乎儒家规范伦理之举,更是家常便饭。小说虽以“严华裔之防,尊君臣之分,标统系之正闰,声猾夏之罪愆”④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序)》,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为宗旨,但展示的却是一幅道德沦丧的社会画卷。
宽泛意义上的“惩创叛逆”,各方都以自己为正统,以对方为“乱臣贼子”,且各有依据。此时所谓的“叛逆”,基本上是一种说辞,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在各方相互的“惩创叛逆”之中显得混乱不堪。《东西晋演义》中既有以晋为正统的严格意义上的“惩创叛逆”,也有在五胡十六国之间的宽泛意义上的“惩创叛逆”。小说采取多纪元的方式对各国予以平等对待,例如:“东晋卷之二”以后,便频繁出现多纪元,“东晋卷之二”开头,“乙酉,三年(赵光初八年,后赵七年)”⑤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等,对隐含作者而言,多少也意味着各国之间的相互征伐都有自己的道理。《新列国志》中,各诸侯之间相互征伐,一般都打着维护正义的旗号。第九十四回,宋康王自认为英勇无敌,“每临朝,辄令群臣齐呼万岁”⑥墨憨斋新编、《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古本小说集成新列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3页。,齐湣王联合楚、魏伐宋,罗列宋王罪状,“僭拟王号,妄自尊大”⑦墨憨斋新编、《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古本小说集成新列国志》,第2368页。便是其中一条。灭宋之后,齐湣王又要求卫、鲁、邹三国之君“称臣入朝”,田文以“大周虽微弱,然号为共主”要求湣王不要生“代周之志”,湣王则以汤武自比而拒绝纳谏⑧墨憨斋新编、《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古本小说集成新列国志》,第2371-2372页。。齐湣王以宋康王为“叛逆”而惩创之,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叛逆”?隐含作者正是在列国纷纷扰扰的“惩创叛逆”中曲折地表达出自己对世道纲常的期望。
另类意义上的“惩创叛逆”,表面上看,与严格意义上的“惩创叛逆”正好相反,不是帝王戡乱,而是部下以“正义之师”来改朝换代。《开辟演义》中,既有女娲朝祝融平共工,颛顼朝勾龙灭九黎,武丁朝傅说伐鬼方等严格意义上的“惩创叛逆”,也有轩辕灭榆罔、商汤灭夏、周武灭商这种以下犯上的另类意义上的“惩创叛逆”。《开辟演义》以后代事推想史前事,以“历代帝王创业”为框架,以“圣主贤臣,孝子节妇”为肌理①王黉:《开辟衍绎序》,载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页。,善恶分明,有德者十全十美,无德者大奸大恶。同为反对无德君主榆罔,蚩尤虽指出“榆罔不德,人民怨恨”,故“举兵以伐无道”“兴兵与民除害”,仍旧被认为是“兴兵作乱”,因为他本是恶人,“荒纵无度,日肆其恶”②周游:《开辟演义》,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8页。;轩辕以“帝虽不德,汝为臣子,安可纵乱天下”为由,诛杀蚩尤。榆罔不改前非,轩辕以“主君不仁,万民涂炭”为由而讨伐之,灭榆罔后被推为黄帝,因为他“生而神灵……成而聪明”③周游:《开辟演义》,第49-51页。,因其“神灵”和“聪明”,终成一代“德配天道之至”④周游:《开辟演义》,第59页。的明君。但反观轩辕行为,他何尝不是和他所责备的蚩尤一样“纵乱天下”,只是由于他“德配天道”,他讨伐榆罔就不是叛乱,而是为民除害。榆罔逆天行事,反而是“叛逆”,轩辕灭榆罔因而成为另类的“惩创叛逆”。和轩辕灭榆罔类似的,还有商汤灭夏和周武灭商,均以臣灭君为结局,但隐含作者以“天道”“仁义”为标准,对商汤和武王予以褒扬。商汤灭夏,是夏桀无道,“汤不得已,会诸侯以正其罪”,又因其“仁义布于四海,恩德著于天下”,被众诸侯推立为王,三让不受后才“即天子之位”⑤周游:《开辟演义》,第145-147页。。周武灭商,因商纣荒淫无道,不纳忠言,商纣之败,“非周败之,天败之也!仁与不仁是也”。⑥周游:《开辟演义》,第177页。但伯夷、叔齐对武王“以臣弑君,可谓仁乎”⑦周游:《开辟演义》,第177页。的诘问终究成为以下犯上者不可回避的问题,或许第三十六回众诸侯逼挚让位于尧时所说的“天下非我主之天下,乃万民之天下也”⑧周游:《开辟演义》,第81页。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以“万民”为根本,所谓“叛逆”,即不为民谋利。如果君主有行,则叛逆受惩创,如共工、九黎、鬼方之乱;如果君主无行,此时无行的君主因逆天而行,可视为民之“叛逆”,如榆罔、夏桀、商纣,当部下为民众利益讨伐他,如轩辕灭榆罔、商汤灭夏、周武灭商,也可以视为“惩创叛逆”,当部下为一己私利讨伐他,就谈不上“惩创叛逆”,而被视为叛乱,如蚩尤反对榆罔。从这些情况来看,隐含作者在判断是非的时候,有自己的伦理标准,在君君臣臣之上,还有一个天下民生。
其二,惩创之艰难。叛逆之所以发生,有其现实根源,或许是主上无德,或许是王朝行将腐朽,但“叛乱者”和“戡乱者”有实力是基本的要求。严格意义上的“叛逆”,往往是叛乱者实力超群,尾大不掉,加上有觊觎王位的野心,于是发生叛乱;宽泛意义上的“叛逆”,乱世中各方为自己利益而相互征伐,无论出于私利还是出于公义,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后,最后角逐者都实力雄厚;另类意义上的“叛逆”,部下为维护天理正道要改朝换代,但旧王朝仍有较强的势力。由于“叛乱者”和“戡乱者”都有实力,戡乱往往比较艰难。
首先,戡乱在讲究具体策略的同时,也能见出当事人的人品。历史小说虽然通过战场的厮杀来最终决定胜负,但谋划更加重要。《三国演义》被视为谋术教科书,主要就在于各方的谋略。官渡之战尽显袁绍和曹操双方主帅和谋士的风采。以袁绍一方为例。袁绍不用田丰、沮授之计,导致失败。但田丰、沮授之人品,却备受赞扬。田丰被逼自杀前慨叹自己“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⑨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6页。,沮授被困,冒死逃走,失败后被杀却“神色不变”,无愧于曹操所说的“忠义之士”⑩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第382页。。袁绍善疑且刚愎自用,“疑所不当疑,又信所不当信”①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0页。,实是“庸主”。如果袁绍不刚愎自用,善听良言,不致落败;如果袁绍不心胸狭窄,怕田丰笑话自己而杀田丰,不致让人心涣散;如果袁绍不多疑,逼走张郃、高览,不致手头无大将可用。袁绍之败,既败于谋略,更败于人品。
其次,戡乱过程中不能忘记世道人心,需要用时行的伦理道德来收买民心。《西汉演义》中的刘邦和项羽,各自的成败不仅在军事较量,也在民心得失。刘邦下咸阳,因畏惧项羽,一改贪财好色之本性,在张良、萧何的劝谏下,不取关中财物,与老百姓约法三章。其用意如范增所言,是为了“安抚百姓,收买人心”②甄伟:《西汉演义》,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项羽和刘邦争锋,最大的错误就是只知道凭借武力,不知道收买人心,反而指使英布等人江中弑义帝,失去民心。项羽暴虐,但讲义气,即使到垓下之围,仍有八千子弟忠心不二,但在张良四面楚歌的计谋下,涣散了军心,终致失败。刘邦虚伪,但知道收买人心,击败项羽后,也能容忍季布当年对自己的羞辱,且赞季布忠心,终将季布留为己用。
其三,惩创之复杂性。站在各自的立场,将对方视为叛逆,从隐含作者的立场看,叛乱一方也未必一无是处,像《开辟演义》那样将人物截然分为品德高尚和品德低劣的历史小说毕竟比较少,大多数小说的人物是比较复杂的,这就导致惩创叛逆时伦理道德方面的复杂性。大致表现有三:(一)总体上受隐含作者支持的一方也有道德上的缺点。《东西晋演义》中的王导,是隐含作者推崇的人物,作为皇帝身边的戡乱者,在诸多叛逆者(尤其是王敦)的映照下,近乎完美。但他也有两个缺点:一是因私恨而害贤良,二是因情势而和稀泥。闻王敦叛乱,王导待罪阙下,周顗虽力救王导,却因不回答王导疑问而被王导误以为说自己坏话,“心甚恨之”③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198页。,当后来王敦想杀周顗而问王导时,王导不回答,终致周顗被害。事后王导发现周顗为救自己所上之表“殷勤款至,词意恳切”④杨尔曾:《东西晋演义》,第200页。,痛悔不已,更映照出他不回答王敦的询问有暗害周顗之心,当为不义。王导平定王敦叛乱重新主事后,明知郭默诬害江州刺史刘胤,却因为担心郭默“骁勇难制”,不仅不惩罚郭默,反而让他担任江州刺史。面对陶侃的责问书信,王导的回信是“包容以伺足下……遵养时晦以定大事”⑤杨尔曾:《东西晋演义》,第238页。,表面上看审时度势,实际上是和稀泥,陶侃看到回信后表示,王导此举不是“遵养时晦”,而是“遵养时贼”,就指出王导和稀泥的实质。作为股肱之臣,王导本应剿杀郭默,却姑息养奸,对照后文陶侃一出兵就能灭郭默,更显示出王导的欠缺。(二)总体上受隐含作者谴责的一方也有道德上的优点。《开辟演义》第三十二回,叛乱一方的九黎中了戡乱者勾龙之计而失败,五人被杀,四人败逃,在败逃过程中九兄弟中最小的黎弼为保护兄长顺利逃跑,单刀断后,“至死而身不倒”⑥周游:《开辟演义》,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老三黎禄单兵出战,英勇无比,寡不敌众后自刎而死,守城的老大和老二也自刎而死。虽然九黎叛乱不得人心,但它们兄弟之间的真情义也让人感动。(三)从各自的道德立场出发,叛逆者和戡乱者孰是孰非难以说清。《梼杌闲评》中的魏忠贤,因熹宗信任而搅乱朝纲,残杀异己,思宗即位后很快就因多人上奏其恶行而败亡。熹宗时魏忠贤以圣旨名义铲除了诸多东林党人,东林党人是不遵守朝纲之“叛逆”;思宗贬斥魏忠贤,魏忠贤又成了和以前东林党人一样的“叛逆”。一朝天子一朝臣,孰是孰非难说清。尤其是小说将魏忠贤行恶置于一个因果报应的框架中。当年朱衡治水时违背诺言,烧死一穴赤蛇,魏忠贤乃赤蛇转世,东林诸人乃治水者再生,魏忠贤残害东林党人,可说是“冤报当然”⑦刘文忠校点:《梼杌闲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64页。;魏忠贤败亡,在他出生时,其父为他求的卦词中就已有预言,他的一切“皆由天数”。
惩创之所以有诸多繁杂之处,其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惩创者还是叛逆者,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道德依据。即使是严格意义上的惩创叛逆,叛逆者之所以叛逆,也有其现实的原因,如《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朱温反唐,是缘于唐末民不聊生的现状和朝廷以貌取人对他造成不公。至于宽泛意义上的惩创叛逆和另类意义上的惩创叛逆,更是将伦理道德作为幌子,各方为自己的利益,将对方视为道德上的叛逆者,下属可以用违背天理来惩创统治者,统治者可以用败坏纲常来惩创下属。惩创叛逆至此已不再出于真正的道义,而是出于功利,只不过以道义的外衣来掩盖罢了。
三、官方伦理与民间伦理
隐含作者用“激发忠义,惩创叛逆”来阐发明代历史小说的叙事宗旨,体现出自己的心声:小说虽是小道,但不妨碍小说家有济世情怀。受儒家规范伦理的影响,隐含作者的济世情怀和真实作者的惩恶劝善互为表里。无论真实作者在生活中的伦理立场还是隐含作者在小说中的伦理意图,都不外乎借助小说来完成风化世教的伦理抱负。栖霞居士《花月痕题词》云:“说部虽小道,而必有关风化,辅翼世教,可以惩恶劝善焉,可以激浊扬清焉。”①栖霞居士:《花月痕题词》,载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791页。绿园老人《岐路灯序》则引朱子的话“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来证明小说“于纲常彝伦,煞有发明”②绿园老人:《岐路灯序》,载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3页。。就明代历史小说隐含作者的济世情怀来看,在“激发忠义,惩创叛逆”之外,还涉及官方伦理与民间伦理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伦理、民间伦理和规范伦理③规范伦理“是以原则、准则、制度等规范形式为行为向导并视其为道德价值之根源的伦理”(吕耀怀:《规范伦理、德性伦理及其关联》,载《哲学动态》2009年第5期),作为底线伦理,规范伦理所要求的是“必须”不能做什么,强制性由此成为规范伦理的一个显著特征。、德性伦理④德性伦理以人内在的精神品质为依托,“着眼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以对人的道德品质、品格和习惯的培养或培育为核心和目标的道德建构”(聂文军:《论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复杂关系》,载《吉首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具有内在性和自律性特征;它以追求完善的道德理想为目标,作为至善伦理,德性伦理所追求的是“最好”怎么样,它一般是超越现实的,因而又具有超越性特征。是对伦理不同的分类,它们之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官方伦理一般是规范伦理,但民间伦理之所以得以流行,也是因为它成为了民间的伦理规范,如寡妇不准再嫁,从来没有写进官方伦理规范,但在某些地方却是约定俗成的伦理规约。官方伦理也有德性伦理的成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通鉴纲目》在对待三国时曹魏和刘蜀谁是正统这一点上就针锋相对,就缘于司马光和朱熹对相关问题的伦理理解有差异。民间伦理之所以和官方伦理形成对比,主要在于其边缘性、实用性、包容性和地域性特征⑤贺宾:《论民间伦理的特征》,《中州学刊》2006年第2期。,这些都与官方伦理大一统的规范性有差别。换言之,民间伦理是在某个区域内流行的伦理观念,它和国家层面上的官方伦理形成补充互动的局面。历史小说的“激发忠义,惩创叛逆”,既是规范伦理对“忠义”的外在要求,也是德性伦理对“忠义”的内在超越。
官方伦理是指官方认定的伦理,对明代历史小说的隐含作者来说,主要是经过官方认定的儒家伦理思想,诸如仁、义、礼、智、信等伦理德目,经过程朱理学的宣扬,四书五经之外的小说大体上归入“宜戒勿读”之类的书籍,儒家伦理几乎成为官方唯一认可的伦理,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小说戏文等通俗文学,“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⑥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也成为它们的金科玉律。对历史小说而言,官方伦理的依据主要是官方授权修订史书中所显示出来的伦理以及当时朝廷发布的伦理禁令。以此观之,除了《东西晋演义》等照抄史书的小说以及《西汉演义》《英烈传》《开辟演义》等完全秉持正统观念所写的小说外,很多小说都不是严格遵守官方伦理的要求来写的。即使像《三国演义》这样总体上秉承官方的正统观念和“忠义”伦理来写的小说,因为其中的一些非官方伦理因素(如对东汉末年、曹魏末年几个皇帝的懦弱无能的描写,曹魏政权和司马氏政权的奠基者曹操、司马懿被写成奸诈之人等,可说是反复地挑战朝廷所严禁的“亵渎帝王”⑦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146页。),一开始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问世一百多年后才得以刊印而广泛传播。对官方伦理而言,它要求的是整齐划一,要求民众要不折不扣地遵守,理学所要求的“存天理,灭人欲”在成为官方伦理后,它对人性的忽视让明朝初中期的官方伦理远离烟火气息,成为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冷冰冰的道德教条。小说的隐含作者在创作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四书五经等官方钦定的经典提出自己的疑问。瞿佑在《剪灯新话序》里认为儒家经典里也有不合圣贤们思想的内容:“《诗》、《书》、《易》、《春秋》,皆圣笔之所述作,以为万世大经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龙战于野’,《书》载‘雉雊于鼎’,‘国风’取淫奔之诗,《春秋》纪乱贼之事,是又不可执一论也。”①瞿佑:《剪灯新话序》,载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0页。野史主人《隋炀帝艳史序》认为专写隋炀帝荒淫之事,是学习孔子修《春秋》:“春秋二百四十馀年,亡国七十二,弑君三十六。”②野史主人:《隋炀帝艳史序》,载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951页。这些序言中的言论折射出隐含作者的心理,历史小说总体上需要和官方伦理一致,这是小说获得官方许可得以流行的前提,但不需要对官方伦理亦步亦趋,它毕竟是小说,是野史,它区别于正史之处就在于它吸收了民间传说,换言之,隐含作者总体上遵从官方伦理的同时,还吸收了民间伦理,让小说显得丰富而不刻板,既说教又充满人情味。
和官方伦理的权威和刻板不同,民间伦理往往是具体的、灵活的,在社会伦理活动中处于边缘地位。民间伦理是“民众在日常生活、生产过程中自发产生、长期积淀而形成的风气、行为方式及价值观等,它根植于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引导规范着大众的普遍行为模式,因而能更真实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③薛柏成:《论墨学复兴与近代民间世风伦理的转变》,《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当社会动乱,官方伦理规范失效时,民间伦理对维护人们处事的伦理行为准则就起到关键作用。即使在官方伦理强盛时期,民间伦理也总能找到一席之地。相传朱元璋曾对《水浒传》深恶痛绝,称之为“倡乱之书”,并认为作者“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必贻大患”④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但不仅施耐庵逃之夭夭,而且《水浒传》也没能禁绝,反而在后世得到广泛的流传。说明明初的政治高压也没能够完全抹杀民间对小说所宣扬的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的喜爱。明代历史小说多写官方伦理作用有限的乱世,民间伦理因而在小说中多有体现。《三国演义》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刘关张的桃园结义,《隋史遗文》张扬的是秦琼、单雄信等人的江湖义气,《杨家将演义》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塑造的杨门女将,更是与官方伦理对女子的要求格格不入。
就官方伦理和民间伦理的关系而言,有论者指出,这种关系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官方伦理和民间伦理之间有一种结构性紧张,官方伦理强行要求民间接受,民间伦理又有自己的土壤,有些和官方伦理有冲突,这就导致第二个方面,民间伦理对官方伦理的四种姿态(循规蹈矩、有限认同、阳奉阴违、分庭抗礼),由于官方伦理最终的执行需依赖民间的认可,民间伦理需要在官方伦理的夹缝中求得自己的生存,这就导致第三个方面,即官方伦理和民间伦理的反馈互动。⑤贺宾:《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就明代的实际情况看,不少主张程朱理学的官方伦理的维护者,在现实生活中纵情声色犬马,言行严重背离,反而是一些凡夫俗子,秉持纯朴的民间伦理,多有合乎伦理之举。也许受世风影响,“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⑥曹学佺的著名对联,转引自龚鹏程:《饮馔丛谈》,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页。在明代历史小说中成为普遍现象。《梼杌闲评》中的发迹之前的魏忠贤和得势之后的崔呈秀,一个因仗义在“峄山村射妖获偶”⑦刘文忠校点:《梼杌闲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页。,一个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魏忠贤都首鼠两端⑧刘文忠校点:《梼杌闲评》,第532页。;《新列国传》中的专诸因感恩而杀王僚,与李兑因担忧个人安危饿死赵武灵王形成鲜明对比;《隋唐演义》中的秦琼和李世民在对待单雄信之事上也形成鲜明对比。
民间伦理和官方伦理之间,除了极端的分庭抗礼以外(由于明代历史小说没有出现完全站在民间伦理立场所写的小说,此点略而不论),其它三种姿态(循规蹈矩、有限认同、阳奉阴违)让二者在总体上趋于一致。明代历史小说的伦理表现由此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在基本不违背官方伦理的基础上,广泛吸收民间伦理因素。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将民间伦理纳入官方伦理之中。《三国演义》虽总体上秉承儒家的伦理正统观,但桃园结义等民间伦理也融进其中,刘关张三人既是君臣,更是兄弟,对帝王之忠和对兄弟之义水乳交融在一起,让《三国演义》在民间产生深远影响。二是以民间伦理来迎合官方伦理。《樵史通俗演义》《剿闯通俗小说》基本上是以民间伦理为立场的小说,隐含作者甚至可以置史实于不顾,完全凭个人好恶对历史事件展开叙述。无论是对阉党的抨击还是对李自成起义军的诋毁,无论是否与史实相合,小说最终所显示出来的是一个亡国子民对昔日王朝的哀悼。这种哀悼既是个人化的民间立场,又体现出自古以来的遗民对故国的忠诚。三是以官方伦理来虚构民间伦理。《三国志后传》为“忠良之后”张目,虚构了蜀汉后人灭晋以复仇的故事,其目的在于“泄愤一时,取快千载”①《三国志后传·引》,载酉阳野史编次,孔祥义校点:《三国志后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虽然借助历史来虚构故事在历史小说中很罕见,但虚构的故事之所以被人认同,与其中所宣扬的“激发忠义”的宗旨分不开,这说明小说最终还是以官方伦理为旨归。
由于明代历史小说将民间伦理与官方伦理融为一炉,而民间伦理有时又与官方伦理相互冲突,这就使得隐含作者在小说中呈现出复杂的伦理面貌:《三国演义》中既有对曹操奸诈的抨击,也有对刘备谋略的赞许;《隋史遗文》中的李世民,既知道民心向背之重要,又因为一己之私而杀单雄信;《西汉演义》中的刘邦,楚汉争锋时知人善用,一统江山后又嫉贤妒能;《梼杌闲评》中阉党丧尽天良,追随魏忠贤的李朝钦则义气为先,陪魏忠贤“投环而死”②刘文忠校点:《梼杌闲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41页。……这些相互冲突的伦理判断折射出明代乃至古代中国伦理社会的独特面貌:“兵以诈立功,商以欺致富,士以伪窃名”③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载《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2页。,孟德斯鸠甚至用“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④[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16页。这样极端的话来理解古代中国人的伦理状况。
无论是激发忠义还是惩创叛逆的具体表现,抑或是官方伦理、民间伦理的相互作用,明代历史小说的隐含作者都试图通过历史小说,传达出儒家以“忠义”为主的伦理观念,为真实作者的劝善惩恶的叙事意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