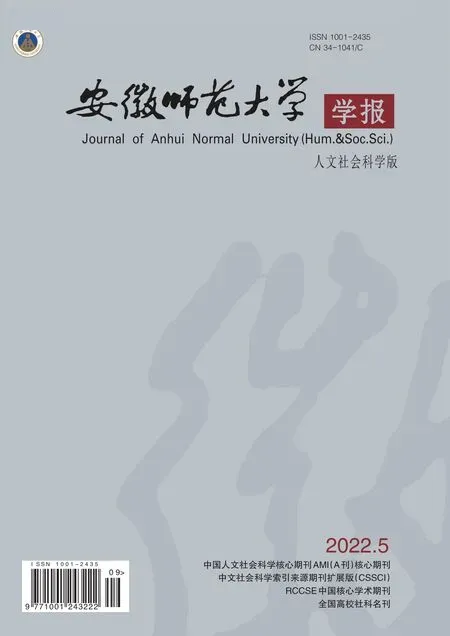夷夏归于中
——商周文化嬗变的神话学阐释*
方 艳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华夏的上古文化史是二重遮蔽的历史,首先是女性文化被男权文化叙事湮没、篡夺,其次是三代文化相继的借用与改写。三代以夏为开端,治理洪水的经验与历史记忆导致其崇水、崇玉的文化特征。商起于东北,太阳族的兴起来源于舜帝部落历法的帮助,然而其成功也需要借助高祖河的神话叙事建构(这亦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早期文化所共有特征)。周与夏一样占据中原地利之便,河源之神秘知识——水利技术,以及从西方传来的金属冶炼技术帮助了农业的发展,最终使得“西土之人”成就了“中国”。
一、水神体系中太阳神格的降解
华夏民族在殷周鼎革之后形成了以混沌—黄帝为至上神的水神体系,①参见拙著《〈穆天子传〉的文化阐释》第二章《以河伯水神信仰为核心构筑的政治神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在这个体系中对于太阳神族的处置方式,就是降级与分解。
“在世界神话中,光明(日、火)之神的象征性置换物或为鸟,或为弓箭等兵器,鸟的飞翔比拟了太阳的运行。”②吕微:《神话何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太阳鸟的概念深入人心,萧兵发现太阳族的射手英雄往往是卵生的,或有一个鸟的形体、鸟的化身,与鸟图腾机制相叠合,并指出这种特点是世界性的。③萧兵:《太阳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而在中国,鸟图腾祟拜、太阳鸟和卵生神话,多见于东夷——东海文化区。古代东夷既祀鸟图腾,也祀太阳神,两者并融为一体。两者相结合的结果便有了太阳鸟——阳离和三足乌。在汉语文化中,“东”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广雅·释天》曾云:“东君,日也。”古代中国认为春季与昼夜一样始于东方,所以将司春之神称为“东后”“东君”“东皇”“东帝”,并于东郊举行隆重的迎春典礼。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又多见太阳为女神的形象,例如在澳洲土著的神话中,“太阳女神伊希、姆顿卡拉以及北部海岸地区流传的许多女性造物者,为使大地万物获得生机而立下创世之功。尤其是太阳女神威力无比,男性的月神对她十分惧怕;有的神话说,主神拜阿米只不过是太阳女神的代表,凡作决定都须经她的同意”。④[澳]A·W·里德等编,史昆译:《澳洲土著神话传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华夏文化中的东母、西母也是古老的太阳女神信仰的产物,因为其自身包含的二元性特征被分身,同样,太阳英雄(或者说男性太阳神)昊,分身为太昊与少昊。殷商时期,母权制文化遗存的东母西母信仰和父权制确立之后的太阳英雄崇拜应是并行不悖的。而后,伴随着太阳族的强盛,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作为华夏共祖的记忆。同时,如同希腊神话中以大地女神的快乐与忧伤来解释四季轮回,东母、西母与太昊、少昊以方位的变化,说明了日升日落的明暗世界的循环。“人类关于复活、来世生活、不朽的最初希望,通过太阳的戏剧性事件的不同说法而表达出来。”⑤[德]麦克斯·缪勒著,金泽译:《比较神话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不过,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上古神话中似乎过于强调西王母之邦,是太阳鸟死去之地。《纪年》云:“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穆王西征,至于青鸟之所解。”这与《穆天子传》“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等相合。《海内西经》曰:“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及所解。在鴈门北。”这个在西北方向的羽陵、羽琌是群鸟脱落羽毛的地方,为有水之沼泽。《淮南子·地形训》云:“北方曰积冰,曰委羽。”高诱注:“委羽,山名,在北极之阴,不见日也。”⑥刘文典:《刘文典全集·淮南鸿烈集解》,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有学者提出:“大鸟脱落羽毛,象征着太阳‘死亡’,即太阳鸟解羽后沉入西方或北方的冰泽。”⑦吕微:《神话何为》,第266页。笔者认可儒学产生于中国东方,而老庄思想产生于中国西方,所谓以柔弱胜刚强,乃是源于周人以小邦周而战胜了大邑商的历史经验。也因此,以夏周文化为主体的华夏神话叙事,是有着独特的立场与态度的,并彰显于民谣俗语之中:“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然后,更以西王母与东王公的偶合直接导致其神格的“恶”化,周人对于商人太阳神信仰的改造,与将伏羲来匹配创世神女娲,以“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文选》)等显性的水族话语来表达其权力意志,如出一辙。李京华在《冶金考古》一书中提出中国金银冶炼开始于商末周初,⑧李京华:《冶金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而玉母变成金母大约也应该就是在这之后。阴阳思想体现在神仙谱系中,最典型的应属东王公、西王母。东王公又称木公,西王母又称金母。“木公亦云东王父,亦云东王公,盖青阳之元气,百物之先也。”①[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五百卷》卷1,神仙类一,扫叶书房1926年版。东王公叙事,将太阳女神的东方属性刻意抹杀,取代了其“生”的神性,从此,西王母的神格似乎只留下了肃杀之气。
黄河下游和淮河下游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区,即传说中太昊族、少昊族等东夷集团活动的区域。这个部落是由许多鸟氏族组成的联盟,少昊如同太昊一样,名字里就蕴有太阳的光芒。太昊与少昊,其远源应是卜辞所谓“东母西母”,是太阳神由母系向父系社会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新的东方太阳神。据《周礼》记载,周人以六辂祭祀昊天玄穹上帝和东、南、西、北、中五方上帝。六辂祭祀:一曰苍辂,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辂,以祀东方上帝;三曰朱辂,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黄辂,以祭地祇、中央上帝;五曰白辂,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玄辂,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神州。其中,昊天上帝为自然上帝,即苍天;五方上帝,即东方青帝(太昊),南方炎帝(神农氏),中央黄帝(轩辕氏),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颛顼),为人格化的五位上帝。一方面,周人所谓的昊天上帝,谓天皇大帝,北辰之星,居于北极,最为尊贵;另一方面,作为殷商始祖神的太阳神作为东方青帝和西方白帝则无形中处于被降格的地位。
需要明确的是,所谓太阳与水,所谓东西,不是相继,而是并存的状态,只是某个时期,某一方面占据了优势而已,当某一地方性集团拥有更强话语权力的时候,他们力图使自己的信仰成为华夏的共同信仰。尧舜禹,是水—太阳—水的交替共在;商与周也是太阳与水的嬗变。在华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这是永恒回环往复的歌声,一阴一阳,在其强弱对比中,展现的是民族性格和文化选择。这些,在看似诡谲的神话叙事中,实都隐含着清晰的历史逻辑。
二、从中商到中国
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指出:“空间本身有它的历史,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时间与空间不可避免的交叉。”②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方位体系的形成是文明成熟的一个标志。四方八极的概念要早于五方,在先民的意识中,四方之中包含了四时,是变动不居的阴阳。四方的观念有两种,一种是方向,一种是以某地为中心的不同方向的地面。③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84页。人类对于四方的界定,出于强烈的文化心理需要。首先是方位的界定取得存在感,对于宇宙的认知,因为稳定而安全;其次是因为可以界定我的世界而产生的生命的狂喜,包含着对于无限的远方的向往与希冀的快乐;最后,通过版图的想象性建构也可以满足政治安全的心理需要。
由甲骨文的发现看,四方与四方风观念的形成,不会晚于商代。据连劭名、胡厚宣等学者研究,商代甲骨卜辞中已有了“方”“四方”的观念,各方均有方神掌管,商王要对方神祭祀、祈年。卜辞中有四方风,饶宗颐指出:“协风二字出殷代甲骨文。”④饶宗颐:《四方风新义》,《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周礼·春官·大宗伯》言:“以青珪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四方本意是指四个方向,但引申为四方之土地,四方之地加上中央,就形成了“五方”的概念。
庞朴在《阴阳五行探源》中,对甲骨卜辞中的所有五数概念进行分析,认为五方是五行观念的起源。⑤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殷人有“中商”的概念,胡厚宣在《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中说:“五行之观念亦为金文所无……五方五祀之说均无丝毫之痕迹可以征考……罗振玉氏殷代五方帝之说故不可信,然殷代确有五方之观念,则可由卜辞证之。……案‘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之起源也。”⑥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版,第383、384、386页。如果说殷人已经有五方的概念,那么,以五方配五色配五帝这样一个严密的王权神话体系的建构、成熟,应该是西周中晚期的事情。
周人以一个西部边陲小国的臣属地位,摧毁殷商政权600年的统治基业,并取而代之获得天下。但作为与商王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广大东方鸟夷系地区始终拒绝承认周人统治的合法性。连续不断的叛乱直接挑战王权的神圣性,尤其是昭王南征而不返,死于汉江,大大损伤了周王朝的国威,造成异族更加叛离,使周王室的政权面临动摇。徐偃王之外,以犬戎为主的戎狄也再次反叛不向周王室纳贡,穆王不得已又西征犬戎。在此时,“居中”成为周人王权稳固的迫切需要,而周人的成功使得华夏真正变成了中国。
《周礼·天官·大宰》中的“祀五帝”,唐贾公彦疏:“五帝者,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五方的概念与中的概念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五方的意义在于他要突出“中”——中国。对于华夏的王权文化体系来说,“中”是最高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导向。在《穆天子传》卷二出现了“中国”一词:“天子于是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国。”这个词的首次出现是在西周《旡可尊》中:“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延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卷4,6014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西周时代的中国,理论上已是一个统一国家,而这种“中国”的概念在《穆天子传》的叙事中表现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对于四方臣服之强调,并且它通过一种“套语”的方式,坚定地加以重复、突出:
□吾乃膜拜而受。(卷二)
智氏之夫……乃膜拜而受。(卷三)
归遗乃膜拜而受。(卷四)
这个“膜拜而受”的表述在短短的《穆天子传》中出现了13次之多,可以说很形象地说明了“万邦朝服”的一时盛况。周穆天子在接受异邦小国的进奉朝拜之时也给予他们一定的恩惠与赏赐的行为本身是富有深意的。英国现代著名诗人和神话学家罗伯特·格雷福斯在其《白色女神——神话诗的历史法则》一书中曾提出真正的诗歌是建立在由少数几个套语构成的神话语言上的,而《穆天子传》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诗意的想象,它所反映的无疑是在周代确立的大国一统的理论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五方帝不过是周人建立其新王权神话体系后对于之前的各方神祇的想象性分封。
三、太一生水与北极为中
大约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大一生水》,其所反映的尚水传统,在先民创世神话的混沌观念有古老的渊源。“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太一生水”,无论解释成生水,还是生于水,都与夏周的水神文化相吻合;《道德经》中一再强调“道”的特性是“若水”。治理洪水是规整世界秩序而使之适于人类居住的一种方式。大禹治水神话的原则在郭店楚墓竹简9号简的文字中被扩展:“削成者以益生者。”②参看[美]艾兰著,张海晏译:《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The Way of Water and Sprouts of Virtue),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附录:《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与〈大一生水〉》。这一神话叙事可以作为《大一生水》宇宙生成论中水先于万物的主题思想来源。《庄子·列御寇》曰:“太一形虚。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水流乎无形,发泄乎太清。”③[战国]庄周:《庄子》,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79页。魏启鹏将该叙述同“浑天”说相连,他认为,“大虚”是水,并引用了纬书《春秋元命苞》:“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焉,万物之所繇生,元气之腠液。”认为尽管该著作的成书年代不详,但它将水和“气”两个概念相连,可以作为尚水传统的又一例证。④魏启鹏:《“太一生水”札记》,《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1期。水在许多早期中国哲学概念中作为本喻出现,其中包括最为重要的“道”。因此,尽管“无为”与“自然”是本于水而生的概念,但在思考这些概念时,人们可以运用其它隐喻性的意象,例如被众星环绕的北极星。北极星,即“大一”,等同于“道”,产生水而生发宇宙。《大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高度抽象,作为一个同占卜相关的理论文献,“大一”生“水”应当被抽象地理解,但是,“水”还意味着“河流”,《大一生水》中从极端流出的水,可以被看作银河,它横贯天宇,环绕(黄泉)而归以利天。由此,地及万物周行复始。支持这一主张的证据在于天在西北方向有缺陷而地低,这与神话中共工怒撞不周山,以至于大洪水暴发而天地倾斜相关。《淮南子·天文训》曰:“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大一”生水也就是说,北极星产生或者生成一条河流,应该就是银河,而银河即天地之源。
“大一”在天空的中心位置,使得它成为统治者恰当的模型。汉代,将皇帝同“大一”相连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其远源可溯至战国之前。例如《鶡冠子》:“泰一者,执大同之制,调泰鸿之气,正神明之位者也。”古人相信北极星是天帝的居所,《史记·天官书》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在华夏文化传统中,北极星被认为是“帝”,表明其最高位置及统治“天”的功能。而“斗为帝车,运行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①[汉]司马迁:《史记》卷27,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89页。《周礼·考工记》中有相关的表述:“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卜,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又八,以象星也。”《道德经》第11章(不见于郭店《老子》)中“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大概指的也是该星群。“大一”即北极星——银河的源头,万物由之而生。司马迁把北极星附近的天空叫做“中宫”,其他则分属东、南、西、北四宫。整个天空被划分为“三垣”和“二十八宿”。北斗星座象征着人间的中枢地区及都城,主宰着大自然以及人世间的一切事物。《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其隐喻性在于,“大一”的中心位置,与神秘的不受伤害性的交流相关,它是唯一没有对立面的点,即它没有敌手。因此,倘若人们能够“守一”或者“守道”,即可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周人恪守“天道”的真谛,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子》才是真正的王者之书。
周人的胜利使得西边的水神变成了中央大帝、混沌大帝、黄帝。为了安抚东方商夷的情绪,并结束东西的原则性对峙,周人创造了“天”神的概念,这个天之中却在“北”,北极、北斗。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其神格为大水神,对应的是北方,“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大荒北经》)。郭璞云:“字玄冥,水神也。庄周(庄子大宗师)曰:‘禺强立于北极。’一曰禺京。一本云:北方禺强,黑身手足,乘两龙。”夏周同源,故以天帝处北极,为“天之中”;以黄帝为中央大帝,处“地之中”。天玄地黄皆为中。天青黑,地黄赤,天数之为笠也,青黑为表,丹黄为里,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对应的也都是中。无论天上、地下,处于中间的都是夏周的祖灵神或以之升华的天下共祖神。《淮南子·地形训》曰:“后稷垅在建木西。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以北为“天之中”,是周人的新创造,北辰与北极,作为天象的“中”而存在,其逻辑发生于周人意图凌驾东西二元的“居中”的文化心理。
如果说周人在立国之初不得不沿袭借用了太阳神族的部分神话叙事,那么,昭穆之后,周人则致力于建构“中国”,为此必须修正三代西东对峙的关系:地上的黄河对应着天上的银河,地上的西源性水族神话被转喻为天上的太一北斗神话,方向性的位移,使得周自然而然地集夏商之大成。
周人把成周为天下大地之中的观念,融汇到了他们的宇宙观与世界观之中。《周礼·大司徒》记有用仪器土圭测量日影以确定天下之中的方法:“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吕氏春秋·慎势》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②[秦]吕不韦撰,高诱注:《吕氏春秋》,四部丛刊景明刊本,第143页。都城不仅是王权统治的中心,也是王权政治的象征。到了唐代,干脆用太极、两仪用作殿名,喻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象征宫城就是宇宙的中心,皇帝就是天子。“尚中正行”象征着帝王江山的四平八稳,天地阴阳的平衡,以及古人一贯推崇的道德理想——“中庸”。邵雍说:“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是以乾坤屡变而不离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则盛,月中则盈,故君子贵中也。”(《皇极经世书》卷一四《观物外篇下》)更是将“中”提升作为一种普泛的社会文化价值追求。“空间生产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①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Blackwell,1991,p.26.所谓“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旁制万国者也。”②[清]阎镇珩辑:《六典通考》卷188,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440页。五方的中的空间概念与作为王权信仰的“中央”的要义划上了等号。“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③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页。后世的文化体系中,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强调“守中”。张默生说:“不如守中”的“中”字,和儒家的说法不同:儒家的“中”字,是不走极端,要合乎“中庸”的道理;《老子》则不然,他说的“中”字,是有“中空”的意思,好比橐钥没被人鼓动时的情状,正是象征着一个虚静无为的道体。④张默生编著:《老子章句新释》,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81-82页。其实儒家的“中”,强调是不走极端,要合乎“中庸”,是从行为实践出发,追求胜利;而道家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是从哲学姿态出发,哪怕我无所作为,也是不可战胜的。
华夏三代史,是东西的冲突史,也是对话史。周人提出的“中国”之中,调和了东白西黑的同时,也不能完全抛弃其西源性的文化背景,所以北辰、北极、玄冥仍然是最重要的价值标指。周人在夏商的二元对峙中获得经验,基于夏周的文化传统而总结提升出一个高于祖先崇拜的天神的概念来,然后统合了东西夷夏。当然,其文化基因中偏西源性的水神信仰,较商人更为坚定深刻。周王权确立之后,周文化以居中意识而统合了天下,其对于东方文化的改造与遮蔽的一个重要手法,也从其居中的立场而来。从此,有了“中”,就有了“天下”,所谓四方之中央为中,左右之中间亦为中。中,是华夏主体的确立,犹如佛诞生之时,四方踱步,我在中间,所谓万物皆备于我,这种文化自信,构成了华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心态。其包容性和开放性,由糅合夷夏东西而确立自身,胜者为“中”的族群记忆而来。
四、凤歌笑孔丘
对于殷周鼎革,华夏文化史上的圣人孔子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孔子的文化身份是东方的儒。胡适提出儒为殷商民族教士说:“我认为‘儒’是‘殷代的遗民’。”“正因为他们是亡国之民,在困难的政治环境里,痛苦的经验,教育了他们以谦恭、不抵抗、礼让等行为为美德,他们因此被取个浑名叫做‘儒’;儒者,柔也。”⑤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267页。其实《说儒》⑥胡适:《说儒》,《“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4本第3分册),1934年。主要是学习了章太炎的《原儒》,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鲁“为殷遗民之国”。傅斯年说“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的影响,其立论确有不够严谨,甚至想象超越了实证的地方,所以,冯友兰、钱穆等分别撰文进行了批驳。不过,尽管笔者也不认同其“殷商民族文化终久逐渐征服了那人数较少的西土民族”,“那六百年殷周民族同化的历史实在是东部古文化同化了西周新民族的历史”等观点,其论述之基础:孔子是殷宋正考父的嫡系,他和这班大弟子本来都是殷人,都是殷儒商祝,他的新儒教运动是殷遗民的民族运动等等,或者都还有思考的余地,但是,他从孔子这个不知父母葬处的贫贱少年,如白川静所言或是巫女的私生子身上看出其“吾从周”断语背后,“调和三代文化的象征意义”,确是不容忽视的意见。周之成就中国,原因在此;儒之传世,原因在此。
一方面,孔子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周礼的拳拳服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又,《论语·卫灵公》记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这些都表明孔子以周人的礼仪道德为标榜的文化态度。另一方面,尽管孔子曾叹息殷礼的不足征,但是他又说殷、周礼之间不过是有所损益,并且似乎对于本源性文化还有着某种留恋。《论语·子罕》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又云:“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治长》)虽然这种话也可能只是牢骚感慨之语,不必真的就立刻启程,但所言去向必非泛语,则是显然的。
孔子意欲东渡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话题。孔子悲伤道不能行,先是要与九夷一起居住,这是身份认同。然后还不能行,欲浮筏渡海,这是礼失而求诸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商亡。之后,传说箕子在朝鲜半岛建立王朝,并得到了灭商的周王朝的承认:“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汉书·地理志》卷28第八下)据说箕子制定了乐浪、朝鲜之民应遵守的八条禁制,教人以礼仪、农耕、养蚕和机织,不仅带去了华夏的风俗教化的规章制度,更将先进技术传到了半岛。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九夷,所谓的东方海上,仍然是孔子的心理归属的反映。这一点非常重要,孔子的向东问道,与周穆王的向西寻根,正是两种文化的不同选择,而其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从”,说明了周非其本源性文化的事实,当然也是对于华夏文化之西方质素普适性的接受。这种矛盾性之中,包含了孔子跨越文化身份的自觉性选择。对此的理解恰恰反向性地体现在“凤歌笑孔丘”的嘲讽之中。
《庄子·人间世》云:“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楚人尊凤,其渊源在商,商遗四散而亡,或东北,至朝鲜半岛而建立箕子王朝。或西南,楚人好巫,不过是继承殷商的遗风而已。①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史学论丛》第1辑,1934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谈到楚人之俗,称“西楚”之民,“其俗剽轻,易发怒”;“徐、僮、取虑”一带,“矜已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屈原笔下的日神东君:“驾龙輈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正是那放浪不羁(“剽轻”)而又热情豪侠(“矜已诺”)的楚民族化身。孟康亦云:“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②[汉]班固:《汉书》卷1《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页。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对司马迁的西楚、东楚、南楚的地理范围做了全面的界定:“沛,徐州沛县也。陈,今陈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荆州也。言从沛郡西至荆州,并西楚也。”“彭城,徐州治县也。东海郡,今海州也。吴,苏州也。广陵,杨州也。言从徐州彭城历杨州至苏州,并东楚之地。”“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长沙二郡,并为(南)楚也。”③[汉]司马迁:《史记》卷129,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7、3268页。东楚西楚南楚,虽范围广阔,其风俗文化,信仰传承,应该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或者说共通性。《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太皡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个所谓咸鸟生巴人可以看作是玄鸟生商的翻版。与之相呼应,后世又有楚狂入蜀的记载:“陆通者,云楚狂接舆也。好养生,食橐盧木食实及芜青子。游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世世见之,历数百年去。”(《列仙传》)所以蜀人李白也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文化认同。所谓“凤歌笑孔丘”,乃是巴楚作为殷遗,对于“故凤之衰”的无奈,对于孔子之理性选择的不认同,或者简单地说,是对其“从周”的否定。楚狂的“笑”里面提示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
殷商时期是神权左右王权;西周时期是神权服从王权。儒家文化原本是植根于东方的殷商文化。甲骨文中的儒像沐浴濡身之形,原来是突出其神职特征。①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孟子·离娄》也说到斋戒沐浴的宗教净化功用:“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说文》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王国维释:“又推之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②王国维:《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可见早期的礼以敬鬼神为核心,是为了体现对鬼神的尊敬而制定的礼仪。董仲舒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礼之所为兴也。”③锺肇鹏:《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卷6,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一般公认为西周时真正成熟的礼乐制度建立,在周成王、周公时代,统治者将事神致福的原始仪式“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扩展化,成为一套早期奴隶制的习惯统治法规”。④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也即是把“礼”从“仪”中分离开来加以强化,礼由单纯的祀鬼神而上升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⑤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卷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礼成为君王维护统治的工具,成为治国之本。“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⑥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卷2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2页。“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⑦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卷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从而使“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秩序社会。又,“鲁城中居住有周人和殷人,故有‘两社’——周人的‘周社’与殷人的‘毫社’。周公庙村西建筑基址的夯土范围,东西残长100米,南北长约115米;西部范围,东西长约95米,南北长约90米,中间隔有一条南北向的道路,宽5米,这大约就是两社之所在。按照鲁城内周人居东、殷人居西的布置,大约路东夯土基为周社遗址,路西夯土基为毫社遗址。此社位于中城内宗庙区之西,正合‘左祖右社’的制度。”⑧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从东西位置的对调中,似乎也可以看出打破旧有的方位秩序,形成新的世界模式的努力。
如果说殷商提供了一个浪漫主义的传统,那就是对于绝对王权的肯定,保留了巫王一体的时代,作为王的优越性,王与帝是血脉关联的。但华夏文化自殷周鼎革,我们就跟随着“郁郁乎文哉”的周礼而前进,三代经周秦之大一统,最终完成了民族融合。华夏文明共同体的确立之中,有对立冲突,有取舍遮蔽,并最终决定了民族文化的走向。从文化基因的角度来看,正是差异化的次族群文化性格,促进了白与黑、激情与冷静、浪漫与理性兼容的华夏文明,换言之,华夏民族的精神活力正来源于其东西交融、四方汇聚的文化多样性。孔儒之从周,是妥协,也是融合,然后集大成,成大儒,成素王,这种文化精神,是华夏的根性力量所在吧。
五、结语
殷周之变究竟是根本性的,还是损益性的?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出,随着“殷周鼎革”的发生,“商之道”和“周之道”便开始了历史性的揖别。他以卜辞研究所得与“周制”作为比较,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自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然后,他又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有三:一曰立子立嫡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关于第三事,他说“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女子称姓,亦自周人始矣”。⑨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2页。傅斯年则以为“东西对峙,而相争相灭,便是中国的三代史。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争,商东而夏西。在周之建业,商奄东而周人西”。⑩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68页。徐中舒也坚持自己的推测,认为殷周似属两种民族,⑪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李懿选编:《徐中舒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确实一语中的。但是,一般认为到两汉时,东西的混合已很深了,然追究这种融合之功,应是开始于周人。
对于先民来说,地理方位的区分一定以已知之世界为限,对于夏商之西东之别,也仅是就相对位置而言其族群文化的源起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偏重而已。夏周以中原为主,受西方戎狄影响大,商起源于东北,与东夷关系密切。水神族系与太阳神族交叉重叠的权力斗争嬗变,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生产技术发展先后导致的实力对比变迁而引起的王权盛衰交替,带来话语权力主体的变革,从而导致叙事体系的解构与重构,这也是华夏神话体系复杂难解的原因所在。
商周鼎革对于华夏民族的文化走向来说,无疑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折,新兴的西周借助其建构的国家宗教和神话观念,影响至为深远,并不亚于一次武力上的革命,带来的是华夏族群性格的深刻变化。周汉之礼的建构,宋明之理的盛行,延续的主流文化传统是更偏向于理性主义的,或者说合理主义的。而商夷文化浪漫炽烈的性格基因则存留于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时不时发为楚狂之言。今天为民族复兴而进行的寻根之路,不仅是对五千年华夏先民物质和精神文明探索过程的追溯,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探寻可期冀的民族未来,因此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更开放的心胸,了解本族群文化的得与失,从而认知在东亚区域文化中与他者的同与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