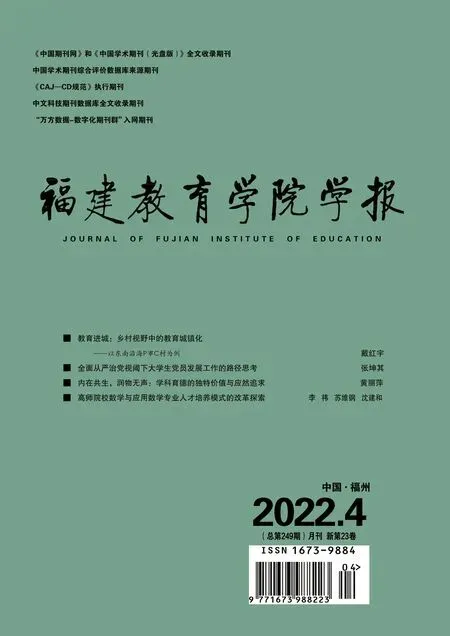澳大利亚“民族英雄”的成长史
——成长小说视角下的《凯利帮真史》解读
严昕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中心,福建 福州 350108)
一、《凯利帮真史》与成长小说
彼得·凯里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目前著有2 部短篇小说集,8 部长篇小说和多部非小说文学作品,被称为“澳大利亚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继长篇小说《奥斯卡与露辛达》1988 年荣获英国文学布克奖后,其著作《凯利帮真史》于2001 年再次斩获布克奖及英联邦作家奖,使得凯里成为史上仅有的两位两度荣获布克奖殊荣的作家之一。
在小说《凯利帮真史》中,彼得·凯里一反官方把澳大利亚历史人物内德·凯利描绘成暴徒和强盗的既定论调,重新塑造了一个敢于反对殖民压迫、带领澳大利亚贫苦大众起义却最终不幸被捕并处以绞刑的“民族英雄”形象。小说中的情节创作立足于澳大利亚殖民历史本身,从亲情、友情、爱情,真实与虚构,压迫与被压迫,颠覆与被颠覆等多个纬度展开描写,成功将角色个人的多样性成长体验和民族心理及文化身份构建的复杂性交织融合在一起。目前,对《凯利帮真史》著作的研究主要围绕小说人物、情节、叙事策略,以及对历史真实性和虚构性、新历史主义下的文本内涵、国家身份和民族认同感的形成、福柯权力理论基础上的权力话语等纬度展开讨论,还未有学者从成长小说视角对该文本进行探究。本文将运用成长小说理论,结合主人公所展现出的不同成长维度、体现出的不同成长性质,从社会化和个人化两种成长模式出发,探讨故事情节变化对于青少年主人公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清晰地展现主人公自我价值确立及民族文化身份构建的动态过程。
作为文学概念,“成长小说”可追溯至18 世纪末和19 世纪初的德国。它是以叙述人物成长过程为主题的小说,旨在通过对一个人或几个人成长经历的叙事,反映出人物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成长小说很快被各国文学广泛接受并加以发展。莫迪凯·马科斯(Mordecai Marcus)在《什么是成长小说?》一文中对成长小说下了定义,认为故事主人公应是在“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改变了自身的性格和世界观,从而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走向“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1]。同时,作为富含文化隐喻性的文本载体,部分成长小说“以人生的启蒙象征一个民族的启蒙,甚至人类的启蒙”,意味着展现“他者的主体化和边缘的中心化”,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起始点[2]4。因此,认识和探究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不仅是对个体思想变化发展的清晰认知,更是对整个民族甚至世界发展演变的有力反思。
《凯利帮真史》将故事背景置于19 世纪60-70 年代的澳大利亚东北地区。小说以主人公内德·凯利写给素未谋面的女儿的13 封信为基调,信件内容以内德·凯利的年龄变化为线索,生动刻画了内德·凯利从12 岁开始认识世界到26 岁在对抗中战死的宝贵人生经历。成长小说的研究视角可以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内德·凯利是如何在遭遇童真幻灭、离家找寻自我、被迫反抗、决心起义过程中,渐渐找到国家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感,从而更好地理解内德·凯利的挣扎和反抗行为背后所透射的澳大利亚人民反殖民的迫切愿望和不懈努力。
二、《凯利帮真史》的成长小说叙事
(一)主人公的社会化成长模式
1.在家庭错位与残酷现实的压迫中成长
幼年时期,被贬低的父亲形象与错位的父亲角色是造成内德·凯利童真幻灭的重要根源之一。无论是在外部舆论,还是母亲口中,父亲约翰·凯利始终都是被嘲笑和打击的对象。正因为遭受过被流放和监禁的痛苦,父亲在面对殖民者的残暴统治时,选择了消极逃避和默默忍受的态度。正因为父亲的“不作为”,母亲与父亲争吵不断。在母亲眼中,父亲已无法承担起家中“顶梁柱”的角色,逐渐沦落为“逆来顺受的窝囊废”[3]7。除此之外,殖民者警官有意地将约翰·凯利“异装癖”的隐私赤裸裸地暴露在心智尚未成熟的内德面前,直接造成了原本高大的父亲形象的破灭。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父亲在孩子性别角色发展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为男孩提供了一种可效仿的基本行为模式,是男孩初步建立性别角色模式的榜样[4]。显然,向殖民文化低头的父亲无法为子女提供肉体或是精神上的庇护和启迪,父亲形象的破灭与角色的错位在还未满12 岁的内德心中造成巨大冲击,失去了人生初期效仿对象的主人公陷入了彷徨失措和困惑迷茫的境地。家庭对于他来说,已不是充满温情和关爱的“避风港”,而是充斥着争吵与破碎的“纷扰之地”。
除了家庭亲情关系的错位之外,殖民环境所导致的贫苦处境直接促成了主人公心智的早熟。内德·凯利出生在一个穷困潦倒的爱尔兰裔移民家庭。代表着帝国利益的政府官员、牧场主、乡绅用尽一切手段欺压贫苦百姓,将国家法律与规章制度玩弄于股掌之间,肆意侵占公共土地,使得以种植和放牧为生的殖民地人民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年幼的内德自打懂事时起,便不曾体会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在父亲病逝后,内德承担起了家中“男主人”的角色,弱小的肩膀扛下了所有重活累活。在残酷现实的冲击下,内德·凯利不得不尽快成熟起来,展现出与年龄不匹配的独立和坚强。
尽管家庭关系的不和谐以及经济条件的拮据都是导致内德·凯利童真幻灭的重要原因,然而一切不幸的根源还是在于殖民体系的残暴与不公。由于警方蓄意陷害,15 岁的内德·凯利以窝藏盗马罪被判入狱3 年。天真烂漫的青少年时光只能消磨在牢狱的无尽黑暗之中,内德·凯利的“青年时代的最后一缕希望之光被扼杀了”[3]202。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的诸多磨难加剧了主人公对周遭环境的无助和愤怒,以及对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困惑。此时此刻,内德·凯利和其他殖民地人民一样,都只是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中的“他者”,在庞大的殖民体系中被边缘化、孤立化,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
2.成长苦旅中的“仪式化”特征
成长仪式的叙述是成长小说独具特色的一个重要叙事载体。人类学研究表明,“仪式”作为一种严酷的考验,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广为流行,被用于检验未成年人是否拥有足够能力步入社会,承担人生义务。内德·凯利的成长轨迹充满了“仪式化”特征,是以种种重大事件的发生来作为成长洗礼,标志着自我力量的壮大,从而证明自我的生存权和存在意义。
与“野人”赖特的决斗并取得胜利是内德重拾人生尊严和意义的重要成长仪式。通过暴力取得的胜利通常意味着个人权威的建立,可以在大环境中不受凌辱、有尊严地生活。在成长小说理论解读背景下,内德“决斗仪式”的意义更接近于“死亡与再生”[5]。被放出监狱且离家出走之后,内德·凯利陷入了对自我的怀疑和对人生价值的困惑中。在最爱的母亲面前,他甚至不如乔治·金值得信赖,曾经建造家园的梦想如今却变成了“踩在靴子下面的粪土”;在不公世道面前,他的愤怒和痛苦郁积于心,终日烦躁不安,找不到前进的方向[3]212。在殖民体系中,内德只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他者”,一个对周遭一切毫无掌控力的可有可无的人。他必须摆脱这样的处境,赋予自身尊严和价值感,才能重获新生。
在与“野人”赖特决斗之前,内德心情激动,他感受到了希望重燃和生命复苏的时刻即将到来:“睡梦中,我和赖特搏斗,拼命撕扯他的嘴巴、眉毛、鼻子、自己的一双手粉碎了,但是一点儿也不觉得疼痛,只是感觉到一种狂喜。”[3]214体验重获生命和力量的欣喜预示着“再生”时刻的来临。“再生”意味着摆脱以往的彷徨状态,确立起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经历了“死亡—再生”成长仪式后,内德重返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开始勤恳干活、结交朋友、阅读书籍,展现出一种新的个性。
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成长仪式亦不断出现并重复。成长小说研究认为,青少年主人公的“顿悟”时刻通常伴随着“震撼性事件”的发生,对于主人公的成长具有决定性作用[2]144。如果说与赖特决斗“仪式”是对自我的重新认知,那么在桉树湾枪杀警察则象征着对殖民权威的颠覆和反抗,更是一次重要的成长“仪式化”特征。桉树湾围堵追捕警察时,在自己亲兄弟和好友性命攸关之际,内德扣动了手中的扳机,向殖民地警察开了枪。枪杀警察事件对于一个长期遭受不公待遇的弱势爱尔兰裔贫民来说,无疑极具颠覆性和震撼性。正是因为这种“震撼性事件”的发生,让内德·凯利清醒地认识到:一味地忍受和退让不会让殖民地人民悲惨的现状得以缓解,只有抓住机会奋起反抗才可能迎来希望的曙光。开枪事件代表着内德的标志性成长,预示着过去那个退缩的、受制于人的“我”已经一去不复返,此刻新生的“我”可以充满勇气和决心,以澳大利亚土地“主人公”的姿态面对殖民力量的压迫和威胁,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3]308。
(二)主人公的个人化成长模式
1.自我迷失下的逃离与成长
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形成与离开原生家庭环境、学会一个人独立生活密切相关。离开熟悉的家庭环境,独自面对复杂且充满挑战的社会环境,是青少年性格养成和人格建立的必经之路。正如成长小说研究指出,“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必须离家远行,才能认识自我,认识社会”[2]94。因此,“逃离”和“出走”等文学元素在成长小说中屡见不鲜。
内德·凯利第一次“出走”的经历是被动成为哈里·鲍威尔的“学徒”。尽管哈里起初带走内德的目的并不单纯,但幸运的是,哈里逐渐承担起了内德成长途中积极的“引路人”这一角色。作为“丛林强盗”哈里的“小跟班”,内德被迫以丛林为家,学会在艰难恶劣的澳大利亚原始自然环境中生存,为日后的反抗殖民政府起义打下铺垫。突如其来的“离家出走”使得内德得以暂时脱离原生家庭的纷扰,第一次走近和感受自己身处的山川河流,并且习得了如何在野外生存的诸多本领。正是与哈里·鲍威尔这段“出走”的经历,打开了内德·凯利对自我的认知,无形中已引领着内德走上他的“生活之路”。
内德·凯利的第二次“离家出走”经历则是主动的。因无法理解和认同母亲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又一个“不靠谱”的新任丈夫身上,内德在刑满释放后,毅然离开十一里湾外出独自谋生,在锯木厂找到了一份工作。此时的内德·凯利虽已年满20 岁,但在接连不断的灾祸和苦难面前,内德仍困惑于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最终选择独自找寻问题的答案。
与第一次被动“出走”不同,第二次的主动“出走”行为是艰难且难能可贵的。内德下定决心离家远走的决定可谓一次重大的心理转变,标志着个人思想和心理的逐渐成熟。在殖民背景复杂的大环境下,个人与自我关系的探索需求驱使着内德离开一成不变的原生环境,在外部世界获取崭新的成长体验和认知。从文中屡次出现的“逃离”叙事中已可窥见主人公自我意识萌芽的产生,反映出了主人公内德·凯利对探究“我是谁”及“我将去往何方”等自我认知问题的迫切渴望。
2.殖民困境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成长小说研究学者指出,一些作家通常以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为缩影,来象征一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发展变化过程,从中展现出一种“广泛的认同性”[2]4。彼得·凯里通过重塑澳大利亚爱尔兰裔“丛林强盗”内德·凯利的故事,把他描绘成一个善良正直且勇于反抗殖民压迫的民族英雄,是对澳大利亚独立民族文化身份重构的尝试与努力。内德·凯利更重要的个人化成长途径在于摆脱殖民文化的禁锢和桎梏,化被动为主动,靠自身努力建构国家身份认同,寻找存在的意义[6]。
最早流放到澳洲大陆的爱尔兰人大多数是政治犯,他们遭到英国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新南威尔士。面对英国政府的殖民统治迫害,坚强不屈的爱尔兰人奋起反抗,各种政治、武装斗争无形中强化了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不畏强权、勇敢正直的坚毅品格。小说中爱尔兰裔后代内德·凯利自幼生长于这片广阔无垠的澳洲土壤,自然延续了澳大利亚本土居民特有的善良、宽厚、坚韧等良好品质。尽管这片土地笼罩在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下,但是正如内德所说,这个国家永远都不会真正属于殖民者[3]241。小说中多次提及,澳大利亚的山山水水就如同“母亲”一样,保护着内德和他的伙伴们免受殖民者的侵扰。也正是对于这片土地上“沟沟岔岔”了然于胸,帮助内德在起义反抗危急关头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内德·凯利都与澳大利亚这片广阔土地紧密联结在一起,国家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样深深根植于内德心底。
然而,想要打破殖民当局的高压统治,仅仅依靠对澳大利亚自然环境的熟悉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彼得·凯里在小说中借内德之口所说:“真正保护哈林的是人。最终出卖他的也是人。哈里明白,他必须让穷人吃饱,必须和他们搞好关系。”[3]360作为被殖民者的一员,内德能够深刻理解贫苦人民处于社会最底层,肉体和精神上所受到的双重折磨和摧残。这个“失语”的群体无处发声,也不知道该如何发声。因此,内德的挣扎、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这个群体对于发出公平和正义呼喊的渴望。
起义运动期间,以内德为首的“凯利帮”从不劫掠穷人。在受到殖民当局的恶意丑化和抹黑之时,内德试图通过“书写”自己的真实遭遇来洗脱“罪名”。在妻子玛丽的支持下,他在艰苦环境中用笔记录下自己一路来的经历,想要通过“可靠”的媒体人卡梅伦发出自己的声音,结果却遭到欺骗和嘲讽。但是,他没有放弃,一遍又一遍地尝试着将“真相”传递给大众,甚至不惜冒着被出卖的风险到印刷厂亲自印信。在一切挣扎和努力都看似行不通之际,他为女儿留下了写有他人生经历的13 个包裹,这些包裹构成了小说主体。然而,作为一个连完整句子都写不清楚的“丛林汉”,为何如此看重“书写”的作用和力量?为何在与殖民者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仍然不遗余力通过各种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内德清楚地知道,为正义和自由而斗争从来不只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事,真正的“主力军”和“后备军”是受殖民压迫的澳大利亚穷苦人民。“凯利帮”的战斗也不只是为个体解放,而是代表着弱势群体和底层人民对“反权威”和“反压迫”的真切渴望。只有让人民群众看到事实真相,让“沉默”和“被失语”的群体重获“话语权”,才有可能迎来国家和民族独立的美好希望[7]。此时,内德·凯利个人史的书写已不是单纯的故事拼接,而是被赋予了深层次的民族性内涵,他的所作所为已上升至民族层面,内德·凯利的国家身份认同已然形成。
三、《凯利帮真史》的成长主题特色
《凯利帮真史》是一部具有多重维度、丰富内涵、深刻意义的成长叙事小说。在社会化成长模式下,分崩离析的家庭环境和残酷冷血的社会环境迫使主人公早早地告别童年的稚嫩,在一个个标志性的成长“仪式化”特征中进行自我启蒙,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逐步发展。在个人化成长模式下,“逃离”和“出走”是成长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带着困惑和迷茫在社会浪潮中翻滚和击打,主人公已不再是懵懂的少年,在勇于反抗和控诉的过程中渐渐确立了民族性,最终成长为坚决抵抗不公和捍卫人民权益的“民族英雄”。
该小说主人公的成长环境多了殖民政治的色彩,此类成长叙事的独特价值和魅力不可忽视。在成长小说视角下,内德·凯利展现出在殖民困境中成长的艰难处境和矛盾局面。一方面,内德需要冲破家庭的负面影响及纠缠拉扯,找到自我存在的立足点;另一方面,面对殖民体系强大的压迫和控制,内德亟需拥抱族群记忆,重构民族历史,为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铺平道路。
总而言之,《凯利帮真史》在成长叙事中融入了民族、族裔、文化等多样化元素,关注成长小说文类中因种族、历史、阶级、地域不同而产生的成长差异,凸显了成长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随着历史时空和研究主题的变化而展现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内容结构特征[8]。与以往关注和讨论较多的西方“主流”国家成长文学不同,《凯利帮真史》的成长主题探究为挖掘其他国家成长小说作品的丰富内涵和特异之处打开了视角,拓展了成长主题叙事的向度和深度,为此类文本的进一步欣赏和诠释,提供了重要参考范式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