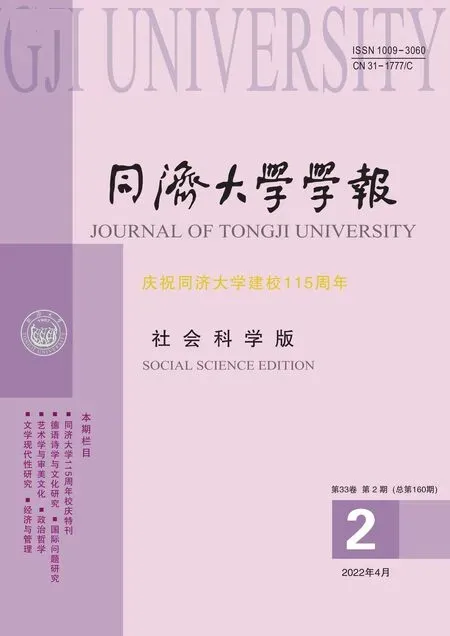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领土国家:一个功能主义的理论构想
朱佳峰
(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现代国家是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领土标识现代国家的辖区,国家只能在其领土范围内享有和行使主权(最高权威)。但现代国家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在关于国家正当性的政治哲学思考中并未获得足够的关注。关于国家正当性的论述,比如政治义务理论,通常聚焦于国家与受治者(subjects)的关系,几乎从来不把领土这一“变量”考虑进来。(1)对政治义务问题的经典讨论,参见约翰·西蒙斯:《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毛兴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乔治·克洛斯科:《公平原则与政治义务》,毛兴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也许有人认为,领土国家是如此显而易见的现实,以至于它构成了国家正当性的思考起点,而其本身不需要进一步反思与论证。这种想法过于轻率。比如,一般我们都接受现代国家领土的稳定性,即一个国家内的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权变更该国的领土,但到底有什么理由可以支持领土的稳定性?或者,假设A国主张,当前属B国领土的一部分土地应归属A国,理由是那部分土地上居住的人和A国人民同属一个民族或族裔。如果反对这个主张,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因此,领土必须被纳入到现代国家的正当性论述之中。此外,从实践意涵上说,一个包含了领土权的国家正当性理论也有助于构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话语体系。
对政治哲学而言,领土国家的政治实践至少带出如下四个问题,它们分别是:(1)什么是领土(主)权?(2)为什么国家能够主张领土权?(3)国家能对哪一块特定的土地主张领土权?(4)能最终主张领土权的主体是国家,还是民族或人民?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这些问题不是旨在对现代领土国家如何形成给出一个因果解释,而是试图探究现代领土国家的道德正当性,因此这个问题“呼唤”道德证成(moral justification)。在这四个问题中,第二个问题最为根本。根据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当代领土权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类:(1)洛克式同意理论;(2)民族主义理论;(3)功能主义理论;(4)政治自决(political self-determination)理论。(2)当然,这四个理论对其他三个问题的回答也有所不同,但在笔者看来,它们之间最为根本的分歧还是在于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对这四个理论的简介,参见朱佳峰:《领土权:当代政治哲学论域中的理论图景》, 《学术月刊》,2018年第2期,第94-102页。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在简要批判现有领土权理论的基础上阐明和辩护一种新的功能主义领土权理论,笔者称之为“洛克式功能主义理论”。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领土国家和领土权作一介绍。
一、 领土国家
现代国家只能在其领土范围内享有和行使主权(最高权威)。对于现代国家的领土性特征,人们习以为常,以至于在建构国家正当性理论时常忽略这一点。然而,国家并不总是以这样地理性的方式来组织和实施其政治权力。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定义国家,而且我们需要一个足够包容的定义,从而使“领土国家”或“非领土国家”都具备概念可能性。基于这一点,本文采纳了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对国家的定义。按照他的界定,国家是一个“为了行使政治权力而持续存在的制度结构”,“行使政治权力”代表了在辖区范围内对制定、应用和执行法律的垄断性和至高性(supremacy)。简言之,国家可被视为一个在辖区内行使最高政治权威的稳定的制度结构。(3)Allen Buchanan, Justice, Legitimacy, and Self-Determi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73.此外,布坎南对国家的定义也有助于区分国家和国家权威的施行对象。笔者把所有服从国家权威的个人称为“受治者”,它通常包括一国的公民和逗留期限不定的居民。
国家行使最高政治权威的辖区(jurisdiction)既可以是地理性的,也可能是人身性的(personal)。地理性的辖区即为领土(territory),它标识现代国家的主权范围。但国家并非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如克里斯多夫·莫里斯(Christopher Morris)在《现代国家论》中指出,公元800年至1200年期间的欧洲封建制政治权威就严重依赖人身依附,“统治是人身性而非领土性的,这倒并不仅仅因为对某个特定土地的控制常常并不完全……更主要的原因是政治效忠(allegiance)的范围并非由领土来决定”(4)Christopher Morris, An Essay on the Modern St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2.。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欧洲封建国家的辖区主要是人身性而非地理性的。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完全因人身性效忠而确立的国家,其“领土”(或更准确地说,被该国管辖的土地)由服从该国权威的成员所拥有的土地拼凑而成(因而很可能是相当分散的),土地的形状和范围都随着成员政治效忠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是相当不稳定的)。换言之,在这样的国家中,“领土”只是人身性政治效忠的派生物(derivative)。
与之相反,现代国家的领土是连续(或相对集中)、稳定而独立的。特别是,现代国家一般允许其成员移民,但不允许因个人国籍的变化而导致国家领土的变化。假设A1在A国拥有一片土地,即便A1改变国籍成为B国公民,他在A国的土地仍然属于A国的领土。此外,现代国家的统治权或管辖权主要依据领土来界定,即它们把所有出现在其领土范围内的人都当作受治者,不管是公民还是游客都受其管辖。比如,一国的公民即便保持国籍不变,只要他居住于另一个国家,那在居住期间他将主要受居住国的管辖。可以说,对现代国家而言,领土是其“铁打的营盘”。
二、 什么是领土权
领土权是一个复合权利(a complex right),故“什么是领土权”的问题其实可以转换为“领土权包含哪些具体的权利”的问题,而答案无非就是从现代领土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解析出国家所主张的有关领土的权利。即便如此,源于对领土权之性质和对象的不同看法,政治哲学家们仍然会给出对领土权的不同界定。
约翰·西蒙斯(A. John Simmons)在2001年提供了对领土权的一个经典概念分析(5)A. John Simmons, “On the Territorial Rights of States”,Philosophical Issues 11,Ridgeview Publishing Company,2001, p.306.,在最近的著作中他进一步完善了该定义。按其更新后的界定,领土权包含了六个权利子项(incidents),它们分别是:
(a)在领土范围内通过强制执行国家法律的所有规则和命令而管理所有人行为的权利;(b)对领土范围内不是私人所有的土地和资源拥有完全的控制权;(c)对领土内私人拥有的土地和资源加以征税以及管制其用途的权利;(d)控制人和物跨领土边界流动的权利;(e)决定领土内所有人的地位(standing)的权利(例如,制定管理居民、外交地位和公民身份的规则);(f)禁止个人或团体实施领土分离或把领土转让(alienation)给其他非成员个人或团体的权利。(6)③ A. John Simmons, Boundaries of Author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4-5; p.125.
围绕西蒙斯树立的这个“靶子”,本文将展开针对领土权概念的三个争议点的讨论。
第一个争议点是(b)子项是否应该被视为领土权的一部分。领土权是一种最高的统治权(dominion)或管辖权(jurisdictional rights),所谓管辖权就是在辖区范围内制定、裁决和实施相关法律规则的权利,而(b)项中的权利指向了一种国家对公共土地的所有权(property rights),这是一种使用、处置所有物的权利。一般认为,领土管辖权是一种比所有权更为高阶的权利。卡拉·奈恩(Cara Nine)指出,对领土内自然资源的管辖权意味着限制或调整行使所有权的权利(如禁止出售某种自然资源或禁止在某地修建摩天大楼等)。(7)Cara Nine, Global Justice and Terri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2.西蒙斯定义中的(c)子项就反映了这一点。如果在对领土权的界定中混入公共所有权,那么作为公共土地之所有者的国家将和私人土地所有者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如私人可以和国家就某些公共土地的租用达成一项协议),而这与领土权所指向的国家主权地位不符。此外,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个完全不包含公共土地所有权的国家,但这并不影响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实施管辖权。出于这两个考虑,(b)子项应该被移出上述定义。
这也许会引来一个质疑:考虑现实中主权国家主张的领土权经常也包含资源权,在领土权定义中排除(b)子项并不妥当。对此,笔者的回应是:首先,国家主张的“资源权”既可能指向对自然资源的管辖权,也可能指向对公共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笔者在上一段的论述并没有排除前者,而只是排除了后者。其次,从评估领土权理论的角度看,如果在概念层面使得领土权包含资源或土地所有权,我们则似乎预先“歧视”甚或排斥了一些无法证成公共土地所有权的领土权理论;反之,我们则在评估领土权理论时能保持最大的开放性。最后,在对复杂概念的界定中,我们经常区分概念的核心要素和非核心但经常关联的特征(core elements VS. non-core, but frequently correlated characteristics),从这个角度看,本文完全可以承认国家的资源所有权是领土权的一个常见特征而非核心要素。
第二个争议点涉及西蒙斯定义中的(d)子项,即“控制人和物跨领土边界流动的权利”,学者们就它是一项管辖权还是所有权而产生分歧。西蒙斯本人并未说明这是一项什么权利,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他看来,“所有权具有管辖权的一面,正如领土管辖权也具有所有权的一面”(8);换言之,他并不认为领土管辖权和土地所有权可以被明确区分,这应该也是他把(b)子项放进领土权的原因。但笔者在上一段中已经指出,管辖权和所有权是可以被明确区分的。对于国家所行使的领土管辖权来说,控制人和物跨边界流动的权利是一种统治权,它高于所有权赋予的控制人和物跨边界流动的权利。但反对把(d)子项视作管辖权的学者也可能指出,按照我们在上一段中的定义,管辖权本身并不包含控制人和物跨边界流动的权利。例如,A国的某个州政府可以在州范围内实施管辖,而正常情况下它没有权利控制A国公民自由进出该州的权利。但这个论点站不住脚。地方政府的管辖权必须与国家的管辖权区分开来,后者具有主权性的地位。因此地方政府通常没有控制人和物跨边界流动的权利,这并不表示国家的领土管辖权就不能包含这一项。因此,(d)子项应该被视作一种管辖权而成为领土权的组成部分。
第三个争议点涉及领土权的对象。从对象上来说,(a)(e)涉及人的管辖,而(c)(d)(f)涉及对土地(及其自然资源)的管辖,因而这指向了两类不同的管辖权。于是,一种观点进而认为,从精确性考量,国家的领土权应该剔除(a)(e)两项,而只保留(c)(d)(f)三项。(9)笔者本人就曾持这一观点,参见朱佳峰:《洛克论领土权:纷争、辨析与新解》,《哲学评论》第2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5-16页。这一观点其实把领土权理解为了“对于领土的管辖权”(jurisdiction over a territory)。这种理解不能说错,但可能失之狭隘。如上所述,现代国家是依据领土来划分统治范围的,尤其是,现代国家中人身管辖权的范围主要是由领土界定的。因此,探究国家的领土权不仅仅是在追问国家是否对某块土地拥有管辖权,更为重要的是要回答,为什么国家的管辖权是以领土的方式来划分和组织的;换言之,领土权不仅仅是“对领土的管辖权”,而是更为广义的“领土化的管辖权”(territorialized jurisdiction)。显然,西蒙斯在定义领土权时采纳了“领土化的管辖权”的观念,因此才把(a)和(e)两项包含在内。
如果关于上述三个争议点笔者的论述是合理的,那么广义领土权则将包含(a)(c)(d)(e)(f)五个子项。本文中,笔者将采纳广义的领土权概念。从这个对领土权的界定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恰当的领土权理论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关于领土国家正当性的理论。
三、 为什么国家能够主张领土权
现在我们转到引言中提及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国家能够主张领土权?即:为什么国家能够主张领土化的最高管辖权?这个问题可被进一步分解为:(a)奠定现代国家管辖权的基础是什么?(b)为什么现代国家要以地理性辖区的方式来划分和实施管辖权?不难想象,问题(b)的答案与证成国家管辖权的基础密切相关:要么地理性辖区本就反映了这个基础,要么地理性辖区最有利于国家的管辖权服务于其基础。纵观已有的领土权理论,我们发现洛克式同意理论、民族主义理论、功能主义理论和政治自决理论的根本分歧在于对问题(a)的不同回答。
我们首先来看洛克式同意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的管辖权由个人在“社会契约”中转让部分自我管理权和土地所有权而形成,此理论当代最著名的辩护者是西蒙斯。(10)参见A. John Simmons, Boundaries of Author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洛克《政府论》中如下一段话准确地概括了该理论的要旨:“任何人既然为了保障和调整所有权而和其他人一起加入[政治]社会,却又认为他的土地……可以不受他……所服从之政府的管辖,这简直是一种直接的矛盾。”(11)洛克:《政府论》下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7页。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暗示了参与“社会契约”的个体(土地所有者)的地理相邻性,因为这种地理相近性带来的纷争和冲突使得“保障和调整所有权”成为签订“社会契约”的决定性理由。既然“社会契约”由地理上相近的人所签订,那么由此建立的国家的辖区就必然是地理性的。
洛克式同意理论虽然经典,但它也从来不乏批评者。他们或否认洛克式同意理论的前提,即否认个体的自然权利;或拒斥该理论的结论,即认为它对国家管辖权或统治权的正当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要求每个成员的同意)。但这些都不是笔者拒斥该理论的理由。笔者认为,洛克式同意理论的问题不在于自然权利本身是不可辩护的,而在于一种高度确定的自然权利(这是同意理论的基础)是不可辩护的。概言之,我们在“社会契约”中所能转让的权利应该是我们确定拥有的自然权利。但问题恰恰在于,无论是洛克,还是后来的洛克式政治哲学家,他们都无法证明仅凭人类理性就能在自然状态下确立人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自然权利(特别是土地所有权),而这正是地理上相近的人们陷入纷争和冲突的重要原因。既然人们所能拥有的自然权利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那么解决冲突的方法就不可能是契约,因为人们无法通过契约转让那些本就不确定拥有的自然权利。下文中笔者将进一步表明,拒斥同意理论的这个理由恰恰指向了洛克式功能主义国家理论。
我们再来看民族主义的领土权理论,此论当前最著名的辩护者是大卫·米勒(David Miller)。(12)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vid Miller, “Territorial Rights: Concepts and Justification”, Political Studies,2012,60(2),pp.252-268; David Miller, “Lockeans Versus Nationalists on Territorial Rights”,Politics, Philosophy & Economics,2019,18(4),pp.323-335.民族主义领土权理论的核心主张是:一个原生的、先于国家存在的民族(往往群居于某一地域)有权建立领土国家,以保持该民族的文化和认同、维系该民族与其居住地的关联等。作为一个国家理论,民族主义领土权理论的最大挑战在于说明到底是民族性的什么特征使得一个民族原则上应该独立建国。显然,仅仅诉诸民族的身份认同并不足以支持民族的政治自决,不然各种文化、宗教团体也都可以独立建国,而这显然是荒谬的。米勒曾主张,一个民族因为在其居住地上创造的物质和符号价值使得它有权管辖这个区域,以便实施某种整体性控制。(13)Miller, “Territorial Rights: Concepts and Justification”, Political Studies,2013, 60(2), p.263.但这个主张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方面,人们通常是以私人(包括家庭、社团)身份而非以民族的成员身份在土地上创造各种价值,因此他们所能拥有的是私人所有权,而非政治性的管辖权;(14)Anna Stilz, “Nations, States, and Territory”, Ethics, 2011, 121 (3), pp.576-577.另一方面,即便一定程度的管辖权是必要的,米勒仍然无法说明为什么这里要求国家层面的最高管辖权,而不仅仅是区域自治层面的管辖权。
根据玛格丽特·摩尔(Margaret Moore)的领土权理论,只有曾参与政治合作并且有治理能力的特定群体,即她所谓的“人民”,才有资格主张政治自决以成立国家。摩尔的核心论证是,“人民”的成员之间因政治合作而产生了集体自主(collective autonomy)价值,这是一种关系性价值。尊重这个价值意味着必须由同属一个“人民”的成员集体性地实现自我管治(self-government),成立国家。(15)Margaret Moore, A Political Theory of Terri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不同于民族主义的理论,并不是所有民族天然就可被看作是一个“人民”,这里的关键在于政治合作的经历。当然,为了避开“先有国家,才有政治合作,因而才有人民”的循环论证,摩尔主张对政治合作持一个宽松的定义,因而前国家的或亚国家的政治运动(例如反对殖民主义运动)也是政治合作。(16)⑥ Margaret Moore, A Political Theory of Terri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5-36; p.63.此外,有政治合作需要的“人民”大体上也群居于某一地区,因而据此成立的国家是领土国家。摩尔理论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说明为什么一个“人民”在政治上不应该受制于“他者”。
问题是:首先,谁可被看作是“人民”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在前国家或亚国家的政治合作中尤为显著,因为参与政治运动的人通常不是该地理范围内的全部人,那些疏离甚至反对政治运动的民众如何成为“人民”的一员?其次,实现政治自决后的国家应该承担什么功能?它应该如何对待组成“人民”的个体成员?摩尔的论述依赖于她对“集体自主”之价值的说明。但按照摩尔对“不依赖于关系的善”(relationship-independent goods)和“依赖于关系的善”(relationship-dependent goods)的区分,⑥“集体自主”是一种完全的依赖于关系的价值;与之相对,共同体成员得到公平的对待以及其人权得到尊重,这些善则是不依赖于关系的价值,即这些善的实现不依赖于该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特殊关系(一个宗主国也有可能实现对殖民地的“善治”)。由于在摩尔那里 “集体自主”的价值完全脱离了其他非关系性的道德价值(如人道、正义等),因此该理论的一个明显短板是:它允许哪怕是一个恶质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群体聚集于一地,通过长期的内部合作和对外斗争成为摩尔所谓的“人民”,从而获得独立建国的资格。(17)参见朱佳峰:《领土权:当代政治哲学论域中的理论图景》, 《学术月刊》,2018年第2期,第102页。
最后,我们来看功能主义的领土权理论。准确说,这是一个理论阵营,当下的代表性理论家是安娜·史蒂茨(Anna Stilz)和奈恩:前者提出了一个康德式的“正当国家理论”,而后者则捍卫了一个“洛克式集体主义理论”。把这些不同理论联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核心主张:国家的功能,也是其统治权的基础,在于实现辖区内的基本正义,即界定和维系一个大体上正义的权利体系;又因“正义的情景”指向地理上相近之人共同生活的境况,故国家的统治权必须以地理性辖区(领土)的方式来组织。在阐述和评判史蒂茨和奈恩的理论之前,我们不妨看一下功能主义领土国家理论的优势。首先,它反映现代国家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洞见,即:国家之所以必要,乃是因为它能克服自然状态中的纷争与失序。其次,在评估现代政治实践时,它具有更好的“理论敏感度”:按照同意理论,由于没有建立在成员的同意之上,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是不正当的;而按照功能主义理论的正当性标准,我们能从中区分出正当和不正当的国家。第三,功能主义国家观对辖区内受治者的语言、文化、族裔等群体认同特征没有要求,特别是它完全兼容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第四,按罗尔斯所谓的正义的自然义务(natural duties of justice),人们负有义务支持正义的机构(包括国家)。(18)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334.因此,对于那些在辖区内实现了基本正义的国家,他国负有不干涉的义务,这意味着该国享有政治自决的权利。不难发现,相比于摩尔的理论,在功能主义的理论中政治自决的权利和实施正义的功能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但功能主义的领土权理论面临至少三个重要的批评:首先,功能主义理论蕴含侵犯个人的自然权利的“道德风险”;其次,功能主义理论无力说明国家应该对具体哪一块土地主张领土权;最后,功能主义理论错误地认为主张领土权的最终主体是国家,而不是民族或人民。笔者将在下一节阐述洛克式功能主义理论时顺便回应第一个批评,第二、三个批评则留待论文最后一节来回应。
四、 哪种功能主义理论
洛克式同意理论认为,一旦我们接受为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那么国家的统治权只能通过“社会契约”由个人权利中自愿让渡而来。因此,同意理论认为,任何非自愿主义的国家正当性理论(包括功能主义理论)必然蕴含侵犯个人自然权利的“道德风险”。显然,功能主义理论想要避开这个指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否定个人的自然权利。(19)奈恩“洛克式集体主义理论”的一个蹊跷之处是,一方面她声称借鉴了洛克证成自然所有权的思路来证成领土权,另一方面其理论中完全不见自然所有权,事实上是以非常隐蔽的方式否认了自然所有权。笔者在别处对奈恩理论有更为详细的评论,参见朱佳峰:《洛克式政治哲学中的领土问题:对当代争论的反思》,《现代哲学》,2021年第5期,第104-111页。康德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特色正是对自然所有权的否定。笔者将对此作扼要介绍以便从中引出史蒂茨的理论。
康德政治哲学的起点是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因此没有人有权强制和支配他人。但这也意味着个人自由的施展要符合康德所谓的“法权普遍原则”,即要能够与他人的自由相容。法权普遍原则并不绝对禁止个人占有自然资源(包括是土地),但在自然状态下,个人对土地的占有就仅仅是通过个人意志施加义务于他人,是对他人自由的干涉,因而违背法权普遍原则。因此在康德看来,个人在自然状态中获得的土地所有权是暂定的(provisional)。克服这种暂定的状态对于地理上相邻之人来说尤其紧迫,因为他们在不可避免的交往和互动中都受制于这种暂定性。因而,他们负有义务(因而可被强制)进入一种法权状态,在其中国家凭“全面意志”(omnilateral will)的理念来立法,以求在领土范围内实现每个公民符合法权普遍原则的自由。(20)Immanuel Kant, “The Doctrine of Right, Part I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Prac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史蒂茨在《自由的忠诚》中所提出的国家理论在相当程度上照搬了康德的理论。(21)Anna Stilz, Liberal Loyalty: Freedom, Obligation, and the Sta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中译本参见史蒂茨:《自由的忠诚》,童志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只有在对如何保证国家的立法意志追踪“全面意志”的解释上,她偏离了康德本人接纳现实国家的保守结论,主张追踪“全面意志”而要求国家施行一种卢梭式的民主制,在其中公民必须完全摒除私人利益(哪怕是多数人的“众意”),而以实现每个公民平等的自由(即“公意”)为宗旨来参与立法。(22)Anna Stilz, Liberal Loyalty: Freedom, Obligation, and the Sta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pp.57-71.
这种康德式国家理论至少有两个问题:首先,它对洛克式自然所有权的否定缺乏说服力。洛克要求个人获取土地所有权时留给他人“足够且好”的土地,这其实意味着洛克同样主张人际间的自由必须相容(compatible)。但洛克不排除个人在自然状态下能理性地遵循这个相容性原则从而正当地获取土地所有权。康德不同意此观点。他认为,允许个人单方面阐释相容性原则(比如法权普遍原则)必然意味着个人对他人自由的不正当干涉;在他看来,只有以“全面意志”的理念为立法根据,对个人土地所有权的确认和调整才能真正符合法权普遍原则。问题在于,现实中个人判断固然会犯错,但无论如何设计政治制度,现实中的立法意志对法权普遍原则的判断同样可能犯错(它总是无法真正体现“全面意志”)。而如果仅仅讨论“全面意志”的理念,那么我们同样不能排除一个理想化的个人意志,它按严格法权普遍原则行动,因此使得个人能正当地获取自然所有权。其次,即便接受康德法权学说的论述,其内部的逻辑也会导向对领土国家的“克服”而迈向一个世界国家。这是因为完善的法权状态须让立法意志体现“全面意志”,而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意志”应该包括地球上的所有人(而不仅仅是一国之公民),也即国家仍然不是最完善的法权状态。(23)参见Sharon Byrd, Joachim Hruschka, Kant’s Doctrine of Right: A Commenta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因此,如果说自然状态中暂定的土地所有权充当了一个通向更完善的法权状态(领土国家)的台阶,那么领土国家其实也只是在为通向最完善的法权状态(世界国家)作铺垫。
也许正因为康德国家理论的上述缺点,史蒂茨在后期的国家理论中作了两个调整。首先,她诉诸个人自主性(personal autonomy),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可以正当地获得一种“占用权”(occupancy rights)。这种对土地的权利比所有权要弱,它只包含居住、使用土地的权利,而不包含买卖获益以及遗赠等权利。但占用权仍然是不确定的,因此它不排除国家进行界定和执行的功能。(24)Anna Stilz, “Occupancy Rights and the Wrong of Removal”,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013,41(4), pp.324-356; Anna Stilz,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其次,她不再要求国家实行卢梭式的民主,而只要求“现实的多数意志”(actual popular will)支持国家的制度与运作。(25)Anna Stilz,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94.这两个调整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其实揭示了史蒂茨对康德政治哲学的背离。一旦主张在自然状态中个人可单方面正当地获取“占用权”,史蒂茨就等于承认康德理论中的“全面意志”不再是正义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她的立场和洛克一致)。既然在史蒂茨看来,国家不再需要卢梭式的民主制使得立法意志追踪“全面意志”,那么对于维系国家实现基本正义的功能而言,(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足矣。
但史蒂茨后期的功能主义国家理论的弱点正在于,既然其立场接近洛克,那它就会招致来自西蒙斯等人的如下批评:为什么诉诸个人自主性证成的是“稀薄”的占用权,而不是所有权?买卖、馈赠占有物的权利难道不也能体现或拓展个人自主性吗?毕竟连康德都承认,个人自由的展开与实现必然需要所有权(只是在他看来,自然状态中的所有权是暂定的而已)。我们不难猜测,史蒂茨的顾虑是,一旦承认自然状态中所有权的正当性,那必然会导向同意理论。但她又不想追随康德,因此她只好设想一种比所有权更弱的自然权利;但问题在于,实现个人自主性所要求的远不止占用权,其更指向了所有权。
不同于史蒂茨,笔者认为在论述领土权时无须否定或忽略自然所有权。但不同于西蒙斯等人,笔者不认为自然权利蕴含(entail)同意理论;相反,维系一个稳定、融贯且复杂的所有权体系内在地要求一个具有管辖权的领土国家,在这一点上笔者又同史蒂茨相似。笔者把这个立场称为“洛克式功能主义理论”。本节余下篇幅中笔者将对此作简要介绍。
我们如何设想正当的自然所有权?如上所述,洛克认为人们的自由应该是相容的。这首先意味着,一个人获取所有权不应该排除其他人获取类似的所有权。因此,自然所有权的辩护者们一般都持有某种版本的“洛克式限制条款”(the Lockean Proviso),它要求个人在获取自然资源时留给他人“足够且同样好”的份额。此外,当多个自然所有权持有者在地理上相互临近因而每个人对所有权的行使将很可能影响到他人的所有权以及生命时,每个人对所有权的行使则将受到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并不依赖于权利所有者的同意,而源于上述相容性要求。因此A不能在其土地上恶意地筑高墙,不然便对其邻居B的所有权的行使构成了干涉。
为了使同意理论成立,西蒙斯等人必须预设人们的自然所有权不但是正当的而且是确定的,因为只有确定拥有的权利才可以通过契约转让。但这个预设显然过于乐观。注意,上述两个相容性要求仍然是抽象的,在试图建立具体的自然所有权时,我们必然要对它们作进一步的解释,而人们对这个解释必然会有所谓的合理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s)。首先,对洛克式限制性条款的理解,即便在洛克式政治哲学家之间也并未达成什么共识,由此形成了所谓平等主义和非平等主义(如诺齐克的解读)之争;就是在平等主义阵营内部,对于“足够且同样好”也有资源主义(要求根据资源的平等价值而分配)和福利主义(要求根据资源对个人福利的平等促进而分配)之争。(26)对此争论的简要回顾,参见Peter Vallentyne, “Left-Libertarianism and Liberty”,Thomas Christiano,John Christman ed.,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Wiley-Blackwell, 2009,pp.138-144。因此,个人在洛克式限制条款下到底能获取多大块土地的所有权,这在自然状态下凭借人的理性是很难确定的。其次,合理分歧也将困扰关于人际间如何行使土地所有权的相容性要求。假设A占有的一块土地完全满足洛克式限制条款,但A对土地内某些资源的使用具有“负外部性”(如开矿或排污)从而影响到其邻居行使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从相容性考虑,则A所拥有的关于这些资源的使用权将不再是完全的。但在具体确定A的使用权时又会面临一系列争议。比如:A完全不能排污么,还是可以先排污后付费?付费的标准如何确定?
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人类理性虽然能为具体化这些限制提供原则性指导,但其效力将相当有限,因此依据不同情形,自然所有权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面对不确定的自然所有权以及有可能产生的争端,人们需要一个公共、权威的调控规则,这些规则的应用或裁定范围正是自然权利不确定的部分,其功能也在于使得争议中的权利变得具有确定性。这个规则的权威不是源于权利所有人的让渡(他们无法让渡不确定拥有的权利),而是源于证成自然所有权的内在道德限制,即上述两个相容性要求。这些调控性规则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我们不难设想,在一个村落般的小规模土地所有权体系中,一些自发形成且行之有效的习俗将充当这些规则,而为了维系一个大规模的权利体系(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体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其他权利关系),一个单一的公共政治权威(领土国家)将是必要的,它将发挥提供与执行调控性规则的功能。(27)参见朱佳峰:《洛克论领土权:纷争、辨析与新解》,《哲学评论》第2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95-96页。
五、 什么主体对哪块土地可主张领土权
在第三节中,我们提到了功能主义领土权理论面临的三个批评。在第四节中,笔者试图论证,洛克式功能主义领土权理论可以避开第一个批评,即它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然权利的侵犯。第二、三个批评是,功能主义理论无力说明国家应该对具体哪一块土地主张领土权,以及它错误地认为主张领土权的最终主体是国家,而不是民族或人民。本节笔者将阐述洛克式功能主义领土权理论如何回应上述两个批评。
第二个批评涉及领土权文献中所谓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问题,它旨在探究一个国家为何能对一块特定的土地主张领土权。“特殊性”问题其实可被分解为两个子问题,分别探究领土的位置和领土的形状(包括面积和边界)。不同的领土权理论对于“位置”问题的回答趋于一致,即领土的位置通常取决于一国之国民所实际栖居、生活的地方。这一点亦为洛克式功能主义理论所认可,据此,国家领土的位置就是其国民事实上所形成的一个土地所有权体系的地理区域。但不同领土权理论对于“形状”问题的回答则大不相同。同意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往往被认为在回答“形状”问题上具备独特优势。对前者而言,领土形状取决于缔约者所拥有土地的形状和面积;对后者而言,领土形状也主要取决于一个民族原本栖居土地的形状和面积。换言之,根据这两种理论,领土形状之所以是固定的,是因为任何扩张领土面积的举动必然会侵犯他人的自然所有权或侵犯其他民族的领土权。与之相对,功能主义领土权理论往往被认为无法说明领土形状何以是固定的。批评者通常会指出,既然按照功能主义理论,领土权的规范性基础在于国家实施正义的管治,那么一个正义的国家似乎可以强行把本不属于其领土的周边土地纳入管理,使之成为辖区的一部分,只要该国家在吞并这些土地后能实施正义的管治。但这种以正义之名实施的扩张主义显然与领土形状基本固定的现代国家领土权体系相冲突。(28)参见A. John Simmons, Boundaries of Author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38。
洛克式功能主义理论如何回应这个批评?我们不妨进一步分析,按洛克式功能主义领土权理论,维系着一个庞大、稳定的土地所有权体系(S1)的国家将如何“看待”周边的土地(L)。这些周边土地不外乎两种性质:它们隶属于或不隶属于另一个庞大稳定的土地所有权体系(S2)。如果属于S2,那么按照洛克式功能主义理论,这个维系着S2的国家就能正当地对这些土地主张领土权,因此其他国家就无权吞并。如果不属于,那L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但地理上的相近性意味着人们之间的交往迟早会在L与S1之间建立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这就需要一个容纳L和S1的全新土地所有权体系,因此原先代表S1的国家把周边土地L纳入管治便不能算“吞并”,这种扩张为洛克式功能主义的原则所允许。
第三个批评涉及主张领土权的最终主体。批评者指出,按照典型的功能主义理论,既然只有国家(作为一套行使政治权力的制度框架)才具有实现基本正义的功能,那么只有国家才能主张领土权。但这意味着,一旦面临国家失败(如索马里)或国家消亡(如纳粹德国),这些国家的受治者或人民将无法对其所栖居的土地主张领土权,因此这些土地就可以任由他国吞并。这个结论显然是不可接受的,相反我们普遍认为二战后的德国人民应保有在其土地上重建国家的权利。据此,批评者认为,主张领土权的最终主体必然不是作为制度架构的国家,而是有权主张政治自决的人民或民族。(29)参见Cara Nine, Global Justice and Terri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pp.54-55。
但这个批评误解了功能主义领土权诸理论(包括洛克式功能主义理论)。这些理论都无须否认“人民”具有政治自决的权利,因此它们完全可以承认二战后德国人民保有在其土地上重建国家的权利。真正的问题在于,哪些人可以被当作同属一个“人民”?论者基本都同意,具有共同的“政治合作”历史的人们才能成为“人民”。但如何界定“政治合作”?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在一定地理性辖区内受相同的政治框架管治的所有人都可被认为是参与了“政治合作”;也就是说,“人民”的形成依赖于一个共同的政治框架,其人员范围包括应用该政治框架的地理辖区上的所有人。考虑到共同的政治框架和地理辖区的组合在通常情况下就是领土国家,因此功能主义理论主张,先有领土国家(无论国家作为一套管治架构是如何建立的),然后才产生“人民”。据此,功能主义理论便能说明为什么二战后的德国人仍然同属一个“人民”并因此享有政治自决的权利。
非功能主义理论家对此主张的可能质疑是:有些殖民地在实现其政治自决之前不曾是一个领土国家,因此按照功能主义领土权理论,这些殖民地上的人们就不能算“人民”,从而无权主张政治自决,但这个结论显然有悖于“殖民地人民拥有政治自决权”这一广为接受的信念与政治实践。面对此质疑,洛克式功能主义理论的独特优势在于,它能够承认,政治框架和地理辖区的组合不但指向领土国家,也包含了殖民地政治。这是因为,一方面,殖民地上的所有人确实因受同一套(压迫性)政治框架的管治而被纳入进了一个庞大且独立的权利(特别是土地所有权)体系中,而他们无论是否参与到对殖民宗主国的反抗运动之中,在独立建国后都会被认为是“人民”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宗主国为了方便统治而给殖民地划定的“行政边界”往往也是该殖民地实施政治自决后的领土边界。换言之,洛克式功能主义理论恰恰有助于说明在何种意义上殖民统治把殖民地变成了一个潜在的领土国家。
六、 结 语
本文在厘清现代领土国家的特征以及领土权之概念争议的基础上,检视了当代政治哲学视域内几种主要的领土权理论,进而提出了一种笔者称之为“洛克式功能主义”的领土权理论。作为一项政治哲学研究,洛克式功能主义理论所设想的现代国家领土权仍然是一个罗尔斯意义上的“理想理论”:它并非乌托邦,但它的实现有赖于在自然和历史的有利条件下所有行动者(个人与国家)严格按照该理论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行动。(30)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245-246.
显然,现实中的国家领土不是按照上述理论来划定的;相反,形成当下各国领土边界的政治过程中掺杂着各种自然界的偶然性(如依据特定河川划定边界)和人类行动中的非正义性(如历史上的各种侵略征伐)。这引发一个疑惑:既然理论和现实不一致,本文所阐述的洛克式功能主义理论有什么现实意义?大致上,我们可以说,在要求现实趋于和理论一致的问题上存在两种非常不同的思考方式。一些理论主张“向后看”,即:分析当下现实为何会错误地偏离理论,并试图通过纠正“历史不正义”来使得现实趋向于理论。就领土权理论而言,民族主义的领土权理论通常采纳这种思路。另外一些理论主张“向前看”,即:接受既定现实,然后思考如何在既有约束下朝理论所设想的方向改进现实。笔者认为,洛克式功能主义理论的一个优点是它具有“向前看”的优势。按此理论,既有的领土权体系意味着,除却少数失败国家,绝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在为国际社会所认定的领土范围内各自建立起了一套独特的权利(特别是土地所有权)体系。这些不同的权利体系或许在稳定性、融贯性和正义性上有所差异,因而有些国家目前未必满足洛克式功能主义理论所设立的正当性条件。但审慎且可行的改进方法不是对现有国家的领土版图“推倒重来”(这必然会带来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而是思考如何发展各种国际规约机制和合作框架来缩小一些国家的“正当性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