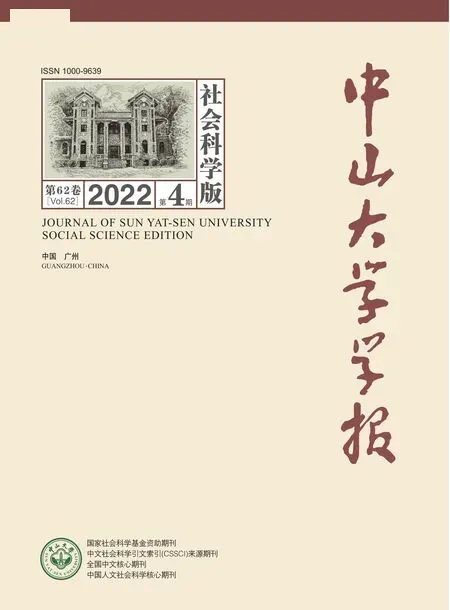王妙如:被忽视的女权先驱*
——兼及佛学与晚清女权思想的发生
马勤勤
晚清风云变幻,思想激荡,借助西学东渐之风,各种与传统相异的新学说竞相出现,从诸多方面影响并重塑了近代士人的精神与生活。其中,女权思想的发生及随之而来的百年妇女解放运动,无疑是其中最重要且最有代表性的事件之一。然而,提起中国女权思想的发生,人们似乎首先会想到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金天翮等男性知识分子的倡导之功。在晚清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初始阶段,男性知识分子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在中国女权思想发展史上,女性也绝非完全无声的“空白之页”。已有学者陆续发掘出吴孟班、何震等若干“女性女权先驱”,论析其以女性本位的言说立场,显现出或多或少有别于男性论者的“异音”,从而在中国女权思想发展史上熠熠生辉。不过,在以上开列的名单中,应该有本文主人公王妙如的名字。
在今人的记忆中,提及王妙如的名字会感到有些陌生,但是知道其苦心孤诣之小说《女狱花》的却大有人在。1904 年问世的《女狱花》,曾被誉为晚清“描写当时女子的不幸与苦痛生活”①阿英:《晚清小说史》,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55页。的代表作。关于小说之倡女权、兴女学,前人也多有论及②代表性的研究有:魏文哲《〈女狱花〉与〈女娲石〉:晚清激进女权主义文本》,《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吴宇娟《论〈女狱花〉中呈现的晚清女学、女权》,《岭东学报》2004年16期;黄锦珠《妇女本位:晚清(1840—1911)三部女作者小说的发声位置》,《中国文学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第53—77页。,但目前研究更多还是着眼于散点式的文本细节,并未将之与作者王妙如的整个女权思想体系相联系,更未注意到其佛教底蕴。事实上,《女狱花》中的女权思想不仅自成系统,而且还有着清晰的结构层级与实践步骤,具有明确的“实操性”;更重要的是,因其与佛学思想的重要关联,使得王妙如在中国女权思想的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别开生面。
此前,笔者已经考证出王妙如之夫罗景仁曾就读于日本东本愿寺创办的杭州日文学堂,并揭示出《女狱花》与日本净土真宗在近代中国传教事业之间的隐蔽关联①参见马勤勤:《〈女狱花〉与近代日本佛教东来》,《复旦学报》2022年第3期。。本文将在中国女权思想发展史的脉络中,重审王妙如另类的女权思想和女权实践,展现其剥离民族国家话语而更加纯粹的女性本位立场,进而抉发晚清佛学与中国女权思想发生之一端。
一、晚清女权论述中的佛学位置
在深入分析《女狱花》的女权思想之前,有必要先厘清在此之前的中国女权思想的基本情况及话语资源。中国女权思想的发生是西学东渐的典型事件,它存在一个逐渐演变的历史过程,简而言之,早期并没有出现“女权”这个词语,在戊戌变法前后形成并流传的还是“男女平等”一语,至20 世纪以后,“男女平等”才逐渐被“男女平权”尤其是“女权”的说法置换②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1页。。
戊戌时期,随着西方平等自由思想的传入,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无可抵挡的西方势力面前,发现“男女平等”或“男女平权”是西方文明昌盛之国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梁启超所说:“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③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既然如此,推行“平等”自然时不我待;然而如何诠释“平等”,则需要在多重话语资源中斟酌协商。
面对“男女平等”这个有些陌生的概念,时人首先想到的是从中国传统典籍中发掘符合时代特征的平等新意。为此,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古代中国,如陈炽即说“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古人立教男女并重,未尝有所偏倚于其间也”④陈炽:《妇学》,《清末民初文献丛刊∙庸书》,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年,第383页。。尽管梁启超十分向往美、日诸国的“男女平权”,但也不无自豪地宣言:“三代女学之盛,宁必逊于美日哉!”⑤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时务报》第45册,1897年11月。与之类似的,还有“妻者齐也”的说法,例如皮锡瑞在南学会第九次演讲中即假借对传统三纲五常的重新解释,认为“尊夫卑妻”不合“中国古法”⑥《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九次讲义》,《湘报》57号,1898年5月11日。。以上论述策略均以“平等”为媒介,刻意在“古代”中国与“当下”西方之间画上等号,从而凸显一种奇妙的“时差”。
除去这些“周秦以前男女平等”之类的笼统说辞之外,诸如儒家之“仁”、墨子“兼爱”、道家“阴阳学说”,甚至佛家“众生平等”和基督教“爱人如己”,也都成为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晚清诸家的平等思想取源驳杂,但基本最后会归于一宗。例如,康有为曾号称“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而悟出“男女齐同之法”⑦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3页。,但最终认定只有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念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谓为“人类公理”。又如,皮嘉祐虽声称“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佛氏,立法于泰西”,但最终还是归宗墨子,称“佛法之平等”与“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己”,均“出于墨子之兼爱”⑧皮嘉祐:《平等说》,《湘报》58号,1898年5月12日。。再如,谭嗣同也曾有意会通孔、佛、耶三教,同时兼取墨家,但最终还是归于儒家之“仁”;《仁学》标举“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⑨谭嗣同:《仁学》,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页。,故“男女内外通”即指男女平等。
梁启超尝言“晚清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学”,又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64页。。佛学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已为学界所公认,上文言及的康、梁、谭诸人,无一不深受佛学影响,并借此来汇通、阐释和介绍他们的政治理想①参见葛兆光:《论晚清佛学之复兴》,《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101页。。于是,在当时有关“平等”之义的阐发上,不难看到佛家身影,但奇怪的是,论者最后的落脚点却俱不在此。可以这样讲,在19 世纪末中国“男女平等”或“男女平权”的思想版图中,儒、道、墨、佛、耶诸多话语资源众声喧哗,纵横交错;佛学作为其中的重要一支,虽反复被提及,但在“竞争的话语”中却始终落败,从未被树为正宗。不仅如此,进入20 世纪之后,伴随着西方“女权”观念的传入,“男女平等”或“男女平权”的说法也逐渐被“女权”一词所取代,其中驳杂的思想来源更不复存在。
根据日本学者须藤瑞代在《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一书中的考证,“女权”一词系从日本翻译而来,最早见于1900年3月《清议报》的福泽谕吉《男女交际论》译文,序言曰:“先生喜言女权。”②[日]须藤瑞代:《近代中国的女权概念》,王政、高彦颐主编:《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7页。真正产生影响的文本,是三个月后刊于《清议报》的石川半山《论女权之渐盛》译文,但这毕竟只是一篇新闻报道性质的短文,并无深邃的理论内涵。此后,在中国女权思想发展史上树立丰碑的人物是马君武,他的功绩主要是两篇翻译:一是《斯宾塞女权篇》,1902年11月与《达尔文进化论》合刊,由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二是《弥勒约翰之学说》,1903年4月发表在《新民丛报》,第二节“女权说”专门介绍了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和社会党人的《女权宣言书》。文章指出,女权革命是民权革命的重要基础,二者不可分离,倘若女性不能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力,则民权革命关于“天赋人权”的理论便不能全部实现。自马君武翻译的两篇文章问世之后,晚清学界对于女权理论的溯源,便由过去的道听途说、众口异词而渐趋一致③参见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第74—77页。。1903年,金天翮《女界钟》问世,“绪论”开章名义,称女权学说是“弥勒约翰、斯宾塞之徒倡之”,而“民权与女权如蝉联跗萼而生,不可遏抑也”④金天翮著,陈雁编校:《女界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4页。。1904年,柳亚子在追溯女权思想的来源时说:“海通以来,欧美文明窈窕之花,将移植于中国。弥勒约翰、斯宾塞之学说,汽船满载,掠太平洋而东。”⑤倪寿芝(柳亚子):《黎里不缠足会缘起》,《警钟日报》第13号,1904年3月。直到1917年《新青年》刊出的曾兰《女权平议》,仍称:“欧洲自卢梭、福禄持尔、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诸鸿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⑥吴曾兰:《女权平议》,《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
至此,19世纪末流行的“男女平等”或“男女平权”的说法,已完全被“女权”一词所取代;中国有关女权发展的叙事,也由过去儒、道、墨、佛、耶等多种话语资源的“众声喧哗”,演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移植”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泰西”或“欧美”才是“女权”的真正故乡,是一朵在它处已经长成了的“窈窕之花”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开启一段新的文明之旅。如果说在戊戌时期的旧故事里,人们还在努力从传统典籍中翻出“话头”,以期解释出平等新意;那么,在20 世纪初年的这个全新的故事里,则已经决定抛弃古老的中国,更彻底地去拥抱西方,借助批判中国传统的不平等来主张新的平等观。有趣的是,无论在哪个故事里,佛学都从未被视为正宗或典范。也正因如此,我们今天也从未正视过佛学与中国女权思想之间的关系,只觉得它曾短暂地作为晚清女权话语的取源之一,昙花一现之后很快就偃旗息鼓,悄无声息的退场了。然而,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佛学与女权的关联不仅在王妙如1904 年出版的小说《女狱花》中有所体现,而且大放异彩。因此,有必要重新钩沉还原王妙如女权思想与佛学之间的关系,进而补全中国女权思想发展史链条上失落的一环。
二、王妙如女权思想的佛学渊源
王妙如,名保福,钱塘人,生于1878 年前后,大约卒于1904 年。她幼显聪慧,嗜读诗书,二十三岁嫁给同乡罗景仁,结缡未足四年即去世。除小说《女狱花》外,尚有《小桃源》传奇和《唱和集》诗词,惜未传世。她曾对罗景仁感慨“近日女界黑暗已至极点”,故立志写小说,以“秃笔残墨为棒喝之具”进行女界“革命”之事。《女狱花》写完不久,王妙如就去世了,罗景仁遂将小说自费出版并亲自撰写跋文,以志怀念①罗景仁:《跋》,西湖女士王妙如:《女狱花》,光绪甲辰刊本,第69页。按,本文所引《女狱花》文本俱出于此,下文不再出注。。王妙如的女权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传世之作《女狱花》中。
《女狱花》又名《红闺泪》《闺阁豪杰谈》,全书共十二回,有光绪甲辰(1904)刊本,题“西湖女士王妙如遗稿,中国青年罗景仁加批”。小说塑造了两个主要的女性人物——沙雪梅与许平权,她们都要争取女权,但具体手段和道路却完全不同。沙雪梅是个激烈的女权主义者,主张以流血革命之非常手段,行夺权之目的;而许平权则主张和平改革,强调“不施教育,决不能革命”(第八回)。尽管王妙如并不认同沙雪梅的流血革命,但也不否认其可能带来的实际功效:“今日时势,正宜赖他一棒一喝的手段,唤醒女子痴梦,将来平和革命,亦很得其利益。”(第八回)相较于沙雪梅,王妙如显然更倾向平和、稳健的许平权,认为女性需要通过教育,在思想道德和知识水平上达到和男子相同的程度,“今女子竟能自食其力,若男人犹行野蛮手段,无难与他各分疆域,强权是无处逞的”(第十一回)。与之相对,王妙如也为二人安排了完全不同的结局:沙雪梅革命失败,与党人自焚而死;许平权则东渡日本学习师范,归国后创办女子学校,在她的努力下,十几年后女界大昌,“女子状态很是文明,与前时大不相同。做男子的,亦大半敬爱女子”(第十二回)。
王妙如塑造了沙雪梅与许平权这两个典型人物,其实也在她们身上寄予了很深的用意。沙、许二人不仅仅是有血有肉的小说人物,同时也是象征意义上的“女权符号”,代表着两种不同来源的女权学说。前文已述,自马君武译出《斯宾塞女权篇》和《弥勒约翰之学说》,晚清的女权叙事便由此前的众声喧哗走向一致,其强调者主要有二:一是女权为欧美文明的产物;二是女权的理论基础为“天赋人权”,是人权得以实现的基础。于是,《女狱花》中出走家庭、从事革命的沙雪梅发出了如下宣言:
我闻天的(地)生人,生命与自由同赋,因泰西人常说,自由与面包不可一日或缺。若缺了面包,人要饿死。缺了自由,人亦要困死的。(第四回)
“生命与自由同赋”一句,明确点明沙雪梅所接受的正是西方“天赋人权”的人权平等观念。相较之下,许平权与黄宗祥的对话则表达了如下女权宣言,显得十分特别:
我闻天的(地)生人,无分男女,则男女应该平等的。(第十二回)
如果说在沙雪梅的观念中,“天的生人”与“男女平权”之间还存在一个重要关节——“生命与自由同赋”,是上天赋予了其子民同等的权力和自由;那么在许平权看来,天地生人原本就没有男女之分,“男女平权”是一个自然而然、无需论述的命题。其实,许平权的这种令人感到有些陌生的平等观,就来源于佛教的众生平等、无二差别。前引两句话,同样以“天的生人”的整齐句式写出,前者出现在沙雪梅第四回在狱中的演讲,后者来源于许平权第十二回在女学堂开学仪式上的演说,宣讲的对象也都是女性。如此,不得不让人赞叹《女狱花》构思布局之严谨巧妙。
那么,在许平权看来,佛教思想究竟是如何与“男女平权”相互连通的呢?这就必须从佛教的女性观说起了。作为反对印度婆罗门种姓特权制度的宗教,佛教从创立之日起,便主张众生男女具有相同之佛性,皆平等。原始佛教的基本经典《长阿含经》云:“尔时无有男女、尊卑、上下,亦无异名,众共生世,故称众生。”②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22,《大正藏》第l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3年,第145页上。就是从众生平等的角度,强调形有男女,性无彼此。尽管在小乘佛教时期,曾将原始佛教“制度上的男性优越主义”和“修行上的女性厌恶主义”等特点发挥到极致,视女性为淫欲、邪恶的标志,采取极端的厌恶态度①参见释恒清:《菩萨道上的善女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0—43页。;但是到了大乘佛教时期,又重拾原始佛教本义,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称“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②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第8册,第749页中。,从“空”义出发重申了众生同一本体,无二分别。可以说,这里“空”的思想正是平等意义的实践,是种姓、男女、一切众生之间的平等③参见永明:《佛教的女性观》,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95—96页。。
可堪印证的是,王妙如在《女狱花》第五回中借助许平权之手,写下了著名女权诗。开篇第一句“情天从古未偏颇,男女平权剏释迦”,“情天”即佛教的“有情世间”,指的是有情识的生物(如人与动物),也就是所谓的“众生”④佛典将世界分为“有情世间”与“无情世间”,与“有情”相对,“无情世间”即指植物宇宙、山河大地等无情识的生物,也叫“器世间”。参见林伟:《佛教“众生”概念及其生态伦理意义》,《学术研究》2007年第12期。。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有情”众生平等,释迦牟尼创立了男女平权之说。也可以说,“情天从古未偏颇”一句,就是许平权所说的“天的生人,无分男女”。这首女权诗出现在《女狱花》第五回,此时许平权尚未正式出场,仅是以“佛婢”的别号在酒店墙头留下此诗,引得观者沙雪梅连连赞叹,引为知己;同时也为后来二人相见,又因女权道路的分歧而发生一场唇枪舌战埋下伏笔。
作为《女狱花》中最重要的两个女性人物,沙雪梅和许平权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来源的女权学说,这从她们女权思想发生及变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女狱花》甫一开篇,沙雪梅隆重登场,于“十九殿”的梦境中看到一幅女性受苦受难的“地狱图”:
里面上头高耸耸坐着老老少少、贫贫富富的无数男子,底下笑嘻嘻跪着老老少少、贫贫富富的无数女人,且与一群一群的牛牛马马一同跪着,旁边摆着从来未见过的各种刑具。
这一阶级森严、布满刑具的“女狱”,无疑是中国女性数千年来遭受男性压迫与奴役的缩影。梦中男子的作威作福,女子的愚昧麻木,在沙雪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为她日后走上女权革命之路的重要关节。然而梦醒之后,她“细把这梦思寻,终不能猜出有什么道理”,直到第三回读到《斯宾塞女权篇》才猛然醒悟:“是了是了,我做女儿的时候,不明明做过一个梦么……我前时模模糊糊,不知这个道理,今日想来,一丝不错。”接下来痛骂“男贼”,反抗丈夫的压制并失手将其杀死。很明显,沙雪梅的女权思想,是阅读马君武所译《斯宾塞女权篇》之后得到开悟。作为晚清诸种女权思想之源头,王妙如设计让沙雪梅通过此书顿悟到男女平权的道理,从而走上女权革命之路,实乃水到渠成,无任何突兀不妥。
相较之下,许平权的女权思想获取方式就显得有些吊诡了。《女狱花》第九回,王妙如借助沙雪梅党人张柳娟之口,讲述了许平权的思想变化过程:
岂知平权自她父亲死后,性质忽然更变,日日夜夜看着大乘佛经,为人甚是冷淡。与妹妹的意思,渐渐不合……到了去年,常因女权之事,与妹妹大起冲突。她的古怪话语,我也不欲尽说。
可见,许平权与沙雪梅党人张柳娟自幼一起长大,本来志同道合;但自从沉迷于大乘佛经,思想为之一变,不仅为人变得冷淡,更因宗旨不合与张柳娟冲突不断。在此,王妙如巧妙地向我们展示了沙、许二人不仅女权思想的来源不同,其中还存在着一重不平衡的阶序——沙雪梅是从懵懂无知走向“革命”,而许平权却从“革命”走向“平和”;其中,更隐含了《斯宾塞女权篇》与“大乘佛经”的高下对比。事实上,这种对于佛教特别是对大乘佛教的尊崇,在《女狱花》中也并非仅此孤例,如许平权第十一回在女学堂的演说:“我释迦涅槃说法,本为万古不灭的大教,应该人人皈依的。但那些(和)尚尼姑,非但大乘经典未曾入目,即小乘经典,亦未能了解。”
此前,笔者已考证出王妙如的夫君罗景仁曾就读于日本东本愿寺创办的杭州日文学堂,夫妻二人深受日本净土真宗影响,在《女狱花》中还留下了不少相关细节,此处不多赘言。与中国相比,日本佛教有一个显著特点,即非常重视大乘佛教的实践主义精神,提倡游历于社会,特别是在平民中从事教化活动①何燕生:《近代文明对话中东亚佛教知识的重构——以“大乘佛教”为中心》,《哲学研究》2020年第5期。。也因如此,佛教曾在日本教育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推动了近代平民教育的发展②关于日本佛教与教育之关系,参见张玉姣:《日本佛教教育初探》,《佛学研究》2009年第1期。。《女狱花》体现了王妙如对佛教众生平等、无二差别的平等观的笃信,并以之为女权思想的理论根基;同时在实践层面上,她奉行大乘佛教“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实践精神,兼取日本佛教的“兴学”特色③参见马勤勤:《〈女狱花〉与近代日本佛教东来》,《复旦学报》2022年第3期。。可见,王妙如这一具有佛学特色的女权思想虽显另类,但也渊源有自,别是一家。她之所以在《女狱花》中苦心经营,塑造出沙雪梅与许平权这两个典型人物,就为了展示两种不同来源的女权学说之间的“缠斗”;而许平权的成功,无疑是大乘佛经之于《斯宾塞女权篇》的胜利,更是佛教“众生平等”之于西方“天赋人权”的较量。不仅如此,这些出现在《女狱花》中的不同来源的女权学说,还进一步标记了王妙如女权思想体系中的结构与层次,并规导了其日后的女权实践。
三、王妙如女权思想的结构与实践
在《女狱花》中,除沙雪梅和许平权这两个“典型人物”之外,还出现了7位女性人物,即文洞仁、董奇簧、张柳娟、吕中杰、仇兰芷、施如曌、岳月君。其中,除了第六回出场的写小说醒世的文洞仁、第七回现身的先为沙雪梅疗病、后随许平权游学海外的董奇簧之外,其余5人都是沙雪梅党人。她们日夜组织密谋,视流血革命为振兴女权的唯一途径,革命失败后,又一同自焚而死。文洞仁之名,顾名思义是“以文动人”。她自述幼年缠足导致身体羸弱,“不能为同胞上办一点儿事业”,但有鉴于这世上“有能行之豪杰,有能言之豪杰,有能文之豪杰”,故“学那能文的豪杰,稍尽些女国民的职任”。对此,罗景仁批注:
激烈党、平和党起,中立党亦追风逐电而起。此中立党,并非中立于新旧,实中立于激烈与平和,其生平思想,恐激烈惨行破坏,平和难以建立,故每以笔墨生涯为醒世之具。(第六回)
不难看出,相较于沙雪梅等6 人代表的“激烈党”、许平权代表的“平和党”,文洞仁则属“中立党”,“每以笔墨生涯为醒世之具”是其特点。在王妙如看来,她代表的是在沙、许之外的第三种女权道路,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可堪与她们并驾齐驱。正如罗景仁评语曰:“作者此回中特出中立党之文洞仁,吾知其学有根底、笔无疏漏矣。”(第六回)
再来说董奇簧,一望便知此名取谐音,意为“懂岐黄之术”。董奇簧出现在小说第七回,此时沙雪梅刚刚越狱来到文洞仁家里,连日奔劳使她“忽觉四肢酸痛,身上发起热来”,却被庸医下了猛药,“身上的热愈觉如火炭一般,兼且人事不知”(第六回)。正在文洞仁焦急流泪之际,住在隔壁的董奇簧来了,她“西医上的学问,虽未知晓,中医上的功夫,很是研究的”。果然,董奇簧很快就找准了沙雪梅的病根并对症下药,治好她的病。当被问及“姊姊学此医道,未知目的何在”时,她这样回答:
我们国中十男九痔、十女九带,真正可算为一国病国。然医道应该人人研究的,且我们女子很害羞耻,有种种病儿,对男医生说不出,以致不医而死。妹妹学此医道,实欲普救二万万疾病的女子。(第七回)
可见,董奇簧学习医道,是立志“普救二万万疾病的女子”。她有感于“西医上的骨学化学,一些不懂”(第七回),故想出洋留学,后来与有着同样想法的许平权结伴而行。“到了东京,平权入师范学校,奇簧入医学校”,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聚首谈心。毕业之后,董奇簧觉得所学不够,因“美国医学,极其讲究”,故再次启程去美国考察医学。一年之后,“乘船回国,开了大大的一个医学堂,我国医学进步,大半奇簧所造”(第十回),可谓成果斐然。
有趣的是,在《女狱花》总计出场的9位女性人物中,“激烈党”沙雪梅6人和“中立党”文洞仁,或因自杀而死,或因患病而亡;真正存活下来且取得女权事业成功的,只有许平权和董奇簧。此前关于《女狱花》的研究,大多没有特别关注董奇簧,但笔者认为,王妙如在她身上赋予了十分重要的结构性象征功能。董奇簧与许平权,一则立志学习医道,救治中国女性身体上的痛苦;一则决心推行教育,改变中国女性精神上的无知愚昧。《女狱花》也反复强调健康的体魄与文化知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许平权曾说“讲求独立的方法只有两条:一条是去除外边的装饰,一条是研究内里的学问”,第一条就是针对身体而言,因为装饰“除去以后,自然身体强壮,手足灵便”。王妙如设置让许平权与董奇簧形影不离,她们一同出洋留学,一同游历世界,又一同作为小说“唯二”的“幸存者”活到最后,并为她们各自加上一个事业成功的光明结局,目的就是让她们互为“影子”,彼此相互补充,相互定义。有研究者认为,《女狱花》中的沙雪梅和许平权“看似矛盾,实为一体两面”①蔡佩育:《〈女狱花〉的女性书写及其文化意涵》,《弘光学报》第65期,2011年12月。;但笔者认为,真正堪称小说“一体两面”的人物并不是沙雪梅和许平权,而是董奇簧与许平权。
前文已述,许平权的女权开悟是受到大乘佛经的启发,其思想具有鲜明的佛教特色。事实上,她与董奇簧的“一体两面”也可以放在佛学的脉络中加以诠释。佛教与医学关系密切,在佛典中,释迦牟尼经常被喻为“大医王”,佛经也常被比喻为能解脱众生苦痛的“阿揭陀药”(agada)。“阿”的意思是普遍,“揭陀”是去掉,意指佛法是治疗世人疾病和痛苦的医药②徐时仪校注:《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67页。。与此同时,佛教将世间的各种学问和知识概括为“五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作为“五明”之一,“医方明”也是很多高僧都掌握的技艺,他们以此来践行大乘“拔苦与乐”的菩萨之道,并作为普渡众生、弘扬佛法的重要辅助③杨曾文:《佛教和医药学的考察与思考》,《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4期。。《大般若经》曾云“诸有情具身心病”,并指出“身病”有四,“心病”亦有四④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331,《大正藏》第6册,第695页下。。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一如是说:
云何说此世俗医方?长者告言:善男子,菩萨初学修菩提时,当知病为最大障碍。若诸众生身有疾病,心则不安,岂能修习诸波罗蜜?是故菩萨修菩提时,先应疗治身所有疾。⑤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第10册,第710页下、711页上。
“身有疾病,心则不安”,可见医治“身病”也是疗愈“心病”的前提与基础,故“菩萨修菩提时,先应疗治身所有疾”;然而身病虽愈,却不代表根本上的痊愈,因为还有精神上的愚昧无知,心苦甚于身苦。因此,必须要通过真理和智慧的力量来斩断“无明”,使众生离苦得乐,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可以说,佛教有关“身病”与“心病”之关系的看法,也正好对应《女狱花》中董奇簧和许平权的“一体两面”。
《女狱花》第七回的标题为“慈航渡人钦巾帼”,“慈航”本是佛教用语,指佛、菩萨以大慈悲把众生从生死苦海中运到解脱的“彼岸”,有如舟航。在中国,多以“慈航”指称观音菩萨,甚至道教也发展出了观音信仰,称为“慈航道人”或“慈航大士”。这一回主要写董奇簧救治沙雪梅一事,因此“慈航渡人”自然是以“观音”喻指董奇簧。巧合的是,自号“佛婢”的许平权在第八回现身时,罗景仁的批注也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出世了”。由此,从佛学视角观之,许平权与董奇簧也是“观音菩萨”的“一体两面”,在王妙如的女权思想体系中,她们隶属最高层级,代表她的最高理想;次之为“著书醒世”的文洞仁;最末才是日夜组织革命、要“杀尽男贼”的沙雪梅六党。这也对应了罗景仁将小说人物分为“平和”“中立”“激烈”三党。王妙如有意将三党整合成一种分工协作的状态,“今日时势,正宜赖他一棒一喝的手段,唤醒女子痴梦”(第八回),所以需要激烈党先去活动一番;“激烈惨行破坏,平和难以建立”(第六回),于是中立党“每以笔墨生涯为醒世之具”的好处便得以凸显;最终,只有女性拥有了彻底的身心健康,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权。可见,“三党”前后接棒、各司其职,共同缔造理想目标,代表着王妙如女权思想中的三重结构体系。
这一“三重结构体系”在《女狱花》中也有明确暗示。第六回写越狱的沙雪梅来到文洞仁住处,看到墙上挂着四幅西方女性画像,依次是“美利莱恩”“奈经慨庐”“独罗瑟”“苏泰流”。她们均来自于晚清风靡一时的《世界十女杰》。此书大约出版于1903年3月,以《世界古今名妇鉴》(1898)和《世界十二女杰》(1903)为基础,“虽曰译编,实近于撰著”①《世界十女杰》未见版权页,作者与出版信息未知,具体参见夏晓虹:《〈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在《女狱花》中,排名第一位的是“北米大教育家”美利莱恩,今译玛莉·莱昂(Mary Lyon,1797—1849),是19世纪美国妇女教育运动的先锋人物,对应许平权;第二位“普救主”奈经慨庐,即大名鼎鼎的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是护理事业的创始人及现代护理教育奠基人,匹配董奇簧;第三位“诗界革命军”的独罗瑟,今译多萝西(Dorothy Wordsworth,1771—1885),是英国著名湖畔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妹妹,寓指文洞仁;第四位“拿破仑之劲敌”苏泰流,仅从标题即可窥得其一生锲而不舍反对拿破仑的事迹,与沙雪梅等六党同出一辙②以上四人事迹,分别参见《世界十女杰》,第53—57、47—52、17—20、21—25页。。可见,看似小说“闲笔”的四幅图片,实际却隐藏了王妙如女权思想的结构体系,及其对女权实践的步骤安排。如此,不得不再次让人感慨《女狱花》谋篇布局之精妙。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不同于宗旨驳杂的《世界十二女杰》,《世界十女杰》“始终将目光集注在对于天赋自由权的争取与维护上,所选人物因此也偏向革命,这是由于编撰者本以之为获取自由必不可免的手段”③参见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 年第3期。,然而《女狱花》却选择了其中最温和的几位引为典范,这自然与王妙如女权思想的佛教底蕴有关。佛教本就讲究慈悲之心,王妙如尊崇的大乘佛教更是主张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因此,她不可能认同沙雪梅“用强力夺权力”的手段,也不会赞同“杀尽男贼方罢手”之类的女权宣言。然而可惜的是,尽管王妙如十分向往做出一番事业的许平权和董奇簧,但天不随人愿,她曾自述:
近日女界黑暗已至极点,自恨弱躯多病,不能如我佛释迦亲入地狱,普救众生,只得以秃笔残墨为棒喝之具。虽然,革命之事,先从激烈,后归平和,眇眇一身,难期圆满;惟此书立意,将革命之事,源源本本,历道其详,非但一我妙如之现影,实千百万我妙如之现影。④罗景仁:《跋》,西湖女士王妙如:《女狱花》,光绪甲辰刊本,第69页。
由于“弱躯多病”,王妙如无法像许平权和董奇簧那样“亲入地狱,普救众生”,只能效法文洞仁,以小说“为棒喝之具”来警醒世人。“非但一我妙如之现影,实千百万我妙如之现影”一句,更是道出王妙如在《女狱花》一书上所寄予的厚望。
与此同时,《女狱花》虽对“中立党”文洞仁着墨不多,但却安排了两个重要补充人物——许杰和黄宗祥。许杰即许平权之父,他很早就有着不凡之洞见,称“教育女儿,亦是父母的天职”,甚至说“我这个女儿长大起来,要比儿子格出尽心教育”。在父母的开明教育下,许平权自幼熟读历史、地理,知晓世界大势。许杰十分看重小说对女性智识的启发,曾说:“这些腐败的小说,实女子的大魔头,我已立志,用些心血,将旧时的小说世界,洗涤一番,普救种种陷溺的女子。”(第九回)黄宗祥与许平权相识于日本,对她一见倾心、敬爱有加,事事都以她的想法为主,不仅拿出巨款给许平权办学堂,而且“住在与学堂相近的家里,著些振兴女界的小说”(第十一回),以此来支持、声援她的女权事业。许平权不愿结婚分心,他一等就是十几年,也毫无怨言。许平权曾对他说:“今日我们女子香闺前的自由花儿,岂不是哥哥一支妙笔中生出么。”(第十二回)如果说《女狱花》更多将文洞仁视为象征意义上的“中立党”,代表了一个“转喻”意义上的女性符号;那么作为许平权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男性,许杰和黄宗祥则在现实世界中,给予了她最为直接且有形的帮助。可以说,许平权的女权事业最终能够取得成功,他们功不可没。
至此,王妙如女权思想中的三重结构体系已经非常分明:致力于女性身心健康的培育,许平权与董奇簧为“平和党”的一体两面,处于最上层;以著书醒世的文洞仁为代表的“中立党”居其中,在《女狱花》中更多代表了一种理念上的象征意义,许杰与黄宗祥作为重要补充以写作小说的方式,为“平和党”呐喊助威,发挥了实际作用;最末是日夜组织革命的沙雪梅等六人代表的“激烈党”,“逆料其不能成功,但此等人在内地运动运动,亦不可少”(第十回)。可见,《女狱花》充分显示了王妙如女权思想体系结构的严谨与完备;同时,她也身体力行地效法文洞仁,以小说《女狱花》的写作努力实践自己的女权思想——尽管只是退而求其次的“取其中”。可以说,无论是从理论的完备性还是实践的结果来看,《女狱花》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若再进一步将之置于近代中国女权思想的发展谱系中加以观照,则更能抉发其独一无二的思想价值及意义。
四、近代女权思想谱系中的《女狱花》
作为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女性小说①参见马勤勤:《隐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9页。,毋庸置疑,《女狱花》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而其写作行为本身,更是王妙如对自己女权思想的一次成功实践,对当时的女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叶女士读后盛赞《女狱花》“无一事不惊心怵目,无一语不可歌可泣”,誉之为“麟麟炳炳之文”②《叶女士序》,西湖女士王妙如:《女狱花》,光绪甲辰刊本,第1页。;俞佩兰也称其“非但思想之新奇,体裁之完备,且殷殷提倡女界革命之事,先从破坏,后归建立”,乃“沧海中之慈航”“地狱中之明灯”③钱塘俞佩兰:《俞女士序》,西湖女士王妙如:《女狱花》,光绪甲辰刊本,第3页。。不仅如此,《女狱花》问世不久,就成为时人心中足以与《女界钟》并驾齐驱的重要著作④《(近世欧美)豪杰之细君》,《女子世界》1904年第1—8期。,后来还被冯自由列入“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⑤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见《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492页。,足见其影响力。细观其蕴含的女权思想,也同样具有不同于流俗的价值及意义。
在人们的一般观念里,提及中国女权思想发生的这一事件,会首先联想到19 世纪末标举“废缠足”“兴女学”口号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又或是津津乐道于以翻译“在中国女权思想传布史上树立丰碑的人物”⑥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第74页。马君武以及被誉为“中国女界之卢骚”⑦林宗素:《侯官林女士叙》,金天翮著,陈雁编校:《女界钟》,第4页。、写出振聋发聩的《女界钟》的金天翮。在以往的历史叙事里,“我们更多地是对那些声称‘第一’的男性创举持全面肯定和欢呼雀跃”,因为“没有他们的那些‘第一’,何来今天的女性独立和进步”⑧刘慧英:《晚清:现代与传统之间——评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例如,2003 年5 月,恰逢《女界钟》问世100 周年,李小江在《读书》上发表了《是这个男人敲响了中国“女界钟”》一文,基本就代表了这种主流看法。与此同时,也有学者站在反思性的批判立场,对这种以男性为主体的女权启蒙予以重新审视,例如刘人鹏的专著《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以及王政、高彦颐、刘禾的“三人谈”——《〈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前者引入“翻译”的角度,指出近代各种女权话语——无论是马君武译《女权篇》还是金天翮作《女界钟》,抑或“废缠足”“兴女学”的女权口号,其源头都是对“强权”的认同,如在西/中、男/女的框架中,都指向了前者⑨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第85页。;后者是为纪念《女界钟》诞生100周年在上海举行的“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学术研讨会而作,此文与刘著论述立场相近,采用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一改过去对“男性女权先声”的“感恩戴德”而加以大刀阔斧的批评,认为他们站在男性主体的位置肆意塑造女性,其女权论述也充满了男性的欲望与国族主义的定义⑩王政、高彦颐、刘禾:《〈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总之,几位女性学者都指出晚清男性知识分子进行女权启蒙时的目的并不单纯,因为在这些男性眼中,足不出户、目不识丁的妇女是国弱民贫的原因之一,正如《斯宾塞女权篇》里流行最广的一句话:“欲知一国人民之文明程度如何,必以其国待遇女人之情形如何为断,此不易之定例也。”①《斯宾塞女权篇》,莫世祥编:《马君武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页。换句话说,晚清那些活在“强国强种”的欲望结构里的女权话语,其出发点都是基于对“妇女一变,则全国皆变”②卧虎浪士:《〈女娲石〉叙》,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7页。的期待,归根到底,解决妇女问题是为了拯救落后的民族国家,具有一目了然的功利性目的。不妨这样讲,中国女权思想从滥觞之日起,就囿于国族主义的论述框架,且主要由男性主导,这一传统经由五四运动而发扬光大,规导了日后百年女权的论述及实践。
不可否认,晚清男性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初始阶段,确实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但晚清女界已有人意识到这种来自于男性单方面的权利赠予,无法让女性获得真正的自由独立——“夫既有待于赠,则女子已全失自由民之资格”③龚圆常:《男女平权说》,《江苏》1903年第4期。。也因此,那些基于女性本位的女权论述,便显得格外珍贵。目前,已有学者陆续关注到吴孟班、秋瑾、何震等“女性女权先驱”,呈现其有关“创立女学会”④参见夏晓虹:《吴孟班:过早谢世的女权先驱》,《文史哲》2007年第2期。、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⑤参见夏晓虹:《秋瑾: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第235—270页。和无政府主义框架下“女界革命”⑥参见夏晓虹:《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中华文史论丛》2006 年第3 期;刘慧英:《从女权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何震的隐现与〈天义〉的变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 年第2 期;刘人鹏:《〈天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视野与何震的“女子解放”》,《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2期。的壮举。这些女性以更加纯粹的女权主义者的姿态,表明了对女性自身命运掌握的意志与决心。然而,上述几位出现在王妙如写作《女狱花》之前的,其实只有吴孟班一人。吴孟班,名长姬,生于1883 年,年纪大约比王妙如小五岁左右,因“时疫”卒于1902年1月4日,年仅19岁。除去“嗜学堕妊”的逸闻为人所津津乐道,吴孟班在中国女权思想发展史上的主要功绩是提倡创立上海女学会,并撰写了《拟上海女学会说》一文。夏晓虹曾指出,中国女权思潮通过两个途径展开,一为“翻译”,一为“本土化论述”,前者源头为马君武所译《女权篇》,后者可追溯到吴孟班女士此文⑦夏晓虹:《晚清女权思潮溯源》,《文史知识》2011年第3期。,可见其重要。吴孟班自述“悼女学之式微,悲女权之放失,思有以匡救之”,故倡议创立女学会,“以增进妇女之学识为事业,以发达妇女之权力为宗旨”⑧吴长姬:《拟上海女学会说》,《中外日报》1901年4月7日。。其女权话语的“女性本位”体现有三:一是以坚定的女性自主立场,在创立女学会一事上拒绝男性越俎代庖;二是由她发端的对女性自身的深刻反省,日后繁衍成晚清妇女论述的一大主题;三是创造性地在“女学”与“强国”之间加上“女权”一环,并以之为第一义⑨参见夏晓虹:《吴孟班:过早谢世的女权先驱》,《文史哲》2007年第2期。。可见,特定的性别立场使得吴孟班比男性论者更加关注女性自身的权益与幸福,纵然如此,她还是十分明确地将中国的衰弱与女权的丧失之原全部追究到女学的式微:
吾中国二千年女权之遏塞久矣。推原其故,岂非妇女不学之故哉!夫惟不学,权利尽失,于是遂得非理加之,奴隶、玩物,皆不免焉。积而久之,妇女亦自甘于奴隶、玩物,习焉不觉矣。此人群之所以不昌也。
可见吴孟班的“女性本位”终究不敌“民族国家”,故其女权论述反复以“女学者,全国文明之母;女权者,万权之元素也”立论,未能脱离“国族主义”的论述框架。此外,“人类同等、男女平权之说,遍唱于欧美、日本诸邦”等句,也鲜明地昭示了其来源(欧美、日本)和基础(“天赋人权”学说),与彼时流行的男性女权论述隶属同一框架。
女性既要恢复“天赋人权”,还要贡献国家,这是彼时知识界争取女权的共同出发点。然而,王妙如所主张的女权,却从未将之与国家利益相联系。即使是小说中最为激进的主张流血革命的沙雪梅,在讲到她如何走上革命之路时,王妙如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岂知天下大势,压力愈深,激力愈大,若顺着时会做去,则将来的破坏还不至十分凶猛。自经一再压制,人心愈奋愈厉,势必推倒前时一切法度,演成一个洪水滔天之祸……不到数十年,就酝酿了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沙雪梅出来了。
如同中国大部分普通女子一样,沙雪梅来自于一个传统家庭,自幼娴习拳棒,不曾读书;长大后嫁给昏庸无能的丈夫,事事受到限制和压制。她经历了失手打死丈夫后的锒铛入狱,在狱中看到无数麻木不仁的女犯人,又遭遇狱卒的无耻盘剥,这一切遭遇都让沙雪梅感到无比悲愤,故发出如下宣言:
男贼待我们,何尝有一些配偶之礼?只当我们作宣淫的器具,造子的家伙,不出钱的管家婆,随意戏弄的顽耍物。咳,男贼既待我们如此,我们又何必同他客气呢?我劝众位,同心立誓,从此后,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男贼方罢手。(第四回)
屡屡被男性压制的沙雪梅,在反复的刺激之下,生发出一种朴素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女权思想——“将男贼尽行杀死,胯下求降的,叫他服事女人,做些龌龊的事业。国内种种权利,尽归我们女子掌握”(第八回)。可惜,这不过是对现有“男尊女卑”秩序的一种简单改造,将上下内外颠倒一番,本质其实没有变化。与之相反,许平权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幼年时,她得到父母的悉心教育,甚至比对儿子的教育还要用心;成年后,又遇到事事以她为重的伴侣黄宗祥,不惜出钱出力来圆满她的女权事业。可以说,许平权一直幸运地生活在男性的尊重与鼓励中,不仅从未遭受过“父权”的压抑,反而受益于其庇佑,故走上一条更加平和、稳健的女权之路。恰如罗景仁所说“人生处世,外界刺激力甚大。所处之境为平和,性质亦渐归平和。所处之境为激烈,性质亦渐归激烈”(第一回)。所以,在许平权看来,男女之间也完全可能存在一种超越压制的新型两性关系——“男女之间,天生成有一种特别的爱情。一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的恩义,皆不足以比他”(第十一回)。
综上,作为中国最早的“女性女权先驱”之一,王妙如在《女狱花》中争取女权的出发点非常单纯,全然出自对数千年来女性被压迫的黑暗现实的不满,故而对女性的幸福与权利大声疾呼。她的女权思想,不是一种被西方强势文化和政治所激发出来的趋利避害和民族自卫,而是男女两性中的一方长期遭受压迫而发自性别本能的“正当防卫”,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这大概也与佛教的怜悯众生、究竟平等,讲求“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①[印]龙树著,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27,《大正藏》第25册,第256b页。不无关联。再来反观晚清其他几位女性女权先驱,最激进、最具颠覆性的当属何震,其无政府主义框架下的“女界革命”以“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为基点,彻底拒绝现代文明及此种文明图景下的女权方案,已然溢出了民族国家的框架。然而,何震曾自白“吾所倡者,非谨女界革命,乃社会革命也,特以女界革命,为社会革命之一端”②震述:《女子宣布书》,《天义报》第1号,1907年6月。,其“女界革命”仍具有一定的工具性。可见,王妙如在《女狱花》中所秉持的这种极致的女性本位立场,毋论男性知识分子,即使是在女性论者中,也绝无仅有。同时,在晚清取资欧美、奉“天赋人权”为女权理论圭臬之际,王妙如却别出心裁地继承了戊戌时期汇通佛教来论证平等之义的余绪,以“男女同尊,究竟平等”为女权理论之根基,同时糅合大乘佛教“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道”精神,以慈悲之心寻求两性之间的和谐平等。她凭借令人惊叹的清醒与洞见,建构出自己女权思想的三重结构体系,以独到的理论性和明确的实操性,先后破除国族主义的藩篱与父权制度的迷思,显现出有别于时代的“异音”。在中国百年女权思想史上,《女狱花》应该是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王妙如这位被忽视的女权先驱,其思想体系及女权实践值得我们大书特书,永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