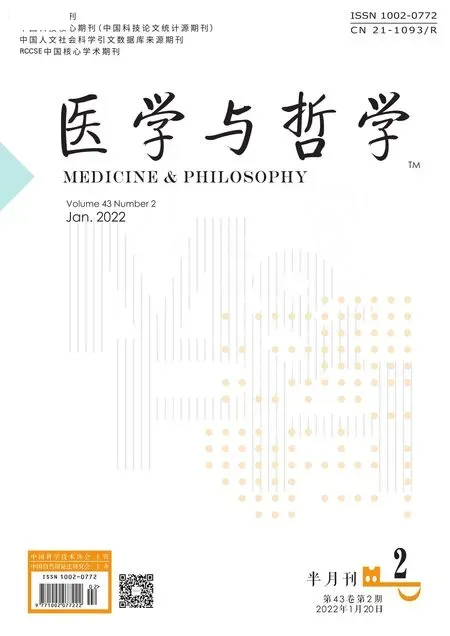白求恩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崔久嵬 葛婷雯 于双成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犹如临床医学的教材中,针对任何一种疾病,都会从病因、发病机制等角度去揭示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规律一样,人们也经常会对思想、意识、精神、信仰、理念等提出相同的追问,如红军的理想信念从何而来,长征精神是怎样形成的,雷锋精神的源泉是什么。弘扬白求恩精神,不仅要追问白求恩精神是什么,更要追寻白求恩精神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但是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多谈及前者,对后者鲜有深入的探究。
精神及其研究,属于哲学的范畴。一切精神,在其本质上都来源于实践,都是实践的产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时代、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的主观能动性的活动。因此,精神既是实践的产物,更是时代的标志。诚如,“在哲学史上,一种哲学的称谓往往不是由创立者本人确定的,而是由后人加以提炼、概括出来的”[1]。对精神的研究与界定同样如此,白求恩精神是在其逝世之后,人们根据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他的先进事迹提炼和概括出来的。因此,揭示白求恩精神的形成,唯有通过实践这一源流追根溯源。此处所说的实践,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白求恩的成长和生活经历,他在加拿大等国接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医疗工作,他在中国抗日前线的医疗与教学实践活动,以及其人生经历的时代背景。
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命体,人的精神更是最奥妙的客观存在。影响一个人的成长与经历的因素甚多,同样,影响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因素亦是甚多。遵循“把历史人物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评价的方法论原则。即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2]笔者尝试从如下几个维度探析白求恩精神的形成之源。
1 家庭教养和社会熏陶奠定其精神品质的底蕴
白求恩家族是16世纪中叶从法国北部迁居到苏格兰,18世纪又从苏格兰移居到加拿大。他的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母亲曾当过传教士。对于一个西方国家的基督教社会而言,基督教精神体现着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对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而言,基督教精神统摄着这个家庭生活的一切,以“爱”为核心的敬畏上帝、尊重平等、救赎原罪、追求奉献的基督教精神是每个家庭成员生命的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曾与白求恩共过事的温德尔·麦克劳德在1979年的回忆文章中写道:“白求恩的父母为家里三个孩子树立了高尚的道德标准。他们虔诚地信奉宗教的哲理,其中包括《圣经·新约》中的诫谕‘像爱护你自己那样对待他人’……贯穿着他一生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显然是承袭了他双亲舍己为人的传统。”[3]还写道“他性格中有强烈的正义感,这是宗教家庭带给他们的品质。”[4]24尽管白求恩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从小深受基督教精神的涵养与熏陶,滋养了他的一种抑恶扬善的情怀。
为了生计,白求恩一家频繁搬家,不停地转换安家之所。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白求恩曾送过报纸、在食堂当过招待员、在客船上做过服务生、在建筑工地做过力工、在偏远的乡村小学教过书、在报社当过兼职记者。甚至为了实现其学习医学的梦想,他前后当过伐木工、餐馆服务员。这种坎坷的生活经历,使白求恩从年轻时代就对社会底层的人们及其生活有了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体验,这种深切的同情心油然而生,从而奠定他日后人生追求的生活基础,尤其是情感基础。影响他一生的另外一位家庭成员,是他的祖父——一位受人尊敬的杰出的外科医生。祖父在白求恩的心目中有极高的地位,是他一生努力学习与效仿的楷模。白求恩在儿时,就决心以祖父为榜样,做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这个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白求恩充满爱心、充满同情心、充满责任感;白求恩有志向、有抱负、有人生目标;白求恩有着自己的性情,有着自己的做事风格,这一切首先是其家庭、社会和那个时代对他的影响,这些影响滋生了白求恩精神最初的萌芽或胚芽,在他的内心深处埋下了爱与善的种子。
2 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形成其精神品质的职业特征
白求恩从小立志学医,要成为像爷爷那样的外科医生。但是由于经济等原因,他的学医之路走得曲折而又艰辛。1909年10月,进入多伦多大学,但因为之前没有上过作为必修课的希腊语或德语,他没能进入医学院。他一边靠打工谋生计,一边时断时续地补习课程。他在阿尔戈马区做过伐木工并兼职给工人们传授知识,做过图书管理员,给《电讯报》做过实习记者等。在1912年10月得以进入医学院,开启新的半工半读的生活和学习状况。他在学校附近的餐馆找了一份工作,赚钱来贴补有限的积蓄并支付食宿。接下来的几个月,他花了大量时间在工作当中,致使他的学习成绩大幅下滑。因一战爆发,在1914年9月,他中断了学业,通过医学考试正式入伍进入陆军医院,他的任务主要是作为担架手到前方战壕去处理伤员,再冒着炮火将伤员运到后方。1915年11月负伤退役后再次返回学校继续学习,终于在1916年12月获得医学学士学位。他的学业,是伴随着做工谋生而艰难前行,伴随着医疗实践、伴随着对社会和时代的认知而不断前行。从现有史料来看,对白求恩的医学学业、对白求恩在医学院校所接受的教育与训练、对白求恩就读医学院校时的医学教育的整体状况等,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所以,无法追寻其医学能力、医学素养之形成。
但从历史背景而言,白求恩就读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期间,恰逢北美医学教育改革的时期。受当时的卡内基基金会的委托,Abraham Flexner(以下简称弗氏)对北美155所医学院校做了实地考察,于1910年发表了调研报告《美国与加拿大的医学教育:呈给卡内基教育基金会的报告》(以下简称《弗氏报告》)。《弗氏报告》对医学教育的现状做了详细的描述,对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更对未来的改革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提示。《弗氏报告》奠定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医学教育的基础,对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医学教育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以《弗氏报告》为导引,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进行了以强化医学的科学基础、强化医学的临床实践为主要特征的系统而全面的改革,形成了科学化的医学教育体系[5]。
虽然我们无从清晰而具体地知晓白求恩所接受的医学教育给了他什么。但是,可以从白求恩在日后的医疗工作经历,尤其是在抗战前线的工作中所呈现出来的优秀的医学品质、丰厚的医学知识、精湛的医学技术,乃至于卓越的医学成就(1934年6月,他当选为美国胸外科协会的五人执委之一[6])逆向推断其形成的来源,那就是白求恩曾经接受过的良好的医学教育,这是他医学素养形成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源泉。当年在加拿大、美国、西班牙,乃至中国,曾经与白求恩共过事的医生和护士,尤其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同行,在回忆白求恩的时候,对他的性情和行事风格有着微词,但是对于他的学识、他的能力、他的工作热情、他的严谨作风,乃至于他对待病人的态度都无一例外地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这些都成为白求恩精神最为感人至深的闪光之处。
3 共产主义思想和信仰构成其精神品质的内核
我们在寻根白求恩的过程中,在走进、亲近白求恩的过程中,在被白求恩其人其事深深感染与感动的过程中,不禁要问,而且是一次次地追问:是什么支撑着白求恩以其凡人之躯创造了如此非凡的人生。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艰苦卓绝岁月的我们,如何理解,进而如何去阐释,或许是颇有难度的学术命题。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7]说过:“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够指导我们前进。”与此最为相似的,就是几十年来国内外的许多政治家、军事家,乃至社会大众对红军长征所提出的同样的追问:是什么支撑着红军战士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胜利到达陕北的延安。对此,邓小平等许许多多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晚年追忆和评价长征时,几乎得出一个非常具有共识性的结论——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信仰的力量支撑着红军战士,是信仰的力量支撑着中国革命事业走向胜利。邓小平[8]概括道:“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通过走进白求恩、亲近白求恩和知晓白求恩,可以清晰而确切地看出,支撑白求恩的同样是他的信仰、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这一点,同样是许多介绍、回忆白求恩的文献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予以阐述、强调的。《不死鸟》一书,对此有过多处叙述,例如,“加入共产党使得白求恩在不知不觉中有了核心信仰……在他的眼中,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是‘真正的宗教领袖之一’,可以亲切地与耶稣相提并论,他愿意为这个新的信仰付出任何代价……在共产主义那里,白求恩感到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兴趣中心,一个成长和改变自己的机会。”[4]151-153“他在美国曾开诚布公地说:‘我很荣幸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他的眼中,这个身份就是信仰的印记,他为此骄傲,并渴望拿来炫耀,因为他已经把整个身心献给了这个信仰。”[4]250
至此,按照思想的逻辑,自然会生成疑问——白求恩的共产主义信仰何以获得、何以形成。在上述内容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信仰”二字,既作为一个名词,更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查阅汉语词典和哲学词典,发现“信仰”与“信念”虽有微妙差异,但基本上可以视为同义词或近义词。《哲学大辞典》对“信念”一词的解释更为详尽:“对理论的真理性和实践行为的正确性的内在确信……信念往往以目的、动机的形式贯穿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并与情感、意志相结合,形成一种稳固的观念意识支配人们的行动。理论对信念的形成具有决定的作用。但理论要通过影响人的信仰(信念)、意志的中间环节来影响人的实践活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共产主义觉悟的集中表现,它促使人们自觉地、积极地去履行共产主义的道德要求。”这一解释为我们研究白求恩共产主义信仰之形成提供了精准而贴切的理论指导。信仰,不是人的大脑中与生俱来的自然之存在,是人后天形成的思想观念;作为统摄人之行动、人之行为,甚至是人之思想的信仰,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由一定的理论引发、诱发、启发而形成的。正如孙正聿教授[9]所说:“理想、信念不会自发产生,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有理论的支撑。”共产主义信仰的形成,亦就唯有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启蒙、启发之思想的种子。
白求恩的人生目标是为人类福祉做贡献,在自身经历了肺结核的生死磨难之后,他以一个医者的角度对社会大众,尤其是生活在底层大众的生活和健康更为关注,对医疗系统乃至社会存在的弊端更是深恶痛绝。借助于参加1935年8月在苏联举办的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大会的机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考察了苏联的医疗体制,参观医院和疗养院,调查了肺结核的治疗方案和防治效果。他认为苏联的确在医疗方面比加拿大进步,对苏联医疗制度的赞赏也激发了白求恩对马克思主义的好奇心。“在苏联的2个月,他看到了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实践,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真理。苏联的建设实践是一部最有说服力的活教材,牢牢地夯实了他的理想信念,使他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10]白求恩曾经画了一幅水彩自画像《患病期间在床上学习马克思著作》送给友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构成白求恩精神品质的内核,成为影响其行动的最为核心的动力源泉。
4 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精神成为其精神升华的热焰
一种高尚的精神,一种可以引领时代发展的崇高的精神,其形成与发展不仅有其文化渊源和理论基础,更有其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实践基础。人们常说,河北唐县是白求恩精神的发祥地,是白求恩医科大学即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的发源地,因为这里是白求恩与中国军民水乳交融、浴血战斗过的地方,是白求恩将自己的热情、才能、心血,乃至生命奉献给他所信仰的神圣事业的地方,是在践行其理想信念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使中国军民深切感受到一种崇高精神品质的地方,这个地方成为了白医人,乃至中国的医学人心目中永恒的圣地。
曾创作了《斯巴达克思》的罗马著名作家乔万尼奥里说过:“伟大的理想唯有经过忘我的斗争和牺牲才能实现。”白求恩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奉献社会的人生理念之追求,不是停留在内心的意向和精神上的向往,而是付诸于充满忘我精神的奉献社会的行动。无论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白求恩以其远见和毅力让他在短短几周内从无到有地建成了一支输血医疗队,他们克服了艰苦的条件,成功地为伤员送去了挽救生命的血液[11],还是在加拿大做外科医生的时候,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根据当时的社会需求所做的有关结核病症状和治疗知识的普及性宣传,以及围绕着结核病医疗与康复的医疗费用和社会的卫生保健制度等所做的欧洲和北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调研[12];乃至于在中国的抗日前线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践行他的理想信念,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理想信念——要为人类福祉做点事情。
可以明确地说,不同于之前在加拿大、美国和西班牙的工作和社会实践活动,白求恩在中国抗战前线的忘我工作和不畏艰险的坚强意志,是受到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坚强意志所感染和激励。白求恩曾和翻译黎雪谈起来到中国后的感受:“我来中国的四个月,来延安近一个月,结识了很多革命同志和朋友,在武汉我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我见到了朱德同志,在延安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医院里我见到了光荣负伤的八路军指战员……黄河之滨确实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你们中间,和你们一起工作和生活。我要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直到抗战胜利。”[13]白求恩后来说:“我来延安前,听人称颂毛的伟大,但只有亲耳聆听了他的谈话后,我才真正理解了‘伟大’的含义。”从那天起,白求恩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哲学思想产生浓厚兴趣,一有时间就和人讨论。他后来甚至请求聂荣臻司令员拿出半天时间回答他关于“持久战”的各种问题[14]。他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见证了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时的使命担当和英雄气概,这一切激发了白求恩融入其中、顽强奋斗的斗志,由此而生成他对聂荣臻司令员说过的那句名言:“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白求恩以其满腔热情的674个日日夜夜、以其留下无数感人至深故事的674个日日夜夜,以其奉献生命和鲜血的674个日日夜夜,践行他自己的诺言。海德格尔[15]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说:“所有伟大事物都只能从伟大发端,甚至可以说其开端总是伟大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军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为民族而战,就是一种伟大的开端——中华民族解放的开端,这伟大开端中生成一种伟大的发端——白求恩精神。
至此,可以明确地阐述白求恩精神形成的逻辑脉络,参加血与火的抗日战争构成其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和在延安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构成其理论逻辑,以基督教精神为标志的西方文化和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构成其文化逻辑。“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充满坚定、刚毅和果敢的“抗大校歌”,这涌动着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精神的旋律,使白求恩热血沸腾,更促使白求恩以满腔热忱投入到这时代的洪流,这种与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思想情感的共鸣构成了白求恩精神的情感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情感,才使上述三个“逻辑”成为逻辑。没有崇高的情怀,不会有崇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