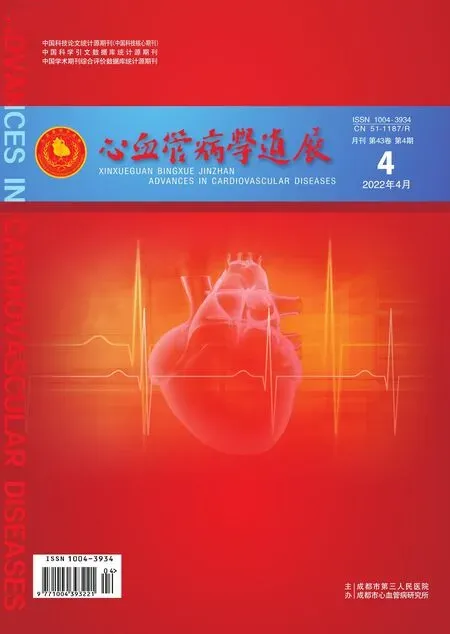糖酵解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及其在动脉粥样硬化病理过程中的作用
王卫卫 于子凯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中医科,北京 100091;2.国家中医心血管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北京 100091)
心血管疾病给居民和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日渐加重。据《全球心血管疾病和危险因素负担1990—2019》统计,以缺血性心脏病和卒中为主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是全球致死和致残的主要原因,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1/3,其中心血管死亡发生率最高的国家是中国[1]。《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显示,ASCVD是中国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2],其中农村为45.91%,城市为43.56%。因此,ASCVD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首要公共卫生问题。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ASCVD的主要诱发因素[3]。既往认为,脂质沉积及炎症反应是参与AS形成的关键病理环节[4]。CANTOS研究[5]首次证实抗炎药物在ASCVD治疗领域具有巨大应用价值。然而,新近发表于NEnglJMed杂志的CIRT研究[6]结果表明,广谱抗炎药物甲氨蝶呤治疗并未降低ASCVD死亡率。因此,寻找阻断与AS相关的特定炎症途径药物靶点可作为新的突破口。研究[7]表明,巨噬细胞极化在AS炎症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研究[8]发现,代谢途径的改变是诱发巨噬细胞极化的关键环节。基于此,现从巨噬细胞免疫代谢途径的可塑性入手,对免疫代谢途径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在AS病理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及研究进展进行阐释,引领未来AS防治研究的新方向,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1 免疫代谢途径在AS中的作用
免疫细胞的功能与细胞内能量代谢途径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在疾病中的调控作用被视为“免疫代谢”[9]。2019年,欧洲心脏病学会AS和血管生物学工作组发布《免疫代谢与AS:前景及临床意义》意见书[10],阐释了免疫细胞代谢途径的改变在AS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掀起了“免疫代谢”这一新的研究热潮。首先证明免疫代谢途径改变诱导AS形成及发展的证据基于18F-氟代脱氧葡萄糖(18F-fluorodeoxyglucose,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技术。18F-FDG是葡萄糖的放射性核苷类似物,通过葡萄糖转运蛋白被细胞吸收,磷酸化为18F-FDG-6-磷酸盐沉淀在细胞内。研究[11-12]显示,18F-FDG的高表达与血管炎症及AS斑块的易损程度正相关。另外一项临床研究[13]纳入159例行动脉内膜剥脱术的患者,对高危和稳定斑块患者的颈动脉斑块进行代谢分析,结果发现,高危易损斑块中代谢途径的改变与糖酵解、氨基酸代谢等途径的改变密切相关。由此可见,糖酵解、氨基酸代谢等免疫代谢途径的改变与AS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该学说的兴起开启了AS防治的新篇章,前景广阔。
2 糖酵解是与AS关系最密切的免疫代谢途径
糖酵解是参与AS形成最重要的免疫代谢途径之一[14]。在低氧条件下,葡萄糖首先通过葡萄糖转运蛋白被转移到细胞中,然后被己糖激酶磷酸化为6-磷酸葡萄糖,6-磷酸葡萄糖经过一系列酶的作用被转化为丙酮酸,并产生少量的三磷酸腺苷,这个过程被称为糖酵解[15]。动物实验[16]结果表明,敲低AS小鼠中葡萄糖转运蛋白1的表达水平,可降低小鼠骨髓和AS斑块中糖酵解通量,从而发挥抗AS的作用。另外一项研究[17]结果表明,通过抑制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减少糖酵解与磷酸戊糖途径的交互作用,可降低血管中超氧化物水平,进一步减轻AS的损伤。由此可见,通过降低糖酵解水平,可达到抗AS的目的。大量研究[18]已证实,巨噬细胞中糖酵解水平与AS过程中炎症的发生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巨噬细胞糖酵解途径及其调控机制,将其作为干预靶点至关重要。
3 巨噬细胞极化是导致AS发展的主要病理生理过程
AS的发展涉及不同类型免疫细胞的内流、增殖和激活,其中与AS发生和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巨噬细胞[19]。动脉壁中的巨噬细胞清除脂蛋白颗粒,转化为泡沫细胞,分泌炎症因子,促进脂蛋白滞留,加剧AS病变的进展[20]。
巨噬细胞具有可塑性和多样性,在AS发生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均有巨噬细胞亚型的浸润。不同微环境信号刺激会将其诱导分化为经典活化的M1型巨噬细胞和选择性活化的M2型巨噬细胞,这种巨噬细胞炎症功能变化的过程称为巨噬细胞极化[21]。其中,M1型巨噬细胞极化分泌肿瘤坏死因子-α、白介素-1和白介素-6等因子,促进炎症反应加速AS进展;M2型巨噬细胞分泌精氨酸酶1、几丁质酶3样蛋白3和白介素-10等因子,发挥抗炎和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22]。除此之外,极化过程中,M2型巨噬细胞可通过吞噬凋亡的M1型巨噬细胞调节M1/M2稳态,促进炎症消退,防止AS易损斑块破裂[23]。由此可见,巨噬细胞极化过程中M1促炎和M2抗炎的平衡,在AS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24]。因此,深入探讨M1/M2型巨噬细胞极化平衡的调控机制,已成为AS防治研究领域的焦点。
4 糖酵解是调控巨噬细胞极化的重要机制
新近研究[25]表明,以巨噬细胞免疫代谢为作用靶点进行干预可稳定斑块,改善AS的结局。糖酵解是一种已被证实的可调控巨噬细胞极化的免疫代谢途径,与巨噬细胞极化过程密切相关。在巨噬细胞中,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的激活使细胞由氧化磷酸化向糖酵解转化,进而促进炎症相关基因的转录[26]。研究[27]表明,过表达葡萄糖转运蛋白1可使巨噬细胞糖酵解水平增强,进而导致促炎表型的M1型巨噬细胞高表达;反之,抗炎表型的M2型巨噬细胞极化程度增加。同样,敲除丙酮酸脱氢酶1使糖酵解水平降低,M2型巨噬细胞表型增加,进而减缓炎症反应[28]。在脂多糖和Ⅱ型干扰素诱导的M1巨噬细胞中,大部分糖酵解产物丙酮酸被转化为乳酸,打破三羧酸循环,导致柠檬酸的积累,驱动琥珀酸生成,促进炎症因子高表达,诱导糖酵解的始动因子(HIF-1α)合成增加,再次反向激活糖酵解,致使恶性循环发生;仅少部分丙酮酸在白介素-4诱导的M2型巨噬细胞中,以乙酰辅酶的形式进入完整的三羧酸循环,通过氧化磷酸化产生三磷酸腺苷[29]。因此,糖酵解在M1/M2型巨噬细胞极化平衡中起着关键作用[30],二者的关联可被视为与AS相关的特定炎症途径药物靶点,为AS防治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
5 HIF-1α/磷酸果糖激酶-2/果糖-2,6-二磷酸酶3是介导糖酵解调控巨噬细胞极化的经典通路
在糖酵解通量的调控机制中,磷酸果糖激酶-2/果糖-2,6-二磷酸酶(phosphofructokinase-2/fructose-2,6-bisphosphatase,PFKFB)为关键控制因子,PFKFB通过调节果糖-2,6-二磷酸在细胞内环境中的聚集,进一步激活磷酸果糖激酶-1的活性,促使果糖-6-磷酸转化为果糖-1,6二磷酸,进而介导糖酵解这一生理过程,其中,PFKFB3在PFKFB家族中具有最高的激酶活性,研究证实其可作为驱动糖酵解水平的调节器[31-32]。新近研究[33]发现,抑制PFKFB3的活性,可降低糖酵解水平,进一步减缓AS发展过程中的炎症反应。除此之外,在缺氧条件下,巨噬细胞PFKFB3表达上调,糖酵解通量增加[34]。由此可见,PFKFB3在巨噬细胞糖酵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HIF-1是碱性螺旋-环-螺旋转录因子家族亚家族的高度保守成员,是由α与β亚基组成的异源二聚体,HIF-1α是α亚基的一种类型。既往研究[35]表明,HIF-1α是PFKFB3上游调控因子,通过抑制HIF-1α/PFKFB3活性,巨噬细胞的炎症水平以及糖酵解活性均降低,进一步证实巨噬细胞糖酵解与炎症水平之间的紧密联系。综上所述,HIF-1α/PFKFB3通路是介导糖酵解发生应用最广泛、研究最深入的信号通路[36]。因此,抑制HIF-1α/PFKFB3通路活性,可降低糖酵解水平,进一步调控巨噬细胞极化,抑制炎症反应,从而达到抗AS的目的。
6 小结及展望
M1/M2型巨噬细胞极化平衡是当下AS防治研究领域的焦点,糖酵解是目前免疫代谢领域的前沿热点,且与AS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巨噬细胞极化密切相关。综上所述,糖酵解是可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参与AS形成的最重要的免疫代谢途径之一,HIF-1α/PFKFB3通路是介导糖酵解发生应用最广泛、研究最深入的信号通路。既往研究[37]表明,通过降低糖酵解速率,可增加巨噬细胞线粒体氧化代谢,调控巨噬细胞极化,抑制炎症反应,从而减轻AS,提示调控巨噬细胞糖酵解水平有望成为AS的治疗策略。但是,目前仍面临众多挑战,例如在体斑块内巨噬细胞代谢表型鉴定技术仍不完善,斑块内巨噬细胞糖酵解代谢相关分子靶点仍有待探索等。因此,深入开展糖酵解及巨噬细胞极化的机制研究,有望从抑制AS中巨噬细胞糖酵解代谢的角度为防治AS提供新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