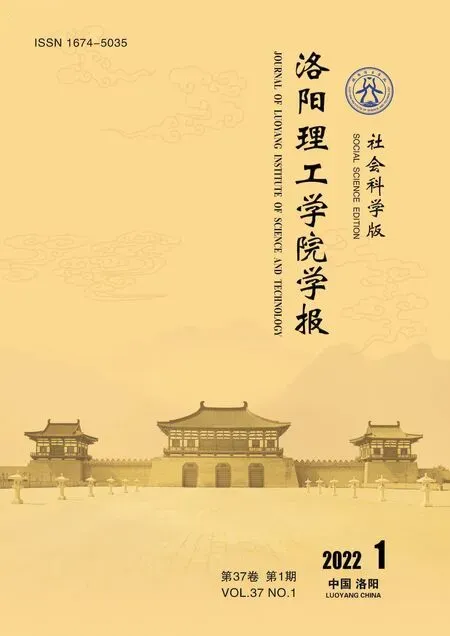论古诗词中的石榴意象
聂 飞, 陈必应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石榴的原产地并非中原,而是由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返回时带入的。唐代元稹有《感石榴二十韵》一诗:“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迢递河源边,因依汉使搓。”[1]52宋代欧阳修也作诗云:“犹胜张骞为汉使,辛勤西域徙榴花。”[1]98上述两诗所指正是汉使自安石国带石榴入国之事。据刘歆《西京杂记》记载:“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树……安石榴十株。”[2]34陆机《与弟云书》云:“张骞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也。”[3]1128清陈溴子《花镜》言:“其种自安石国,张骞带归。”[4]51上述所称“安石榴”即今天的石榴,因其自安石国传入,故古时称“安石榴”。关于“石榴”这一叫法,最早见于曹植《弃妇诗》“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1]13一句,描写石榴树之颜色。石榴既传入,先于骊山一带定居繁衍,而后则遍布各地。
石榴传入后,自宫廷至民间皆颇喜爱,赢得天浆、若榴、沃丹、丹若、金庞、金罂、涂林等美名,而农历五月也因石榴花开得最艳而被历代文人雅称“榴月”。同时,或因其为中外结合之产物,汉代以降,历代名家文士吟咏石榴诗词甚多,石榴赋、石榴诗、石榴词、石榴曲连绵不绝,而在古往今来的不断吟咏颂誉间,所形成的石榴文化逐渐积累沉淀,意蕴丰富。
一、石榴的歌咏之作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提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5]693四时变化必然影响万物,而物色之变对文学创作感召颇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迂,辞以情发。”[5]693文学创作往往取材于对自然景物的体察描写,而石榴作为“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1]1,自然进入历代文人视野,他们写景图貌、体物抒情,留下了为数众多的歌咏石榴之作。
(一)石榴赋
赋中言及石榴,最早或见于东汉张衡《南都赋》:“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割周楚之丰壤,跨荆豫而为疆。若其园圃,则有蓼蕺……乃有樱梅山柿,侯桃梨栗,梬枣若榴,穰橙邓橘。”[3]838所谓“若榴”,即石榴别称。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浮图前荼林、葡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荼林实重七斤,蒲陶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于中京。帝至熟时,常诣取之,或复赐宫人,宫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味,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京师语云:白马甜榴,一实值牛。”[6]172可见汉代自石榴传入后,已逐渐传播开来,但仍未普及全国,因而达到“白马甜榴,一实值牛”的珍贵程度。
自汉至晋,因石榴逐步由皇家宫苑向士人民众普及,故而出现了大量歌咏石榴的赋作,而这些赋多以“安石榴”相称。石榴赋创作以晋代尤盛。汉魏时期,石榴多于赋中有所提及,而多不为赋的主体。到晋代,专篇歌咏石榴的赋作迭出,呈一时之盛。如潘岳的《河阳庭前安石榴赋》,潘尼的《安石榴赋》,夏侯湛、庾鯈的《石榴赋》,张载、张协、范坚、应贞、傅玄等人的《安石榴赋》。而晋代以降,虽有吕令问的《府庭双石榴赋》、梅尧臣的《矮石榴树子赋》、颜测的《山石榴赋》等,但总体而言,未及晋代之盛。
石榴赋作以铺排的语言描摹石榴之美。如潘尼的《石榴赋》云:“冒红牙于丹须,披绿叶于修条,接翠萼于绿叶,缀朱华于弱干,岂金翠之足玩,实兹葩之可玩。”[1]1红、绿、翠、朱、金一系列色彩词的运用,写出石榴周身色彩之丰富。又如潘岳的《河阳庭前安石榴赋》:“似玻璃之栖邓林,若珊瑚之映绿水。”[1]2张载的《安石榴赋》:“似西极之若木,譬东谷之扶桑。”[1]3以玻璃、珊瑚、若木、扶桑状石榴之姿。而对于石榴果实的赞美,因其“千房同蒂,十字如一”“千房同膜,千子如一”[1]2的独特结构,又加之果实鲜美,“剖之则珠散,含之则冰释”[1]4“柔肤冰洁,凝光玉莹,漼如冰碎,泫若珠迸”[1]5,而广受赞誉。由是,石榴于赋中赢得“冠百品以仰奇,迈众果而特贵”[1]3“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1]1的盛誉。
(二)石榴诗
据《中国石榴栽培史》转引《陕西果树志》言:“两晋南北朝时期,从石榴受到大量人士讴歌中可以看出石榴已经有广泛种植,而成为当时人们园篱中的佳果。如果说西汉时期的石榴还以皇家宫苑种植为主,用来饷馈外宾、赏赐权臣和观赏,那么此时则开始融入普通士人阶层乃至民众的生活。”[7]到盛唐时期,石榴栽培进入全盛时期,一度曾出现石榴“非十金不可得”和“榴花遍近郊”的盛况。在《全唐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多达近百首描写石榴或与其相关的诗歌。从汉代到清代,都有石榴诗的创作。
早在汉代,石榴便作为文学形象进入诗歌创作中。《汉乐府诗·黄生曲三首其一》中就有“松柏叶青茜,石榴花葳蕤”[1]11之句。另《丹阳孟珠歌》中有“扬州石榴花,摘插双襟中”[1]11;《黄门倡歌》有:“点黛方初月,缝裙学石榴”[1]12。可见,这一时期石榴已经传播到扬州地区,且石榴花已深受人们喜爱。汉代以降,由于石榴已融入普通士人阶层乃至民众的生活,不再为宫廷所独有,石榴歌咏之诗愈发彰显。如南陈江总的“岸绿开河柳,池红照海榴”[1]2、隋魏澹的“新枝含浅绿,晚萼散轻红”[1]22等,可见文人对石榴的青睐。
唐宋时期石榴诗尤盛。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梅尧臣、欧阳修、黄庭坚、陆游诸人诗中均有石榴意象。元稹的《感石榴二十韵》《山石榴花》、白居易的《山石榴花十二韵》《喜山石榴花开》、李商隐的《石榴》《石榴花》、梅尧臣的《石榴》《石榴花》、欧阳修的《榴花》《西园石榴盛开》、黄庭坚的《题安石榴双叶》《记梦》、陆游的《山店卖石榴花取以荐酒》《初见石榴花》等都有吟咏,佳句迭出。如“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鲜”[1]37“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1]27“榴花最恨来时晚,惆怅春期独后期”[1]97等,诗人不仅描写石榴的外观,而且将主观情感注入其中。元明清时期,石榴诗创作虽从未消歇,然终不及唐宋盛况。
(三)石榴词
“宋元时期,石榴的栽培、采收、储藏和加工技术日趋精细,并得到全面推广。栽培范围进一步扩大,苏颂称‘安石榴……今处处有之’;品种大量增加,仅《洛阳花木记》一书就记载了9个不同的品种”[7]。因石榴的“处处有之”,所以宋代词作不乏石榴的倩影。
宋代词家喜欢以石榴入词,佳篇佳句层出不穷。欧阳修喜以石榴入词,《渔家傲·端午》中“五月榴花妖艳烘,绿杨带雨垂垂重”[1]173,以榴花绿杨带雨之姿,言端午时节环境之惬意,以至于因好梦惊醒徒生懊恼:“叶里黄鹂时一弄,犹瞢松,等闲惊破纱窗梦。”其《渔家傲·海榴》“六月炎蒸何太盛,海榴灼灼红相映”[1]174,词末写梦醒之语,与《渔家傲·端午》有异曲同工之妙。苏轼的《贺新郎》“石榴半吐红巾蹙”[1]171,《阮郎归·初夏》“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1]172,《南歌子》“无人不道看花回。惟见石榴新蕊,一枝开”[1]172。吴文英《踏莎行》“榴心空叠舞裙红,艾枝应压愁鬟乱”[1]175,张先《浣溪沙》“轻屟来时不破尘,石榴花映石榴裙”[1]186,皆以石榴之景衬构词境,而所写石榴娇艳盎然。此外黄庭坚、晏殊、叶梦得、秦观、贺铸、周邦彦等的词中亦多石榴意象。
除却宋代,其他时期石榴词创作也很多。如唐陆龟蒙《虞美人》“红裙妒杀石榴花,为言客愁无不在天涯”[1]169,唐毛文锡《月宫春》“红芳金蕊绣重台,低倾玛瑙杯”[1]170,元刘弦《蝶恋花》“人自怜花春未去。萱草石榴,也解留春住”[1]221,明文征明《青玉案》“庭下石榴花乱吐,满地绿阴亭午”[1]224,清陈维崧《贺新郎》“携酒石榴花下醉,还选腹腴亲煮”[1]229,由此可见石榴入词的悠久传统。
(四)石榴曲
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曲,亦喜以石榴意象穿插其间。21世纪初发现的五代之前的抄本曲子词《云遥集杂曲集子》中有《倾杯乐·五陵堪娉》一曲:“脸如花自然多娇媚。翠柳画峨眉,横波如同秋水。裙上石榴,血染罗衫子。”[1]233表明早在五代之际已以石榴入曲。及至宋代,汪元量的《失调名·宫人鼓瑟奏霓裳曲》有:“绿荷初展。海榴花半吐,秀帘高卷。”[1]234可明确石榴已经出现于曲间。元曲石榴意象迭出不穷。关汉卿的《双调·大德歌·夏》“困坐南窗下,数对清风想念她。峨眉淡了谁教画?瘦岩岩羞戴石榴花”[1]234,以羞戴石榴花之态言闺怨之情。可见元代之际女子对石榴花之喜爱,以之插戴发间。李致远的《双调·水仙子》“萱草发无情秀,榴花开有恨。断送得愁浓”[1]235,元好问的《双调·骤雨打新荷》“海榴初绽,朵朵簇红罗”[1]235,以花草树木如萱草、高柳、榴花为写景之物,而衬所言之情。元曲喜用石榴写景言情,且多有佳句。如白朴的《双调·乔木查》“恰春光也,梅子黄时节,映石榴华红似血”[1]236,张可久的《湖上晚归》“桃花马上石榴裙,竹叶樽前玉树春,荔枝香里江梅韵”[1]236,不胜枚举。因石榴的加入,使元曲之情思更加氤氲缱绻,韵味隽永。
明清时期,也见石榴入曲之传统。明青蕖在《玉娥郎》中以石榴言富贵人家:“对对佳人把彩扇儿拿,三伏似火发,熏风透体纱,赏名园,开败了海榴花。”[1]243明兰陵笑笑生在《山坡羊》写道:“叫了你声娇滴滴石榴花儿,你试被九花丫头传与十姊妹,什么张致?可不交人家笑话叉了。”[1]246因在明代插花的“主客”理论中,榴花被列为花主之一,而以孩儿菊、栀子、石竹、蜀葵、紫薇等为辅,故有“九花丫头传为十姊妹”之谓。清代,孔尚任在南曲名篇《桃花扇》中有“榴裙裂破舞风腰,鸾靴剪碎凌波靴”[1]247之句。
二、石榴的文学意象
人处天地自然之间,风花雪月、花鸟缠绵无不激荡心灵。历来文人作品对石榴借物喻人、状物言情,使诗词章句之间弥漫着朦胧的花果幽香。元马祖常的《咏石榴花》云:“只待绿荫芳树何,蕊珠如火一时开。”[1]135金王庭筠的《河阴道中二首》言:“一色生红三十里,际山多少石榴花。”[1]134写出榴叶的深绿、榴花的娇艳似火及繁多。出于对“安石开花比御衣”[1]113“膏凝玉润,光犹莹削……红肤贴素,揉以紫的。红须内艳,赪牙外标”[1]6的喜爱,在古诗词中石榴往往起着以物喻人的作用,其中又以女性之美为主要表现对象。晋张协的《安石榴赋》云:“荫佳人之玄髻,发窈窕之素姿,游女一顾倾城,无盐化为南威。”[1]5石榴、佳人相互辉映。宋曹勋的《题禁中黄石榴二首》说“上林别有娇黄贵,如剪冰绡衬玉肌”[1]113,榴花已然娇美,而言上林宫禁之中别有娇黄贵,实则言宫中女子的空耗青春与不得自由。
以石榴直表女子之美,随之生发出“石榴裙”的文学意象。“石榴裙”一词出现于南朝梁元帝萧绎的《乌栖曲》:“交龙成锦斗凤纹,芙蓉为带石榴裙。”[1]16“石榴裙”在唐代尤为兴盛,在诗歌中多有描写,而最为著名者莫过于武则天的《如意娘》:“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1]23将自己对唐高宗的思念化为“石榴裙”上的斑斑泪痕,此句也成为描写思念之名句。杜审言、万楚、于兰等诗人也有“石榴裙”的相关描写。大唐女子把“石榴裙”染为榴花之色,石榴花火红的色彩既映示着大唐昌盛的国运,也表现出唐代女子的活泼热情。而在唐代之后的诗歌中,“石榴”这一意象则更多带有一种幽怨、凄美的感情色彩。如宋欧阳修《榴花》“榴花最恨来时晚,惆怅春期独后期”[1]97,感伤春愁;明赵弼《石榴花塔》“至今塔畔榴花放,朵朵浑如血泪红”[1]143,寄托着对屈死孝妇的深切同情;清林瑛佩《浣溪沙》“朱阑残照映榴花,他乡客思总无涯”[1]230,表达了思乡之情。
以石榴寄寓情感之作迭出,或抒欢愉或表悲情,总能在其身上得到慰藉。白居易《卢侍御小妓乞诗座上留赠》“郁金香汉裹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1]28,诗中的“山石榴花”带有娇美之态,小妓“好似文君”“胜于神女”,即使宋玉、荆王也慕羡,此处情感是喜悦、欣赏的。而其《山石榴寄元九》“商山秦岭愁杀君,山石榴花红夹路。题诗报我何所云?苦云色似石榴裙”[1]29,此诗感情在“思我”“忆君”,故而事物也带上了伤感色彩,“商山秦岭”是“愁”的、美丽的“石榴裙”此时也色似“苦云”。
因为石榴的花期较晚,所以石榴意象也往往用以表达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郁塞之情。宋晁冲之《戏成》“榴花不得春风力,颜色何如桃杏深”[1]109,唐黄滔《奉和文尧对庭前千叶石榴》“移根若在芙蓉苑,岂向当年有醒时”[1]51,此类诗皆借为石榴鸣不平以表达诗人内心的不平之情。唐人许浑《游灵伽寺》诗云:“碧烟秋寺泛湖来,水打城根古堞摧。尽日伤心人不见,石榴花满旧琴台。”[1]72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之感借火红的石榴花映衬,更显对“旧琴台”往事故人的思念。司空曙《赠李端》诗云:“楚田湖草远,江寺海榴多。载酒寻山宿,思人带雪过。东西几回别,此会各蹉跎。”[1]69此去各东西,往昔自蹉跎,虽有海榴见证,而往后也只有睹物思人了。
三、石榴的文化寓意
石榴在历代的歌咏传承中,有着大吉大美的文化寓意。晋潘岳《河阳庭前安石榴赋》云:“曾华晔以先越,含荣蘤其方敷;丹晖缀于朱房,缃菂点乎红须。煌煌炜炜,熠烁入蘂龠委累;似玻璃之栖邓林,若珊瑚之映绿水。”[1]2潘尼《安石榴赋》云:“披绿叶兮修条,缀朱华兮弱干,岂金翠之足珍,实兹葩之可玩。”[1]1宋祁《淡红石榴》诗云:“移植自西南,色浅无媚质。不竞灼灼花,而效离离实。”[1]103他们对石榴质实不媚,不竞花事的品质多加赞赏。石榴色彩艳丽,形态富贵雍容,因而寓意大吉大美。
“五月榴花照眼明”,榴花是美丽的表征。古代有以花名月份的传统,柳月、杏月、桃月等,而农历五月因其为榴花盛放的季节,被称为“榴月”。每逢榴花绽放季节,亦是诗家诗兴大发之时。唐元稹诗《感石榴二十韵》云:“何年安石国,千里贡榴花。……风翻一树火,点转物云车。”[1]52把烂漫绽放的石榴花比作火,而随风吹过花朵摇曳犹如火花跃动,可见榴月花势之盛。
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传统,因“榴”与“柳”同音,故而也有“送榴传谊”之说。如梁王筠《摘安石榴赠刘孝威诗》诗云“相望阻盈盈,相思满胸臆。高枝为君采,请寄西飞翼”[1]18,将满心的相思与祝福寄寓石榴,望友人得知。相传宋人以裂开石榴籽数占卜科举上榜人数,“榴实登科”一词即从此流传而来。南梁陶弘景言:“石榴花赤可爱,故人多植之。”[8]1287古人多喜于庭院栽植石榴,以寄寓繁荣昌盛、和睦团结、吉庆团圆。宋陈师道《后山谈丛》载:“广济衙门之上有石榴木,相传久矣。元丰末枯死,既而军废为县,元祐初复生,而军复。”[9]21把石榴之枯荣看作一地兴废之预兆,石榴似乎也带上了一层奇幻色彩。
石榴不仅因其鲜美多汁而深受人们喜爱,更因其胚珠多数、种子众多,使之有着多子多福的象征。明王谷祥《题石榴》诗云:“榴房拆锦囊,珊瑚何齿齿。试展画图看,凭将颂多子。”[1]149此处化用《北史·魏收传》魏收解石榴之典故:“安德王延宗纳赵郡李祖收女为妃,后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荐二石榴于帝前。问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10]2033石榴腹内多子的结构使之在婚事间多受青睐,俗称“榴开百子”。新婚时,新房中的陈设,如窗花、帐幔、枕头等,图案上往往是连着枝叶、露出累累硕果的石榴,以此象征多子多孙;或者图案上一群婴孩嬉戏于石榴树旁,谓之“榴开百子”。此外,石榴的“多子”寓意也和官爵相联系,画着石榴和黄莺图案的“金衣百子图”,寓意着人们对未来的祝愿与期待——高官位显,百子围膝。
多子多福的生殖崇拜映射在石榴上,使得石榴有着母亲、爱情、后代的角色寓意,在古诗词中,这种寓意也多有反映。如宋张幼谦《一剪梅》词云:“同年同日又同窗,不似鸾凤,谁是鸾凤。石榴石下事匆忙,惊散鸳鸯,拆散鸳鸯。”[1]191宋韩元吉《谒金门·重午》词云:“往事潇湘南浦,魂断画桥萧鼓。双叶石榴红半吐。倩君聊寄与。”[1]196石榴在爱情、婚姻上寄寓着的不仅是一种美好意愿,更是一种文化积淀。唐段公路《北户录》载:
郑公虔云:石榴花堪作烟支。代国长公主睿宗女也,少尝作烟支,弃子于阶,后乃丛生成树,花实敷芬。既而叹曰:“人生能几?我昔初笄,尝为烟支,弃其子。今成树阴映锁闼,人岂不老乎!”[11]29
石榴生命力极强,昔日作胭脂而抛的“弃子”,竟能丛生成树,花实敷芬。代国长公主面对此情此景,不由发出岁月易逝、韶华不再的感慨。《汉乐府·黄生曲三首》其一云:“松柏叶青茜,石榴花葳蕤。迮置前后事,欢今定怜谁。”[1]11此诗表达了美好逝去而无可奈何之情。
四、结 语
石榴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观赏价值,其作为一种文学意象被人们带入赋、诗、词、曲等文体中,人们以石榴喻佳人,在大量的石榴描写中抒发内心情感。同时,石榴还被人们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一为大吉大美之意,二为由其独特的生物特征引发的“千子千房”的生殖寓意。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赞美下,石榴由实用性的植物发展为一种文学意象,并由此形成深厚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