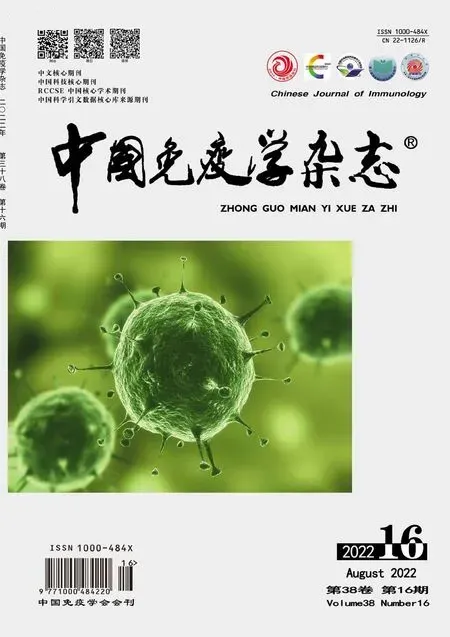胆汁酸免疫调节作用及其与肠道、肝脏炎症性疾病相关性的研究进展①
于 爽 顾志敏 樊亚东 李玲玲 边育红 (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1600)
胆汁酸是一类具有类固醇结构的有机酸,由肝细胞以胆固醇为底物合成,在胆囊中储存,并在肠道与肝脏间不断循环,主要功能为促进脂类物质的消化吸收[1]。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胆汁酸具有多种生理功能,不仅参与机体脂类物质的代谢,还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对维持肠道、肝脏内环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2]。肠道及肝脏是机体内外环境之间的主要界面,为进行营养物质的交换,长期直接或间接与食物、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等肠源性抗原物质接触,依赖肠道微生物群、肠上皮屏障、肠道免疫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对无害共生抗原保持免疫耐受,对有害危险抗原产生免疫反应,以形成稳定平衡的内环境[3-4]。胆汁酸可在肠肝循环过程中通过抑制肠道致病菌,维护肠上皮屏障来预防肠道、肝脏炎症反应的发生,同时也可通过调节免疫细胞功能,维持肠道、肝脏对无害抗原的免疫耐受,在肠道、肝脏内环境稳态维持中起到关键作用[2,5-6]。研究表明,多种肠道、肝脏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可能与胆汁酸参与的免疫调节作用失调有关[2]。本文就胆汁酸对肝及肠道的免疫调节作用进行综述,为进一步明确胆汁酸在相关肠道、肝脏炎症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及治疗作用提供参考。
1 胆汁酸的肠肝循环过程
胆固醇在肝细胞内直接转化为两种初级游离胆汁酸:胆酸(cholic acid,CA)和鹅脱氧胆酸(chenodeoxycholic acid,CDCA)。CA和CDCA分别与牛磺酸(Taurine,T)或甘氨酸(Glycine,G)结合,于肝脏内形成初级结合胆汁酸:T/GCA和T/GCDCA,经胆管分泌至胆囊储存,随进食排入十二指肠。约90%的初级结合胆汁酸在回肠末端经主动重吸收机制返回肝脏,小部分经肠道菌群去结合作用还原为初级游离胆汁酸,再经肠道菌群脱羟基作用形成次级游离胆汁酸:脱氧胆酸(deoxycholic acid,DCA)、石胆酸(lithocholic acid,LCA)。初级和次级游离胆汁酸经被动重吸收在小肠前段及结肠各部回到肝脏。返回至肝脏的游离胆汁酸转化成结合胆汁酸:T/GDCA和T/GLCA,与重吸收和新合成的结合胆汁酸一起随胆汁排入肠道,由此形成胆汁酸的肠肝循环(图1)。在肠、肝、胆管、胆囊的共同作用下,肠肝循环每日进行6~12次,每次均有约95%的胆汁酸被重吸收。肠肝循环的最大意义在于使有限的胆汁酸得到充分利用,以满足机体日常消化吸收的需求[1,7]。

图1 胆汁酸的肠肝循环[7]Fig.1 Enterohepatic circulation of bile acids[7]
2 胆汁酸的免疫调节作用
胆汁酸在进行肠肝循环的过程中发挥免疫调节作用,可通过抑制肠道致病菌,维护肠上皮屏障来预防肠道、肝脏炎症反应的发生,也可通过调节肠道、肝脏免疫细胞功能维持肠道及肝脏对无害抗原的免疫耐受,以此维持肠道、肝脏内环境稳定。
2.1 胆汁酸抑制肠道致病菌 哺乳动物的胃肠道内寄生着大量菌群。这些菌群参与宿主的消化、代谢、能量转化等生理活动,与宿主共同进化、互利共生,各类菌群在数量、比例及定位上保持动态平衡[8]。肠道致病菌是菌群中能够引起疾病的一类菌群,正常情况下难以在宿主肠道内定植,以少量形式存在,大量增殖将损伤肠上皮细胞,使肠黏膜通透性增加。菌体及毒素进入肠黏膜后将激活免疫细胞,诱发强烈的免疫反应,造成肠道、肝脏组织损伤[9-10]。胆汁酸可直接作用于致病菌,通过减少致病菌的过度增殖,抵御肠道致病菌感染,防止感染引起的肠道、肝脏内环境紊乱[11]。胆汁酸抑制致病菌增殖的主要方式为破坏菌体细胞膜完整性[12]。研究表明,不同浓度的CA、CDCA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的增殖均有抑制作用。低浓度的胆汁酸即可降低菌体内pH值、影响细菌细胞膜流动性及渗透性,而高浓度的胆汁酸则直接溶解细菌外膜,导致内容物渗漏,促使细菌死亡[13]。胆汁酸还可促使致病菌发生基因突变、染色体重排,通过直接损伤DNA的方式诱导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死亡,从而抑制其在肠道内生长增殖[14]。除直接损伤细菌结构外,胆汁酸还可影响条件致病菌的毒力和侵袭能力。HAMNER等[15]发现胆汁酸可下调大肠杆菌毒力相关基因mRNA表达,影响其鞭毛及趋化性基因的转录。临床研究表明,肝硬化患者常伴有肠道致病菌的过度生长、菌群失调,易引发肠道局部及全身的炎症反应,可能与胆汁酸不能正常排泄发挥抗菌作用有关[16]。胆汁酸对肠道益生菌损伤则非常小,可能与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可通过外排泵、转运蛋白等抵消胆汁酸的有害作用有关[17]。
2.2 胆汁酸维护肠上皮屏障 肠上皮屏障由肠道上皮细胞、细胞间紧密连接及细胞表面黏液层构成,在防止致病菌及其内毒素等有害物质侵入机体、维护肠道、肝脏内环境稳定方面发挥极重要的作用[18]。肠道上皮细胞及细胞间的紧密连接是保证机械屏障功能正常发挥的结构基础,覆盖在肠上皮细胞表面的黏液层则可通过物理隔绝作用有效阻止致病菌和肠上皮细胞的接触,肠道上皮细胞中的潘氏细胞还可通过分泌抗菌肽降低致病菌丰度[19-20]。胆汁酸可通过维护肠上皮屏障阻止致病菌入侵,间接防御致病菌感染,保持肠道、肝脏稳态平衡[21]。胆汁酸对肠道上皮细胞的增殖具有促进作用。研究表明,TDCA可通过增加细胞增殖基因C-myc表达促进肠上皮细胞增殖,TCA可通过激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诱导细胞增殖[22-23]。胆汁酸可促进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将胆汁酸与大鼠小肠隐窝上皮细胞IEC-6共同培养,可发现胆汁酸通过激活有丝分裂活化蛋白激酶ERK1/2增加ZO-1等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降低上皮细胞通透性[24]。胆汁酸可增加黏液层厚度。在大鼠和兔的结肠中,游离胆汁酸可直接刺激杯状细胞分泌黏液,使结肠黏液层增厚[21]。胆汁酸还可促进抗菌肽合成。用含CDCA的饲料喂食小鼠,可上调α-防御素、Reg3b、Reg3g等抗菌肽的转录与表达,在基因和蛋白水平上促进抗菌肽合成[25]。
2.3 胆汁酸对肠道、肝脏免疫细胞的调节作用肠腔内存在大量的共生菌群及食物蛋白,肠道、肝脏需要对这些无害抗原保持免疫耐受才能在满足机体需求的同时维持内环境稳定。肠道、肝脏对无害抗原免疫耐受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多种免疫细胞的共同作用[6-7,26]。胆汁酸可通过抑制巨噬细胞功能及促进调节性T细胞分化维持肠道及肝脏的免疫耐受状态。胆汁酸对巨噬细胞功能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激活胆汁酸受体实现。胆汁酸受体主要包括法尼醇X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FXR)等核受体,以及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1(G protein-coupled bile acid receptor 1,GPBAR1,TGR5)等膜受体,巨噬细胞主要表达TGR5[27]。研究表明,胆汁酸激活巨噬细胞TGR5受体后,主要发挥抑制性调节作用,可降低外周血及肠道、肝脏来源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减少其TNF-α、IL-1α、IL-1β和IL-6等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同时促进巨噬细胞由促炎型M1(高IL-12)向抗炎型M2(高IL-10)转变[28-29]。此外,巨噬细胞激活后可通过促进炎症小体的生成加剧炎症反应,LCA可通过TGR5-cAMP-PKA通路抑制炎症小体NLRP3活化,阻断NLRP3依赖的caspase-1活化和IL-1β分泌[30]。肠道固有层中的调节性T细胞(Tregs)是具有预防、减弱、终止炎症反应功能的免疫细胞,是维持肠道免疫稳态的重要因素[31]。胆汁酸可通过影响Tregs的分化,维持肠道、肝脏对无害抗原的免疫耐受。HANG等[32]将小鼠初始T细胞与LCA代谢产物3-oxoLCA、isoalloLCA共同培养,发现isoalloLCA可通过产生线粒体活性氧的方式促进Treg特异性转录因子FoxP3表达,增强Treg分化;而3-oxoLCA则直接与辅助性T细胞17(Th17)特异性转录因子RORγt结合,抑制具有促炎作用的Th17分化。SONG等[33]在小鼠饮用水中加入不同类别的胆汁酸,发现CA、CDCA、LCA等均可使小鼠体内RORγ+Treg细胞数量增加。在硫酸葡聚糖钠(dextran sulfate sodium,DSS)诱导的小鼠结肠炎模型中,补充含有胆汁酸的饲料及饮用水可通过增加小鼠肠道中的RORγ+Treg细胞数量缓解小鼠的肠炎症状。
3 胆汁酸免疫调节作用与肠道、肝脏相关炎症性疾病
胆汁酸的免疫调节作用对肠道、肝脏内环境稳态维持具有重要意义。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肠源性内毒素血症、非酒精性脂肪肝等肠道、肝脏相关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可能与胆汁酸参与的免疫调节作用发挥失调有关。
3.1 炎症性肠病 IBD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慢性肠道炎症性疾病,近年来我国患病率显著增高。IBD患者常伴有致病菌大量增殖、肠上皮细胞损伤、肠黏膜组织炎症细胞大量浸润等病理表现,肠道稳态环境破坏是IBD发病及持续进展的重要原因[34]。研究表明,与健康人相比,IBD患者血清胆汁酸谱发生明显改变,胆汁酸代谢紊乱可能在IBD进展中起到关键作用,补充胆汁酸可有效改善炎症性肠病[35]。在用三硝基苯磺酸(trinitrobenzene sulfonic acid,TNBS)和DSS诱导的急慢性结肠炎中,胆汁酸明显改善了小鼠结肠组织的炎症性损伤。奥贝胆酸(obeticholic acid,OCA)是一种人工合成胆汁酸,结构与CDCA相类似。OCA与TNBS一同喂养小鼠可有效预防TNBS诱导结肠炎的发生。用OCA治疗TNBS、DSS诱导的结肠炎小鼠,可减轻体重减少、肠道长度缩短及溃疡出血的症状,改善其炎症细胞浸润、肠黏膜通透性增加、杯状细胞丢失的病理状态[36-37]。熊去氧胆酸(ursodeoxycholic acid,UDCA)在人体内含量较少,主要在动物胆汁中提取,可人工合成,UDCA及LCA均可在DSS诱导的小鼠结肠炎症模型中减轻炎症因子的释放,从而减轻结肠炎的发展[38]。虽然胆汁酸对IBD的治疗作用在实验室研究中已得到初步验证,但目前还缺乏临床相关证据。
3.2 非酒精性脂肪肝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一种非酒精因素造成的以肝脏中脂质沉积、肝细胞脂肪变性为特征的慢性肝病,全球患病率高达25%[39]。一般情况下NAFLD进展较为缓慢,一旦发展为非酒精性脂肪型肝炎,则可迅速演变至肝硬化、肝癌。迄今为止,肝移植是NAFLD肝硬化患者唯一的治疗方法,因此亟需明确其疾病进展原因并应用药物延缓其发展[40]。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失调、肠上皮屏障受损等肠道稳态失衡是NAFLD病情进展的重要原因。大量肠源性抗原随门静脉进入肝脏后,氧自由基、脂多糖将会直接作用于肝实质细胞或库普弗细胞,促使炎症、氧化应激、内质网应激的发生,造成肝脏进一步损伤[41]。有证据表明,NAFLD疾病状态下发生的胆汁酸代谢异常、胆汁酸组成改变可能是肠道稳态失衡、促进NAFLD进展的重要原因[42]。人工合成的胆汁酸OCA可使NAFLD肝脏病变明显改善,减缓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肝硬化进展,其治疗作用与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密切相关[43-44]。目前美国正在进行多中心的Ⅲ期临床试验(NCT02548351、NCT03439254)以评估OCA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推动OCA成为治疗NAFLD的一线用药[42]。
3.3 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肠源性内毒素血症是一种由于肠道稳态环境破坏,肠道细菌及内毒素突破肠上皮屏障进入全身血循环的病理表现,可出现在梗阻性黄疸、肝硬化等多种疾病进程中,易诱发全身炎症反应、多器官功能衰竭[45-46]。研究表明,肠腔中缺乏胆汁酸可能为梗阻性黄疸、肝硬化患者易发展为内毒素血症的主要原因[47-48]。病理组织检查显示,梗阻性黄疸患者肠上皮细胞可见大量空泡、肠绒毛稀疏水肿,实施胆道内引流术恢复肠道内胆汁酸循环后,可明显减轻梗阻性黄疸患者肠上皮细胞损伤,而将胆汁体外引流出的手术方式则无此治疗效果[47]。肝硬化患者及实验动物模型常伴有肠道菌群过度增殖、上皮细胞间紧密连接受损、抗菌肽合成障碍等异常表现。口服OCA可纠正肝硬化模型大鼠的菌群失调,上调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ZO-1及血管生长素-1表达,减轻大鼠肠道炎症细胞浸润及全身炎症反应[48]。因此,通过手术或口服药物的方法维持胆汁酸的肠肝循环可有效预防、治疗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4 小结
胆汁酸在肝脏中合成,在肝及肠道中不断循环。临床及实验研究初步证实,胆汁酸在循环过程中可通过抑制肠道致病菌、维护肠上皮屏障来预防肠道、肝脏炎症反应的发生,也可通过调节肠道、肝脏免疫细胞的功能维持肠道及肝脏对无害抗原的免疫耐受,以此维持肠道、肝脏内环境稳定。胆汁酸的免疫调节作用与多种肠道、肝脏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均有密切联系。胆汁酸有望成为相关炎症性疾病的新型治疗靶点。
尽管胆汁酸对肠、肝组织的免疫调节作用已逐步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但当前阶段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不足,需要通过体内及体外试验进一步探究、验证胆汁酸的免疫调节作用及机制,不断开发其治疗肠道、肝脏炎症性疾病的潜力,同时努力促进已有实验室研究成果向临床转化,推动胆汁酸类新型药物的研发与应用。在研究和临床应用过程中应关注胆汁酸本身的结构与性质。胆汁酸是具有亲水基团(羟基、羧基)和疏水基团(烷基)的两性分子,有亲水和疏水两种构型。疏水性胆汁酸(DCA/CDCA等)具有细胞膜破坏作用,刺激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的释放,并可引起线粒体氧化应激造成细胞凋亡,且亲水性胆汁酸(UDCA)在超过一定浓度时也会产生明显的细胞毒性作用[49]。因此在临床应用过程中要全面考虑胆汁酸种类、浓度与作用的关系,保证药物的安全性,使胆汁酸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目前应用于临床的胆汁酸类药物主要为OCA和UDCA,其中UDCA主要来源于熊、牛等动物的胆汁[50]。熊胆汁的干燥品——熊胆粉,是一味珍贵的传统中药,具有清热解毒、保肝利胆、豁痰开窍等多重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保肝、利胆、抗菌、抗病毒、抗炎、抗肝纤维化等多种药理作用,常用于治疗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胆囊炎等多种肝胆系统疾病[51]。有研究表明,熊胆粉可减轻NAFLD肝脏损伤,延缓肝纤维化及肝硬化的发生[52],但机制尚未明确。进一步研究熊胆粉是否通过其主要药效成分胆汁酸发挥免疫调节作用而延缓NAFLD疾病进展,将有利于明确熊胆粉治疗NAFLD的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对中医药现代化的研究与应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