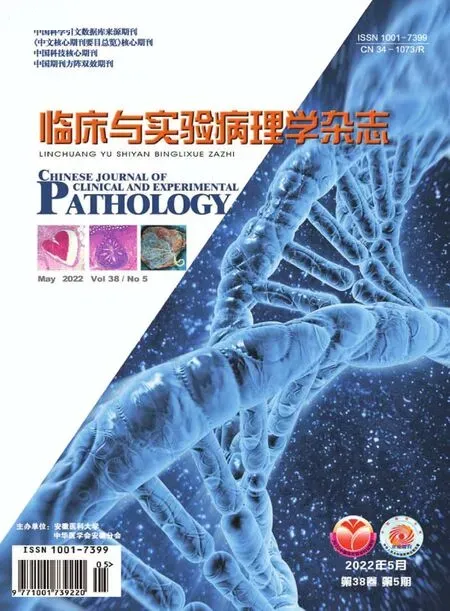结直肠癌中MCL-1基因的研究进展
罗灵芝,张雨涛
髓样细胞白血病-1(myeloid cell leukemia-1, MCL-1)是BCL-2家族中的重要抗凋亡基因,在调节细胞分化和凋亡中起重要作用。在肿瘤性疾病及其癌前病变中有MCL-1基因重排现象[1]。研究表明,MCL-1在肿瘤细胞生存和耐药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是消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均较高。MCL-1在CRC组织中较正常肠黏膜和腺瘤组织高表达,提示其在CRC的发生、发展中可能起一定的作用,其表达可能与治疗、预后密切相关。本文现就MCL-1在CRC中的研究现状及进展进行综述。
1 MCL-1的结构及功能
MCL-1基因定位于人染色体1q21,全长6 502 bp,含有3个外显子和2个内含子,具有结构特异性,并广泛分布于线粒体和细胞质中。MCL-1含有三段BCL-2基因同源区域(BCL-2 homology regions, BHR)BH1、BH2、BH3和C末端跨膜结构域(transmembrane domain, TMD),可使MCL-1与细胞内膜结合;以及一段潜在的PEST(富含脯氨酸P、谷氨酸E、丝氨酸S、苏氨酸T)序列,可介导蛋白质快速降解[3]。MCL-1基因在转录过程中存在短拼接变异,可转录生成2种mRNA,并翻译为2种不同的蛋白。(1)MCL-1L蛋白:由3个外显子翻译而来,含有350个氨基酸残基,该蛋白含有BHR和TMD,主要功能为抑制细胞凋亡;(2)MCL-1S蛋白:丢失外显子2,仅由外显子l和外显子3翻译而来,含有271个氨基酸残基,与MCL-1L相比,缺失BH1、BH2结构域和TMD,功能与BH3-only蛋白相似,作为死亡配体,促进细胞凋亡[4]。
MCL-1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调控细胞凋亡:(1)MCL-1通过线粒体介导的内源性凋亡通路调控凋亡,与促凋亡蛋白Bak结合并维持其在线粒体膜表面的活性,保持对Bak活化的抑制作用,阻止Bak与Bax形成二聚体,进而抑制细胞色素C释放,抑制细胞凋亡。(2)MCL-1通过与具有激活作用的BH3-only蛋白(Bid、Bim和Puma)结合发挥抗凋亡作用,且MCL-1在肺、前列腺、乳腺、卵巢、肾脏和胶质瘤等癌细胞系中具有较高的mRNA水平[5],提示MCL-1可能通过抑制凋亡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分析。
MCL-1广泛表达于人类正常组织,在上皮组织(如乳腺、胃、前列腺、小肠、结肠及呼吸道等)、淋巴结生发中心B细胞区域和神经内分泌细胞(如肾上腺皮质、交感神经元、部分胰岛细胞及睾丸生精细胞等)均有表达,在调节细胞存活和凋亡中起关键作用[2,6]。MCL-1蛋白定位于细胞内膜系统,主要存在于线粒体外膜,但MCL-1在细胞核内也有表达[7]。MCL-1的主要功能是维持线粒体膜稳定,抑制细胞色素C释放,从而阻止凋亡发生,促进细胞生存。因此,即使在各种诱导细胞凋亡的刺激条件下,MCL-1也能延长造血细胞的生存能力,同时亦是肿瘤细胞生存的关键因子。另外,MCL-1的裂解产物也可以促进细胞凋亡,其裂解产生的细胞死亡促进蛋白可参与形成正反馈回路,诱导更多的Caspase活化。MCL-1除具有抗凋亡功能外,也可直接调控细胞分化和细胞周期[8]。MCL-1可以与PCNA、CDK-1、CHK-1相互作用,引起细胞周期阻滞[9-10]。MCL-1在一些恶性肿瘤中过表达,提示其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并且可以诱导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产生抵抗作用;而下调MCL-1蛋白表达可促进肿瘤细胞凋亡,提示MCL-1是肿瘤治疗的潜在靶点[11]。
2 MCL-1在CRC中的研究进展
2.1 CRC的流行病学特征2019年1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全国癌症统计数据。由于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统计数据一般滞后发布时间3年,故本次公布的数据系2015年全国恶性肿瘤的发病和死亡情况。该数据显示CRC总发病率位居中国恶性肿瘤的第4位,病死率位居第5位;在男性患者中发病率位居第4位,病死率位居第5位;而在女性患者中发病率位居第3位,病死率位居第4位;在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中,CRC的发病率均位居前5位。由此可见,CRC是危害中国人群健康的危险肿瘤[12],如何提高CRC治疗效果,降低病死率等问题急需解决。
2.2 MCL-1与CRC抗癌作用机制CRC的进展是由一系列明确的遗传基因改变所驱动的,包括APC、BRAF、KRAS、PIK3CA、p53、FBW7等基因突变[13-14]。MCL-1可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凋亡和增强CRC的血管生成导致肿瘤进展,进一步证明MCL-1在CRC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可以作为潜在的抗癌治疗靶点[13]。
目前,外科手术仍然是CRC的首选治疗方式,尤其是对处于疾病早期的患者。但大量临床实践表明仅靠手术切除并不能完全杜绝肿瘤复发和远处转移。因此,手术联合放、化疗成为提高患者预后和生存率的关键。天然和人工合成药物通过多种途径下调MCL-1在CRC中的表达,发挥抗癌作用,如多种小分子MCL-1抑制剂。体外实验也证明,可通过多个信号通路途径下调MCL-1的表达,抑制CRC肿瘤细胞生长[15]。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许多药物可以通过调节CRC中STAT/MCL-1轴的表达,从而达到抗癌效果,如利用Magnolin可以阻断LIF/STAT3/MCL-1轴,促进肿瘤细胞自噬和细胞周期停滞[16]。Furowanin A也有类似作用,可通过抑制STAT3/MCL-1轴以促进肿瘤细胞自噬,进而促进肿瘤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停滞[17]。Ruxolitinib则是通过下调JAK1/2-STAT1-MCL-1轴,促进肿瘤细胞凋亡[18]。此外,热休克蛋白90(heat shock protein 90, HSP 90)抑制剂也可以抑制JAK2-STAT3-MCL-1轴,促进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的肿瘤细胞凋亡[19]。Lu等[20]通过评估依维替尼抗癌特性的潜在机制,表明该药物也是通过抑制CRC中抗凋亡分子MCL-1的表达,诱导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停滞。抗癌活性肽(anticancer bioactive peptides, ACBP)系通过调节PARP-p53-MCL-1信号通路,抑制人CRC肿瘤细胞生长和诱导癌细胞凋亡[21]。此外,一些新的激酶抑制剂通过靶向作用于CDK9和GSK-3β信号通路,也可以降低CRC中MCL-1的表达[22]。与其他多数肿瘤一样,CRC的肿瘤微环境存在多种免疫细胞浸润,通过FBW7-MCL-1轴可以抑制M1和M2巨噬细胞在结肠癌的肿瘤微环境中生长[23],而针对MCL-1的免疫治疗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除常规抗肿瘤药物以外,新近发现常用降血糖药物二甲双胍,也可以通过Mule降解CRC癌细胞中的MCL-1,提高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的表达从而导致凋亡[24]。总之,通过多种途径降低CRC中MCL-1的表达均可起抗癌作用,未来的药物研发方向不一定仅仅局限于特定的抗肿瘤药,其他专科用药或许也有抗癌疗效。
2.3 MCL-1与CRC化疗耐药性的关系耐药是肿瘤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CRC耐药患者中MCL-1出现过表达,提示耐药性可能通过MCL-1的抗凋亡作用所导致的。有文献报道,GST-π和P-gp可通过不同的机制参与肿瘤耐药[25]。CRC患者中MCL-1的表达与GST-π无相关性,而与P-gp的表达相关[26-27],提示MCL-1基因可能与肿瘤耐药相关,但具体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因此,可以假设通过抑制MCL-1的表达或者阻断MCL-1相关信号通路,降低CRC患者对化疗药物的耐药性。MCL-1的降解是受到多种激酶抑制剂诱导,其中主要依赖于GSK3β磷酸化和依赖FBW7的泛素化降解[28]。在CRC中有一种新的激酶抑制剂可通过GSK3β通路下调MCL-1,促进肿瘤细胞凋亡[22];而其他一些药物也可以通过调节FBW7-MCL-1轴达到或加强抗肿瘤作用[29-30]。FBW7突变引起的MCL-1降解阻断,可调节结肠癌对靶向治疗药物的抵抗力[31]。上述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多种抗肿瘤药物可下调MCL-1的表达,解除耐药并促进肿瘤细胞凋亡。在BRAF V600E基因突变的CRC患者中,其介导的MEK/ERK信号通路激活可通过磷酸化稳定作用上调MCL-1,从而赋予其凋亡抗性。MCL-1拮抗剂和Cobimetinib可逆转该凋亡抗性,提示其为新的针对性治疗途径[32]。这也与He等[33]的研究结果相似,即PI3K/MEK/ERK介导的MCL-1上调,导致BRAF V600E阳性肿瘤细胞对依维莫司耐药,但可以通过药理学措施进行逆转。证实了MCL-1表达上调和BRAF V600E突变是mTOR抑制剂在CRC癌细胞中耐药的关键机制,提示MCL-1与CRC耐药有相关性。在CRC中,MCL-1抑制剂可以通过恢复凋亡路径来克服Regorafenib的先天性和获得性耐药[34],提示通过抑制MCL-1的表达,可以恢复抗肿瘤药物的疗效而拮抗耐药,为耐药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方向,即抗肿瘤药物与MCL-1抑制剂联用,可提高抗肿瘤药物的疗效并降低耐药性。
2.4 MCL-1与CRC的预后国内文献报道MCL-1在CRC中的阳性率为76%~79.76%,明显高于癌旁正常肠黏膜和结直肠腺瘤。MCL-1的表达亦与CRC分化程度、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及5年生存期相关(P<0.05),提示其可能在CRC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可作为CRC治疗和预后的判断指标[26,35-36]。这与Henderson-Jackson等[37]的报道相吻合,即CRC中MCL-1的表达与肿瘤分级、分期及远处转移相关。本组仅有9例CRC转移,转移病例数较少。尽管大部分文献报道MCL-1在CRC中的过表达与不良预后有关,但Xin等[38]分析31例伴BRAF突变和错配修复蛋白缺陷的CRC,发现MCL-1的表达与低分级、淋巴管浸润和淋巴结转移及AJCC分期低相关,认为MCL-1表达的CRC患者有良好的预后,与文献报道不符。由此可见,还需积累更多样本和长期随访进一步分析。
远处转移是CRC患者预后不良及生存率低的重要原因。脯氨酰羟化酶3减弱MCL-1介导的ATP产生,可抑制CRC细胞的转移潜力[39]。Lee等[13]的研究结果亦认为过表达MCL-1可能与CRC发生远处转移有关,但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3 结语
正常情况下,人体通过调节细胞凋亡与抗凋亡平衡,维持其正常生长发育过程,该平衡一旦被破坏,易导致疾病的发生。MCL-1具有抗凋亡作用,其高表达可能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在CRC患者肿瘤组织中MCL-1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正常肠黏膜和结直肠腺瘤,提示MCL-1的过表达与CRC的发生、发展有关。
综上所述,MCL-1在CRC中过表达与组织学分级、分期、分化程度、淋巴结和远处转移、化疗耐药及预后等有相关性。化疗药物通过下调MCL-1表达或阻断MCL-1信号通路,可促进CRC肿瘤细胞凋亡,提示MCL-1是治疗CRC的潜在靶点,而抑制MCL-1过表达也是抗肿瘤药和解除化疗药耐药性的重要研发方向。因此,了解MCL-1在CRC中的表达,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和患者预后评估具有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