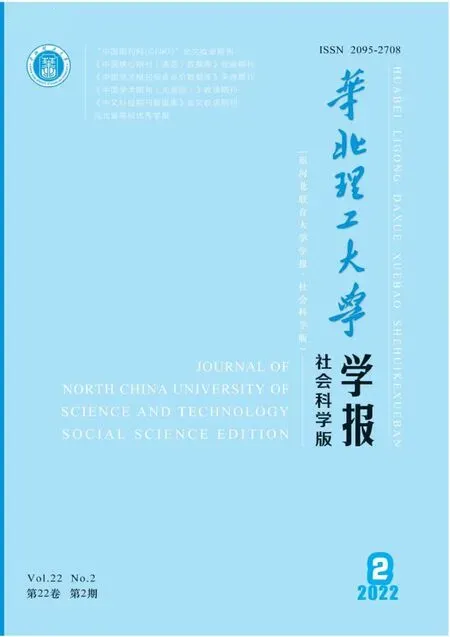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的目的与边界
任学婧
(1.华北理工大学 人文法律学院,河北 唐山 063210;2.河北大学 法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引言
药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事关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2019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1]确保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2020年12月26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十一)》)与2019年《药品管理法》相衔接,回应现实关切,修改了涉及药品的相关犯罪,将妨害药品管理秩序的行为剥离出假药的范畴,不再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但仍然具有刑法可罚性,新增妨害药品管理罪进行规制,完善了涉药品犯罪罪名设置体系。然而,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正确适用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对妨害药品管理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目的是什么?如何理解妨害药品管理刑法规制的行为类型?妨害药品管理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是什么,换言之,如何界定妨害药品管理刑法规制的范围?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解读分析,希冀有助于妨害药品管理刑法规制的合目的性及司法适用的有效性。
一、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的目的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每个刑法分则条文都源于保护法益的目的。《修(十一)》增设妨害药品管理罪,将值得科处刑罚的妨害药品管理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是法益保护原则的体现。因而,厘清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的目的是本罪司法适用的前提和基础。
(一)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的直接目的是维护药品管理秩序
2019年《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劣药的概念进行调整,科学划定假药、劣药的范围,以药品质量功效为标准重新界定假药、劣药的定义,[2]更加符合普通民众对假药的认知,并且进一步将原来拟制型假药、拟制型劣药中属于单纯违反药品管理秩序的行为,排除出假药、劣药的范畴,部分置入《药品管理法》第124条予以调整。由于前置法《药品管理法》的修改,《刑法》第141条、第142条无法再规制这类违反药品管理秩序的行为,因此,为了弥补违反药品管理秩序行为的刑罚处罚漏洞,《修(十一)》增设妨害药品管理罪,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维护药品管理秩序。从《修(十一)》对《刑法》第142条之一增设的条文内容来看,“违反药品管理法规”表明妨害药品管理罪违反的法规内容是药品管理法规,而药品管理法规作为行政性法律,其规范目的是保护国家对药品的正常监督管理秩序,进而印证了妨害药品管理刑法规制的直接目的是维护药品管理秩序。
(二)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妨害药品管理刑法规制的直接目的在于维护药品管理秩序,但不能止于此。有论者指出,“罪刑规范的目的并非单纯保护行政管理规范的效力,也不是仅仅为了保护某些抽象的行政管控秩序,而意欲保护特定的、与构成要件紧密关联的法益”并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为例,认为其保护法益“不能笼统地理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其侧重点在于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权。”[3]同为《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妨害药品管理罪,刑法规制的目的并不是仅限于维护药品管理秩序,根本上是为了保护公众的人身权利。质言之,药品管理法律法规维持药品管理秩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的利益。药品管理秩序是服务于保护公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各种规章制度,维护药品管理秩序最终是为了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药品管理秩序与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具有目标和价值上的一致性。例如,《药品管理法》第1条就明确规定:加强药品管理的终极目的是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刑法是将值得科处刑罚处罚的行为作为自己的规制对象,学界普遍认为刑法保护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等基本权益。[4]质言之,刑法维护的秩序是与个人的实体权益直接相关的那部分,并且保护这一秩序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保护个体的基本权益。
具体来说,刑法保护药品管理秩序最终是为了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那些与公众的生命健康权益无关或关联度不大的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并不在刑法的规制范围之内。《刑法》第142条之一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作为妨害药品管理罪的入罪条件,表明刑法规制妨害药品管理深层次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这是因为违反药品管理法规的行为都侵害药品管理秩序,如果刑法规定妨害药品管理的目的是保护单纯的药品管理秩序,那么只要违反药品管理法规,侵害药品管理秩序的行为就可以成立妨害药品管理罪,这样与刑法要求成立本罪必须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规定不符,违反罪刑法定主义,同时会导致违反药品管理秩序的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界限不清,模糊了刑事处罚的边界。因而,刑法规制妨害药品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公众生命健康安全。
二、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的行为类型
妨害药品管理罪列举的四种行为皆是违反药品管理法规的行为,这里的药品管理法规应当是指以《药品管理法》为核心,包括药品研发、生产、经营等一系列过程的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5]明确刑法规制的这四种妨害药品管理行为的内涵,是合理界定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范围的前提和基础,下面对这四种行为做出类型化解释。
(一)生产、销售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使用的药品
这种行为来源于《药品管理法》第124条第1款第(五)项规定,主要针对药品生产者和药品经营者。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主管全国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一般出于保证药品质量、保障药品的安全、有效、可及,保护公众健康的目的禁止使用某种药品。这类药品经过检验,如果属于假药、劣药,则可能与假药、劣药犯罪构成竞合;如果不构成假药、劣药,则由于关系到公众健康,立法机关仍将这类妨害药品管理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以实现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
(二)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药品或者明知是上述药品而销售
该种行为来源于《药品管理法》第124条第1款第(一)项及第2款规定。具体来说又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形。其一,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药品。药品是特殊商品,药品的生产要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审评审批,才能保障其安全有效性。实践中,药品“黑作坊”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条件、卫生条件简陋、不达标,生产出来的药品存在巨大安全隐患,该项法律规定为打击药品“黑作坊”提供有效依据。[6]其二,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进口药品。依据《药品管理法》第64条规定,药品进口要经过法定报备和批准程序。如果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进口药品,则可能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因此将其纳入刑法规制。其三,明知是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的药品而进行销售。其四,明知是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进口的药品而进行销售。上述两种情形下的“明知”一般来说,表明了行为人故意的心理状态,是对主观要素的表述,也明示了客观要素。[7]行为人在客观上销售的必须是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的药品,同时行为人也明知是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的药品,否则,如果行为人不明知该情况,就不成立本罪。
(三)药品申请注册中提供虚假的证明、数据、资料、样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
该种行为来源于《药品管理法》第24条第2款和第123条的规定。《药品管理法》第123条规定提供虚假的证明、数据、资料、样品或者采取其他手段骗取药品注册等许可的是需要受到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药品管理法》第24条第2款规定:申请药品注册,应当提供真实、充分、可靠的数据、资料和样品,证明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药品注册申请是药品生产、流通、使用之前的阶段,处于药品全生命周期起点的位置,一旦造假进入药品流通环节,就会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需要严厉打击药品申请注册环节造假,把好药品注册关。2017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药品注册申请材料造假的犯罪进行规定,但存在惩罚范围不足、适用罪名不准确的问题。[8]因此,《修(十一)》新增妨害药品管理罪,将数据造假骗取药品批文纳入妨害药品管理罪的处罚范围,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在防控药品风险的应有作用,从源头确保用药安全,完善药品上市前对申请注册环节造假的刑法规制。
(四)编造生产、检验记录
该种行为来源于《药品管理法》第44条和第124条第(六)项,是针对药品生产企业在生产药品过程中对药品所做的各项生产、检验记录。药品生产、检验记录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重要组成,关系到药品的质量和安全,用以保证药品生产全过程持续符合法定要求。生产、检验记录应当完整准确。[9]行为人编造生产、检验记录就是伪造、篡改生产、检验记录,对药品生产、检验进行虚假不实记录,是药品生产过程中的造假行为。编造生产、检验记录往往是为了掩盖药品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不符合法定要求和规范之处,威胁到药品安全,因而需要刑法予以规制。
三、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的边界
如前所述,《刑法》第142条之一妨害药品管理罪与《药品管理法》第123条、第124条相衔接,对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形成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双层制裁体系。《刑法》第142条之一为妨害药品管理行为设定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入罪条件,以划定妨害药品管理行政违法与犯罪的合理边界,体现了构成要件罪刑法定主义功能。[10]“‘足以’是一种危险状态的判断,一般属于可能性的情形。”[11]即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达到可能的危险程度。然而,如何对这种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程度作出准确判断,却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要明确“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含义,必须以妨害药品管理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为指导,厘清妨害药品管理刑法规制的边界。妨害药品管理罪的规范保护目的是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应当是与该规范保护目的具有直接关联性,或者关联性较大的情形。根据上述行为类型,生产、销售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使用的药品,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或者销售的药品,药品申请注册中采取欺骗手段或者编造生产、检验记录生产出的药品,如果这些药品是不能产生相应疗效只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药品,或者根本就没有治疗效果只是属于食品类,不会危害公众的生命健康,那么就可以排除出“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情形。
(一)运用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方法
从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对“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判断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犯罪已有的司法解释。例如,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前的生产、销售假药罪也包含“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求,尽管《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原《刑法》第141条并取消了生产、销售假药罪“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要求,但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详细规定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判断依据。此外,《刑法》第145条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也包含“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件,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21条同样对该罪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做了解释。
上述司法解释都是着眼于行为对象即药品或者医用器材本身的安全性进行解释,换言之,妨害药品管理行为的危险性要通过行为对象即涉案药品的危险性来体现。基于刑事政策一贯性的要求,笔者认为妨害药品管理罪中“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也可以参考上述两罪名已有的司法解释规定,将造成涉案药品不符合安全性要求的情形,认定为“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具体来说,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构成要件行为,达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情形包括:涉案药品含有超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涉案药品缺乏有效成分或者不符合标准,可能贻误诊治;涉案药品超出规定范围标明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可能贻误诊治或者造成严重不良反应。
(二)借助专业的司法鉴定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涉药品犯罪案件专业性很强,在判断“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时需要法定有资质的药品检验机构对药品的安全有效性进行专业鉴定。故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需要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对涉案药品进行司法鉴定,出具专业司法鉴定意见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完成“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司法判断。[12]
四、结语
《修(十一)》贯彻法秩序统一原理,与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相协调,将妨害药品管理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妨害药品管理刑法规制的终极目的是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明确妨害药品管理刑法规制的边界,贯彻刑法的补充性,合理界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以正确适用妨害药品管理罪,实现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