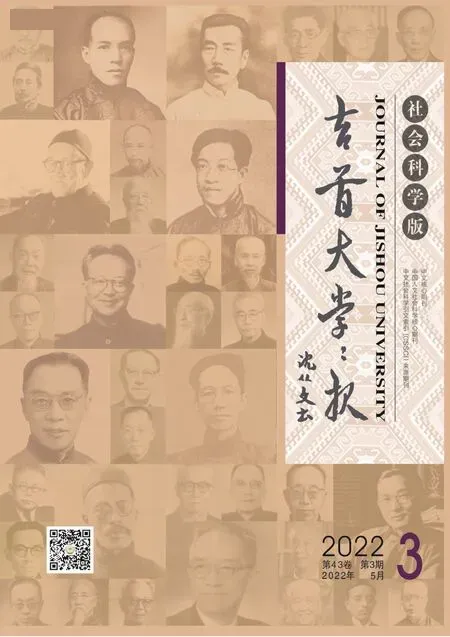舞蹈身体的生成逻辑、表达图式和对美的塑造*
郭昳欧
(中南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舞蹈中的身体先因物质实在呈现,再因精神活动深入人类实践生活,最终在身体主体性实践中落入美学范畴。身体作为舞蹈中的本体,其生成逻辑体现在:身体作为物质基础为主体开拓时空、身体作为精神基础为主体提供灵感、身体作为表达机制为主体赋予个性化调控。应当说,舞蹈艺术首先在生命力的冲动下找到身体的实在,其次在对内知自我、对外知世界的探索中建立身体知觉,同时在映射心灵与超越心灵的实与虚、模仿与演绎中建立适度的身体表达,进而从身体再现、身体隐喻、身体间性、身心关系的表达图式中,形成舞蹈身体的实践考察,最后在对自然的模仿、概念的赋予、他者的互动与自我的探索中,生成舞蹈身体的“四元”美学。
一、舞蹈身体的生成逻辑
(一)舞蹈身体的物质逻辑
生命的冲动为舞蹈身体在物质存在层面提供了支持。在人类历史中,生命的发生问题被宗教神灵思想所垄断。神创造了世界与人,将人放置于世界并安排其行事与命运。随着人类个体的不断进化,人类逐步意识到自身具有特殊且强大的能力,此种能力源于人类主体的生命自觉,也源于自然环境的推波助澜,不仅可以认识世界,而且具备改造世界的能力。有机地看,人类的身与心均通过自然选择演变而来,形成人类高级的处理符号、情感、合作的能力。历史地看,人类基因最初源于非洲稀树草原上的南方古猿,通过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每一个器官的完善化的状态中有诸级存在,每一级对于它的种类都是有利的”[3],使得优质、适宜生存发展的基因不断延续,落后性状基因逐步淘汰。最终,人类逐步演变生成利于直立行走的长腿长脚,垂于体侧帮助劳作与平衡的双臂,用于支撑内脏的空心状骨盆,重心挪至腿部之上等。身体的进化,使人类形态从简至繁,不断优化,为的是延续并促进壮丽、奇特的生命。
宏观上,生命的冲动依靠着身体结构的支撑。从解剖学角度,人类身体构成“三面三轴”(1)人类身体可分为三个基本面,分别为左右纵切的额状面、前后纵切的矢状面与横切的水平面,以及三个基本轴,分别为左右方向的额状轴、前后方向的矢状轴与上下方面的垂直轴。参见:运动解剖编写组编《运动解剖学(第二版)》,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的标准化坐标体系。其中,骨骼支撑全身,起保护、运动等作用。骨又连接关节,增进身体运动的幅度与灵活度。骨骼肌是附着于骨骼之上的肌肉,其收缩或舒张,牵动关节与骨骼,在神经系统调控下支配人体各类运动。上述身体的物质机理为舞蹈身体规范的形成奠定基石。譬如,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国王建立皇家舞蹈院,制定了芭蕾舞者需“双腿外旋”等沿用至今的规则[4]9-10。外旋指芭蕾舞者的踝、膝、髋、胸、肩需五位一体地向身体两侧转开,旨在增加舞者运动时的身体稳定性、幅度与灵活度。另可从芭蕾舞者“三长一小”(臂长、腿长、颈长与头小)的身体形态选材要求看出,四肢修长有助于身体线条的形成与展示,而头小则利于舞者运动时保持平衡[5]。亚洲人身形纤细,以手臂、脖颈、腰部为代表,依此形成源自自身特点的身体形态。譬如,汉代女乐中“长袖拂面”“腰如束素”的身体诉求,在“扬袖拧腰”“绕袖折腰”的身体动律中,强调了袖(手臂的延伸)与腰之间的和谐关系,形成了袅袅长袖、纤纤细腰的女乐身体形态[6]。直至今日,中国专业舞蹈院团依旧将“长臂”“长腰”作为古典舞、汉唐舞选才的标准之一,是“振飞縠以舞长袖,袅细腰以务抑扬”[7]审美思想的延续。
微观上,生命的冲动在人类表情等情绪表达上得以实现。达尔文指出,表情是人类情绪的语言,而高等动物的表情一般从两个原则出发:一是因兴奋神经系统不依赖意志与习惯,形成了独立作用于人类身体的体系[8]59,是原发性表情来源;二是因主体欲求得到满足或参与了有益活动,从而重复多次,形成习惯,往后但凡有此种欲望的产生,即使十分微弱,也会出现条件反射般的表情[8]317,是继发性表情来源。原发性表情将身体视为未被开发过的璞玉,全凭情感调控,而非因专业训练形成的惯性痕迹。例如,或当舞者听到慷慨激昂的乐曲时,当舞者饰演命运悲惨的角色时,常常情绪激动,大汗淋漓,甚至掩面哭泣,这是表演的状态激发了其自身的兴奋神经系统,从而表现出源自内在的情绪表达。而继发性表情的形成,因受训的舞蹈身体在规则与限定中生长,故衍生了一系列条件反射的表情情绪。例如,中国古典舞继承传统戏曲之精髓,沿用了“手眼身法步”的典型特征,讲究“眼随手动”的眼神动态,旨在形成“手与眼”默契配合的表演形态。
可以肯定的是,进化的身体,成就了生命的发生;宏观的身体,造就了生命的可能;微观的身体实现了生命的可感。至此,生命的冲动立于舞蹈身体之上,形成实现舞蹈身体内外感知、肆意表达的物质逻辑。
(二)舞蹈身体的精神逻辑
1.身体知觉:“内省自我”与“外通世界”
谈及知觉,则离不开对感觉的阐述。感觉是“我接受影响的方式,我自身状况的感受”[9]23,即一种感性的知觉。温度、湿度、颜色、饥饱、轻重、快慢、大小等,可对人形成较直接的感觉,而时间、空间、情绪等,则对人形成较间接的感觉。感觉是知觉的初步状态,知觉的形成除感觉外,还需通过“联想”和“回忆的投射”进行探究。“联想”依靠人类情感的迁移,产生一种人类共通的感觉理念,运用此种共感(Sensus Communis),使自身判断仿佛凭借全部人类理性[10]118。“回忆的投射”则通过人类过去积累的经验,从中提取对当下有意义的感觉进行运用。应当说,知觉是直接且间接的感觉,在移情作用下,通过主体掌握的经验性知识,产生一种联合性感觉。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一种以胃黏膜固有腺体萎缩伴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为病理特征的临床疾病[1]。慢性萎缩性胃炎发病与Hp感染、细胞因子作用、胆汁反流、药物、饮食等因素相关[2]。同时,慢性萎缩性胃炎是引发胃癌的重要环节,对人类生命健康有着极大的威胁。在慢性萎缩性胃炎治疗中,现今尚无完善的方案。替普瑞酮是一种胃黏膜保护剂,属于萜烯类衍生物,除了可以保护黏膜以外,还可以发挥抗炎、促进血流、修复黏膜等功效[3]。本文对2016年5月—2018年4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108例幽门螺杆菌(Hp)阴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进行分析,研究替普瑞酮治疗的临床效果。
身体知觉产生于神经系统,其基本单位是神经元,以突触方式相互连接,凭借神经纤维遍布全身,以反射方式完成基本活动[11]。身体与知觉之间的关系可分为间接性、辅助性与一体性。间接性在于,“我的身体不知觉,而是好像被装置在通过它才形成的知觉的周围”[12]。身体不直接生产知觉,而是形成一个仿佛带有知觉传感器的管道。通过此管道,形成了知觉,传递到人的接收器中。辅助性在于,身体需要且一直需要心灵作为辅助。若心灵不拥有任何表达手段,就会衰退、瓦解,若身体丧失了意义,就处于一堆物理-化学状态中,身体和心灵不会绝对分开,在于意义的安置,使身心在此栖息、呈现和存在[13]306。一体性在于,身体各个部位的知觉并非彼此分割,正如“这种表达和这种连结在我身上是一次完成的。”[9]198当手指触碰到丝绸,指尖触觉神经元通过对丝绸质感的捕捉,依靠神经纤维传达至大脑,以反射的方式分泌愉悦情绪,最终反馈在表情、言语上。一言以蔽之,身体知觉以身体作为感觉中介,依据身心始终联合、贯通一体等特征,从内、外两方面表达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内省自我”的身体知觉,生成于对激情与行为的省思。激情由刺激人类的感官对象所引发,包括惊奇、爱、恨、渴望、高兴和悲伤等[14]39-45。激情不仅促发人类情绪的起伏,更深层次而言,是对身体器官内在运动的改变,从而引发情绪改变。当产生恨的激情时,人的脉搏跳动变得不均、微弱且快速,人会不自觉感到寒意,产生不舒服的热量,刺激人的胸膛;当产生爱的激情时,大量血液涌入心脏,激发起更强劲的热量;当产生渴望的激情时,对心脏的刺激比别的激情要更加猛烈,因此感官将变得前所未有地敏锐,身体所有部分都活跃起来了[14]63-64。激情的省思运用身体知觉的间接属性,突出在身体动作质感之上。例如,表现愤怒时,身体肌肉呈现紧缩状,动作断点式,用僵硬的向下势态表达由于热量不足、脉搏不均所产生的身体不悦能量;表现喜悦时,身体内血液迸发,肌肉呈现舒展态势,用流畅、激烈、向上的动作表现身体各部分的活跃。行为的省思在于传递身体知觉的间接属性,当看到来自他者的身体行为时,对他者的激情判断将传达到自身身体的知觉当中。例如,当观赏到神情愤怒的雕塑时,观者通过雕塑紧张的肌肉感受到凝固的血液,便在自身身体中形成了愤怒激情的感受;当看到造型圆润的雕塑时,观者又会因感受到气血通畅而身心愉悦。身体的知觉在内在激情与行为的反思中,以贯通身体场域传递到人类心灵的方式,生成内部知觉。
“外通世界”的身体知觉生成,体现在对外部空间与时间的联通,此种联通需开启身体的“辅助性”,在心的协作下,以身心联合认识外部世界。外部空间指除人体之外的一切外部环境,包括与道具之间、与舞伴之间、与其他群舞成员之间形成的空间关系。例如,一舞者以椅子作为道具,舞者身体之于椅子之上或于椅子之下,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关系,贴近椅子与远离椅子形成对立的空间关系。再如,双人舞中,二人身体在空间中形成的托举关系、牵拉式的对抗关系、各占半部空间的分离关系,均代表身体在空间中产生的知觉意识。外部时间则指由外部世界制造出的包含节律、韵律的震荡。自然界存在诸多拥有节奏的事物,例如微风的缓慢、疾风的迅猛、海浪的平静、雷电的激烈等。外部时间先在心灵中产生对时间的体会,再由身体予以表现,对身体质感起影响作用。例如,微风般的肢体体现绵延、流动的质感,疾雨般的肢体表现碎片、闪顿的质感。外部时间以介入身体节奏的方式,影响并改变身体行为,以促进身体外部的知觉。
2.身体表现:“映射心灵”与“超越心灵”
“表现”曾指艺术家是否精准地临摹其对某主题的判断。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为艺术家个性表现提供空间,艺术不再是世界、社会秩序、赞美他人的体现,而是更注重艺术家个人情感的表现[15]。“在舞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一定的目的。哪怕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也要有特定的目的,而不是单坐在那里给观众看。”[16]34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指出,演员在台上的任何行径都需目的指引,此目的即情感的推动力。例如,人在见面寒暄时会向对方伸手问好,是表现友好的情感驱动了动作的生成;在见到他者跌倒时会向对方伸出援助之手,是表现同情的情感驱动了动作的发生。无论是外部的动作还是内部动作,哪怕是身体的静止,也是由于内心强烈的情感所引起的[16]35。在情感的动机下,身体表现可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对心灵生活直白地映射;二是对心灵生活映射后的超越与升华。
对心灵生活的直接映射,从戏剧的缄默化与动物的拟人化两种典型中体现。芭蕾历史悠长,其根源以古希腊舞蹈、古罗马拟剧、意大利职业戏剧、中世纪杂耍者为雏形[4]1。上述舞蹈形式皆具有通过戏剧手法,依靠身体表现,形成缄默化心灵表达的特点。缄默化戏剧动作在古希腊悲剧与戏剧表演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利用身体做出象征意义的姿态,并称之为符号性动作,融入生活化的手势、行为、动作,有助于释放悲剧的真实效应与喜剧的滑稽效果[17]。缄默化身体表达将心灵的戏剧式愿景予以展现,而拟人化身体则还原了心灵对自然生灵的本真。据知,人类共有22种来自动物模仿的舞蹈(2)在原始部落中,人类是因模仿动物才学会跳舞的,例如模仿熊、鹿、鹰、火鸡等,不仅模仿动物的每一个动作,还模仿其足迹。参见:库尔特·萨科斯《世界舞蹈史》,郭明达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例如安达曼人善跳龟舞,模仿龟游泳的动作;澳大利亚北部河域女舞者,在沙地留下母龟产卵路线的舞蹈运动轨迹;新爱尔兰的犀雀舞模仿犀雀审慎警惕的捕食动作。[18]原始人类对世界具有诸多困惑,便将对大自然的崇拜与敬畏转嫁于其他生灵之上,将动物形态拟人化处理,祈求得到狩猎、繁殖等生存安定,是心灵图画的全景展示。
身体表现之于心灵映射之后的超越与升华,从“寄情于形”与“向往自由”两方面体现。古人体悟“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形成对寒来暑往、日月星辰变化的认识,产生对自然的关注与敬畏。中国古典舞中“圆”的意象,是人类将天道、地道、人道的情感,寄托于形体之上的体现,形成古典舞“阴阳相合,圆融归一”的基本追求。另从古典舞的“拧、倾、圆、曲”的体态可见,身体“拧”的体态,实则“意”在“圆”中;身体“倾”的体态,实则“迹”行“圆”上;身体“曲”的体现,实则“象”从“圆”生。总而言之,中国传统舞蹈中身体“圆”之形态,是古代人类将天地和谐、人尽圆满寄托于身体形态的表现。“寄情于形”是对心灵的超越,而“向往自由”则表现出对心灵的升华,以即兴舞蹈为一种典型。即兴舞蹈,指舞蹈主体跟随主观意图,不经预先排演,从心灵深处激发出身体表现的欲望,其类型大致可分为音乐即兴、主题即兴和环境即兴。音乐即兴要求主体在规定音乐下,运用身体实现音乐的可视化呈现;主题即兴则规定主题范围,主体用身体表现主题的相关表演;环境即兴则设立环境范围,主体用身体表现空间中的异同。即兴舞蹈常用于激发舞者的肢体能动性,在西方现代舞训练中运用广泛,其目的在于促进舞蹈主体深度探索心灵与身体的连接,找寻多种身体表现方式,打破身体固态表现,实现对身体的自由表达与心灵的超越。
灵魂是与身体的所有部分都相连在一起的,身体就是一个整体[14]20。在内部激情与行为中,身体作为知觉的通道,体会到知觉的存在;在外部空间与时间中,身体作为心灵的反映,尝试与知觉共频率。身体的知觉在内省与外通中,达到联合性、一体化的呈现,再经身体表现对心灵的映射与超越,构成舞蹈身体的精神逻辑。
二、舞蹈身体的表达图式
人类与其他生物体的区别在于,除饮食等生存必要外,还需拥有更高尚的祈求,即除去因环境限制的“有所为而为”,还需追求主宰心灵的“无所为而为”,这便体现了美的价值。舞蹈身体形成于物质逻辑与精神逻辑的共同作用力,而其根本在于,通过身体的表达,生成“娱”人效果。所以,帮助主体形成美感体验,是舞蹈身体表达的本质所在。图式(schema),指“一种内化的或简化的心理组织或结构,是认识结构的单元”[19],强调认识活动是一个内部结构不断组织与再组织的过程,经过不同阶段事物的同化与顺应,实现稳定图式的结构性表达。对舞蹈身体表达的认识过程亦是如此,其中涉及自身与内部自我、外部世界以及历史文化生活等复杂因素的糅合,又在上述要素中生成普遍的图式表达。实际上,舞蹈身体的表达图式无外乎是对身体美的捕捉、甄别与品味。而美的生成过程是人生境遇的缩影,与审美主体的境况与欲求,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如尼采指出,精神的变形是由精神变成骆驼,骆驼变成狮子,最后由狮子变成赤婴的过程。其中,“精神”象征对真理的追求,需大量负重;“骆驼”象征强壮有力、迎难而上,以负重的精神走进自己的沙漠;而“狮子”象征着忍辱负重后对权力与欲望的征服心理;可是这些都不足够创新,便用赤婴代表一个原始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1]29-32。简而概之,尼采勾勒了一个追求真理、成就“超人”的轨迹,从被动接受,到辩证扬弃,再到自立创新,甚至于推翻自我。舞蹈身体表达图式的形成亦是如此,从运用身体对事物进行模仿的身体再现,到运用身体表现抽象象征的身体隐喻,再到探究主体间关系的身体间性,最后挖掘身心之间勾连关系。
(一)身体再现
从古希腊戏剧哲学起,对现实中表面现象的模拟受到艺术家的重视。“X是一个艺术品,仅当它是一个模仿品”[20]22,艺术品是对某物的模仿,否则将不属于艺术品。模仿是再现概念的古典用法,旨在关注艺术作品与现实世界间学问的关系。模仿论还有另一个名字——表象论,当某一艺术作品表象(Representational)了某一对象(Object)时,表象论得以实现。表象论的主张者认为,凡是艺术作品都具有表象性属性,因艺术作品实则是一种语言,且该语言应具有认识功能[21]15。艺术作品首先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连接,其次此种连接建立在共同的认知之上,以拓宽认知、加深认知为导向。所以,艺术作品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创作主体有计划地对某种客观对象进行发自内心的呈现,不同艺术门类拥有不同呈现方式,如绘画是对某物的具象,文学作品是对某故事情节的表现,即便是音乐舞蹈等非具象艺术,也是对人类情感或某历史性事件的反映[21]16。无论是再现、表象还是模仿,其意涵均为对客观世界实存之物的再次显现,人类不仅从此种方式中获得最初的知识,且从对事物观察、提取、模仿、演绎过程中取得了快感[22]47。身体是最令人信服的描述,无论是体验烦躁、愤怒,还是忘乎自我地投入,身体作为再现的工具,映射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诗人还应尽可能地将剧情付诸动作”[22]125的主张。
(二)身体隐喻
身体再现是身体表现的原始状态,而身体隐喻是身体表现的例示与象征手法,从身体的指涉,到身体的拥有,最后实现身体的隐喻。“X表现Y,当且仅当(1)X指涉Y,(2)X拥有Y,(3)在方式上是隐喻的。”[20]102用X实现对Y的隐喻,首先需在X中找到Y的映射,其次使X中拥有Y的痕迹,最后X与Y间的隐喻方可形成。例如,舞者运用身体隐喻火,因火具有热烈、沸腾的属性,故舞者身体呈现张扬四射、活力跳跃的姿态;舞者运用身体隐喻自由,身体呈现肆意跑动、灵活动感的自由状态下的姿态。隐喻相较于比喻而言,具有间接、模糊等特性,而身体表达通常不具备清晰与明确属性,故隐喻更适用于身体表达。
(三)身体间性
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身体”一方面与“躯体”相对应,一方面又与“心灵”相对应,构成了“躯体”与“心灵”的结合点,是自我身体与他者身体的感知交汇。当“自我”身体与“他者”身体互知时,异己躯体与异己意识联结在一起,构成了异己主体的灵肉统一,他者的身体便这样被定义出来[23]297。身体间性在于以“自我”身体感知“他者”身体,并在“他者”身体之上以“自我”身体的“同一性”,寻求自我意象的异己化延伸。梅洛庞蒂认为,身体间性是研究主体之间存在意义的概念,也就是当“他者”感知到他身体中的他的意向,以及和他身体在一起的我的身体,并由此感知他的身体中我的意向。同理,当我的目光落到有机生命体上,该身体周围的物体便利己地赋予新的意义,在此情况下,“自我”的世界不仅属于“自我”,也将会呈现给“他者”,体现于他者身体上的另一种行为[9]443-445。通俗而言,不同有机主体之间拥有相互关联的身体,或结构的相似、或知觉的相通,如“自我”的身体安放“自我”的意义,隐含“自我”的心灵世界,是观照“他者”身体的显现,所以,“自我”身体之中蕴含着“他者”的意义与心灵世界,包含着对“他者”身体的体会。正是这种身体间性,让人类成为世界意义的共同承载者,在交互主体的共同体之上,相互交流、合作、倾听,以实现胡塞尔看来最高意义的共同体,即“爱的共同体”[23]201。
(四)身心关系
身与心从来都是辩证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身体是心灵的对象,确立了心灵活动轨迹的外在显现。心灵又是身体的对象,唤醒了基于身体的生命表现。二者中对某一种的认识缺失,都将导致自我意识的残缺。真正的人的身体经由身体机体的整合,达到一种比生命层次更高的层次,当身体行为借助心灵机制获得理解时,身体已作用于心灵[13]297。简言之,生命从未纯粹地由肉身或心灵单独组成,相反,当身体行为可以用心灵机制来理解、解释、接纳时,身体和心灵已经融为一体。“在我们抽象地把身体看作是物质的一部分时,心灵与身体的各种关系是晦暗不明的,当我们把身体看作是一种辩证法的承载者时,这一关系得到了澄清”[13]299。这代表当用多视域角度看待身体存有时,身体就形成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有机的肉身不再庸俗于“躯”的现世,而在于“身”之意义的承载。所以,身体的表达不仅基于肉体的体会,还需融入心灵机制,实现身心共同作用下的合并效应。
三、舞蹈身体对美的塑造
通过舞蹈身体的四种表达图式,从舞蹈形象、动作形式、他者关系和自我意识,形成舞蹈身体对美的塑造,分别在肢体美、概念美、交互美与状态美的“四元”美学中体现。
(一)舞蹈形象确立肢体美
身体再现的行径创造舞蹈形象,从而确立舞蹈肢体美。身体再现从类型上可分具体再现与抽象再现,前者偏向哑剧式、简单直接地模仿,后者则偏向对单一元素析出后间接地演绎。18世纪,强调模仿属性的剧场舞蹈逐步兴盛,为“情节芭蕾”(Ballet d’action)统治19世纪的舞台奠定了基础[20]25。情节芭蕾是身体具体再现的途径,将舞蹈视为无言的交流对话,“一切都在说话,一举手一投足皆成文章,每一个Attitude(法语,为芭蕾舞姿的术语表达)都描述一种情景,每一手臂动作都揭示出一种内心活动,每一目光流盼都宣示一种新的感情。”[24]51“情节芭蕾”的主张者乔治·诺维尔(Jean-Georges Noverre,1727—1810)认为,“任何舞剧题材的处理,都必须包括三部分:陈述、纽结、解结”[24]9,揭示了芭蕾舞剧的创作离不开设立矛盾、交代矛盾,以及打开矛盾的情节过程。舞剧《关不住的女儿》(3)舞剧《关不住的女儿》(又名:《无言的谨慎》)从动作语汇运用上,吸取哑剧式将生活动作过渡为舞台动作的手法,剧中多次运用日常手势与动作,如打哈欠、左顾右盼、托腮等待、四处找寻、彼身躲藏等,并广泛运用日常用品为道具,如长椅、缎带、奶油桶、手杖、镰刀、马车、纺车、花束、草帽等。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磨坊主儿子笨拙、夸张幅度、同手同脚的喜剧动作,凸显人物的生动体态;在情节交代过程中,穿插青年男女丰收割麦子情景,映射了乡村生活热闹场景,凸显人文和谐氛围。《关不住的女儿》作为现实题材芭蕾舞剧的典型代表,将司空见惯的日常场景塑造于舞台之上,使观者对情节展开与人物发展一目了然,以舞者的动作形成了身体的具体再现,实现了诺维尔所形容的理想舞蹈图景:“熙熙攘攘的街道、专供散步的林荫路、露天的咖啡馆、乡村娱乐活动和劳动、村民的婚礼、打猎、捕鱼、收割、收葡萄、浇花、摘花、把花送给心爱的牧羊姑娘时的田园风姿、掏鸟窝、吹牧笛,凡此种种,都向我们呈现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图景,十分别致、色调独特的图景。”参见:若望-乔治·诺维尔《舞蹈和舞剧书信集》,管震湖,李胥森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是“情节芭蕾”的代表作,从舞台图景上一反往日神话惯例式布排,反映法国乡村生活的真实场景,为身体具体再现提供了发展场域。舞者的身体形象在现实主义场景中得到充分发挥,体现出了身体在朴素生活中的真实质感,形成身体的世俗美。
19世纪,浪漫主义者主张艺术作品应受个人情感的控制,以自我表达为主线。浪漫主义的芭蕾作品在身体的抽象再现中,以质感和力度,获取舞蹈形象超感官的审美体验,体现了身体的崇高美。以芭蕾舞剧《仙女》与《天鹅湖》为代表。《仙女》剧中舞者身穿过膝白色蓬松纱裙,肩颈与双臂裸露,背后装饰轻盈透明的翅膀,开创了“白裙芭蕾”的惯例。“仙女”在动作表现上,上肢保持优雅灵巧的手臂动作,脚下通过Suivi(法语,为芭蕾舞脚步动作的术语表达)足尖碎步向旁移动,体现仙女安逸灵动的形象质感。舞剧《天鹅湖》则从服饰上改变往日长纱裙,以及腰平开裙代替,裙摆质地丰厚,层次间显现出蓬松质感,犹如湖面上天鹅漂浮的羽毛。从质感上,对天鹅身体质感的再现,体现在舞者四肢延展且轻盈的长线条动作上。剧中多处群舞的集体静态姿态,从直立的主力腿、修长后掖的动力腿、上下延伸的双臂,以及低垂的头部,表现了湖面上众天鹅闲适休憩的景象。从力度上,对天鹅身体节奏的力度再现,体现在舞者腿部及跳跃动作,一系列细碎、快速、伶俐的足部动作,从节奏切分与力度分布上,再现了天鹅灵活的足部划水动作(4)在《天鹅湖》中的《四小天鹅》片段,芭蕾舞者脚步动作由左右脚轮换Cou-de-Pied跳跃(法语,芭蕾舞中术语表达,意为动力脚位于主力脚脚踝处),接快速Tombe pas-de-bourree连接动作(法语,芭蕾舞中术语表达,Tombe意为倾倒,指人体重心由一条腿转到另外一条腿,pas-de-bourree为一个使用频繁的脚下连接动作),然后Entrechat Trois换脚打击跳跃(法语,芭蕾舞中术语表达,意为从五位脚位起跳,在空中形成三次打击后落回原处),后接 Passé(法语,芭蕾舞中术语表达,意为经过,指动力腿屈膝将脚尖靠至主力腿膝关节处),将重心迅速挪移至单脚。。康德提出心灵有一种超越感官尺度的能力,是崇高美的形成条件[10]78,无论是仙女或是天鹅的舞蹈形象,通过对其质感与力度进行再现表达,给予观者实存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感官体验,形成了超然脱俗的身体崇高美。
(二)动作形式赋予概念美
舞蹈身体通过对“权力”与“情爱”的隐喻,产生了符合概念美的动作形式。权力是对一切主体掌控的可能,而主体即个体,又以肉身为物质承载单位,所有权力的展现都体现在对人类身体的掌控中。“操练是人们把任务强加给肉体的技术”[25],对身体的规训与操演形成统治阶级对平民的治理。将个体身体放置于广大身体当中,消磨个体的特殊感,使其融入广大身体中不显个性,运用广大身体的一致性、协调性,推动个体身体向广大身体靠拢。操练是身体实现对权力隐喻的一种手段,在此基础上,权力向身体下发喻旨,身体形成权力的喻体,身体实现对权力的隐喻。《吕氏春秋·仲夏纪·奢乐篇》载:“夏桀、殷纣作为侈乐,……以巨为美,以众为观。”[26]“巨”则优、“众”则强的身体准则,体现在舞人队伍的身体数量上,可见“巨”与“众”是封建社会形成并沿用的身体审美准则。如在《旧唐书·音乐志》中:宣扬唐太宗以武功定天下的《破阵乐》,由披甲持戟的一百二十个舞人组成;《大定乐》有舞人一百四十人;唐高宗的《上元乐》有舞人一百八十人;武则天的《圣寿乐》有舞人一百四十人(5)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制歌辞。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兴。”“《大定乐》,出自《破阵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彩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纮同轨乐’,以象平辽东而边隅大定也。《上元乐》,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人。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故曰‘上元’。《圣寿乐》,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字。”参见:刘旭昫等撰《旧唐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9-670页。。宋代宫廷队舞,由“小儿队”七十二人与“女弟子队”一百五十三人组成。清朝“佾舞”对身体操演的规模达到巅峰,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知,坛庙祭祀的乐舞生共有五百七十名,其中乐生一百八十名,文舞生一百七十名,武舞生一百五十名,执事乐舞生九十名(6)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二十八记载:“清袭明制,顺治元年(1644)定太常寺神乐观乐舞生五百七十名,内分:乐声一百八十名,文舞生一百七十名,武舞生一百五十名,执事乐舞生九十名,用于坛庙祭祀。”参见:冯双白,茅慧《中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康德指出,人们惯于将绝对大的东西看作是崇高的[10]76,身体对“权力”的隐喻体现在由广大身体个体组成的巨型阵仗规模的宏观动作形式上,呈现出“巨”的概念美。而对“情爱”的隐喻,则源自个体身体线条与姿态的微观动作形式,生成了“欲”的概念美。
鲍德里亚指出:“女性及女性身体被赋予了作为美丽、性欲、指导性自恋的优先载体。”[27]女性身体形象具有头至肩、肩至腰、腰至髋弧度的“三道弯”曲线,从视觉上突出流畅的线条感,加之女性身体较于男性而言动态细腻,更具备用身体叙事的客观条件。《管子·轻重甲篇》中的“女乐三万人”[28],是桀对女性身体形象之感官刺激的追求;商纣对女乐的沉迷,从《史记·殷本纪》中“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29]中可见一斑。另从《西京杂记》记载的汉高祖宠姬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可见“长袖细腰”“翘袖折腰”是古代女性舞蹈形象的典型代表。“长袖”形成身体的延伸部分,使身体形象更具有线条张力,袖在空中经过舞人手臂力量的控制,形成弧线造型,为身体形象增添线条表现力。“腰”的姿态在“舞袖”的过程中通常有如下三种形式:一是向侧方或后方下腰九十度以上,形成“折腰”;二是通过塌腰撅臀,呈现出腰与髋部夹角曲线;三是通过向侧方腆跨倾腰,突出整体身形曲线,故“腰”是形成中国传统舞蹈中“性审美”的关键所在。事实上,传统乐舞本质是对观赏者的供奉与谄媚,满足其对“欲”的概念美,这在女性身体舞姿线条上予以生动呈现。
(三)他者关系构建交互美
舞蹈审美产生于不同主体间身体交互的知觉集合,对于主体的“我”而言,“他者”可以是共舞的舞伴,可以是群体舞中其他舞者,也可以是借用“我”身体以创作的编导。上述三种“他者”关系构成了舞蹈中身体间性的发生土壤,各个“他者”关系间的主体,在相互共感彼此的肢体质感、聆听彼此的肢体节奏、反馈彼此的肢体语言中,形成纯粹自我与经验自我汇合的交互美。双人舞中的身体间性体现在对现实世界中人与人关系的模仿,其中身体动作以“托举”与“齐舞”代表。“托举”指一名舞者运用自身力量,将另外一名舞者托举至空中,形成静态或动态舞姿过程。“托举”动作常发生于男女双人舞中,亦常出现于剧情所需的同性双人舞中。“托举”过程首先由一方舞者在另一方舞者身体之上找到便于借力的支点,然后“被托举”方经重心转移,将身体重量挪移至“托举”方处,最后“托举”方发掘力量最优路径,形成“被托举”方在空中舞姿的动作状态。“托举”动作的完成需要两方舞者对彼此身体进行了解与探索,在反复磨合中达成“合二为一”的默契程度。“齐舞”讲究多个舞蹈主体间的协调一致,所以更需要舞者之间对彼此身体的倾听。因舞蹈主体间纯粹自我的差异,所以要在主体的差异间寻找内在的相似,以经验自我感知他者的身体,体现“齐舞”的质感与节奏。若双人舞是“一对一”,群舞则体现在“一对多”,即自我身体是群体性身体中的一元,强调以纯粹自我融入经验自我,并无痕地融合于他者身体之中。例如,以色列巴切瓦舞团(Batsheva Dance Company)的经典群舞片段《十舞》(Decadance)中,舞者环坐于舞台一周,以“多米诺”式依次从椅子上弹起并倒地。此过程不仅要求舞者对“自我”身体的质感与节奏进行集中控制,且需对“他者”身体静观并延续,将“自我”身体置于“他者”环境之中,磨去异质化特点,最终形成流畅的整体舞台景观。
在舞者与其编导的身体间性中,编导角色形成的是纯粹自我与经验自我的汇合点。作为编导,首先运用纯粹自我,构成舞蹈作品的宏观图景,然后细化成特定舞者擅长的身体表现形式。在以色列巴切瓦舞团编导欧汉·纳哈林(Ohad Naharin)的纪录片《嘎嘎先生》(《Mr. Gaga》)中,一舞者在其指引下,通过即兴舞蹈寻求动作素材,当他看到舞者的一处倒地动作时,让其停下,原因为该舞者的身体过度控制,致其倒地动作僵硬又缓慢,随后经反复磨合,在数次练习后,舞者的身体质感达到了欧汉的要求。由此可见,编导将自我对舞蹈的能动性施加至舞者身体上,此过程不仅需要遵循自我的原初想法,并照顾观者的感受,还需依舞者身体经验而变换方式,在多重他者关系之中,建立纯粹自我与经验自我的交互中枢,以获得舞蹈主体的接纳与正向身体反馈,形成身体的交互美。
(四)自我意识投射状态美
自我意识是成就完整人的途径,舞蹈中的自我意识分“身”与“心”两方面。舞蹈中“身”的意识源自舞蹈训练中身体部位的训练,分微观意义上的局部训练与宏观意义上的整体训练(7)微观训练指舞蹈基本功的训练,常见于古典舞、芭蕾基础训练中的把杆训练与中间训练,前者多为单独身体部分的细节训练,例如脚部的勾绷、膝部的屈伸等;后者多为整体平衡综合的舞姿训练,例如跳、转、翻组合等。宏观训练指对舞蹈身体风格塑造性的把控,以中国民族民间风格舞蹈为典型,例如藏族舞蹈形态的“曲背哈腰颤膝”的风格特征、蒙古族舞蹈“立腰挺背”的风格特征、东北秧歌“既哏又俏,既稳又浪”的风格特征,均是对身体整体表现力要求的体现。。而舞蹈中“心”的意识则多数源自对角色刻画时的感知与理解。总而言之,舞蹈演绎中“身”与“心”的关系始终密切相关,“身”“心”合二为一,故生成“里应外合、里随外感、外随里动”的状态美。从舞蹈动作而言,身体内在力量的运行依靠心灵意念的指引,首先由意识引导,到达身体的规范层面,然后运用意识,实现动作质感的细致程度(8)例如,芭蕾训练中始终要求舞者将髋关节放正,避免向前或后的倾斜。此时的训练应从舞蹈主体的意念入手,感觉骨盆的形状如一碗装满水的容器。若前后倾斜便会导致水洒出,保持容器的平稳,并将此观念延续到动作中去。芭蕾训练中常提到“双腿外旋”,该动作的起始是引导舞者在进行Plié(法语,为芭蕾中的一个术语表达,意为蹲、屈膝)动作时,双侧膝盖向身体侧方转开,舞蹈主体的意念应是双膝向双耳方面靠近,以自身器官的关联性引导身体的潜在力量与质感。再譬如,当舞者完成如小踢腿与大踢腿等需腿部爆发力的动作时,意念要赋予动力腿如同射箭一般的力量,以脚尖为末梢延伸至最远处;做跳跃动作时,舞者在空中形成的舞姿要在半空中“挂住”片刻,以留给摄影师拍照的瞬间。。加入意识参与的舞蹈活动,舞者身体展现出主动、兴奋的状态,不仅明确了身体力量的出发点,开发了易被忽视的深层肌肉群,还唤醒了身体未被开发的休眠技能。意识形成于心,利用心与脑的神经调动,控制身体肌肉与关节,此时的身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意识共为一体,增强了身体向外的释放与汇集的力量,使身体饱含张力与表现力。另外,舞蹈中的呼吸也是自我意识外化于形的一种体现。呼吸是有机生物维持生命存在的共同功能,为生命的更迭提供养分。吸气伴随着肺部系统的扩张,随之引起身体向上的牵引力量;而呼气伴随肺部系统的收缩,随之引起身体向下释放力量。生物性的呼吸在艺术表现中通常将转化成艺术性的呼吸,即呼吸活动对艺术行为的影响,在舞蹈活动中表现尤为明显。舞蹈主体的动作过程始终伴随着呼吸(9)譬如,当身体处于屈膝、下蹲、肘部下沉、点头等向下方位运动的行进状态时,通常伴随着呼气动作,因这时的身体正处于释放能量的状态,呼气有助于身体对外界的倾泻之感;当身体处于伸展、上提、上扬式动作形态时,通常伴随着吸气动作,因这时的身体正处于积蓄能量的状态,吸气有助于身体向外界收集能量;当身体处于定点舞姿亮相、或是大型跳跃动作的空中舞姿时,舞姿形成前的过程伴随着身体的吸气,因吸气动作为身体提供向上的“挺拔”之力,而舞姿亮相的一瞬,则伴随吸气之后的即停,短暂的呼吸断点是上一个舞姿动作的顶点与终点,也是开启下一个动作短句的起始点。,且随着主体活动幅度和力度的增大,呼吸也变得频繁与急促。呼与吸的张力引导着主体舞蹈动作的起承转合,有助于舞蹈身体在自然反馈之中生成“形神合一”的状态,形成自我意识投射于身体与心灵的方式,强调了身体具有的浑然天成的状态美。
结语
“‘艺术化生存’甚至将整个人生放到艺术视角下考量,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和事绝没有艺术含量。”[30]人寄居于身体的躯壳之中,身体为主体提供无限可能,或理性地活着,追随身体规则的本真;或感性地活着,打破身体规则的限制。在这有迹可循与无迹可循的辩证张力当中,形成主体在身体中诗意栖居的状态。本文从舞蹈中身体的生成逻辑、表达图式以及对美的塑造三个维度切入,整体上是对舞蹈身体良性生成过程的总体考察与呈现。舞蹈中的身体是身体哲学中具有共性表达的特殊形式:一方面,要遵循客观生成逻辑,尊重物质身体对生命冲动的真实显现,聆听精神层面的身体知觉与表现;另一方面,注重发掘源自主体能动性的身体表达图式以及对美的塑造。为此,要引导舞蹈中的身体向正确、健康的途径发展,将外部身体形式与内部精神内容相结合,以艺术化身体促进和谐人文生态的构建,旨在升华品格、净化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