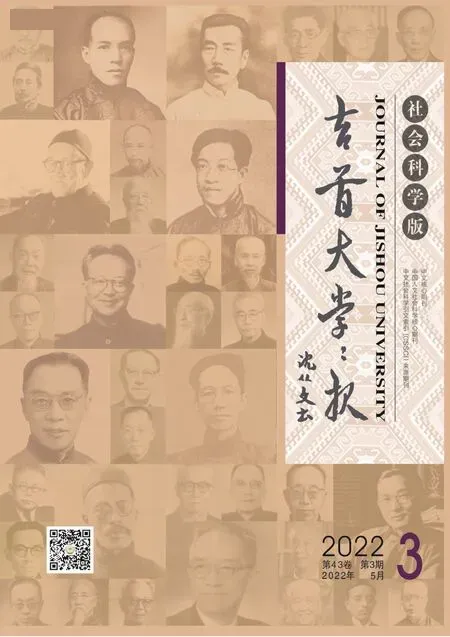清代苗疆书院与“大一统”的国家建构逻辑*
暨爱民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传统中国,儒家思想架构、伦理政治原则以及华夏历史文化观念支撑了“大一统”国家的认同体系,实现自“中心”到“边缘”对国家政治结构与统治形式的赞同和服从。或谓于传统中国“大一统”国家建构,文化建设乃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方略。一般意义上,作为传统中国具体且典型的文化形式,书院集中反映了传统社会代代相承却并不复杂的文化理想。然于古代中国边疆或民族地区,从儒家思想传播到一体的文化网络结构,从共同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型塑到各族民众的认同导向与社会整合,书院的文化致思与实际运作却在区域之国家进程中更趋于明确的政治建构,凸显出“大一统”国家的思想逻辑。
观乎当下学界之书院研究,或谓成果丰硕,但多为“内地”书院历史变迁、文化功能和社会影响的阐发,而对边疆或民族地区书院情状、内在的政治指向及于“大一统”国家建构的价值意义却鲜有论及。本文拟从古代中国“中心”与“边缘”交融互动的历史视角,考察清代被视为“边缘”之地的湘西苗疆书院发展,解读苗疆之国家化具体历史情境中书院建设与文教开展的政治意义,以期为传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提供历史文化要素的支持。
一、清初苗疆书院渐兴及其局限
位于湘、黔、川交界之处的湘西苗疆,自古为苗、土、汉等多民族聚居地,社会、文化结构与地缘、族群关系向来较为复杂,历来被视作“边缘”“化外”,文教长期落后。至明初,随着国家力量深入、学校渐兴才稍有改观。有载泸溪县学,自元至正中期达鲁花赤创建,到明洪武、成化、嘉靖、万历年间先后得以重建或扩建[1];凤凰在明以前则无学校,至明万历元年始设五寨司学,“附辰州府考试”[1]。弘治十六年(1503年)朝廷明确要求,“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若“不入学者”则“不准承袭”,是以湘西土司子弟皆往附近州县求学[2]7997。在“边缘”之地的国家进程意义上,此举明确表达了中央王朝之边地社会治理方式及建构国家认同、服从国家体系的政治运思。然彼时湘西这一僻远之地,文教多为地方社会上层独享,普通民、苗子弟自难入学受教,“文治”受限,苗疆大部仍为无管“化外”,国家进程缓慢。
至清初“敷治”,倡“文教为先”[3]3114。随湖南各地官学兴起,苗疆亦有反应。以凤凰、乾州、永绥三厅为例,顺治十六年(1659年),凤凰照明例设“司学”,“文武各入附学生八名,廪膳生六名,增广生六名”。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改属麻阳训导“兼摄”[1]。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时,凤凰“司学”改为“厅学”。按照“创辟大一统之业,乘此遐荒初辟,首明教化,以端本始”认识,要求今后土官“应袭”,“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者,听补廪科贡,与汉民一体仕进,使明知礼义之为利。”[4]978乾隆十九年(1754年),“以应选教谕者兼摄训导,学额如旧”。乾州之镇溪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设“所学”,“学务以附近之泸溪训导兼摄”,“入附学生八名,武生四名,廪生四名,增生亦四名”。雍正十三年(1735年),亦改“所学”为“厅学”。永绥之地兴学稍迟,约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始建文庙。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开设学校,“移辰溪县训导作永绥厅训导,仍以应选教谕管训导事”,“入附学生八名,武生八名”,十年后又“补廪膳生四名,增广生四名”[1]。
上述清初苗疆凤、乾、永三厅文教纪事提示,苗疆之学虽起步稍晚,但随域内渐入秩序亦逐步发展起来。以后见之明,清初苗疆兴学,深层谋划一如前明,仍在“大一统”之业“创辟”之际由“化外”而“内地”的实用主义政治操作。进言之,苗疆地方从书院创设到民、苗入学受教和“与汉民一体仕进”,其文化用功仍是中央王朝“大一统”国家建设题中之义,预设苗疆从社会整合、文化改进到国家建构的演进位序。一如时人“以弦诵柔其桀骜之性,以衣冠化其榛莽之风”,“渐知尊君亲上之义”之谓[5],即内蕴整合“化外”归于“制内”的政治目标。故较于“内地”之文教指向,苗疆学校教育于国家建构的目的性更为明确。
其实早在顺治年间,就有地方官员注意到了以“文”化“苗”背后的政治指向。顺治十六年(1659年),湖南巡抚袁廓宇奏请于五寨长官司设学,言“五寨界接苗、瑶,向事诗书,今更归化输诚,应请设学”,并按国家学制范式,详定五寨司“考取童生七名,廪生六名,增广生八名。出贡年分,俱照各县事例,两年一贡”[6]。又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在平定湘西“红苗”事后,偏沅巡抚赵申乔、巡道孙调鼐倡建凤凰厅学,“以麻阳县学训导,改拨为凤凰厅学训导,专司学务”[5]。尽管其时朝廷准于苗疆部分地区设学开教,规模不大,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但重要的是,内于其中的国家化的理念深入和“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即如雍正皇帝曾在张广泗平黔省古州、清江等地“生苗”后对鄂尔泰所言:欲使苗疆这一“自古未服王化之地”“均得沾被朝廷之声教”[7]33,化“顽梗”、期“善良”,“国家教养”势所必然[7]826-827,其意即在“边缘”之地融入王朝国家的一体进程。
依边地的治理需要及其国家归趋,苗疆各厅县书院相继建立。乾隆十三年(1748年)兵备道永贵捐资、通判潘曙于凤凰厅建敬修书院[1];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永绥厅同知张天如于吉多坪建绥吉书院;保靖县则于雍正和乾隆年间分别建起崇文、炳文、莲塘3所书院[8]。笔者以为,上述书院的先后兴建,在表征苗疆文教开展积极气象的同时,又反映了“边缘”之地国家化进程的内在需求。但总体而观,无论文教意义上的苗疆书院初兴,还是政治逻辑中儒家思想传播与一体的政治建设,清初苗疆书院的局限仍是明显。
首先,清初苗疆所建书院规模皆小,又大都位于各厅、县政治中枢之地,受教者多为富家子弟,而大量普通民、苗及长期被隔“界外”的“生苗”则难入学,致书院社会、政治影响之广度、深度皆受限制。
其次,书院缺乏稳定的经费保障而运转维艰。以清初凤凰敬修书院为例,每年用于房屋修缮以及师生膏火之资,原由辰沅永靖各府州厅县“量力议捐”,“賚解道署转存凤凰厅存储支销”(1)据载,书院开办之时,各府、州、厅、县官员纷纷“议捐”,其中兵备道岁捐银二十两,辰州知府五十两,永顺知府五两,沅州知府十四两,靖州知府十两,凤凰同知十两,永绥同知十两,乾州同知十两;沅州县知县十两,泸溪县知县十两,辰溪县知县十两,溆浦县知县十两,永顺县知县五两,保靖县知县五两,龙山县知县五两,桑植县知县五两,芷江县知县十两,麻阳县知县八两,黔阳县知县八两,会同县知县五两,通道县知县五两,绥宁县知县五两,共计得银二百数十两。参见黄应培,孙均铨,黄元复:(道光)《凤凰厅志》卷六《学校》。。这在书院开办之初或可敷用。然于书院之后续运行,建立在“议捐”基础上的经费,实则难以稳定。事实上,起始之时所捐经费就已出现“賚解不及时”等问题,又因相关地方官员“或升迁或事故”,作为书院经费来源的“议捐”更为不稳,后来虽不乏“循例捐解”之人,但也有视之为“绥务”而“置之后图”者,“兼之前后交待未清”而致“此项遂成虚矣”。因此,以官员“议捐”为书院经费来源,自难为“可久之计”。正因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和制度保障,苗疆书院运转常陷困境,边地文教之兴亦唯寄望于未来,翘首以待后之“再兴者”[5]。
最后,部分地方官员脱离苗疆社会文化与族群实际的“形式化”认知。即谓湖南仍有一些地方官员罔顾苗疆历史文化与族群差异而坚持“边缘”与“内地”、“苗人”与“汉人”一体对待。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提督湖广学政潘宗洛即要求湖广各府州县“熟苗”中“通文义者”,当与汉民“一体应试”[9]206,苗人“取额”“不必加增”,卷面也“不必分别”[10]1945。如所周知,因长期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自然诸因素的制约与差异,苗疆士子“鲁朴者”多,文理学力远逊“内地”,若“与通省诸生较艺”,自难“获售”而最终“有失无得”。故潘宗洛等人所谓“同等”“较艺”,“汉、苗无殊”等“形式”之论,根本而观,既无益苗疆文教推进,更有损边地各族士子“向上之心”,给苗疆治理和边地的国家进程带来阻遏[11]。
事实上,就清初全国书院恢复或设置情形而观,中央王朝的政策考量仍在“大一统”的国家逻辑中。一如后来有研究者指出,清初书院政策的总趋势意在“因应‘遗民’问题”,以化“遗民”为“臣民”,而其最终目标是“将书院由‘外在’变为‘内在’,纳入国家的整个文化教育体系之中”[12]475。虽然于清初统治者的“大一统”政治理想,苗疆文教开展很难说是“遗民”问题之因应,但却有着另一重苗疆由“化外”融入“内地”的使命。只不过,一些地方官员在面对苗疆社会秩序和经济情况时,在思想观念上生出了重重顾虑和限制,致一些新的文教气象徒具象征意义。以此而言,“边缘”之地一体的文化与政治建设仍任重道远。
二、乾嘉“苗变”后之书院发展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湘黔边爆发大规模苗民起义,以“逐客民、复故地”相号召,迅速席卷苗疆,朝野震动,直到嘉庆二年(1797年)苗疆形势才渐趋稳定。此次“苗变”将清初以来苗疆治理中的社会、经济、文化与族群关系等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引起朝野上下关于苗疆治理转型的“深刻”反思[13]260,随事平后苗疆“屯政”开展,“以文化导”遂成苗疆治理题中之重要一义。
嘉庆十二年(1807年),在湘西苗疆田地均输大抵完成后,湖广总督汪志伊、湖南巡抚景安即以苗疆各厅县“僻在边隅,士习文风,尚多弇陋”而会奏朝廷,筹议重建苗疆被战火损毁的书院,以“广教育”“资化导”,“振起休风”。具体说,要求凤、乾、永、泸、麻、保等厅、县各设书院一所,“慎选师儒”“宣讲圣谕广训”,“教迪考取民、苗生童肄业”,期民、苗能“一体读书”,以“诗书礼义”“约束身心”,“僻壤山陬之地”“广修”文教,风俗“日臻纯良”[11]。透过汪、景二人奏议的理想图景,可见其苗疆设书院、兴文教的根本用心,即在苗疆这一“边荒”“化外”的社会秩序与认同建设。在获朝廷议复之后,汪、景等人鉴于苗疆各地书院未能整齐、设施亦欠完备之实际,一面“饬令各该厅县先行借赁住所”,招收生童,“令民、苗各生及时就学,无有荒废”,“以资造就”;一面“饬令各厅县率同各委员、总屯长等,勘估兴工”,除麻阳县原有书院保存较好而“毋庸另建”外,于凤、乾、永、泸、保等五厅县,先各拨付银一千两,有司“庀才鸠工”,另行兴建书院[11]。
但须说明的是,其时具体督责湘西苗疆书院建设、推动文教迅速发展的,实为以凤凰厅同知身份总理苗疆边务的傅鼐及一众苗疆地方官员。他们在完善边墙体系、全面推开“均田屯防”的同时,尤其重视文教在苗疆社会稳定、秩序规复和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们针对前述清初苗疆书院建设中存在的规模小、经费短缺和学力薄弱等问题,从书院兴建、条规订立、经费保障及科考名额优遇等方面谋求改进。其多重努力及书院发展情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首先,加大投入,扩大规模,重建书院。如傅鼐言,他先于“屯租项下”“通融垫发”书院等修建“工料银”共计一万两[11],分别建成凤凰敬修书院、乾州立诚书院、永绥绥阳书院、保靖雅丽书院、麻阳锦江书院和泸溪浦阳书院,“延请师儒”“培植斯文”,教诲民、苗子弟“勉务实学,奋志功名”[11]。各书院规模较以前大为扩展。以凤凰厅敬修书院为例,乾隆十二年(1747年)首修时建有“头门一座,前厅三间,后厅三间,左右厢房各二间”。后因战争损毁不堪复用,于嘉庆初年傅鼐莅任后重修。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凤凰厅同知姚兴洁于“学署之左”,“买民房十余间,以为书院”。然此际书院仍“规模狭隘”,“肄业者多不能容”。于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护道袁廷极又“于辕门之东街口买民房一所,头门一间,前厅三间,左右厢房各二间,正厅三间,后屋三间,厨房一间”,将书院“移额于此”,且“与前道姚兴洁所买房屋后路相通”。这样,书院房舍在姚兴洁建置的基础上又扩大了许多,能容纳更多民、苗子弟入学读书[5]。
其次,订立条规章程,完善书院管理制度。鉴于此前书院大都“制度不称”,后又因战火损毁而实亡。在嘉庆初苗疆社会安定后,各地方官员遂重新订立书院条规章程,规定由官方敦聘山长、馆师,直接参与生童“考录”,每月定期教授“官课”,尤其对生童膏火、考课、奖励,馆师、监院教官、生童、火夫薪俸,科考支持与经费管理等各类事项做了明确规定[5]。不难发现,苗疆书院之建设、管理、经费、课业与科考等诸般事项的制度化背后,其实是国家力量的彰显;或言书院章程制度的订立完善与落实执行,在苗疆的象征意义不止于书院自身的渐入“正轨”,深层更有“边缘”之地国家权力运作与意识形态的政治表达。
再次,建立并完善书院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书院延聘山长之“束脩”,生童之“膏火”、考课奖励、科考盘费资助、书院杂役开销以及房舍修缮各项,所需费用确实不少。而且如前述苗疆地方官绅认知,充足、稳定的经费,既是书院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条件,又为苗疆社会治理绩效的主要表征,提示了国家建构的符号意义。是以如何确立稳定的经费机制以保障书院正常运转,苗疆地方官员以及书院管理者们皆能用心对待。于此用功,可从以下两项来看:
其一,由官府统一拨给书院经费田。历史地看,清代湘西苗疆各厅县书院,始自雍正、乾隆时期。刚起之时,苗疆秩序未定,书院常因经费短缺而运行维艰,后又因“苗变”毁损而更趋衰颓。史载凤凰厅有学田两处,“一坐枫木林大冲口田一亩三分,纳租米一石二斗;一坐芭蕉溪田二亩六分,纳租谷四石六斗,除完正赋外,易银四两一钱,为赈给贫生之用”。乾州厅学田虽稍多于凤凰,但总量仍十分有限:乾隆六年(1741年)“同知王玮以改学田,请于总督孙嘉凎,得允,计田一百六十丘,四十二亩七分,共纳谷六十一石一斗八升。又续垦学田二十四丘,计田五十八亩四分五厘零,共纳谷五十八石四斗二升”[1]。以如此微薄的学田收入,自难维系书院运转所需。因此,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田地均输大体完成之后,湖南地方官员奏请于苗疆官赎田内动拨相应田亩作为书院经费田,应付束脩、膏火等项开销。具体为凤凰厅五百亩,永绥厅四百亩,乾州、泸溪、麻阳、保靖四厅县各三百亩,共计二千一百亩。后又因书院规模扩大,肄业者渐多,既有经费田所获已然不敷,日趋支绌。于是嘉庆十四年(1809年)湖南布政使朱绍曾、按察使傅鼐等议奏,凤、乾、永、保、泸、麻六厅县各加拨新垦田一百亩,以保障书院膏火、役费等支销所需[5]。由此,苗疆各书院获得了稳定的办学经费。
此外,书院生童参与乡、院各试的盘费也是一笔较大支出。于此,苗疆各厅县财政计划原本未有定制,而主要由历任道台筹捐应付。然而,此种筹捐以资的方式,靠的却是筹捐者个人能力与意愿,充满了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随“苗变”后书院规模扩大,民、苗生童日多,所需经费更甚,而筹捐所得毕竟有限,难以支承。为此,傅鼐等酌情“于凤、乾、永三厅屯苗各佃新垦田内,拨出田一千亩”,按田亩招佃收租变价,专备书院生童参与乡、院各试所需盘费。尤于苗童应试盘费支持,几无条件限制,云:苗童“无论是否前列十名,凡赴县、厅、府、院试者,各给盘费银一两;苗生则无论科考之正案录取与否,凡赴乡试者,各给盘费银十两”[11]。
其二,地方官员与乡绅捐赍,为书院经费的另一重要来源。如前述凤凰厅敬修书院创置之初,时任道台永贵倡议道属府厅州县官员量力捐赍,共得银二百三十两,以济书院师生束脩膏火之急。实际上,自嘉庆以来,每逢登科之岁,苗疆若有举人会试,道台亦捐银四五十两不等作为盘费,且成惯制(直至道光二十八年,规定从屯防项中列支额定屯谷为民、苗举人会试盘费,此制始才改变)。道光十七年(1837年),凤凰厅绅“捐助水田二处及公置房屋数间,所收租赁钱文,或作文庙暨书院岁修,或给宾兴旅费,或帮童试卷资”。同治六年(1867年),凤凰厅黄丝桥廖氏将所有之“懒板凳田岁收租课,折钱五千文”,“捐入书院管业”。同治十年(1871年),道台杜鹤田履任之初,见敬修书院“月试书院课文寥寥无几,而监院汇齐试卷迟或半月”,经询获悉,乃书院生童“大半乡居寒畯,势难频集”,于是“特捐清俸,月添生童课奖钱十二千文”。光绪元年(1875年),复“重叨厚赉五百金,付首事贷商生息,益增堂课月奖之赀”[14]。又如保靖县早在乾隆时期就有地方士绅先后捐给书院田亩百余丘;嘉庆七年(1802年)至十一年(1806年),“书院公买”刘定国、宋长升,生员宋正察、监生宋恒芳等捐田六十七丘入书院,“以作膏火”;道光八年(1828年),保靖知县谢元谟将其四都那洞田“一塅”,“捐置以作书院膏火”;次年监生胡绍兴将十四都草菓坪田二十六丘捐入书院;同治四年(1865年)保靖知县王敦仁“捐廉八十千文”,“并捐充两项三载生息”,当九都、二都、十五都等地水田大小四十四丘,“所收租谷,俱归入书院,作县课奖赏”[8]。
甚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但湘良莅任辰沅道后,因凤凰厅新设尊经书院,“事属创始,膏火无资,规模亦多未备,殊属有名无实”之情形,当即“捐廉”购置各种“经籍”,交由监院保存,以便书院诸生“翻阅讲习”。后又“捐廉”加奖“每月官课”成绩优秀者,“以示鼓励”[11]。
最后,为苗疆士子争取科考名额优遇。嘉庆初年,因前期“苗变”致苗疆书院大多毁损,民苗士子“荡析离居”,“丹铅弃置”,“读书无力”,以致每届科考之期,应试者寥寥,所获鲜少。因此,许多地方官员努力为苗疆“鲁朴”士子争取更多学额及科考、校艺中的优待。嘉庆十二年(1807年)湖南巡抚景安、学政李宗瀚奏请将“苗疆士子及苗生等乡试另编字号,分别取中”,要求苗疆凤、乾、永、保四厅县“请照四川宁远府另编宁字号之例,数至三十名以上,另编字号,于本省额内取中一名”;苗生则“照台湾府另编至字号之例,另编田字号,仍照云南等省顺天乡试另编中皿字号之例,于十五名内额外取中一名”。事实上,朝廷也意识到民、苗生童文理学力与“内地”的实际差距,认为若“边缘”与“内地”科考取中名额等同一致,于苗疆各族士子实不足“以示鼓励”,更无以坚其“向上之心”。故于景、李所请,大都准奏[11]。嘉庆十七年(1812年)湖南学政汤金钊会同巡抚广厚再次奏请朝廷,在保靖县“添设苗童进额一名”,以鼓该县苗众“向化之心”[11]。
上列苗疆书院建设、制度完善、经费保障和科考优遇等,固有地方官员基于苗疆文教迟缓、师生穷困、民苗生童学力薄弱之虑,但其用力显然不只为了在苗疆昭示一种自上而下的“体恤”,而更重要的是“边彝诸生”“益增向化”的政治谋求[11]。这其实也不难理解。自顺治四年(1647年)中央王朝力量进入湘西苗疆始,“大一统”的国家建构毋庸成为从朝廷中枢到地方基层统治者处理边疆或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务和族群关系的根本考量。或在苗疆地方政治和社会精英看来,其时苗疆书院的文化用功与“均田屯防”等社会政治举措实际并无二致,皆为“边缘”之地国家建设推进的具体需要。一如傅鼐所提示苗疆社会从知识传播到认同整合,再到“边缘”与“内地”政治文化一体建构的逻辑进路,言:如此推进,“则今日书院之苗生,即可为异日各寨之苗师,以苗训苗,教易入而感动尤神,则礼义兴而匪僻消,苗与汉人无异”[11]。以此而观清代苗疆书院从实体建设、条章规制到“文化生产”,在“边缘”之地“大一统”国家建构的意义上,其推播儒家理想、贯彻“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功用或许更为突出和重要。从清代苗疆文教开展的结果来看,书院之文化政治功能发挥确也不错。有谓两载以来,各厅县民、苗生童“观感兴奋”,胥知“荣名足贵”而“矢志编摩感化之心,蒸蒸日上”[11],既反映出国家与地方、“中心”与“边缘”政治文化的积极互动情势,也说明了苗疆各族民众之地域、族群认同向王朝国家文化与政治认同的转变。
三、苗疆书院的国家目标
一般意义上,书院往往被视为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通过形于“前台”的一系列如讲学、读书、著书、藏书、祭祀等形式,表达其文化积累、研究、创造和传播等主要功能指向[12]63。观乎清代书院,尽管内有讲求学理、考试时文和博习经史词章等类项之别[15]154,但文化功能亦大体如是。随着书院与科举的深度结合,书院的教学功能“明显成为建设者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同时也决定了后世书院发展的主要方向[12]86。然而,因所处区域、历史、文化与族群的生境情势,在清代“边缘”之地的国家进程中,苗疆书院的主要功能和价值指向则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才培养和文化研究,而始终贯有“大一统”国家建构的政治目标。
如前所言,清初时学校教育即被视为推进苗疆这一“边缘”之地“大一统”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其文教开展的深层诉求,更多在于促进苗疆社会整合和政治建构,进而融入“内地”一体的政治文化之中。随着嘉庆初年苗疆的治理转型,地方官员接续清初以来就已确立的政治方向,更为突出书院如何“以文化苗”、建构“边缘”与“中心”的共同性,使苗疆书院不仅体现出王朝国家政权的治理效力,而且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超越了经济形态、地理空间以及族群结构差异,在共同文化、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基础上凝聚各族民众,建构起一体的政治和国家认同,使得具有历史、地域、族群等多重意义向度的苗疆,作为共同体社会空间形态的一部分,朝“大一统”的方向发展[16]。
有学者将清代书院发展大体分为四个阶段:顺治、康熙时的恢复发展期,雍正、乾隆时的全面发展期,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相对低落期以及同治、光绪时的高速发展、快速变化并最终改制期[12]484-485。总体来看,创置于改土归流之后的湘西苗疆书院,其变迁轨迹与该趋势有所不同。具体说,在嘉庆以前,苗疆书院多因经费不足、师资匮乏、“制度不称”而呈衰颓之势,在乾嘉之际更因战火而大多损毁,故于此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书院的政治文化绩效并不彰显。不过,与嘉庆、道光、咸丰时期全国书院渐入低潮不同的是,湘西苗疆书院于此际却得以快速发展。就前述朝廷中枢和苗疆地方官员的言说而观,这种积极气象,难免不是“边缘”之地国家进程的政治需求。故而较于“内地”书院废替和文教转型,苗疆书院的演递轨迹及功能有其不同,尤边地社会整合和“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化基础,更为明确也更显重要。
进言之,苗疆书院建设及其文教开展,既反映了国家与地方、“中心”与“边缘”的政治文化互动,同时也是国家力量在“边缘”之地的重要象征——创置后即作为苗疆传播“大一统”意识形态与价值准则的主导机构,形塑“边缘”与“中心”的文化一致性,以此建构、强化苗疆各族民众的认同取向。正是因为苗疆社会秩序与政治建设的“迫切”需要,作为苗疆治理的一个重要选项,苗疆书院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承载。傅鼐曾在《治苗论》中就很明确地表达过这一治理逻辑:欲谋苗疆久安,惟有化移“最为犷悍”红苗之习,克其“犬羊之性”,以“奠其身家,格其心思”。如此,“苗乃可得而治”。然欲格苗“心思”,必“申之以教”,否则,“其心犹未格也”[11]。傅鼐等人之如此体认,显为其书院建设的“行动指南”。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支持,苗疆书院与“均田屯防”“边墙体系”一起,结构了彼时苗疆社会的治理体系。对应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苗疆书院与一批逐渐成长起来的本地读书人,越来越多地参与苗疆防卫、秩序、赈灾等地方公共事务[17],同时也作为桥梁和纽带,联系、沟通“国家”与“地方”、“中心”与“边缘”,从而强化“边缘”之地的国家性。而书院祭祀则借助一系列仪式化过程,助推边地各族民众确立共同信仰,引导其认同结构由地域、族群到一体政治与国家的升华。
总体而言,在清代“边缘”之地的国家化意义上,苗疆书院以其目标明确的“文化生产”,将“大一统”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全面渗入这一族群关系颇为复杂的边地社会,确立域内各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型构并深化各族民众一体的政治与国家认同。可以说,相较传统意义上书院的文化指向和功能发挥,苗疆书院作为边地国家化的重要一环和表征,始终贯有清晰的“大一统”国家建构逻辑,在清代苗疆社会变迁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其政治意蕴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