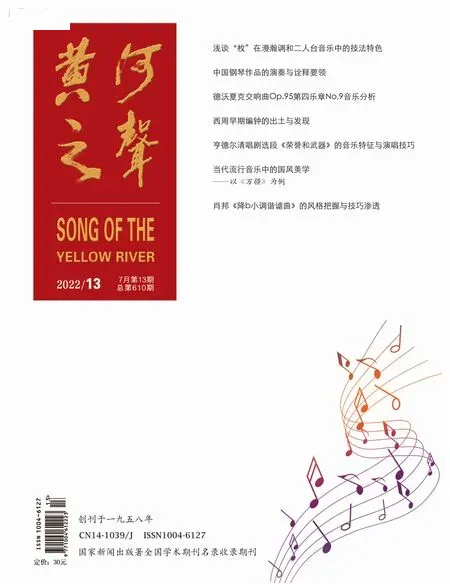钢琴改编曲《松花江上》的民族精神研究
刘菁菁
引 言
《松花江上》作为我国较具代表性的钢琴改编独奏曲作品,由作曲家运用娴熟的创作技巧进行再次创作,在抒发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一、崔世光与《松花江上》
中国钢琴改编曲有着较为漫长且曲折的发展历程,直至20世纪80年代,钢琴改编曲在我国的发展才趋于完善。众所周知,中国的钢琴改编曲多以民歌、民间乐曲或一些广为流传的歌曲为创作基础,其中流传较广的作品有:朱践耳的《流水》、陈培勋的《平湖秋月》、崔世光的《松花江上》等等。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创作于1936年11月,彼时的东北已被日军侵占,日本更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张寒晖在耳闻目睹了中国人民流亡的惨景后,熊熊燃起的爱国之情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并以北方女人在坟头为亲人哭诉的哀声为创作素材,创作了《松花江上》的曲调。作为我国抗战时期脍炙人口的歌曲,《松花江上》与《流亡曲》、《复仇曲》并称为“流亡三部曲”,这一组歌曲也在流传祖国各地的同时,鼓舞着全民抗日到底的决心,对动员全民走向抗日战场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周恩来总理曾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表明:“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20世纪60年代,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松花江上》被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之中,由此可见,该歌曲在当年对全国人民参与抗战的巨大影响。也可以说,正是在《松花江上》这些革命歌曲的召唤下,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才更加坚定,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不但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更对全面夺取世界反法西斯侵略胜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松花江上》为彻底粉碎德日法西斯的全球性侵略行径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48年,中国现代作曲家兼钢琴家崔世光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他的母亲作为当时最早一批学习钢琴的女大学生,有着较高的音乐素养。在家庭浓厚的音乐氛围下,崔世光自小就表现出敏锐的听力和良好的节奏感,并对钢琴有着浓厚的兴趣,自幼便开始在母亲的引导下学习弹琴。当崔世光10岁左右的时,其灵活的即兴创作能力越发凸显,当姐姐在唱歌曲时,他的双手会娴熟地配合歌唱旋律,而这种日积月累的即兴伴奏能力也为其之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崔世光顺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跟随郭志鸿和陈静斋学习钢琴表演,求学期间,他利用假期这一空闲时段,将《喜洋洋》、《灯节》和《赶集》这三首小曲子进行改编,改编后的钢琴曲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并被学校油印出版为教学材料,这极大地鼓舞了崔世光在钢琴音乐上的创作,对此,该时期也被视为其个人的创作萌芽期。1967年,崔世光在一次排练中,即兴演奏了《松花江上》,他在原有歌曲音调的基础上,通过钢琴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表现力,巧妙地编配了织体与和声,因这一改编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随后便被其成功的改编为钢琴独奏曲,该作品体现了崔世光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其超强的感染力更使之成为活跃于音乐会上的常备曲目。
二、钢琴改编曲《松花江上》音乐分析
钢琴曲《松花江上》为再现复二部曲式的曲式结构。尽管这部钢琴改编作品整体上保留了原歌曲对称的结构特点,但在结构内在的音乐表现力上来看,钢琴改编曲对原作品进行了大胆的调整和突破。
引子
原歌曲中并没有引子部分,为了更好地营造出歌曲凄美的意境,崔世光对歌曲中“爹娘啊”和“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的旋律变化进行创作,将其发展为改编钢琴曲的引子,用柔板的速度和三行谱的复调叙述方式,使低沉的低音琶音与高音旋律遥相呼应,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那般,愤懑地诉说着悲凉的历史伤痛。在引子结尾处,崔世光利用属和弦的一小节休止呼吸,将音乐情感自然地过渡到主和弦上,使听众的思绪由凄美的回忆转入到怀念的故乡之中。
(一)第一段(8-29小节)
钢琴改编曲第一段采用3/4拍E大调的方式来推开,极富明朗的旋律歌颂了美丽富饶的家乡,崔世光在保留了张寒晖歌曲旋律结构和拍子的基础上,对作品的调式和伴奏织体进行了变化处理。全曲以#F大调为主,在9-29小节,崔世光通过复调搭配平静的叙事手法来推动音乐发展,为了进一步增强前面的音乐情感,崔世光在19-29小节增加织体的同时,在26和27小节采用左手三连音的织体形式,以营造出预示的紧张感,行进至29小节,左手的低音伴音则对“九一八”事变进行了预兆。
(二)第二段(30-55小节)
钢琴曲《松花江上》第二段旋律铿锵地在低音区八度的半音阶级上行,有力的音符既宣泄着人们对祖国灾难的悲痛,又燃起了人们对侵略者的愤怒之情。紧接而来的是沉重且带有哀怨语气的半音阶下行,音调犹如悲切的哭泣。演奏者在弹奏此处时,要注意把握好情绪和力度的瞬间变化,可以通过运用小臂的力量来弹奏八度,为听众带来低沉的声音,同时可以对上层旋律音做轻微的突出处理,以便通过音乐刻画出人们哀怨的声音。行进至作品的41小节至53小节,钢琴曲逐渐活跃起来,音乐在左右手的快速交替中急促地进行,左手急剧上下起伏的琶音刻画了人们澎湃沸腾的情绪,同时也预示着人们即将挣脱悲痛束缚的美好生活。演奏者在进行左右手快速交替的弹奏时,应将肘关节作为发力点,在手腕迅速移动的同时,手指要敏捷地快速触键。当远距离触键的跨度较大时,演奏者应提前在意识上考虑下个音的位置,为接下来手指的触键动作做好充足的准备,以避免影响到触键的精准度。演奏作品第42至43小节时,演奏者需要注意谱面所标记的重音符号,手臂在弹奏时要从容地用力,切不可因用力太重而影响声音效果。崔世光在乐曲第41至48小节的旋律中,穿插了大量的和弦与分解和弦,在这种音乐氛围的烘托下,表达了作者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控诉。演奏者在弹奏时要明确分清主旋律和伴奏织体,在勾勒旋律的同时,控制好伴奏织体的音量,并要时刻注意伴奏声部的横向线条,为听众呈现出音乐作品的流动性。自作品的49小节开始,右手的旋律音乐开始慢慢拉宽,而左手则以急剧起伏的分解琶音来传递躁动不安的情绪。演奏者在弹奏时要保证手指跑动的敏捷性,有控制地去触键,以避免生硬触键所带来的音乐停滞感。第54小节在音区降低和左手半音音型的不断重复中,再次引发出紧张的情绪,此时不但表达了人们的悲愤之情,更是对人们参与斗争的强烈呼唤。
(三)第三段(56-73小节)
本段也是作品的再现段,即全曲的高潮部分,崔世光分别以柱式和弦、三连音等技法,生动地表达了内心的愤怒与急切。“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在这呼天抢地的呐喊中,作品的情绪达到高潮,在这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强劲的反抗力量,也正是这种力量激励着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在实践中,人们常会在和弦的演奏上忽视旋律音,由于此处的旋律音主要分布在高音区,对此演奏者应将手的重心放在小指上,如若坚持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弹奏每一个音,那么反而会带来一言难尽的效果。在弹奏强有力的大和弦时,演奏者应用往前推的力量去弹奏,在手指贴键的同时,将手腕处于较高的位置,运用手臂本身的重量加上爆发力,瞬间发力,将所有力量毫无保留地集中到指尖,并在几乎发力同时,迅速放松手腕和手臂,以此带来既极具震撼力又不刺耳的声音。相较于声乐作品,钢琴能够通过辉煌、震撼的和弦与八度技巧,淋漓尽致地展现出管弦乐队强奏的宏伟效果。钢琴作品的第70小节中的低音和弦是原调的VI级和弦,生动地刻画了那种妻离子散、国家将亡的恐怖与愤恨。第72、73小节中,崔世光以重属七和弦进行到属七和弦的方式,诉说着内心的苦苦挣扎。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流离失所的同胞,每个中国人的爱国之心都会被唤醒,只有大家团结一心、抗日到底,才能夺回我们失去的家园。68-73小节作为全曲的最高潮,在不和谐的和弦及半音阶下行中,表达了作者对亲人、对父母、对家乡的热切呼唤,演奏者需要通过极致的音量来弹奏出此刻沸腾的心情,更要将低音和弦演绎得沉重而震撼。弹奏者需要对每一个和弦做好充分的演奏准备,集中全身的爆发力来触键,通过钢琴的声响再现出管弦乐队的最强奏,使音量与音色双双达到巅峰。值得注意的是,演奏者要将和弦的“渐快”和“渐慢”把握得恰到好处,切不可因过快而影响旋律的力度,也不可因过慢而干扰旋律的气势。在弹奏68、69小节的八度末尾两个音时,演奏者可以进行适当的渐快、渐慢处理,犹如破茧成蝶的新生过程一般,由慢到快,直至最后一个和弦时,爆发出火山喷溅般的上涌热血,加上带有重音记号的三连音伴奏,情感真切,令人心如刀绞。“爹娘啊!爹娘啊!”是广大同胞们含泪的呐喊,我们的爹娘、同胞、祖国都在哪里?在这一声声的呼喊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也正是这股强大的力量激励着人们去战斗、去抗日、去救国、去收复我们可爱的家乡。在密集和弦的层层推进中,全曲激荡的情绪达到最高潮,在悲愤与无奈的交织下,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人们嚎啕的哭腔与撕心裂肺的呐喊!
(四)尾声(74-81小节)
随着前面小节逐渐淡化的和声,音乐情绪也发生了悄然的转变,逐渐由愤怒转化为对胜利的向往,由钢琴在高音区对短笛模仿的声音再现了作品的主题材料,犹如此时的交响乐队已经安静下来,在短笛与竖琴伴奏交织的旋律中,思绪在人们所向往的和平生活中慢慢走远,象征着人们夺取胜利、重返家园的希望。崔世光所改编的钢琴独奏曲《松花江上》,堪称钢琴技巧与音乐情感的完美结合。通过系统的分析,我们不仅看到了作曲家扎实的创作功底,也真切地体会到了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三、钢琴演奏的艺术特色
崔世光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更是一位优秀的钢琴演奏家,毕生致力于钢琴音乐的创作。他在钢琴改编曲《松花江上》的创作中,充分地发挥了钢琴音域宽广、音量变化大、可奏声部多的优势,将原声乐作品不到两个八度的音域扩大到七个八度。除此之外,他还将作品的演奏力度控制在ppp到fff之间,并在各个声部中穿插演奏乐曲的主题旋律部分,极大地强化了乐曲的音乐表现力。同时,他还在钢琴曲的引子和结尾部分采用了三行谱表的记谱方法,以此来充分地表达出乐曲的内在情绪。
(一)充分挖掘钢琴本身艺术特色
钢琴改编曲《松花江上》相较于声乐作品而言,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钢琴不但有着音域宽广、音量变化大、表现力强、可奏声部多等多个明显的优势,还能通过丰富细腻的和声来模拟独奏乐器,以磅礴的气势再现整个管弦乐队,为听众提供更加宽广的想象空间。除此之外,钢琴还能在演奏者高深的演奏技巧下,为听众勾勒出真切的意境,不断激发人们的想象,引人陷入深深回忆,不断地催人奋进、勇往直前。
(二)民族音乐与钢琴的完美结合
崔世光先生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巧妙地将民族音乐融入到钢琴演奏之中。钢琴曲《松花江上》旋律饱含传统音乐的精髓,其丰富的织体更是作者扎实功底的有力证明,流畅的琴声情真意切、荡气回肠,透露着来自人民底层的深沉气息,始终充盈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不可否认的是,钢琴改编曲《松花江上》依然是当代中国艺术钢琴曲库中不可或缺的珍宝。
结 语
中国音乐有着独特的旋律、和声、曲式、节奏和音色,崔世光创作的钢琴改编曲《松花江上》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巧妙地融入了他娴熟的创作技巧,凭借着旋律本身的感染力,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品中真挚的音乐情感。在其大胆的创新下,一首原本较为规整的声乐歌曲变得更富有情绪变化,不断交替变化的拍子刻画了人们忐忑的内心,而和弦三连音音型的融入不但烘托了作品的音乐气氛,还在张弛有度的节奏中,给人以一种悲凉、沉痛的感觉,这也是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无尽控诉。演奏者在演绎该作品时,不但需要具备扎实的弹奏功底,还要通过对乐曲内涵不断加深的理解来感悟作品,将激昂的旋律融入到悲愤的情怀之中,用完美的音响效果带来强劲的感染力。时至今日,钢琴改编曲《松花江上》对我们的启示仍旧深远,这也正是中国优秀钢琴音乐作品的独特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