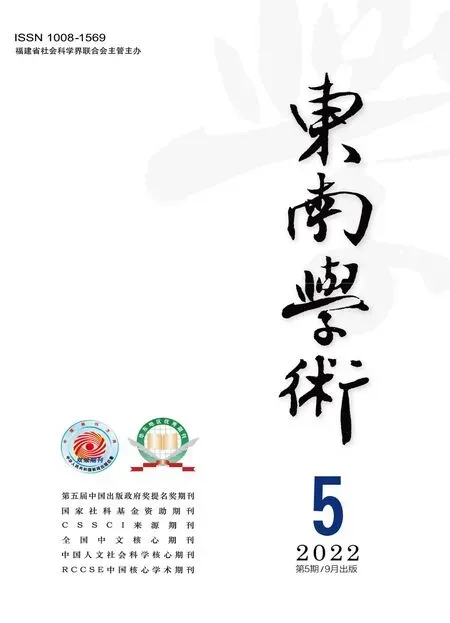符号学视角下智能算法对人类主体性的消解及其反思
冯月季
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智能算法正在深刻影响与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一方面,人们憧憬和享受智能算法技术所带来的便利与效益,对其保持着乐观的想象和盼望;另一方面,许多人表达了对智能算法技术的隐忧。当智能算法成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后,人们发现,智能算法除了由其技术本身缺陷带来的各种不确定风险之外,最严重的危机在于其对人类主体性的消解。近年来,许多学者围绕智能算法与人类主体性关系从不同理论视角展开研究,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从宏观理论角度探讨智能算法技术建构的虚拟景观与用户的沉浸体验,从而导致主体能动性的丧失,(1)K. W. Lee,“Addiction by Design: Machine Gambling in Las Vegas by Natasha Dow Schüll(review)”, Technology and Culture, 2014,55(1), pp.278-280.并思考智能算法时代主体性复归的认知和实践路径;(2)王敏芝:《算法时代传播主体性的虚置与复归》,《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二,从哲学角度分析智能算法时代的人与机器的关系,(3)常晋芳:《智能时代的人-机-人关系——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东南学术》2019年第2期。智能算法引发的主体伦理危机,(4)M. Ananny,“Toward an Ethics of Algorithms Convening, Observation, Probability, and Timeliness”,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16,41(1), pp.93-117.以及“算法伦理”的建构路径;(5)郭林生、李小燕:《“算法伦理”的价值基础及其建构进路》,《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年第4期。第三,从法学角度阐释智能算法中的法律主体性危机,如主体不明、决策不公等,(6)陈姿含:《人工智能算法中的法律主体性危机》,《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或从司法伦理和算法正义的立场建构算法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制;(7)金梦:《立法伦理与算法正义——算法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制》,《政法论坛》2021年第1期。第四,从新闻传播学视角研究算法新闻中的主体关系构成维度,(8)杨保军、李泓江:《论算法新闻中的主体关系》,《编辑之友》2019年第8期。通过对算法透明度概念的阐释探讨智能算法时代传媒伦理以及主体道德建构的原则和条件;(9)王娟、叶斌:《“负责任”的算法透明度——人工智能时代传媒伦理建构的趋向》,《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12期。第五,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以主体理性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在智能算法时代的终结,(10)蓝江:《走出人类世:人文主义的终结和后人类的降临》,《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伴随着智能算法时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离散,一种模糊“身体-机器”界限的后人类主体显现出来。(11)Rosi Braidotti,“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ritical Posthumaniti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9(6), pp.31-61.综合来看,学者们对智能算法技术与人类主体性关系进行的多维阐释拓展了问题研究的广度,也在理论深度上触及人类主体性在智能算法时代所面临的根本困境。
基于既有成果,笔者尝试从符号学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其理据在于,传统哲学中的主体概念只有在符号学理论视野下才获得了新的意义解释,主体不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而被看作具有动态衍义结构的符号。这种符号学转向为主体理论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将人对符号意义的解释和追寻看作是主体存在的根本特征。从宏观角度来说,符号学作为一种研究理论和方法,旨在探寻文本意义的符号生成和表达机制。尤其在探讨智能算法技术对人类主体性消解问题上,通过符号学理论透视能更深入地呈现问题的肌理,其对问题的阐释建立在元反思的层次上,进而探寻智能算法时代人类主体性复归的符号学路径。
一、符号域的物化:智能算法时代人类主体的存在语境
(一)主体概念的符号学阐释
近代以来的主体哲学研究往往将主体视为一个固定绝对的实体,由此导致了主体哲学研究的困境。对主体概念研究的转向始自符号学领域,符号学将主体看作一个由意义建构的符号,因为追寻意义乃是人的本质,而意义必须通过符号表征出来,主体通过意义和符号产生了内在的联系。更进一步而言,人所谓的主体性或主体意识,不仅在于人本身就是符号,而且人就生活在一个符号域中。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人们所使用的词语和符号就是人的自我。因为把每个思想是一个符号的事实与生命是思想的列车的事实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证明人就是一个符号,因此每个思想是一个外在的符号,人也是符号。”(12)The Peirce Edition Project,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Vol.1(1893-191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5.在皮尔斯的阐述中,人只有在使用符号时才能产生观念,如果所有的观念都是从符号产生的,那么人也就是一种符号化存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更进一步认为:“所有事物都是象征和符号,它们充当两个主体之间的媒介。”(13)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2卷,俞宣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在他看来,主体依托于符号作为交往的媒介才能存在,可见主体浸泡在符号的意义世界中。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Umberto Eco)认为符号学是研究话语和行为主体的理论:“我们,作为主体,是由诸符号域产生的形式而形成的……我们只有作为运动着的符号过程、含意的系统和交往过程才相互理解。”(14)翁贝尔托·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从符号学的立场来说,原子化的主体无法单独存在于世界中,主体必须落入符号域中与其他符号构成一种主体间性存在。主体被认为是具有能动性的、三元的符号表意结构,正是认识到了主体的这种“符号共在性”,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20世纪初就提出要创立一门“主体符号学”。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也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倡导“为符号学补上‘主体’这一课——建立主体符号学,是完成符号学奠基性事业的关键性环节”。(15)唐小林:《寻找灵魂:建立一种主体符号学》,《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应当说,主体符号学理论的建构是哲学与符号学的一场完美“联姻”,不仅夯实了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为主体哲学理论的演化和进展开辟了新的天地。更为深层的意义上,其使得现代以来饱受批评质疑、即将退隐的“主体”重新恢复了与意义世界的关系。
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巴黎符号学派将其试图创建的“主体符号学”称为“激情符号学”,其目的在于强调符号意义来自于主体与世界的激情碰撞,主体的“符号共在性”只有融于符号域中才是有可能存在的。符号域是一个开放、动态、多元的语义系统,“对话是符号域的本体特征”。(16)皮特·特洛普:《符号域:作为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对象》,赵星植译,《符号与传媒》2013年第1期。主体性在符号域内部生成的过程,也是主体对经验世界进行符号化的过程。符号域的多维度特征与主体的认知活动有着相同的逻辑,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经过时间的累积和空间的延展,主体面对的必然是一个意义无比丰富的符号域。事实上,现代世界的演进也遵循着符号化逻辑展开,主体在世界上生存,不得不处理社会文化中越来越多的符号意义问题。符号域既是主体意义认知活动的结果,也是主体意义认知的条件。正因如此,主体栖居的符号域才能成为意义不断生成的符号域,而不是意义被给定的固态实体。正如米哈依·洛特曼(Mihhail Lotman)所言:“符号域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概念,就像主体世界的概念需要新的范式和逻辑一样,它不是建立在决定论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对话之上的。”(17)米哈依·洛特曼:《主体世界与符号域》,汤黎译,《符号与传媒》2013年第1期。
(二)人类主体存在的符号域被物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劳动异化现象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释和批判,认为当劳动异化发展到极端情况下就会出现社会生产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在被物化的世界当中,人彻底沦为商品和资本的附庸,主体性遭到了彻底的消解。(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7页。卢卡奇(Georg Lukács)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批判的基础之上,系统性地提出了“物化”理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种基于可计算性和机械化生产的原则逐渐成为社会劳动普遍遵循的律令,进而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本身,与商品、劳动、生产等外在客观世界物化相比,人的意识被物化才是最深层次的危机。(19)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8-99页。
与马克思、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阐释不同的是,智能算法时代的物化是一种符号域的物化现象。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超越了单纯追求物质商品的阶段,开始进入追求符号意义的社会,符号化生存成为人类主体存在的新形态,符号域构成了主体在其中创造和追寻意义的多维空间。然而,智能算法技术兴起后,人类主体存在的符号域开始呈现出被物化的表征。从技术进步主义的角度而言,智能算法通过数据模型的建构使得嘈杂纷乱的现代世界变得更有条理性和逻辑性,为建构一个理智明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这种对智能算法极端乐观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却隐藏着现代人对算法技术空前依赖而导致的主体性丧失的危险。算法技术生成新的逻各斯,将符号域的意义抽离使之变成纯粹的对象物,而主体作为一个符号也不能幸免被物化。正如卢卡奇所言:“对象性形式掩盖了它们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范畴这一事实,它们表现为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20)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79页。海德格尔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对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物化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在现代社会的技术座架中,人被摆置、促逼而沦落为技术的附庸,从而被物化且遮蔽了主体本真的存在意义。(21)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1页。
相比于马克思、卢卡奇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和商品的物化,智能算法技术对符号域的物化是一种更隐匿的虚拟化和数据化形式,当主体栖居的符号域被智能算法技术物化,主体与符号之间已无法通过意义产生关联,只剩下被算法技术模块支配的数据运算和控制。在剔除信息熵的同时,运用算法技术的主体呈现出悖论的一面,成为被物化和数据化的对象,由此主体与物的关系发生了翻转,使得主体成为被控制和物化的对象。在智能算法技术的运作过程中,主体成为算法工具控制的对象,具体表现为通过数据挖掘实现对用户内容偏好的控制、对内容生产流程的控制以及对用户信息反馈的控制。在算法技术的控制论模式中,当符号域的意义退隐时,主体存在的根基被动摇,主体符号自身以及符号域被物化,由此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卡西尔所说的最极端的文化悲剧,那些由人类主体所创造的文化价值“变成一些纯然对象性的东西,变成一些纯粹为物性的当前存在和一些物性的被给予,而再不能为自我所理解和掌握”。(22)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子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页。
二、元符号能力丧失:智能算法时代人类主体性的消解
(一)人作为元符号存在
何为元符号?卡西尔在他的符号形式哲学中将人定义为符号动物,与之观点相似的还有列维-斯特劳斯、翁贝托·艾柯等人。可以说,与主体哲学将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相比,符号学对人的定义更能显现出人的社会文化本质。不过,近年来这种观念开始发生改变,德国哲学家汉斯·兰克(Hans Lenk)通过科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也具有制造和使用符号并运用符号交流的能力。(23)汉斯·兰克:《人是元符号和元解释的存在》,王伟译,《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homas A.Sebeok)也认为动物具有符号能力,并一直致力于建构一门动物符号学。芬兰符号学家塔拉斯蒂(Eero Tarasti)在其《存在符号学》中提出“符号细菌”“符号细胞”“符号行动者”等概念,认为“这些概念既可以覆盖生物和文化方面,既包含动植物世界也包含人类世界”。(24)埃罗·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魏全凤、颜小芳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因此,在兰克看来,卡西尔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这种观点已经无法显示出人的独特性,需要对其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修正。
兰克进一步解释说,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能够使用符号,并不意味着它们和人具有同样水平的符号能力。不同之处在于,灵长类动物不会再次利用符号表达元层次或更高层次的对象,而人能够超越不同的文化层次使用并解释符号,“人类不仅仅是使用记号的符号动物,不仅仅发明符号、塑造符号、改变符号、利用符号并用符号表达,而且还是将符号突出、建立并改变为处于更高层次的符号化过程之对象的动物,即人类解释这些经过分析的人造的‘对象’是在一个元层次上进行的”。(25)汉斯·兰克:《人是元符号和元解释的存在》,王伟译,《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由此,将人定义为元符号动物或元符号存在更能显现出人的独特性。人所具有的元符号能力即是通过符号意义解释创造产生新的符号的能力。符号学界对元符号阐释得最清晰的莫过于皮尔斯,在皮尔斯的三元符号学思想中,解释项使得符号具有了无限衍义的可能性,符号接收者通过对符号意义的解释具备了创造新的符号的能力,皮尔斯说:“一切思想都是符号……每一个思想符号都会被解释成一个新的符号。”(26)Charles 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Peirce, Vol.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p.308.最早提出“符号学”概念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也认为,符号学的任务主要是考察人是如何理解事物意义的,我们若要互相传达思想,就必须为各种观念创造一些符号。(27)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77-778页。不难看出,洛克在创造“符号学”这个术语之初,就隐含着一种典型的元符号思想。依靠着元符号能力,人类主体意识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层次,进行符号意义的认知和解释活动。
(二)智能算法对人类主体元符号认知能力的遮蔽
正如兰克所表明的,人类的元符号能力能够跨越不同的元层次进行符号意义的解释和反思,这个过程首先表现为主体的元符号认知活动。主体在符号域中生存必须不断处理符号意义问题:将已经认知的符号意义储存为生活经验,对新生成的符号意义进行解释。可以想象,无论从空间的广度还是时间的延展来说,主体都被包裹在符号域的意义世界中。符号域既是主体认知的结果,也是主体认知的起点。从空间的广度来说,符号域并不是一个意义超稳定的世界,而“是差异产生和形成的空间……是质的多样性空间”。(28)卡莱维·库尔:《符号域与双重生态学:交流的悖论》,张颖译,《符号与传媒》2013年第1期。符号域系统内部分化为若干个符号意义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存在着意义的交流、冲突以及融合。从时间的延展来说,哪怕符号域内部的意义世界再复杂,也依然跳不出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序列,在三元的时间结构中,符号域的意义结构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在这样的存在状态下,主体意识 “操心”意义问题,必须从半透明甚至混沌的符号域中提取相应的符号以夯实自身的意义根基,这需要主体意识具备相应的元符号认知能力。然而在智能算法技术逻辑下,基于“万物皆数”的哲学理念,人类主体也被迫成为机器和技术处理的数据对象,智能算法通过数据爬取技术对用户的媒介使用痕迹进行标签化处理,将其作为内容生产的框架,试图通过算法技术将主体存在的喧嚣嘈杂的符号域整理成一个充满秩序、和谐稳定的意义景观。人类主体对智能算法的依赖性越强,越说明智能算法在更多领域中替代了人类主体的思考。例如发生在2018年的Facebook 数据泄露丑闻事件中,剑桥分析公司(CA)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使用Facebook创建的应用程序收集数百万用户个人数据和信息用于政治研究。这不仅是一起严重的用户信息泄露和隐私权被侵犯事件,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当智能算法技术代替人类主体意识进行认知和判断之后,人类主体性被“降维”和“虚置”,成为机器和技术所建构的数据模型进行程式化计算的对象。
我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追问和反思:基于元符号认知能力的人类主体所具有的理性认知和判断被智能算法取代之后,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是一个超稳定且具有确定性的意义世界,人类主体曾经因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熵”的存在构成对信息意义的曲解而苦恼,而智能算法以追求“确定性”为目的,最大化剔除信息传播中的“熵”。因为算法技术的这种运行逻辑恰恰是基于主体符号认知的“经验基模”,而“经验基模”只是主体时间过往的意义累积,从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延展上,构成“经验基模”符号意义的都是窄化和陈旧的主体,只是主体的“拟像”或者碎片化的主体,并不包含任何创造性的或新的符号主体部分。
(三)智能算法对人类主体元符号意义解释能力的消解
人类主体的元符号能力表现为元符号认知能力和元符号意义解释能力。通常而言,主体的符号认知行动是沿着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连续结构展开的,人类主体对意义的追寻是一个符号过程,类似于皮尔斯所说的符号解释项的存在使得符号意义能够向未来无限延展,这也是兰克所说的人的元符号能力具有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很显然是朝向未来的时间向度,“意义的本质是向未来的动力性发展”。(29)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9页。然而,智能算法技术强行将主体从时间的连续序列中割裂开来,主体的符号意义解释活动仅局限在“过去-当下”的二元时间结构中。并且智能算法技术改变了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将不在场的符号意义推至前台,使之与符号发生了重叠,符号的表意距离消失,其表意过程中的噪音和意义悬置都被抽离,此时的符号对于主体而言是一种“绝似符号”。主体面对符号失去了意义解释的动力机制,也就不再有探索外部世界的符号能力。
智能算法技术为人类主体建构了一个被数据化和计算化的生态环境,并日益对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实施浸入式控制,机器的运行逻辑逐渐嵌入人类主体生活并生成一种新型的人机关系。智能算法技术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拟主体”,它们正在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过人类的智力。以色列法律科技公司LawGeex生产出了一种能够阅读法律文书的AI,并在2018年2月将其与20名专业律师进行比赛:理解法律文书。结果AI的平均准确率是94%,而人类律师的平均准确率只有85%。(30)环球网:《机器学习算法在NDA法律分析测试中打败20位律师》,2018年11月1日,https://smart.huanqiu.com/article/9CaKrnKeisX。这个例子是一个极大的警示,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按照智能算法技术的这种发展速度,人脑“黑箱”问题是否会得到终极解决?人类主体被机器化、数据化正在演变为现实。
当人类主体被智能算法技术奴役,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元符号能力,主体自身不再是一个具有弹性的符号表意结构,而是被智能算法技术囚禁在封闭躯壳中,只能面对过去的陈旧自我镜像,成为平面化、原子化的个体。人类主体被智能算法技术的幽灵所缠绕,“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技术时代,也是一个人类正在逐步丧失主导权的时代。在看似以我们为中心的智能生活中,各种数据、智能、算法正在成功地接手这一切,人们逐渐在智能设备的安排下,退守到自己狭小而惬意的空间中,满足着屏幕和智能环境为我们制造的幻象”。(31)蓝江:《走出人类世:人文主义的终结和后人类的降临》,《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当人类主体的目光和视界被局限在狭小封闭的空间时,自然也就失去了探索外部符号域的意愿和能力,人类主体不再是皮尔斯等人所说的符号意义的解释者和新的符号的创造者。由于元符号能力的缺失,通过符号行动超越自身有限性的主体不复存在了。
三、符号具身:智能算法时代人类主体性复归的路径反思
(一)他性与责任:智能算法时代的主体符号伦理
智能算法技术所固有的“垃圾进—垃圾出”运行机制,使得“机器学习在吸收具有正面价值的数据时,也会吸收具有负面价值的数据……算法是基于统计的相关性做出推理的,数据之间的统计学关联可能隐藏着人类的过失、偏见和歧视”。(32)孙保学:《人工智能算法伦理及其风险》,《哲学动态》2019年第10期。其中的问题在于,智能算法做出的所谓优化判断和决策,是工程师基于某些固定数据变量和样本通过计算推理之后生成的决策依据,数据变量和样本的来源、质量以及智能算法技术的开发者的认知和价值观等诸多因素,都使得表面上看起来客观公正的数据运算充满了不确定性。由此所导致的后果是:出于所谓优化判断和决策的考量,某些个人、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在数据统计与运算过程中被剔除掉,然而他们并不知情。这有点像罗尔斯(John Rawls)所说的“无知之幕”,并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
因此,从根本上而言,由智能算法所导致的偏见、歧视背离了主体的符号伦理。当我们将主体看作是符号化存在时,首先意味着主体不被当作一个独立自主的实体,而必须与其他主体形成共在主体性;其次,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符号主体都具有同样的表意结构,没有谁会比其他人的身份更优越,这体现了一种符号平等的原则,至于主体之间的差异,则取决于三元符号表意结构中的解释项。而在智能算法的话语逻辑下,符号化的主体被向下还原为“物质的实证主义,以及将人还原为有机生命的生物论。……它们都缺乏人性的三元关系模式中的解释项”。(33)诺伯特·威利:《符号自我》,文一茗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208页。我们看到,智能算法将符号主体中的解释项抽离,将原本多元化构成的符号主体进行压缩和扁平化处理,基于优化选择和决策的数据运算逻辑必然导致某些个体或群体的思维逻辑成为智能算法征用的对象,并被放大为一种表征理性和秩序的行动指南,另外一些个体或群体则在某些方面不符合数据统计标准而被排斥在智能算法逻辑之外。
这或许是智能算法运行逻辑的一种悖论,当然这种悖论源于人类主体性内部。无论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座架”还是美国学者托马斯·修斯(Thomas Hughes)所说的“技术体系”,都表明了当人类主体被科学技术所裹挟并植入人类思维的“前理解”时,科学技术就具有了一种人类主体不可控的惯性动能,并直接将人类主体推向一种原子式的绝对自我观念,从而导致主体符号伦理中“他性”和“责任”的缺席。为了跨越这种“责任鸿沟”,有必要重申以“他性”和“责任”为旨归的主体符号伦理,就人类能够通过符号进行反思并作出审慎思考这种元符号能力而言,“正因为人类能够对符号——自身的和他者的——进行反思,因此,和这种能力相关的责任意味着不仅为自身的符号,而且为他者的符号有所担当”。(34)苏珊·佩特丽莉:《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周劲松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对于智能算法技术的开发者而言,将这种基于“他性”和“责任”的主体符号伦理内化为约束机制尤其重要。需要明白的是,数据的提取和运算关切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主体符号,如果导向一种纯粹的结果主义,其本质是对“他性”和“责任”主体符号伦理的背离,最终将导致人性沦为智能算法的奴役对象。
“他性”和“责任”主体符号伦理的确立,同样依赖于他律层面的对智能算法的价值引领和法律规制。2017年,中国计算机协会就发布了针对算法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一些具体原则,强调运用智能算法加强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监管,建立必要的纠错机制。为了破解智能算法暴露出来的“流量至上”以及用户权益被侵犯问题,2019年,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要通过“价值引领”策略抵制智能算法中的恶俗行为,塑造向上向善的价值观,通过立法确保数据开发和个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平衡。在国外,为智能算法立法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美国计算机协会2017年颁布的《算法透明与追责原则》和欧盟2018年颁布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都对数据主体的权益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无论从自律还是他律的角度而言,为智能算法立法都是为了避免将其单纯地作为某种达成目的的工具,从而确立以“他性”和“责任”为主旨的主体符号伦理,维护人类主体的尊严。
(二)从“技术具身”到“符号具身”:智能算法时代的主体性复归
智能算法对人类主体性的消解表现为当下一种鲜明的“技术具身”论,美国技术现象学家唐·伊德(Don Ihde)是“技术具身”论的倡导者,他将人类身体分为两个部分——现象学范畴中“活的身体”和被社会文化建构的“权力身体”,为了弥合这两种“身体”之间的鸿沟,伊德提出通过技术将两种“身体”联结而生成一种具身体验,由此人与技术相互形塑。正如伊德所说:“我通过对技术的感知,以及通过我的知觉和身体感知的自反性转变,以特定的方式将技术带入我的体验当中。”(35)Don Ihde, Technology and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3.“技术具身”论看似为当下人类与技术融合提供了完美解决之道,但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着根本困境。正如人类主体进入所谓“算法化生存”语境之后,智能算法就会超越技术层面而上升为一种话语逻辑,成为一种现代社会人的价值观和认识论,从而捆绑人类的思维。智能算法就有可能僭越人类主体性,将人当作数据统计和运算的对象。因此,“技术具身”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将人类社会存在的所有问题都看作“一个有待于解决的技术问题,而非有待于沟通的意义问题”。(36)周午鹏:《技术与身体:对“技术具身”的现象学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技术具身”论并不能解决智能算法对人类主体性的消解问题,而必须回到人类主体追寻符号意义的层面思考问题的解决之道。区别于伊德的“技术具身”论,笔者认为智能算法时代人类主体性的复归必须秉持“符号具身”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具身认知研究开始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和文化进路,尤其是隐喻理论和知觉符号理论被用于具身认知研究当中,更加凸显出人在具身认知过程中通过符号意义对主体性的建构。
作为表征人类主体心灵和意识的形式载体,符号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意义。人类主体心灵和意识驱动身体的行动才能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正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所言:“身体用它的各个部分作为关于这个世界的一般符号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因而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理解它,并发现它的意义。”(37)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Cambridge: Routledge Press, 2002, p.237.关于人类主体的“符号具身”问题,乔治·米德在其“符号互动论”中有过清晰的表述,他认为人类的心灵和意识是在与符号意义的互动交流中产生的,心灵和意识的运作获得了关于符号的意义进而产生了自我意识,这一过程是自我作为主体与外部对象之间通过实施具体的符号行为发生的,符号及其意义构成了自我的本质。(38)George Herbert Mead, The Philosophy of the ac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pp.658-659.换言之,人类主体浸泡在符号世界中,外在的身体与内在的心灵和意识必然要通过符号意义才能联结起来。“在与符号活动耦合的生命世界中,人类符号活动被赋予了元符号活动的特点,既有可能对符号进行反思,也有可能使符号不仅作为与对符号所做反应没有区别的解释对象,而且作为对符号的反思、搁置反应这种解释对象,同时,有可能做出审慎思考。”(39)苏珊·佩特丽莉:《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第22页。因此,在智能算法重构人与技术的关系并对人类主体性消解的语境下,“符号具身”才是向人类主体性复归的本真路径。
四、结 语
人类已经进入了“算法化生存”的时代,不管愿意与否,作为个体的主体已经被裹挟进入了这样的“技术体系”或“技术座架”中。与历史上任何一次科学技术革命一样,人类在享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福祉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技术所捆绑和奴役。由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而导致的人类主体性的消解,其根本缘由在于人类对符号意义的探求和追寻过程伴随着思考的痛苦,而当技术能够代替人类思考并缓解这种痛苦之后,人类主体意识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惰性和对技术的依赖,从人类主体栖居的符号世界中抽身,然后追随并服膺于技术所建构的权力话语。在这样的处境中,“人,不再是个人生活的支配者,而是算法社会的剩余物……算法社会对剩余快感的精妙规划,让主体陷入抽象性压抑之中”。(40)周志强:《算法社会的文化逻辑——算法正义、“荒谬合理”与抽象性压抑》,《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在智能算法技术的影响下,人类主体性被囚禁在狭窄的自我意识内部,完全丧失了对所谓意义、价值和真理的探索。人类需要技术进步,但是与技术进步相比,对意义的追寻才是人类主体的终极本质。这一切都建立在符号意义的阐释基础之上,而符号是无形的关系网,将人类主体密切地联结在一起进行意义的交流。人类文明自诞生起就一直受制于交流,不是因为交流的和谐与融洽,而是因为交流的不完美性和缺陷性。美国学者约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中细数了交流的种种困境,但他仍然坚信:“一切交谈都是带有信念的行为,其基础是相信将来会出现我们追求的世界。”(41)约翰·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这是一个人类主体栖居的意义丰富的符号世界,为了建构这样一个世界,我们不能偏执于数据理性和优化决策,仅仅考量智能算法的技术维度;对智能算法的道德和伦理规约同样重要,因为它关切的是人类主体自身。而人类主体的道德感就来自于符号意识——每一个主体都是符号并与其他符号形成共在主体性,这是一种超主体性的“人类责任”意识,只有通过“符号具身”行动,在认知和解释符号意义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性才会显现出追求终极价值和真理的伟大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