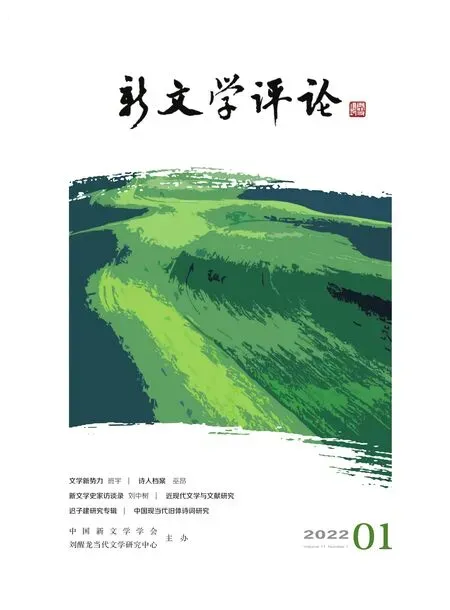日常生活诗学及其伦理本真性
——论迟子建的《烟火漫卷》
□ 王思远
1986年,迟子建在她的《北极村童话》一开篇写道:“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①三十余年来,迟子建始终怀着如斯的真纯写作,那种无法割舍的至情至性的童话气质是她始终如一的浪漫情怀,是她的血脉所在。北极村的那个小姑娘“灯子”(抑或是作家本人),这一“极地之女”(戴锦华语)从北极村出走闯荡,曾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自然与历史的灵性之中跋涉而来,走入伪满洲国仓皇的历史之中去反复质询,她见证了“白雪”与“乌鸦”的坚韧与恐惧,也品味了来自“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痛苦与哀矜……最终她在哈尔滨这座北国之城落地生根。三十年过去了,迟子建无可避免地要对哈尔滨,或者说她自己“成熟丰满的今天”说点什么,这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终于在《烟火漫卷》中展示了它全部的泪光,和全部的生活景象。
《烟火漫卷》中,俯拾皆是的是哈尔滨的日常生活:清晨时刻蔬菜批发市场的讨价还价、早点摊儿前的热闹景象,或者夜幕低垂前菜市场的喧嚣、饭后人们久违的休闲时光……但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像语言一样,日常生活包括了表现形式和深层结构,深层结构蕴含在日常生活的活动中,贯穿在日常生活之中,隐藏了起来。”②庸常而不庸俗的日常生活正是《烟火漫卷》得以展开的语言形式,在伦理、自然与城市的语言经纬之中,潜隐着的是迟子建一以贯之的真纯理想,是一种在日常书写之中重建伦理本真性的冲动。
一、 寻找:日常生活与伦理本真性的建构
与其说刘建国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不如说他是引线一般的存在——这部不足二十万字的小说所塑造的十余个人物都经由他而相识相知。小说中,刘建国倾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曾经弄丢了的好友于大卫的孩子。但就小说文本而言,迟子建却并未过多着墨于刘建国寻找孩子的过程,每次提及也只是寥寥几笔带过。如果回看小说的开头之处,刘建国甫一出场,他就已经是寻找了数十年而不得的花甲之人。数十年的寻找作为故事出现而成为刘建国这一人物的前史,而他一生中寻人的主体部分则被迟子建浸于小说未及叙述的冰山之下。
显然,这种文本的处理方式提示出迟子建并不意在书写一个通俗意义上的“寻找—找到”的都市寻人传奇,因而她也就并未过分渲染刘建国这三十余年来寻人的苦痛。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小说中设悬解谜的叙述方式则只是文本的外壳。在这一皮相之下,莫不如说,刘建国的一生,其内在实则是一个关于寻找本身的象征。换言之,寻找这一动作已然成为刘建国生活的同构形式,从而替代了他应有的日常:刘建国驾驶爱心救护车用以温饱的工作乃是因为这种工作形式更便于寻找孩子;而他固执地认为那个当年丢失的小孩会继承于大卫的音乐才能,因而本是用于消遣生活的音乐会也成为刘建国用以寻人的重要线索;甚至小说中黄娥、翁子安得以找上刘建国,则也是因为他的“寻找故事”已经众所周知。寻找这一行为已经统摄起刘建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刘建国之所以是个远近闻名的好人,则是在于寻找背后所附带的强烈的伦理动机——正是已经成为一种伦理行为的寻找,刘建国奔忙的一生也才具有了意义。
然而,刘建国寻找之伦理的中断却是小说中相当悲剧性的时刻之一,即刘建国在好友于大卫的口中竟意外得知了自己日本遗孤的身世,只有在这时,刘建国才“彻底放下寻找铜锤的念头”,因为“他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③。刘建国一生都服从于一种他者的伦理学,为了弥补内心的歉疚而为他人寻找一生,结果到头来丢掉的却是他自己的来处。而更具有讽刺性之处在于,当刘建国放弃寻找之后,那个他终其一生也未能找见的孩子铜锤却主动出现在他面前,且正是早已出现在他生活之中的翁子安。至此,刘建国的寻找才真正终止,这背后的伦理之重也才在他拥抱着翁子安的痛哭之中被释放,寻找及其伦理所替代的生活也在这时得以中断。身在兴凯湖隐居的刘建国,才忧伤地和于大卫说:“该说的我都说了,以后就别打电话了。”④刘建国想要彻底告别这种伦理所替代的生活形式。
隐居显然是极富象征意味的行为,告别哈尔滨熟悉的人情与日常,自然也就是要告别这背后的伦理生活。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建国选择去兴凯湖隐居的根本原因却来自他另一种伦理上更隐秘也更深沉的负罪感,即他当初对幼年武鸣所实施的猥亵行为所带来的心灵负重。这种同性之间的禁忌伦理行为,无论是在这部小说中,还是在迟子建以往的书写谱系中都是相当突兀的存在。按照小说中所言,刘建国是在酒醉后将六七岁的小男孩武鸣错认为了自己的初恋女友,但在此之外,这一情节是否能够在人物本身的历史中获得更为内在的解释?显然,作为一个以自己的一生为代价来寻找伦理救赎的人,刘建国始终都未曾获得一个真正的答案,即他自己究竟是谁?然而,这一答案真正到来之际,却反而带来了更为悲怆性的反讽,他所以为的一切都被强制性地更替,或者说抹除。血缘以其无可更改的规定性力量,将刘建国抛入了前历史的深渊之中。或许是日本人这一身份所具有的苦难深重的历史之重,也或许仅仅只是丢失了自己大半生生活的过分之轻,刘建国毕生以寻找来救赎自我的伦理歉疚最终却为另一种伦理原罪所替代。因而,刘建国这一同性行为的发生,以及最终他做出的与武鸣共度余生的决定,或许在个体救赎的意义之外,同时还象征着他对自我历史的一种阉割。日本遗孤这一来自父辈的无法抛弃的前历史,最终只能由隐居这一方式所封闭,断绝缠绕自己一生的伦理生活,和业已疯癫的武鸣遁入无历史的生活。这是刘建国所找寻到的解脱之道,无论是那个弄丢孩子的伦理之罪,还是日本遗孤的血脉,都只有在这一刻才能象征性地中断。隐居提供了一种逃逸出伦理生活与血缘前历史的可能,但刘建国的隐居乃是为了弥补对武鸣的罪孽,因而也就仍在另一种伦理的支配之下,小说的结尾为此而唱响了全书最为抒情性的时刻:黄昏时分,刘建国与武鸣两个男人在夏里亚宾所歌唱的苦难中传来了微弱的哭声。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在《暗店街》的结尾,主人公拿出了一张相片,上面是一个小女孩,莫迪亚诺这样写道:“薄暮时分,小姑娘随母亲从海滩回来。她无缘无故就哭了,因为她还想再玩一会儿,她走远了,到路口已经拐了弯;我们的一生,不是跟孩子的这种伤心一样,倏忽间在暝色中消失吗?”⑤《暗店街》的主人公也始终在寻找自己的身份,结果到头来不知道自己所找寻到的一切,究竟是自己的历史,还是一场虚构的空无?显然,刘建国也遭遇了这场困局,他和武鸣的哭声,就如同相片中那个小女孩的哭泣一样,伴随着小说的结束而“倏忽间在暝色中消失”了,并因而成为与伦理和解的可能与不可能的一种隐喻。但略显不同的是,刘建国在回望自己一生的寻找之后,却顽强地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隐居决定,他迫切地要在虚无之中建立自己的肯定性。
相比之下,黄娥的寻找也同样建基于一种伦理学之上,即她与丈夫卢木头之间心照不宣的情感契约。黄娥认为是自己的背叛气死了丈夫卢木头,因而须得以死抵偿,然而又不能抛弃儿子杂拌儿不管,她必须虚构出一个寻夫的故事来为杂拌儿找到未来的托付。表面上黄娥对卢木头的假意寻找,实则是为杂拌儿寻找寄托,这一寻找故事对赴死的延宕,来自婚姻与亲情的伦理,最终却将黄娥置于更大的伦理危机之中。她不仅感觉“丈夫在她假意的寻找中,竟蒙骗了所有善待她的人,也令她倍受良心的折磨”⑥,而且她在延宕之中始终不忍“赴死”,这也成为对她更深沉的伦理质问。
伦理在刘建国与黄娥的或真或假的寻找故事之中,成为他们的生活本身,也构成了他们活动的全部动机。他们的日常生活无法离开伦理的规约,他们每时每刻都要接受伦理的诘问与质询,同时他们也为这种伦理做出了自我的决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本真性的伦理。
本真性(authentic)是伦理学意义上相当重要的概念,可以说,这是西方个人主义和现代性的渊薮之一,这里不妨借用查尔斯·泰勒在《本真性的伦理》中讨论“自我的本真性”的观点。在泰勒看来,本真性乃是现代文化所独有的,是当代文化自18世纪末以来大规模地主观转向之后的产物,它将“自我”视为一种有内在深度的存在物,并在卢梭“自决的自由”的思想背景之下,强调对自我的原发性保持真实,并以自我来定义自我⑦。而值得注意的是,泰勒指出,这种本真性文化的中心被放置在日常生活之中,需要在私人领域的关系间得以实现⑧。可见,本真性的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之中的一种自我实现的纯粹理想。无论是刘建国寻找铜锤的真情一生,还是黄娥向死而生的假意寻找,都是在一种日常的伦理关系(亲情、友情、爱情)之中得以展开,并向着本真性而前行。
二、“我们与鹰的距离”:自然的本真性
黄娥显然是迟子建心心念念的自然的遗留之物,或者说自然之子,她从那个“不能被地图上找到的”七码头渡舟而来,仿佛跋涉过额尔古纳河右岸,来到大城市哈尔滨,为的是要托付孩子杂拌儿,好放心地追随已逝的丈夫而去。但她这一哈尔滨的外来者,又不可避免地随着作为前现代的来处七码头的衰败而丧失灵性,最终落入自然与生活的混沌之中,回到七码头的生活。
还在七码头的时候,黄娥觉得“能和岸上垂下的树枝说说话,跟河里的鱼儿说说话,跟灰云中的飞鸟说说话”的那种生活非常美好,而且,“非得是独行时刻,才说得出口”⑨,她享受与自然独处的感觉。来到哈尔滨后,也只有她,能读懂刘光复弥留之际给刘建国发的短信“基督的血,门神的泪”的含义,她知道那是有关生死的人生体悟。显然,作为自然之子,黄娥携带着前现代的神秘与灵性来到哈尔滨的现代历史中,她身上始终存在着与现代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特质:在榆樱院生活时被投诉、在市场做工时又总是给客人高点秤而被辞退、刻舟求剑式地要记录下这座城市的日常却又总是被抛在后面……同时,黄娥对待性的态度,也使得她在自然这一意义上成为迟子建笔下的女性角色的异质:“黄娥说她不是水性杨花的人,可是在风雨中航行,她格外渴望男人的怀抱。”⑩在送客途中与男人偷情后,黄娥和卢木头会心照不宣地以自己的方式化解这件事带来的尴尬。她的那些在刘建国看来不可理解的生活,卢木头却完全可以理解——他不能接受的只是情感共同体上的背叛——卢木头被气死也是因为黄娥主动去找刘文生。这一切正在于卢木头与黄娥在七码头有着完全不同于作为城市的哈尔滨的一套生活逻辑,现代性只能理解现代性自身,而所谓不可理解的生活,乃是因为其溢出了现代性所能理解的范围。
黄娥将丈夫卢木头的尸体丢进鹰谷,这一类似天葬的悼念仪式将卢木头重新放归自然。黄娥最终决定要以死来追随丈夫,这里黄娥赴死的冲动与延宕相当值得玩味。在海德格尔看来,死亡乃是一种置于面前的需要领会的终结现象,作为永远面向自身的展开,以及完全逾越此在的不可能,死亡才绽露为“最为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一种“与众不同的悬临”。正是在死亡的催促之下,人的存在才得以被筹划为一种本真性的存在。黄娥为自己书写了死亡的敕令,她在哈尔滨的生活全然都是在一种向死的冲动之下的规划,这毋宁说是一种本真性的追求。黄娥作为小说中最为临近自然的角色,正是在向死而生之中,将自我置于一种本真性的生存论之可能性之中。黄娥的赴死计划并非海德格尔所怀疑那种“为他人赴死”的代理,而恰恰完全是黄娥自己的此在的存在,是一种“亲自”的冲动。无疑,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死亡,乃是生存论意义上的一种绝对追求与领会,黄娥因卢木头之死而具有一种向死的本真性冲动,这样一种纯粹的理想追求似乎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为继,“随着在哈尔滨待的日子久了,她悲哀地发现,这个原本她视为生命最后一站的地方,竟俘虏了她。她恋上哈尔滨,或者说依然贪生,似乎已无勇气殉葬了”。黄娥对死的延宕,可以说是海德格尔所谓的“逃遁”,或者“沉沦”,是面向日常生活的一种下沉,但同时,黄娥为此而感到的悲哀情绪却又唤起了她对本真性的留恋与伤感,并从反面显示出了她对死亡的自决之自由。迟子建并未将黄娥的自然历史书写为绝对纯粹之物,它浸染了日常生活的跌宕与起伏,却又保留了本真性的理想与冲动。
与之相应,那只小鹞子,那只或许是从《候鸟的勇敢》中飞来的雀鹰,则是对自然的本真性更为寓言化的展现。雀鹰显然是自在而自为的自然之物,它在迟子建的这部小说之中几乎是唯一被写作的动物,因而也就更显意味。这只本应归属于自然的生灵,从莫名之处跌入城市之中,它似乎时刻都有着一种通灵的状态:它叼来卢木头的帽子,喂养榆樱院里的猫,甚至还能辨别出老郭对黄娥的别有用心……它显然是自然灵性的象征,但同时,“通灵”却也意味着它已经置身于人类伦理的内在之中。黄娥起初惊恐地将它认成是讨债鬼,是卢木头的索命,随后经由刘建国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她又认为或许这正是卢木头的保护神,雀鹰由此获得了完全歧异化的理解。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然作为一种与城市生活绝对的异质性力量而被如今眷恋城市生活的黄娥所恐惧,那么后者则是黄娥以其混杂自然历史与城市生活的方式来试图理解雀鹰。
在这一意义上,雀鹰也就因之而成为一种混沌之物,成为一种混沌化的自然。最后,这一只甚至不食喂养之肉的自然之鹰却死在了塑胶跑道上,尽管“那段塑胶跑道已被它搅得破烂不堪,但它终归没能再飞起来。它的翅膀张开着,还是飞翔的姿态……而它的头像一枚哨子,朝向黎明的天空”,或许可以说,这只雀鹰是黄娥这一人物的象征化表达,同为自然之子,黄娥无法切近的死亡最终由雀鹰来完成。然而,雀鹰的死亡将其凝固为一种飞翔的符码而宣示着自然逃逸此在的脱身法则,同时又以死亡本身来抒发对现代与自然的混沌的惊叹。
王德威在论及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时曾问道,“在我们度量与恶的距离时,如何想象、诠释善?”“鹤”这一从传统延续到现在的神话元素,乃是对善与生命高洁的象征,“我们与鹤的距离”,那是一种对至善的追问。如今,当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询问,我们与鹰的距离呢?《烟火漫卷》已不再致力于勾画善恶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每个人都带着恶的隐秘与善的冲动,也不意在围起一座前现代的自然之域——现代日常与自然历史在其中渗透交融。因而,或许这个距离会相当暧昧,我们时刻都涉足其中,又与之无穷遥远,这既是雀鹰的象征意义,也是“杂拌儿”这一名字的隐喻,与他血缘的驳杂一样,他也是现代生活与自然历史的“杂拌儿”。“杂拌儿”寓意着一种自然与日常的混杂,却构成了自然与现代城市之间一个微妙的连接,他被黄娥从自然中带来,再孤身回到自然中去,只留下一个背影,吸引着黄娥重返自然。黄娥母子的路径之中,现代城市成了自然的中转站,或者说,自然正以其本真性理想贯通了现代及其日常。
三、 城市书写与本真性追求
继《黄鸡白酒》《起舞》《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等作品之后,迟子建在《烟火漫卷》中再度触及了哈尔滨这座城市,这一次,她要为其建造“强悍的主体风貌”,并“独立地呈现”。城市文学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弱项,诚如陈晓明所言,“城市文学只是断断续续地以破碎的形式和他者化的方式在不同的阶段显现,没有一种完整的历史,也不可能有其完整的自身……只有关于城市的感受,关于城市的书写愿望一直存在,我们只是追踪那些感受、那些愿望”。《烟火漫卷》当然并非完美的城市文学,但在阅读了哈尔滨的城史之后,又在这座城市生长了十余年,迟子建确实有着前所未有的为其写作的愿望。可以说,《烟火漫卷》如同一次哈尔滨的城市巡礼,或是为哈尔滨的当代史做序,迟子建选择直面这座城市的首要方式就是直面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不难发现,对哈尔滨的城市风情,包括著名风物,历史建筑乃至街头巷尾的散文化描写,在这部小说中占有不少的篇幅,这种细腻的散文化笔法,确实是迟子建所擅长的方式,但就一部小说而言,这种方式就显得有些散漫,迟子建显然对此不无考量,因而她着重之处往往是那些城市与人物之间的关联地带,毕竟正如理查德·利罕所言:“城市经常以换喻的方式现身,比如体现为人群。”
首先是在城市风貌的平面意义上,迟子建勾勒了一幅哈尔滨的城市地形图。这不仅仅在于小说中黄娥为杂拌儿所写作的那个小册子,而更在于小说中的人物都以他们的视点与关切而切近这座城市运行的肌理。曾经“不信上帝和神明”的黄娥,因为要托付杂拌儿,而带着他游历了哈尔滨的寺庙与教堂,正如黄娥这个角色始终与神性相连;于大卫在误认了那个速写老建筑的中俄混血青年后,才开始关照老建筑的局部,他转变了看待世界的方式;更不用说开着“爱心救护车”的刘建国,他移步换景,走过松花江,也走过兴凯湖,他始终都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就好像榆樱院这一糅合中国传统合院式和西洋建筑特点的空间,也以其“朴拙的顶”,来“告诫自己和提醒世人:我是谁”。“我是谁”这一艰难的质询早已在刻写在刘建国的每一次远行之中。哈尔滨的城市地理正是在不同人物的多线程视野之中而被徐徐展开,每个人物各司其职,导览着专属于他们的城市风貌。
其次是在城市历史的纵深意义上,迟子建让哈尔滨的历史变迁成为人物的内在构成。于大卫的犹太后裔身份、谢普莲娜的家族史、刘建国作为日本遗孤,以及杂拌儿的父亲卢木头的蒙古血统,都让小说中的人物与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起了深刻的历史勾连,并深刻地对应着这座北方城市百年的历史变动:帝国政治、民族国家的建立、二次大战、种族迁徙……李永东认为,“由于聚焦于族群身份和个人家世,小说对殖民、抗战、反帝等城市历史重大事件等书写,便从民族国家的宏大书写模式中逃逸出来,转化为家世背景、个人身份、血脉亲情的生活叙事。由此,哈尔滨的历史叙事与‘烟火漫卷’的当下日常生活书写,毫无违和感地交融在一起。”确实,深沉的历史叙事因而被引渡到了具体人物的日常生活,哈尔滨的城市书写的日常性也因此得到凸显,这座城市的当下日常就是盘根错节的历史源流的结果,它有着足够的吞吐能力来消化浩渺的历史变迁。
哈尔滨的日常既有着平面的展开,也有着历史的深度,因而一种立体的日常生活诗学就得以形成。在这一意义上,《烟火漫卷》获得了一种哈尔滨的城市书写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哈尔滨的城市空间也因之而成了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叙述主体。迟子建在小说中显见的两套笔墨:一是散文样式的哈尔滨风景书写,另一则是小说样式的人物故事铺叙,二者互为表里,现代小说所追求的意义深度和中心主体因此而弥散开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烟火漫卷》与赵树理的《三里湾》一样,“并不存在一个统摄小说世界及其意义构造的中心人物”,因而地理空间成为小说的主体构成。但与《三里湾》当中“每个人物只有被置于某种组织单位之中才有意义……内在是‘空无’”又明显不同,《烟火漫卷》中的城市空间与人物叙述彼此叠印,两者彼此交融,在城市的日常之中人物展开他们的命运,而在人物的命运之中城市的日常才得以运行,这也是迟子建小说散文化特质的一种表现,她的叙述的涣散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另一种小说经验。正如谁来为这城市的清晨署名?谁又来为这城市的夜晚落幕?都是这城市当中的生灵,城市在其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生成,自我书写着自己的当代史。
正因在《烟火漫卷》中,城市与人物乃是具有同等位置的书写主体,二者因而也就共享着同一种认知逻辑。首先,城市的历史与现实都获得了一种日常化的理解。正如于大卫开始以一种局部的视角来重新理解他所熟知的哈尔滨的建筑群落,局部则意味着不再具有整全性,也就正如哈尔滨纵深的历史进程始终要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之中得以牵引流转,历史化约为日常的形式与肌理。其次,城市的自我质询同样被贯穿在本真性的理想之中。榆樱院对“我是谁”的追问,这一问题同样也贯穿于刘建国、杂拌儿等人的一生,回答“我是谁”,就是要对自己真诚,确认自己的真实与本真。因此,哈尔滨这座近代历史当中交错纵横的风云之城,也是在迟子建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之中,执着地获得了一种本真性的追求。
四、 日常与伦理:重建本真性的冲动
李洱在论及日常生活的诗学形式时曾说:“命名其实就是一种穿透能力。当你试图对生活进行命名的时候,这种写作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在李洱看来,穿透日常生活的困难就在于其当下性的变化难以把握。迟子建在《烟火漫卷》中显然也直面了这一难题,伦理、自然与城市三者之间的混杂交错,共同催生了《烟火漫卷》中的日常生活诗学的生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简单的对抗、冲突或彼此区隔,而是共同为现代性潮流裹挟,而相互交融,从而展现出一种混为一体的混沌状态。所以,《烟火漫卷》中迟子建所书写的烟火人间,其间的日常生活正是一种悬而未决的混沌之物,其内部不是对抗,也不是顺从,而是暧昧的交融。
《烟火漫卷》直面了日常生活的复杂性,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迟子建重申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正如陈培浩所言,“人们通常忽略了看似‘透明’的写实机制依然是一套充满符号中介性的叙事机制”。因而他认为,《烟火漫卷》中写实的艺术运思同样体现在小说中作为叙事装置的护送车、榆樱院和小鹞子。从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来说,“装置”在现实主义书写当中的使用当然是一种重要的思路;但现实主义的“非透明性”还不止于此,“在现实逻辑的规定中运思”之外,在主题上,作家势必要为其所书写的现实灌注进强悍的主体意识,而以作家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去统御他所面对的现实。
面对日常生活的变动不居与含混复杂,迟子建显然不愿意落入任何一种窠臼之中,无论是新写实主义对日常琐屑的关注以及以此构建的与宏大叙事的二元对立,还是以自然之名对现代性生活所作出的简单化约的道德主义批判,迟子建显然都与之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迟子建依然如她一直以来所选择那样,不被任何一种潮流所归纳而游走在写作的边缘地带。她要直面烟火,直面生活的混沌与复杂,但她又始终不愿意放弃她一以贯之的向善的上升力量,也就是所谓的“悲伤与苦难之上,从不缺乏人性的阳光”,由此,小说中的理想主义也就因之而显现。刘家三兄妹的理想主义情怀是小说中最为柔韧的核心力量,哈尔滨城无论有多少阴影,都无法掩盖他们的星火:大哥刘光复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也想着那部为哈尔滨的物景人情所拍摄的纪录片;老二刘建国为好友奔走呼号三十余载只为寻得当年丢失的幼童;老三刘骄华从狱警岗位上退休,仍旧惦念着的是如何帮助出狱之人谋求生路……不仅如此,黄娥向死的冲动、杂拌儿复归七码头的选择,无一不体现出迟子建在人物身上寄寓的本真性的理想。这是迟子建突入现实的日常烟火,而又得以以文字获得“越过云层的晴朗”的原因。
然而,本真性所具有的现代性的一种隐忧即是个人主义的陷阱,迟子建没有让她笔下的人物成为失真的理想英雄,而是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展现自我的追求;她同样也没有在单一的现代性维度来书写他们的故事,而是正如泰勒所强调的,在伦理关系当中来寻找本真性这种理想的可能性与肯定性,从而避免滑向柔性相对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淖。因此,在刘建国无望而反讽性的寻找中,在日本遗孤自我阉割的历史中,在黄娥的来于自然又重归自然的向死而生之中,甚至在榆樱院混杂的建筑风格与各色人物之中,可见的是迟子建重建伦理本真性的强大动力。正如李敬泽在评论《烟火漫卷》时曾说道:“整个小说能够把我们串起来,能够让我们跟上去的,就是看到这样一个一个封闭着的人,看到各种机缘碰到以后,在哪个缝里忽然打开,甚至在互相打开里互相照亮,能够意识到这个时候我的生命,尽管我是这么卑微、这么贫乏,甚至这么不靠谱,我最后还是做了一个好人。而这个好人不是别人评判的,不是给你发个匾,是自己能够对着天,对着自己的心说我是个好人。这是我看这个书的时候最为感动和最为打动我的东西。”所谓“自己对着自己的心”,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私密而又相当日常化的体验,它与任何宏大的历史与未来都无关,而只关乎我们自己。但同时又正因为,道德之所以是道德,乃是因为它是每个人内心中的准绳,因而这又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伦理理想。《烟火漫卷》中的每个人物都缘起于一个强大的伦理动机,并在对伦理本真性的追求之中,叩问自己的内心,去重建一种自我实现的崭新理想。
泰勒曾说:“如果本真性就是对我们自己真实,就是找回我们自己的‘存在之感觉’,那么,或许我们只能整体地实现它,倘若我们认识到这个情感把我们与一个更宽广的整体连接在一起的话。在浪漫主义时代自我感觉和感觉到属于自然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或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或许,一种借助公共被定义秩序的归属感的丧失,需要用一种更强烈的、更内在的归属感来补偿。”“整体地实现”与“更内在的归属感”,这正是《烟火漫卷》面对混沌的日常现实所生发出的执着的浪漫理想,这种对伦理本真性的呼唤与追寻,这种直面日常现实的勇气与担当,正是这部作品的动人之处,那是对无法到达的本真性的渴望,那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介入与质询。
迟子建在后记中提到自己始终无法忘怀那一条“谋杀”了雀鸟的塑胶跑道。那么,到底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塑胶跑道?它是人工的造物,又是走向自然的通道;它区隔、保护我们,又吸纳、接收我们。这就是混沌的日常生活,然而生活之上,亦有烟火。以伦理本真性之名,《烟火漫卷》重新命名了一种烟火,烟火升空,首先迎来的不是熄灭,而是照亮人间。
注释:
①迟子建:《北极村童话》,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
②列斐伏尔著,叶齐茂、倪晓晖译:《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44页。
③迟子建:《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67页。
④迟子建:《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98页。
⑤莫迪亚诺著,李玉民译:《暗店街》,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1页。
⑥迟子建:《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9页。
⑦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本真性的伦理》,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2~38页。
⑧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本真性的伦理》,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6页。
⑨迟子建:《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页。
⑩迟子建:《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