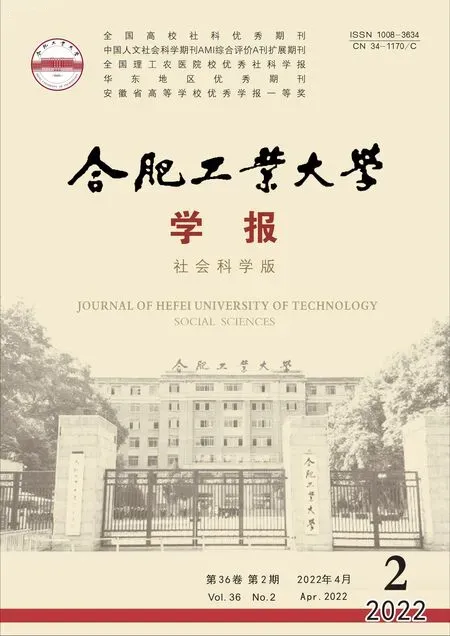日记体·疯癫形象·“吃人”意象
——鲁迅《狂人日记》与安德列耶夫《红笑》之比较
涂 旭, 卢志宏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提到鲁迅《狂人日记》的创作渊源,最先浮出脑海的便是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这不仅因为两部作品书名相同,更源于鲁迅曾明确表示过《狂人日记》受到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但同时鲁迅也将自己的作品与果戈理的作品进行了区别[1]246-247。事实上,细读文本就会发现,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只是在书名、小说形式以及结尾的“救救孩子”等方面给予鲁迅以启示,而实际上与鲁迅《狂人日记》最相似的作品是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的小说《红笑》。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列耶夫(1871-1919)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小说家、剧作家。鲁迅与安德列耶夫之间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这时鲁迅就已经阅读过译成日文的安德列耶夫的作品。1908年,鲁迅根据德文转译了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谩》(又译为《谎言》)和《默》(又译为《沉默》)。1921年,鲁迅又翻译了安德列耶夫的两篇小说《黯淡的烟霭里》和《书籍》,并在译后记中对安德列耶夫做了简单的介绍:“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2]172周作人曾记载鲁迅最喜欢的作家是安德列耶夫[3],最重要的是鲁迅自己也明确表示安德列耶夫对自己的创作产生过影响[4]。
至于《红笑》,早在1909年鲁迅就阅读过,并评价:“长篇有《赤咲》一卷,记俄日战争事,列国竞传译之。”[2]172后来,鲁迅还亲自翻译过《红笑》的部分章节,以及校阅过梅川翻译的《红的笑》等。虽然鲁迅未曾直接指明《红笑》与《狂人日记》之间的关联,但两部作品是存在影响关系的,帕特里克·哈南[5]、雷纳特·兰德伯格[6]等学者已经有过研究,暂不赘述。本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这一方法,对《狂人日记》和《红笑》的小说形式、人物与意象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旨在探讨两部作品存在相似之处的深层原因,以进一步理解两部作品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日记体二重奏:建构中的解构
日记体小说是采用不连续的日记片段结构故事的小说类型,它兼具日记的形式和小说的内容,但又区别于传统小说对“故事中心性”的强调,侧重于“情绪中心性”的表达。因此,如果选择用日记的形式进行小说创作,那么注定了小说情节的弱化,而更倾向于叙述者内心感受与情绪的抒发。《狂人日记》与《红笑》最直观的相似点是二者均选择了日记的形式,但与果戈理《狂人日记》中小公务员单一的叙述视角、标注明确日期的这种典型的日记体小说不同的是,《狂人日记》与《红笑》都是两部分构成,且由两个不同的叙述者讲述故事,没有标记具体的写作日期的日记体小说。
《狂人日记》于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7]。它由文言序言和十三则白话日记两部分构成,文言序言以叙述者“余”为视角,交代了日记的来源与内容;十三则日记则是以狂人作为叙述者,记载了狂人的心理活动。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自评《狂人日记》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1]246,其中“格式的特别”是就小说形式而言的,而“特别”之处在于,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打破了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和由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构成的小说模式。《狂人日记》以日记的形式展现了患有迫害症的狂人的精神世界,在现实、幻觉、梦境与回忆中反映了狂人对“吃人”现象的发现、深入探究和反省,以及对未来的寄托。《红笑》两部分一共十九则日记,第一部分的九则日记主要是哥哥记叙在战场上的经历:无休止无停歇的行军、战斗双方的厮杀、军队内部的自相残杀、不堪忍受者的自戕、伤残者在旷野里的呻吟等;第二部分的十一则日记的叙述者换成弟弟,讲述哥哥回家后“我”的感受:哥哥的疯狂与死亡、剧院起火的臆想、梦境中年幼的杀人犯等。《红笑》通过兄弟俩叙述自己的所见、所思和所感,以及俩人最后悲惨的结局,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性。
日记作为一种私人化写作,其目的不以满足他人为需求,故多记载个人生活的流程与内心的感受,因此日记的内容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与随意性。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安德列耶夫的《红笑》都选择由两个不同的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日记体小说形式构建文本,但两个叙述者构成的两重叙事中的矛盾之处也对小说的真实性进行了解构。
陈思和教授指出:“《狂人日记》里用两套文本,一套文言文,一套白话文,文言文是代表了现实世界的声音,而白话文则是代表了一个狂人的内心世界的声音。”[8]事实上,《狂人日记》不仅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且两个世界彼此之间相互消解与否定。在白话文日记中,发疯后的狂人成为了先觉者,洞察到了常人无法察觉的历史真相: “吃人”文明。但是在最开始的文言序言中,“余”却说日记“语颇错杂无伦次”,是“荒唐之言”,并且交代狂人最后也病愈去赴某地候补了。这样看来,若文言序言内容属实,那么狂人先觉者的身份不复存在,整个日记也只是狂人的臆想,小说的反封建意义也消失了;若日记中狂人的发现是事实,那么文言序言的真实性就存疑,而以“余”为代表的常人以及整个现实世界都仍然处于蒙昧之中。因此,《狂人日记》的两部分是相互矛盾且相互解构的。《红笑》的第一部分是哥哥的日记,前七则日记描述战场上的场景,后两则日记记叙回家后的生活。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哥哥在战争前线时还是比较清醒的,他是在回家后发疯的。但在第二部分中,弟弟却指出哥哥的话“时常很混乱”“前后矛盾”,这样弟弟的日记对哥哥的精神状态以及哥哥日记内容的真实性都提出了质疑。但同时弟弟又反复发出“我要疯了”“发疯”之类的呐喊,精神上常常产生幻觉,最后也确实发疯了。因此尽管弟弟对哥哥的日记进行了解构,但弟弟的日记本身就不具有可信度,所以小说的真实性在两部分之间完成了相互解构。此外,《红笑》还有一个副标题“残稿拾遗”,副标题显示出整个小说只是一份没有来历的、残缺的、不连贯的稿件,这样又从文本的材料对小说的真实性进行了一次解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狂人日记》与《红笑》的内部都形成了解构,但两者解构所产生的作用是有区别的:《狂人日记》是两部分相互解构,这使小说在反封建的檄文与疯子的胡言乱语之间摇摆,造成文本的割裂,而这恰是文本的张力所在;而《红笑》中,无论弟弟对哥哥日记的解构,还是弟弟日记的自我解构,又或是副标题的补充,它们都是在诉说同一个主题,即战争的残酷与罪恶。概括而言,《狂人日记》的解构使文本形成一种张力,而《红笑》的解构强化了小说的主题。
三、疯癫人物形象:以疯狂呼唤理性
疯,与癫、狂、愚、痴、傻等词语意义相近,一般定义为精神错乱、神经失常。而疯癫者因其异于常人的精神状态,故不受传统的社会习俗与伦理的规约,能够言常人不能言之语,做常人不能做之事。在文学历史中,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到《河边的错误》中的疯子等,从《哈姆莱特》中的哈姆莱特、《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到《简爱》中的疯女人等,无论古今、无论中西,疯癫形象一直是作家们创作的经久不衰的素材与题材。
鲁迅与安德列耶夫也表现出对疯癫形象的偏爱,他们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疯癫形象,如鲁迅《长明灯》中的疯子、《白光》中的陈士成、《祝福》中的祥林嫂和散文诗《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傻子等;安德列耶夫《墙》中的麻风病人、《谩》中的“吾”、《瓦西里·菲韦斯基这一辈子》中的白痴及戏剧《往星中》中的尼古拉等。《狂人日记》和《红笑》分别作为鲁迅和安德列耶夫的代表作之一,两部作品的主要人物不仅都无名无姓,且都是典型的疯癫形象。
《狂人日记》在开篇的文言小序中交代狂人所患“迫害狂”之类。日记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狂人患病时期非正常的心理活动而展开:开始,狂人发现赵家的狗、赵贵翁、小孩子和路人等怪异的眼光;然后,又发觉似乎所有人都怕他、都想害他;接着,狂人认为大哥表面上是请医生来诊治病情,实际上大哥是与刽子手假扮的医生合伙,借看病之名,实行吃人的密谋;最后,狂人又猜测妹子是被大哥、母亲以及“我”吃了,等等。由此可以看出,狂人常常通过别人的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进而幻想周围的人对他的迫害,所以狂人是一个符合病理学特征的精神错乱、敏感多疑、混淆现实与虚幻的疯子。与鲁迅《狂人日记》中单一的疯癫形象不同,《红笑》塑造了一个的疯癫群像:战场上军人们在烈日下厮杀、行军,一连十来天不吃、不喝、不睡,因此敌我双方都出现了比伤号还多的疯子,从战场上遣送回国的士兵因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也发疯了,而没有参加战争的人则都沉浸在战争的疯狂之中。《红笑》中的主要人物兄弟俩分别是战争背景中,上了前线与未上前线的但都发了疯的人群中的典型代表:哥哥亲历战争,双腿截肢后被遣送回家,想恢复正常生活而不能后陷入狂热的创作中发疯致死;弟弟关注报纸上的死亡人数,见证亲人朋友的发疯,他虽然努力保持理智,但也不免发疯的结局。兄弟俩殊途同归的命运说明了不仅是直接参与战争的人会发疯,甚至只要与战争有所关连的人也都会失去理性,走向疯狂。在大多数人眼中,疯癫往往被看作理性的对立面,但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其著作《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adnessandCivilization:AHistoryofInsanityintheAgeofReason, 1961)中,从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近现代三个阶段分析了疯癫与理性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同时援引多部文学作品为事例,以此说明疯癫与理性绝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9]。事实上,正常人变为疯子,这本来就不符合人们的常规认知,如果对发疯现象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发疯的表象之下潜藏的是人理性的迷失。而鲁迅和安德列耶夫的创作都说明了这一点,《狂人日记》和《红笑》都是通过疯癫人物的语言、心理,乃至疯癫本身强调理性的重要性。
狂人发疯后在“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的钻研琢磨精神下,发现了现实生活中与历史上的吃人事实,史册的每一页都写满了“吃人”两个字,四千年的文明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但是狂人发疯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吃人问题的提出,他又在“从来如此,便对么?”的问话中对世人习以为常的吃人事实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否定,表现出一种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精神。同时,狂人还规劝大哥和所有吃人的人改掉吃人的习惯:“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10]19并且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认识到自己原来也是这吃人中的一份子,即被吃者也是吃人者。此外,结合鲁迅曾说《狂人日记》的主题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1]247,以及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到“……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11]365。由此可见,鲁迅借狂人的发疯,不仅批判了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而且还企图唤醒愚昧无知的国民的理性,希望他们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敢于质疑与反抗的精神。
而《红笑》中,当整个社会因战争而陷入疯狂之际,部分人努力保持理性,试图以个人的力量与疯狂的世界对抗,特别是弟弟与反战演说者。弟弟看清了战争的真面目,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疯狂的大屠杀,“上百万人聚集在一处,互相厮杀”,而战争产生的根源就是人类理性的丧失,是一群疯子的聚集与狂欢。失去理性的人在战争中失去自我,变得冷漠、残酷、麻木不仁;失去理性的人承受着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创伤,却仍然甘之如饴地沉浸其中。长此以往,失去理性的人终将导致自我与社会的毁灭,恰如发疯的军医宣称疯人院将是我们的祖国。如果说弟弟是强调了失去理性的危害,那么反战演说者则规劝人们保持理性,“……摆脱这疯狂,保全你们自己,保全你们的后代”[12]316,保持理性不仅可以拯救自己,也可以拯救我们的后代与整个社会。虽然弟弟最后仍然发疯了,演说者也承认自己是疯子,但结合安德列耶夫所说:“《红笑》应成为对理智的一个独特的赞颂——这种赞颂,该说成是‘从相反方向’的。”[13]可以看出,作者正是通过他们的挣扎乃至他们的发疯来呼唤理性,他们虽疯犹荣。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两部作品实际上是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呼唤理性:《狂人日记》揭示狂人疯癫世界中的理性,《红笑》赞颂疯狂世界之外犹存的理性。除此差异之外,两篇小说中塑造的主要疯癫人物形象(《红笑》中特指兄弟俩人)也存在差异。
首先,发疯的过程不同。《狂人日记》开篇就指出狂人已经发疯了,随着狂人对“吃人”现象的深入了解,狂人的反应越来越激烈,狂人的病症也越来越严重。总结而言,狂人所有的变化都是其病症基础上的加重,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红笑》中兄弟俩的发疯是从清醒开始到发疯(乃至死亡)结束,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相较而言,兄弟俩从清醒到疯狂的过程更具有深刻性。其次,发疯的意义不同。狂人是在发疯之后发现封建文化“吃人”的本质,而一旦病愈了,狂人便回到常人的世界中了,也失去洞察历史真相的能力,故发疯是狂人作为精神界战士的先决条件,是小说的前提与开始;而《红笑》讲述的是兄弟俩竭力在疯狂中保持理性,但最后都发疯了,因此发疯是兄弟俩最后的结局,也是小说的结尾。从总体上看,狂人的发疯更具有精神上的意义,体现被压迫者觉醒的肇始,而兄弟俩的发疯更具有现实意义,小说正是通过他们俩从清醒到发疯而对战争进行猛烈的抨击。
最后,疯子的结局不同。若仅从“吃人者”与“被吃者”的角度来看,狂人与兄弟俩最后的结局是“被吃者”与“吃人者”的差别:《红笑》中的兄弟俩,一个发疯后死去,一个最后也发疯了,两人的命运是战争中普通人被吞噬的必然结局;而狂人病愈后去某地候补了,他继续与封建制度为谋,回归到他曾厌恶的“吃人者”行列去了。
四、“吃人”意象:现实与象征的交织
《狂人日记》和《红笑》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意象——“吃人”,它不仅指向现实层面的吃人,更喻指象征意义上的“吃人”。《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用狂人的思想与心理活动将“吃人”意象明白无误地传递给读者;而《红笑》中,安德列耶夫没有直接点名“吃人”二字,而是运用“红笑”意象取而代之。通常而言,“红”代表着一种艳丽或喜庆的颜色,“笑”表现出一种高兴与欣喜的情绪,因此“红笑”仅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愉悦、开心的笑,但是在小说中“红笑”却代指“吃人”。
鲁迅曾在《黯淡的烟霭里》的译后记中写到:“安特莱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2]201这段对安德列耶夫创作特点的总结与评价,说明了安德列耶夫这种将现实与象征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鲁迅比较欣赏的地方,而鲁迅也在其最初的白话文创作中试图运用这种创作手法。因此,现实与象征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既是安德列耶夫对鲁迅产生影响的突出表现之处,也是两位作家的相似之处。而《狂人日记》与《红笑》中的“吃人”意象便呈现出典型的现实与象征相结合的特征,“吃人”不仅是贯穿小说的主要线索,更重要的是小说的整体氛围与思想主题都是围绕“吃人”意象而展开。
首先,“吃人”意象的反复出现,为小说营造了一个阴森、恐怖与疯狂的氛围,也即鲁迅所说的“安特莱夫式的阴冷”[1]247。《狂人日记》整个行文都是围绕“吃人”意象而展开,主要描写了四种吃人现象:现实中,狼子村的大恶人被打死并挖出心肝用油煎炒了吃、徐锡林的心肝被炒了吃,以及用人血馒头治痨病等;历史上,典籍中记载“人肉可以煎吃”“易子而食”“食肉寝皮”和易牙蒸自己的儿子献给齐桓公等;心理上,狂人发现街上的女人打儿子时想要“咬几口”、哥哥与医生合伙打算吃“我”,而“我”也吃了妹子的肉等;文化上,子女割自己腿上的肉来治疗父母的疾病。此外,小说在叙述吃人的同时,也对小说的环境进行了描写,“很好的月光”“全没有月光”“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等等。昏暗的环境与“吃人”意象相映衬,不仅《药》的结尾留着安德列耶夫式的阴冷,《狂人日记》作为鲁迅的第一部白话小说,也营造出阴冷和恐怖的氛围。“红笑”是安德列耶夫的一个亲身经历:“今天晚上在我们别墅边炸伤了两个土耳其人,其中一个伤势异常严重,一只眼睛被炸飞了……他整个人就像一块抹布,满脸是血,他已经没有了记忆,很怪异地微笑着。大约是面部肌肉萎缩了,所以才出现了这个丑陋的、红色的微笑。”[14]安德列耶夫基于这一经历和报纸上的惨烈报道写成《红笑》一书。“红笑”不仅是小说的书名,也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要意象。“红笑”第一次出现在片段二的结尾,哥哥从那个中了弹的年纪比较小的志愿兵脸上看到了红笑,“而这个又短又红的、在喷着血的东西,似乎还挂着一抹微笑,一抹无齿的笑——红笑。”[12]245小说的结尾也是弟弟在遍布整个大地的尸体上看见了红笑。因此“红笑”,即流淌着鲜血的笑容,与之同时出现的是战争、流血、伤残、死亡和尸体等。此外,小说还反复渲染疯狂和恐怖情绪,反复强调疯狂和恐怖的氛围,同时还穿插着一系列荒诞而恐怖的事件,如士兵与亡魂共同参与的茶话会,弟弟与哥哥幽灵的对话,死人写给死人的信,等等。至此,小说中阴森、恐怖与疯狂的氛围油然而生。
其次,《狂人日记》和《红笑》的核心思想与主题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吃人”的象征意义表现出来的。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中写道:“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11]228而狂人从文化上发现“吃人”现象就是鲁迅这一观点的体现。狂人查阅没有年代的历史,发现“仁义道德”实际上就是“吃人”,此外狂人还从“割股疗亲”这种代表着传统文化的孝道理念中发现了吃人,由此可见,传统的道德理念反映出的是封建制度所形成的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与迫害。
最后,狂人还发现四千年的文明就是“吃人”的历史,每个人都是“吃人者”与“被吃者”,这更进一步揭示出在封建文化的长期统治下国民愚弱、麻木的精神状态和集体无意识“吃人”的社会。《红笑》中,哥哥在年轻的士兵的脸上看见红笑,军医在伤残的士兵的身上看见红笑,弟弟在粉红色的尸体上看见红笑,等等。红笑存在于一切残缺的、破损的身体之中,因此有“红笑”的地方就有流血,有“红笑”的地方就有杀戮,有“红笑”的地方就有尸体,而“红笑”产生的根源就是战争。此外,战场上的士兵被战争折磨成一群没有思想、没有意识,甚至是没有形体的影子,他们变得既小心翼翼、动作迟缓,又焦躁不安,但凡有一点声响就惊慌失措,而唯一可以刺激他们的神经的是战斗与厮杀,杀人使他们喜悦、兴奋。而战场外,流言、揭发和告密等层出不穷,报纸上一面通报数以万计人口的牺牲,一面又呼吁新的血液投入到战争中,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战争的疯狂之中。至此,“红笑”象征着战争对人类的摧残与迫害,即战争吃人的意义完全展现出来。
最后,虽然《狂人日记》和《红笑》都在“吃人”意象下营造出阴森、恐怖的氛围及表现出各自作品的思想内涵,但是鲁迅与安德列耶夫在具体表现上有着各自的特点。《狂人日记》中,狂人从最开始发现“吃人”现象到最后觉悟自己也是吃人中的一份子,整个小说被鲁迅设置在一个探索与追寻“吃人”与“吃人者”的框架之中,而随着狂人“吃人”认知的逐渐深化,小说的气氛越来越凝重,象征意义也越来越明显;而《红笑》以“疯狂与恐怖”开篇,从哥哥第一次看见红笑,到最后弟弟发现红笑结束,无论是恐怖氛围的营造,还是战争吃人的寓意的表达,安德列耶夫都是利用“红笑”这一意象将其直接、明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五、结 论
可以发现,前文从日记体、疯癫形象和“吃人”意象三个方面对《红笑》与《狂人日记》进行比较时,不仅指出了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也对它们的差异进行了简单的说明。不可否认,安德列耶夫对鲁迅存在或显或隐的影响,这也许是两部作品相似的原因,但模仿并不是创造,《红笑》和《狂人日记》作为两个独立的经典文本,鲁迅与安德列耶夫思想上强烈的共鸣,才是两个文本共通的真正原因。
一方面,安德列耶夫和鲁迅分别借《红笑》和《狂人日记》表现出对各自社会秩序的否定与批判。文学是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文学作品中也隐含着作者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态度。瑞典汉学家雷纳特·兰德伯格说:“鲁迅认为沙皇俄国正如中国一样处在黑暗和专制统治之下”[6],20世纪前后的俄国和中国有类似的社会背景,而鲁迅和安德列耶夫都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们分别用作品表达了对社会秩序的否定与批判。《红笑》完成于1904年11月,当时俄国正处于日俄战争时期和1905年革命前夕的紧张状态。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俄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红笑》直接批判了战争的残酷与暴虐,而战争的起源就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故《红笑》也间接地表达出安德列耶夫对沙皇专制的否定。《狂人日记》完成于1918年4月,辛亥革命并未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仍处于封建制度统治之下,人民仍深受封建文化的荼毒,而《狂人日记》正是鲁迅应“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兴起而作的一篇反封建的战斗檄文,借狂人之口揭露了封建专制的“吃人”本质。
另一方面,安德列耶夫和鲁迅分别通过《红笑》和《狂人日记》展现出“为人生”的文学观念。文学是人学,关注人、反映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俄国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15]443,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安德列耶夫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的《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在地下室》和《沉默》等作品就特别表现出对人的关注。鲁迅写小说的目的也是“为人生”和“改良人生”,这不仅与“五四”时期人的解放主题相吻合,更是因为鲁迅始终关心与怜悯社会底层的人民,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5]526。而这“为人生”的文学观念是安德列耶夫和鲁迅思想上的契合点。《红笑》关注战争背景下普通人物的命运和精神状况,批判战争对人的迫害。《狂人日记》通过狂人与常人的对立,狂人对“吃人”现象的探究,一方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艰难处境,另一方面反映出人的觉醒。
总体而言,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将《红笑》与《狂人日记》进行平行比较,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分析两部作品在小说形式、人物与意象等方面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两部作品的美学价值,并以此探究两位作者思想上的共同性,反过来也可以促进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