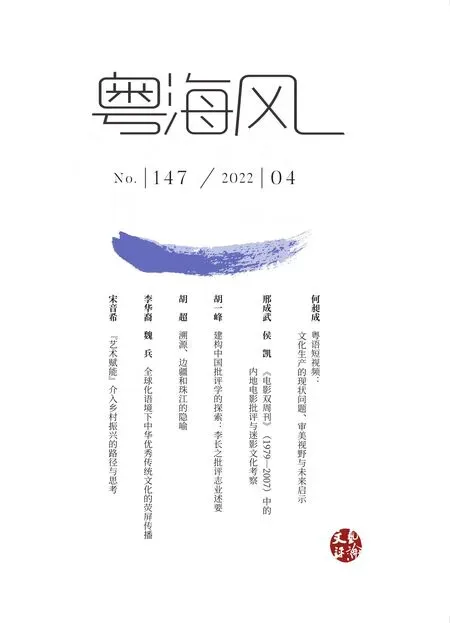近年新主旋律电影中的风景呈现
文/刘畅
风景是近年艺术研究中的关键词。米切尔(W. J.T. Mitchell)将风景看作一种象征体系,认为风景能够被嵌入到文化传统之中,激发并重塑意义与价值,因此风景不再仅是供人欣赏的审美对象,也成为一种能够形塑人们精神的文化实践。[1]在风景研究的文化转向中,作为自然物的“风景”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地,而属于框取风景的社会学的眼睛。电影是以形象进行表达的视觉艺术形式,倾向于以“潜在文本”的方式传递内容、形式及精神上的话语。风景正是这样一种内涵丰富的“潜在文本”,它是影片中“最自由的因素,最少承担实在的叙事任务,并最能灵活地表达情绪、感情状态和内心体验”[2],不仅可以作为叙事的空间背景、情节的引入和过渡出现,起着调整叙事节奏、渲染情绪氛围的作用,也能够脱离服务功能,与人物、故事以及影片的生产语境展开有机互动,成为独立存在的叙事元素。电影中的“风景”不同于“纯粹的大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马丁·列斐伏尔(Martin Lefebvre)认为,风景被视觉装置框取后可以实现审美愉悦之上的概念超越,即风景一旦成为被再现的对象,就被打上了主体意志的烙印,实现了从自然向文化的迈进,变为一种有意味的文化地理景观,能够表达某种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诉求。[3]正如Harper与Rayner指出,电影风景不是纯粹的现实记录,它受制于美学处理、技术改进和意识形态的规约,它承担着容纳文化意义、改进视觉审美风格及维护、宣传民族身份认同的作用。[4]在这一意义上,风景既有视觉上的美学意义,又与故事空间的呈现及文化内涵的生成密切相关,承载着丰富的价值意蕴。
风景历来是中国当代电影镜头表达与影像开掘的重要载体。随着中国社会与电影生态的变迁,以风景为代表的影像环境也承载了更多的可阐释空间。主旋律电影是中国当代电影艺术的重要类型,从广义上说,主旋律电影是“一切汇聚于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文化交流中的成功之作”。[5]在现代影视语境下,凡是以讴歌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流价值观为旨归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都具有主旋律的色彩。近年来,电影产业化和院线制改革推动了主旋律电影的转型发展,一种基于“主旋律+”的“新主旋律电影”[6]逐渐占据国产电影的重要份额,创作者以艺术审美与多类型杂糅叙事为媒介,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追求影片思想性与观赏性的统一,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的三分界限。在政治性、商业性、文化性与艺术性交融的新主旋律场域里,风景从传统意义上人物活动和事件发生的场景背景变为相对独立的“自主风景”[7],关联着影片审美空间的建构与文化价值的拓展。本文以近五年来国内上映的新主旋律电影为对象,分析其中“风景”如何通过叙事编码及影像修辞进入电影文本的复调场域,并以意识形态风景、文化记忆风景与视觉奇观风景三种主要样态有效参与到政治、文化与商业场域的建构与运作中。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风景
斐迪南·滕尼斯指出,共同体是“由本质意志推动的,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联系和组织方式,它以血缘、地缘和精神共同体为基本形式”。[8]在自然本性的推动下,以家族、社区和精神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族群具有同样的信仰和需要,以此建立起统一团结的集体,并形成渗透于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各个层面的“共同体艺术”。通过特定的物件、符号、仪式与场面,共同体艺术记录了一个族群的精神生活,激发、传达着特定的情感与观念,传达共同性、维护共同体团结是共同体艺术的重要功能。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国家历史或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电影也是承载民族精神的共同体艺术形式,民族大义、家国意识、友爱互助等共同体精神历来是渗透在电影血肉之中的审美追求。[9]作为弘扬社会正能量、传达主流价值观的视觉载体,当代新主旋律电影在“意识形态风景”[10]中寄托了形塑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期待。肯尼斯·罗伯特·奥维格(Kenneth Robert Olwig)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后认为,当风景与自然、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便具有了隐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11]通过建构民族物恋情结的象形符号与展现脱贫攻坚时代成就的影像载体两种样态,近年新主旋律电影中的风景发挥了共同体艺术的凝聚作用,因而成为建构民族“想象共同体”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巧妙地缝合了观众与影像世界的意识形态在心理或想象关系上的缝隙,促进了民族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一)建构民族物恋情结的象形符号
在民族危亡、国家危难之际,作为意识形态的风景表现为建构民族物恋情结的象形符号,在战争题材的主旋律影片中格外凸显。弗洛伊德认为,物恋是“被想像为失去了或可能失去的某物的替代品”,涉及主体形成过程中的匮乏、替代和认同。[12]上升到民族层面来说,当一个民族陷入主体性丧失的创伤情境时,意义和秩序的重建与填充需要围绕某种具有共同体意义的对象,这时符号性、仪式性的行动可以弥合现实的裂缝,风景就充当了这种角色。“物恋”的对象是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文化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隐喻与约定俗成的认知。生死危亡之际,人们需要寻找一种中介物来重建自己的民族身份感,以凝聚民族意识,对于中国人来说,长江、长城、黄河、黄山等风景意象带有民族认同性,它们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形符号,承载着意识形态的“询唤”[13]任务,将民族价值观念进行了实证化和物质化,并且使人们对这些民族价值观念充满快感地认同[14],在风景的感召下,“个人”成为“主体”,“家园”变成了“国家”。
战争题材主旋律影片有将风景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表达体系的传统。《中华儿女》(凌子风,1949)中已经使用富于象征意义的青松、白云高山等风景象征英雄牺牲的崇高和神圣,《上甘岭》(沙蒙、林杉,1956)也已出现借助风景传达保家卫国民族情怀的镜头语言。《长津湖》(陈凯歌、徐克、林超贤,2021)中风景的呈现继承了这一历史认同的传统,影片利用长城这一风景意象,表达了国家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朝鲜战争爆发后,伍千里重回战场,他的弟弟伍万里瞒着父母坐上了奔赴战场的火车。初次入伍的伍万里不适应组织纪律,在火车上逞强闹事,伍千里只好将他的授枪仪式取消,叛逆的伍万里固执打开火车门想要跳下车时,奇观化的万里长城映入眼帘,随着火车的移动,蜿蜒的长城披着朝阳不断延伸,看着壮美的祖国河山,伍万里和老战士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满足。万里转变了自己的态度,坚定了遵守组织纪律、投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万里长城和伍万里的名字形成了巧妙的对照,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长城的职责是守卫祖国边疆。作为长城的儿女,伍万里在民族受到威胁时,坚定地选择守护祖国。长城的出现起到了推进人物成长、推动影片叙事的作用,在长城的感召下,新战士在成长,民族精神得以凝聚。
(二)展现脱贫攻坚时代成就的影像载体
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意识形态的风景更多地成为展现脱贫攻坚时代成就的影像载体。据统计,截至2021年,我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5]城镇与乡村的界限逐渐消弭,乡村不再是城市的对立面,而成为与城市共存的新主体。在近年新主旋律电影中,曾经破败的农村风景呈现出美好明朗的新风貌,《十八洞村》(苗月,2017)中水墨画卷般的湘西风光,《又是一年三月三》(马会雷,2018)中清新质朴的壮族村庄,《我和我的家乡》(宁浩等,2020)中碧波荡漾的千岛湖、金黄遍地的稻梦空间,《一点就到家》(许宏宇,2021)里绿意盎然的云南茶园,不仅为观众呈现了祖国从南到北独具风情的山川乡野,也借此赞颂了中国人勤劳奋斗、百折不挠的时代精神。在这些电影中,明亮温暖的色调、意境开阔的航拍镜头、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的融合一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康时代影像,潜移默化地宣扬主流意识形态与传达美好生活理念的内涵。以明丽的风景展现取代直截了当的颂扬式话语体系,让观众在无意间再次体会党对人民幸福生活的引领作用,增强对国家发展的自豪感和对党的认同感,也向世界展现了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
《我和我的家乡》中壮阔秀丽的祖国风光是承载着意识形态的柔性表达策略。作为一部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家乡》创作的初衷是记录脱贫攻坚与新农村建设的时代成就,歌颂国家精准脱贫政策的先进性与正确性,但影片另辟蹊径地将镜头投向了祖国诗情画意的乡村景观,让诗意呈现的风景唱出了生动的赞歌。取景于陕西榆林市毛乌素沙地的《回乡之路》单元讲述的是这一地域防风治沙的生态建设故事,影片首先以灰黄的色调交代了这里过去的恶劣环境,教室里沙尘遍布,窗外是漫天飞舞的黄沙,在沙尘暴的映衬下,孩子们面如土色,毫无生机,暗示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关系。在村民的努力下,黄土高坡重新焕发了生机,导演运用明亮的阳光作为画面的主要光源,营造出宁静温暖的色调,将陕西人民焕然一新的生活环境展现得美轮美奂,在大俯拍镜头的切换下,笔直的公路与青翠的农田和谐共生,风力发电机、立交桥、火车这些象征着现代化的人文景观与喜人的绿茵地构成了一幅动人的风景画,上面写满了退耕还林还草、防风治沙建设的时代成就,反映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也奏出了一首热烈而婉约的家乡赞歌。
二、作为文化记忆的风景
作为一种文化机器,电影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影响着人们对于“时间”的记忆。争取电影对民族特性乃至民族历史的记录与“重写”,唤醒民族记忆与身份认同是发展中的现代民族国家电影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主题。[16]作为书写中国革命与改革历史的影像载体,主旋律电影是制造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来源,“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的红色经典影片创造的经典斗争记忆更是深深烙印在老一辈人们的脑海中。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潮流为文化领域带来了传统价值观的激荡,主旋律作品不再执着于创造宏大的集体历史记忆,而是致力于再现与传承那些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消散的个人与民族文化记忆。
卡尔·索尔(Carl O.Sauer)将风景分为“自然风景”和“文化风景”两个层面,前者强调风景的自然、物质形态,后者则是风景的社会关系形态,由媒介表达。[17]在新时代文化生态背景下,风景兼具自然风景与文化风景的双重属性,关联着文化记忆的构建与记忆资源的影像化再生产。作为影片的基本元素,风景搭建起了被回忆的物质世界,独特的影像符号将过去的行为导向与精神情感体验保存下来,以此展现本民族群共同的生产创造、生活场景与人文历史等文化记忆,借助影像传播框架的呈现,风景又被不断书写和重构,成为观众个人视野中的“家乡”的文化记忆符号,唤起了储存在人们心灵深处的记忆编码,特定的“乡愁”情绪被再次生产。近年新主旋律电影中以新农村、新民族为题材的作品格外擅长利用临摹性还原与诗意呈现的风景唤醒文化记忆、重拾心理认同,以“乡土”与“怀旧”为突破口,风景将地方的山川地貌,人们的风俗习惯、精神信仰和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结为共同的“凝聚性结构”[18],从而将不同的时空串联起来,让观众在不断回顾过往中感受乡村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寻找记忆中的情感点,并通过自我意识、自我记忆与之相关的现实语境关联在一起,此时,风景唤起的不仅是个体层面上对故土的思念,还自然地上升为群体层面对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衰落、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反思,因而形成了对民族传统与主流价值观的心理认同。
作为一部“抢救性”民族志电影,《远去的牧歌》(周军、阿迪夏·夏热合曼,2018)以半记录半虚构的方式讲述了新疆哈萨克民族在传统与现代、游牧与定居、生存与生态之间的矛盾与选择,记录民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巨大变迁的同时,深描其民族传统与历史,在对边疆自然风貌与风土人情的诗意描绘中构建了哈萨克的“影像民族志”[19]。电影将古老游牧传统的消亡凝结在四季景色的轮回变化之中,以四季景色变迁暗示时空关系与民族命运的改变,揭示了一个民族消亡与重生的心理变化过程。导演注重选取哈萨克代表性的景观元素展示“游牧文化”的历史、人文情怀与丰厚内涵,通过展现自然风景与文化风景的统一,将民族的自然之性与人类之性相融合,也将原始的草原游牧文化基因镌刻在影像中。航拍下的大俯拍镜头呈现出草原的广袤悠远与群山茫茫,马群、骆驼群、羊群、人群在迁徙中的景象配以优美的哈萨克音乐、民歌与舞蹈,深沉而朴素地营造了哈萨克游牧民族原生态的生活质感,这不仅是历史痕迹的记录,也是文化流传的抢救。
新农村题材主旋律纪录片《中国村落》(夏燕平,2019)通过对中国传统村落的自然风景、文化历史与民风民俗的诗意呈现,唤起了人们心中共同的集体记忆与传承愿望。其中《如画》篇将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有机融合,再现了新疆阿勒泰布尔津县、江西婺源簧岭村、安徽黟县西递村、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等遗落在现代文明之外的村落风景,并将其展现为中国的文化符码,在青砖黛瓦、绿水青山的西递村中,在崇高宁静、原始浪漫的乡城县中,在淳朴自然、沉稳传统的西湾村里,人与天地同呼吸共命运,耕读传家、天人合一、仁义礼智、忠义节孝的传统价值观也得到了审美化表达与传播。在乡村文明逐渐被现代化进程淹没的时代中,村落风景搭建起了文化记忆的空间框架,用具象化的符号传递着浓浓的乡愁情感。在这个共同的回忆场所之中,观众将个人经历与影像化的记忆进行叠加,追忆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发展历程,回忆着自己家乡的山水,引发了观众心底的思乡情感。
三、作为视觉奇观的风景
居伊·德波(Guy Debord)认为,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景观(奇观)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操纵杆。[20]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 SKellner)进一步指出,媒体奇观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特征,而电影自其诞生以来就是滋生“奇观”之地,在各种由电影制造的奇观中,最直观、最重要的还是“奇观电影”。[21]由于数字技术对电影的长驱直入,电影对风景的呈现也开始朝奇观化的方向发展,电影从利用风景,直接变成了表现风景。[22]长期以来,在承担建构主流意识形态任务的主旋律电影中,奇观这个带有电影本质属性的元素处于缺位状态,“板着脸、端架子,不鲜活、不自然”成为传统主旋律电影饱受人诟病的原因之一。新主旋律电影在坚持思想性的前提下,开始兼顾影片的艺术性与观赏性,风景的呈现向传统东方审美取“境”(意境),也在商业语境中造“惊”(震惊)。一方面,电影技术的进步与审美观念的转变为风景的呈现脱去了朴素的本色,无人机镜头、CGI制作、4K高清等数字技术的使用增强了风景的影像表现力,在东方古典审美观念的滋润下,具有民族特色的“诗化书写”使得风景展现出意蕴悠远而又别具一格的隽永之美;另一方面,糅合了灾难、冒险、惊险等商业类型元素的新主旋律电影借助模式化的非真实特效,将风景变为一种视觉消费对象。综合来说,盖瑞·特维(Gerry Turvey)对早期境况电影美学追求的界定正契合了当代新主旋律电影中风景奇观的特点:美丽(令人享受、使人惬意)、有趣(能够满足视觉上的好奇)和生动(具有活力的)[23]。对于新主旋律电影来说,审美化、奇观化的风景呈现不仅是其类型创新的突破口,更隐秘地成为传播国家意志的一种有效方式。
新主旋律电影通过中国古典韵味的风景影像创造令人陶醉的美丽奇观,建构影片的艺术审美空间。导演有意识地将风景的展现与故事的内核紧密结合,使用散点透视的镜头语言、卷轴式横移镜头、“移步换景”的空间叙事等具有东方艺术美的诗意手法,营造出主客交融、诗画一体的中国意境。《我和我的家乡》在回归纪实美学的基础上,创新摄影技法、光线运用及意境营造,为影像带来了丰富的质感与极强的观赏性。影片开头便以俯拍大全景的方式呈现了四幅魅力各异的风光图,从青山茫茫的黔南苗寨、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漠到清明澄澈的千岛湖、遍地金黄的稻梦空间,处处洋溢着人间温情与绿色发展交织的祥和氛围。其中《最后一课》叙事单元运用东方古典文化的写意手法,从画面构图、色彩、光影等方面还原了范老师记忆中的山野村庄,在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中凸显了浓厚的师生情。这一单元取景于千岛湖景区,大量的运动镜头与航拍取景塑造出开阔的大空间、大场面。在营造范老师记忆空间时,瓢泼大雨适时而来,冲淡了影片的彩色调,湖光山色、青竹荷花、溪水潺潺以写意手法与中和之美将中国传统美学的含蓄与静穆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以“主旋律+灾难”、“主旋律+冒险”为题材的新主流电影中,出其不意、变幻莫测的风景奇观提升了影片视听观感的真实性,在短时间内不断刺激观众的神经系统,带给观众早期“吸引力电影”[24]的“震惊”体验,进而与商业性、大众化接轨。《中国机长》(刘伟强,2019)以快速利落的剪辑风格、震撼人心的声音效果及好莱坞式惊险刺激的奇观画面呈现了时而壮丽时而危险的风景。飞机飞行过程中风景的三段式变化构成了影片视觉风格的美学传达,也是推动叙事的重要元素。飞机平稳起飞时,视野开阔的山水风光是高潮前的铺陈,飞机遇险时激烈的电闪雷鸣则将影片推向叙事的高潮,当飞机平稳迫降时,窗外出现了肃穆崇高的雪山之巅,叙事节奏重新归于平静,风景的奇观化呈现与影片叙事节奏的跌宕达成了和谐一致。
围绕影片建构的种种奇观风景不仅是电影技术与商业市场的成功,更是一次意识形态场域的胜利。“不论电影被视为是一种艺术形式、政治工具还是商业性企业,电影都旨在诉诸于尽可能多的观众,必须打入社会集体成员的意识中,利用集体潜意识,电影的商业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和审美功能才能奏效”[25]。审美化、奇观化的风景是新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表征,其直接抓住了观众的审美趣味,吸引观众纷纷走入影院,从而为主旋律的政治宣传与理念输出提供受众基础,这也正是主旋律电影利用风景粘合政治、商业与艺术的机制所在。
结 语
风景深刻影响着电影视觉风格与精神文化价值的建构。近年新主旋律电影通过不同形态风景的呈现,将“家园”变成“国家”,将“空间”化为“地方”,将“自然”变为“奇观”。在新主流的语境下,主旋律电影中的风景不仅能够作为意识形态风景参与国家形象认同的建构,也具有文化记忆风景的样态,发挥着“影像民族志”的独特作用,又能化身为视觉奇观风景,为观众带来持久的审美享受与感官震惊,由此风景从传统意义上叙事的背景变为具有丰富意味的景观式存在。在多声部风景话语的共同作用中,新主旋律电影的政治性、商业性、艺术性、民族性被缝合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因而实现了影片外在画面表象与内在文化意蕴的融合。在面临价值多元化严峻挑战的当下,以主旋律电影作品为载体,用中国方式表达中国话语,为中国电影树立民族文化形象,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以及中国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国际观,是未来新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方向,而风景作为一种电影艺术中稳定呈现的因素,能够在其发展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
[1][美]W.J.T.米切尔编:《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2][俄]C.M.爱森斯坦:《并非冷漠的大自然》,富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年版,第316页。
[3]Martin Lefebvre(ed.),Landscape and Film,London :Routledge,2006,p. xv,pp. 19—60
[4]Graeme Harper and Jonathan Rayner,“Introduction:Cinema and Landscape”,in Graeme Harper and Jonathan,eds,Cinema and Landscape,Bristol/Chicago :Intellect,2010,p.22.
[5]滕进贤:《增强责任感,为提高影片的思想艺术质量而努力——在 1989 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当代电影》,1989年,第2期。
[6]作者注:“新主旋律电影”是新阶段主旋律电影的特定发展样貌。新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越来越明显地趋于转向创作类型化和市场运作商业化,“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开始相互融合。近年来,“新主流电影”说法使用较多,在打破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三分的语境下,“新主旋律电影”基本相当于新主流电影。
[7]Martin Lefebvre,“Between Setting and Landscape” in Landscape and Film,Martin Lefebvre ed,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23.
[8][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65页。
[9]蒙丽静:《电影理论中的共同体美学渊源》,《当代电影》,2020年,第6期。
[10]作者注:张英进将以宣传政权为中心的意识风景称为“意识形态风景”。见张英进、郑焕钊:《民族文化,个人视野,多地记忆:当代中国电影的真实风景》,《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11]Barbara Bender,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Oxford :Berg Publishers,1993:p307—339.
[12]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页。
[13]作者注: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对主体的询唤(interpellation)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功能与运行机制。意识形态是抽象的,而以概念、观念、形象等形式存在,是阿尔都塞所说的“隐而不露的神秘角色”。只有在询唤下,个人成为主体,服从于意识形态所需要的物质实践,意识形态才能发挥作用。
[14]厉梅:《论抗战文学中风景的物恋性》,《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0期。
[15]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002版。
[16]张颐武:《历史/记忆/电影:时间之追寻》,《当代电影》,1992年,第3期。
[17]邵培仁:《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
[18]作者注:“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它起到的是一种连接和联系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社会层面和时间层面。凝聚性结构可以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其方式便是让他们构造一个 ‘象征意义体系’……它将一些应该被铭刻于心的经验和回忆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并且使其保持现实意义,其方式便是将发生在从前某个时间段中的场景和历史拉进持续向前的‘当下’的框架之内,从而生产出希望和回忆。”见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19]乔慧:《〈远去的牧歌〉:民族心志与历史宏图的诗意言表》,《新疆艺术(汉文)》,2020年,第4期。
[20][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21][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析》,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2]周宪:《论奇观电影与视觉文化》,《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
[23]TURVEY G.Panoramas, Parades and the Picturesque: The Aesthetics of British Actuality Film,1895—1901[J].Film History,2004(1):p9—27.
[24]作者注:爱森斯坦将电影对观众产生一种类似窥探癖式的感官效应称之为“吸引力”,它的本质是表现主义的。汤姆·甘宁在对早期电影的考察中发现这一阶段电影的独特之处是为了让“形象变为可见”,由此他称这些尚未成为叙事艺术载体的电影为“吸引力电影”(cinema of attractions)。在他看来,吸引力电影强调震撼或惊慑的直接刺激,并不关注叙事本身。
[25]吴琼:《当代中国电影的类型观念》,见杨远婴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文化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