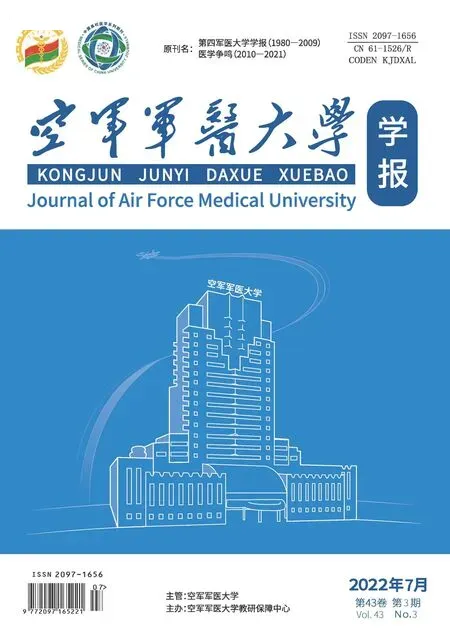间充质干细胞对类风湿关节炎的免疫调节作用研究进展
邹晓荣,苏 瑞,李 芳,王黎明,李世梅,孙 蓓,李 铭
(1空军第九八六医院肾脏病科,陕西 西安710054; 2陕西省组织细胞库,陕西 西安 710065)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以侵蚀性关节炎为主要症状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临床表现为关节僵硬、疼痛、炎症、活动受限以及关节侵蚀,可导致关节畸形及功能障碍,其病理基础是滑膜炎。该疾病也可累及关节外器官。RA慢性炎症以先天性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改变为特征,包括针对自身抗原的免疫反应、细胞因子网络失调、免疫复合物介导的补体和破骨细胞的激活等[1-2]。RA目前常用的治疗药物包括糖皮质激素、传统抗风湿药(disease-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DMARDs) 、生物制剂以及靶向分子类药物,这些药物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善RA活动性,降低RA患者的致残率,但依然存在患者不耐受、药物不良反应多、产生抗药性的可能[3-5]。随着近年来对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认识的加深,已有大量体内体外实验证实MSCs可通过抑炎反应、免疫调节和免疫耐受诱导等作用,缓解RA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这为RA治疗带来新的思路和方向。
1 MSCs对RA的免疫调节作用
MSCs是一种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及多向分化潜能的成体干细胞,其来源广泛,几乎可从所有中胚层组织中分离,包括骨髓、脂肪组织、脐带血、脐带、胎盘、经血和牙髓[6-8]。MSCs已被证实具有免疫调节、促进损伤修复再生、促进血管形成和防止纤维化等作用[9],特别是对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炎症性疾病的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例如MSCs能够抑制不同类型免疫细胞代谢,降低活跃分裂细胞的增殖率,从而抑制炎性因子释放,介导强大的免疫调节作用[10];还可促进单核细胞极化为M2巨噬细胞[11],抑制单核细胞向树突状细胞分化,并形成耐受趋势[12]。此外,在炎症条件下,MSCs在1型辅助性T细胞(T helper cell 1,Th1)、17型辅助性T细胞(T helper cell 17,Th17)[13]以及调节性T细胞(Treg)增殖方面的作用也被多项研究证实[14]。
RA的疾病特征主要为优势致病免疫细胞释放促炎因子,同时外周免疫耐受改变所导致的免疫应答缺陷。MSCs可通过调节来自先天免疫细胞亚群及获得性免疫细胞亚群的激活、增殖及分泌功能来实现对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治疗。
1.1 MSCs对先天免疫功能的调节
1.1.1 巨噬细胞 巨噬细胞可产生参与RA发病的核心细胞因子,包括目前生物药物靶向的肿瘤坏死因子-α(tumour necrosis factor-alpha,TNF-α)和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beta,IL-1β)等,这些因子参与组织重塑性和耐受性。除此之外,巨噬细胞还通过产生活性氧、一氧化氮中间体、基质降解酶、CXC趋化因子8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来促进疾病进展,而以上因子对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在关节中的募集至关重要[15]。在炎症环境中,MSCs能够通过吲哚胺 2, 3-双加氧酶(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IDO)、C-C基序配体18及前列腺素2(prostaglandin E2,PGE2)将巨噬细胞从M1型(促炎)转化为M2表型(抑炎)。例如MSCs释放的PGE2可通过依赖性机制在IDO参与下与巨噬细胞受体EP2和EP4结合,将巨噬细胞极化为M2表型[16]。除此之外,活化后MSCs能够分泌免疫抑制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刺激基因-6(tumour necrosis factor α stimulated gene 6,TSG-6),TSG-6可与巨噬细胞表达的CD44相互作用并减少核因子κB的核易位,通过负反馈回路减弱炎症级联反应[17]。有研究者发现,在RA患者特异的免疫环境下,MSCs可显著抑制NLRP3炎症体介导的IL-1β产生以及TNF-α的分泌,同时在环氧合酶2和TSG-6信号的协同作用下诱导M2型巨噬细胞的产生,抑制RA患者循环血液中M1型巨噬细胞的活化,从而减轻关节炎的炎症反应和临床表现[18]。
1.1.2 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 在RA疾病过程中,DC是炎症的主要诱导者,可将抗原提呈至自身反应性T细胞,继而产生与辅助T细胞分化相关的不同细胞因子。MSCs可影响单核前体细胞向DC分化,抑制DC成熟,使DC处于耐受状态,并且还可调节DC刺激淋巴细胞增殖的能力,使其从促炎因子分泌转为抗炎因子分泌[19]。MSCs可通过分泌IL-6破坏DC表面Toll样受体的活化来干扰DC成熟,产生耐受型DC,DC参与活化的表面标志物表达被下调后,DC无法处理抗原并提呈至T细胞,最终引起T细胞增殖下降[20]。同时MSCs和DC共培养实验显示,经过MSCs教育后的DC能诱导更多Treg细胞的扩增,而该过程和Notch/Jagged1信号途径相关[21-22]。此外,单核细胞衍生的DC可通过MSCs产生的生长调节癌基因趋化因子获得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MDSC)的表型,这一类DC被发现具有高水平IL-10和IL-4的分泌能力以及IL-12和γ干扰素(interferon-gamma,IFN-γ)的低水平表达能力[20]。同时MSCs可通过分泌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与MDSC表达的受体c-Met相互作用,诱导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3磷酸化,促进MDSC的增殖,另一方面HGF还可诱导MDSC表达一氧化氮合酶和精氨酸酶,抑制T细胞活性并促进Treg的扩增[23]。
1.1.3 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 研究发现MSCs影响NK细胞有多种机制,包括:细胞间直接接触;释放可溶性因子如外泌体、细胞因子[IFN-γ、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IL-1等];通过调节其他细胞如Treg,间接影响NK功能[24]。NK细胞在RA患者关节中含量丰富,在RA患者骨质破坏过程起关键作用。NK细胞的功能性可受到多种受体调节,继而产生激活或抑制信号。当静息态的NK细胞暴露于激活的细胞因子(如IL-2)环境下会增加激活受体NKp44、NKp30和NKG2D的表达,而MSCs可以通过IDO、PGE2和TGF-β,协同减少NK细胞激活受体的表达,显著抑制IL-2诱导的NK细胞增殖,阻止细胞毒活性和杀伤性细胞因子的产生[15]。另外,MSCs产生的TGF-β家族的另一成员活化素A也被证实,可通过抑制IFN-γ的产生来抑制NK细胞的功能[25]。
1.2 MSCs对获得性免疫功能调节
1.2.1 B细胞 如前所述,在RA发病机制中,先天免疫细胞不仅可直接诱导炎症,还可通过募集、激活获得性免疫的不同细胞,如B细胞和T淋巴细胞一同参与发病机制。其中参与RA获得性免疫相关机制中一个关键事件便是自身抗体的产生。B细胞可产生自身抗体及细胞因子,影响NK细胞、巨噬细胞和T细胞,因此在RA的发病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RA患者中,其自身反应性B细胞数量约是非RA患者的3~4倍。MSCs可直接与B细胞相互作用,减少浆细胞形成,同时促进调节性B细胞的诱导。调节性B细胞可通过免疫耐受获得免疫抑制的特性[26]。有研究显示,MSCs可通过减少CD69、CD86的表达,浆细胞分化以及免疫球蛋白IgG的产生,抑制B细胞的增殖和激活[27]。ASARI等[28]实验表明,MSCs可通过降低B淋巴细胞诱导成熟蛋白-1 mRNA的表达来抑制脂多糖刺激的B细胞增殖。其抑制程度与培养液中B细胞与MSCs的比例有关。CORCIONE等[29]实验提示,MSCs通过阻滞细胞周期的G0/G1期抑制B细胞增殖。该项研究表明,B细胞经MSCs处理培养后,浆细胞IgM、IgG和IgA的分泌下调。另一项关于外周血淋巴细胞的研究表明,在MSCs、B细胞和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共培养中,MSCs可以抑制B细胞的增殖、B细胞向浆细胞的分化以及免疫球蛋白的产生[30]。在一项临床研究中,研究人员对13例难治性RA患者静脉输注MSCs,12个月后观察到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CD19+B细胞的百分比显著下降,同时BR3+CD19+B细胞和BCMA+CD19+B细胞百分率明显下降,推测MSCs可能通过减少B细胞活化因子和增强诱导配体细胞因子的产生以及下调其在B细胞表面受体的表达而抑制B细胞反应性,继而影响机体的体液反应[31]。
1.2.2 T细胞 虽然目前对RA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RA患者T淋巴细胞的异常活化、增殖及分化在RA炎症反应、免疫系统激活以及骨破坏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RA疾病发展过程中,大量CD4+T细胞浸润滑膜组织,并在抗原和细胞因子作用下激活分化为各种具有免疫功能的T淋巴细胞亚群。CD4+T细胞也称为Th细胞,在免疫应答过程发挥多种作用,包括诱导B细胞的分化和功能以及CD8+T细胞的活化[32]。目前研究最多的亚群主要有Th1、Th2、Th17和Treg等。以往的研究认为,RA是由于Th1/Th2失衡所驱动,但后来研究发现RA患者滑膜中主要由Th1细胞分泌的IFN-γ数量很少,Th1/Th2失衡不足以解释RA的发生机制。一些研究发现,RA患者外周血中Th17细胞的比例以及IL-17、IL-23、IL-6和TNF-α的水平显著增加[33-34]。Th17/Treg失衡和RA的严重程度紧密相关。Th17和Treg细胞是高度可塑性细胞,当暴露于不同生理或病理条件时,可以表现不同的表型和功能[35]。Th17细胞主要分泌IL-17,可调节由Th1细胞介导的炎症应答,促进TNF-α、IL-6以及 IL-1的表达,并导致滑膜的持续炎症。IL-17同时也是一种抗凋亡因子,可导致T细胞和B细胞凋亡受阻,诱发炎症恶性循环[36]。此外,Th17细胞还可促进CXC趋化因子8、C-C趋化因子配体2和3以及基质金属蛋白酶的释放,最终导致软骨和骨的破坏。 Treg细胞主要分泌TGF-β和IL-10,可抑制T细胞的异常活化和炎性因子的分泌,并维持免疫耐受。因此,Treg细胞与Th17细胞之间的平衡(Treg/Th17比率)通常会影响免疫反应的结果(免疫抑制或炎症)[37]。现已有大量证据支持MSCs对CD4+T细胞分化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MSCs可抑制Th1亚群的增殖和促炎细胞因子如IFN-γ和IL-12等的产生。MSCs还可以促进T细胞分化为Th2亚群,增加IL-4和IL-5的产生。除此之外,MSCs可促进T细胞分化或诱导为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Treg细胞。其调节Treg细胞与Th17细胞之间的平衡可通过旁分泌可溶性因子、细胞间接触、线粒体转移机制及分泌外泌体等方式实现。在RA的炎性环境下,MSCs被促炎性免疫细胞如Th17细胞释放的因子激活,获得免疫调节表型和功能并进入免疫调节状态,随后抑制Th17细胞的分化程序,同时伴随有T细胞分泌IL-10并高表达Foxp3,直接诱导Treg细胞增殖,从而抑制免疫炎症反应[38]。
因此,MSCs的免疫调节能力可以根据RA患者关节局部的炎性情况而获得抗炎表型,尽管其免疫调节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但已有大量体内、体外证据表明MSCs可诱导复杂的免疫反应,特别是通过减少DC、巨噬细胞、NK 细胞、B 细胞和 T 细胞的促炎表型以及促进抗炎反应来影响患者的关节局部炎性环境。
2 MSCs治疗RA的临床前研究
在近期一项MSCs治疗RA的临床前研究meta分析中,RA动物模型的临床症状、组织学评分和足爪厚度等指标显示MSCs可明显改善RA的治疗结局。但通过不同的给药途径比较临床评分时,腹腔内注射和其他给药途径(如静脉注射)相比,能更显著降低临床评分。在剂量方面,MSCs每次(2~3)×106细胞剂量范围内的多次注射显示更佳的治疗效果。此外,结果还显示异种MSCs的治疗效果比其他移植类型更显著[39]。但在一项研究中,通过对胶原蛋白诱导关节炎(collagen induced arthritis,CIA)小鼠静脉单次注射2×106细胞即可显著降低TNF-α和IL-6水平,改善小鼠临床症状和组织学评分。该机制可能与MSCs诱导M2型巨噬细胞产生及上调FoxP3+Treg水平相关[40]。这项研究提示,即便单次中等剂量的注射亦可达到显著的治疗效果。除此之外,在MSCs的来源方面,有研究报道骨髓源性MSCs(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SCs)、脐带源性MSCs(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UCMSCs)和乳牙源性MSCs(exfoliated deciduous teeth-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EDMSCs)对CIA小鼠静脉给药后,均可改善小鼠滑膜炎症状及关节破坏,其中治疗效果方面,EDMSCs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MSCs在RA应用中获得的一些令人鼓舞的结果,在RA临床前研究中依旧有矛盾的发现。DJOUAD等[42]将剂量为1×106或 4×106的MSCs单次静脉输注至已建立CIA或正值发作期的小鼠,均未显示出治疗效果。SULLIVAN等[43]将1×106数量基因错配的BMSCs从BALB/c小鼠移植至DBA/1小鼠体内,则出现了局部炎症加重,临床症状恶化的结局。另外, PAPADOPOULOU 等[44]发现,除非在疾病发作之前给予MSCs,否则MSCs在体内无效。除此之外,已证实MSCs在培养扩增环节还可增加MHC-Ⅰ和 MHC-Ⅱ类分子的表达,影响研究模型的免疫反应[45-46]。以上研究一方面提示同种异体MSCs以及MSCs扩增所带来的免疫原性变化可能在体内引起体液和细胞免疫;另一方面也提示MSCs治疗对其所处环境敏感,体内环境可能会改变其治疗潜力。 由于物种差异,临床前研究数据可能仅局限于动物模型,其结局和影响同人体的相关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动物模型数据会受MSCs来源、制备方法、细胞剂量、递送途径和疾病状态等变量的影响,而这些也可能是未来开发RA相关的MSCs细胞产品的重要指标。 近年来由于MSCs的特性和治疗潜力,MSCs治疗RA已成为一种新颖且有前途的细胞治疗方案。已有大量研究将MSCs和传统DMARDs、生物制剂以及中药新药联用,减少不良反应并最大限度地发挥MSCs治疗潜力。 在一项大规模非随机对照试验中,172名对传统治疗药物反应不足的活动性RA患者中,36名患者作为对照组接受DMARDs常规治疗, 136名接受4×107UCMSCs静脉注射并联合传统DMARDs治疗。患者在输注UCMSCs期间和输注之后均未出现任何严重副作用,在实验中还观察到UCMSCs联合DMARDs在治疗12 h内,有患者关节痛疼、肿胀和僵硬等临床症状得到缓解,显示了UCMSCs治疗活动性RA的安全性及快速临床反应性。同时该实验还显示UCMSCs能够显著提升Th2细胞分泌的IL-4水平,增加外周血CD4+CD25+FoxP3+Treg细胞百分比,降低TNF-α和IL-6水平,和DMARDs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疾病活动度,且该治疗效果可维持3~6个月[47]。在另一项长达3年随访时间的前瞻性Ⅰ/Ⅱ期研究中,64名患者接受4×107UCMSCs静脉注射联合个性化低剂量的DMARDs治疗,在长期安全性评估中,所有患者在治疗1年及3年后均未出现任何严重不良反应,同时RA症状减轻,健康评定问卷(Health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HAQ)和28处关节疾病活动性评估(disease activity score in 28 joints,DAS28)评分降低,除此之外,类风湿因子(rheumatoid factor,RF)、C反应蛋白(C-reaction protein,CRP)、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和抗环瓜氨酸肽抗体等炎症和/或RA血清标记物水平显著降低,该治疗效果在经UCMSCs治疗后可维持3年,这提示UCMSCs联合个性化低剂量DMARDs治疗可长期维持低水平的疾病活动性,从而提高RA患者的生活质量,这可能与UCMSCs调节患者自身免疫耐受及提高RA患者抗风湿药物耐受性相关[48]。在PARK等[49]进行的Ia期临床试验中,对处于中度活动期的患者进行1×108人脐血MSCs的单次静脉注射并联合甲氨蝶呤治疗,治疗4周后未观察到任何毒副作用,同时有效降低第4周DAS28评分[44]。另外在一项随机三盲安慰剂对照的1/2期临床试验中,通过对15例RA患者关节内单次注射4×108BMSCs并联合传统DMARDs治疗,随访12个月,发现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视觉模拟评分法评分以及无痛步行距离均有改善趋势,特别是在随访前6个月,MSCs显示有助于降低DMARDs摄入量。但1年后膝关节的MRI成像并未显示与基线组及安慰剂组的差异,且前期临床症状的改善趋势也未能延续[50]。这提示,MSCs对于不耐受传统DMARDs或药物响应性较差的患者来说可能是一种良好的治疗策略,同时MSCs和传统DMARDs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RA的活动度。但MSCs的疗效维持时间可能受细胞来源、剂量、和疾病活跃状态等因素影响,且存在一定疗效差异。 近年来MSCs对RA的免疫调节功能已被多项研究证实具有可塑性,可由炎性微环境诱导,因此有研究者通过生物制剂的联用方案增强MSCs的免疫调节功能,用于对难治性RA患者的病情干预。在一项Ⅰ/Ⅱ期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中,对常规治疗反应不良的RA患者联用MSCs和IFN-γ后,随访3个月结果显示,多数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单用MSCs者相比有显著改善,ACR20应答率达93.3%。除临床症状得到缓解外,患者疾病活动性指标如CRP和ESR水平明显降低,同时患者总体状况如精神状态、体力、饮食和睡眠活动等也显著好转。经治疗后患者Treg/Th17细胞比例迅速增加,Treg细胞活性增强,这提示与IFN-γ联用可显着提升MSCs的免疫调节功能和治疗效果[51]。 除此之外,中药和MSCs联用也已被证实能显著增加MSCs治疗RA的有效性和长期稳定性。如鹿瓜多肽(Lugua polypeptides, LG)在一项体外细胞实验中被证实可通过浓度依赖的方式促进HGF、PGE2和TSG-6抗炎因子的分泌,增强UCMSCs的免疫调节功能[52],随后一项临床随机对照研究通过LG、UCMSCs和DMARDs序贯疗法对活动性RA患者进行临床干预,利用LG刺激UCMSCs减少微环境中促炎因子释放,强化UCMSCs的免疫调节和组织修复能力。治疗结果显示,该方案明显缓解RA患者临床症状并减少DMARDs用药的不良反应。这提示LG联合UCMSCs可提高UCMSCs治疗活动性RA的有效性及稳定性,从而改善临床疗效并减少副作用[53]。此外,中医认为肾虚血瘀症更能全面反映RA的病理病机,因此补肾活血是RA的重要治则之一。李世梅等[54]借鉴细胞移植前预处理机制,通过MSCs和补肾强骨药LG以及活血化瘀药丹参酮Ⅱ联用,通过下调TNF-α以及IL-23表达,调节炎性因子释放,增强MSCs迁移、归巢、修复和免疫调节等特性。经过3个月随访,患者HAQ、DAS28、ESR、CPR、RF、抗CCP等指标明显改善。 由于MSCs的治疗效果已得到大量临床案例验证,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开始开发新策略以增强MSCs在RA中的免疫调节及抗炎特性。包括通过MSCs的3D微环境培养,利用细胞-细胞及细胞-基质相互作用模拟体内生理环境,使之表达高水平PGE2、TGF-β1、IL-6 和 IDO等,激活MSCs的免疫调节能力[55-56];另一个有希望的策略是MSCs的预处理手段,如MSCs通过联合应用缺氧及IFN-γ处理后,能够对CD4+T细胞和CD8+T细胞的增殖带来抑制效果,同时还可上调IDO的表达水平[57];利用IL-17A预处理MSCs则可抑制T细胞活化和增殖、Th1细胞因子(TNF-α、IFN-γ 和 IL-2)的产生,以及促进诱导性Treg细胞的产生[58]。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策略如MSCs遗传修饰[59]、MSCs支架包裹[60]及MSCs衍生外泌体[61]等,均得到令人鼓舞的实验结果,而以上新策略的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验证则还需进一步的数据积累和研究。 MSCs的免疫调节能力已被研究数年,已证实MSCs可与参与免疫反应的多种因子、细胞等相互作用,且牵扯机制广泛。因此,在涉及巨噬细胞、DC细胞、NK细胞、T细胞、B细胞及其他细胞的RA病理机制下,MSCs可作为一种具有潜力的治疗方案。虽然MSCs具有的免疫抑制作用被证实可改变免疫细胞功能,但无论临床前实验还是临床实验均提示,MSCs可因细胞来源、剂量、给药途径、周围微环境的影响或控制等因素而表现出可塑性,可能会改变对RA的临床治疗效果。因此,基于MSCs治疗种子细胞的选择、细胞最优剂量、细胞用药次数和间隔时间,以及MSCs免疫调节状态的启动条件等均是未来应用亟待解决的问题。3 MSCs治疗RA的临床研究
4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