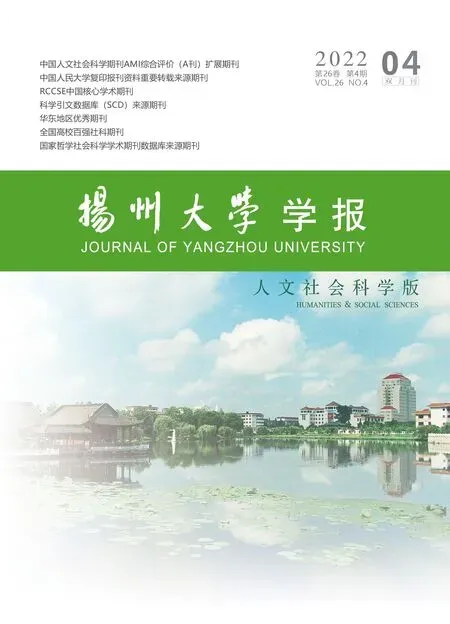左翼文学视域中儿童文学“范型”的重构
吴 翔 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驱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伴随着左翼思潮的兴起,儿童文学的范式也发生了新的转向。左翼文学运动的推进使得“儿童是什么”被注入了新的意涵。与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强调儿童与成人的“二分”差异不同,左翼儿童文学融入了更为鲜明的阶级性与政治倾向性,“儿童”的个体性让位于“人”的普遍性,被抹去身份的儿童与成人一道致力于由外而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此情境下,儿童本位论式微,逐渐让位于“阶级本位”和“民族本位”。本位的转换促发了儿童文学重构新“范型”的诉求,五四儿童文学“价值单元”的儿童自然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手段化”了,(1)杜传坤:《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儿童文学普遍具有“生活教科书”的性质,成为帮助儿童实现“社会角色”的有效途径。这种强化儿童社会性的文学观念延续至新中国成立,汇入了国家文学体制的“一体化”运作之中。(2)吴翔宇:《国家文学体制与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44-64页。
一、本位转换与纯化“儿童观”的阻滞
五四退潮后,“革命文学”的提出点燃了青年作家狂热情绪,也推动了鲁迅、茅盾等人的思想转变。“革命文学”的口号论争直接促成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思想结盟。左翼文学的现代性并未割裂新文学的“为人生”传统,从整体上看两者都属于以启蒙理性为内核的现代性,左翼文学“大众化”本身就包含了启蒙大众的旨趣。只不过在语境转变后,启蒙的对象、范围、力度、方案都发生了改变,不仅关注“个人”,而且关注人与社会革命、人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如果说五四文学的启蒙现代性尚在理论预设的倡导层级,那么左翼文学的革命现代性则借助“大众化”运动上升至民族国家整体主义的实践层面,承继了五四未竟的启蒙重任,开启了从被动现代性到追索主动现代性的道路。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儿童文学领域伴随而来的是鲁迅所说的“向后转”。当时儿童读物的内容,“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己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3)鲁迅:《〈表〉译者的话》,《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页。。对于中国古代《神童诗》《幼学琼林》《太公家教》等粗制滥造的儿童读物,鲁迅认为并不有益于儿童。为了纠正那种遁入中国古代传统典籍的偏狭,鲁迅提出了儿童文学“有益”与“有味”的双重标准。在他看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4)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9页。。此外,对于这种远离现实人生的创作倾向,以及“王子”“公主”“神仙”等充斥于各类童话中的弊病,张天翼在《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中讽喻了“求神仙的‘好处’”。(5)张天翼:《为孩子们写作是幸福的》,《我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76页。而那种廉价的童话幻境,张天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假的,是哄人的……这是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它。跟它一点也不认识。世界上并没有这种东西……还有一些人,简直就是欺骗小朋友。他们告诉你:要是你受了欺侮,你不要反抗。他叫你等神仙来帮忙……这些故事,原来就是这些欺侮人的人做的?……只要不是一个洋娃娃,是一个真的人,在真的世界上过活,就要知道一点真的道理。”(6)张天翼:《〈奇怪的地方〉序》,《张天翼文学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28-331页。关于以王子、公主为主人公的童话,胡风的态度与张天翼并无二异,他重申了“有益的儿童文学”的价值是“反映人生真实的艺术品”。(7)胡风:《〈表〉与儿童文学》,《胡风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235页。茅盾没有盲目认同五四时期大量外译童话,他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要“少用舶来品的王子,公主,仙人,魔杖,或者什么国货的吕纯阳的指头,和什么吃了女贞子会遍体生毛,身轻如燕,吃了黄精会终年不饿长生不老这一类的话”(8)茅盾:《关于“儿童文学”》,《茅盾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413页。。同样,对于从国外翻译的“国王呀,王子呀,公主呀,甚至仙子呀”等童话,钟望阳也揭露其本质,“只是引导我们孩子们做一场美丽的、空虚的、不可捉摸的幻梦罢了”(9)钟望阳:《我们的儿童读物》,《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0页。。在论及神话物语的选择标准时,张匡指出:“有封建思想的文字,不使混入,就是国王,王后,王子,公主等材料,皆在摈弃之列。”(10)张匡:《儿童读物的探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0页。在对中国儿童读物市场深入分析后,碧云得出结论,彼时的儿童读物充斥着“神奇鬼怪王子公主之陈腐童话,花月猫狗之无聊诗歌,以及含有迷信意味,或封建意识色彩极浓重的东西”,而儿童所需要的健康、积极的读物却非常稀少。对此,碧云感慨道:“儿童教育职责的作家专家与出版家们,所以不能辞其咎的!”(11)碧云:《儿童读物问题之商榷》,《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68页。可以说,前述学人认识到了旧式童话远离现实的弊病,从理论批评的角度为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受到极大关注的安徒生童话在左翼文学主潮下影响力日趋式微,甚至成了批评的对象。徐调孚将安徒生童话视为“麻醉品”:“惟有他的思想是我们现在所感到不满意的。他所给予孩子们的粮食只是一种空虚的思想,从未把握住过现实,从未把孩子们时刻接触的社会相解剖给孩子们看,而成为适合现代的我们的理想的童话作家。”他进一步指出,“逃避了现实躲向‘天鹅’‘人鱼’等的乐园里去,这是安徒生童话的特色。现代的儿童不客气地说,已经不需要这些麻醉品了。把安徒生的童话加以精细的定性分析所得的结果多少总有一些毒质的,就今日的眼光来评价安徒生,我们的结论是如此”。(12)狄福:《丹麦童话家安徒生》,《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62页。金星则将安徒生界定为“一个住在花园里写作的老糊涂”,他推崇苏联作家伊林的作品,认为这是以物质建设、近世的机械工程、天文地理一切日常生活必要的知识作题材。因此,在认识人生的基础上也促进了儿童的成长:“读着这册书的儿童,也跟着那孩子变做了大人。”(13)金星:《儿童文学的题材》,《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9页。范泉也认为,像丹麦安徒生那样的童话创作法,尤其是那些用封建外衣来娱乐儿童感情的童话,是不需要的,并旗帜鲜明地指出:“处于苦难的中国,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忘记了现实,一味飘飘然的钻向神仙贵族的世界里。尤其是儿童小说的写作,应当把血淋淋的现实带还给孩子们,应当跟政治和社会密切地连系起来。”(14)范泉:《新儿童文学的起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8页。凡此等等,并不是安徒生童话的文学性出现了偏误,而是基于语境转换后国人对于域外资源有了全新的认识。
应该说,上述批评家反对的并非童话本身,而是童话所制造的幻境或将儿童引入遁路的思想观念。对于这一问题,20世纪30年代关于“鸟言兽语”的论争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予以进一步探究。“鸟言兽语”是童话惯用的拟人化的艺术手法,这本不稀奇。早在五四时期,关于“猫话狗话”是否符合儿童教育规律的讨论就已经开始了。“猫话狗话”是一种拟人化的手法,正因为赋予了动物说话的能力,儿童与动物就开启了对话、交流的通道。譬如学衡派的柳诒徵就认为“猫话狗话”有悖于“五伦”,是“大错特错”,给儿童灌输这样的教育的结果是:“他们由国民学校毕业之后,固然不配做世界上的人,更不配做中国的国民,岂不是要变成猫化狗化畜牲化的国民么?”(15)周作人:《童话与伦常》,《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第215页。对此,周作人并不认同,他认为恰是童话不讲传统教训才使得儿童不会沦为“猫化狗化”的国民。到了30年代,“鸟言兽语”写进教科书的做法引起了何键的不满,并贬之为“一种荒谬之说”。事实上,“鸟言兽语”只是童话的艺术手法,它不会在儿童身上种植远离现实的种子,因而也并不背离左翼文学运动的主导思想。何键并非文学界人士,他的这一论断反“鸟言兽语”是表,而宣扬其所在政党的主张则是真实的目的。何键的主张获得了初等教育专家尚仲衣的赞许,他将“鸟言兽语”等神仙故事、童话视为“教育中的倒行逆施”,并为其开具了“五大罪状”:“一是易阻碍儿童适应客观的实在之进行;二是易习于离开现实生活而向幻想中逃遁的心理;三是易流于在幻想中满足或祈求不劳而获的趋向;四是易养成儿童对现实生活的畏惧心及厌恶心;五是易流于离奇错乱思想的程序。”(16)尚仲衣:《再论儿童读物——附答吴研因先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4页。显然,这已不是一个文学议题,而是上升为儿童教育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了。
面对这种“围剿”童话的荒谬行为,吴研因、陈鹤琴、魏冰心、张匡等人撰文予以反拨。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也加入了这次论争。对于那些认为“鸟言兽语”有违共和精神的言论,他认为是“杞人之忧”,他从“为儿童”的立场出发指出童话的“有益无害”:“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绝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17)鲁迅:《〈勇敢的约翰〉校后记》,《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3页。鲁迅并不担心“鸟言兽语”这种拟人化的艺术形式会对儿童产生负面影响,他真正担心的是儿童不能继续受到教育,“学识不再进步,则在幼小时所教的神话,将永信以为真,所以也许是有害的”(18)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5页。。鲁迅的这一观念与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所讨论“猫话狗话”异曲同工:“儿童相信猫狗能说话的时候,我们便同他们讲猫狗说话的故事,不但要使得他们喜悦,也因为知道这过程是跳不过的——然而又自然的会推移过去的,所以相当的对付了,等到儿童要知道猫狗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到来,我们再可以将生物学的知识供给他们。”(19)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在这里,鲁迅以“儿童会进化”的角度来驳斥何键、尚仲衣将文学论争与政治立场杂糅在一起的观念,护卫了童话这株新苗。为了声援鲁迅,叶圣陶还创作了《鸟言兽语》,这篇童话通过麻雀和松鼠的对话引出“鸟言兽语”论争背景,并借松鼠之口说出:“咱们说咱们的话,原不预备请人类写到小学教科书里去。既然写进去了,却又说咱们的话没有这个资格!要是一般小学生将来真就思想不清楚,行为不正当,还要把责任记在咱们账上呢。人类真是又糊涂又骄傲的东西!”(20)叶圣陶:《鸟言兽语》,《叶圣陶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麻雀和松鼠认为“人言人语”与“鸟言兽语”并无多大差异,无所谓哪一种高贵,哪一种低贱。联系前述左翼批评家批评与护卫童话两种不同的路径,不难发现:他们反对的并非童话这种艺术手法,而是批评童话所预设的理想化的虚空幻境。通过这次论争,童话并未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政治”主导的语境中被湮灭,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展,童话不断求取幻想性与现实性的平衡。
不过,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关于“鸟言兽语”的讨论仍在继续,其论争的重心在于“鸟言兽语”的艺术手法对于抗战是否有利的问题上。立足于抗战的政治语境,当时有人从“儿童教育的本位”出发,主张废止那些无关国家社会的教材。对此,吴研因提醒国人,“羊拒狗,狗拒狼”的主题中依然可以洞见“弱者抵抗强者的意识”。(21)吴研因:《儿童年与儿童教育》,《教与学》1935 年第3期,第16-29页。心岂从科学性与文学性的角度出发,论定了儿童文学“文学性”的主体地位:“违背自然规律比如‘猫狗说话’‘鸦雀问答’确实不符合科学原理,但最要紧的问题是能否把握住‘儿童文学’究竟是属于‘文学’范围,而非属于‘科学’范围。”(22)心岂:《儿童文学中应否采取物语问题》,《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4页。作为儿童文学的主要文体,童话的艺术手法与思想观念的平衡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在抗战的语境下,思想的显效被提至优先的位置,由于要传达现实的、时效性的思想内涵,艺术性势必会受到思想性的挤压。不过,强调思想性也未必要以牺牲艺术性为代价。事实证明,在当时的童话创作中,作家借助“鸟言兽语”来传达迫急的抗战信息较为普遍。陈伯吹主张童话以“社会与自然”为内容,同时注意儿童阅读的“趣味”的观念,(23)陈伯吹:《陈旧的“旧瓶盛新酒”——关于儿童读物形式问题》,《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2页。实质上是从内容和形式两面辩证地考察童话的发展方向。那种割裂童话内容与形式统一性,或因童话拥有“鸟言兽语”的艺术形式而排拒童话的做法,显然是不科学、不理性的。
返归儿童文学“元概念”,“儿童性”与“文学性”构成了儿童文学本体的内外两面。然而,儿童性与文学性并不天然接洽,在不同的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张力关系。儿童性是儿童文学发生的基点,没有儿童的发现就不可能存在儿童文学,体现了文学思想的先决性。当走出了旧“礼”对于儿童身体及精神固化的牢笼后,儿童与儿童文学才能浮出历史地表,成为一个“现代”概念。(24)吴其南:《“礼”与中国儿童的身体建构》,《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02-108页。思想的转换衍生了艺术审美观念的新变,“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等注重非功利性的儿童文学主张在左翼文学运动的大潮中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儿童文学亟须在新的语境下重构新的范式,引领新的文学潮流以适应时代与文学的发展。
二、革命现代性与左翼儿童文学“生活教科书”功用
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便确立了现代性目标与阶级性路径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在规范革命文学的同时,左翼知识分子提出了基于无产阶级“正义标准”的革命功利性的诉求,(25)陈国恩:《革命现代性与中国左翼文学》,《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49-156页。由此推动了左翼文学的发展。左翼革命现代性有明确的政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革命而非启蒙的方式唤起民众的阶级觉悟,这正是革命文学区别于文学革命的根本所在。从“革命文学”到“无产阶级文学”,中国新文学的价值功用性日趋明确。左翼文学在推动“人”的个性解放的同时也强化了社会解放的意识。五四时期“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得到调整,儿童文学被纳入阶级政治的轨道。纳入左翼文学体系的儿童文学也深受这种革命现代性的影响,被灌输了一种“革命范式”。
“左联”成立后,左翼文艺运动就将儿童文学纳入其系统之中。左联机关刊物《大众文艺》开辟了“儿童文艺专栏”——“少年大众”。1930年5月,《大众文艺》第2卷第4期开设“少年大众”栏目,该栏目的“发刊词”为:“这里的种种,都是预备给新时代的弟妹们阅读的。这个光明的时代快到了,我们的社会是不断地在进展着。也许我们所讲的种种是你们所不曾知道过,不曾看见过的;但是这些都是真的事情,而且是必定会来的。因为这些种种都是你们在学校里和家庭里所不会谈起的,大人们是始终把这些事情瞒着你们的。我们要告诉你们,过去是怎样,现在是怎样,将来又是怎样。我们要告诉你们真的事情。这是我们新编《少年大众》唯一的抱负。”(26)《给新时期的弟妹们》,《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在《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意见较为一致。钱杏邨指出,“少年大众”要“给少年们以阶级的认识,并且要鼓动他们,使他们了解,并参加斗争之必要,组织之必要”(27)《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4页。。华汉认为,“儿童读的东西与成人读的不同,儿童读物应该要有趣味——当然仅仅是技术上的趣味。内容方面虽则是给少年看的,但是也不能忘记了一般的大众,因为少年不过是大众中的一部分,题材方面应该容纳讽刺,暴露,鼓励,教育等几种”(28)《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4页。。田汉则强调:“对于少年,我们第一先要使他们懂得,其次要使他们爱。我们不论著译,文字总要通俗。好比新文学的不普通,最大的原因还是文字不通俗。文字的通俗浅显是使他们懂得的重要条件。其次说爱。儿童是喜欢泥人,糖果的,现在我们要另外给他们一点新的,有益的东西。并且我们要使他们对于爱好泥人的心理转向我们所要给他们的东西上来。所以我们不妨把过去英雄意识化起来以使他们了解,指示他们新的世界观。并改变他们日常所接近的故事以转移他们的认识,抵抗他们的封建的思想。”(29)《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4-115页。当然,与会者也意识到了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在主张“大众化”的同时没有漠视其文学性。例如蒋光慈就曾指出:“少年不是成年,少年有少年的兴味,成年有成年的兴味,所以《少年大众》应该大众化而且要少年化。”(30)《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在《少年大众》中,苏尼亚的《苏俄的童子军》、冯锵的《小阿强》、钱杏邨的《那个十三岁的小孩》、樱影的《顾正鸿》、屈文翻译的《金目王子的故事》、李允的《谁种的米》即是这种儿童文艺思想的一种具体的创作实践。“左联”的另一个机关报《文学月报》刊发了多篇儿童小说和儿童诗,如金丁的《孩子们》、杨骚的《小兄弟的歌》等。在《文学月报》第三号的“编辑后记”中,主编周扬曾预告了要出版一种“儿童文学”的附刊:“我们将附刊一种‘儿童文学’,并不钉在本刊篇幅内,是另外装成美丽小册,使读者可以拿来赠送小朋友。内容将尽量采择一些面对现实的、趣味的儿童文学读物。”(31)《编辑后记》,《文学月报》第3号,1932年10月15日。尽管该计划未能实现,但该刊对于主题的设定折射了左翼儿童文学的观念:“关于儿童的读物,近来出版得很多,但大多数都是把儿童当作现实以外得一群,尽拿迷离的,无内容的梦幻,来麻醉幼稚的头脑。”(32)《〈文学〉第七卷第一号(儿童文学特辑)编后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这种面向现实、面向儿童的文学观念符合左翼文学的主流话语,儿童文学也被整合于文学大众化、革命化的系统。
儿童文学本身并未贴有阶级性或政治性的标签,但在这场追逐革命现代性的运动面前,儿童文学基于儿童、阶级、政治而开启的民族国家想象传统被重新激活,“五四”时期所推行的启蒙现代性手段让位于革命现代性。那么,对于“阶级”或“阶级意识”的认知,儿童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遗传”或“后天”说都各执一词,各有各的道理。对于这个问题,茅盾主张从阶级论的角度来整体考察:“在阶级社会内,儿童自懂事的时候起(甚至在牙牙学语的时候起),便逐渐有了阶级意识,而且,还不断地从他们所接触的事物中受到阶级教育(包括本阶级和敌对阶级的),直到由于自己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而确定了他们的阶级立场。”(33)茅盾:《1960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茅盾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494页。茅盾的上述观点是建构在“阶级社会内”的语境下的,儿童的阶级意识既获致于自己的出身,也成型于阶级社会的语义场。这种融合了阶级社会语境的身份与意识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与前述启蒙现代性与革命现代性的分野并不矛盾,两种现代性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于儿童思想意识的转换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方面,冰心的儿童小说《分》的出现是上述思想观念转变的标记。小说通过两个出身不同的婴儿的对话,隐喻了社会阶层的差异及贫富分化的结果。冰心的这种创作观念也走出了之前以“爱”为主导的价值模式,儿童的差异由其不同的阶级出身所框定,那种永恒的平等早已不见踪迹。这是冰心在20世纪30年代深刻体认社会后的写照,表征了其儿童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颇有意味的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里的双胞胎则在不同阶层中长大,而这种穷人与富人不同的家庭生长环境也注定了相异的人生道路。如果说冰心的《分》还停留在以单向度的“出身论”或“血缘论”来判明人生道路的层面上,那么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则开启了对儿童“根性”与社会环境双重考量的新高度。
与“五四”儿童文学中抽象的“儿童”隐喻不同,这一时期的儿童已具化为现实中的人,是阶级分立和斗争的亲历者、见证者。胡也频《黑骨头》里的童工阿土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自然人,而是一个打上了阶级印记的社会人。萧红的《手》以染坊店女儿王亚明的“手”标记了阶级分化下下层儿童的全部心酸与苦楚。那双“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的小手成了学校教师和学生嘲笑的对象,烙上了“异样”标记的王亚明的语言和行为,演变成为贫困、无知、愚蠢者的“示众”。深受鲁迅影响的萧红以“越轨的笔致”描摹了自然之子被阶级化、社会化扼杀的事实。基于“我的人物比我高”(34)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序〈萧红选集〉》,《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第186-189页。的观念,萧红处处克制自己情感的显露,不干预人物命运的走向。同样是描写儿童、描摹儿童的“手”,郭沫若的《一只手》就与萧红的《手》有很大的差异。《一只手》并非为了书写“病态儿童”的生存状态,而是要凸显小普罗英勇反抗的儿童主体精神。在这里,小普罗已不再是沉默的儿童,他们团结一致,高喊“同志们起来!起来”“反抗一切资本家”,并最终打死了资本家鲍尔爵爷。当儿童走出自我世界、介入阶级政治的生活时,他们的观念、精神为社会化的广阔结构所拉升,而这时的儿童文学也就充当了“生活教科书”的价值功能,与五四儿童文学所开创的思维、观念和价值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受左翼思潮的影响,欧美资源失魅,俄苏资源则在中国文学界的传播不断加速,并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其中,苏共文艺政策和观念深刻地影响了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界。而这种翻译文学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民族性与主体性品格生成至关重要。茅盾的《儿童文学在苏联》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及“儿童文学大会”的决议。(35)茅盾:《儿童文学在苏联》,《茅盾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445-446页。他以其翻译的《团的儿子》为例指出:“向来有一种‘理论’,以为儿童文学是应当远离政治的,但在苏联,这种‘理论’早已破产了。”(36)茅盾:《〈团的儿子〉译后记》,《茅盾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442页。他推崇苏联作家马尔夏克,认为马尔夏克在儿童文学上确已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他指给儿童们看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37)茅盾:《儿童诗人马尔夏克》,《茅盾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456页。在他看来,马尔夏克的作品“和旧时代的儿童文学不同”,展现的是“苏维埃的新世界”,是“劳动人民劳作的成果”。(38)茅盾:《马尔夏克谈儿童文学》,《茅盾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461页。曾多年留学苏联的萧三非常熟悉苏联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他指出苏联在新儿童文学创作中克服了两种倾向:一是将神话和幻想完全从童话中驱除,二是使儿童读物完全脱离现实。由于解决了上述问题,“苏联儿童文艺便走上了康庄大道”(39)萧三:《略谈儿童文学》,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3页。。高尔基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中国决不仅仅是‘他山之石’,而是照耀中国左翼运动发展的‘太阳’,所以当他逝世时,被比喻为‘人文界的日蚀’,他事实上参与了中国左翼运动的发展,塑造了中国左翼文学理论的特征和品格”(40)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92页。。对于儿童文学写什么的问题,高尔基将教育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在我国,教育的意义就是革命;也就是将儿童的思想从他祖辈和父辈们的旧生活所预定的思想技术习惯和思想错误中解放出来。”在他看来,对于儿童教育而言,光有事实、思想和理论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儿童叙述劳动过程。他以原始神话为例分析指出:“原始神话里没有一个神不是能手,这些神都是技术熟练的铁匠,或是猎人、牧人、航海者、音乐家、木匠;女神也是一些能手:织女、女厨师、女医师等。被称为‘原始人的宗教创作’的东西,其实是完全没有神秘性的纯艺术创作。”(41)高尔基:《儿童文学的“主题”论》,《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83页。鉴于此,高尔基认为创造新的儿童读物势在必行。高尔基站在国家前途的立场上指出,“我们的孩子们应该被教育成更活跃的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因此,我们就有义务将他们从小就武装起来,使他们具备抵抗旧生活的保守主义和沉滞的小市民环境的影响的一切必要知识的威力”(42)高尔基:《文学散论》,孟昌译,北京:文献出版社,1941年,第96页。。
在译介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方面,鲁迅翻译班台莱耶夫的《表》对当时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鲁迅坦言译介该著是“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发荣滋长的”(43)鲁迅:《〈表〉译者的话》,《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6页。。该译作出版后,胡风认为其对于传统儿童文学最大的反抗是将流浪儿“放浪习性底脱除和蜕变,被描写在这里的是一个真实的过程”(44)胡风:《〈表〉与儿童文学》,《胡风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9页。。到了抗战时期,《表》的译介出版还引发了一场“儿童读物应否描写阴暗面”的论争。这与成人文学领域的“暴露与讽刺”的讨论具有同构性。
在社会本位取代儿童本位的潮流中,耽溺于幻想的作家及作品受到了当时学界的批评。与前述安徒生在中国的际遇不同,意大利作家科诺迪的《木偶奇遇记》受到了苏苏的高度评价,并改写了《新木偶奇遇记》。匹诺曹的漫游被置于中国的情境下,他也蜕变为一个堕落的、任人摆布的木偶。应该说,这种改写有抗战救国的内在需要,但峻急的思想性还是限制了艺术性的书写,这也是这种改写难以成功的根本原因。颇有意味的是,与苏苏《新木偶奇遇记》的改写不同,左健改写的《匹诺曹游大街》则延续了原著人物的性格。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匹诺曹表现出了鲜明的阶级意识。这种借外国作品原型来揭示中国社会现实的改写显然渗透了中国本土的民族化立场,所改写的作品与原著之间的差异是审思中国作家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渠道。
注重社会功用性及其对儿童读者的塑造作用是左翼儿童文学观念的主导方向,这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旨趣是同频共振的。事实上,儿童文学在聚焦儿童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拒斥时代、社会和历史等内容,那种打着保护儿童而排拒其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观念显然违背了儿童文学的本意。受时代的感召,左翼儿童文学观念表现出较为明确的政治化和革命化的倾向。在《关于“儿童文学”》中,茅盾就曾指出,儿童文学“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给儿童们‘到生活之路’的,帮助儿童们选择职业的,发展儿童们的趣味和志向的”。(45)茅盾:《关于“儿童文学”》,《茅盾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412页。茅盾的《阿四的故事》一改五四时期人类学的方法,而采用了社会学的视角,儿童世界里增添了诸多成人与社会的文化内涵。阿四是一个“疾病儿童”的形象,“绿油油浓痰似的脏水”等外在恶劣生存条件使他“瘦弱如猴”,在其父母眼中,“死了倒干净”。在“儿童与时代”互为表里的故事框架内凸显了文本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如果说,《阿四的故事》是以儿童视角“速写”的小说,那么茅盾创作的《大鼻子的故事》则是一部带有社会剖析的“城市流浪儿的传奇”。茅盾以“大鼻子”这一流浪儿的遭遇来折射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状,并将当时社会的重大事件也介入其中,现实主义的底色很鲜明,而主人公“放浪习性”的蜕变也表征了作家对于时局的深入思考与探索。
可以说,茅盾等人的本土儿童文学创作没有将儿童视为抽象物或神秘的存在,其所塑造的儿童没有屈服于特定的道德世界,而是能在苦难、战争的情境下完成蜕变。即如陈伯吹所说:“不再是常见的家庭里的好儿子、学校里的好学生了;而是无产阶级的工人子弟,以及被‘三座大山’压垮了家庭的流浪儿童,还有生活鞭挞下、饥饿线上挣扎的童工等,作为表现作品主题的小主人公了。”(46)陈伯吹:《谈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陈伯吹文集》第4卷,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年,第84页。显然,这是左翼文学运动主潮下儿童文学遇合中外资源的结果,直面中国、面向儿童,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三、从“稻草人主义”到“张天翼模式”的转换及反思
叶圣陶的《稻草人》融入了成人的悲哀,郑振铎在为其作序时也予以理解的同情,在他看来,儿童“需要知道人世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识一样,我们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加以防阻”(47)郑振铎:《〈稻草人〉序》,《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5页。。可以说,这种渗透了成人社会和时代的童话体小说体现了以叶圣陶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现实情怀,与那种反对在儿童文学中表现社会宏大主题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观念有着较大的不同。五四时期那种表现“爱”和“美”的儿童文学作品也显得不合时宜了。例如黎锦晖的儿童剧就受到了质疑:《小小画家》《紫竹林中》《小国民的归宿》《麻雀与小孩》《蝴蝶姑娘》《葡萄仙子》“多半是童话式的,剧情多半是美丽、圆满的,中国的穷苦的小孩子们看了之后,只觉得好玩,并没有多大教育意义”(48)张早:《抗战中的儿童戏剧》,《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17页。。
受左翼思潮的影响,叶圣陶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开始转向。在《皇帝的新衣》中,叶圣陶借涌上街头的民众的呼喊“撕掉你的虚空的衣裳”来警醒国人不要遁入虚空,要起来反抗。如果说《稻草人》里“成人的悲哀”色彩还比较隐晦的话,那么到了《鲤鱼的遇险》时,叶圣陶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他要对丑恶的世界发出控诉:“咱们先前赞美世界,说世界上充满了快乐。现在咱们懂得了,世界实在包含着悲哀和痛苦。咱们应当诅咒这个世界。”(49)叶圣陶:《锂鱼的历险》,《叶圣陶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4页。叶圣陶认识到,儿童尽管有自己的小天地、小心灵,但在时局转变的语境下,他尖锐地指出:“小学生识见的范围已经从学校、里巷、家庭扩大开来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50)叶圣陶:《时势教育着我们》,《叶圣陶集》第5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30页。相比五四时期的童话,叶圣陶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古代英雄石像》《含羞草》《绝人种的人》《熊夫人的幼稚园》《慈儿》《火车头的经历》《鸟言兽语》等童话延续了其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但其批判性、讽刺性日趋强化。
在现代中国文学画廊中,张天翼的讽刺和幽默文风是独树一帜的,并且贯彻于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创作过程中。他贯彻了“生活就是斗争”的思想,儿童小说《搬家后》和《蜜蜂》都刻画了“反抗儿童”的形象。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旧式的倔强儿童,后者则是新时代的“伟大的斗争者”。(51)汪华:《张天翼的儿童小说〈蜜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55页。《小林和大林》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童话,出版后好评如潮。胡风认为,由《稻草人》到《大林和小林》,大概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但张天翼的童话却取了和《稻草人》完全不同的崭新的样相。对于这一结论,他是这样解释的:“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出现的《稻草人》,不但在叶氏个人,对于当时整个新文学运动也应该是一部有意义的作品。当时从私塾的《三字经》和小学的《论说文范》等被解放出来了的一部分儿童,能够看到叶氏用生动的想象和细腻的描写来解释自然现象甚至劳动生活的作品,不能不说是幸福的。可惜的是,那以后不但叶氏个人没有从这个成绩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且很少看到其他的致力儿童文学的作者。这个现象一直继续到《大林和小林》的出现。”(52)胡风:《关于儿童文学》,《胡风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页。无独有偶,孙犁也认为叶圣陶所开创的“稻草人主义”有“蜕变”和超越的可能。(53)孙犁:《谈儿童文艺创作》,《孙犁文集》补订版,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62页。如果说《稻草人》反映出文本的诸多“话语裂隙”体现了作家在“为儿童”与“为成人”两难的话,那么到了阶级政治与抗战政治的语境下,这种多声部的混杂被同一性的主题所整合,一种表征政治现实主义的儿童文学范式由此生成,张天翼即是这种范式的先行者与推动者。
在论及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差异时,张天翼洞见了儿童文学在教育儿童方面的独特性,认为写东西给孩子们看确实是关系到教育少年儿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的大事。针对当时儿童文学创作存在的误区,“做一个不劳而获的大富翁最幸福,而且用不着念书,用不着干活做事,受了欺辱也不要反抗,只等着神仙来帮助就是”,张天翼利用大林“吃得好,穿得好,不用做事情”的破灭来警示儿童读者,其创作的动机在于“想使少年儿童读者认识、了解那个黑暗的旧社会,激发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使他们感到做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虫那么可耻和无聊”(54)张天翼:《为孩子们写作是幸福的》,《我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76-77页。。为了凸显价值观念对于儿童人生走向的影响,张天翼以大林和小林为参照系来阐释其“真的道路”。《大林和小林》对“不劳而获”价值观的批判是尖锐的。为了彰显人物价值观念选择和命运走向同构的主题,张氏还将这种观念贯穿于人物成长的过程之中。小林童年时的天真、幼稚在社会发展及其成长过程中也逐渐隐退,劳动人民的觉悟和话语则日趋显露。关于小林话语转换,可以通过比照其儿时给大林的信及此后与站长的对话来一窥究竟。毋庸讳言,这种思想的直接介入显然有图解阶级话语的印记,不过,张天翼并没有将人物形象僵死于阶级话语或政治话语之下,跌入“思想大于形象”的窠臼。从思想层面看,《大林和小林》将现实内容与幻想内容细腻地糅合在一起,诸多诙谐、夸张情景的加入增添了童话的喜剧色彩,塑造了具有鲜明文体风格的政治教育童话。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大林和小林》突破了此前《稻草人》“小说体童话”的杂糅形式,以完全儿童式的想象和幽默来创作童话文体,从而推动了童话文体的自觉与发展。通过两兄弟一善一恶的比照,张天翼以“漫画式”的手法将阶级政治与民间童话中的故事类型结合起来,其本身故事形态的趣味性掩盖了沉重的社会讽刺和政治说教思想。
无论是将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标本”(55)汤锐:《中国儿童文学的生动标本》,《张天翼论》,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79页。,还是所谓的“张天翼模式”(56)杨佃青:《“张天翼模式”论》,《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第89-94页。,都从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融合来肯定张天翼童话的成就。具体而论,将童话的视角从“过去”拉到“现实”,借助儿童来展示社会广阔生动的讯息,传达教育的文学功用,这既是张天翼童话创作的特点,也是这一阶段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趋向。张天翼并不讳言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存在着某种套路,他说:“假如说到我们的写作有点‘差不多’,或者害了‘八股’症,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我们自己指出这些毛病,也完全跟艺术至上主义大爷们的用意不同:我们跟他们恰正相反,我们恰正是为了要增强艺术的战斗力。”(57)张天翼:《论“无关”抗战的题材》,《张天翼文学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66页。为了使思想和艺术都充满战斗力,张天翼学习了鲁迅关于创作儿童读物的“有益”与“有味”标准,(58)鲁迅:《〈表〉译者的话》,《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6页。不过,他并未融合两者,而是将其“益处”置于“有趣”之前。(59)张天翼:《〈给孩子们〉序》,《张天翼文学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50-351页。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思想性与艺术性难以接洽的困境。从时代的召唤看,这种主题先行的创作观念原本无可厚非,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型没有离弃社会现实而加入了全民抗战的洪流。但是从艺术层面看,这种过剩的思想性的前置还是压抑了艺术形式的探索。关于这一点,胡风敏锐地观测到了:“当然作者的目的是想简明地有效地向读者传达他所估定了的一种社会相理,但他却忘记了矛盾万端流动不息的社会生活付与个人的生命决不是那么单纯的事情。艺术家的工作是在社会生活的河流里发现出本质的共性,创造出血液温暖的人物来在能够活动的限度下面自由活动,给以批判或鼓舞,他没有权柄勉强他们替他自己的观念做‘傀儡’。”(60)胡风:《张天翼论》,《胡风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40页。即使《大林和小林》中也有诸多幻想的成分,但这种幻想还是被“功能化”,蕴涵着一种教育儿童的创作旨趣。对此,方兴严评论道:“张天翼的《蜜蜂》与《大林和小林》的语气和格调,极合于儿童趣味,虽然大林和小林的叙述形容得有些过分夸张,却能在儿童生活中发生极深刻的影响。”(61)方兴严:《儿童文学创作三条路》,《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37页。此后张天翼创作的《秃秃大王》《金鸭帝国》也延续了其传达“真的道理”的创作意图,在注重思想显效性的同时折损了艺术审美性。
事实上,这种有缺憾的艺术形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思想性的表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张天翼并没有忽视儿童文学是写给儿童阅读的这一事实,除了要“有益”外,他还注重以幽默的方式来传达思想。在这一点上,张天翼的观念与高尔基颇为类似。有人将认真、严肃理解为“枯燥无味的说教”,高尔基并不认同,他主张儿童文学作家要具有发挥诙谐的才能,“我们需要那种发展儿童的幽默感的、愉快和诙谐的”儿童文学作品。(62)以群:《高尔基对儿童文学的贡献》,《高尔基论儿童文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24页。《奇怪的地方》《失题的故事》延续了张天翼一贯的批判与讽刺风格,而且加入了符合儿童接受的幽默艺术手法。但是,他也重申了幽默艺术是为批判、讽刺服务的主旨:“幽默固然也是一种暴露,但暴露不一定是幽默。”(63)张天翼:《什么是幽默——答文学社问》,《张天翼文学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7页。张天翼这种幽默的艺术使其童话创作没有成为图解政治之物,表征了左翼儿童文学走出了此前的“稻草人主义”,并成为新时期“热闹派”童话沿袭的传统。
四、结语
在论述“范式”议题时,库恩反复提及了“危机”的意义,“危机是新理论突现的适当的前奏……一个新范式往往是在危机发生或被明确地认识到之前就出现了,至少是萌发了”(64)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伦吾、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9页。。左翼儿童文学的范式革命导源于启蒙现代性与革命现代性的转换,两种现代性的衔接并不是天然接洽的,它们之间存在着裂隙。对于这一裂隙的理解,学人常用“启蒙”与“救亡”的变奏来论究社会思潮转换的必然性。这原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启蒙与救亡并不决然对立,甚至还是同一议题的延展与深化。在中国历史动态语境下,启蒙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复杂扭结,并不能简单地认为仅是先后替代的关系。置身于这种危机之中的左翼儿童文学亟须重构新的范式,以适应时代和文学双重发展的需要。然而,在阶级本位取代儿童本位的过程中,儿童的“个”性消泯于“人”的群体性中,思想性的高涨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左翼儿童文学艺术性的发展,而这种受缚的艺术形式又反过来制约着思想性的表达。到了抗战时期,这种“悖论性的怪圈”(65)吴翔宇:《中国儿童文学“母语现代化”重构的逻辑与路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47-152页。并未消失,反而在民族本位强化的语境下逐渐加剧,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也日趋弱化,从而夯实了现实型儿童文学体系和文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