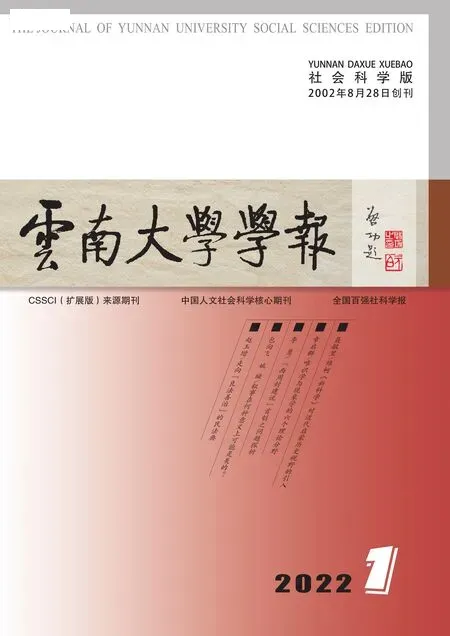王朝是“帝国”吗?
——以寰宇图和职贡图为中心
成一农,陈 涛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一、问题的提出
在清代晚期之前的中文文献中,几乎从未将历代王朝以及本朝称为“帝国”,检索《四库全书》电子版,也基本没有“帝国”一词。(1)虽然以“帝国”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能检索到318条记录,但其中绝大部分结果实际上都不是“帝国”一词,而是由于古汉语缺乏标点形成的类似于“皇帝国号”这样的检索结果。西方人将历代王朝称为“帝国”,大致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早期,即“大量欧洲古文献证明……早在明朝时期,欧洲通过耶稣会士等媒介,将中国称之为‘中华帝国’的说法已然确立并初步流行开来”。(2)曹新宇等:《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帝国”这一概念在清代晚期也逐渐影响了清人对清朝的认知,再加上鸦片战争之后,传统“天下秩序”的转型,因此清人逐渐开始将清朝称为“大清帝国”。同时,从清末开始,中国学者也开始将“帝国”一词应用于之前的历代王朝,且逐渐接受了“中华帝国”这一提法。
时至今日,在很多研究中,尤其是西方学者的研究中,通常将历代王朝称为“中华帝国”,如著名的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3)[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以及笔者翻译的林达·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4)[美] 林达·约翰逊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在众多的清史研究中也经常将清朝称为“清帝国”或“大清帝国”(5)如[美]柯娇燕著:《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陈兆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等;且这样的提法也已经被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以“中华帝国”“清帝国”为关键词在期刊网上就能查到众多的论文;这种用法也逐渐渗透到了民间,如国内的一些电视剧以及众多通俗读物中逐渐开始将清朝称为“清帝国”,此外还有“秦帝国”“汉帝国”“唐帝国”“明帝国”等众多提法。
总体而言,将清朝以及历代王朝称之为“帝国”,在历史学界以及民间似乎成为一种共识,甚至成为一种常识,但截止目前极少有学者去考虑这样的提法是否合适,或者这样的提法是否在所有研究中都适用,以及是否会带来一些误解。
近年来,随着“新清史”的兴起,少量中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将“清朝”视之为“清帝国”是否合适。(6)参见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反思的出发点是将“帝国”定义为“介于民族国家和国家联盟之间的半国家形态”,并由此讨论一种近现代意义上的“帝国”的定义是否适用于“清朝”。(7)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对此,以汪荣祖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帝国有许多不同类型,不能一概而论;近代的‘大英帝国(the British Empire)’与古代帝国就极不相同”,因此“习用‘帝国’描述传统中国并无不妥” 。(8)汪荣祖:《“中国”概念何以成为问题——就“新清史”及相关问题与欧立德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帝国”一词的含义确实在历史上存在变化而且是多元的,正如曹新宇指出的,16、17世纪,“当时欧洲使用的‘帝国’概念比较宽泛,只要是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专制皇帝所统治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治理着多民族臣民的大国,或拥有臣服之国(如‘藩属’)的大国,都可泛称为‘帝国’” 。(9)曹新宇等:《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就这一定义而言,今人将历代王朝称之为“帝国”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我们今人的视角和定义,由此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这种定义,即“专制皇帝所统治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治理着多民族臣民的大国”只是一种从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民族构成等角度进行的定义,而没有涉及空间结构等结构性的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因此,以往有意无意使用的这一“帝国”的定义虽然宽泛,但并不全面,因此必然有适应范围,亦即在讨论与地理空间范围、民族构成等相关问题时,使用“帝国”一词来指代清王朝或者历代王朝,应当没有太大问题,但如果涉及空间结构等方面时,用“帝国”来指代清王朝或者历代王朝可能就会存在问题。不仅如此,上述这一定义中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一种现代人的认知,不一定是当时人的认知。
面对上述问题,本文即以图像史料作为主要材料,结合以往的研究,从空间政治结构和“疆域”的角度,讨论“帝国”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
二、王朝的“天下”与“天下秩序”
以往从古代地图,主要是寰宇图(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世界地图”)和职贡图入手,研究古人对历代王朝的空间结构和政治结构,即“天下秩序”观念的文章虽然数量众多,但观点基本是一致的,代表者就是葛兆光,如《想象天下帝国——以(传)李公麟〈万方职贡图〉为中心》,(10)葛兆光:《想象天下帝国——以(传)李公麟〈万方职贡图〉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还有管彦波的《明代的舆图世界“天下体系”与“华夷秩序”的承转渐变》和《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11)管彦波:《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这些研究或者只是简单地叙述了“华夷秩序”,或者在将历代王朝理解为一个“国家”或者“帝国”的背景下,对“华夷”构成的“天下秩序”进行了论述,如葛兆光的《想象天下帝国——以(传)李公麟〈万方职贡图〉为中心》,“本文以(传)宋代李公麟创作《万方职贡图》的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为例,考证当时北宋王朝与周边诸国的朝贡往来实况,并与《万方职贡图》中的朝贡十国进行比较,试图说明如果《万方职贡图》真是李公麟所绘,那它的叙述虽然有符合实际之处,但也有不少只是来自历史记忆和帝国想象。这说明宋代中国在当时国际环境中,尽管已经不复汉唐时代的盛况,但仍然在做俯瞰四夷的天下帝国之梦。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职贡图’的艺术传统还一直延续到清代,而类似‘职贡图’想象天下的帝国意识,也同样延续到清代” 。(12)葛兆光:《想象天下帝国——以(传)李公麟〈万方职贡图〉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此外,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一书的第三章《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的“从天下到万国:古代中国华夷、舆地、禹迹图中的观念世界”一节中以一些地图为例,谈论了古代的“观念世界”,结尾谈及利玛窦地图的传入“给中国思想世界带来了一个隐性的、巨大的危机。因为它如果彻底被接受,那么,传统中华帝国作为天下中心,中国优于四夷,这些文化上的‘预设’或者‘基础’,就将‘天崩地裂’”。(13)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1页。管彦波《明代的舆图世界“天下体系”与“华夷秩序”的承转渐变》的结论就是“然而,入明以后,承继蒙元帝国东西扩张的世界经验,有了郑和下西洋和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新鲜域外地理知识的持续发酵,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念也在被消解、重构的过程中有了太多的变化,许多睁眼看世界的开明士大夫,他们在重新寻找解释天下体系的合理依据的同时,也有了明显的‘世界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只是天下万国中的一个国家。正是在这种天下观向世界观逐渐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天朝上国’的帝国观念,实际上已悄然在发生变化” 。(14)管彦波:《明代的舆图世界“天下体系”与“华夷秩序”的承转渐变》,《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此处先不讨论上述这些结论是否成立,也先不关注其中提到的“帝国想象”“帝国意识”和“中华帝国”是否成立,但以往这些研究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他们似乎在心目中将王朝与周边各国(四夷)在空间上区分开来,即虽然周边各国(四夷)臣属于王朝,但在地理空间上,周边各国(四夷)是在王朝之外的。退一步讲,这些研究没有能清晰地表达王朝与各国(四夷)在地理空间上的关系或者政治结构和空间结构。
下文首先在这些认知的基础上,分析历代王朝的政治结构和空间结构。虽然在分析时,我们还是以地图和职贡图为材料,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一、尽量用现代人的话语来阐释这些图像中所反映的历代王朝对于王朝空间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认知;二、在分析时尽量不使用“帝国”“国家”这类具有近现代西方涵义的词语。
以往研究者经常关注的寰宇图(大致相当于“世界地图”)基本就是《华夷图》和《禹迹图》等能反映“华夷”观的地图,虽然有时也提及了《大明混一图》《天下九边分野 人迹路程全图》和《大明九边万国 人迹路程全图》以及《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和《皇舆全览图》,但大都只是对其中蕴含的“地理知识”和“华夷观”的分析,而没有意识到这些地图实际上反映了历代王朝对于王朝空间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认知,而这也是本文不同于以往研究之处。下文先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寰宇图”进行介绍。
《大明混一图》,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绘制,绢底彩绘,作者不详,清朝初年,将全部汉文注记用满文标签覆盖。地图长347厘米,宽453厘米,方位上北下南,描绘范围东起日本,西达欧洲,南至爪哇,北抵蒙古。图中着重描绘明王朝各级治所、山脉、河流的相对位置,镇寨堡驿、渠塘堰井、湖泊泽池等共计数千余处。明初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治用粉红长方形书地名表示,其他各类聚居地均直接以地名定位,不设符号;蓝色方块红字书“中都”(今安徽凤阳)、“皇都”(今江苏南京)表示首都所在;山脉以工笔青绿山水法描绘;全图水道,除黄河外,均以灰绿曲线表示,黄河则以粗黄曲线表示。该图现藏北京故宫第一历史档案馆。需要注意的是,这幅地图的绘制范围涵盖了亚非欧,远远超出了明初所能直接控制以及与其有着朝贡、藩属关系的地区,且图中并没有明显的“疆域”界线,仅以地名方框的不同颜色加以区别,但该图为“大明混一图”为名,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天下九边分野 人迹路程全图》,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金陵曹君义刊行,此图除了大量的说明文字和表格外,中间地图部分为纵92厘米,横116厘米的椭圆形全球图。该图虽然以明朝为主要表现对象,且明朝直接控制的地域占据了图幅中的大部分面积,但受到西方传教士所绘地图的影响,图中绘出了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以及南极,且标绘有经纬网。《大明九边万国 人迹路程全图》,绘制者不详,原图为王君甫于康熙二年(1663年)刊印发行,由日本人“帝畿书坊梅村弥白重梓”,但“重梓”时间不详。在内容上该图与曹君义的《天下九边分野 人迹路程全图》几乎完全一样,图面上的显著差异就是删除了经线和纬线,此外由于经由清人翻刻,因此在行政区划上进行了一些修改,如“应天府”被改为“江宁府”,“南京”改为“南省”。不过还有几处改动很可能是日本人“重梓”时造成的,如:虽然并未从日本人的角度对图中关于“日本”的描述重新改写,但补有“今换大清国未”;在“琉球”的文字说明后补有“清朝未到”。通常而言,清朝人绘制的地图通常不会称清朝为“清朝”或者“大清国”,而应称为“大清”“清”或“本朝”。与《大明混一图》类似,从绘制范围来看,该图实际上是一幅“天下图”,或者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地图”,而不是一幅表现今人所理解的明朝“疆域范围”的地图,其图名中的“大明九边万国”同样颇为值得深思。
还有清代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系列地图。这一系列地图的祖本应当是黄宗羲的《大清全图》。黄宗羲于康熙十二年刊刻的《大清全图》基本上接受了《广舆图》的风格,地图所反映的地理范围与《广舆图》的“舆地总图”一样。继黄宗羲的地图以后最早出现的属于同一类型的地图就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制作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此图基本轮廓与黄宗羲图差不多,文字注记比黄图多一些,在朝鲜半岛、中国西南部分、图的右下角都有图文。此图与黄图表现上差别最大的部分在于东北,图中在东北和今内蒙古地区画了一些线框分别记载了蒙古部族的名称。此外,该图还把朝鲜半岛绘制出来。该图的这些特点,影响了以后的同类地图。它的影响实际上比黄宗羲的原图更为深远,以后出现的黄宗羲系列地图也主要受到了此图的影响。黄宗羲的孙子黄千人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从地图的外貌上来看,该图应该近似于康熙五十三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且该图受到传教士地图的影响,标注了欧洲国家的国名。嘉庆年间,以乾隆三十二年黄千人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为底本摹刻的,名称、内容、形式和图文相似的印本甚多。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幅嘉庆十六年(1811年)刻本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墨印着手彩,未注比例;分切八条幅挂轴,全图拼合整幅为134×235厘米。全图覆盖范围东起日本,西抵温都斯坦(印度),北至俄罗斯界,南至文莱国,欧洲诸国均以小岛屿形式列于图左。黄河源画了三个相连的湖泊:星宿海、鄂灵湖、查灵湖;山脉为立面形象饰蓝色,海水以蓝色波纹,沙漠为红色点纹,省界用各种颜色相区别。(15)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8页。总体而言,《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同样是一幅“天下图”和“世界地图”,但以“大清”为名似乎同样是今人无法理解的。
康熙《皇舆全览图》,前人研究成果众多,这里无意进行太多细节上的描述。大致而言,该图以通过北京的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绘制范围东自黑龙江口,西迄哈密,南起海南岛,北至贝加尔湖。哈密以西因准噶尔部之乱未能实测,西藏仅派喇嘛测量了旅程距离;湖南、贵州苗疆因未能进入,尚属空白;朝鲜半岛的绘制取自朝鲜王宫内的旧图,只是在两国边境上由传教士进行了校正。雍正《十排皇舆全图》,雍正三年(1725年)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编绘而成,该图所绘地域要比《皇舆全览图》辽阔,北起北冰洋,南至海南岛,东北濒海,东南至台湾,西抵里海。乾隆《十三排图》,又称乾隆《内府舆图》,以康熙《皇舆全览图》为基础增绘而成,该图的绘制范围东北至萨哈林岛(库页岛),北至俄罗斯北海,南至琼岛(海南岛),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及红海,绘制范围约是康熙《皇舆全览图》的一倍。虽然这一系列地图不是“世界地图”,但其涵盖范围同样超出了清朝当时所能实际控制的区域,由此“皇舆”一词对于今人而言就显得颇为“突兀”。
总体而言,这些“天下图”“寰宇图”虽然大都以某某朝作为图名,但其所描述的地域都远远超出了这些王朝所直接控制以及存在藩属、朝贡关系的国家、政权和部族的范围,显然其对王朝“疆域”的认知以及王朝的政治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认知完全不同于今人所定义的“帝国”。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还需要分析一下《职贡图》。
以历代的《职贡图》入手讨论“华夷秩序”和“天下秩序”的研究数量同样众多,除了上文提及的葛兆光之外,还如苍铭等的《〈皇清职贡图〉的“大一统”与“中外一家”思想》、(16)苍铭等:《〈皇清职贡图〉的“大一统”与“中外一家”思想》,《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杨德忠的《元代的职贡图与帝国威望之认证》(17)杨德忠:《元代的职贡图与帝国威望之认证》,《美术学报》2018年第2期。以及赖毓芝的《图像帝国:乾隆朝〈职贡图〉的制作与帝都呈现》(18)赖毓芝:《图像帝国:乾隆朝〈职贡图〉的制作与帝都呈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期(2012年),第1页。等,但这些研究同样大多是基于将王朝作为“国家”和“帝国”而进行的讨论。而且,这些研究基本都忽略或忽视了对“职贡”含义的分析。
中国古代“职贡”一词的含义指的是各地按等级、地区向王朝中央交纳贡纳的制度,也即“纳职贡”是臣属于王朝的地区的职责和义务,也是其臣属于王朝的标志。以往将王朝作为一个“国家”或者“帝国”进行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王朝”与朝贡的国家、部族、政权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但没有意识到“纳职贡”意味着“臣属”。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臣属”是王朝视角的,即王朝认为“纳职贡”意味着“纳职贡”的地区承认了王朝的统治权,但来“纳职贡”的地区是否意识到了这点或者是否认可这点则是另外一回事。
以乾隆时期绘制的《皇清职贡图》为例。这一图册的绘制始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基本绘制完成,此后经过多次补绘,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才最终绘制完成。此后,嘉庆时期又进行了补绘。(19)参见祁庆富:《〈皇清职贡图〉的编绘与刊刻》,《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皇清职贡图》第一卷包括朝鲜国、琉球国、安南国、暹罗国、苏禄国、南掌国、缅甸国、大西洋国、小西洋国、英吉利国、法兰西国、瑞国、日本国、文郎马神国、文莱国、柔佛国、荷兰国、鄂罗斯国、宋腒朥国、柬埔寨国、吕宋国、咖喇吧国、亚利晚国等国的外国官民,及达赖喇嘛地方政权所属藏民,伊犁等处厄鲁特蒙古,哈萨克头人,布鲁特头人,乌什、拔达克山、安集延等地回目,哈密及肃州等地回民,土尔扈特蒙古台吉等。第二卷为东北边界地带的鄂伦春、赫哲等7族,福建所属古田县畲民等2族,台湾所属诸罗县诸罗等13族,湖南省所属永绥乾州红苗等6族,广东省所属新宁县傜人等10族,广西省所属永宁州梳傜人等23族。第三卷为甘肃省与青海边界地带土司所属撒拉等34族,四川省与青海及达赖喇嘛地方政权交界地带土司所属威茂协大金川族等58族。第四卷为云南省所属景东等府白人等36族,贵州省所属铜仁府红苗等42族。(20)以上介绍还可以参见王蔚《〈皇清职贡图〉的绘画史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齐光在《解析〈皇清职贡图〉绘卷及其满汉文图说》中提出“《皇清职贡图》绘卷中的满文图说在涉及各种‘国家’‘民族’等‘人的集团’时,显示出其特有的功能和统治理念。首先,是表示‘国家’的‘gurun’,及相应的‘国之官员 gurun i hafan’‘国人 gurun i niyalma’。其次,是表示内陆亚洲政治集团的‘部 aiman’,及相应的‘头目 aiman i data’‘部人 aiman i niyalma’。再是,表示人的地缘结合的‘土司 aiman i ahūcilaha hafan’,及其‘土民 aiman i niyalma’,以及‘土千户 aiman i mingganda、土指挥 aiman i jorisi、土百户 aiman i tanggūda’。另外,由来于自汉语的‘番子 fandz’‘番民 fandz irgen’,及表示血缘结合的‘社 falga’等等。以上这些都不是随意的称呼,都反映了清朝对该人群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去实行的统治政策” ,(21)齐光:《解析〈皇清职贡图〉绘卷及其满汉文图说》,《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不过在该文中,齐光依然将清朝称作“国家”和“帝国”,即“清朝是一个以不同的统治形式,基于不同的支配理念,统合众多持有不同生产方式及社会秩序‘民族’的,各地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清朝皇帝权力或清朝‘国家’权力渗透当地‘民族’社会的程度又有所不同的,一个多样性的、多层次的、多种政治制度并存的东方大帝国” ,(22)齐光:《解析〈皇清职贡图〉绘卷及其满汉文图说》,《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其所使用的“帝国”一词的定义显然是之前提到的学界常用的定义。
但基于“职贡”的含义,《皇清职贡图》实际上反映了清朝自认为其是所有“纳职贡”的诸国、部族、政权的统领者,而《皇清职贡图》中记录的“职贡”的诸国、部族、政权包含了欧亚非,显然远远超出了清朝当时直接控制的区域。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结构中,王朝是超越于“国家”“部族”之上的一种存在。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的话语体系中,虽然偶尔也将王朝称为“国”,也存在以“国”命名的少量机构,如“国子监”“国史馆”等,但在大多数语境下,王朝名之后通常是不加通名“国”的,如明朝,通常就被称为“明”“大明”。在《明史》中,没有将明朝称为“明国”,而称为“大明”的则多达100余次;《宋史》中也极少将宋朝称为“宋国”,而称之为“宋朝”“大宋”的则数量众多。大致而言,在古代的话语体系中,王朝是高于“国”的存在。(23)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于这点,今后当另撰文叙述,但上述观点应是基本成立的。
通过上述对古代“寰宇图”和“职贡图”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王朝认为其所统治的地理空间的范围,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今人所认识到的王朝“疆域”,应当涵盖了“世界”,或者当时人所认识到的“世界”,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且在这一空间中,王朝是超越于“国家”“部族”之上的一种存在,而不是众多“国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空间中存在着等级差异,王朝直接控制的区域在级别上要高于周边,这点在“寰宇图”和“职贡图”中都有着明确的表达。如在几乎所有清末之前绘制的“寰宇图”中,《禹贡》所描绘的“九州”或者王朝直接控制的区域都被放置在了地图的中央,且不成比例地放大,而其他“国家”“部族”几乎只是装饰性的被点缀在周围。(24)参见成一农:《中国古代舆地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而在《皇清职贡图》中,没有绘制来“纳职贡”的是汉人、满人以及一些蒙古部族,这反映了清朝政权的构成,(25)齐光:《解析〈皇清职贡图〉绘卷及其满汉文图说》,《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反映到空间上,则对应于“九州”、东北以及蒙古东部。总体而言,在王朝的空间中,存在着一种等级差异,且其中《禹贡》所描绘的“九州”固定作为这一等级系统的中心。
实际上,王朝的这种空间结构和政治结构,是先秦以来构建的“天下秩序”的反映。唐晓峰在《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26)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中对上古“天下秩序”的构建及其对后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对于我们理解“寰宇图”和“职贡图”所展现的王朝的空间结构和政治结构有着极大的帮助,唐晓峰认为:“在周朝分封地域范围的四周,全面逼近所谓的‘夷狄’之人。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华夏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王国维称其为‘道德之团体’)直接面对夷狄世界的局面。居于中央的华夏与居于四周的夷狄的关系遂成为‘天下’两分的基本人文地理格局。”(27)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第209页。“对夷狄是绝对的漠视,反之,对华夏中国是绝对的崇尚。华夏居中而土乐,夷狄远处而服荒,这种地域与文化的关系被推广到整个寰宇之内,唯有中国是圣王世界,其余不外是荒夷或岛夷,越远越不足论。如此全世界二分并以华夏独尊的地理观念在随后的千年岁月中一直统治着中国人的头脑。”(28)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第211页。“需要注意到的是,华夷之限不是政治界限,更不是国界,也不是种族界限,而只是文化界限……反而希望‘四海会同’‘夷狄远服,声教益广’,也就是要与夷狄共天下,当然,前提是‘夷狄各以其贿来贡’”。(29)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第212页。
大致而言,王朝的空间结构和政治结构就是:首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亦即“天下”或者“全世界”都是王朝名义上的管辖范围;其次,“天下”是由“华夷”两部分构成的,其中“华”所在的“九州”居于首要地位,同时是王朝理所应当直接占有的;再次,“蛮夷之地”虽然不一定要去直接加以控制,但王朝应当要做到“四夷宾服”,或者应当追求“四海会同”“夷狄远服,声教益广”。理解了这些理念,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清时期绘制的那些“寰宇图”其范围要远远超出其直接控制的范围,也就可以理解“好大喜功”的乾隆为什么要绘制涵盖了如此广大地域的国家和部族的《皇清职贡图》了,这些图像反映了王朝对其所认为合理的空间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认知,同时也是这些认知的产物,由此不仅宣扬了王朝的合法性,而且通过描绘范围广泛的“蛮夷”以宣扬王朝的“盛”。
三、结 论
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在所有的历史研究中,我们都是“他者”,真正的“我者”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都必然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认知基础上的,而不可能真正进入到所研究的历史语境和场景中,这应当是历史研究者的无奈。但史学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不仅要尽可能清晰地意识到研究者所持的视角、立场、知识背景、目的和语境,而且更不能用今天的视角来解释古代且认为这也是古人的认知,并由此“议古论今”。当前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与外国学者相比,自己是“我者”,但对这种差异的强调,是“五十步笑百步”,所有研究者实际上都是“他者”,且很可能正是这种自我认知与现实上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学者忽视了一些我们习以为常但存在问题的认知,本文所涉及的“帝国”就是一例。
如上文一再提及的,虽然“帝国”一词并没有非常精准的科学定义,但通常“帝国”指的是领土非常辽阔,统治或支配的民族、人口众多,拥有极大的影响力的强大国家。从今人看来,用这一概念来称呼历代王朝,尤其是那些强盛的王朝似乎并无不妥。但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帝国”与上述图像所阐述的“王朝”,存在两个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帝国”无论地域多么辽阔,但都有着一定的范围,而“王朝”的地域则涵盖了整个“天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涵盖”,并不是要去直接占有,而是名义上的“占有”,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除了“华”和“九州”之外,其他的“蛮夷”之地,并不值得去关注。
第二,虽然“帝国”之间必然存在争斗,但大部分“帝国”在名义上是可以并存的,或者并存是帝国之间的一种可以接受的状态。但对于“王朝”而言,同一时期,在名义上,“王朝”只有一个。虽然很多时候,存在多个“王朝”并存的局面,且这些“王朝”之间由于无力消灭其他“王朝”,因此对于这种“并存”在表面上也达成了一些“默契”,但在内部话语上,则都一再否认其他“王朝”存在的合理性,(30)参见黄纯艳:《绝对理念与弹性标准:宋朝政治场域对“华夷”“中国”观念的运用》,《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且都力求最终要消灭其他“王朝”。
总体而言,就空间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的“疆域”(31)“疆域”一词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王朝时期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具有领土色彩的疆域意识。和“天下秩序”而言,“帝国”与“王朝”是根本不同的。基于此,在研究与“疆域”“国家的构成方式”等问题时,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将一些对“帝国”的认知潜移默化的带入到“王朝”的研究中。
如“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欧立德,虽然其认同且试图理解延续至清朝的“华夷观”,但在其研究中依然将清朝称之为“帝国”,如在《乾隆帝》一书中提到“到了乾隆生活的时代,情况已大不一样。此时的世界,边疆已然封闭,疆界已然划定……因此,乾隆的普世天下观只适用于大帝国中的那些小的领地,这些领地中的统治者通过书信、朝贡以及册封等形式,承认清帝的至上君权,但是这种承认有时仅具有象征意义”。(32)[美]欧立德:《乾隆帝》,青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82页。就这段话整体而言,属于现代人的认知,因为对于当时的乾隆以及大多数士大夫而言,依然相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华夷”两分的天下,否则就无法解释《皇清职贡图》以及《内府舆图》这样的作品了。欧立德的这本书总体上希望通过站在乾隆的角度来对一些问题加以解释,如在上面所引这段话之前,他还提到“乾隆也知道在清朝之外还存在其他国家,如荷兰、印度或者俄罗斯,而且也很清楚他对于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丝毫的控制力可言”,“乾隆承认其他国家的独立存在”,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视角实际上还是现代的,而不是乾隆的,因为在乾隆眼中的“独立”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独立”,而在“华夷”体系下,不是所有“蛮夷”对于王朝都是有意义且需要控制的,它们通常只需要“朝贡”表示“顺服”即可,或者王朝认为它们表示了“臣服”即可,因此欧立德并没有真正理解古代的“天下秩序”,而根源则在于其没有真正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角度来对王朝的空间结构和政治结构加以理解,其中学界常用的“帝国”一词也对其产生了误导。
笔者认为,“新清史”最大的症结就在于他们自认为从清朝统治者的角度来认知清朝,但实际上在出发点上他们的很多认知就是“现代”的,从其所用的词语“帝国”“中国”和“国家”等就可以看出这点,且他们还试图以这样的结论来理解和解释今天的中国,当然大多数“新清史”的批评者也是如此。如果从现代认知古代的话,那么必然会存在可以并存的多种视角,因而这也是参与“新清史”辩论的都认为自身是基于清朝的视角但实际上骨子里是现代视角的各方,难以真正说服对方的根源,这也是以往“新清史”的反驳者很多时候显得无力和不彻底的重要原因。此外,“新清史”认为“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且不论“清帝国”一词本身就不恰当,按照上文的分析,实际上自秦汉以来的王朝都是超越于“中国”的,这再次表明“新清史”实际上未能真正理解王朝的政治和空间结构。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且不仅涉及“新清史”,而且涉及目前古代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如“中国疆域沿革史”等,与本文的主旨无涉,不再展开。
最后,在很多研究中使用的“中华帝国”“帝国”“清帝国”等语词,实际上只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界定(即王朝存在的时间和王朝直接控制的空间),因此对研究本身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等。不过在这些研究中,完全可以用“王朝时期”“清朝直接统治的地域”等语词,因此建议今后在有关“王朝”时期的研究中都应当避免使用“帝国”一词,且要慎用“国家”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