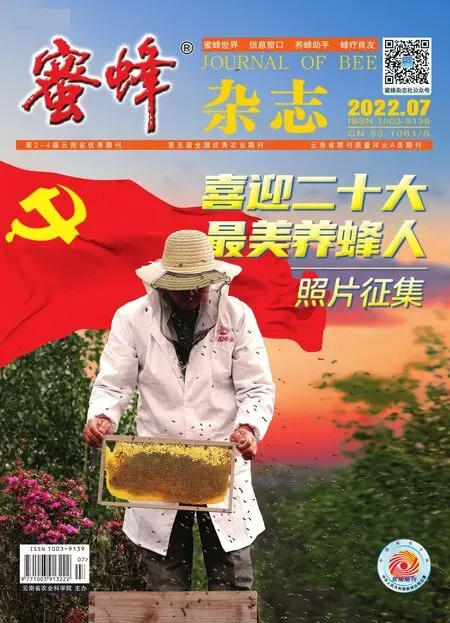我与蜜蜂(一)
王凤贺
(北京海淀区曙光花园中路5号院11楼4门503,北京 100097)
1 童年记忆
笔者(曾用名王凤鹤)于1955年10月出生于北京市顺义区杨镇汉石桥村一个中农家庭。从儿时记事起,我家院外东房山坡上就有3个桶状的东西——中蜂;屋檐下方有很多鸽子窝,30多只鸽子在院落上空来回飞翔,时常还吃到乳鸽肉饼。家中还有数10只山羊,鸡、猪、兔等动物,这些都是我祖父的喜爱,也是留给我童年的记忆。
其中最吸引我的是那3桶中蜂,每当春暖花开时节,花朵上总是嗡嗡作响,却不知中蜂在采花传粉繁育后代扩大家族成员。每当我不高兴或偶尔哭闹的时候,祖父、祖母就会用香甜的蜂蜜水哄我,甜甜的味道是我童年美好快乐的记忆。每当过年、过节时家里来了一些亲朋好友,等他们走时,总见祖母分别送给他们一两罐蜂蜜。但是由于蜂群数量少,产蜜有限,这种快乐也不是经常能有的。当时我就想,以后长大了也要养很多很多蜜蜂,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能喝到香甜的蜂蜜水。
2 家乡的回顾
老家的村庄处在低洼地带,为了防涝全村所有的房屋都建在很高的土台上,村内村外就出现了很多较大水坑,这是盖房时取土形成的。村庄的东、西、南三侧方向均被土堤包围,大堤外边是上万亩的芦苇荡(现成为汉石桥湿地),在童年时代,每年6~8月份雨季来临,村里道路便开始积水,各个水坑水满溢出与低洼处连成一片,人们出入劳作或上学都要蹚水经过。1968年村里安装了三个抽水站,此后每到雨季水站昼夜工作往堤外排水,为加紧防汛排涝,村民也自发组织到田间、地头排涝,在各个道路交叉路口,早已建起了许多小型石桥,石桥两侧挖好了排水沟直通村南边的主导河流,便于汛期雨水被机站排入水库,防止村庄大田庄稼被淹没,村庄名字是否因石桥过多而得名(汉石桥村)未得考证。虽然村庄的低洼环境给本村作物生产带来不便,但却给我们孩童时期带来美好的环境和无穷的乐趣。每年雨季一到是村民到田间排水,同时也是大家在田间捕鱼捉虾蟹的好机会,给村民的生活增添了“美好鲜味”。在当时经济匮乏的年代,近万亩的芦苇荡鱼虾成群,鸟语花香、蜂蝶飞舞,构成了一副完美的画卷。目前已成为“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汉石桥村湿地”是北京市自然湿地保护区之一,是目前北京市现存唯一大型芦苇沼泽湿地,也是多种珍稀水禽的栖息地。调查发现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7种,成为汉石桥湿地的标志性特征。目前,汉石桥湿地是一个以休闲、娱乐、度假、健身、会展为主要内容的5A级湿地生态旅游区,同时,这里植被资源丰富,环境良好,是发展养蜂业的理想地区,国内以蜜蜂授粉为龙头的大型授粉专业蜂场(北京蜂为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农之翼养蜂场)于2009年就建在汉石桥湿地西侧。
3 我的养蜂之梦
1971年我中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到密云县溪王庄镇黑山寺村参加国家的沙通铁路建设工程,这里是山区,近邻密云水库西部2 km的路程,工作之余跟同事一起散步闲逛,无意间发现山区里有几家庭院内有很多箱蜜蜂,这也不禁让我回忆起童年的“甜蜜”时光。这些家庭与祖父养蜂不同,他们有的用活框饲养(西方蜜蜂)有的用竹篓和木桶,一了解他们把养蜂作为家庭副业来对待,生产的蜂蜜可以上交给土产部门卖钱支撑家庭的经济开支,个别家庭院落饲养群数较多,用活框蜂箱饲养的西方蜜蜂,大部分以定地饲养为主小转地为辅,主要在6~8月份采集山上的荆条。由于当地资源环境适合发展养蜂,每到7月中旬荆条流蜜时节,一些外地蜂场也会来此地放蜂,采蜜量很好(每箱蜂的产量在65 kg左右)。由于触及我儿时的兴趣和喜好,我经常跟这些养蜂人聊天沟通,发现当时养蜂作为家庭的另一种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随着不断的接触和了解,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爱养蜂,决定回家后购买几群蜜蜂进行饲养,等技术成熟了再逐渐扩大规模,完成儿时的梦想与愿望。
4 返乡务农
1975年铁路修建好,我回到了村里,当时的工作是负责全村农业植保工作(玉米制种和庄家病虫害防治)。由于工作较忙,购置蜂群的计划也暂时搁浅了。在工作期间,时常遇到和接触病虫害防治与农药拌种和土壤施肥等相关知识的难题,由于上学时期知识储备有限,在指导各生产队应用方面感到力不从心,做梦都想能再有第2次学习这些知识的机会该有多好,此时才懂得“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的真正含义。上天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
1976年7 月的一个晚上,在经过一天忙碌工作即将结束,傍晚当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我隐约听到村大队广播站播报政府要招收一批学员去大学读书的信息,愿意参加的青年可到大队报名,我仔细听清之后,瞬间我就从睡意中清醒过来,翻身跳起直奔大队报名登记。一天的身心疲惫一下子就没有了,只觉得机会来了,心想若能被录用,我一定抓住机会,认真学习知识,勤奋工作,回报家乡,争取早日改变我村粮食产量低的落后面貌。
当我到达村部时,已有四五个初中同龄青年在村部等待报名,过了一会,村部一位领导向我们说明了这次招收学员的基本情况,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本村只有一个名额,并且属于“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学员,户口在家不动,读书毕业后还回到农村。当时的农村青年只要离开农村,到外边当个工人都要挤破脑袋,甚至还要托人走后门,何况出去读书这么好的机会,于是大家纷纷报名。
看到此景,我瞬间有些灰心了,因为村里仅有一个指标,参与竞争的人又多,如果里面有跟村领导关系密切的人,那我岂不是没有机会了?幸运的是经过激烈推荐竞争后,大队没有自己决定名额给谁,而是把报名上学人员分配到全村4个生产队去投票推荐选举,幸运的是我的选票最多,顺理成章我的名字被大队报到公社(乡政府)完成了我的心愿。后来得知确实有些人想通过“特殊渠道”把我替掉,最终乡教育部领导坚持原则,我才如愿以偿实现第2次上学梦。就这样我成为全国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之一,在1976年10月22日开始入学,我荣幸的进入了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学制为3年。
5 我在北大的生活
似乎从我出生就注定了与蜂的缘分,上学的第一天我就得知自己被分到了北京大学生物系昆虫专业学习,学习的内容是面对农村植物保护和常见的8大种类昆虫分类,同时涉及病虫害鉴定与防治等课程。当时心情和现在一样,北大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之一,老教授、老专家都是留学归来或者是学成留校的优秀人才。我们这批工农兵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在年龄、学历、资历、工作各方面都不相同,年龄大到40多岁,小到20岁;有参过军的、有来自学校、农场、机关的相关行业,多数是来自京郊区县乡镇农村的;学历包括小学、中学、高中毕业。虽然大家各方面不尽相同,但是都有一颗虔诚的心,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机会,学到更多的知识,回报社会回报家乡。因为我们是“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批学员,老师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耐心和高度重视,尽可能地为我们传授多一些知识。
大学3年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明确了学习目标以及回到家乡改变农村面貌的决心,每天晚上和周日都到那里看书,不敢怠慢,生怕虚度大学时光。然而,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最后一年的毕业实习期。当时由于我的勤奋好学,以及如饥似渴的求知态度,老师也很关照我,在准备去实习的时候,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是从农村来的,毕业后还要回到农村,出差到外地的机会不多,也不太容易,如果想趁实习机会出去走走看看,可以帮我安排到瓢虫迁飞调查组工作,正好现在学校安排一些同学到外地实习,搞黏虫迁飞瓢虫迁飞调查,老师亲自征求我是否愿意去?当时我一心只想着学成回乡解决水稻白叶枯、稻瘟病病害和大豆菟丝子等具体防治问题,从没思考过要去外面走走看看的想法,于是我表明了自己的意见,感谢老师对我的格外关心,决定留在学校从事水稻白叶枯、噬菌体课题的实习研究。
面对很快就要结束的大学生活,我们一起留在学校实习的学生,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抓住最后3个月实习期,学习更多的知识。老师了解到我们的想法后,为了让我们多掌握一些实用知识和实用技能,平常跟我们一起加班加点,帮助我们查阅文献资料、做实验,特别是李玲君老师把她监测水稻病虫害的所有知识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我们。那段时间实验室几乎就成了我的家,利用仅有的3个月时间,我们不但很好地完成了“水稻白叶枯噬菌体调查”毕业实习论文,还能够准确的从水样、土壤、植株叶片等样本中检测到水稻病害发病程度,可提早进行预防。此外,我们还掌握了配置“鲁保一号”(防治大豆菟丝子)的方法以及蘑菇、灵芝等人工生产栽培技术。这些为我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及家庭种养殖技术奠定了基础。
6 社来社去(毕业返乡)
1979年7 月,我含泪告别了母校和尊敬的老师们回到了家乡,当时返乡后的同学各奔东西,京郊班里其他区县的同学直接被分配到县里乡里工作,唯独顺义区几名学员回到村里面,真正遵循招生时说的标准“社来社去”。当时回到村里我很自信,一心想把村里的农业搞好。说实话,当时与其他同学相比,心里压力很大,也很不服气。记得当时有人问我今后有何想法,我为了赌一时之气不加思索就回答说:“除了市里录取我去,乡里、县里我都不会去,就在村里好好干,做出一点成绩来。虽然是一时之气,但却给自己造成了不必要的负面影响,让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痴心妄想,骄傲自大的人。但这些我都不在乎,也没往心里去,我只想着一心一意与村书记进行大田种植结构的调整,根据我村地势低洼,十年九涝的特点,结合不同地块土壤施肥和氮、磷、钾的含量测定,选择适宜的品种搭配和种植创新。
回乡一年,我利用所学知识,采取科学种田技术,对大田种植结构、作物品种进行调整,效果显著。1980年我承担县、乡的玉米试验田、水稻试验田、小麦试验田的技术工作,均获得了历史性的高产,震惊了全村人民。记得当时县里农业局领导组织各乡镇农业技术员来我村召开了2次现场会,要求我在会上作高产经验报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百余人面前作报告,心里十分紧张,但还是赢得了在场人员热烈的掌声。1980年7月,我又被邀请到顺义县宾馆召开水稻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上我接到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录用的通知,应了我逞一时之勇的话,也开启了我一生与蜜蜂结缘的工作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