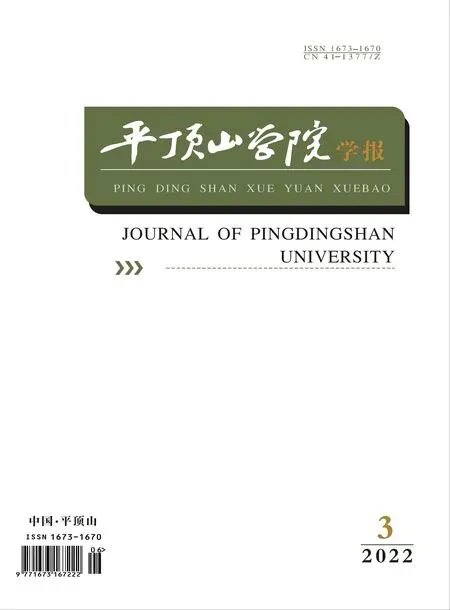敦煌写本《秦妇吟》综合研究
廖小红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秦妇吟》是唐末诗人韦庄的鸿篇巨制,借秦妇之口吟黄巢之乱的悲惨景象以及官兵的残暴扰民,是唐末离乱社会的“诗史”存照。全诗238句,1 666字,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叙事诗。然而,由于韦庄本人出任后蜀丞相之后的讳莫如深及人为干预,此诗遂致不传(1)据《北梦琐言》记载:“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巢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王国维由此提出韦庄自禁《秦妇吟》原因为“止谤说”,陈寅恪则认为自禁乃是“志希祸免”。。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王国维首先从伯希和处索抄到《秦妇吟》的文本,开《秦妇吟》研究之先河,韦庄巨制重见天日(2)王国维见到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抄于英国图书馆的敦煌写本,文中存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一句。王国维据《北梦琐言》记载判断此为韦庄失传近千年的《秦妇吟》,此后学术界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秦妇吟》的热潮。。其后相关写本被不断发现,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迄今为止,敦煌写本中的《秦妇吟》共发现14件,是同题诗作传抄最多者(3)14件写本分别为P.3381、P.3780、P.3910、P.3953、P.2700、S.692、S.5476、S.5477、S.5834、羽57R、Дx.4568、Дx.4758、Дx.6176、Дx.10740。其中 Дx.4758与Дx.10740可缀合,羽57R与S.692可缀合,P.2700与S.5834可缀合。。今综合已有研究成果,试从写本的形制、功用及传抄流布等方面,对这14件写本作一综合观照。
一、写本形制
现存14件《秦妇吟》写本的保存形制主要有三种,即卷轴装、册子本与残片。形制不同,其功能用途也相应有异。
(一)卷轴装
卷轴装是刻本出现之前纸质书籍的主要流存形式,源于简帛时代的简册翻卷形制。在14件《秦妇吟》写本中,卷轴装有6件,其中部分可缀合。
1.P.3381,首残尾全,由五纸粘合而成。楷书,起笔数行工整清秀,往后渐次率意,文字间有错讹,且多有遗漏。首行至第55行均有朱笔句读。首尾均题“秦妇吟一卷”,卷末有题记一行:“天复伍年乙丑岁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诗的开头写道“中和癸卯春三月”,可知韦庄创作该诗的时间是公元883年。据题记可知,此卷的抄写时间是在公元905年,此时离创作时间仅过去22年,韦庄也尚在人世。本件是目前所知所有《秦妇吟》写本中抄写时间最早、内容也最为完整的一件。
2.P.3780,首残尾全,由三纸粘合而成。前半部残缺严重,有污渍浸染,卷尾有明显断裂痕迹。先粘后写,正面有较均匀的界栏,楷书,书法工整。正文起自“中和癸卯春三月”,讫于“咏此长歌献相公”,卷末另有题记“显德二年丁巳岁二月十七日杨定迁手令□、显德二年丁巳岁二月十七日就家学士郎马富德书记、大周显德四年丁巳岁二月十九日学士童儿马富德书记”。题记覆盖着四行朱笔杂写,为“弟一 弟二 散 弟三君不见生生鸟,弟四送,送远还通达,逍遥近道是。是逢遐逢□,进退厘游连”。背面杂写“丙子年五月十五日学仕郎杨定迁自手书记之耳已”“大周显德四年丁巳岁九月□□日就家学士郎马富德书记”“崔氏夫人训女文 香车宝马”“大云之寺”“丙子年五月十五日小次张文成到此索僧政院内见海”等。由题记和杂写可以推断,该写本是在寺院中流传的写本,且流传时间较久。
3.P.3953,首尾皆残,无题记,由两纸粘合而成。楷书,抄写工整,字迹虽迟滞稚拙,但笔锋成熟,且所存正文无错抄、漏抄和涂改现象。起自“喧呼来酒市,一朝五鼓人惊起”,讫于“诸剥生灵过朝夕,妾闻此语”。该写本无题记与署名,无法判断其确切的抄写时间。
4.羽57R+S.692缀合本(4)张涌泉在《敦煌写本〈秦妇吟〉汇校》中首次将这两个写本缀合并入校。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1-341页。。羽57R,首全尾残,有少许污渍浸染,保存良好,有朱笔句读。楷书,笔迹迟滞,卷首有四枚钤印。S.692,首尾皆残。每行字数与羽57R略同,楷书,有两种字迹间杂。一种笔迹迟滞,体势拘谨,另一种笔迹流畅,字形较舒展,据笔法特征判断当为同一人所书。卷尾有题记“贞明伍年己卯岁四月十一日炖煌郡金光明寺学仕郎安友盛写记”,可知该卷的抄写时间为公元919年。写卷缀合后首全尾残,内容完整,尾题下有杂字“一米锹鑃”。据题记可知该写卷与金光明寺有关,是在寺学教材中学郎所抄写本。
5.P.2700+S.5834缀合本(5)柴剑虹1983年发表的《〈秦妇吟〉敦煌写卷的新发现》中发现S.5834与P.2700实为同一写卷。。P.2700首全尾残,首题“秦妇吟,右补□韦庄撰”。卷中有三种字迹,第23-30行较流畅圆润,第39-49行较迅疾锋利,其余字迹较迟滞。卷中字虽多脱讹,有淡墨涂改痕迹,但字迹工整。卷背有正书、倒书,多已模糊不清。背面杂写共计11行,有“张海昌年书壬□□为”“龙兴寺”“蓝图寺”“金光明寺”“大云寺”“张兴顺”“丁亥年正月一日洪润乡百姓”等字样。S.5834,仅余一残片,13行,字迹末行有题记“贞明陆年岁在庚辰拾贰月”,可知该卷抄写时间为公元920年。S.5834可以缀合于P.2700卷末左上侧,正好与前句“匣中秋水拔青蛇”相接。该写本背面内容繁杂,出现了多个寺院名,与寺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写本应该也是在寺学中被作为教材使用,后来被学郎带到民间,所以背面出现了“洪润乡百姓”字样。
6.Дx.4758+Дx.10740缀合本(6)潘重规据吴其昱抄本定Дx.10740-6为《秦妇吟》残片,徐俊进而指出该号第6、7、8、9、10为同一《秦妇吟》写本残裂而成,张新朋又提出Дx.10740-11和Дx.4758亦断裂自此写本,后张涌泉《敦煌写本〈秦妇吟〉汇校》将此缀合本全部入校,收入《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1-341页。Дx.4758见《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Дx.10740见《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4页。。由7个碎片缀合而成(7)分别为Дx.4758、Дx.10740-6、Дx.10740-7、Дx.10740-8、Дx.10740-9、Дx.10740-10、Дx.10740-11。,Дx.10740-11与Дx.10740-9形状不甚贴合,有交叠部分,当Дx.10740-11在下时正面、背面字迹均非常贴合(8)缀合发现,Дx.10740-11背与Дx.10740-9背习字中两个“际”残缺笔画刚好可以补足。。Дx.4758仅余一残片,起于“夜卧千重剑戟围”之“戟围”二字,讫于“昨日官军”。Дx.10740残余部分字迹清晰工整,书法美观。两者缀合部分之间约缺6行。缀合本背面共存24行习字。Дx.10740除《秦妇吟》外,还有两残片。第一张残片起自“肌扶轮可惜力”,讫于“如今落□”。据文中“欲得身才命”可考,此为王梵志诗残片[1]。S.3393号写本中所存王梵志诗与本文相似。第二张残片起自“拥千群之□”,讫于“流血诸余钗”。据文中“草头浑赤不见山”可知,此残卷为《秦将赋》[2]。
(二)册子本
《秦妇吟》册子本共有三件,编号分别是P.3910、S.5476和S.5477。
1.P.3910,共19纸,有界栏,栏宽不等。楷书,笔迹粗率稚嫩。该册封面污损严重,有正书与倒书,存“第五广要道章”“四五刑”“十一”“记孝行章弟”“圣至章弗”“气若”“二爰满”“经写”字样,为《咏孝经十八章》章题六行。正文依次抄写《茶酒论一卷》《新合千文皇帝感辞壹拾壹首》《新合孝经皇帝感辞一十一首》《秦妇吟》。《茶酒论一卷》,顶格写“茶酒论一卷”,后空格写“并序乡贡进士王敷撰”。正文共68行,尾题“茶酒论一卷”。全文错处多且痕迹明显,行文歪曲未对齐。《新合千文皇帝感辞壹拾壹首》,正文19行,首题单独列行,尾题“新合千文一卷”。《新合千文皇帝感辞壹拾壹首》为重新组合的千字文,是敦煌地区重要的蒙学读物。《新合孝经皇帝感辞一十一首》,正文60行,尾题“新合孝经一卷”。所抄《秦妇吟》不全,起自“中和癸卯春三月”,讫于“城外风烟如寒色色色色文”。书首有题记一行:“己卯年正月十八日阴奴儿买策(册)子。”“阴奴儿”在敦煌写本中出现的频率很高,S.5441《捉季布传文》有“戊寅年二月十七日阴奴儿写之手书自手书”。“己卯”是公元979年,是此卷抄写时间。册子末亦有题记“癸未二月六日净土寺弥赵员住左手书”,接着又重复抄写了一遍,但不完整,且落款为“赵托”。此时为公元983年,该册是阴奴儿买来作抄写之用,卷尾题记是四年后赵托拿到该写本所题。写本中有两行杂写“无耻辱之患,对食不贪,盖是修身之本,争财必有灭身之祸”,意为不贪不争,静心养性,这两行杂写也符合净土寺僧所求。写本前后字迹不一致,当非一人所书。
2.S.5476,首尾皆残,无题记,前后有脱页。现存9纸,共存103行。前半部分书法工整,后半部分书写粗率,但据笔法特点分析或当为一人所写。起自“门外起红尘,已见街忠(中)擂金鼓”,讫于“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魇”。
3.S.5477,首残尾全。共10页,除第8、9页外,各页均有界栏,栏宽不等。首题无,尾题“秦妇吟一卷”。楷书,字迹工整。开头与中间墨迹浓淡不一,但字迹笔锋相同,当为同一人所写。写本起自“斜开鸾镜懒梳头”,讫于“咏此长歌献相公”。徐俊认为S.5477与P.3910皆为阴奴儿所写,张涌泉认为P.3910中的缺句“斜开鸾镜懒梳头”刚好是S.5477的开头,所以S.5477是P.3910错抄后的重抄卷,两个写本刚好合成完整的一卷。田卫卫认为S.5477是脱落自P.3910的折页,且抄写于同一个母本[3]。但S.5477与P.3910不能合成完整的一卷,不是同一人所抄,也不是同一个母本。理由有二:其一,两者在用词与书写笔法方面有很大差别;其二,P.3910中抄漏的“斜开鸾镜懒梳头”,中间接两行杂写,本人抄写时并未发现漏抄,是粗心所致。故S.5477应该不是脱落自P.3910的折页。
(三)残片
1.Дx.4568[4],共两件残片,字迹工整。右侧残片存“□□独向绿杨阴下歇,凤侧鸾欹鬓□斜,红攒黛敛眉心折,借问女郎何处□含嚬欲□……袂谢”三行。左侧残片存杂写“今朝 今朝到此寺壁上亭台字 字曰受 顮”两行。徐俊认为此残片可与Дx.10740拼接,张涌泉和田卫卫则认为不可,今从张、田之说。从写本形态与字形字距来看,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Дx.4568每行字数约为14字,Дx.10740 每行字数约为22字。Дx.4568为行书,字迹修长拙稚;Дx.10740为楷书,字迹工整圆润,两卷不可拼接。
2.Дx.6176[5],现存三残片,残片中间部分有压痕,或原为册子本。字迹工整,笔势锋利。据判断该写卷前后都有脱页。此写本《俄藏敦煌文献》未定名,徐俊最早发现并校录[6]。依次抄有《鹰赋一卷》《鹘赋》《秦妇吟》。《鹰赋一卷》有尾题,下重复写“鹰赋一”三字,起自“鹯鹞小而咸轻”,讫于“比无用于不用,岂童年而者论”,中间由于残泐而诗句有缺,共存65行。《鹰赋》又见Дx.10257。《鹘赋》一卷,下仅存“伊鸷之雄毅”。《秦妇吟》首题“秦妇吟 补阙”,一行正文后接两行杂写,为“天福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乡百姓□愿成□”。据此判断该卷抄写时间为公元946年。后又题“秦妇吟 补阙”,正文内容起于“中和癸卯春三月”,讫于“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
二、功能用途
写本的形制不同,它的功能用途也应有差异。通过对写本内容的细读,本文将这14件写本分做以下几类进行考察:
(一)文士写本
这类写本主要有Дx.4568、Дx.6176、S.5476、S.5477,普遍抄写工整,笔迹也相对娴熟,大概是文士抄写用来备考或专供学习之用。Дx.4568末行中间部分缺失,依稀可见界栏,字迹拙劣但抄写工整。Дx.6176 中有“□乡百姓□愿成□”字样,可知该写本应是在民众之间传播的写本。S.5476前9页有乌丝界栏,栏宽较均匀。前后书写风格不一,或肆意或工整。据其笔法特点分析当为同一人所书,书写时随心而写,造成了书写风格的差异。S.5477除第8、9页外,各页均有乌丝界栏。楷书,前后书写差异较大,但据笔法可见为同一人所书。文士写本的抄写大都较随意,不受行款的约束,但字迹工整。能随心所欲地书写,可见其书法造诣,归为文士写本或为一说。
(二)学郎抄本
学郎抄本有P.3381、P.3780、羽57R+S.692缀合本、P.2700+S.5834缀合本、Дx.4758+Дx.10740 缀合本。每个抄本后都有“学仕”“学士郎”“学士童儿”的称谓,这些不同称谓指的都是求学的学子。古代学子历来都是“学而优则仕”,这些学子自称为“学仕郎”,饱含着对出仕从而建立功业的期待。“士”为“仕”简写或俗写。学郎写本既是学生完成的“家庭作业”,也作为教材在敦煌地区流传。
P.3381卷末有题记“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P.3780卷末题记“显德二年学士郎马富德书记”“显德四年学士童儿马富德书记”,田卫卫认为“显德二年”为误写[7]。但不应是误写,此学郎写本作为教材传播,流传的时间长。因此“显德二年”应是学士郎马富德抄写完诗歌后所写的题记,此时是公元955年,两年后他又一次拿到了自己的抄本,兴致使然又在上题了一则题记,这时是公元957年。背面杂写中有“丙子年”字样,为公元976年,可见此写本存在时间很长,有成为教材的可能性。“显德四年”的字迹较“显德二年”更工整成熟,自称从“学士郎”变成了“学士童儿”。第一则题记字迹潦草,和写本的抄写字体不一。“手令”一词指亲手下的告谕、指示令,一般是上级对下级。因此不妨大胆猜测一下,此学郎写本,杨定迁为师,写本为课后作业。第一行题记是老师批改作业后的标记,就像现在的“已阅”。题记后附学郎诗“手若(弱)笔恶,若有决错,名书(师)见者,决丈五索”。“手若(弱)笔恶”这类词经常出现在敦煌写本中,大抵意为“抄写不当、敬请见谅”,表示谦虚求教、请指正等意。P.3433与P.2604都出现了类似谦辞,可见这类谦辞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也符合学郎的身份。P.2700+S.5834缀合本背面同样也出现了“手若力恶多”字样,不过前后已残损,无法辨认。背面杂写中“龙兴寺”“蓝图寺”“金光明寺”“大云寺”等字样也表明该写本作为教材在各寺学的传播情况,故P.2700+S.5834缀合本为学郎写本无疑。
羽57R+S.692缀合本,卷尾接学郎残诗一行,诗云:“今日写书了,合有五升米。亭代不可得,坏(还)是自身灾。”大意为抄了诗歌来换粮食。卷背有“西州”“张德宗(?)市牛”“将有”等少量文字。“今日写书了”类似的学郎诗又见于BD01199号、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卜天寿《论语》抄本,但仅首句相似。徐俊认为,此诗未必为安友盛所写,有可能是流传于敦煌地区的带有集体性创作特征的诗歌,与P.3780“手若笔恶多”类似。柴剑虹根据其内容推测,此写本当为金光明寺学郎安友盛为折抵米债而代写《秦妇吟》这一长诗[8]。伏俊琏认为,此诗记述了学郎安友盛替别人抄书取得报酬的情况,而所抄的书就是本卷的《秦妇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郎们业余的“勤工俭学”生活[9]。此判断可信,学士郎为了补贴家用而代抄作业在当时或时有发生,这首诗应是抄完后为抒情而作。Дx.4758+Дx.10740缀合本背面为习字,每字书一行,所习文字依次为“达驯之性大师讲化”“升升蜂台澜挹之无际之旧”“雾集行檀驰”,田卫卫考订其出自《重修开元寺行廊功德碑并序》[10]。该习字抄写工整,应为学士郎练习书法所抄。故此两件写本都为学郎写本。
无论是学郎写本还是文士写本,都是当时敦煌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学校教材,《秦妇吟》的写本数量与流传广度都与学校教育密不可分。一方面,《秦妇吟》作为教材丰富了敦煌教育的内容;另一方面,敦煌的教育也提高了《秦妇吟》的知名度,扩大了其影响,对《秦妇吟》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讲唱写本
敦煌写本中有许多抄有散韵相间讲唱文学的写本,这类写本通俗易懂,在民间的传播范围极广。P.3910就是用作讲唱表演性质的写本,除《秦妇吟》外,其中所抄的《茶酒论》《新合千文皇帝感辞壹拾壹首》《新合孝经皇帝感辞一十一首》都是讲唱文学。关于《茶酒论》的文体历来颇有争议,大体可以分为小说、变文、俗赋、戏剧讲唱、论议散文。赵逵夫认为《茶酒论》应该是一份戏剧脚本,他认为:“完全用代言体形式写成的《茶酒论》,可以看作是唐代俳优戏演出脚本的实例。由此断定,我国在唐代以前已经有了可以付诸演出的戏曲脚本,《茶酒论》是一份珍贵史料,能够对今人认识唐五代的戏曲状况和剧本创作情况提供帮助。”[11]《茶酒论》是晚唐时人模仿俳优戏采用对话形式而作的脚本,全篇采用代言体这种极具戏剧特征的形式,这是其作为讲唱文学流传的有效例证,故文体为戏剧讲唱更佳。
同抄的《皇帝感》是敦煌地区重要的蒙学读物。“皇帝感”原为教坊曲,是民间俗唱。任半塘认为:“盛唐歌场之设可能已遍及州郡,‘皇帝感’辞既入歌场,体虽不演故事,若曾穿插说白,入讲唱,已极明显。”[12]743可见《皇帝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曲调,除赞颂皇德外,还对《千字文》的句子进行形象的演绎。它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吟咏,达到导俗训世的目的,是民间生动通俗的启蒙教材,故《新合千文皇帝感辞壹拾壹首》与《新合孝经皇帝感辞一十一首》在敦煌地区作为讲唱文学传播的可能性很大。现有敦煌写本大多按某个规律集成,如佛经写本、藏文写本、诗歌写本。P.3910中《秦妇吟》与《茶酒论》等讲唱文学抄写在同一个写本上,P.3780背面也有抄《崔氏夫人训女文》。再加上《秦妇吟》本身人物关系单纯,结构巧妙,描写生动细腻,有作为戏剧再现的可能性。《秦妇吟》与讲唱文学抄在同一写本上,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其作为讲唱文学传播的可能性。且古代文学传播比起书本教材更多的是口耳相传,文本在传播过程中成为变文或讲唱的可能性极大。
三、《秦妇吟》的流传
《秦妇吟》无传世本,其失传虽大都认为是韦庄自禁所致,但细推之下难以成立。P.3381的抄写时间距该诗的创作时间很近,可见其在很短时间内就迅速传播开来,说明该诗流传很广。在已经传播开来的情况下,单凭作者本人的自禁意愿是很难阻止其继续流传的。虽《秦妇吟》在中原地区没有受到极大欢迎,但不致消弭。那为何宋代以来未见《秦妇吟》传世本?《秦妇吟》以何种原因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与中原地区相反,《秦妇吟》在敦煌地区却是极受欢迎的。由现存写本可知,敦煌学校教育中以《秦妇吟》教授学童,学郎手抄口诵,扩大其流传。又由于该诗在诗歌上的巨大成就和描写唐末离乱社会的深刻感人,使之进入世俗讲唱文学的视野,将其与《茶酒论》等讲唱文学归为一途,成为俗讲的内容,更是扩大了它的流传。
《秦妇吟》作为唐代最长的叙事诗,采用直叙与倒叙结合的叙述方式,通过“秦妇”与“老翁”的视角,将起义军对民众的迫害、官军的无能与残暴、战后社会的萧条与人民的惨状描写得淋漓尽致。诗篇以“秦妇”自叙的口吻展开,内容分为四部分:她在黄巢攻破长安时的遭遇,陷在黄巢军中的痛苦生活,东奔时社会的动乱与惨烈,老翁自述悲惨的经历。诗歌塑造的人物形象典型生动,语言极富韵律美。这样优秀的长诗在传入敦煌地区后,深受普通民众与敦煌学子的喜爱,除诗歌本身的优秀外,也与传抄人群的经历密不可分。
中原地区长期受儒学思想影响,像《秦妇吟》这种描写血淋淋战争的非正统诗歌,不会得到广泛的传播。敦煌地区长期处于古代版图的边缘,时局动荡,经常发生战争。《秦妇吟》在敦煌流行时恰逢陷蕃战争后,社会生活受到战争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教育。这时教育从传统的州学、州医学、道学等转入寺学。为了避祸而进入寺院的“破落官”教师与学子在寺中学习,将《秦妇吟》选为教材,故各抄本频繁出现 “大云之寺”“生生鸟”“金光明寺”等佛教用语。可见,《秦妇吟》被选为教材与当时文人亲身经历敦煌陷蕃的动荡有关。这时的他们不再只关心儒学大义,而是对和自己切身感悟相关的战争题材作品更加关注。
此时的寺学作为教育机构,有众多学子与教师。这些学子与教师和世俗生活紧密相连。他们在学校中所传抄的文章,通过平时的生活传播到家庭和市井中,使《秦妇吟》深入大街小巷成为一种可能。从学校到家庭、从家庭到市井的传播方式,使《秦妇吟》的受众极广,传播范围也极大。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秦妇吟》写本的抄写者属于不同阶层,有“学士郎”也有“百姓”;写本所属学校与地理位置也不同,所抄写本的功用也不同。学子们往返于社交圈时,给《秦妇吟》创造出从学校到家庭、到社会的传播机会。学子们的传诵是《秦妇吟》主要的传播方式,他们的喜爱也使得《秦妇吟》广为流传成为可能。从社会环境来说,当时的敦煌处于归义军统治时期,社会风气较宽松,当权阶层对诗中所写中原王朝腐败无能、将领残暴无义的行为毫无避讳,甚至对描写自己“胜利”与朝廷无能的诗歌会无意识地推崇,任其流传。而中原地区当权阶层对于“抹黑”自己的诗歌则会大力禁止,造成公卿谈《秦妇吟》而垂讶的局面,致使作者不得不自禁其传播。基于诗歌内容、传抄人群经历、敦煌社会环境、传播方式等各方面原因,使《秦妇吟》在中原地区被禁,而在遥远的敦煌地区得以广泛流传。
四、结语
通过现存《秦妇吟》写本形制进一步探讨其抄写者、抄写时间及功用,对了解写本流传及内部联系具有重要意义。将写本通过功用分为文士写本、学郎写本与讲唱写本,有助于还原《秦妇吟》在敦煌地区的流传情况。诗歌所描写的离乱社会与当时动荡的敦煌社会环境极度相似,受到了敦煌文人的传抄与追捧。根据写本的留存情况来看,《秦妇吟》在敦煌地区流传甚广,这是诗歌内容、传抄人群、社会环境以及传播方式等多重作用的共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