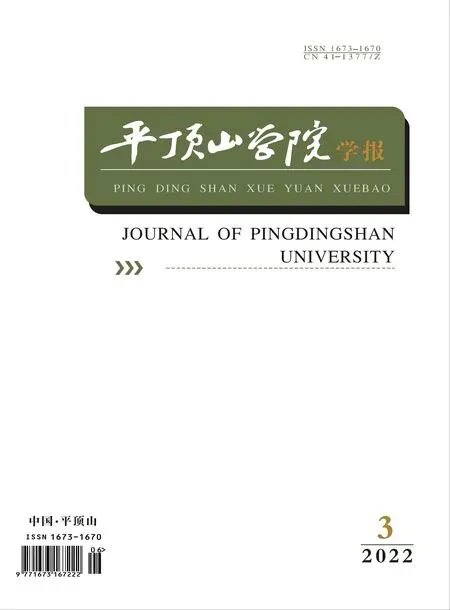机遇与优化:新媒体时代红旗渠精神的传播
苗智慧,裴利萍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红旗渠精神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河南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在修建红旗渠过程中形成的,是林县人民改造自然、战天斗地、改变命运、造福后代的真实写照,也是在此期间所产生精神的高度凝练。其内容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这些革命创业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1]随着时代的发展,红旗渠精神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人们对于红旗渠精神的理解也更为深刻。在新媒体时代,以新媒体为平台传播红旗渠精神是更深入有效发挥红旗渠精神的必然选择。以各种形式的新媒体平台如朋友圈、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为载体,丰富了红旗渠精神的传播形式与呈现方式,其传播力度与广度也空前增大,红旗渠精神的影响得以迅速增强。“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的变革,给红旗渠精神的弘扬和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同时红旗渠精神传播面临着紧迫的挑战。”[2]当前,对新媒体环境下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路径进行优化,一方面可以使红旗渠精神的传播更加契合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将红旗渠精神深度融入人们当下生活中,使红旗渠精神更好地发挥时代作用。
一、新媒体时代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迎来新机遇
新媒体的普及与应用,使红旗渠精神的传播具有高效率、高渗透、覆盖广的特征。与很多其他红色精神不同,关于红旗渠精神所遗留下的实物多,参与红旗渠建设的人员大多还健在,丰富的原始影像资料被保留下来。这些基础的条件使得红旗渠精神在当下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具有先天优势。新媒体条件下信息的传播主要借助手机、电脑等,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使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迎来新机遇。
(一)新媒体为红旗渠精神的高效传播提供了手段支持
与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在传播信息上进一步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通过互联网将信息快速精准地传递到受众面前。“新媒体传播模式表现为节点化的个人、媒介组织和机构在互联网中以互动方式形成交互链接的网状传播结构,实现包含单向、双向和多向的信息传播过程。”[3]传统媒体进行信息传播时通常需要一个专门的信息收集者,将信息收集后作为核心的信息传播中枢一层层中转至受众。而在新媒体条件下,一方面信息直接由受众所有的移动终端呈现,向受众传递的过程中中转次数大幅减少,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垄断格局已被打破,每个人的时间被无数App分割成无限碎片”[4],传递的模式由传统媒体环境下的单一核心传递转变为新媒体条件下的多核心传递,受众本身也可以成为信息的生成者与传递者。
新媒体作为红旗渠精神的传播媒介,其优点得以充分发挥,为红旗渠精神的高效传播提供了手段支持。对于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而言,承载红旗渠精神的实物丰富。修建红旗渠过程中遗留下的实物众多,修建过程中的工具、勘测仪器与资料、会议文件等被大量留存下来,特别是总长度1 500公里的红旗渠实体依然完整地盘旋在太行山腰。更为可贵的是,当年本来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到林县采访拍摄英雄渠的摄制组,对红旗渠的建设跟踪拍摄了十年之久[5],大量修建红旗渠时的原始影像资料被保存下来,为红旗渠精神的传播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载体。在新媒体环境下,红旗渠精神的传播不再仅仅是文字和图片的表现,也不是偶尔在电视中可见的当年林县人民修渠的画面,体会“誓把林县河山重安排”的精神也不需要到红旗渠边上,当年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画面、修建红旗渠所用的实物等通过手机等客户端瞬间可以呈现在受众眼前。大量实物和影像资料的留存,契合了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使新媒体高效传播信息的优势在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过程中得以发挥出来。
(二)新媒体为红旗渠精神的亲民性提供了展现的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传递信息的中心数量急剧增加,每个人手中的手机既是信息的接收终端,也是信息向外发散的中心。智能手机的应用使人们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成为信息制作的参与者和信息的传播者。“新媒体具有社群聚合功能,使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被压缩,形成多圈层协同传播的信息共享机制。”[6]新媒体环境下,人们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角色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信息传播的参与者。对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而言,新媒体为红旗渠精神的亲民性提供了展现的平台。
一方面,在红旗渠精神传播方式的改变上体现了红旗渠精神的亲民性。新媒体环境下,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路径被大大拓宽,人们不需要到红旗渠畔就能直观地体会到红旗渠精神。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将有关红旗渠精神的表现内容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直接呈现在受众眼前,大大缩短了受众与红旗渠精神的距离。另一方面,新媒体为红旗渠精神亲民性的展现提供了优质的平台。红旗渠精神本身就是在当年林县人民群众修建红旗渠过程中形成的,产生于林县人民一锤锤的敲打、一筐筐的肩挑、一次次的风餐露宿于悬崖之上。新媒体的出现为红旗渠精神亲民性的展现提供了全新的媒介。作为媒介,新媒体有展现红旗渠精神亲民性的优势。例如,在抖音平台中,以“红旗渠”为关键词,能够搜索到149个用户,这些账号中粉丝超过万人的有四个,其中个人账号“红旗渠李俊生”所发布的作品中单个作品点击量最多达到3.9万次,总获赞量达到14.8万次。此账号发布的作品主要为红旗渠建设者的日常生活与日常对话,使受众在移动客户端能够直面众多的红旗渠建设者,通过生活化的作品进行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而公司账号“红旗渠旅游”粉丝量达到5.4万,总获赞量达到53.8万次。
(三)新媒体为红旗渠精神传播的多元化提供了路径选择
红旗渠精神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传播的多元化有利于全面立体地展示与弘扬红旗渠精神,使其影响更加深入人心。以新媒体作为红旗渠精神的传播媒介,提升了红旗渠精神的多元化传播程度。这种多元化不仅体现在红旗渠精神传播的形式上,还体现在新媒体环境下红旗渠精神传播者的多元化和受众的多元化。
首先,新媒体环境下,各种网络平台具有不同的特色,其传播与表达信息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在红旗渠精神传播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网络平台的特点把红旗渠精神融入不同形式的表达中。例如,既可以通过抖音以短视频的方式展现,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图文并茂或以视频与文字的结合展现红旗渠精神,还可以通过朗诵类的App将关于红旗渠的诗作展现在网络中。其次,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者不再仅仅是官方平台和专业的媒体从业者,普通人也可以将与红旗渠精神有关的内容编辑后在网络上进行发布,成为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者。因此,进行红旗渠精神传播的门槛降低,既不需要专门的技术训练,也不需要对传播的主体进行严格的要求。最后,红旗渠精神传播的受众也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新媒体环境下,手机等电子产品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处于不同环境的人们之间普及。在大数据的分析下,信息的传递可以以量身定制的方式深入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环境的人们中。这使红旗渠精神传播末端的受众覆盖面更广,受众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二、新媒体时代红旗渠精神传播的困境
近年来,新媒体发展迅猛,使红旗渠精神的传播搭上报快车。但新媒体作为新生的事物,红旗渠精神在以其为媒介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借助新媒体进行红旗渠精神传播的过程中,一方面,新旧媒体交替的情况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传播理念等发生碰撞,造成红旗渠精神传播的困境。另一方面,红旗渠精神传播与新媒体的契合存在一个磨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产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对现阶段红旗渠精神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红旗渠精神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红旗渠精神传播过程中去中心化过度
在新媒体环境下,红旗渠精神的传播呈现多点扩散的特征。每个人手中的智能设备都能够成为传播红旗渠精神的工具,每个人不仅仅是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者,同时,也可以根据个人想法和偏好对关于传播红旗渠精神的视频进行编辑加工,成为红旗渠精神传播内容的制作者,这就使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无数个小的信息传播中心。而传统媒体通常是由官方管理,作为大的信息传播中心成为红旗渠精神传播的主要阵地。新媒体环境下红旗渠精神传播方式的灵活性大大提升,但话语权很大程度上被动下放,由官方媒体下放至自媒体甚至个人。对于自媒体和个人而言,“私人的需求也会投射在他们所参与的公共活动中,他们对信息的选择、接收与传递,很多时候是基于私人目的”[7]。由于这些自媒体和个人缺乏对红旗渠精神的正确把握,以及重商业盈利目的等原因,话语权被下放的过程中出现话语权使用的自发性、盲目性。“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泛娱乐化、碎片化的自娱自乐自传播的方式吸引了众多受教育程度与利益诉求不同的受众,从而带来了正能量信息与反向价值观的无序竞争。”[8]
红旗渠精神在多点扩散的传播状态下,传播媒介总数迅速增加,各种传播渠道并行。对于官方媒体而言,与自媒体、个人社交账号并行传播的过程中地位下降,以官方媒体为中心的红旗渠精神传播格局不再牢固,使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过程中去中心化过度。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传播红旗渠精神的内容上也存在去中心化过度的状况。新媒体的兴起,使红旗渠精神传播的话语表达更加多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红旗渠精神的广泛传播与其积极作用的发挥。但在缺乏管理的状态下,红旗渠精神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容易出现话语表达混乱的情况,使得红旗渠精神传播过程中内容的表现存在去中心化过度的状况,缺乏核心引领。
(二)红旗渠精神传播过程中线上与线下的融合度有待提升
新媒体作为传播媒介有其自身的特点。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更加具有视听性,信息的呈现更加具有多样性,信息的表达更加具有灵活性。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媒介在传播一种精神的过程中很难与承载着这种精神的实物等进行有机结合,相互融合的难度大。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将承载红旗渠精神的实物等融合进线上传播不再是难题。但当下红旗渠精神在传播过程中受传统媒体模式的影响仍然较重,导致新媒体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新媒体自身优势能够顺利发挥,又是实现红旗渠精神传播过程中线上与线下传播深度融合的前提。
对于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而言,一方面,新媒体环境下红旗渠精神传播过程中线上与线下融合的载体选择混乱。当下,新媒体所包括的种类繁多,既有以视频为主要呈现方式的,也有以文字、图片和音频为主要内容的,还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在红旗渠精神传播的过程中,缺乏根据表达主体与内容对传播的载体进行选择,导致线上与线下机械式融合。另一方面,线上与线下的融合重形式而轻内容。能够表达和传播红旗渠精神的实物和故事非常丰富,新媒体的出现更是为这些实物和故事更好地表达和传播红旗渠精神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由于缺乏对与红旗渠精神有关的资料和故事等的深度研究挖掘和细致整理,在新媒体平台上对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过程中,反反复复对几个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再现的情况突出。在这种情形下,红旗渠精神传播过程的线上与线下的融合就往往表现为线下故事搬上新媒体平台的再现和对线下活动的宣传。
(三)红旗渠精神在传播的过程中缺乏与其他红色精神线上互动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装上了“风火轮”,但当前红旗渠精神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大都为单线式的传播,也就是传播的过程中仅是对红旗渠精神这一种红色精神做文章,而未将各种红色精神融入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过程中。将其他红色精神融入红旗渠精神传播的过程中,是新媒体环境下红旗渠精神传播与发展的需要。
红旗渠精神的传播是红色精神传播的重要内容,新媒体的普及与应用大大地推动了红旗渠精神的传播。但从红旗渠精神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过程来看,缺乏与其他红色精神的线上互动。在传播过程中与其他红色精神进行互动,能够使不同的红色精神进行相互交融,使不同时期所产生的红色精神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合力,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对受众产生更大影响。在传播过程中主动将红旗渠精神与其他红色精神进行互动融合式传播,顺应了新媒体通常采用的用户推荐算法。在与不同的红色精神互动融合式传播的情况下,搜索其他红色精神的同时也会出现与红旗渠精神相关的内容,这为向更大范围传播红旗渠精神提供了契机。在进行红旗渠精神与其他红色精神的互动上,新媒体有独特的优势。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多点齐发并呈裂变状态,且利用新媒体传播红色精神时内容编辑门槛低,网络素材充足,为红旗渠精神与其他红色精神的线上互动提供了条件。
三、新媒体时代红旗渠精神传播的路径优化
新媒体环境下,对于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而言,既有巨大的机遇,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深刻认识新媒体,剖析新媒体传播信息的机制与特征,同时抓住红旗渠精神的实质、充分发掘红旗渠精神的承载实物,将红旗渠精神的传播与新媒体环境充分融合,实现新媒体助推红旗渠精神的广泛传播与能量的发挥。要实现新媒体更好地服务于红旗渠精神的传播,既要规避新媒体环境为红旗渠精神传播带来的风险,也要破解现阶段红旗渠精神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线上与线下融合度低的问题,还要借助新媒体加大红旗渠精神与其他红色精神的互动。
(一)推动形成“突出‘大中心’,引领‘小中心’”的红旗渠精神传播格局
对于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而言,去中心化利弊同存。一方面,去中心化给红旗渠精神的传播带来灵活性,丰富了红旗渠精神传播的方式;另一方面,过度的去中心化会使红旗渠精神的传播出现混乱。所以,要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红旗渠精神传播的去中心化趋势,促使形成“突出‘大中心’,引领‘小中心’”的红旗渠精神传播格局。
以官方主流媒体为“大中心”。官方主流媒体在所开设的新媒体账号上发布红旗渠精神宣传的相关内容经过严格的审核,并根据新媒体类型的不同,将这些内容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官方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应该是关于红旗渠精神基本内涵、重大事件的重现、红旗渠精神对人们当下生活的影响等大方面的内容。“大中心”在作用上重在为红旗渠精神的传播引领正确的方向,牢牢掌握红旗渠精神传播过程中的话语权。与“大中心”不同,各种自媒体、粉丝量大的抖音、快手、微博等账号在与受众的不断交流中形成“小中心”,这种“小中心”有的是地方性的,有的甚至可以成为全国范围内有一定影响的账号。在不同“小中心”的引领下,通过辐射传播,形成一个个具有不同特色的红旗渠精神传播“圈子”,这些不同的“圈子”所覆盖的受众可能存在交集,也可能是完全重叠的。形成交集和重叠后,更多关于红旗渠精神的内容会呈现在受众的面前,更加有利于红旗渠精神的深度传播。不同的“圈子”对红旗渠精神的表现方式与表现内容各有自身特色,可以避免受众在接受红旗渠精神的过程中出现疲劳和厌倦。
在红旗渠精神传播的过程中,无论是对于“大中心”还是“小中心”,都要对其加大控制与监督。既要坚固“大中心”在红旗渠精神传播过程中的引领与权威作用,又要激活“小中心”在红旗渠精神传播过程中的灵活作用,不断为红旗渠精神的传播注入活力。首先要成立红旗渠精神传播的专门部门,对红旗渠精神传播的过程进行统一指导;其次是投入力量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红旗渠精神传播的特点,挖掘和整理适用于新媒体的素材,为新媒体环境下正确引导红旗渠精神的传播提供基础;最后是扮演“大中心”角色的官方主流媒体和林州当地政府增加举办有关使用新媒体平台传播红旗渠精神的活动,既可以激发新媒体环境下红旗渠精神传播的活力,也是对新媒体平台传播红旗渠精神在方向上的引领。
(二)提高红旗渠精神承载实体的数字化、优化传播媒介组合
近年来,红旗渠精神发源地的相关部门在红旗渠精神的传播上花了很大工夫,相继举办了红旗渠旅游节、文化节等活动。在新媒体方面,通过直播活动、短视频大赛等形式促进了红旗渠精神的进一步传播。提高红旗渠精神承载实体的数字化是进一步推动新媒体环境下红旗渠精神传播的基础性工作。修建红旗渠的十年间,丰富的会议文件、修渠时的技术记录、信函、修渠工具等被保存下来,由于数量巨大,大多都被保存于林州市的档案局和红旗渠管理处。这些实物资料大都没有经过精细的整理,更是未曾与公众见过面。建立专门的数据库,将这些丰富的实物资料进行数字化,通过拍照、扫描等手段将其上传至数据库,既为新媒体对红旗渠精神的传播提供丰富的电子资料,也可为有关红旗渠精神的史料和文物的研究提供新的路径。
在新媒体环境中,红旗渠精神传播的最终效果是不同类型媒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作为红旗渠精神传播的工具,它们最终的作用都在于将红旗渠精神传播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中,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精神养分,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红旗渠精神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与各种媒体共同配合的程度紧密相关。首先,不同的媒介要坚持一个方向,坚持党的引领,坚持主流方向的引导,保证不同媒介对于红旗渠精神传播方向的一致性,为不同传播媒介组合在一起提供前提。其次,要认识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9],注重在传播过程中将不同的传播媒介优化组合。将传统媒介与新媒体进行适当的组合式运用,使红旗渠精神的传播更加立体化。最后,着力形成“拧成一股绳”的媒介组合。媒介之间的组合,不仅仅是不同媒介运用多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不同媒介怎样进行有机融合的问题。着力突出不同媒介的优势,重视不同媒介组合后对红旗渠精神传播的有益影响,通过不同媒介的优化组合为红旗渠精神传播的优化提供路径。
(三)搭建新媒体红色精神交流平台,推动红旗渠精神与其他红色精神互动式传播
借助新媒体促进红旗渠精神与其他红色精神的互动,既是红旗渠精神传播与时代相适应的表现,也为各种红色精神在交流中传播提供平台。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开放性等特征,因此可以成为红色精神交流的公共平台。各种红色精神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精神上的精华,它们不是独立存在的,各种红色精神都有共同的精神核心和千丝万缕的联系。搭建新媒体红色精神交流平台,为红旗渠精神与其他红色精神的交流提供官方渠道,能够促进各种红色精神在交流中激发出更大的作用。
通过搭建新媒体红色精神交流平台,推动红旗渠精神与其他红色精神的互动式传播。一方面,要由官方牵头建立红色精神交流新媒体中心。林州具有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纪念馆和红旗渠旅游景区,这些单位均注册有新媒体账号。将这些单位的新媒体运营部门联合起来,组建成红旗渠红色精神交流新媒体中心,成为官方的新媒体红色精神交流平台。这些单位都位于红旗渠畔,掌握着关于红旗渠精神最原始、最丰富的实物资料,也有对红旗渠精神研究的深厚积累,是红旗渠精神传播的高地与中心。在这些单位的基础上建立红旗渠红色精神交流新媒体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红旗渠红色精神交流新媒体中心要着力与全国红色精神传播的官方新媒体平台建立常态化联系与沟通机制,形成制度化新媒体传播红旗渠精神的交流互鉴。另一方面,要举办丰富的线上红色精神互动活动。通过设计正能量、有趣、参与性强、传播广的新媒体平台活动,将不同的红色精神融入一个活动中,在红色精神的交流中推动红旗渠精神的全国性传播。例如,红旗渠在太行山腰上从山西平顺县一直蜿蜒盘旋至林州境内,可以将修渠的路线和长征的路线进行类比,将红旗渠的修渠过程和走长征的过程联系在一起,设计参与感强的小游戏,将其嵌入新媒体平台中,吸引大众参与,这样既可以使红旗渠精神和长征精神得到融合式的传播,又具有趣味性,提高受众的参与感。
四、结语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变革式改变。新媒体环境为红旗渠精神的传播提供了崭新的样式,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广泛深入传播红旗渠精神提供了机遇。同时,在新媒体时代传播红旗渠精神,既要筑牢红旗渠精神传播的话语权,也要掌握好红旗渠精神传播的新思路、新技术、新方法,还要注重红旗渠精神与其他红色精神的线上互动,使红旗渠精神的传播更加契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