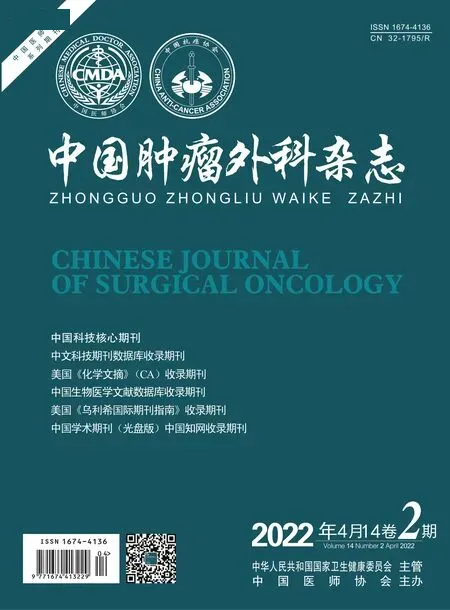早发性结直肠癌的研究进展
胡淼, 刘玲, 顾佳麟, 李灵常, 霍介格
Research progress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为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于高位,近年来,随着治疗手段的进步和一级预防的开展,CRC的发病率有所下降。尽管如此,早发性结直肠癌(early-onset colorectal cancer,EO-CRC)却表现出完全相反的趋势,相关研究发现50岁以前患者发生CRC的概率在2000—2017年之间增长了1.4倍[1]。相较于普通CRC,EO-CRC有其特征性的病理特点,且具体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临床针对EO-CRC的诊治方案有所欠缺。指南对EO-CRC的年龄范围没有明确的定义,目前的研究普遍将50岁以前发病的CRC定义为EO-CRC。近年来,研究者对EO-CRC的临床和分子生物学特征进行研究后发现其可能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非CRC的一个亚组[2-3]。本文主要研究患病年龄<50岁的CRC患者,归纳、总结其流行病学特点、危险因素、临床特征、分子遗传学表征、治疗预防研究进展,以期为此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1 流行病学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CRC发生率逐渐呈年轻化趋势[4]。发达国家的CRC发病率呈平稳和下降趋势,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等为代表的国家,EO-CRC发病率却有明显的上升趋势[5]。有学者按照目前EO-CRC的发生率增速预测,美国到2030年,年龄<50岁的患者中,被诊断为CRC的患者占比高达32%[6]。我国的EO-CRC的统计数据也不容乐观,姜艳芳等[7]通过搜集2004—2009年我国青年大肠癌(发病年龄20~39岁)的数据发现,2004年我国城市青年大肠癌发病率为2.38/10万,2009年为2.80/10万,平均增长速度为3%;农村青年大肠癌发病率逐年降低,从2004年的2.43/10万降至2009年的1.94/10万,城市、农村大肠癌发病率之比为(0.98~1.46)∶1,由此可见2004—2009年我国EO-CRC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存在城乡差异,城市青年大肠癌发病率高于农村。亦有国外研究表明[8],EO-CRC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地域相关性,美国各个州的EO-CRC发生率差别很大,以密西西比州和肯塔基州发生率最高,与其他地区相比死亡率也较高。以上统计数据表明,全球范围内CRC的发病正日趋年轻化,且地域的不同影响了EO-CR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强调了EO-CRC预防和治疗的迫切性,也说明了EO-CRC的可干预性。由于EO-CRC的发病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遗传、饮食和行为因素等,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以挖掘不同地区之间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差异。
2 危险因素
肥胖、久坐、饮食模式、红肉和加工肉类的高摄入是CRC的关键风险因素,这些因素在EO-CRC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此外,一项针对EO-CRC与晚发性CRC或无癌症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确定了一些与患者生活方式无关的危险因素,包括性别、种族、炎症性肠病和CRC家族史,结果显示EO-CRC患者的性别更倾向于男性,种族大多为黑人和亚洲人,有炎症性肠病和CRC家族史者更易患病[9]。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年龄增加及性别为男性与患有EO-CRC风险增加相关,而阿司匹林的使用与患病风险降低相关,年龄每增加1岁,EO-CRC的患病概率增加5%(OR: 1.05,95%CI:1.03~1.07);男性患病率是女性的2.2倍(OR: 2.21,95%CI:1.68~2.91);与没有使用阿司匹林患者相比,服用阿司匹林后EO-CRC的发病率降低了34%(OR:0.66,95%CI:0.52~0.84)[10]。一项Meta分析表明,EO-CRC的重要危险因素包括一级亲属有肠癌病史(RR: 4.21,95%CI:2.61~6.79)、高脂血症(RR:1.62,95%CI:1.22~2.13)、肥胖症(RR:1.54,95%CI:1.01~2.35))和乙醇摄入(RR:1.71,95%CI:1.62~1.80)[11]。Liu等[12]采用前瞻性研究分析肥胖和成年后体重增加与EO-CRC风险的关系,发现肥胖与女性EO-CRC的风险增加有关,而在男性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联系。另外一项大型回顾性研究发现,年龄在20~39岁的CRC患者的肥胖率是健康人的2倍(48%.0vs.24.9%,P<0.001),且这部分个体主要是女性(93%),表明在年龄为20~39岁的女性患者中,肥胖与CRC相关[13]。以上两项研究强调了肥胖症对女性EO-CRC的影响。EO-CRC患者中遗传性癌症综合征占比偏高,最常见的是遗传性非多发性CRC,又称为Lynch综合征,此类患者终生患CRC的风险为70%,并且有40%的患者CRC发病年龄<40岁[14]。EO-CRC的危险因素和病因尚未明确,大型的流行病学调研和临床前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这在EO-CRC的筛查和诊疗中有重要意义。以上研究EO-CRC危险因素的文章,有一些相似的结论,比如性别为男性、有CRC家族史的患者患病概率更大。
3 临床特征
EO-CRC与CRC在临床特征方面存在差异,因50岁以下的患者不常规筛查大肠癌,故大多数EO-CRC患者因出血、腹痛、排便习惯改变等不适症状就诊后才得以确诊。有报道显示,EO-CRC患者与老年肠癌患者相比,更容易出现便血和腹痛的症状[15],EO-CRC起病较为隐匿,待症状出现时大多已经中晚期,发生转移[16]。Chen等[17]指出,左侧CRC约占年轻患者的40.7%,约占50岁以上患者的33.6%,即年轻患者与老年患者相比,肿瘤在左侧结肠的可能性更大,这表明年龄与CRC的原发部位之间可能有关联。一项临床研究发现,约61.8%的EO-CRC患者被诊断时已为Ⅲ期或Ⅳ期,其中老年CRC占46%%~50%。此外,与迟发性CRC相比,EO-CRC患者的肿瘤组织分化差,多呈低分化,病理类型以黏液细胞癌最为常见[18]。EO-CRC患者的瘤体与CRC相比,体积更大,最大径>5 cm多见,淋巴结阳性率、周围神经浸润率和边缘阳性率均更高(P<0.01)[19]。EO-CRC与CRC的预后比较尚没有统一定论。熊启敏[20]收集了97 369例原发性CRC病例,发现肿瘤相关生存期年轻组(39.2个月)长于中老年组(33.8个月),同一分期年轻组生存期亦高于中老年组,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指出该结果可能与年轻患者更多接受根治性手术、合并症较少、接受综合治疗人数多有关;而Khan等[21]比较30岁之前及50岁之后的CRC患者,发现年龄<30岁的CRC患者预后更差。以上两个研究的结论恰恰是相反的,研究存在分歧的原因可能与分组年龄的差异、控制的不可变量不同有关。目前,尚无针对EO-CRC发病的预测模型,对患有潜在风险的年轻个体进行临床筛查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癌症协会已将应接受肠镜筛查的年龄从50岁调整至45岁[22],这一举措使33.3%的EO-CRC患者从中获益[23]。
4 分子遗传学表征
有研究表明,微卫星不稳定性与EO-CRC右侧比例较低、晚期组织学发生率较高、诊断时分期较晚有关[24]。而Cavestro等[25]认为无家族史的EO-CRC更倾向于是微卫星稳定的(80%),且不具有CpG岛甲基化子表型,与老年CRC相比,这些癌症的基因组通常更常见整倍体和低甲基化。一些学者对EO-CRC患者的基因进行了分析,Chouhan等[26]发现BRAF基因突变和高甲基化在EO-CRC患者中非常少见,KARS基因在EO-CRC中发生突变的概率较低。Lieu等[27]则通过实验研究发现,EO-CRC患者中TP53(FDR<0.01)和CTNNB1(FDR=0.01)的基因突变更为常见,而APC(FDR<0.01)、KRAS(FDR<0.01)、BRAF(FDR<0.01)及FAM123B(FDR<0.01)的基因突变在老年CRC患者中更常见。还有研究发现,某些基因突变发生率与年龄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相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BRAF基因V600突变的发生率从<30岁患者的≤4%上升到>70岁患者的14%,MAPK通路突变在18~29岁的患者中最低(48%),在>70岁的患者中最高(65%~70%)[28],表明CRC患者V600、MAPK通路发生基因突变的概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有研究发现,癌症的共识分子亚型(CMS)的分布似乎也受到发病年龄的影响,EO-CRC患者相较于年龄≥70岁的CRC患者CMS1患病率较低(22%vs.23%),CMS2患病率相似(43%vs.43%),CMS4(22%vs.20%)患病率较高[29]。目前EO-CRC具体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需要更多的基础实验研究及进一步的探索。
5 治疗
尽管EO-CRC可能是不同于CRC的独立个体,但目前EO-CRC的治疗和CRC相似,没有针对EO-CRC的特殊治疗方案。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指出,对于结肠癌家族史较长或年龄<50岁的患者,应考虑进行更广泛的结肠切除术,对于<50岁散发性CRC的患者,节段性结肠切除术或直肠切除术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且建议仔细、定期监测剩余的大肠组织[30]。Kneuertz等[18]研究EO-CRC患者的治疗方式和预后,发现与老年CRC患者相比,更多的年轻患者接受化疗,但在接受更多治疗的情况下,年轻患者与老年患者相比,疗效优势不明显,相当多的年轻患者接受了具有潜在毒性的治疗。Kolarich等[31]评估了2004—2014年间在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中诊断的43 000多例EO-CRC的患者,显示患有Ⅰ期疾病的早期发病患者更有可能接受NCCN指南推荐以外的放射治疗,而在年轻患者中,Ⅱ期和Ⅲ期疾病的新辅助放化疗与总体生存获益无关。EO-CRC中MSI-H状态更为常见,预后相对较好。考虑到化疗有可能会造成过度医疗,NCCN指南建议Ⅱ期患者都进行MSI/ MMR测试[32]。到目前为止,靶向治疗EO-CRC的反应性还没有得到明确的验证,基于EO-CRC的分子生物学特性,靶向治疗很可能成为EO-CRC治疗上的突破[25]。关于EO-CRC的免疫治疗,少有报道,免疫治疗能否使得EO-CRC患者受益还需进一步实验与临床研究探讨。综上,EO-CRC的治疗相对局限,包括了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等,其中化疗、放疗及靶向治疗在改善预后方面尚无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6 预防策略
EO-CRC尚无最佳治疗方案,所以针对危险因素早期预防尤为重要。针对CRC的相关危险因素,主要包括CRC家族史、炎症性肠病、红肉和加工肉类摄入、糖尿病、肥胖、吸烟、大量饮酒,对于EO-CRC的预防这些危险因素也同样重要,可以早期干预的措施包括增加运动量、戒烟戒酒、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谷物等[33],服用阿司匹林也属于保护因素。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癌症协会已将应接受肠镜筛查的年龄从50岁调整至45岁,这也提示应该更积极地完善肠镜的检查。基于目前筛查CRC技术的限制,万深妹[34]利用甲基化的荧光MethyLight技术,初步确定可用于早期CRC识别的甲基化标志物:ZNF132、FBN1、NEUROD1、FAM72C、KCKQ5、C9orf50及ST8SIA4,这使得EO-CRC的预防有了明确的观测指标。2020年《中国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35]推荐评估为高风险的人群,在40~75岁就要接受CRC的筛查,最常见的筛查手段就是结肠镜。虽然结肠镜是筛查CRC的金标准,但因其属于侵入性检查,且需要做充分的肠道准备,故我国结肠镜检查的参与率不高,相比较而言,免疫法粪便隐血试验(FIT)与新型风险评估筛查方案参与率更高[36],可见开展健康宣教以提高我国结肠镜检查参与率也十分必要。
7 小结
EO-CRC的诊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①国内关于EO-CRC的关注及研究极少,但患者数不在少数,相关的诊疗指南需及时更新。②EO-CRC没有明确的年龄定义,其分子细胞学研究太过表浅,需要深入探讨以解释其发病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受益临床。③EO-CRC的临床研究数量偏少,大多数研究皆为回顾性分析。④现有的EO-CRC研究的结论尚存在矛盾之处,如EO-CRC与CRC的预后比较,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以得到准确的结论。
临床工作中,我们要重视此类疾病,注重EO-CRC的健康宣教,加强患者对EO-CRC可干预危险因素的认识;完善诊断流程,做到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严格按照《中国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30]进行筛查及诊治;科研方面,需重点关注EO-CRC的分子细胞学研究,探索其与CRC分子细胞学的异同,加大研究力度,关注有争议的问题,得出准确的结论;此外,需广泛开展更多的关于EO-CRC的大样本、随机、双盲临床试验,以便发现更好的治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