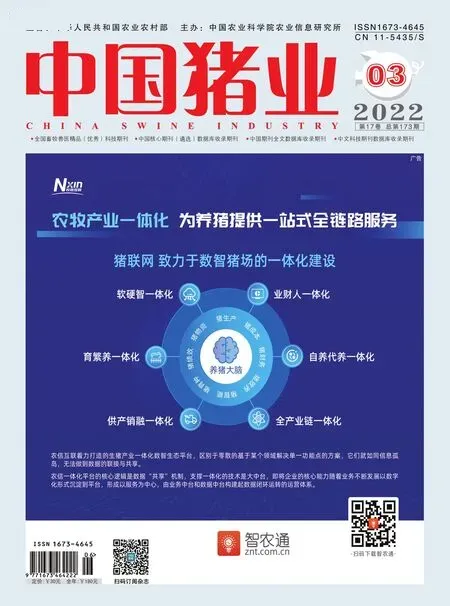非洲猪瘟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宋志霞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山东淄博 256100)
非洲猪瘟(Africa swine fever,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frica swine fever viru,ASFV)感染引起的猪的高度传染性和致死性的多器官出血性疾病[1]。ASF最早见于1921年的肯尼亚,随后ASFV一直在非洲地区扩散传播;20世纪50代末至80年代初,I型非洲猪瘟病毒在欧洲、南美洲等国家出现;2018年,在比利时、波兰的野猪中发现ASFV,同年8月,我国辽宁首次报道了非洲猪瘟疫病,随后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点状散发,同时我国周边国家如蒙古、越南、朝鲜也出现了非洲猪瘟疫情[2]。本文对非洲猪瘟病毒的病毒学特征和非洲猪瘟的流行病学特点进行综述,为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控、相关抗非洲猪瘟病毒的药物和疫苗的研发提供参考。
1 我国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猪肉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53%[2]。2018年以前,我国每年出栏生猪约7亿头,但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后,2019年我国的生猪出栏量为5.44亿头,生猪出栏下降22.3%,猪肉产量4 255万吨,下降21.3%。由此可见,非洲猪瘟对我国生猪养殖业造成危害的严重性[3]。我国确诊的首个非洲猪瘟病毒毒株为ASFV-SY18,属于基因Ⅱ型毒株,p72基因片段与格鲁吉亚、俄罗斯和爱沙尼亚分离的毒株具有100%的核苷酸同源性,表明与上述国家的毒株有着密切关系。在我国,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主要为西南地区(生猪养殖密集),其次为东北地区,尤其黑龙江省。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2019年我国猪肉供给出现严重缺口,导致国内市场猪肉价格大幅上涨,从12.2元/kg(2019年2月)上涨至2020年2月36.1元/kg[4]。
2 非洲猪瘟病毒的病毒学特征
ASFV是一种大型的双链DNA病毒,病毒结构非常复杂,病毒粒子直径为175~215 nm,包括包膜、衣壳、内包膜、核壳和类核[5]。ASFV大小约为170~190 kb,编码150~200种病毒蛋白,其中包括68种结构蛋白和100多种非结构蛋白。p72是ASFV的主要衣壳蛋白,因编码该蛋白的基因序列在不同基因型的毒株中较为保守,因此常用作ASFV的血清分型[2]。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是ASFV入侵和复制的靶细胞,但相关的感染机制未完全清楚。目前已知ASFV主要通过网格蛋白依赖性内吞途径和巨胞饮作用进入宿主细胞,但是介导这一过程的细胞膜受体和病毒蛋白尚不清楚。内化的病毒颗粒会逐渐移动到宿主细胞内,在宿主细胞内去除核壳和内包膜释放出病毒基因组,ASFV在宿主细胞核中大量复制和转录,且不依赖宿主细胞参与,但蛋白翻译过程仍需宿主细胞参与[6]。复制的病毒DNA在宿主细胞内被翻译成病毒蛋白后,通过内体系统将子代病毒转运至细胞膜,通过出芽的形式释放到细胞外。在病毒的入侵和繁殖过程中,为了防止被宿主的免疫系统识别和破坏,ASFV可通过被cGAS识别然后通过信号通路线向下游传递信号,拮抗cGAS/STING通路上的多个分子阻断信号传递来削弱免疫反应[7]。ASFV编码的多种病毒蛋白可在感染早期抑制外源性和内源性细胞的凋亡。如ASFV可以抑制宿主细胞中的干扰素(IFN)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活化、转录和表达,同时抑制其下游蛋白的表达[8]。此外,ASFV还可以抑制适应性免疫反应,例如主要阻止相容性复合物(MHC)-Ⅰ/Ⅱ的表达和细胞毒性T细胞的活化及转录因子核因子kappa beta(NF-κB)诱导促炎因子表达,同时,ASFV可以通过调节NF-κB来调节机体的一些炎症反应[9]。
3 非洲猪瘟的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
非洲猪瘟的临床症状与其病毒的毒力有关,同时还与感染猪只的年龄和免疫状态有关。除一些急性出血死亡的症状外,还有可能出现慢性和亚临床病程。ASFV的高毒力毒株可在感染后的7~10 d内引起猪的急性至重度临床症状,致死率高达100%;而弱毒力毒株(Ⅰ型毒株)感染猪只后,其病程潜伏期相对较长,感染猪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但会排毒,一头猪一旦出现症状,可能已经感染了整群猪。因此,需要做好非洲猪瘟病毒的定期监测。
非洲猪瘟的临床症状通常是非特异性的,包括高烧、厌食、呼吸困难、呕吐、下痢、皮肤发绀、共济失调和过急性死亡等[10],怀孕母猪可能会因高烧而引发流产,此外,还有病猪白血球和淋巴球数量减少。感染猪的外观可见耳、鼻、腋下、腹、会阴、尾等部位出现紫斑,解剖可见胸腹腔、心包、胸膜、腹膜上有许多澄清、黄或带血色液体,显微镜下观察组织可见血管内发生纤维性血栓,血管周围有较多的嗜酸细胞。Sanchez-Vizcaino等[11]解剖感染欧亚非洲猪瘟病毒分离株的病猪,发现包括肝脏、胃等的出血性淋巴结肿大和不同程度的脾肿大,此外,肾脏、膀胱和胃壁的瘀点以及肺水肿和出血性胃炎等病变也十分常见。
4 非洲猪瘟的流行病学
4.1 易感宿主
ASFV具有较强的宿主特异性,猪是非洲猪瘟病毒的唯一脊椎动物宿主;此外,多种软蜱,尤其钝缘蜱属的软蜱是ASFV的节肢动物宿主并在家猪的感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2]。钝缘蜱的寿命较长,在感染ASFV可在其体内迅速复制至较高的滴度并持续很长时间,非洲猪瘟病毒对蜱虫影响较小,但也可造成蜱虫死亡。对软蜱中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后的复制研究表明,非洲猪瘟病毒感染软蜱后需要15~21 d才能到达病毒复制开始的中肠上皮,在感染后28 d达到峰值病毒滴度。在蜱的生活史中,非洲猪瘟病毒可以通过性行为从受感染的雄性传播给雌性软蜱,通过雌性软蜱卵巢传播给后代,并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中经生殖道传播。在带毒软蜱叮咬生猪后,通过血液造成对生猪的感染。
在非洲地区,非洲猪瘟病毒主要维持在软蜱和疣猪之间的森林循环中;疣猪在感染非洲猪瘟病毒后会出现病毒血症,但不会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非洲地区的其他野猪,如丛林猪也可以感染并传播非洲猪瘟病毒。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家猪后,可使家猪产生多种临床表现,从慢性、亚临床或低水平疾病到出血热和过急性死亡,具体取决于病毒毒株的毒力和宿主的易感性。对高毒性欧亚基因型Ⅱ非洲猪瘟病毒分离株的研究表明,该毒株对家猪和野猪的致死率为100%,且一般从非特异性临床症状(发烧、抑郁、厌食、腹泻)迅速发展至死亡。
4.2 非洲猪瘟病毒的传染源与传播途径
非洲猪瘟病毒的传播方式复杂多样,可在家猪—野猪、野猪—软蜱—家猪之间传播,并可通过直接和间接接触或短距离气溶胶在猪群内传播。同时,感染猪的排泄物、唾液、鼻腔分泌物等均可带毒,并通过短距离气溶胶传播;此外,同圈舍的猪通过直接接触被污染的饲料、饮水器、地面等均可感染该病。隐性感染猪只作为病毒的携带者和传播者而成为新的传染源。
在户外,野猪的活动范围较广,非洲猪瘟病毒可以在感染的野猪尸体和被污染的环境中存活数月,一旦带病毒野猪尸体被其他食肉动物或鸟类吞食,就可能发生非洲猪瘟病毒的机械传播。此外,人类的贸易、动物诊疗、物资运输等活动也可造成非洲猪瘟病毒的传播。对2018年8—11月的68起非洲猪瘟疫情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19%的非洲猪瘟疫情是由生猪和猪肉制品的跨区域运输引起的,46%是由车辆和人员流动引起的,34%是由泔水喂养引起的,揭示了人类活动在非洲猪瘟病毒传播中的作用。
5 结语
自2018年以来,非洲猪瘟在我国的发生,给我国养猪业带来较大影响,但在国家政策正确引导、养猪企业的积极配合下,通过生物安全管理、监测淘汰等机制使得国内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控制,且疫情发生数量呈逐年降低的趋势,表明我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已初见成效。非洲猪瘟的流行病学研究在防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非洲猪瘟的传染机制、病毒与宿主细胞的相互作用等方面仍有待深入研究。因此,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仍需加大对非洲猪瘟病毒基因的致病机制研究,为非洲猪瘟病毒检测和疫苗研发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