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星空 立足脚下
张竞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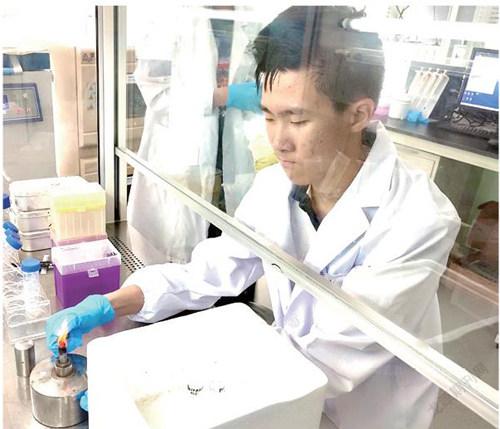



初识“月宫一号”
2021年,我有机会参加了英才计划项目,并幸运地加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红教授“月宫一号”课题组,这是一个为人类未来移民太空而建造的、模仿地球环境的大型密闭生态系统。第一次来到北航,进入“月宫一号”这个密闭的不锈钢舱体中,我非常激动,仿佛来到科幻小说中描绘的太空世界。我想到了埃隆·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想到科幻小说《时间深渊》中长满热带雨林的太空飞船“深渊号”,还有电影《火星救援》中马特·达蒙种的土豆……结合兴趣,我选择研究BLSS (生物再生生命保证系统)中的微生物,具体就是研究BLSS体系中的秸秆发酵,这个题目好像既不科幻,也不浪漫,也不好玩,但是,通过阅读文献,我发现这个研究很重要。在BLSS系统中,以秸秆为代表的植物不可食用部分的处理是限制整个体系能量循环、物质平衡的重要环节,因为秸秆固定的碳破坏了体系的碳平衡,它所蕴含的生物能得不到利用,就会大大降低体系中的能量利用率。
立题之路多坎坷
当我踏入这个领域,才发现需要学习的知识是多么庞杂,需要看的文献也浩如烟海。为此,我阅读了《太空生存》《木质素降解菌的降解机理和应用》《木质纤维生物质的酶糖化技术》等专业书籍,查阅了秸秆预处理、生物燃料乙醇技术、菌种筛选和转基因技术、食草动物粪便菌群、糖化酶合成技术、类土壤基质、深空探测方面的文献……经常刚明白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另外的问题。看了这么多文献后,我彻底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更不知道路该怎么走。我所设计的方案和路线,或者没条件,或者没意义,或者不可行……
放眼星空,立足脚下
与导师就研究目的和方案进行了多次探讨,最终在导师和师兄的鼓励下,我决定在放眼星空的同时立足脚下,先弄清楚“月宫一号”中秸秆的发酵过程。发酵菌群来自驯化的食草动物粪便中的微生物,秸秆来自“月宫一号”中种植的小麦。秸秆的发酵过程或许前人已经有过研究,但我设计了新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新体系中的发酵过程开始了全新的探索。幸运的是,不管我计划怎么做,课题组的老师都给我尽可能多的支持和帮助,给了我探索的自由,同时也会在我偏离正确路线时及时提醒。
在实验室老师的指导下,我不仅学会了无菌操作、菌种筛选、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等技术,还建立了测定发酵产物中还原糖含量的方法,分析了菌群中微生物种类,探索了提高微生物分解效率的方法,并对分解产物的成分进行了分析。我的实验数据为提高BLSS系统中植物不可食用部分的利用提供了数据支持。
未来可期
在BLSS系统之外的地球生态系统中,如果从食草动物粪便中分离出的纤维素降解菌能将秸秆中的纤维素转化为糖,那么地球上所有的树木、草丛都可以成为人类的食物,地球上将不再有粮食危机。在刘慈欣的小说《天使》中,通过对人类基因的改造,使人类的肠道产生纤维素分解酶,创造出了能吃草的人,解决了地球的粮食危机。其实比这更可行的办法是在食草动物的肠道菌群中提取出能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在体外将草变成糖,变成美味的食物。在这条道路上,我刚刚迈出了探索的一小步,希望未来有机会继续深入研究。
有了目标,问题便是进步的动力源泉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很多困难。虽然文献上有实验方法,但在实际动手时,仍然有很多细节不知道该怎么做。比如,最基础的纤维素降解菌的筛选,不同文献培养基的配方不尽一致,培養条件也不同,我应该如何选择呢?最适合的培养条件和配方是哪一个呢?在测定发酵产物中的还原糖时,文献上说水洗,怎么水洗?是浸泡还是冲洗?需要加热吗?需要加洗涤剂吗?每一步在文献上一笔带过的实验方法,都隐藏着很多问题。此外,实验结果与预期不同,是新的发现还是操作错误呢?或是还有未考虑到的因素?有时,在微生物培养了很长时间后,才发现一个重要的条件被忽略了,一切又要从头开始。总之,在科研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只能在解决一个个小问题中向前推进。
周末,我经常徒步北京周边的野山,山上没有清晰的路标,甚至没有路,爬的时候既要小心探路、披荆斩棘,又不能忘记大方向;既要记住走过的路,以便回撤,也要清楚前方的目标;既要在“六只脚”APP上搜索前人走过的路,也要走出自己的路。科研也是如此,要在解决每个当下问题的过程中推进实验,既要参考前人的工作经验,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方向,要有自己新的发现。
我喜欢爬山,因为我在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虽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也能看到少有人看到的风景,科研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