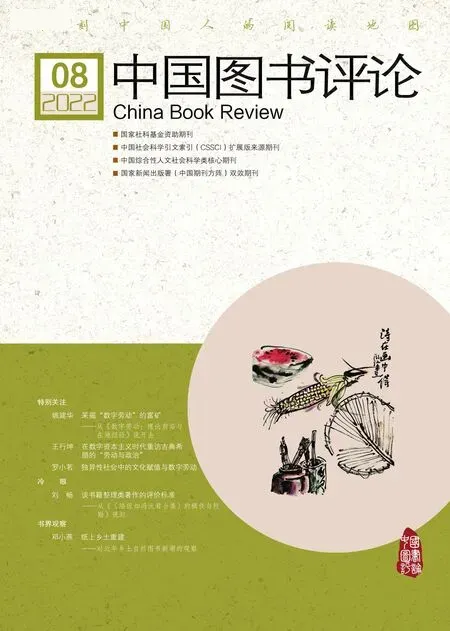纸上乡土重建
——对近年乡土自然图书新潮的观察
□邓小燕
一
21世纪走完了21个年头,回顾围绕乡村展开的讨论,话语中心经历了从“三农”问题向“乡村振兴”的转换,这也清晰地体现在乡土书写的变迁上:在世纪初引起轰动的是诸如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2000年),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2002年),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2004年)这类图书,乡村危机的全面呈现是这一时期乡土书写的核心主题。后之则有梁鸿的《中国在梁庄》(2011年),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2011年),尤其是《中国在梁庄》,似乎可视为一个殿军性的文本。此后有关农民处境讨论的重点逐渐转移到都市农民工的生存境遇上,如2013年梁鸿的《出梁庄记》以及2015年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这一写作趋向逐渐汇入底层写作的脉络中。
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整体改观以及城市化在造成乡村空心的同时也客观上带来乡村生态环境的改善,“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具有问题化特征的“三农”问题话语逐渐让位于“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这类观念。在这种大背景下,新的乡土书写逐渐现出端倪,对乡村生活的细节,诸如风物民俗之美、草木虫鱼之趣乃至于农事生活、饮食、器物、技艺等的呈现,成为一种新趋势。从表面上看,乡村话语从一种残酷的现实主义风格转向了具有牧歌色彩的田园主义风格,似乎回避了社会矛盾,但几乎所有写作者都有深深的隐忧,面对一去不返的乡村生活,乡土文化消失的不安萦绕在作家心中,留住乡愁的情感诉求希望通过文字形式得到满足。作家们致力于在文字世界中呈现已逝的乡村生活,这与自民间到官方的乡村建设实践是相呼应的,就其文化意图看,可将这一写作新潮视为“纸上乡土重建”。
早在2006年,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八溪峒笔记》就预示了这种新的倾向的出场,这部作品至今已有了11个版本,充分显示了新的文化偏好的吸引力。事实上,在2000年,韩少功就逆潮流而动,回到汨罗山村居住,乡间生活构成了他的《山南水北》的主要内容。《山南水北》有意识地将重点放在乡村的人和物以及两者的关系上,他弱化了20世纪80年代“寻根”时期强烈的启蒙主义立场,把乡土生活看作一种有意味的生命状态,并将之命名为一种低调务实的“次优主义”生活[1],这是一种反思现代化的生活方案。同时期乡村书写热衷于从社会学和人类学汲取理论资源,产生出具有明确问题意识的调查报告。韩少功与此不同,他不认为寻绎村庄结构的方法能够抵达村庄的本质,乡村的动植物、农作物以及农民(包括作者自己)及他们的关系才是韩少功最看重的内容。
与韩少功书写八溪峒笔记差不多同时,同为楚人的湖北襄阳作家舒飞廉创作了《飞廉的村庄》(2004年)。舒飞廉以富于温情的笔墨,在纸上还原自己村庄的身体,“将这个村庄,通过我微不足道的文字,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个一个人地建立起来”[2]。韩少功与舒飞廉都选择以散记、笔记的形式呈现村庄,就村庄书写的文本形式探索而言,都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文体意识。韩少功以短篇散记的方式展开八溪峒的世界,舒飞廉则从周作人所开启的美文传统中汲取经验,其文字风格颇有周作人所译《枕草子》的风味,短章中富于乡土风物、村居生活的趣味。直到2012年,舒飞廉在文体探索上才有了更为明确的自觉意识,在《飞廉的村庄》修订版《草木一村》中,他将原本散乱的笔记归入季节、动植物、农事、人物传记、民俗等几大方面,形式上调整之后,飞廉村庄的身体就显得更加清晰了。这看似是一个小的变动,却涉及作家在书写乡村时如何选择或创造一种合适文体的问题。
2007年前后,浙江桐乡作家邹汉明开始他的江南书写,创作了《江南词典》《少年游》。值得注意的是,邹汉明的“江南”想象是以作者从小生活的塔鱼浜为根据地的,即从乡村想象“江南”,但因为塔鱼浜在2009年被拆迁,邹汉明又从“江南”回归塔鱼浜,写成《塔鱼浜自然史》(2020年),记录了塔鱼浜的地理、岁时、动物、植物、昆虫以及农事,在纸上重建起一个在地图上已经消失的江南村庄。邹汉明的写作,用孙郁的一个说法,可归入“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3],这尤其体现在周氏《故乡的野菜》这类乡土自然书写对邹汉明的影响上,周译《枕草子》的文风也渗透进邹汉明的文章中。邹汉明是熟悉舒飞廉作品的人,他们的写作显示了周氏传统对当前乡土自然写作的巨大影响。
还有一位不能忽视的作者是湖南郴州的黄孝纪,他的“八公分村系列”显示出对“纸上乡土重建”高度的自觉意识。大约受到梁鸿“乡土非虚构”产生的社会效应的影响,黄孝纪在2012年前后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家乡八公分村,此时正是梁庄受到公众关注的时候。但与梁鸿以社会学、人类学方法考察村庄结构变迁不同,黄孝纪更重乡村生活经验和乡土记忆,他将“恢复”村庄的肉身作为自己的文学使命,因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乡土植物(2019年《八公分的时光》)、村居饮食(《一个村庄的食单》、2021年《八公分的味道》)、岁时节庆(2021年《节庆里的故乡》)、农器杂具(2018年《江南旧物》、2019年《瓦檐下的旧器物》)、农事技艺(2020年《故园农事》)等方面。黄孝纪和邹汉明是当前乡土书写中最具自觉意识的两位作者,他们致力于从塔鱼浜、八公分村乡土自然的方方面面着手,在纸上重建故乡。创作自述中,他们也一再袒露这一意图。
此外,还有一些作者也可归入这一潮流,如陕西汉中作家李汉荣,他的创作自觉继承了汉水流域“周南”之地的《诗经》传统,乡土自然世界是其写作的中心内容,这体现在他的《家园与乡愁》(2017年)、《牛的写意》(2019年)、《万物有情》(2019年)等作品中,最集中的呈现,则是在他的“乡土自然三部曲”中,包括《动物记》《植物记》《河流记》(2019年)。李汉荣是散文界的老将,也是一位美文家,文字极富情思,很能显示他在写作上的苦心孤诣,也因为作品进入教材而颇著声誉。但他未把建立一个比较清晰的地方乡村世界作为写作目标,这与其强烈的散文性追求不无关系,即为了成就散文的完美而失去了对具体的地方形象的建构,这一点是不同于沈从文的地方,虽然两者都是秀美山河中的作家。广西桂林作家霍香结近年围绕故乡汤错展开的文体探索,也有强烈的乡土自觉性,《铜座全集》(2021年)是对汤错地方的疆域、民俗、草木鸟兽虫鱼、历史文化的近乎人类学式的深描。其中,《汤错草木鸟兽虫鱼疏》是一部具有民族植物学色彩的乡土自然文学。另外如山东菏泽作家宋长征的《乡间游戏》(2017年)、《乡间食味》(2020年),诗人胡桑的乡土散文集《在孟溪那边》(2017年),江苏徐州作家杜怀超的《大地册页》(2017年)、《苍耳》(2017年),宁夏西吉作家郭文斌的《农历》(2016年)等作品,都显示出致力于“纸上乡土重建”的努力。这一潮流孕育于本世纪头一个十年,最近几年则形成了一个写作高潮。
二
“纸上乡土重建”的作者大都具有“农”的身份,在目前的文学版图中,他们多住在离生活过的村庄不远的“地方”小城,在离开曾生活过的乡村多年之后,乡愁构成了他们写作的巨大动力,空间上的接近则为其纸上还乡提供了诸多便利。实际上,不少作者最初的写作动机并非为了文学,而是眼见村庄的消失,在恋乡情绪的驱动下进行创作,因而在形式上与主流文体也相对疏离。
与新文学传统内的乡土文学相比,当前的乡土写作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其一,当前的乡土写作弱化了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和启蒙主义的立场。现代乡土文学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在现代化焦虑下,作家对乡土文化和乡村生活普遍持批判的态度;近年的乡土作者则相反,他们整体上认同乡村,在立场上,他们多以村人的身份写村庄,而不是作为归来的知识分子。其二,当前的乡土书写普遍没有从一个村庄想象乡土中国命运的野心。现代文学的乡土作家,他们的根本动机在于从乡村看中国,乡土书写即中国书写,鲁迅笔下的未庄和鲁镇实际上是乡土中国的一个切片,21世纪初期的村庄书写,包括以梁鸿为代表的“乡土非虚构”写作,也是在这个传统内的;当前的乡土写作者则更强调村庄的地方属性,他们试图记录一个曾经存在过的、有独特个性的村庄共同体,放弃了从一个村庄中寻绎乡土中国的冲动。其三,当前的乡土写作格外看重乡村的自然因素。如果说现代乡土文学的核心命题是“人的文学”,重点是讨论人的处境,普遍将注意力集中在宗族关系、伦理以及父权制度对人(主要是青年和女性)的压迫问题上,当前的写作者则不仅强调乡土伦理温情的一面,还看到乡村不单单是一种独特的伦理空间,更是一种人与自然协作造就的地理空间,因而风物、自然、草木虫鱼、农事、饮食等,都成为关注的重点,这无疑是生态意识兴起的结果。
前文已经提及,“纸上乡土重建”在写作实践中,首先面临着选择何种形式来承载乡土情绪,即乡村的文本形式问题,他们较少从虚构传统中获得文体启发,普遍倾心于“非虚构”写作,但与梁鸿的近于人类学、社会学调查的文本不同,当前的乡土写作有着更为多元化的探索。就目前的创作实践来看,西方与本土两方面的资源为其文体想象提供了支撑。
其一,转化西方自然文学、博物写作的经验。自然文学对乡土文学的影响,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梭罗对散文家苇岸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博物学的复兴,自然文学与博物图书大量涌现,这种影响也越来越普遍,并带动了一大批中国作者对本土风物与动植物的关注。自然文学对当前乡土文学的影响,首先体现为强烈的命名意识,同时也格外重视人与物的情感关系,这构成了当前乡土写作中最具有情感吸引力的一个面向。当前乡土书写对物的兴趣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特征,这与以往乡土文学的自然书写多呈现为风景化的景物描写是很不相同的。具体来说,韩少功的《山南水北》背后有《瓦尔登湖》的影子,这本书甚至被认为是“中国版的《瓦尔登湖》”。[4]邹汉明的《塔鱼浜自然史》采用“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这一概念,显然受到了英国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伯恩自然史》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经过了周作人的中介作用。李汉荣的写作虽然有强烈的美文意识,但他的大量作品,诸如《万物有情》《动物记》《植物记》《河流记》,都有为自然物立传的意图,其对自然生命所展开的细致的观察,对心与物接的情味的捕捉,都有自然文学的影子。如果说美国的自然文学、博物写作体现为对荒野精神和自然主义的追求,它在文化上构成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思和批判,那么在中国,这种文化精神则体现在乡土文学中,因而“纸上乡土重建”对现代化、都市化的反思和批判,与自然文学和博物书写便具有相同的时代品格。
其二,利用与转化传统文体形式,主要包括一些相对边缘的文体,如方志、史传、博物志、名物注疏、月令、物候、岁时记、农书以及食单等。邹汉明的写作显然受到了史志传统的影响,他在创作《塔鱼浜自然史》前就有相当丰富的史志编撰经验,曾编写《桐乡历史文化丛书·名物小识》《嘉禾丛谭》《炉头三记》等地方史志,《塔鱼浜自然史》也可视作一部个人化的村志,人物志部分虽未单独呈现(作者称该部将单独成书),但人物故事实际被很好地结构进“自然史”了。霍香结的《铜座全集》建立在对传统方志的继承和改造上,目录中列出凡例、疆域、语言、风俗研究、虞衡志、列传、艺文志,都是典型的方志体例,甚至按照方志惯例附了地图,最终形成了一部文学化的地方志。《铜座全集》第四卷《虞衡志:汤错草木鸟兽虫鱼疏》,显然是对古代名物注疏之学的继承,题目也是对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效仿。农事活动在乡村生活中具有灵魂性的地位,因而农书的利用就更为普遍。农事生产在现代乡土小说中很少有系统性的呈现,“纸上乡土重建”却特别看重农书的文体意义,几乎所有作者都有意识地书写农作物与农事活动。以茅盾和邹汉明为例,他们都是桐乡人,但茅盾的《春蚕》与邹汉明的《蚕》显示了完全不同的写作取向,前者关注世界经济霸权如何影响到水乡蚕农,蚕事活动的记录是支离的,后者则算得上一卷文学化的“养蚕经”。邹汉明对同乡先儒张履祥推崇备至,张氏的《补农书》对他的写作也有影响,这种农书意识集中体现在《农事诗》一章中。黄孝纪的《故园农事》本身就是一部文学化的农书,全书分“种田”“作土”“育山”“养殖”“手艺”“农闲”几章,是对地方农事活动的系统记录,实际上,农事书写也贯穿于黄孝纪故园写作的全部作品中。对岁时记与月令的利用转化,也较为普遍,从汪曾祺的《葡萄月令》到阿来的《成都物候记》,岁时记、月令、物候写作等文体形式作为现代文学的一条暗线始终不绝,显示了此类文体在记录乡土与自然知识上的优长。舒飞廉的《草木一村》就将物候与岁时结合起来,《塔鱼浜自然史》也将“岁时记”单列一章,《节庆里的故乡》则以四季为序记录岁时节令。
在西方,自然文学与博物书写被视为“非虚构”的重要内容,当前的乡土写作有一种大散文的特征,普遍具有“非虚构”写作的倾向,不少写作者都有脱离既有文体窠臼的意图,就散文而论,抒情散文和学者散文都难以团拢土地上的方方面面,因而吸收古今中外的各种文体资源,以创造一种大地文体、村庄文体、自然文体,就成为“纸上乡土重建”在文体探索上最突出的特征。
三
考察“纸上乡土重建”写作潮流的形成,需要注意其发生的文化背景,其中有三个相互联系的因素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是地方意识的兴起与地方文化的重审。乡愁是与具体的地方相联系的,在启蒙视野中,地方文化往往因其不符合现代知识标准而受到批判,如医疗经验、生活习惯以及民间信仰,但在“纸上乡土重建”中,这些资源成为承载地方意识的重要基础,因而鬼怪故事、民间医疗经验和草药知识、民俗文化,都成为确认人与地方情感的重要内容。这些个性化的地方知识往往是富于人情味和趣味性的,如动植物的地方名称、民俗的地方化表现等。以南方常见的野生植物薜荔为例,霍香结的书中写道当地人称之为“鬼馒头”,这是极形象的名称,而黄孝纪的八公分村,当地没有明确名称指代它,因为长得如乒乓球,所以可叫它“乒乓”,又因可用于做凉粉,因此人们也叫它“凉粉果”。这里,地方知识成为彰显村庄个性的基础。
其二是博物学的兴起与物的意识的兴起。20世纪以来,乡土话语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文明进步论者将乡村视为进步之链上保守落后的一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则将乡村视为一个有别于现代都市的熟人社会结构,阶级视野下的乡村则是农民与地主斗争的历史场所……认识乡村与采取何种认识眼光是密切相关的。近年来,随着博物学的复兴,数量庞大的博物图书的出版和形式多样的博物实践的推广,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博物意识随之兴起,乡村中的动植物、农作物、器具风物等,都被纳入到观察者的视野中来,结合对传统农书、名物考证之学的借鉴与改造,一种融入了个人生命体验的博物书写就此产生,这也是“纸上乡土重建”普遍重视乡村地理空间中的物的意义的原因之一。
其三是生态意识的兴起。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成为关注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普遍呈现出生态转向,文坛宿将诸如贾平凹、迟子建、阿来、韩少功等,都显示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当前的乡土书写,也普遍倾向于呈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李汉荣写作的生态主义立场是最典型的,他笔下人与牛的亲密关系动人至深。《动物志》一书分为“向牛羊致敬”“写给猪狗的赞美诗”“小兽们”“飞鸟与鱼”“对不起,虫儿”五部分;《植物记》一书分为“蔬菜情谊”“植物传奇”“草木忠厚”“水果诗篇”四部分;《河流记》的副标题为“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生态意识是李汉荣写作的核心伦理。韩少功《山南水北》一书最富魅力的地方,在于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自然生命的不可言说的性情,譬如青蛙能辨别捕蛙人的脚步声,葡萄会发脾气使性子,一棵树会发疯,草木也各有心性等,这种对物类品格的把握是平等对话的结果,这构成了《山南水北》的伦理品格。黄孝纪在书中也谈到农民与鸟类的关系以及祈鸟节的风俗等。邹汉明、舒飞廉等人的书中,这种伦理品格也体现在人与土地、农具、作物乃至于鬼神的情感关系中。
四
“纸上乡土重建”与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但同时又具有某种边缘品格,这种边缘性不仅体现为这批作家在文学版图中的位置,也体现在文体选择上放弃主流小说而倾向于“非虚构”写作。这种品格与其文化追求是相关的,理解这一点,不妨将之与当前两种主流的乡土书写做一对比:其一是乡土小说,其二是主旋律乡村书写。乡土小说可以阿来、贾平凹等人近年的创作为代表,如阿来的“山珍三部曲”(《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2016年)、《云中记》(2019年),以及贾平凹的《山本》(2018年)等,都是近年受到较多关注的小说。阿来与贾平凹用心经营的仍旧是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乡村与土地的形象实际上是很模糊的,是背景性的。阿来通过三种地方特产(虫草、松茸和岷江柏)的命运书写,直面乡村自然与文化生态的当下境遇,虽然插入了大量博物学知识,但作者显然无心构成一个乡土博物馆。贾平凹小说《山本》虽是历史题材,但他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位因无法施展抱负而埋头编撰《秦岭植物志》《秦岭动物志》的麻县长,这透露了作者尝试触摸秦岭身体的意图,但虚构的小说实际上无法托起秦岭的山河草木。另一方面的乡土书写是近年在“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产生的主旋律作品,如王宏甲的《塘约道路》(2017年)、纪红建的《乡村国是》(2017年)、关仁山的《金谷银山》(2017年)、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2018年)、赵德发的《经山海》(2019年)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都在书写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典型人物与典型村庄,展示农村扶贫工作与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以此配合现实农村的政治实践,乡愁并不构成作者内在的情绪动力,写作者也未将记录乡村的传统形象视为自己的文化使命。与上述两类乡土书写相比,“纸上乡土重建”的文化重建特征是很突出的,这种文化品格在传统乡土文化消失的大背景下显得尤其重要。
当前,一方面是城市化、现代化的高歌猛进,另一方面则是地图上乡村的不断消失,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目前每天平均有80~100个村庄正在消失。无论这一数据是否准确,乡土的消失是中国当前非常普遍的文化焦虑,留住乡愁也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诉求,“纸上乡土重建”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用霍香结的说法,正是“将这种乡愁肉身化的意志从深处引导了写作者的趣味”[5]。黄孝纪也写到,既然乡村无法挽留,那就趁它的背影还未完全消失,“用真实而朴素的文字,一颗赤子之心,尝试将它们列入一个永不褪色的记忆的博物馆,为几代人的乡村生活、乡村记忆立传”[6]。“纸上乡土重建”眼光虽是向后的,但并不是谱写一首乡村挽歌,而是对乡土知识做全面打捞与构建的工作,将地方的自然造物、人造物、人与自然合作造物、精神造物等,编织为一体,进而确认人与土地以及域内万物的独特的亲缘关系,以这样一种温柔的方式参与对现实的反思,实际上也是对乡村文化价值的确认。
近年,随着经济条件的成熟,官方和民间推动的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与此同时,乡土文化建设的意识也越来越明确,“纸上乡土重建”作为最近几年比较突出的一个文学潮流,它在乡土文学谱系中的新品格,在乡土重建中独特的文化价值,都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出版社和专业编辑,也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出版倾向,并成为“纸上乡土重建”在近年异军突起的重要推手,广西人民出版社对黄孝纪创作的大力支持,百花文艺出版社对李汉荣作品的编选,韩少功作品的一版再版,霍香结探索性写作的推出等,无不如此。
注释
[1]韩少功.山南水北[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343.
[2]舒飞廉.飞廉的村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0.
[3]参见孙郁.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J].当代作家评论,2001(1).
[4]钟芳.中国版的《瓦尔登湖》——韩少功《山南水北》赏析.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1/2011-04-21/96605.html.
[5]霍香结.铜座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928.
[6]黄孝纪.瓦檐下的旧器物[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自序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