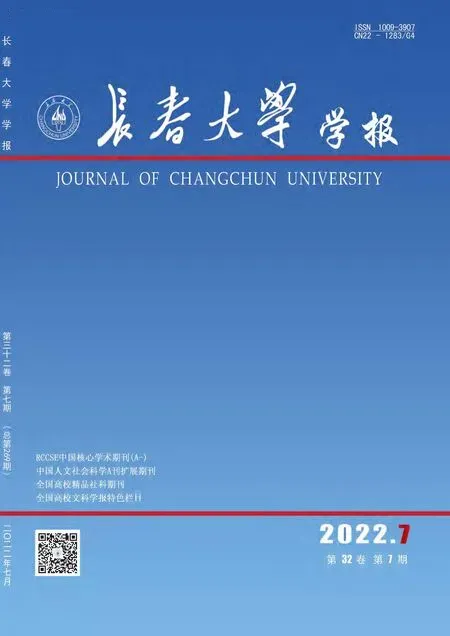作为“反乌托邦小说”的《撒旦探戈》及其美学
符 晓,孙 雪
(长春理工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22)
《撒旦探戈》(Satantango)是匈牙利当代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László Krasznahorkai,以下称“拉斯洛”)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关于欺骗、希望、欲望和覆灭的小说,具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与艺术特征。拉斯洛虽然在讲故事,但作为独立的故事、故事与故事之间的嵌套与勾连及其衍生出的线索和情节非常复杂,加之“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小说甚至哥特小说及让·贝西埃(J.Bessiere)所谓“当代小说”(le roman contemporain)所具有的诸多特征,都在《撒旦探戈》中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存在,同时,小说中也存在一些属于拉斯洛的“私人”特征,为小说提供了更为深广的阐释学空间。
一、作为“反乌托邦小说”的《撒旦探戈》
《撒旦探戈》讲述的是关于欺骗的故事。在一个经历了从繁荣到衰落的穷村庄里,农业合作社被废弃了,大部分村民都选择逃离,留守的人们无路可走,在阴雨的深秋等来了“救世主”伊利米阿什的出现。伊利米阿什承诺给他们“未来”,但实际上这个承诺除了一场骗局之外,一无所有。小说以伊利米阿什回到村庄为界,上半部分以延宕的话语将视点集中于人们对于“救世主”的等待,下半部分则跳跃性地讲述骗局的发生和人们如何面对骗局,具有很强的反乌托邦(Anti-Utopia)小说气质和特征。
莱曼·萨金特(Lyman Sargent)认为,“反乌托邦”是建构“一个不存在的世界,通过非常丰富的细节呈现出一定的时空定位,并致力于对乌托邦的批评或对正面乌托邦作品的攻击”[1]。可见,反乌托邦小说的理论支点是从形式到内容上否定乌托邦。在《撒旦探戈》中,几乎所有人都在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他们来的消息》一章中的弗塔基、施密特及夫人都觉得这个没落的村庄还有希望,所以当得到朦胧的好消息(伊利米阿什和菲特利纳即将回来)时,施密特夫人发出了一连串既怀疑又感慨的关于未来期许的叹息,而弗塔基“充满快乐和希望地吐着烟圈”[2]27,期待好消息的降临。骗子之一伊利米阿什也洞察到了村民的心,所以在《伊利米阿什如是说》一章如伏脱冷一般的演讲中极力鼓吹他要带领村民去的“理想国”:“在那里每个人都能丰衣足食,生活得既平静又安全,每天晚上能够有尊严地坠入梦乡。”[2]236双方面建构都指向了这个村庄关于未来的“乌托邦”,但现实是,村庄的最后一个秋天充斥着淫雨、烈酒、谎言、通奸、阴谋、死亡、背叛和等待,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乌托邦都并没有实现和实现的可能,相反,这完全是对“乌托邦冲动”的反抗。
从形式上说,《撒旦探戈》也呈现出很多反乌托邦小说的倾向性。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反乌托邦和乌托邦在相对长的时间里是一体两面。英国学者库玛(Krishan Kumar)曾指出:“无论是整个世界还是个人生活都没有出现他们在乌托邦中所努力渴求的景象。反乌托邦是他们对自己的愚蠢幻想的恶意报复,是对高贵却又虚幻的乌托邦期望的间接讽刺。”[3]反乌托邦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无限地放大了乌托邦小说的细节,在形式上更极端,因此,《撒旦探戈》在反乌托邦小说的意义上也形成了其独特的美学。一是反讽。拉斯洛建构了一个在读者和“骗子”看来都显而易见完全不能实现但在弗塔基等人看来马上就能够抵达的“迦南地”,本身就是巨大的反讽。等待“希望”的人们在黑色的清晨伴着布满蜘蛛网的手风琴跳起探戈,他们以为迎接他们的是天使,而对“撒旦探戈”浑然不觉,这些都在细节处指向反讽。二是荒诞。《撒旦探戈》的荒诞既是贝克特意义上的,又是加缪意义上的。如《等待戈多》一样,村庄里留下的弗塔基们同样等待着“戈多”,只不过“戈多”的肉体虽然来了,但是人们盼望的“戈多”的灵魂并没有出现。同时,等待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对话主体间语言能指和所指的不对等,环境描写尤其是对“物”的新小说式的描摹,相信与不相信的循环等,都构成了荒诞的最初表征。拉斯洛尝试着将小说中的“可能”存在于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世界里,并披荆斩棘寻找新的归途,可是正因为人们荒诞地存在,又自始至终都一无所有,印证着加缪的哲学。
希尔莱加斯(Mark R.Hillegas)认为,所谓“反乌托邦三部曲”“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它们都描绘了在噩梦般的国度中,人们被迫屈从于乌托邦政权,自由被消除,个性被碾碎,历史遭到有计划的全面破坏,人与自然相隔绝”[4]。《撒旦探戈》中呈现出来的未来梦魇、束缚自由、个性泯灭在某种意义上也呈现出了这些特点,人们渴望的“美丽新世界”充满了荒诞、反讽和不可能,乌托邦世界没有到来,他们反而在反乌托邦世界里继续苦苦挣扎。这些属性都使《撒旦探戈》成为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也只有以此为视域,才能进一步讨论小说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二、“赤裸生命”及其存在状态
法国思想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在评论由贝拉·塔尔(Béla Tarr)拍摄的同名电影《撒旦探戈》时曾指出:“这是一个有关承诺和欺骗的故事。乍看之下,它是一部反映共产主义的电影的最平庸的剧情。”[5]如果不考虑文学和电影的边界,朗西埃的这种说法或多或少也可以言说这部小说。
在《撒旦探戈》中,存在着多重骗与被骗的欺骗关系。一是伊利米阿什和菲特利纳骗取弗塔基们的“存款”,他们戴着伪善的面具占领所谓的道德制高点,表面上像先知一样,实际上巧舌如簧,扫荡了留守村民最后的“血汗”和尊严。这个欺骗关系也成为整部小说的“行动元”,是前述朗西埃所言“承诺和欺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小艾什蒂被哥哥诱骗,种下“钱种子”,每天为它浇水,期待它瓜熟蒂落,这显然是一个低级的骗局。在人间处于食物链最底层的女孩只能到动物界寻找浅薄的“尊严”,种钱、虐猫、自杀这一系列惨烈的“事件”透露出了小艾什蒂的双重单纯。三是施密特、克拉奈尔和弗塔基打算欺骗村子里的人“携款潜逃”,虽然只是一个想法,但悲剧在于,他们做了如“骗子”一般的计划,却被“骗子”以一种“已知”的方式骗走了他们的生活。四是小酒馆的老板被一个施瓦本(1)施瓦本指的是德国西南部历史地区,包括符腾堡公国、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省和巴伐利亚的施瓦本行政区,其中心城市是斯图加特市。人所骗,在他接手这个小酒馆之前,并不知道这里蜘蛛泛滥,而“合同里没有提这些蜘蛛”,导致他面对这种局面束手无策。五是以施密特夫人和弗塔基通奸及和其他男性的“暧昧”对丈夫的欺骗,虽不是重要的叙事内容,但日常的欺骗强调了村庄中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为故事逻辑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某种必然的条件。这多重骗与被骗的关系使故事更具有复杂性,尤其是塑造了关于村庄中被骗者的群像,他们之所以被骗,是因为他们的贫穷、贪婪和欲望,而当最后的尊严也丧失殆尽,他们就变得一无所有,成为彻彻底底的“赤裸生命”。
“赤裸生命”本身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无论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那里,都和政治存在紧密的关系。亚里士多德、阿伦特、阿甘本(Agamben)都认为“赤裸生命”是一种“政治剥夺”;而洛克认为,“就自然理性来说,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权利,因而可以享用肉食和饮料以及自然所供应的以维持他们的生存的其他物品”[6],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在于财产而不是政治,而“赤裸生命”首先是从财产的匮乏程度来加以判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撒旦探戈》完全是一部关于“赤裸生命”的小说。一方面,在这个关于欺骗的故事中,金钱实际上是叙事的内核,无论是弗塔基和施密特,还是伊利米阿什和菲特利纳,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获得钱或财产,即便是离开贫穷肮脏的故乡去追求“美丽新世界”,可是“行李就占了半个车斗”,可见家当和财产对他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虚假的“承诺”和愚蠢最终让村庄里的人们一无所有,他们相信“重建废墟,再次崛起”的“初衷”,毕其功于一役,来到城市寻找生路,却从贫困变成了“赤贫”。失去财产,甚至无家可归,这在洛克的意义上是典型的“赤裸生命”。
这样一来,被骗就成为了“赤裸生命”的主要存在状态。在前述五种骗与被骗的关系中,或多或少形成了被骗者的人格,而人格的通约性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疏离所产生的不信任,几乎每一个个体都戴着伪装自我的面具,在面对两个“骗子”时,他们是“傻子”,而面对其他人,他们则又成了聪明人,以至于整个村庄都充斥着欺骗和谎言。这可以看作是《撒旦探戈》中“赤裸生命”的存在特征,也是人格特征。无论读者如何迷失在小说精密而多元的叙事圈套中,都会对这些“赤裸生命”产生共情,因为村庄的破败和无秩序、村民的愚蠢和赤贫化、骗子的谎言和无道义这些指向洛克意义上“赤裸生命”的存在,不是假象,而就是事实本身。
三、《撒旦探戈》的隐喻和象征
朗西埃在谈及贝拉·塔尔的电影和拉斯洛的小说时注意到了雨在电影和小说中的反映,并认为拉斯洛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雨的帝国”。雨,是《撒旦探戈》的重要意象,但并不是全部意象,在这部小说中,拉斯洛有意识地凸显出作为意象的物,“撒旦、探戈、雨、蜘蛛、猫、《圣经》等都有隐喻和象征的内涵,使小说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特征更鲜明”[7]。从此意义上说,拉斯洛的小说既是卡夫卡式的,又是艾略特和里尔克式的。
首先,“撒旦探戈”本身就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在《圣经》中,撒旦在传统象征中是作为一个形象存在的,但在《撒旦探戈》中却具有群体性指向,因为“探戈”限定了撒旦。探戈和其他舞蹈的最大区别在于这种舞蹈必须由双人完成,而且,在探戈中,舞者之间的接触紧密,花式动作偏多,且具有某种“攻击性”。“必须由双人完成”反证了《撒旦探戈》中的撒旦必须是成对出现的,所以小说中的“撒旦”并是不“孤身一人”。一是骗子伊利米阿什和菲特利纳。他们的“行动”(act)最符合“撒旦的活动”,如“模仿上帝”“散布虚假的道理”“使人受苦”“引诱人犯罪”等。二是小说中的男人和女人。村庄的“夫人”们与男性本身就存在着很多具有挑逗性(探戈中也存在)的暧昧关系,如果没有愚蠢的男男女女和他们之间为了私欲而呈现出的不团结、不合作,“赤裸生命”也不会如此不堪,所以他们本身就是“撒旦”。三是骗子和被骗的人。“骗与被骗”是小说的中心逻辑,也是“赤裸生命”的存在方式,正是这样的双重人物使村庄“坍塌”,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有形或无形的“撒旦”,被骗者配合着骗子完成了对“撒旦”的建构。这三种“撒旦”能指或所指的可能,无论哪一种都指向村庄和人的覆灭,探戈本身具有狂欢的性质。
其次,“雨”在《撒旦探戈》中具有倾覆功能。雨是《撒旦探戈》中最重要的意象,小说中几乎包含了所有关于雨的“性状”,比如寒雨、湿雨、冷雨、秋雨、暴雨等,并多次出现雨、雨水和雨滴等。从《圣经》隐喻层面上说,《撒旦探戈》中的雨是《创世纪》(7:4)中所谓的“我要降雨在地上七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灭除”,实际指向的是惩罚。一方面,如果连续的雨是某种惩罚的象征,那么小说中的“雨水”惩罚的对象就既包括村民的愚蠢,又包括他们的欲望,无形中加深了小说和读者双重的沉重感,也造成一种压抑的既视感。另一方面,如果将《撒旦探戈》与对匈牙利政治的影射建立关联,那么雨又成为了某种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和包袱(如苏联)。无论是当代还是上溯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时期、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匈牙利在本质上都处在“外族”的控制之下,“淫雨”的笼罩显然可以看作是这种控制的象征,虽然不能将之全部理解成是惩罚,但控制本身也呈现出了《创世纪》中的毁灭。
最后,《撒旦探戈》中还存在一些关于动物的象征,最重要的是蜘蛛和猫。从叙事空间的角度说,小酒馆在小说中是各种“赤裸生命”的集散地,具有枢纽的中心空间位置,也可以看作是整个村庄的象征。而小酒馆遍布蜘蛛网,成为“铺设在酒馆内的某种新的陷阱”,神秘而恐怖。所谓“蜘蛛事件”,实际上是被骗者主观上仍然相信“美丽新世界”的到来,蜘蛛网也就可以看作是在包裹着人们最后的若隐若现的希望。但如《圣经》里所言,蜘蛛网脆弱而不堪一击,所以“希望”也同样“神秘而恐怖”。此外,小艾什蒂的“虐猫”事件“拆解”了整部小说,仿佛是一个游离甚至多余的存在,但事实上,猫与小说中的其他事件是存在一定关联的。猫可以被看作是“被骗者”的隐喻或象征,小艾什蒂则摇身一变成为“骗子”,而这个独立事件亦可以看作是“骗与被骗”的象征。韦勒克等将象征分为“传统象征”和“私人象征”两种[8],虽然这是新批评维度的划分,却也可以用在小说批评中。由此观之,《撒旦探戈》中既存在传统象征(如撒旦、雨),又存在私人象征(如蜘蛛、猫)。
四、“医生”作为讲故事的人
在所有的“赤裸生命”中,医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拉斯洛在十二章的小说中用了两章描述这个“独立”的人物。相对于弗塔基们来说,医生是个“例外”,他看上去并没有等“骗子”归来而是在等着其他什么。医生又成为了这部小说的叙事者,小说的最后一章,医生“着魔似的”继续在日记本上书写村庄的每一个“存在”,当他把之前的“创作”全部否定掉之后,重新写的“日记”恰好是拉斯洛所著《撒旦探戈》的开头部分,二者一模一样,使小说呈现出了环形结构。医生突然成为小说的“叙述者”呈现出了很强的叙事学意义。
首先,“医生”在客观上完成了《撒旦探戈》从“简单故事”到“复杂故事”的转向。就情节而言,《撒旦探戈》是一个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意义上的简单故事[9]。故事发生在一个相对短的单位时间里和一个相对小的有限空间内,“被骗”几乎是唯一的主题,所以,朗西埃在评论同名电影时曾直接指出:“在这部七个半小时长的电影里,除了一场骗局之外几乎没发生任何事情。”[2]24然而,这个简单故事是由一种宏大叙事完成的,“医生”成为了宏大叙事的主体,使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在一部小说中重复出现。此外,如果将“医生”看作唯一的视点,作者又以医生的视角从多个方面形成了某种“散点”叙事,虽然很多情节和事件对小说故事发展产生的影响和意义不大,但“医生”的日记即便是“看上去毫无意义的人的动作,他都必须不断观察着进行跟踪,记住一切”[2]76,导致很多人、物、事被准确、完整地记录下来,并产生了很多“成分故事”,使这个情节上很简单的故事复杂化。
其次,“医生”作为叙事主体的处理提供了一种叙事人称的新范式。“医生”是一个特殊的叙事者,他既是小说中的人物,又是“讲故事的人”,他时而与叙事者合体,时而与叙事者分离,而《撒旦探戈》又不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将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会发现,“医生”是个复杂的综合体。但“医生”并不能被简单归入华莱士·马丁(Wallace Martin)叙事学划分中的任何一种[10]。如果将之看作是第三人称,则“他”又出现在了小说中成为“自我”,又不能回答关于“谁在说”的问题。而且,小说的大部分情节和言论由医生日记记录,但他的日记中又不存在时间,他虽然用日记本记,但记录的并不是具有日记形式的内容。同样,也不能将文本还原成“书信”,虽然看上去医生的“话语”是写给别人的,但也不具有书信的要素。这为理解医生作为叙事主体提供了很多不确定性。同时,也可以将《撒旦探戈》的视角看作是一种上帝视角,但这里所谓“上帝视角”并非全知全能叙事,而指的是由上帝“扮演”叙事者身份所形成的多种可能,这样也就能解释“医生”身上的叠加身份问题,他既是叙事者又是人物的第三人称形象是由“上帝”策划完成的,拉斯洛的这种选择也为小说叙事人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最后,“医生”作为叙事主体丰富了《撒旦探戈》的艺术性。其一,医生是一个对所有事物都进行仔细深入观察的人,所以小说中存在很多几乎是“照相机写实主义”的描写,尤其是针对“物”的描写,而且有时候会借鉴电影中的蒙太奇(montage)手法,体现出了诸多“新小说”的元素,这与“医生”作为叙事者不无关系,也无形中将小说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其二,《撒旦探戈》的结尾是医生“新”日记的开头,也是小说本身的开头,如果将其本身“自我吞食者”(Self-devourer)及“永恒”的意义与小说的情节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蛇衔尾”的哲学循环。其三,除了索引,医生的日记并没有一定之规,看到谁、看到什么就记什么,想起谁、想起什么就记什么,由此看《撒旦探戈》本身,大部分章节也是意识流小说的写作策略。这些在叙事学上都强调了“医生”的重要性,同时也使小说呈现出隐秘的复杂性。
贝西埃在谈到20世纪后半叶的小说时曾指出:“小说与书写的混淆现象,即小说家更愿意把自己等同于书写,也还是小说在自己历史上实现其无可代替和其权威性的方式:它被自己的观察游戏和叩问游戏所俘获。”[11]从这个意义上说,《撒旦探戈》也是拉斯洛的文学实验,他小心翼翼地讲故事,并在讲述的过程中掺杂了很多属于个人的美学要素。如果说现代主义是一种反传统的“骚动”,那么拉斯洛则让这种“骚动”更真实、更精彩,所以在《撒旦探戈》中甚至能够看见非常极端的反传统“骚动”,也就是涉及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建构,反乌托邦小说、荒诞的“赤裸生命”、叙事多样性、深邃的隐喻和象征实际上都指向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