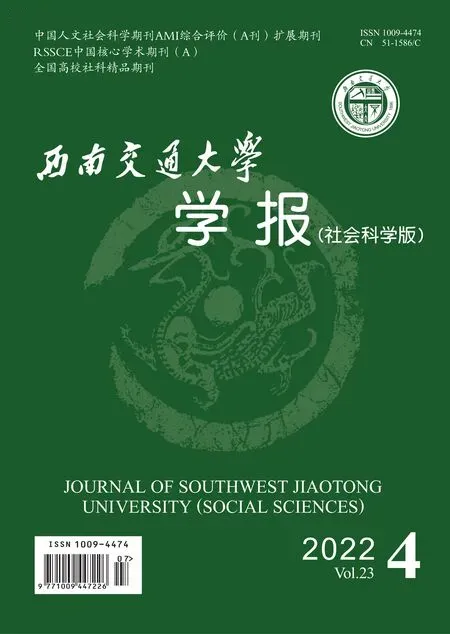张仙的变容:从苏轼出生故事论起
张志杰
一、引论:苏轼的出生故事
清道光十六年(1836),程恩泽、祁寯藻等名流雅会寿苏,梅曾亮作《展东坡生日序》,结尾申述寿苏会的意义说:“凡有文字之日,皆谷神不死之时。岂独丙子之年,为张仙降生之日?此南华火传之薪,即东坡长生之学者矣。”〔1〕丙子年即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是年旧历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文化巨子苏轼出生在眉山县纱縠行。所谓“张仙降生”之说,则具体涉及苏轼出生的故事。
关于苏轼的出生与“张仙”之间的关联,本源于苏轼父亲苏洵的记述。苏洵有《题张仙画像》一篇,自记:
洵尝于天圣庚午重九日,至玉局观无碍子卦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乃云:“张仙也,有感必应。”因解玉环易之。洵尚无子嗣,每旦露香以告,逮数年,既得轼,又得辙,性皆嗜书。乃知真人急于接物,而无碍子之言不妄矣。故识其本末,使异时祈嗣者于此加敬云。〔2〕
苏洵的这一题识是有关张仙最早见于记述也是最重要的记述之一,成为后世纷繁的张仙谈论中被反复引述的内容。张仙延嗣的信仰,当不始于苏洵,但是苏洵礼张仙画像而得苏轼、苏辙的记述,无疑是张仙叙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并且因为苏轼兄弟的卓越成就,这一故事引发后世关于张仙的种种谈论,似乎也就成为必然。
张仙在北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文人的笔记杂录、诗歌创作以及图像的题跋赞颂中,有纷繁的记述。现代以来,学者对于张仙的关注也并不缺席,民俗学、人类学相关书籍中通常会有一定的介绍,在广义神话学的视野下,一些神话学著作也有论及,如袁珂《中国神话史》在宋代初年蜀中神话部分即特别论到“张仙送子”之说〔3〕。不过就笔者知见所及,当前的研究中,关于张仙的琐细繁复的谈论并未得到有效的梳理,本文拟通过对历代张仙叙事的综合考察,厘清诸说生成与传播衍变的源流关系及其结构方式,谨就教于方家。
二、花蕊夫人的慧黠:“孟昶图”与张仙历史化的焦点
胡应麟《诗薮》论花蕊夫人云:“尝供事故主像,宋主问之,以张仙对,信慧黠女子也。”〔4〕历代关于张仙的谈论,主要以花蕊夫人“假神祀昶”〔5〕故事为焦点,而中间又关联其他神祇、人物,呈现出张仙历史化的复杂纠葛。
将张仙与花蕊夫人关联起来的记载,较早见于明中叶陆深的笔记《金台纪闻》,云:
世所传张仙像者,乃蜀王孟昶挟弹图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宫,念其故主,偶携此图,遂悬于壁,且祀之谨。一日,太祖幸而见之,致诘焉。夫人诡答之曰:“此吾蜀中张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实有所谓张仙也。蜀人刘希召秋官向余如此说。苏老泉时去孟蜀近,不应不知其事也。〔6〕
陆深记录了传闻始末,并且特别表明其说来源,可知此前蜀中即已存在着这样的口头流传,花蕊夫人与张仙故事在民间已经结合。对于这一传闻,与陆深同时的都穆在其《谈纂》中也有议论,谓:“今世祈子奉张仙,其状纱帽挟弹者,乃蜀主孟昶像也。初,花蕊夫人得幸于昶,国亡入宋,艺祖亦宠之。夫人德故主,日悬其像室中。一日,艺祖入见而问之,夫人仓卒对曰:‘此张仙也,奉之宜子。’由是传播民间。”〔7〕郎瑛所述也大体相同,《七修类稿》卷二十六云:“蜀主孟昶美丰仪,喜猎,善弹弓。乾德三年,蜀亡,掖庭花蕊夫人随辇入宋宫。夫人心尝忆昶,悒悒不敢言,因自画昶像以祀,复佯言于众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宋祖见而问之,夫人亦托前言,诘其姓,遂假张仙。蜀人历言其成仙之后之神处,故宫中多因奉于求子者,遂蔓延民间”〔5〕。
以上三种叙述之间存在明显的承续关系,而对于花蕊夫人“假神祀昶”这一传闻,都穆与郎瑛相较陆深态度更加肯定,并且也将这一传闻认定为民间张仙信仰的起源。之后胡应麟的议论更进一步推动了此说的历史化。除了以上所及《诗薮》,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特别引述陆深《金台纪闻》之说,并认为“《纪闻》以此说得之蜀中一士夫,或颇近实”,并且进一步在辩驳他说中肯定了孟昶图故事的真实性〔8〕。从众多的记述看,花蕊夫人“假神祀昶”之说至迟在明清之际已完成其历史化。比如方以智即径称“张仙乃孟昶”〔9〕,其依据也是陆深《金台纪闻》所述。
从陆深记录此本事,到都穆、郎瑛等给予肯定,到胡应麟力破他说以定此说为信史,再到后人不断的传录和确认,张仙在关于花蕊夫人“孟昶图”事件的议论中走向了历史化。不过同时也可以看到,对于“假神祀昶”是否信实,陆深虽然最先记录了此事本末,但也有所谓“苏老泉时去孟蜀近,不应不知其事也”的疑惑,苏洵的《题张仙画像》中并没有提到花蕊夫人,这让陆深对此佚闻的可靠性也有所保留。事实上,其后明清两代的文人对于此说的辩驳与对它的肯定同样多。如彭大翼《山堂肆考》论及此说时,在引述苏洵、花蕊夫人之事后认为:“老泉时去孟蜀不远,乃不知有此事,何耶?”〔10〕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六论“张仙挟弹”,对于此一传闻的否定更加有力,徐氏特别指出“孟昶太祖时曾屡入朝,无缘不相识貌”〔11〕。以上彭、徐二氏所秉持的这两个方面的意见,事实上也成为后人否定“假神祀昶”说的两个基本依据。在诸人的辩正中,尤以赵翼之论有代表性。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论到:“昶之入汴也,宋祖亲见之,花蕊果携其像,宋祖岂不能识别,而敢以诡辞对?”“此像本起于蜀中,闺阁祈子久已成俗。是以花蕊携以入宫,后人以其来自蜀道,转疑为孟昶像耳”。他经详细考订,认为所谓张仙即是仙人张远霄:“蜀中本有是仙,今所画张弓挟弹,乃正其生平事实”〔12〕。赵翼所论,在否定花蕊夫人“假神祀昶”的意见中最为有力。
围绕花蕊夫人“孟昶图”故事,明清文人进行了大量的辩正。陆深、胡应麟等试图从源头对张仙进行历史化还原,对其作为信史的追溯也确实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和信从,但也遭到同样众多并且理由充足的质疑与辩驳,呈现出张仙历史化还原过程中正反两方面意见的复杂交汇。
实际上,在陆深之前的张仙记述中,并不能找到有关孟昶的信息,宋太祖接见过孟昶也是史有明言,这似乎表明反对方的意见更加雄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就此宣告“孟昶图”故事意义的瓦解。虽然有袁珂所谓“从神话转化出来的历史也不能算是历史的幸事”〔3〕的提醒,但作为一种观照视角,神话、传说或信仰等故事中的历史因素当然自有其价值,如果不特别强调历史化对其故事原有形态与性质可能造成的破坏与改变,而着眼于它对于认识故事本身源流演变的意义,那么这种将故事历史化的方式所展现的认知视角和文化心理及其具体的历史化“还原”,当然是有重要价值的〔13〕。历史上,人们总是一方面虔诚信仰和崇拜着神祇超现实的能力,一方面又试图在现实的历史中寻找渊源,从故事里探求历史的心理可谓根深蒂固。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花蕊夫人“假神祀昶”的慧黠故事极大推动了文人关于张仙的讨论,并引发了明清文人对于张仙身份的种种重塑和诠释。
三、张仙的变容:诸种身份的重塑及其结构关系
否定花蕊夫人“假神祀昶”的历史真实性,也就开放了诠释张仙身份的更多可能性,吸引着更多人加入这一讨论。对于张仙其神的身份,文人们一方面感叹莫知其所从来、莫知其为何神,另一方面又不断尝试给出各自所认为合理的答案。在孟昶之外,仙人张远霄、梓潼神张恶子、文昌星、周人张仲与黄帝子张挥、灌口二郎神以及张宿等等诸说于是纷纭而出。然而事实上,几乎每一种新的建构都必然引发对应的否定,或者辩驳某说以支持某说,或者在指斥他说中确立己说,以至相互错杂纠扯。但它同时也体现了明清文人关于张仙普遍的兴趣,并且正是在这种错杂纠扯中,张仙叙事的共性特征得以显现。综合看,诸说包含三个方面的共性要素,即张姓、蜀神(人)、挟弹,且分别从姓氏、地域、形象三个方面规约着这一主题,也制造着张仙的变容。下文即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诸说的生成、衍变及其结构关系作一些解析。
1.张仙为张远霄之说
认为张仙即是张远霄,是在否定张仙为孟昶说的过程中出现的第一种新的解释。首先提出此说的是都穆门人、《谈纂》的编者陆采,在都穆关于花蕊夫人的记载之下,陆采加按语称:“张仙,五代人,名远霄,于青城山遇四目仙翁得道。广西碑刻其像并苏老泉赞,则又若真有其人者,不可晓也。”〔7〕陆采结合民间事迹与历史记述,将送子张仙与仙人张远霄的传说联系了起来,虽然带着“不可晓也”的疑惑,但却由此引发了明清文人对于张仙其神种种身份的重塑。
与陆采同时代的郎瑛也辨正都穆之说称:“张仙名远宵,五代时游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赞。《谈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张仙也。”〔5〕徐应秋则给出了更多依据:“及考地志,卭州有挟仙楼,仙人张远霄者往来于此,每挟弹,视人家有灾者为击散之,疑世传张仙挟弹或本此耳。”〔11〕然而实际上从上文可知,诸人引以为据的苏洵《题张仙画像》并没有提到画中张仙即是张远宵,《嘉祐集》中也别无其他关于张仙与张远宵关系的记述。不过以上诸人所论碑刻与挟仙楼的存在,则说明二者在民间的口耳流传中早已结合。
2.张仙是梓潼神张恶子说
朱彝尊的议论可为此说代表,其《重修张仙祠碑》称:“花蕊夫人所画实仙,非昶象也。考仙即梓潼神,世乃分而为二,又以梓潼神为文昌星神号,于是乎失辨矣。”〔14〕可见梓潼神之说仍然是在否定孟昶说时提出来的。不过,实质上在此之前,胡应麟对民间流传的梓潼神之说早已有过辨正:“梓潼自有像,氅衣纱帽,与张仙殊不类。且道家言梓潼出处,谓文昌尚近之,祈嗣绝无干也”,并进一步指出二者结合的原因在于“梓潼之神本蜀人,且张姓,因缪相传。今又以梓潼,《化书》传文昌耳”〔8〕。原因当也不限于此,虽然梓潼神与文昌星合一而被主要作为司文运之神崇拜,但是至少在北宋后期就已同时被作为生育神信奉了。杨万里所撰虞允文神道碑中,就记述了虞允文的父亲虞祺“祷于梓潼神”而得允文的故事〔15〕。到了明清时代,此类叙述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3.张仙与文昌星、周人张仲与黄帝子张挥的关系
清代董醇《甘棠小志》中曾综合民间的各种传说,谓:“梓潼之祀张君,自汉已然矣。至神之名,或称亚,或称恶子。《化书》谓即黄帝子张挥,始制弓矢者。又谓即《诗》所称张仲孝友者。或又以为即张仙,苏老泉祷之而得二子者”〔16〕,将梓潼与文昌、张挥、张仲以及张仙等神祇人物的关系串联勾勒出来。
至于梓潼被传为文昌,其实二神本无干涉,至宋代始附会为一。而因梓潼有文昌星神号,于是又有了张仙为文昌星之说。南宋理宗朝以后,梓潼神被加上忠孝的内容(参见唐代剑《试论梓潼神在宋代的发展》一文的研究〔17〕),而文昌星因被实以姓名,于是流传中又与周宣王大臣张仲关联起来,如高攀龙《题张仙像》即称“《诗》称‘张仲孝友’者,即神也。今且列星于天,司命于世”〔18〕云云。而张挥被传为张仙,则更顺理成章,如谓“黄帝之子名挥,始造弦,张罗网,世掌其职,因以张为姓,则张仙之立名可思已”,世传挥子作弓,“则其为神而为张也,不过以弓故也”〔19〕。《吴越春秋》又本有所谓“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之说〔20〕,这应当也是流传中将张仙与皇帝子张挥以及“忠孝”的梓潼神、“以孝友闻”的张仲附会在一起的原因。
4.张仙与灌口二郎神的关系
灌口二郎神是蜀中护国神祇,曹学佺《蜀中广记》据《灌县志》记述其与张仙的关系云:“治西一里,离堆北洪厓山有斗鸡台,秦时二郎神与蹇龙斗鸡于此。世传川主即二郎神,衣黄弹射,拥猎犬,实蜀孟昶像也。宋艺祖得花蕊夫人,见其奉此像,怪问之,答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灵者辄应’”〔21〕。花蕊夫人的答辞与陆深、郎瑛诸人所叙大异,但张仙为二郎神之说也从花蕊夫人“挟弹图”故事而来则确然无疑。不过,在来集之等人看来,“人以二郎挟弹者即张仙也,二郎乃诡词”〔19〕,即认为以张仙为灌口二郎神之说只是附会诡合而已。
灌口二郎神被尊为“川主”,历代以来蜀人德之,孟昶甚至封其为“应圣灵感王”〔22〕,并且其形象也是挟弹的,这当是二者被诡合的主要原因。
5.张仙即张宿说
赵翼在《陔馀丛考》中曾称:“世所称张仙像,张弓挟弹似贵游公子,或曰即张星之神也”〔12〕。不过这一传说此前已遭到胡应麟的讥斥:“世又谓张星之神为张仙,按《酉阳杂俎》:‘天翁姓张名坚,又曰姓张名表。’则天与日与星皆张姓,宜海内张姓独多也,闻者莫不绝倒。”〔8〕所谓张仙即是张宿,除了张姓的附会,应该也包含与以上文昌星之说相似的所谓“列星于天,司命于世”的观念。
从口耳辗转到文字传录,诸说既相互辩驳又相互承续衍变,张仙议论呈现着彼此纠扯的复杂关系。明清文人对流传诸说的不断传录与反复论辩,实际上透视出同一种历史化思维,即认为张仙应该存在一个唯一确定的身份,并各自按照某一方面的依据试图寻求合理的解释。就发生学的视角看,神话、传说或信仰的叙事关系中,更本源更基础的方式无疑是口述而不是文字记述〔23〕,但具体口传故事与其文本记录之间又往往存在错杂的时间差,很难确定孰先孰后。在长时段里形成的送子张仙,身份到底是哪位神祇或人物,几乎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似乎也不必苛求定于一尊,但厘清诸种叙事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则是研究者必须的义务,正如袁珂所提醒研究者的,对于神话、传说、信仰故事等,“不妨从一些细小的蛛丝马迹处,求零片缀合的痕迹,却无须太花力气去加以辩驳,力图去拆散它,如果是这样,那就会成为正真的书呆子”〔3〕。
四、“挟弹”的谱系:张仙图、题诗与张仙形象
从以上诸说不难发现,被附会为张仙的各路神祇,实质上与张仙神格最核心的诞子之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张远霄是禳灾之神,梓潼神、文昌星是司文运主仕禄之神,二郎神是治水之神,周人张仲与黄帝子张挥以及张宿皆与延嗣无干。然而张仙的变容正是在以上神祇部分相似要素的附会诡合中生成的。如前文所略及,诸说的共性要素主要体现在蜀神(蜀人)、张姓、挟弹三个方面。前二者不须赘言,需要特别作一些论析的是其挟弹的形象。
“挟弹”在古代社会事实上有着渊源久远的传统。自先民“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以降,“挟弹”的场景在史籍中就颇为常见,甚至很早即从实际功用走向了游戏。《吕氏春秋》载晋灵公从城上弹人而观其避丸,《战国策》庄辛谏楚王有“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的形象描绘,《庄子》隋珠弹雀的议论以及《金楼子》中燕太子丹以秦武阳性好弹而为作金丸等,都为人所悉知。并且,这些记述议论也并不完全是传闻或寓言,比如在曾侯乙墓的考古中,就发现色彩斑斓的“蜻蜓眼”琉璃珠173颗、陶珠38颗以及不少紫晶珠(有学者认为曾侯即隋侯)〔24〕,可见“挟弹”在先秦即已成为公子王孙生活的日常。
历史上的“挟弹”形象,韩嫣与潘岳也许是最为人所乐道的。《西京杂记》记述:“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所失者日有十余。”〔25〕《世说新语》的记载更著名:“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26〕“挟弹王孙”与“挟弹潘郎”也成为后世反复使用的两个熟典。到唐五代,文人对少年贵公子挟弹的描写就更不可胜计,比如崔颢《渭城少年行》、李白《少年子》以及李益《汉宫少年行》等诗。尤其应该特别提及的是,自北宋以来即认定为孟昶妃花蕊夫人所作的《宫词》中,也有不少对宫人“挟弹”的描写,如“侍女争挥玉弹弓,金丸飞入乱花中”“裹头宫监堂前立,手把牙鞘竹弹弓”〔27〕等等。史载孟昶好弹,加之这些诗歌的描绘,无疑为后人诡合张仙之说提供了充足契机。
“挟弹”的形象也很早就进入了图像领域,学者确认,唐初淮安郡王李寿石椁内壁线刻《侍女图》以及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中即有挟弹的形象〔28〕。而据日本学者西上实的研究,成都羊子山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砖《弋射图》已见挟弹形象〔29〕。但“挟弹图”在市民社会的真正流行当在元明以后,并且通常以唐人挟弹形象入图,这从流传下来的诸多挟弹图题诗中可以得到确认,如杨维桢《题开元王孙挟弹图》等即是如此。元明以后,挟弹图与题挟弹图诗交相呼应,以明人汪砢玉所编《珊瑚网》为例,其中题《子昂春郊挟弹图》的文人便有宋濂、胡俨、黄溍、胡广等等一众名流。清编《题画诗》中所收录的题挟弹图诗,则有元杨维桢、张逊,明孙蕡、黄哲、汪广洋、张适、李东阳、陈绍光、陈继儒等的诗作十数首。元明及清历代的文人所题咏挟弹图,数量颇称大观,张仙挟弹图是其中重要一种。
图像作为一种特别的叙事方式,已越来越为研究者所重视。法国学者利奥塔(J.F.Lyotard)站在图像的立场,试图将图像从传统的言语、文字的遮蔽状态中释放出来,并认为“可以在不脱离言语的情况下进入图形,因为图形居于其中”〔30〕。中国本来就有“以空间为宗旨,重本体而善画图案”的叙事传统〔31〕,重视图像的意义因此可说是自然而然。张仙信仰本来即主要是一种画像崇拜。从苏洵的题识可以确认,北宋已有张仙图流传。明人吴其贞的《书画记》中,也著录有宋代无名氏白描张仙图小纸画一幅。不过苏洵以玉环所换购的张仙图与佚名的这幅白描张仙图都没有被详细描述,所以图中张仙的形象无法确知。当前所见张仙图多为清代以后年画中的张仙画像,更早的似乎只能见于石刻中保留的张仙画像了。《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在《民间年画》卷中收有清光绪间山东潍县“张仙射天狗”年画一幅〔32〕,《石刻线画》卷中收录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赵时雍所立石上线刻“张仙挟弹”像一方、明代“祈嗣张仙”像一方〔33〕。再之前的张仙画像则很难见到。日本学者西上实撰有《〈探幽缩图〉中所画的张仙像》一文,该文考察后提出,在日本江户时代御用画师狩野探幽(1602-1674)的《探幽缩图》中保存有明代以前张仙图的原画缩图数帧(原文附图)〔29〕,虽是缩略摹本,却保留了更早期的张仙形象,因而弥足珍贵。
传世张仙图中的核心要素自然在挟弹。挟弹的形象在明清笔记关于张仙的议论中多有叙及,前文所论笔记中已略呈数例,比如“今世祈子奉张仙,其状纱帽挟弹”(都穆《谈纂》),“世所盛传张仙像,张弓挟弹若贵游公子”(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等等。而在文人的张仙画像赞或题诗中,更强调“挟弹”的这一符号化特征,这里不须详述。可以说,“挟弹”的这一象征性形式是世人礼拜张仙图的最核心要素,一副满足了其他所有因素而没有挟弹形象的图画,显然不会被拜祀。如弗莱(Northrop Frye)所论:“可以断言,整个绘画艺术都不外乎把画的‘形式’即结构,与画的‘内容’即主题结合在一起”,并且“公众在要求一幅画酷似所画之物时,他们实际所要求的,往往是恰好相反的东西,即一幅画应该严格遵守他们所熟悉的绘画程序”〔34〕。
五、结语
有关张仙的记述在宋元时期并不多见,至明清时期始成大观,民间绘图像、作祠记,口耳辗转,流传不绝;文人笔记杂撰、题铭赞颂的议论也颇为热烈。口传、图像与文字的跨文本叙事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互文关系,既相互承续又转移衍变,形成了纷繁错杂的张仙叙事谱系。
综言之,由苏洵《题张仙画像》中所谓礼张仙像而得苏轼苏辙兄弟的记述,引发了后世关于张仙其神的种种想象、谈论与考证,其中陆深对花蕊夫人“假神祀昶”之说的记述以及由此形成的正反两方面的大量辩正尤其值得注意,它们层累叠加,呈现出张仙历史化议论的复杂交汇,同时也启发了文人对于张仙其神渊源的各种想象与重塑,并且正是在这一繁复的辨正与重塑中,显现出张姓(姓氏)、蜀神(地域)、挟弹(形象)的共性要素,三者既规约着这一主题,也制造着张仙新的变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