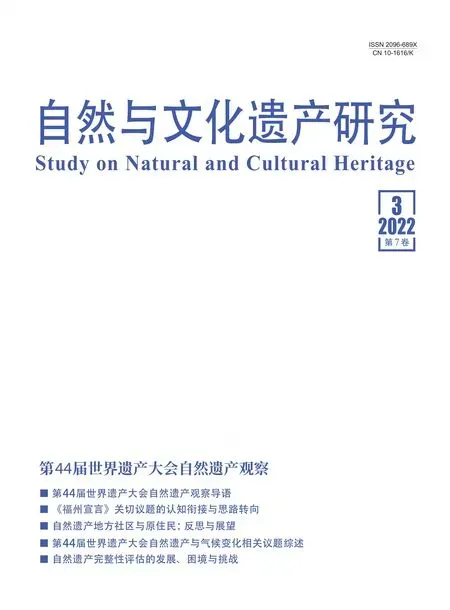遗产与生命意义——读《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十四个人类学讲座》
吴璨莹
(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十四个人类学讲座》收录了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的14篇讲演稿和1篇附录,本书作为“社会人类学丛刊”于2016年11月第1次出版。该书完整呈现了罗兰多年来在人类学、物质文化与博物馆等领域的研究心得,收录的讲演稿中不仅涉及对历史、遗产与物质文化等方面的具体个例,对非洲、欧洲以及中国的博物馆事象进行生动描述,更从学术史与方法论的层面重新审视了“遗产”的当代性,强调面对当代遗产文化“运动”趋势的情形,研究者应该具备更长时段、更开阔的学术视野。同时,在田野中聚焦技术、器物的有形文化遗产之外,也要关注人、记忆的无形文化遗产,尽可能突破视野局限,探讨文明的可能。该书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反思与继承的同时,将西方物质文化的有关论述与中国遗产研究有机关联,提出“宇宙观”“草根价值”等概念,对当下遗产所呈现的井喷与割裂现象以叩问和启发。
1 “历史、物质性与遗产”的关联
上篇“历史、文明与人类学”收录7篇讲演稿,主要以人类学家的角度对“文明”和“历史”进行研究与思考。开篇《从民族学到物质文化(再到民族学)》区别回归民族学与回归物质文化需要改变对物质性的理解,认为在物质性与文明的研究中,民族学的方法对人类学视野的局限是有益的。在《文明与非洲的一体性》中,罗兰认为:对非洲的认识应从分割的“地方性传统”转为探索是否存在更具综合性的文化形式,尝试把“文明/文化”概念从“复杂的”“先进的”社会模式界定中摆脱出来,并举例非洲的案例,以此说明“容器”与“人”的概念在非洲的盛行,以及整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上所形成的以“身体社会”为特征的文明形态和图式。《长时段过去和断裂》一文中,罗兰认为:用宇宙观理解时间的方式行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也由此提出“范围”“物质性”“时间性”3个核心概念,来阐明长时段的不同时期可能共存。《超越封闭文化:中国境外的文明、区域和长时段的延续与断裂》是对“长时段”理念的再延伸,讨论中非到西非“文明”的某些基本共同点,作为“容器”的身体不是在包含其他形式的意义方面被隐喻性地理解,而是通过物质消化和仪式实践的具体形式被塑造和构建。《文明作为对照的宇宙秩序:西非与中国》记录了罗兰在文明的比较研究上的进一步思考,以及建立于宇宙观、宇宙秩序上的讨论。“宇宙秩序”是罗兰自创的概念,强调:文明的本质是一种关于宇宙秩序的处理和表达方式,提出“不可见/可见”的二分法及其“沟通/相互渗透”的观点,是许多非洲文明的核心。同时,这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理解中国的文明,只是在中国表现为神像、庙宇等不同的方式。《作为宇宙统治之比照的文明》再度肯定了莫斯关于文明论述的重要性,举例在非洲和中国人提起“文明”时的不同想法,更客观地阐明“宇宙秩序”拓展下的“宇宙统治”的不同处理方式,将探讨的视野延伸至秩序之外,以此探讨不可见的文明世界。《新石器化:从非洲到欧亚以及更远之处》是罗兰对新石器时代的界定和影响的重新审视,通过更广阔的文明视野,发现新石器时代物品流动方式的变化,有着和欧亚文明不同的传播方式。
下篇“物质性、遗产与博物馆”同样收录了7篇讲演稿,以“物质性”为聚集,讨论遗产、记忆与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器物之用:物质性的人类学探究》表明罗兰对器物的观点,认为“激活”是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核心观点,物品有其自身内在的吸引力,以人类学的视角对考古学家提出器物的自主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献祭行为:对世界“之间性”的物质化》一文中,“献祭”遵循的是莫斯基于身体技术而进行的理解,是作为赋予生命的行为,通常与食用和供奉有关,通过喂食等身体行为作为干预力量激活物品,从而使“之间性”的物质化得到实现。《遗产、记忆与后殖民时代的博物馆》以“后殖民时代的博物馆”为切入点,对“遗产”和“记忆”进行剖析,罗兰认同博物馆未来的包容和反映文化的多元,与民众间的关系也将从培养纯粹的学术知识转换为促进社会意识的觉醒。《对遗产与记忆的再思考》阐述“文化遗产”是“二战”后提出的、较新近形成的概念,历史、记忆、文化遗产之间是不可相互化约的,罗兰叩问“遗产能否治疗创伤?”“何种记忆能赋予人们能力以一种健康的方式进行回忆?”,也由此探讨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严肃性。在《重新定义博物馆中的物品:中国遗产的井喷》中,罗兰提出:中国的博物馆发展是建立在西方和中国的“遗产”观念混融上的,对于文化遗产的实践应从政府和社会2个层面去探析,文物和遗产是多重力量交会商榷的领域,是非常动态的。《中国的新博物馆时代到来了吗》,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背景下表达了对博物馆建设的关注,并举例中国西南的3个案例,讨论中国情境下的博物馆与遗产。《“新型”民族志博物馆:数字化非遗技术、社区参与及文化还原》的主题是数字化博物馆,讨论技术革新对博物馆展示方式与转型的影响,探讨展品与来自社区间的联系、展示理念的更新,以及当代文化还原诉求加深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等所发挥作用的影响。
迈克尔·罗兰始于考古学,后沉浸人类学的学术经历,使他的研究具有“物质、物品同样是形塑与确立文化认同的传播过程的一部分”[1]3的视野。“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并不是探讨整个人类社会关于物质、关于文化遗产的大概念,而是在每一个长时段过程中,所生产的物品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在社会语境下的意义。因此,并不对社会语境进行解读而是更关注物品的心理联觉和外观,感受关联的断裂和不协调。罗兰认为:文明的遗留与遗产不可分割,遗产区别于考古、保护与博物馆研究。从政治上看,遗产概念也与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遗产组织间的关系相关,遗产的定义既有自上而下的来自组织、机构和专家的定义,也有仅仅指称个体经验的“遗产”。每个人都有独属的记忆,社会群体拥有集体记忆,群体中的人们也共享着一些记忆,尽管“基于不同的文化诉求与身份定位而呈现的多元化的遗产挖掘方式”引发对“本真性”的探讨,但这也使遗产不止被注视,而更加活化。
2 “遗产”的保护与割裂
“遗产”概念的兴起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关,“二战”后为反思战争的毁灭与破坏以及保护生命与文化财产而重新给出定义,确立可移动和不可移动财产[2]1-2。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75第1条规定文化遗产的范围为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后1976年《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2]101-102对“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环境”“保护”做了定义,克服了传统单体保护的局限。1987年《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2]171序言与定义(二)确立整体历史城镇与城区的保护,进一步扩展了整体文化遗产范围。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条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范围,包括:①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风俗、礼仪、节庆;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的手工艺技能[3]。《公约》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畴,更加全面地保护整体文化遗产。对于“遗产”的理解是一个不断实践与扩充的过程,罗兰提道: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概念在今天被广泛运用与实践,但对它的使用仍要十分谨慎,提醒“西方语境中产生的遗产定义是将文化给实体化了,使得身份认同成为‘物件’与财产”和“跨文化遗产对比的一个可能的共同基础,即对‘物品’(object)这一概念进行对比”[1]184。
在各国申请世界遗产的同时,中国也积极加入其中。截至2021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上公布中国的世界遗产数达56项,位居世界第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无形文化资产保护公约》,区分出有形遗产(tangible heritage)和无形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这2种类型的字面意思是“有形”和“无形”遗产,但在中国的概念里,分别译成“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1]183。在过去,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理解是认为它包含有3种形态的遗产:①“有形的物品”(physical objects);②“实际运用的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③“表演和展演”(performances)[1]183。所谓无形文化遗产是包含后2种形态遗产的,但在2006年以来,第3种形态的遗产,即表演和展演,被广泛强调,而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1]184。这是书中迈克尔·罗兰对中国遗产实践作出的总结,并不止一次阐述:“有形文化遗产如今被越发认为是那些‘死的’物品,重点在于物品与手工艺品;而无形的遗产则聚焦于活生生的文化展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世界遗产’为将过去储存于现在(restore past in present)的有形遗产,因这些物件都与记忆相关。随着对文化遗产与遗址的理解加深,‘无形文化遗产’的概念被提出,并被界定为一种活的记忆(living memory),并尤其关于活生生的仍在今天延续的文化展演。”[1]173中国的长城、明清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等文化遗产都极具代表性,其背后所蕴含的是关于被凝固的真实历史记忆,而“无形文化遗产”则被界定为一种活的记忆。以南音为例,南音也称“弦管”“泉州南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该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仅音乐本体被属于,而是包含了南音的乐器形制、曲谱(谱字)、古方言、缜密的曲牌体系、南音乐人、乐人们所拥有的关于南音的记忆以及南音馆阁文化等,其背后所传递的关于古乐历史的存留才构成了“文化遗产”。南音也成为闽南人的独属记忆,让人们在离开家乡时能够以一种健康的方式进行回忆,由此与游子间也构成独特的联结。南音作为文化遗产,在拥有专业演出团体和学界理论研究的同时,仍旧保有源源不断的民间爱好者,“玩南音”被喜爱南音的人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可交流自娱,可表演展示,不只被单纯地放置于高阁,这也是一种特别的保护方式。时至今日,南音没有一套“标准化”的奏唱模板,人们仍较多保持传统“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给予南音人更多的留白与探索,没有对南音馆阁与爱好者进行规划和约束,散落在各个乡镇村落间的南音馆阁不只是静态的文化遗产建筑本身,而是成为活态的文化遗产空间,与居民生活融为一体,并成为泉州这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事实上,对于遗产的保护无法只在定义上进行区别,“自上而下”与地方层面对遗产概念的认识、理解、反思与实践是多重力量商榷的过程,应基于地方文化和多元理解来激活当地的文化魅力,尽可能避免“封存”保护,造成遗产与实际生活的割裂。遗产是具有历史性和人文价值的。书中罗兰以考古学眼光出发,提出疑问:“什么样的遗产值得保护?”在遗产的修复实践中,也需要不断询问自身“我们到底在修复什么?”面对已经成为和即将成为遗产的遗产本身和所在场域是否原封不动地保护?或是仅仅保护遗产本身?泉州成为遗产地之后的遗产保护,除了关注遗产本身外,其活态遗产又如何对泉州古城和民居生活发生影响。由此,罗兰又以人类学的视野介入,认为应重视地方记忆、故事与美学,以重现一个完整的感性世界。
3 “宇宙观”与“草根价值”
泉州古称“刺桐”,是闽南地区的城市之一,因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发展,泉州的古海港留存至今。罗兰认为,古老的泉州城的生成逻辑是“宇宙观”式的,即“人们所共享的一套理解世界以及知识传播的方式”[1]85。在泉州成功申遗前夕,迈克尔·罗兰几次到泉州进行田野调查,并基于泉州遗产的保护、泉州城的水路贸易体系和城市面貌、泉州的活态遗产以及传统生活方式和艺术对泉州遗产价值的影响4方面出发,回应泉州遗产的未来,他认为可以从“宇宙观”的角度来理解,并提出了“草根价值是活态传统的一部分”“草根价值应被视为城市‘活态遗产’”[4]的看法,围绕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官方遗产,对“什么样的泉州值得保护”进行回应。
“草根”(grassroots)一词最早产生于19世纪美国淘金潮时期,意指一种经验总结,它在本土文化所指与外来文化所指的碰撞中产生了自己丰富的、新的文化所指,具有民间的、民众的属性特征与自强不息精神,被赋予了“基层民众”的内涵。“草根文化”相对于主流文化来说,是属于基层的、大众的,其核心源自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对新兴文化的创造[5]。泉州的“草根价值”包含当地家户和寺庙的联系在仪式生活中的重要性。虽然在某些意义上,人们认为它是“低”的文化,但罗兰表示:更接地气的遗产反而是构成地方自信和骄傲的核心,而泉州的历史积淀构成对美的感知能力是值得发扬与保护的。正如王铭铭谈到他在闽南地区的田野经历:“村民很少用‘遗产’这个词,而当他们谈到过去和现在时,却能够表露出一种强烈的文化连续性意识。倘若用‘遗产’这个概念来指代现在依然延续存在的‘过去的文化’,那么,村民们就不缺乏这种观念。然而,对于现代性政治和文化精英来说,‘遗产’表达着断裂的意义,它是一个‘经过选择的传统’(selected-tradition),代表着已经为现代革命和改革所破除的完整历史的有选择性复兴,代表着文化的最终消失和不符合现代性的文化形式的革除,更代表着民族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正当性”[6]。
王斯福也提出过:“在中国,不管在书面还是口头上,人们都认为仪式大略包括了规矩、礼仪、款待客人以及交换礼物的规则,这些人生仪式和岁时节庆仪式,使得原本隐藏的宇宙法则得以显现出来。人们相信靠自我修炼超越时空,或者靠正心、诚意的行为与生活,即可永恒不朽。”[7]泉州古城的传统街巷格局顺应了地理环境,依山水格局和传统文化人文基础,在受到风水观念和传统民俗影响下,形成了“一铺一境”的空间分划。“铺境”作为县以下城乡区划基层单位在泉州的遗存,是特定历史背景和地缘条件下的产物,泉州“铺境”是我国远古时期“里社”的孑遗[8]。而每一“铺境”都有“铺境主”,也是泉州神明信仰体系之一,在“铺境”空间中对“铺境主”的信仰整合人们的认同,“铺境”仪式则增强了吸引力。
民俗信仰是泉州“草根文化”一重要组成,在泉州鲤城区泉郡富美宫王爷信仰与送王船民间信俗的仪式中,“王爷”是早期统领“行瘟布毒”的使者,因此仪式的举行是为了驱逐瘟鬼恶疫,祈求合境平安。泉州的天后宫是泉州妈祖信仰的重要宫庙,人们用以祈求海上风平浪静,商旅平安。泉州人在民俗信仰与仪式中接受地方文化熏陶,包括地方民俗信仰在内的“草根文化”又影响着人们,从而形成了“地方-信仰-人”共同构建的宇宙逻辑。
这些对于仪式、对于“遗产”的集体记忆展现了地方文化所承载的“宇宙观”,在可见与不可见、物质与非物质的关系之间,叩问着人们对生命超越性和延续性的追求。世界文化遗产的列入以物质载体为主,通过载体来呈现非物质文化,在泉州遗产地的场域里,宫庙等建筑成为民俗信仰的物质载体,人们所奉行的关于祖先崇拜、关于生命伦理的观念也由此相连,庙宇、仪式的存在使得普通民众的生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泉州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或许更应关注完整性,在泉州遗产地保护的同时,也要将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进行关注。世界文化遗产所衍生出的文化意义与历史价值,在保护也在传承。人们对遗产保护的关注更多在物质保护、复原物件与修复建筑,认为以此保留地方的本真性,但往往将地方记忆、口述故事等置后,从而在物质保护的过程中产生对非物质文化的割裂,进而使当地人对遗产保护产生类似隔膜,尤其伴随年轻人的成长,对于“草根文化”既不能够坦然面对也无法完全割舍,并在长年累月中不自觉地完成了传承的过程,实现对“遗产”的再度延续。这或许与涂尔干和莫斯提出的“人观”相洽。人是道德的,在角色与功能的体系中有相应的位置和系列体验,能够以道德的人格包容、学习和实践。作为第二天性,我们每个人自然而然都有想象出来的自我和他者的形象:从孩提时代起,我们会以习得的行为和模仿他人的习惯,并从它们及其相关的矛盾感觉中来进行调适[9]。总之,“草根价值”所具有的包容性使泉州的文化遗产更加保有生命意义,能够使人们更加充分参与并介入到“多种形式来激活文化行为和传统”[4]的事业中。
4 结束语
“宇宙观”的视野有助于从更广阔的层面进行问题研究,遗产的本质是对人们生命意义的追问,而任何事物始终接受外界的刺激,被外界评价和赋值,因此遗产本身也是不断变化和实践的过程。迈克尔·罗兰的《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在物质研究的基础上给予更广阔的视野,以考古人类学的视角看待遗产问题,具有更深厚的意义,为中国当代的遗产保护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启发。在探讨遗产的问题时,除了自上而下的保护与推动,也不能忽略“草根价值”对遗产生命的再延续。正如罗兰所认为的:遗产保护必须以整体性的思考尽可能地保存人文的、美学的、感性的地方世界,这是最重要的。
——泉州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