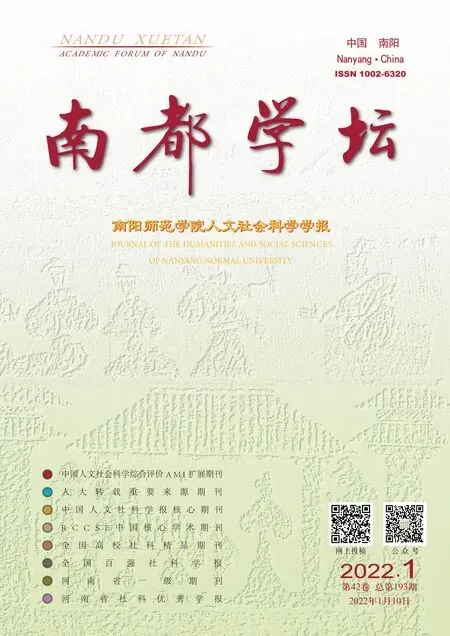刘宋明帝的皇权与佛教
徐 芬, 邹童舒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发展日益扩大,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汤用彤先生说东晋南朝帝王多有信奉佛教的,如东晋明帝、孝武帝,而恭帝造丈六金像于瓦官寺,亲自步行10余里迎像。宋武帝刘裕鼎革之时,利用释法称“嵩神言江东有刘将军,汉家苗裔,当受天命”说,借佛教僧徒制作劝进符瑞,则“朝廷之颇重佛法”,而佛教对当时政治社会所具备的相当影响,足见一斑[1]298。后来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又进一步推进深入(1)杨耀坤教授集中讨论了刘宋初期武帝和文帝采取崇佛措施,借以构建政权合法性以及强化皇权,参见《刘宋初期的皇权政治与佛教》(《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而孙英刚《布发掩泥的北齐皇帝:中古燃灯佛授记的政治意涵》(《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一文,分析北齐文宣帝高洋以当时高僧法上为佛,模拟燃灯佛授记的场面,布发于地,让法上踩之,通过这样的仪式,塑造自己佛教转轮王的身份,从信仰和政治的双重维度加强统治的神圣性。。宋明帝即位之初和之后崇佛举措与武帝以来的官方佛教政策,具有一贯的逻辑,有学者对此也有丰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僧侣世俗化,或僧官制度进一步世俗化等方面(2)如王永平《刘宋时期佛教僧尼与社会政治之关系考述》(《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一文,也言及明帝时期僧尼与宫中妃主联系紧密,地方诸王甚至利用僧侣觇视宫中消息等,但该文整体上讨论刘宋一朝从中央到地方僧尼群体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当时国家政治生活,并断言刘宋僧尼与政治紧密联系,是当时佛教僧徒生活世俗化的表现。林飞飞《刘宋帝王与宗教关系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专辟一节论述明帝与佛教关系,分别从明帝扶植佛教举措(延揽僧人、厚加礼遇,修建佛寺、以为功德,铸造佛像、崇信净土,延僧讲经、盛开法席,弥留之际、祈愿于佛等五个方面),扶植佛教原因(归依受戒,拉拢佛教等六个方面)以及加强佛教管理等等发面展开,视野较大,具有一贯性,论述详实,条理清楚。不过,可能论文着眼在整个刘宋一朝皇帝与宗教关系上,侧重点明显,对明帝即位的特殊性关注不够,在分析上稍有欠具体,还有补充的空间(第219-252页)。。但因各自关注点和侧重点不同,个人觉得还有未尽之处,故不揣粗陋,略作分析。
一、宋明帝即位之初的佛教举措
刘宋文帝元嘉之世政治社会长期稳定,为佛教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上自帝王,下到公卿士大夫,广泛信奉佛教;同时统治集团也认识到佛教在教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使家家持戒,则一国息刑”[2]262,在这些有意无意的政策引导下,佛教在政治社会层面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点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孝武帝、明帝时期。明帝即位之初,就积极采取一些重视佛教的举措,以下略作梳理分析。
第一,重新任命僧正。据《高僧传》卷7《释僧谨传》,释僧谨“游学内典,博涉三藏”,孝武帝敕之为湘东王刘彧师,湘东王“从请五戒,甚加优礼”。僧正智斌为当时佛教领袖,“义嘉构爨,时人馋(谗)(智)斌云为义嘉行道,遂被摈交州。时湘东践祚,是为明帝。仍敕谨使为天下僧主,给法伎一部,亲信二十人,月给三万,冬夏四时赐,并车舆吏力”[2]294。由上可知,智斌、僧谨僧正职位的更迭,与明帝践祚革故鼎新有密切联系,政治因素排在第一位。
沙门智斌“德为物宗”,受到孝武帝赏识,被任命为僧正。湘东王刘彧仓促之间与心腹谋弑刘子业而得立,而刘子业弟晋安王刘子勋在军府长史邓琬等人怂恿下在寻阳(治今江西九江)称帝,年号“义嘉”,两方阵营形成鲜明对峙,在这种情况下,智斌的处境就比较尴尬了。对智斌被摈一事,《释僧谨传》中陈述用语“时人馋(谗)斌”云云,或有给智斌辩解回护之意;不过切实而言,智斌“为义嘉行道”之事真假已经不重要。“时湘东践祚,是为明帝”,新朝伊始,革故鼎新,智斌被摈交州不过是表象而已。释僧谨受孝武帝敕命担任湘东王师父,最后获得湘东王信任,两人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明帝即位伊始,就在僧正人选上加紧布置,任命自己戒师僧谨接任智斌,“为天下僧主”,除了给法伎、亲信、车舆吏力外,还嘱咐各方州镇刺史赴任前都要到僧谨那里辞行,四方献贡所得,都要先问问僧谨那里有没有[2]294。明帝与僧谨有师徒之份,两人之间肯定有超出常人的信任和情谊,但明帝皇帝的身份和释僧“天下僧主”的任命,很明显是皇权在佛教政治秩序上的延伸与展示,有着强烈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意味,既凸显了皇权的权威,某种程度也有皇权寻求佛法支持配合的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明帝即位之初,也任命两位比丘尼为僧职。宝贤尼“操行精修,博通禅律”,受到文帝、孝武帝礼遇,“泰始元年(465)敕为普贤寺主,二年(466)又敕为都邑僧正”[3]108。宝贤尼任内“甚有威风,明断如神,秉性刚直,无所倾挠”。法净尼“戒行清洁,明于事理”,与宝贤尼名望相埒,明帝“泰始元年敕住普贤寺,宫内接遇,礼兼师友。二年敕为京邑都维那”,任事公正,“归德如流”[3]113。两位比丘尼虽然是女性,但都是有头脑、有修持、有决断、有持守之人,在佛教界积累相当声望,明帝选任他们担任僧官,也有倚重之意。
第二,建造兴皇寺,精心选任寺纲,敕令讲经。兴皇寺,据《高僧传》卷7《释道猛传》,释道猛博通经藏,“《成实》一部,最为独步”。后东游建康,居止东安寺。明帝还是湘东王时,就“深相崇荐,及登祚,倍加礼接,赐钱三十万,以供资待。太始之初,帝创寺于建阳门外,敕猛为纲领。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今得法师,非直道益苍生,亦有光世望,可目寺为兴皇寺’”[2]296。
关于兴皇寺创建时间,《释道猛传》仅言“太始之初”,“太”同“泰”。同书卷7《释僧导传》有“孝建之初,三纲更始”说,根据上下文,这个“孝建之初”指的是孝武帝即位改元的孝建元年(454),“三纲更始”很明显是说孝武帝即位拨乱反正,重新树立君臣、父子纲常。据《宋书》卷94《戴法兴传》记载,“太宗(明帝庙号)初,复以(巢)尚之兼中书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下面接“(泰始)二年,迁中书侍郎,太守如故”[4]2305。则“太宗初”的“初”就是泰始元年。同据同卷《戴明宝传》记载,“太宗初,天下反叛,军务烦扰,以明宝旧人,屡经戎事,复委任之,以为前军将军。事平,迁宣威将军、晋陵太守,进爵为侯,增邑四百户”,下接“泰始三年”云云[4]2305。按明帝平定刘子勋在泰始二年八月(“事平”),则这里“太宗初”之“初”意指泰始元年。《资治通鉴》卷132引裴子野论称“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满百里,卒有离心,士无固色,而能开诚心,布款实,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荡,寓内褰开”,根据上下文,裴子野“太宗之初”的“初”很大可能也是指明帝即位的泰始元年(或延至泰始二年正月)。根据上述各条史书撰写惯例来看,“太始之初”极大可能就是泰始元年,也就是说明帝即位之始,就启动了兴皇寺的创建(3)释志磐撰《佛祖统纪》卷36明确记载:“泰始元年,诏于建阳门置兴皇寺,敕沙门道猛为纲领。”这里释志磐径言兴皇寺创建在“泰始元年”,或有所据,聊备一说。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佛祖统纪》,第346页。。建阳门,建康都城东面正门,原名建春门,后改为建阳门[5]180。则明帝一即位,就在建阳门外兴建寺院,还取名“兴皇寺”(振兴皇业或使皇业兴盛之意),寄望释道猛以个人声望对新朝的建立添砖加瓦。就建寺的急迫性和寺名选取的着意性来讲,兴皇寺意义不一般。
对比孝武帝的中兴寺,两寺颇有相似之处。元嘉三十年(453)太子刘劭弑逆,武陵王刘骏自江州寻阳起兵东讨,一路沿江而下,临到建康,暂驻新亭寺,“銮旆至止,式宫此寺”。随即受朝野拥戴,在新亭禅堂即皇位。平定刘劭后,孝武帝又临幸新亭禅堂,“为开拓,改为中兴”,而“中兴禅房,犹有龙飞殿焉”[2]172。孝武帝在新亭禅堂即位,故扩建新亭精舍,并改名为中兴寺;作为龙飞之地,中兴寺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味。孝武帝即位有中兴寺,明帝即位于建阳门创兴皇寺,都是昭示皇权和正统性的存在。
同时,明帝给释道猛的待遇,与僧正释僧谨相差无几,这也充分说明兴皇寺与其它一般寺院不一样。兴皇寺建成,明帝敕释道猛开讲《成实》,开讲第一天,明帝亲临;讲经之后,明帝下诏对释道猛宾友以待,“可月给三万,令吏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车及布舆各一乘。乘舆至客省”[2]296。月钱三万,亲信或者白簿吏二十人,给车舆及吏力,释道猛的资俸待遇,与国之僧正的释僧谨同等,明显是超规格的。这种超常的礼遇,明面上是给释道猛的,实质上是给兴皇寺的。究而言之,与释僧谨僧正的任命一样,兴皇寺的创立和释道猛纲领的选定以及待遇的确定,依然是明帝皇权和权威在佛教政治秩序领域内的延伸和展示,也是明帝寻求正统性的昭示。
第三,在全国范围内,远到岭南、湘州,近到浙东,广泛征请高僧大德入京传法,这既是明帝利用皇权重塑规范佛教政治秩序,也从侧面反映他在积极争取佛教界的支持和合作。
除释僧谨、释道猛、释弘充、释法瑗和释慧隆等人之外,明帝即位之初,还积极征请地方各州高僧释超进、释道盛、释智林、释僧远、释慧基等进京弘法。山阴嘉祥寺释超进讲道浙东,明帝泰始中,“被征出都,讲《大法鼓经》”[2]297。湘州释道盛善《涅槃》《维摩》,兼通《周易》,明帝“敕令下京,止彭城寺”[2]307。释智林,师多宝寺释道亮,随侍师释道亮被摈岭南。后继踵传道番禺,明帝即位之初,“敕在所资给,发遣下京,止灵基寺”[2]310。灵基寺是僧正释僧谨以“四方献奉”所建,用作禅慧修行的寺院[2]294,释智林被征,可能与释僧谨有关系。上定林寺释僧远有名当时,孝武帝诏定沙门敬事王者,僧远谢病,隐迹上定林山,“宋明践祚,请远为师,竟不能致”[2]319。释慧基,师祇洹寺释慧义,博通经典,居止山阴法华寺,讲宣经教,学徒千有余人。明帝“遣使迎请,称疾不行”[2]324。虽然释僧远和释慧基未能成行,但明帝即位之后,远从岭南、湘州,近取浙东、建康,征请时望大德入京,既是践行“护法弘道,莫先帝王”的宗旨,同时也借由皇权对佛教的参与和规范,寻求佛法对皇权的认可和拥护。
此外,明帝也积极参加大规模法会,除兴皇寺、湘宫寺之外,明帝还曾亲临与孝武帝关系密切的庄严寺法会。“太始之初,庄严寺大集,简阅义士上首千人,敕亮与斌递为法主,当时宗匠无与竞焉。”[2]292何园寺释慧亮和庄严寺释昙斌善讲经论,在当时佛教界声望很高,被时人比拟为东晋高僧释道安和释法汰[2]292。庄严寺是孝武帝母路太后所立,寺有七层刹柱,冠绝京师。明帝即位之初,就亲临参与庄严寺法会,先简阅“义士上首千人”,最后定释慧亮、释昙斌相继为法主,先立威再树德,检饬在前,安抚在后,既昭示皇权,又争取民心。如果说释僧谨僧正任命、兴皇寺的创立,属于硬币的正面,那么对庄严寺僧众的处置,就明显属于硬币的反面了。
总之,明帝即位之初,就有意识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佛教资源,积极在佛教领域拓展势力和影响。如释僧谨是明帝湘东王时的戒师,被任命为僧正;释道猛是湘东王时旧识,被敕请为兴皇寺纲领;释智林被敕请回京和安排居住止灵基寺,或是释僧谨的建议和推荐,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明帝即位伊始,就有意图在佛教界延伸和加强皇权,借由佛教的影响寻求佛法对皇权的支持和合作。
二、明帝即位之初佛教举措原因分析
明帝之所以在即位之初,就积极在佛教界延伸和展示自己的权威。这主要是因为他皇位的取得过于仓促和侥幸,在法理和法统上有严重欠缺,不得不借助佛教来昭示和强化他皇权的合法性,有着明确而强烈的政治诉求。
明帝皇位是在景和末年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获取的。大明八年(464)闰五月,孝武帝崩,太子刘子业即皇帝位[6]4067。刘子业在短时间通过诛杀权臣和辅政大臣等确立自己的权威,大权独揽。完全没有顾忌和约束的刘子业“凶悖日甚,诛杀相继,内外百司,不保首领”[4]146,朝廷内外笼罩在恐怖的政治氛围中,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湘东王刘彧因为年长,受到猜忌,被拘在建康,又因为身体尤其肥壮被称为“猪王”。刘子业曾用木槽盛饭,加以杂食搅和,挖地为坑,填以泥水,让刘彧裸处坑中,以嘴就食,用为调笑戏谑[4]1872。景和元年(465)十一月戊午(二十九日),刘彧府主衣会稽阮佃夫联合吴兴寿寂之等人趁机举兵,弑杀刘子业[4]2312-2313。事起仓促,当时刘彧还被刘子业独自撇在秘书省,忧惧莫名之时,建安王刘休仁赶过来对他称臣,并引导其到西堂登御座。仓促之间,刘彧鞋子都掉了,赤脚到西堂;坐定之后,刘休仁才命主衣进白纱帽,换去刘彧头上的乌纱帽[7]。以路太皇太后令,纂承大统,教令内外。十二月丙寅(初七),正式即皇帝位,改元泰始[6]4087-4090。
刘子业身死,政治恐怖氛围解除,朝廷内外都松了一口气;但刘彧在兄弟辈中排行十一,即便有翦灭刘子业之功,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也不够,这导致他皇权合法性严重不足,号召力有限。时任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孝武帝三子,不奉明帝教令,在寻阳建牙,传檄建康,随即即皇帝位,改元义嘉。刘子勋檄书承认“嗣主(指刘子业)荒淫”,自述“任居藩长”有“黜幽陟明”之责;而明帝擅立,“蔑我皇德,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气,犹有十三,圣灵何辜,而当乏飨”[4]2132。即刘子业嗣立,狂悖不道,就算废昏立明,刘子勋兄弟辈还有十三个呢,什么时候轮得到湘东王刘彧了!檄文所到之处,郢州、荆州、雍州、徐州、江东五郡、益州、湘州、广州、梁州等普遍响应。“四方贡计皆归寻阳,朝廷所保,唯丹阳、淮南等数郡,其间(丹阳)诸县或应子勋”[6]4098,以此可见一斑。
对这个问题,朝野内外认知具有一致性。时任豫州刺史殷琰被军府僚佐挟持举兵响应刘子勋,明帝招蔡兴宗询问:“诸处未平,殷琰已复同逆;顷日人情云何?事当济不?”蔡兴宗答道:“逆之与顺,臣无以辨。今商旅断绝,米甚丰贱,四方云合,而人情更安。”明帝责怪殷琰“同逆”,对此蔡兴宗称“逆之与顺,臣无以辨”,很明显是回避推脱之词,无疑是委婉地承认了明帝立场的不正。胡三省注称“寻阳起兵,名正言顺”[6]4099,给蔡兴宗的回答作了很好的一个注脚。刘子勋称帝后,地方州镇纷纷响应拥戴,消息传到益州,时任益州刺史的萧惠开集合军府僚佐商议,他说:“湘东,太祖之昭;晋安,世祖之穆;其于当璧,并无不可。但景和虽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犹多。吾荷世祖之眷,当推奉九江。”[6]4096-4097萧惠开先就湘东王刘彧、晋安王刘子勋昭穆次序称“并无不可”,但他也说,刘子业虽然昏暴,“不任社稷”,但孝武帝儿子还有不少,“其次犹多”,潜台词是很明显了。再加上孝武帝对他有眷顾之恩,他选择站在刘子勋一边。随即派遣巴郡太守费欣寿率五千人东下支持刘子勋。跟徐州刺史薛安都一起响应刘子勋的太原太守清河傅灵越后来被擒,被明帝方大将刘缅面责叛逆,傅灵越不服气,反驳道:“九州唱义,岂独在我!”[6]4114“唱义”云云,很明显傅灵越认为支持刘子勋才是大义所在,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认知,而是九州人所共知的基本政治常识和判断,所以他压根不认可刘缅的指责。明帝即位的法统不足由上可知了。
当然,不可否认,明帝皇权的维系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军事上的胜利。在当时“普天同叛”[6]4098的形势下,明帝大胆起用出身低微甚至军户的将领,泰始二年(466)二月底,吴喜、任农夫等人凭借武勇先后收复义兴、晋陵、吴兴、吴郡、会稽五郡,稳定了东部大后方,随后又投入西线的平叛。八月底,建安王刘休仁所率张兴世、沈攸之、吴喜等部击败刘子勋主力,突入寻阳,刘子勋授首。至此,明帝的军事优势完全确立,但因其法统的先天不足,明帝在政治舆论上还有加强的必要。如寻阳平定后,明帝遣派两路使者招抚萧惠开,因水路招抚萧窦首私心欲独揽平蜀之功,激起萧惠开军事对峙,明帝收执萧窦首,萧惠开接受招抚。事后明帝责问萧惠开兴兵事,萧惠开大言:“臣唯知逆顺,不识天命。”[6]4128可见萧惠开认为自己在政治上站刘子勋一方是大义所在,并无不妥,至于明帝称自己承统为“天命”云云,萧惠开并不以为然。萧惠开依恃自己在益州的实力和声望影响对明帝有点有恃无恐,但从根本上来讲,他选择拥戴刘子勋符合当时的政治常识和政治道义,即便是明帝对此也无可奈何。所以即便明帝在军事上取得明显优势,但他在政治和社会舆论上还必须强化一下朝野民众中皇权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认知,由此他必须寻求佛教和僧众的支持和合作。
刘宋立国之初,刘裕就积极利用佛教为鼎革制造舆论和符瑞,如借冀州法称道人说嵩高灵神“江东有刘将军,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镇金一饼为信”的预言,派遣释慧义到嵩山求取,果然在一所寺庙石坛下掘得璧、金,携返京师[2]266。学者分析刘裕出身寒微,得不到门阀士族积极支持,而佛教在当时政治社会上影响很大,所以他不得不利用佛教和僧徒制造各种神异祥瑞来为自己代晋创造舆论攻势,借以凸显刘裕的天命所在,强化鼎革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文帝、孝武帝取得皇位之后,在与辅政大臣和宗室执政过程中为了加强皇权,也积极利用佛教和僧徒力量[8]。
孝武帝平定刘劭之乱,立即派遣使者迎请寿春东山寺的释僧导入京,止于中兴寺。“銮舆降跸,躬出候迎。(僧)导以孝建之初,三纲更始,感事怀昔,悲不自胜。帝亦哽咽良久,即敕于瓦官寺开讲《维摩》,帝亲临幸,公卿必集。”[2]281释僧导从武帝刘裕起就积极与朝廷合作,北伐中又搭救刘裕第二子刘义真,刘裕大为感念,“令子侄内外师焉”[2]281。就这种因缘关系来讲,释僧导对刘氏宗亲子弟扮演着某种家族长老的角色。孝武帝即位伊始,就迎请释僧导来建康,并安排他居住在中兴寺;两人见面之后,僧导“感事怀昔,悲不自胜”(刘劭构难,文帝被弑),孝武帝也“哽咽良久”,表现出很有人情味的一面。讲经之后,僧导嘱咐孝武帝“护法弘道,莫先帝王”[2]282。孝武帝在当时特定政治背景下迎请释僧导入京,除却他个人与刘氏宗室极富人情味的私谊外,更多的应该是要借重释僧导的声望和地位,来安定和抚慰朝野人心,为孝武帝的皇权助力加码和保驾护航。这充分说明元嘉以来佛教在国家政治层面所具备的特定意义和影响力,明帝即位之初的一些举措,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解读(4)据《高僧传》卷8《释僧柔传》记载:“齐太祖创业之始,及世祖袭图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义士。”南齐高祖萧道成创业和武帝萧赜袭位时“建立招提,傍求义士”,推溯而言,或是宋孝武帝、明帝以来的成例。这是否说明用创立特定寺院和精选僧望来彰显皇权的获取和确立已然成为惯例做法。。
关于这一点,即位若干年后,明帝对孝武帝一支还有强烈的竞争和攀比之心,可见明帝心底对法统问题始终耿耿于心,不能释怀。泰始七年,明帝舍城东清明门外湘东王旧宅建湘宫寺,从建筑到纲领选任、法会讲主等等,明帝极为用心,也无意中透露出着意压制孝武帝一系的政治意图。
据《南齐书》卷53《虞愿传》记载:“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费极奢侈。以孝武庄严刹七层,帝欲起十层,不可立,分为两刹,各五层。”新安太守巢尚之刚罢任回京,明帝对着他大为炫耀:“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原是湘东王府常侍,明帝即位后继续受到信任和重用,当时在场,听后大泼冷水:“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9]916尚书令袁粲在坐,闻之色变。综上可知,其一,湘宫寺是明帝“践祚”后,舍旧宅湘东王府邸而建;其二,湘宫寺修建规模极尽浩大奢华,动用大量财力物力,凸显强烈的政治攀比色彩。又据《高僧传》卷8《释弘充传》记载,释弘充博通经论,思解入微,受到太宰江夏王刘义恭的信重。曾在大明二年(458)受刘义恭资助注解刊布《新出首楞严经》,可见两人私谊甚笃[10]。“明帝践祚,起湘宫寺,请充为纲领。”[2]308-309明帝请释弘充担任湘宫寺纲领,或与江夏王刘义恭和释弘充之间的这种因缘交谊有关系。湘宫寺建造时间,上面只说“明帝践祚”,而《资治通鉴》称其系于泰始七年(472)十一月[6]4167。根据《南齐书》上下文,当时在场的官员还有尚书令袁粲,袁粲泰始七年五月从尚书右仆射迁尚书令[4]168,则事件可能发生在七年五月以后,《资治通鉴》称其系于七年十一月,或有可据(5)元释觉岸编《释氏稽古略》卷2言“泰始四年(469)帝造湘宫寺成”,不知何据,录此备说。见觉岸编《释氏稽古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792页。。湘宫寺在建康城东最南面的清明门外附近,清明门三道,正对“湘宫巷门”,东出清溪港桥[5]180。四通八达,地处冲要[9]790。
除少数皇家寺院外,南朝建康佛寺比较少兴建佛塔,而普遍以木刹柱代替[11]119-121。刹原是顶部有覆钵状柱头(后多以金为之)的高杆,加以悬旛装饰,(钵部)用以安放佛舍利骨[12]。当时佛塔、刹柱规模,基本上都是三层、五层,只有极少数皇家寺院达到七层[11]119。孝武帝母路太后在宣阳门外大社西药园造庄严寺[5]225,树刹七层,属天家独有,既给国家(孝武帝)祈福,同时也昭显了皇家威仪和功德。明帝想要在湘宫寺立十层刹柱,就是要盖过孝武帝一支风头,有明显的政治竞争和攀比之意。可见即便这个时候,他对孝武帝及其一脉,心底还有着深深的不甘和不满。估计当时建筑技术水平不够,明帝意图无法实现,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立了两个五层刹柱。
除此之外,明帝还将彭城寺释僧亮所造丈六金像以及文帝后来配造的金箔圆光一并强行移到了湘宫寺[2]485。同时礼请当时僧望天保寺释法瑗、何园寺释慧隆,在湘宫寺开讲。“湘宫新成,大开讲肆,妙选英僧,敕请瑗充当法主”[2]313,释法瑗在天保寺时与明帝舅兄琅琊王景文有旧交,湘宫寺新成开讲,释法瑗被请为法主,或许是王景文的推荐。又有何园寺释慧隆,是当时佛教界一时之选,“明帝请于湘宫寺开讲《成实》,负帙问道,八百余人”[2]327。如此种种,前后不可谓不用心。除佛教功德之外,湘宫寺的创立,凸显湘宫寺、明帝一体,湘宫寺既是明帝皇权象征,也是其合法性展示。这与即位之初兴皇寺的创立具有前后一致的逻辑,也是明帝寻求和确立正统性的所在,可见法统性问题(与孝武帝一系争胜)是明帝心底不能释怀的心结。
当然,除了上述鲜明的政治意图外,因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佛教氛围浓厚的环境下,明帝的举措和行为也不排除个人层面的信仰因素。“湘东王彧龆龀之年眠好惊魇,(文帝)敕从净贤尼受三自归,悸寐即愈。”[3]195长大后从释僧谨受五戒,明帝本人是佛教徒毋庸讳言。但就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来讲,明帝佛教举措政治性的诉求是主要的,但也不乏个人信仰方面的因素(候选人具有太过明显的私人情谊等)。
总而言之,佛教在当时社会的广泛传播和兴盛发展,使得佛教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统治者出于各种考虑,加大对佛教的利用和合作,已形成惯式和传统。明帝即位之始,就借“为义嘉行道”的罪名撤了释智斌僧正的职位,任用自己五戒师释僧谨为僧正,优礼崇重,有异于常;然后在建阳门外创立兴皇寺,敕令自己早相结识的释道猛为纲领,优礼待遇与释僧谨同;对与孝武帝关系密切的庄严寺僧众予以“简阅”,选定释昙斌和释慧亮相继为讲论法主;又在全国范围内广肆搜求,远至岭南、湘州,近到浙东(山阴),征请有道高僧入京居止传法等等,就是利用释僧谨、释道猛等人在佛教界的威望和影响,既树立自己政治上的权威,同时寻求佛教和僧众对皇权的支持和合作。这些举措的施行具有明显的急迫性和鲜明的政治诉求,最主要原因是明帝皇权的获取法统性不足。前废帝刘子业凶狂无道,使得朝野内外笼罩在政治恐怖氛围之中,为了生存,时为湘东王的明帝和府中官员联合内外,仓促之中发动宫廷政变,弑杀刘子业,而明帝在这种混乱危急之中被拥立为帝。明帝为文帝之子(第十一子),孝武帝之弟,刘子业之叔,因排行和统绪问题,政治地位和声望不足,号召力有限。与此同时,刘子业弟弟晋安王刘子勋以寻阳为根据地建立义嘉政权,地方藩镇纷纷起而响应,建康部分官员外逃投奔不绝,构成对明帝的严峻政治军事对峙。在调兵遣将分兵讨伐义嘉叛乱的同时,明帝也积极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佛教资源,借用佛教和僧众力量延伸和昭示皇权权威和影响,拉拢佛教僧人,借助佛教控制和引导社会舆论,强化自己皇权的合法性和正统地位。这些举措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化特色,符合历史发展逻辑和合理性,也因明帝自身身份地位和情势的特殊性,凸显出明帝极具个人化特点的政治诉求。这是本文所要突出和强调的问题所在。
OntheImperialPowerofEmperorMingofLiuSongDynastyandtheInfluenceofBuddhism
XU Fen1, ZOU Tongshu2
(School of Philosophy, History, and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his reign, Emperor Ming of Liu Song Dynasty appointed his own five precepts teacher, Shih Sin-Jin, as the monk leader, and gave him extraordinary treatment. He established the Xinghuang Temple, chose a senior monk, Shih Dao-Meng, with whom he had an old friendship, to be the platform speaker, and gave him the treatment of the monk leader, with excellent courtesy. He invited senior monks and great masters to the capital to preach the Dharma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spected the monks of Emperor Xiaowu’s Zhuangyan Temple, and redefined the Dharma master of the Dharma assembly, et cetera. Some of these initiatives were obviously urgent and had distinct political demands. Emperor Ming intended to use the socio-political influence of Buddhism and monks to extend and expand the authority of imperial power in the Buddhist political order, to shape and strengthen the legitimacy of imperial power and his own position,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lack of legitimacy of his succession. The former abolitionist Emperor Liu Ziye was fierce and lawless, and the dynasty was shrouded in a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terror, so Emperor Ming was forced to stage a palace coup and was hastily installed as emperor. Because of the lack of legitimacy, he was challenged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by Liu Zixun, the king of Jin’an, Liu Ziye’s younger brother. Although he eventually won a complete military victory, Emperor Ming had to actively seek the cooperation of Buddhism and monk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his legitimacy in terms of jurisprudence and public opinion, which w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various Buddhist measures he took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reign.
Keywords:Emperor Ming of Liu Song Dynasty; imperial power; Buddhism; Yijia Rebellion; Xinghuang Temple; Xianggong Te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