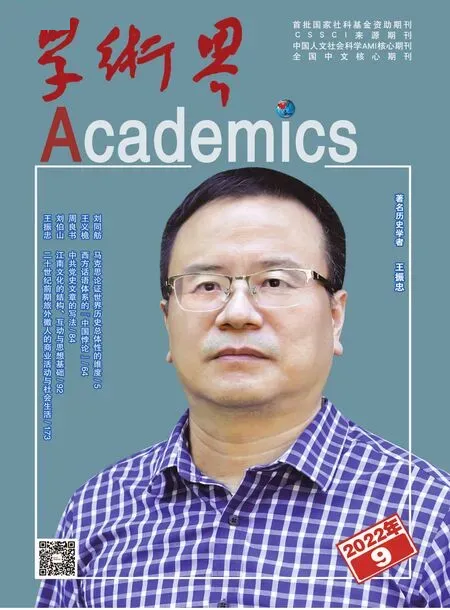国家认同建构:从“五族共和”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王江成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从民族或国民认同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重要目标看,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议题。对多民族国家而言,对各民族的双(多)重身份认同,以及不同类型或性质的民族的身份认同进行整合,即认同整合(identity integration),〔1〕是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内容。简单而言,民族的认同整合至少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在保持各民族身份的基础上,经由国家民族的规约,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二是为各民族建立统一的国家民族身份,整合起国家民族认同,进而实现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合。归结起来,要经由国家民族认同,推动实现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已有研究鲜有直接论述民族研究领域的整合议题与认同建构的关系,较多讨论民族整合、族际整合、族际政治整合本身,涉及协调族际关系、协调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等,强调的是多民族国家的建构、统一,民族关系和谐等。事实上,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理论探讨中的上述几类“整合”都蕴含着建构国家认同的目标,而认同整合进一步明晰了“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关系,把对认同的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对应起来。认同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表述”,通过对各民族多重认同的整合本身是为了实现国家认同,而这也正是国家认同建构的内涵。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以中国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为研究对象,以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不断依次出现的民族观念(五族共和、国共两党的民族观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实践所蕴含的“认同整合”为观察视角,分析中国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演变逻辑,重点讨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蕴含的整合特征与认同建构逻辑,并从新时代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实际出发,思考和展望国家认同建构的认同整合路径。
一、“五族共和”与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
“五族共和”思想是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政治力量维护民族统一和疆域稳固的主流思考。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当天发表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正式提出“五族共和”思想。从“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到“五族共和”的真正达成并非一蹴而就。诚如有学者所言,“‘汉、满、蒙、回、藏’咸于共和,才是‘五族共和’的完整含义”。〔3〕而各族对“共和”(相对于君主)的赞同或默认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南北议和”〔4〕及《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的提出,《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等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这一系列事件和相关主体的互动中,“五族”〔5〕终于达成了对“民主共和政体”的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民国的合法性,并在形式上搭建起了五族认同的新国家。关于“五族共和”达成的历史政治过程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意在从“五族共和”本身蕴含的民族观念及认同整合理念出发,分析“五族共和”对于国家认同建构的影响。
今天来看,“五族共和”蕴含着“中华‘各族’”的观念,呈现出“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二重面相。“五族共和”一面强调五族之统一,通过融合甚至同化建构一个“大民族”或“大国民”;另一面承认国内各族的地位,更多的“族类群体”开始自觉。即一面强调为各民族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民族身份或国民身份;另一面试图通过承认各民族身份来整合起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一)“国家民族身份建构”与国家认同建构的“融合同化”进路
“五族共和”的提出伴随着对实现“国家之统一”“民族之统一”的追求,它具有明显的“国家民族”取向。“五族共和”思想的这种“国家民族”取向在“南北议和”之后,逐步演变出“五族同化”“民族大同”“大民族”“大国民”,以及具有国家民族内涵的“中华民族”等观念。在建构统一的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整合观念下,国家认同建构被理解为融合国内诸族为一“大民族”,或是以某一民族为主,同化其他各族,并由此开启了国家认同建构的“融合同化”之路。
从革命派和南京临时政府的角度看,孙中山对“五族共和”的宣传大体集中在民国元年。关于孙中山与“五族共和”的关系,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其一,孙中山在宣扬‘五族共和’时更多指向满、蒙等少数民族,认为其用意在于安抚少数民族。并且,他在关注‘五族’问题时多使用‘五族一家’的提法;其二,孙中山在发表“五族共和”的相关演说后不久,即在同盟会内部电文和《国民党宣言》中明确要求‘励行种族同化’。可见,孙中山内心并未认同‘五族’的划分;等等。”〔6〕而更重要的是,“五族一家”〔7〕“种族同化”〔8〕的提法反映了孙中山民族观念中的“融合同化”倾向。
革命派内部对促进“五族同化”“民族大同”也孜孜以求。辛亥革命爆发不久,“邓实、黄节、胡朴庵等国粹派(原属革命派一支,偏重于‘排满’)人物在上海创办《民国报》,宣布所谓‘六大主义’,其中之一便为:以汉族主治,同化满、蒙、回、藏,合五大民族而为一大国民。”〔9〕1912年3月19日,黄兴、刘揆一等革命党领袖发起成立包括满人恒钧等参加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这一改称标志着一种超越五族的整体性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在革命党人的意识中出现)。特别强调五族“意识之感通”的紧迫性,主张和推动“民族同化”;〔10〕革命党人陈其美(沪军都督)等人更是倡议发起成立“融洽汉满禁书会”,一律禁止鼓吹“排满”和有违“五族共和”的书籍;新疆伊犁革命党组织则发起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1912年7月至8月,《中国同盟会杂志》连载多篇文章宣扬“民族同化”。〔11〕
北洋政府掌权后,更多从“清帝逊位”的角度来宣扬自己对于缔造共和的正统性,并弱化“革命”的作用。为此,北洋政府标榜本集团在继承清朝统治权、达成南北统一、五族共和当中的重要功绩。在积极宣传“五族共和”的过程中,袁世凯并非强调“五族”的划分,而更多也是主张“五族一家”“五族大同”。并由此引申出“五族”融合为一个“大民族”的思想,同时,以“中华民族”来指称这个“大民族”,〔12〕试图通过国族整合来构建一个以“大民族”或“大国民”为基础的民族(国民)国家。
具体来看,在《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回复外蒙独立集团1912年3月12日来电的电文)中,袁世凯强调“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13〕这应该是北洋政府当政后,首次使用具有“大民族”(包括国内诸族)内涵的“中华民族”概念。同时,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把中华“各族”的走向引导到“融合”“同化”“大同”的道路上。1912年4月13日,北洋政府颁布《豁除五大民族婚姻禁令文》,〔14〕提出五族一家、五族通婚的“融合”倡议;并且,在当时,五族融合同化的声音还见于地方。1912年年初,上海的地方官员就曾发布《化除种族见解之文告》,禁止使用“大汉”字样,以示民国“大同主义”。
同时,具有官方背景的政治团体也纷纷倡导五族融合同化。1912年4月10日,以内务总长赵秉钧为总理的“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该会的宗旨便是“化除‘五族’畛域,谋一致之进行”,主张“融化五族,成一坚固之国家……”;〔15〕1912年5月12日,“五族国民合进会”在北京成立。总统府边事顾问姚锡光为会长,赵秉钧(汉人)、志钧(满人)、熙凌阿(蒙人)、王宽(回人)、萨伦(藏人)为副会长。该会在《申报》上发表的 “会启”分析了五族“同源共祖”的历史。强调民国建立后,正好“……举汉、满、蒙、回、藏五族国民合一炉以治之,成为一大民族”。将来五族“合进”收效之日,也就是“汉、满、蒙、回、藏”之名词“消弭而浑化”之时,故“今日所称为‘五族国民’者,犹不免为赘语”云云。〔16〕该会启明确提出了五族融合、同化、归一的大势。由于“五族国民合进会”吸纳了当时社会上重要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17〕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其内容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洋政府的态度。
在官方话语的影响下,当时出版的教材、图书也在传播和输送“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观念。1912年秋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高等小学用的历史课教材——《共和国教科书 新历史》,其中,从“民国统一”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的民族构成及其族际关系的整体性。〔18〕
实际上,主张各族融合同化已经成为民国初创阶段社会政治力量的共识。为此,社会政治力量纷纷成立相应的政治团体,并不约而同地指向“五族同化”,且有意以“地方”“区域”来淡化“民族”“文化”“血缘”的区分。就连梁启超的追随者吴贯因也在1913年撰写了《五族同化论》一文,“逐一论析五族的混合性质,说明各族间血统等互相渗透的历史,进而主张五族的最终同化。”〔19〕北洋政府则融汇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观点,在政治上强调共和平等,在文化上强调五族大同,最大限度地凝合了社会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革命派与立宪派、袁世凯北洋政府在民族观念与政治立场上的分歧,他们在这一时期对如何实现各族的“融合同化”产生了不同看法,并主要存在“以汉族为主同化其他各族”与“融合国内诸族”两种“整合”形式,两种形式表现为“A+B+C+D+E=A”与“A+B+C+D+E=F”的区别。但可以明确的是,两种“整合”类型都试图构建一个“大民族”(中华民族)或“大国民”,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大民族认同的国家。
(二)“承认各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平等共治”进路
在强调“国家之统一”“民族之统一”的“国家民族”进程中,“五族共和”思想常常是以承认“各族身份”“国民平等”为前提展开论述并得到认可的。这种承认各族身份地位的认同整合谋求以有限的“平等共治”来换取各族特别是他们中的上层对共和民国的认同。
有趣的是,革命派在推动“五族平等共治”过程中的贡献值得关注。正如上文所述,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重要领袖刘揆一就在《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中提出了“五族平等共和”的成熟思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公布)第5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20〕同年9月,孙中山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欢迎会和在张家界各界欢迎会等演说中,进一步宣扬“各族平等”“国民平等”的共和思想,盛赞“今日此会,聚蒙、藏同胞于一堂,实为亘古以来未有之盛举……凡我蒙、藏同胞,首即当知共和国家异于专制国家之要点,……共和国家政府为公仆,无贵族、平民之阶级,无主国、藩属之制度”。〔21〕
北洋政府坚持和延续了“五族共和”思想,并承认各族平等。1912年4月22日,在《裁撤藩属名称文》中,袁世凯明确提出了各族平等或国民平等的思想,称“……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民国政府不设立专门处理藩务的部门,蒙、回、藏诸部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地方政治,均属内务行政范围。……”〔22〕1913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4条、1914年5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第4条均规定了体现“各族平等”或“国民平等”观念的内容。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官方所强调的“平等”隐含着消除歧视的意味。
“各族平等”观念在北洋政府时期得到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的实践。〔23〕首先,重视优待少数民族及他们中的上层。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以大总统的名义“先后颁布了《劝谕蒙藏令》《蒙藏主权声明》《劝谕汉、满、蒙、回、藏联姻令》《蒙古待遇条例》《恢复达赖喇嘛号令》《待遇西藏条例》等优待汉族以外民族的政令、声明和条例。”〔24〕从边疆危机凸显的现实看,在少数民族社会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的长期作用下,是否优待少数民族的上层直接影响到这些民族上层的“民族主义”抉择,进而关系到少数民族社会的政治走向。因此,当具有传统政治思维的袁世凯当政后,自然试图在“五族平等共和”的框架下,以形式上的“共治”重构中央与地方(疆部)的政治关系。
其次,设立“民族事务治理机构”〔25〕专营各族事务。1912年5月21日,“袁世凯在内务部下设负责处理蒙、藏等地少数民族事务的‘蒙藏事务处’,后几经更名、申格,最后发展为蒙藏院”。〔26〕而除了设立专门的“民族事务治理机构”之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还特设了一些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临时机构或特使。比如,蒙疆经略使、蒙番宣慰使、西北筹边使等。这些机构的设立在形式上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利。
最后,推动各族的政治参与,并主要体现在参、众两院中“各族”议员的选举、议席的分配,以及参与国家事务等方面。与此相关,民国初期公布了一些具体的组织办法和条例条令,如《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蒙古西藏青海众议院议员选举施行令》《参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西藏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施行法》等。正是通过上述及其他诸多选举规定的实践,蒙古、西藏、青海地方,以及蒙族、藏族都有名额及代表参与国家政务,表达政治诉求,一些少数民族的政治精英(贡桑诺尔布、马福祥、马麟等)还充任国家和政府要职。并且,袁世凯和北洋政府还很注重听取少数民族上层的建议。在看到驻边官员多有措施不当,使“少数民族地方”心生怨恨,进而影响中央政府权威的问题后,袁世凯特批“王公喇嘛组织‘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希望他们在中央和地方重大事宜上能够各抒己见,毫不保留”。〔27〕
“各族平等”观念的传播和实践进一步拓宽了“各族”的范围,催生了“各族”意识,也提升了人们对“各族”的认知。相对于中华“各族”的多样性,“五族”只是一个泛称,“各族”并不局限于“五族”。“五族共和”对于“各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遥远的新疆,伊犁起义的领导者并没有采取种族革命的策略,而是提倡“保国何分种族,举动最重文明。汉、蒙、回、缠、哈,均应一视同仁。平日私仇私利,此时概勿存心。同造共和幸福,众志可以成城。”〔28〕在西南边陲,1911年11月3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发布了《布告全省同胞文》,声称“各省义军旨在废除专制政体,建造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29〕提出了“七族共和”的思想。
这一时期的社会团体、出版物也在传播“各族平等”观念。上文提到的“五族国民合进会”不仅提出各族融合同化的目标,也强调聚各族智慧共谋合进的过程,从这点看,它还是一个含有五族平等联合性质的组织。在该会的“简章”中,特别提到在“我五族国民以外,西北尚有哈萨克一族,西南尚有苗瑶各族,俟求得其重要人员,随时延入本会”。〔30〕1912年10月,潘武编辑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本国之部》中对“民族”进行了解释,写道:“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位,其他各族更起迭仆,与汉族互有关系者,曰苗族,曰通古斯族,曰蒙古族,曰土耳其族,曰西藏族”。〔31〕
民国政府及其地方势力对国内诸族的承认和关注,从政治和文化上维护了“五域之地”的完整和族际关系的稳定,为国家认同的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
应该注意的是,“五族共和”思想蕴含的“民族之统一”“国家之统一”的目标与“各族平等”“国民平等”的价值及相关实践是相互推进、互为条件的。为实现“统一”或“一体”目标而主张的“融合同化”进程常常是以承认各族在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平等地位为前提的;而优待少数民族上层、设立专营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推动少数民族参与政治等,则是以改善中央与边疆地方的政治关系、经营边疆政治行政事务、推动少数民族融入国家等为根本目标的。从认同整合的角度看,“五族共和”试图在国家民族身份建构与承认国内诸族之间找到平衡,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民族统一和各族平等的整合。但是,“五族共和”所蕴含的民族观念的二重性在客观上导致了中国现代民族建构的结构性和国家认同建构的复杂性。指出“五族共和”在民族观念上的二重性及其影响并非是要假设历史,而是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民族结构的由来,并从历史中找寻经验,把握好今天实然的民族状况和国家认同建构的应然逻辑。
二、国共两党民族观念之争与国家认同建构两条进路的分野
国家民族身份建构与承认各民族在“大、小民族主义”〔32〕的牵引下常常此消彼长、此强彼弱,在民国政治社会失序及其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野。国民党在国族主义的认同整合取向下,淡化各民族观念,甚至否认各民族的存在,把对国家民族的建构推向了国族同化的境地;共产党则从推动各民族解放的实际出发,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自治。在此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角逐中,这种民族观念上的分歧及认同建构路径的分殊进一步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并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加剧而更加清晰。而国共两党的民族观念之争加剧了国家认同建构两条进路的张力。
分析国共两党有关认同整合的理念或国家认同构建路径的分野还需追溯到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以1919年为界,孙中山的民族观念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五族同化论向民族(国族)同化论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在孙中山阐述大中华民族主义思想的进程中,苏俄(联)和共产国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认识到中国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勾结,并造成中国四分五裂且处于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的尴尬处境后,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并在已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自决”中加入了反对本国封建军阀的内容。这样一来,孙中山民族自决的主张便由中华民族的自决扩展到国内各民族的自决,而这也成为国共合作达成的重要政治基础。1924年,由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民族主义的两个含义: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主张反帝反侵略;一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正式提出了“少数民族”概念。〔33〕不可否认,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达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共两党的政党属性及其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两党民族与国家观念分殊的某种必然性。即使是在国共两党共同参与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两党对国家结构形式仍存在分歧(自由统一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国家),其核心是如何看待国内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或者说是要以何种认同整合的方式来建构国家及国家认同。
(一)国民党的国族建构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国族同化”进路
国民党方面,在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和国民党关于民族自决和民族主义的重心仍是“国族”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独立和自由。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公布的三天后,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连续演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这一系列的演讲是孙中山晚年国族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因为“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完全是一个民族。”〔34〕并认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不能及于国族……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组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主义来救中国”。〔35〕又因为“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盘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所以,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而这也被认为是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支论”的源头)。〔36〕
大体上看,之后蒋介石片面地坚持孙中山的“国族主义”道路,力行国族同化,并把其发挥到极致(即否认“各民族”、中华民族“宗支论”等)。而这样一条试图建构均质化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整合道路因国民党自身的问题而走向失败,不仅没有巩固好国家认同,反而失去了少数民族的支持,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
(二)共产党推动各民族解放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各民族平等自治”进路
共产党方面,1922年7月,在党的二大上就明确提出“各民族”自治和“自由联邦制”的思想。1923年1月,李大钊在论述“平民政治”时专门解释了“联邦主义”。他讲道:“譬如中国的国旗,一色分裂为五色,固然可以说他是分裂,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了一个新组织,也可以说是联合。……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37〕针对国民党内部一部分党员关于“共产派主张民族自决,首先就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的误会、攻击,1924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就认为“民族主义有两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民族,这可称作矛盾的民族主义;一种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作平等的民族主义”。〔38〕
共产党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观,从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关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强调被压迫民族的自决(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自决出来,并与无产阶级联合)。根据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积极争取联合受到本国封建军阀、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压迫的“国内各民族”,回应各民族的诉求,坚持国内各民族的自决。如果从国共合作破裂之后的民族政治走向来看,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阐述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面,即“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等。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赢得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增强了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为日后成立各族人民拥护的新中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囿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没有对国共两党民族观念及认同整合的具体实践作全面的展开。而重要的是,国共两党认同整合路径的分野使得国家认同建构的进路进一步分立。国共两党把民族观念及认同整合上的分歧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而使“五族共和”蕴含的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渐行渐远。即国民党强调国族同化,谋求以强制压迫的手段建构起统一的国家民族身份;共产党则尝试从各民族的实际出发,反对民族压迫和歧视,试图在承认和保障各民族平等自治的基础上赢得各民族的认同。历史已经证明,国民党推行的国族同化政策滑向了“大汉族主义”的泥沼,遭到少数民族的反对,反而刺激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情绪;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十分灵活,一套围绕少数民族形成的民族观念在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进程中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果,实现了预期的治理目标,推动了少数民族的发展,赢得了少数民族的认同,但也使“中华民族”在一段时间里被虚置,“中华民族”建设的任务悬而未决,〔39〕国家认同的主体内部仍然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因此,割裂地建构国家民族身份,或是一味地强调各民族的权利都可能使国家认同建构陷入困境。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认同建构两条进路的协调统一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在2021年8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40〕“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具有更强的历史和现实包容性、建构性,是党的民族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从“共同体”概念看,滕尼斯基于传统的自然社会与现代的人为社会的区别最早提出了用于描述自然社区这样的基于血缘、文化等纽带而联结在一起的小社会;马克思提出了共同体(社会)演变的三个阶段,并从“自由人的联合体”出发来定义真正的共同体,即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的社会。由此可知,共同体可以用来描述一个小的社区,或是一个大的社会,或是社会的某些领域,或是不同阶段的社会。比如,今天广泛讨论的社区(会)治理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它们基于共同的血缘、地缘、文化、历史、政治、价值、目标、归属、情感、利益等要素联结在一起,“共同体”是一个比较宽泛和包容的概念。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以从多种要素出发来理解和定义它。从认同的角度看,与先前孤立地强调国家民族身份建构(国族同化)或一味地承认和保障各民族权益相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突出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地位,也不否认共同体建构的复杂性和现实性。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在国家民族与各民族此消彼长之间,或者说在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的纠葛之间进行了更深刻的阐释,它强调以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来规定和表述中国民族的多样性,而不是继续以各民族的多样性来描述中华民族。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述试图规避中国民族结构的内在张力,强调有机统一、目标一致。
基于“共同体”的新思维,认同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具有了新的内涵和要求: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嵌合互构”〔41〕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出认同整合的两重内涵,既建构统一的国家民族身份,实现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合,又要整合各民族的多重认同,协调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蕴含的两重认同整合实际上涉及到国家认同建构的两种进路及其关系,即要实现经由国家民族和经由各民族建立起国家认同的进路的协调统一。在这个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决定性作用,要以此为纽带破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性因素。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嵌合互构”与民族认同整合的整体推进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交织嵌合与国家民族认同的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以及各民族之间交织嵌合的关系体。“交织嵌合”是指一种超结构性的互嵌(嵌入)与结合,是对两类民族间结构性张力的破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交织嵌合关系超越了“五族共和”所蕴含的“国家民族与国内诸族”的条件依存关系,及其之后国族同化或各民族平等之间的对立发展关系,而表现出一种共同体的整体性意识或共同的国家民族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交织嵌合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及两个方面,即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交织、各民族之间的交织,以及她们之间的政治嵌合与文化嵌合。首先,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以“中华各族”的形式嵌合在一起,即各民族嵌入中华民族之中,同时,结合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在政治上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具有固定明确的意涵,体现为国家民族与国内民族之间的统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42〕在文化上,“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43〕其次,各民族之间在政治上享有广泛的平等的自由权利,特别是少数民族在民族区域自治框架内有发展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如同大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团结互助;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的居住空间(文化土壤)、认同符号、传统节日、语言文字、流行文化等的融合程度和相互间的信任程度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整体性进一步加强。
第二,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规约互构与两类民族认同的整合。中华民族建构与各民族建构是两类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族体建构,各民族的发展丰富了中国民族建构的内容,各民族建构与中华民族建构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建构的二重结构。中华民族建构与各民族建构的过程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相互纠缠并相互影响,〔44〕中华民族的建构规约着各民族的认同边界,各民族的建构以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为原则。从认同整合的目标出发,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互为条件,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在通过强化中华民族认同实现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二)共同体建构与国家认同建构两条进路的协调统一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近代各政党、各阶级等社会政治力量对共同体内部的国家民族和各民族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一些社会政治力量强调“国内诸族”“各民族”自决而批评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的单一民族论、国族同化论;反之,强调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则很少提及“各民族”。这就使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国家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因近代社会政治力量的不同主张及力量对比而出现相互牵制的局面。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虽在现代国家建设层面强调国族主义,但终因当时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特别是共产党对“各民族”的关注而不得不在国民政府的宪制变迁中承认了中华民国各民族的地位。同理,一贯主张“各民族自决”的共产党,在中华民族整体自觉的背景下,也强调了中华各族的统一性。应该承认的是,在国家民族与各民族相互纠缠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建构始终无法融化内部的各民族,而各民族的建构也没有超越中华民族的范畴,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建构的整体特点。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政治逻辑出发,要辩证地处理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的关系,推动两条进路实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纽带的协调统一。第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阶段,特别重视处理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的关系,并在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观念中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今天,在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既要看到民族观念及认同整合追求政治一体的目标及努力,用好“中华民族”这一宝贵的历史政治遗产,有效地构建起整体性的中华文化,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提升中华民族认同,巩固国家认同,也要关注到各民族的发展实际,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联系、近代演变及现实情况,学会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目标中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螺旋式前进,维护好国家认同。第二,“五族共和”思想开启的“国家民族”与“国内诸族”观念,以及引发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路的张力应能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进而得到消解。诚然,新时代的民族工作已经进一步明确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但在实践中尚未真正建构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和政策,仅靠加强民族团结的“各民族进路”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国家民族进路”上下功夫,构建国家民族机制、国民化机制等。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走向深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性始终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法律层面、宣传教育层面等进行思考和推进。
注释:
〔1〕“认同整合”作为认同研究领域的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已经被广泛用于心理、文化、性别、民族等领域的研究中,本文所讨论的认同整合主要是指对民族的多重身份认同的整合,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
〔2〕〔8〕〔21〕《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96、425-428页。
〔3〕常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95页。
〔4〕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在各方政治力量的斗争博弈之下,清政府被迫派出袁世凯同南方革命军议和,最终以《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而得以实现,并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妥协,史称“南北议和”。
〔5〕这里的“五族”并非今天意义上的五个民族,而是较为笼统和宽泛的五大族类群体,这一时期,“五族”的说法具有较强的政治象征性,表示新生民国对国内诸族的承认,意在使各族认同并参与新生民国。从这种层面看,“五族共和”不是简单的民族观念,更是建立民国的政体设计,其重点不在有几个民族,而是共和。
〔6〕郑信哲、周竞红主编:《民族主义思潮与国族建构——清末民初中国多民族互动及其影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9页。
〔7〕在1912年2月18日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布告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公告中,孙中山指出:“今中华民国已完全统一矣。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以和衷共济……因此敢告我国民,务当消融意见蠲除畛域;以营私为无利,以公益为当谋,增祖国之荣光,造后民之幸福。”而“五族一家”的提法具有长幼有序的文化倾向。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5页。
〔9〕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11页。
〔10〕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7页。
〔11〕〔17〕〔31〕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9、105、90-91页。
〔12〕袁世凯较早使用了具有“大民族”内涵的“中华民族”概念。“法国汉学家巴斯蒂就认为袁世凯率先用‘中华民族’的名称来涵盖(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参见法国汉学家巴斯蒂在2001年10月给“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的民族国家》,后该论文收入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51-974页。
〔13〕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25页。
〔14〕《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二,上海:新中国图书局,1931年,第13页。
〔15〕〔30〕刘苏选编:《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章程》,《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1期。
〔16〕《姚锡光等发起五族国民合进会启》,《申报》1912年6月11日。
〔18〕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共和国教科书 新历史》(高等小学用第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
〔19〕吴贯因:《五族同化论》,《庸言》1913年第1卷。
〔20〕《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11日。
〔22〕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346页。
〔23〕这一时期“各族平等”的实践是有限的、不广泛的。一方面,广大少数民族没有真正体会到政治平等,他们受到多重压迫,“各族平等”在一定意义上主要针对汉族以外民族的上层,“五族共和”被演绎为“袁世凯等军阀集团与汉族以外民族的上层集团的共和”;另一方面,各种优待条件,议员名额分配更多倾向于未设行省的蒙藏地方及蒙古族和藏族。“回部”及内地回族并没有获得专额议员。内地省份的议员也少于蒙、藏地方。而这种有限的平等、不广泛的平等也激发了“受到不公正待遇”之民族的政治参与意识。特别是“五族”中的“回”。这里的“回”实际上是一个泛称,包括新疆“回部”(即缠回)和内地回回(即回族自称)。
〔24〕常安:《清末民初宪政世界中的“五族共和”》,《北大法律评论》2010年第2期。
〔25〕除了重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之外,“民族事务治理机构”和特设机构的设立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一是推进边疆与内地的政治和行政一体化;二是处理边疆事宜,客观上增进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关注和认知。相关机构的设立为加强“少数民族地方”同中央政府的联系搭建了官方平台,特别是为“少数民族上层”同中央政府保持积极沟通发挥了一定作用,因而北洋历届政府均设有这一机构。同时,需要明确,北洋政府时期设立的“民族事务治理机构”与传统的“理藩部”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具有现代民族(国民)国家官僚机构的性质。
〔26〕邓亦武:《1912—1916年北京政府的民族政策》,《绥化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
〔27〕《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30日。
〔28〕《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0页。
〔29〕《布告全省同胞文》,《民立报》1911年12月8日。
〔32〕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38-3号刊登《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主张在“小民族主义”之外,实行“大民族主义”,提出“大、小民族主义”学说。小民族主义为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认为,只有以汉族为中心吸收满族,合汉、满、蒙、回、苗、藏为一大民族,才能实现大民族主义的目的。梁启超更多是把汉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小民族主义”,而实际上,汉族之外的一些群体也存在从本民族出发的意识和情绪,本文把各族的这种意识和情绪统一概括为“小民族主义”,与其相对的是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
〔3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原文中写道:“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摧毁无余,则国内诸民族宜可平等之结合,……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7-118页。
〔34〕〔35〕〔36〕《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4-185、189、237-238页。
〔37〕〔38〕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6、60页。
〔39〕周平:《“中华民族”建设: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4期。
〔40〕《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
〔41〕民族研究领域“嵌合互构”的表述最早由云南大学民族政治学博士刘春呈提出,此处借用,笔者作了进一步思考,并用来描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关系结构,在此表示感谢。“嵌合”是对物理的机械嵌入的深化,是对结构性嵌入的超越,强调实现嵌入基础上的更深层次交往交流交融,它是进一步破解结构性嵌入的一种目标机制。
〔42〕《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
〔4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09页。
〔44〕周平教授指出,“在中国特殊的‘民族’生态及结构中,事实上出现了中华民族构建与少数民族构建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极富特色的二重性民族构建过程及民族构建的双重变奏。”参见周平:《中国民族构建的二重结构》,《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