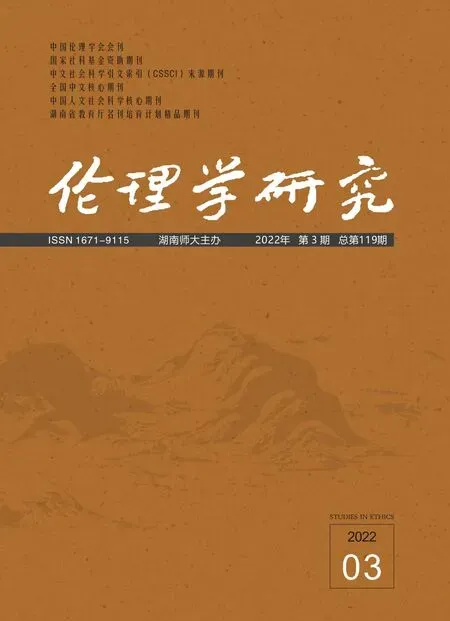西方哲学中的谎言悬案及其道德判决
冯书生
如果将日常语词划分为正向评价和负向评价两个方面,那么在不设置特定语境的情况下,“谎言”绝对会被列为负向评价词汇。不要说谎、做人要真诚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道德教诲。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谎吗?关于不要说谎的自信也绝对会受到沉重的打击。为了缓解谎言造成的内在紧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使用“善意的”或者“高贵的”等表达美好的词汇进行修饰。但是求真才是人类的内在冲动,谎言再有用也无法自证清白。本文的目的便是要考察西方哲学中关于谎言悬案的经典道德判决,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在充满谎言的世界中如何抵御虚假生存。
一、“谎言何以高贵”
西方哲学中关于谎言悬案的第一次道德判决是由柏拉图提供的。在《理想国》中,有三次涉及谎言。第一次是在讨论欠债还债是否正义时提出的。“欠债还债即为正义”是对话中比较富有的克法洛斯的正义观。苏格拉底给出的反驳是把武器还给已经变疯的朋友,甚至告知其真实情况都是不正义的。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疯子,也就意味着面对疯子,头脑清醒的人可以甚至应该说谎以确保安全。第二次提到谎言则是讨论如何用讲故事来教育护卫者。苏格拉底认为首先需要审查故事的编者,拒绝丑恶的假故事。那么,何种故事是丑恶的假故事?在苏格拉底看来,以赫西俄德和荷马为代表的诗人所讲的那些故事就是假故事。因为他们把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没有描绘出神与英雄的真正本性。苏格拉底主张神是尽善尽美的,本质上不会作恶,也不会撒谎。而且哪怕赫西俄德和荷马的描述是真的,神真的在作恶,也不能随便讲给年轻人听。对护卫者讲故事的时候,要做到“尽量以假乱真”,原因是“我们不知道古代事情的真相,要利用假的传说达到训导的目的”[1](80)。
如果说对疯子说谎,尚可符合人们的普遍认知,那么利用谎言进行教育就显得不那么理所当然了。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一方面苏格拉底批评诗人们说谎,另一方面自己又主张利用说谎来教育护卫者。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自己说谎会消解批评别人说谎的效力,批评别人说谎会否定自己说谎的合法性,如若无理由地坚持就会立刻导向赤裸裸的权力意志。柏拉图在这里展现的论证悖论,涉及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需要追问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赫西俄德和荷马等诗人传唱的故事史诗是否是真的,诸神的世界是否真的像人的世界一样充满仇恨、阴谋与争斗;二是要说清楚,为什么作为诗人的赫西俄德与荷马不可以说谎而理想国的设计者也就是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可以说谎?是因为说话者的身份还是因为说话的内容?抑或二者都不是,另有第三种考量?对于第一个问题,柏拉图的论证是,关于神的真相是无法考证的,但是如果把神的世界描述为充满私欲斗争和阴谋诡计,就会导致年轻的受教育者效仿而为恶。“先入为主,早年接受的见解总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1](73)这里的逻辑是,由一个不愿意接受的可能实践后果,倒推神的世界一定是真实与善良的。如若不让年轻人模仿神的形象而学坏,苏格拉底关于神的描述就要好于诗人的描述,而好的就被认为是真实的。既然神尽善尽美,神的世界不存在谎言与欺骗,那么要反对诗人的谎言就理所应当了。
对于第二个问题,柏拉图的解决套路是,对谎言的定义进行澄清和明确具体含义,把谎言区分为心灵上的谎言和言辞上的谎言。心灵上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也就是心灵无知是真的谎言,而嘴上讲的谎言不是真的谎言,只是心灵的摹本。“神不存在说谎的动机”“心灵和神性都和虚伪无缘”[1](80),所以不能传播关于神的谎言,但是为了善的目的可以传播关于人的谎言。“虚假对于神明毫无用处,但对于凡人作为一种药物,还是有用的。”[1](88)既然是药物,就不是谁都可以说的,正如药方只能由医生来开。这样,说谎人的身份就有了限定,不是人人都可以说谎。比如病人不能向医生说谎,运动员不能就自己的身体状况向教练说谎,水手不能向舵手说谎,公民不能向统治者说谎,因为说谎会导致说谎者处于不利的境地,甚至导致整体的毁灭,但是反过来可以,因为后者相对于前者更具有真知。对于具有真知的人,言语之谎不是真的谎言,而只是在向无知者开药方。诗人的言辞之谎不能治疗年轻人的心灵,反而会为年轻人作恶树立神的榜样,所以要把诗人排除在理想城邦的构建之外。
《理想国》中第三次提到谎言就是在哲学史上引起长期争论的“高贵的谎言”。苏格拉底关于这个谎言的讲述并没有太多自信,但不是对谎言内容没自信,而是对能否说服其城邦的构成者没自信,也就是对此谎言的药效没有自信,但是仍然开出了这一药方:
首先说服统治者们自己和军队,其次说服城邦的其他人:我们给他们教育和培养,其实他们一切如在梦中。实际上他们是在地球深处被孕育被陶铸成的,他们的武器和装备也是在那里制造的;地球是他们的母亲,把他们抚养大了,送他们到世界上来。他们一定要把他们出生的土地看作母亲看作保姆,念念不忘,卫国保乡,御侮抗敌,团结一致,有如亲生兄弟一家人似的……我们在故事里将要告诉他们: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2](128-129)
在第二次处理谎言问题的时候,柏拉图为言辞谎言的合法性开辟了道路,此时又把谎言提升到“高贵的”层面。按照谎言作为药物使用的逻辑,谎言之所以高贵,应该是因为能够治疗疑难杂症,不然难以配得上高贵二字。对于理想城邦来说,最大的病症在于各群体的不团结,以致互相攻讦征伐,所以高贵谎言的第一个医疗目的就是维护群体团结。而团结的前提是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三部分人群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分工的基础则在于每个人群身上内在的金银铜铁成分。所以谎言的第二个医疗目的就是劝说各类人群认清自己的内在构成,安于各自合适的位置。谎言之所以高贵,是因为谎言承载着解决不同个体何以能群且群而不乱的理想城邦何以能存在的问题的重任。“故事从整体看是假的,但是其中也有真实”[1](71),这是柏拉图在设置故事教育开始前就让苏格拉底说出来的预设。高贵的谎言中潜藏着城邦最大的真实。对于城邦的存在来说,最大真实就是各分工群体的团结共存。
从柏拉图对谎言的处理来看,谎言本身不具有自在价值,他总体上对谎言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真实才是本身可欲的。但是谎言本身又是可利用的,统治者对谎言的合理利用如同医生用药治病一样可以达到医治城邦混乱和争斗的功效。后世研究者对于柏拉图的异议,一方面在于质疑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理想国是否可靠,另一方面认为对统治者利用谎言治理的辩护可能导向极权主义。但是对于谎言本身的存在状况来说,本文认为柏拉图的处理是写实的,是对他所处时代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在精神写实的基础上表达了自己的价值确认和理想建构。在谎言中求真实,也许这就是人类精神进展的真实。如尼采所说,人们所痛恨的“主要不是欺骗,而是某些欺骗的令人不快的可恨的后果”[2](102-103)。在柏拉图这里,善的才是真的,而真的一定也能导向善的。
二、“说谎言的,你必灭绝”
西方哲学中关于谎言悬案的第二种有典范意义的道德判决是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提供的。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M.Schofield)评价说:“在说谎的道德哲学史上,奥古斯丁代表着古代与现代之间的一道分水岭。”[3](135)奥古斯丁不像柏拉图那样保留谎言的药物治疗价值,给言辞之谎留有存在的道德空间,而是持一种绝对主义的禁止态度。
关于何为谎言,奥古斯丁坚持从动机上来判断,如果没有说谎的动机,即使说了与事实不符的话,也不被认为是在说谎。“判断是否说谎,是从说话者本人的意识来说,而不是就事实本身是真是假来说的。”[4](165-166)奥古斯丁根据说话的动机来判断是否说谎,同时根据其后果对谎言进行分类。奥古斯丁将谎言分为八种:第一种是有害于信仰教义的谎言;第二种对他人有害的谎言;第三种是对某人有益但对他人有害的谎言;第四种情况是无益也无害,单纯为了骗人而说的谎言,奥古斯丁称之为纯粹的谎言;第五种是为了取悦他人的谎言;第六种是对他人有益的谎言,比如不透露他人金钱存放处;第七种是除非审判官来传问,无害于任何人而有益于某些人的谎言;第八种是为保护他人身体纯洁的谎言[4](189-190)。奥古斯丁认为,所有这八种谎言都是罪,虽然罪的大小不同,但“无论哪一种,我们都应当一律憎恨之。因为没有哪种谎言不是与真理相对的”[4](212)。
关于允许说谎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圣经》中的例证;二是日常生活中的难题。不管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中,都有很多说谎的经文和例证。奥古斯丁采取了自认为有效的三重回应:一是有些被认为是谎言的经文,只要理解正确,就不能被看作谎言;二是虽然有些例子明显是谎言,但是不能效仿;三是在信仰教义上,任何时候都不许说谎[4](236)。关于日常生活中的谎言,奥古斯丁讨论了关于善意谎言的例证。比如,有一个人跑到你这里来避难,只要说谎就可以救他的命,你说还是不说?如果一个病人提出一个他不宜知道的问题,不回答会让他备受煎熬,告诉他实情就会毁灭他的生命。对此,保持沉默,还是说善意的谎言以维持他虚弱的身体?[4](169)奥古斯丁给出的辩护如下:(1)每个人都有两种生命,此生和永生,且永生重于此生,不能为了此生而牺牲永生;(2)“要爱人如己”,对邻人的爱要以对自己的爱为界限,不能牺牲自己的此生换取别人的此生;(3)为了挽救别人的生命说谎,是在牺牲自己的永生换取别人的此生;(4)所以不能为了救人而说谎,因为这远远超越了合理教义的规则。但是反过来可以,就是牺牲自己的此生换取别人的永生,因为基督就是这样为我们而死的。还有更进一步的例子:拒不做基督的假见证,拒不向魔鬼献祭,即便他自己的父亲被带到自己面前被杀死。为了缓解自然情感的张力,奥古斯丁区分了“与他相关”和“与他人相关”的概念。与他相关的事,他有能力做或不做,所以他能决定不做;与他人相关的事,他只能希望事成或不成,但是可以谴责。其中的逻辑推论是不能以自己犯罪为代价阻止他人犯罪。
隐藏在谎言分类和禁止撒谎救人背后的是奥古斯丁的价值排序:理论的真实>灵魂的纯洁>身体的贞节。“理论的真实性,即信仰和敬虔的真实性,若不是说谎,是不会受到玷污的;而最高最内在的真实性本身,是绝不可能被玷污的。真理要达到的就是这样的真实性本身。”[4](202)说谎玷污的是理论的真实性,否定的是最高价值。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撒谎。关于经由言辞谎言达到真理的柏拉图做法,奥古斯丁给出的否定理由是,“用说谎来使人接受真理,结果当他说真话时,就不可能有人相信他”[4](177)。对比柏拉图和奥古斯丁,二者的处理方式其实都有合理之处。比如“狼来了”的故事所要表达的道理就属于奥古斯丁的版本。但是“狼来了”的故事本身却是一种谎言。在柏拉图的意义上,就是要用“假”故事传达“真”道理。事实上,对于《圣经》中的谎言例证,奥古斯丁也是采取了柏拉图的处理方式,只不过虽将其作为通达真理的手段,却否认其为真正的谎言:
不仅雅各为得他父亲的祝福所做的或所说的,而且约瑟愚弄他哥的话,大卫假装疯癫,必须认为全不是谎言,而是比喻意义上的话语和行为,引向对那些真实之事的领会,那些真事可以说被比喻的外衣遮盖着,目的是为了训练敬虔的探索者的能力,也为了不让他们显得一目了然、浅薄粗俗……它们之所以被当作谎言,仅仅因为人们不明白所论说的事就是所意指的真事,误以为所论说的事是虚假的事。[4](233)
关于《圣经》中的记录,如同柏拉图的对话记录,也可以看作人类精神状况的写实,是实际生活的映照。虽然奥古斯丁采取了貌似严苛对待谎言的绝对主义态度,但是在处理《圣经》中的谎言例证时事实上是做出了妥协,不过不是像柏拉图那样承认谎言的疗效,而是取消《圣经》中例证的谎言属性,这与哲学王可以说谎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把城邦统治者置换成了上帝,也就是真理的化身,同时否认尊者说谎为谎而是教诲甚或微言大义。简言之,人不可撒谎,“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先知和圣徒可以撒谎,但其谎不是谎,而是上帝救赎的比喻和寓言。奥古斯丁比柏拉图更进一步的是对规则的强调,因为《圣经》中的先知与使徒属于过去,而哲学王属于未来。未来的目的是要打破现在,而过去需要的则是现在对既成规则的继续与延续:
谎言一旦得到承认和许可,信心的整套法则都将被颠覆;法则既荡然无存,也就不会有任何领悟的获得,用法则来培养孩子就是为了最终获得领悟。这样,真理的一切道理都消失了,让位于最放荡的错谬,因为谎言,即使是出于好意的,也可能从四面八方为它打开进入的门道。[6](177)
善意谎言的例外导致的是整个真理规则的坍塌,所以奥古斯丁要严厉禁止谎言。人类说谎的内在冲动如此之大,哪怕是借助信仰上帝,也是难以阻挡的。那么,如果没有上帝,应该怎么办?岂不是群魔乱舞?当王者与神者都失去权威,人类历史呈现的是一幅赤裸的诡诈与争斗景象,人们不再遵循可预期的游戏规则,而是被对可能导致当下即毁灭的力量的恐惧感所驱使。或者反过来说,因为存在诡诈的残酷现实,才有了柏拉图式的谎言审慎和奥古斯丁式的谎言禁止。
三、理性的谎言禁令
西方哲学中关于谎言悬案的第三种道德判决是目前具有广泛影响的康德的理性谎言禁令。康德让人类理性取代了哲学王和上帝作为谎言的终审裁判者,不过在判决上跟随了奥古斯丁而不是柏拉图。“如果一个凶犯问我们,我们那被其追杀的朋友是否躲在我们家中,对该凶犯说谎也会是一种犯罪。”[5](434)如果跟随柏拉图,处理方式可能就会是相反的,因为谎言可以作为治疗凶犯的药物,判定言辞之谎不是真的谎言。但是康德强调的是,“但凡是他说的,他都必须是真诚的(他不应当欺骗)”,对“真诚义务的违反即为说谎”[5](429)。虽然人可能会犯错误,但是人所说的一定是他相信或确认的,也就是不能把自己认为是假的说成是真的以及把不确定的说成是确定的。康德否定了柏拉图的言辞之谎与心灵之谎的区别,也阻止了奥古斯丁的内在后退,要求“在一切说明中都要真诚(正直)”[5](436)。
对于如何破解撒谎救人引发的道德难题,奥古斯丁的“永生>此生”的论证逻辑,在康德时代已经不好使了。但永生/此生的分析框架似乎存活了下来,只是在康德这里变成了本体/现象框架,人本身被视为同时处于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二重存在。在重要性排序上,本体之我>现象之我,恰如永生>此生。在康德看来,谎言是对人的本体存在的否定,对人格的最大侵犯,也是对人之尊严的丢弃和摧毁。承接奥古斯丁,康德把谎言引发的人与上帝的外在纠结转变成人与自身的内在纠结,把对谎言的抵抗寄希望于对自身人格尊严的捍卫。人为自己做主,所以人要为自己负责。撒谎不再是亵渎上帝,而是取消人本身,是现象界的肉体自我对本体界的精神之我也即形式之我的奴役。撒谎对人的尊严伤害之大,以至于把人的价值降低到物品以下的层面,因为物品毕竟还有可用的现实价值。
说谎(在该词的伦理学意义上)作为一般而言蓄意的不真实,也不需要对别人有害才能被宣布为卑鄙的。因为那样的话,它就会是对他人的法权的侵犯。说谎的原因,也可能只是轻率,或者完全是好心,甚至可能是旨在一个真正善的目的,但是,致力于这一目的的方式却由于纯然的形式而成为人对他自己人格的一种犯罪,而且是一种必定使人在他自己的眼中变得可鄙的无耻行径[6](208)。
对于“撒谎救人”的道德挑战,除了撒谎侵犯人格尊严从而取消人自身存在的理由,康德还演绎了撒谎的现象界后果:(1)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对凶犯撒谎未必能救其他人,但是对于撒谎者来说,却需要承担所有可能后果的法律责任;(2)如果严守真诚,不管结果如何,“则公共的正义不能对你有所指摘”,即使说真话伤害到他人,也只能作为一种偶然事件[5](436)。撒谎一方面是对自身人格的蔑视,另一方面则是对人际信任的破坏。真诚既是人格的保障,更是法权的存在基础。“我在事情取决于我的时候使得陈述(声明)一般而言没有获得任何信任,因而也使得所有建立在契约之上的法权被取消。”[5](435)在康德看来,谎言禁令不仅维护自身的存在,而且具有根本的政治意义,是群体存在的基础,因为真诚是一切法权契约的前提。“一切法权实践的原理都必须包含着严格的真实性……绝不能包含着它们的例外,因为这些例外毁掉了普遍性。”[5](439)撒谎救人牺牲的是群体连接的根基,换取的则是不确定的个体后果,哪怕从后果论的角度考量,也是无法得到辩护的。而且按照康德的理性设想,如果所有人都遵从本体界的普遍化道德律,那么撒谎救人的案例从一开始就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目的王国根本不存在违反道德律的杀人犯。撒谎与救人,在康德的处理方式中,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这在内在理路上仍然是“永生>此生”的逻辑,但是置于永生地位的不是上帝和来世,而是个体尊严与群体理性。此生服从永生,现象服从本体。个体内生命服从尊严,群体中政治服从法权。康德面临的真正挑战不是两种义务的冲突,也不是对生命的忽视,而是理性是否真的能够支撑起人的尊严和群体连接,以及群体理性是否真的可靠。
四、真相、真理与真诚
不管是柏拉图的言辞之谎与心灵之谎的区分,还是奥古斯丁和康德一致反对的撒谎救人,都是将谎言作为绝对之恶来看待的。然而,尼采告诉我们,“各种不同语言的共存表明,对于语词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理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正确表述问题,否则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语言了”[2](104)。尤瓦尔·赫拉利(Y.N.Harari)则走得更远,认为“除了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外,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7](26)。人类本来就是生活在自己的想象构造之中,在有意义的人类世界开端上,谎言比真理更真实。因为能够说出与事实不一样的东西,人才能够打破自然规律,而进入康德意义上创造自身序列的本体界。但是世界既然已经开端,如果时光不会倒流,人类就只能往前走,哪怕是在荒诞中也要努力寻找真实。不管是柏拉图、奥古斯丁,还是康德,关于谎言的讨论都是在默认人类群体首先存在且要追求更好存在的意义上。
真诚的价值高于谎言。谎言之所以为谎言就在于有真诚作背景。撒谎救人的案例已然预设了凶犯暴露自己意图的真诚。真诚是绝对的,但真理却不尽然。谎言的直接对立面是真诚,而不是真理。在这一点上,康德的真诚是对的,尼采的真理也是对的。除了真诚、真理,与谎言相对立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真相。真诚相关于体验,真理相关于理性,真相则相关于存在。对于人类总体事务来说,也许永远无法揭露真相,因为存在永远在创造和变动中。但是一旦存在,真相就永久留存并等待着被揭露,同时也等待着被解释,而真理就存在于被解释的真相中。被解释通畅而不自相矛盾的真相就变成了真理。当真相被掩盖、真理被扭曲时,能够突破谎言的则唯有真诚。如果区分一下与谎言斗争的三种哲学模式,可以认为柏拉图追求的是真相,奥古斯丁着眼的是真理,康德诉诸的则是真诚。从柏拉图到康德,关于谎言悬案的道德判决既可以说是层层递进的探索,也可以说是层层递减的探索。因为沉重的文明累积逐渐消解了真相和真理,只有无假于外的真诚尚可以提出自我要求。
用真相对抗谎言,相应于物理运作层面,遵循的是知识规律。医生比病人知道更多的医疗真相,舵手比水手知道更多的航海真相,统治者比公民知道更多的治理真相,所以前者认为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向后者撒谎。基于更多真相的谎言,前提是说谎的一方被认为比另一方具有更多的知识,哪怕并不真的具备,只要后者认为具备,谎言就可以成功。
真相可以被掩盖,但真理不会。被谎言解释所掩盖的真相经常会被真理戳穿。真相和谎言之争终究会上升为真理和谎言之争。真理总是来源于不那么可靠的社会事实,所以真理永远处于被再次阐释和确认的过程中。真相抵抗谎言,常常处于地下的涌动状态。而真理对抗谎言,则是公开的较量。真理相关于理性,但理性并不完备,通过普遍化测试的准则也未必就是道德的,所以真理经常被谎言打败。真理之所以抵挡不住谎言,尤其是组织性的谎言,是因为后者可以阻止真理的传播,而不被传播的真理就成了被掩盖的真相。
抗争至最后,能够在根本上对抗谎言的只剩下真诚。说谎源于自欺的冲动,真诚源于自由的冲动。只有冲动才可以对抗冲动。康德将真诚的反面定义为谎言,既是理性的洞见,也是情感的悲怆。真诚在根本上是灵魂的裸露,比肉体的裸露更让人感到不安。真诚的体验诞生于生命之初,纯粹如母婴之间。道德完人并不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在寻求他者认同的过程中如果屈从于自欺的冲动,就会撒谎。但当能够虚心承认道德过错且能够知错就改时,便可以认定为诚实或真诚,这就是一种伦理上的成熟。只要真诚还在,无论谎言多么强大,历史都会再次开启新的意义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