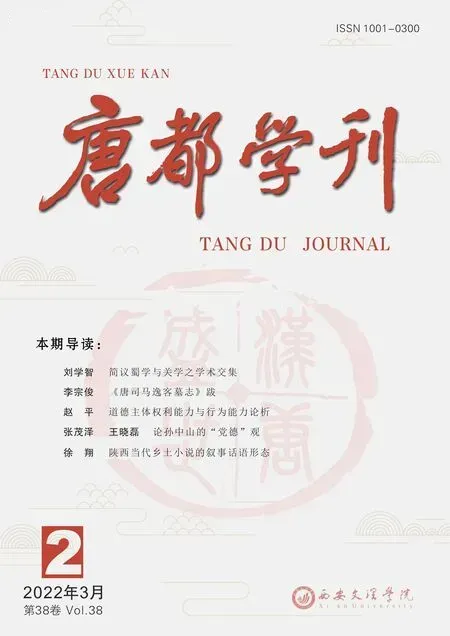尼采的“宿命”:命运的超越之思
华 锐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西安 710119)
在尼采生命之思的历史进程中,《苏鲁支语录》(《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的问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尼采在该书中首次提出“超人”概念,这代表着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之后,对人自身固有超越性问题的再思考,即认为该问题的处理不能发生在一个超验的领域之中,而应落实在当下此岸世界(echte Welt)之内,同时要让此在自身在面对命运的复杂多变之时,仍然具有幻化痛苦为快乐的能力,即保有对命运的绝对肯定与超越。
一
“超越”之思在《苏鲁支语录》卷1《精神之三变》当中体现得最为鲜明,尼采道出了一种“神圣的肯定”:“婴孩乃天真,遗忘,一种新兴,一种游戏,一个自转的圆轮,一发端的运动,一种神圣的肯定。”[1]21在此前一句尼采略带提醒地与我们交流:“请说出婴孩又何以能狮子之所不能呢?何以猛悍的狮子必化为婴儿呢?”在“骆驼”向“狮子”变化那里,尼采却没有如此一问,因为精神的负重势必要走向精神的自由这是情理之中的:“现在必在此神圣中看到了任意与狂放……要夺取则必成为狮子。”[1]20但只有当狮子变为婴孩,精神才称得上完成最终的变化——超越。前言之中,苏鲁支(查拉图斯特拉)向内心说出“上帝已死”,并来到城镇之中向世人说出:“我教你们超人的道理。人是一样应该超过的东西。你们作了什么以超过他呢;超人是土地的意义;他便是这大海,其中你们的大污蔑视能够沉默;他便是那电光,那疯狂药!”[1]8
尼采充满热情地提出“超人”,足见对此概念的重视。何为超人?尼采首先说了人就是应当被超越、被克服的东西,他借用 “进化论”,对“人类”开始了几句略带鄙夷的讥讽:“猿猴于人类是什么,可笑的对象或痛苦的羞辱。人与超人亦是如此;从爬虫进到人类,你们内里许多地方还是爬虫;你们中间最为智慧者也还是植物与魔鬼的岐出生与两性生。”[1]6同《精神之三变》当中使用具有否定性的三种精神来克服精神上升的阻力以获得智慧的手法类似,尼采使用超人的进步和猿猴的丑陋来否定人类脆弱的道德,以及由理性带来的技术成果。“被超越和被克制”表明了人类是处于线性时间之中受到命运摆布,随时准备被取代而不欲求超越的那种东西,这正是尼采所要揭示的“末人”。同时,尼采强调超人是大地的意义,朗佩特认为此处说明了超人若不以大地作为自己的归宿,则无任何意义可言;大地是潜在的意义。在“忠于大地”这一关节处,查拉图斯特拉描述了人类未忠于大地的方式——他们幻想着彼岸;上帝之死即灵魂的灭寂,大地和身体被遗与一片废墟之中……不过现代使这些都不再可信……只有未来才是新的有意义行为的理由。所以,“你们能经历的最伟大的事业是什么?那是大蔑视的辰光。那辰光,便是你们的幸福也于你无谓……如今能有的最伟大体验也不过是对过去和当下的藐视。”[2]30但尼采的“超人”远不止“对过去和当下的藐视”,他是朝向未来的人,体现为超越以往一切形而上学体系的“此岸之思”,并且会因其批判对象的特性,而被染上一些“形而上学”的色彩(姑且称之为“神圣性”的色彩)。众所周知,尼采本人是“反形而上学”的,如果继续使用超人“发号施令”,就会将“此在”又一次悬于形而上学的云端而被否定。故而尼采在其后期文本之中让超人“存而不显”,但始终引导和参与着有关“相同者永恒轮回”学说的构建,根据朗佩特记载,尼采后来提到超人的地方只有《论道德谱系》第1卷第6节,《不合时宜的漫游者》37节,以及《敌基督者》4节[2]32。超人存而不显的原因在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提出,相同者即为此在自身,同时又是在轮回之思当中经历超越的“我自身”,既保持了超人的“神圣性”,又让略带“神圣”的超越落在了大地之上,避免了重蹈形而上学的覆辙。
尼采对古希腊文典知之颇深,他认同古希腊悲剧强调冲突和颠覆,左右生命的绽放或使之枯萎、甚至死亡与终结的强力,虽然他的超人“存而不显”,但却绝不会屈服于冥冥之中的那种悲剧式的宿命,取而代之的是与命运共舞、克服死亡以致超越。“超越”一词在德文中有多重表达,如“Jenseits” “Außerhalb” “Überschreiten”等等,前两个侧重于超越、超过,汉语里面“越过”往往是同义反复使用,而这里德文兼具二者词义,更指达到某个程度之后运动的延续,这与“生成”之意义十分接近。尼采了解19世纪的宇宙论,并且在《命运与历史》之中将这种强力当作一个“合乎规律的宇宙”,而把历史交由缺乏总目标的因果性和偶然性去处理。但“尼采不愿放弃意义和目标”,且那时的他已然不愿使用基督教虔诚的信奉,那怎么办?尼采想出了一个“把世界作为阻力来体验”的自由的意识,把世界、决定论的宇宙称为“命运”,自由的意志就是“命运的最高潜能”[3]25。年轻的尼采创造性地采取了一种重塑生命的痴爱取代了对彼岸世界的虔信,以实现生命意志的内在超越。在尼采看来,命运的确具有一些“神圣性”,而且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但此处“神圣性”发生的场所被指定在与大地相结合的此岸世界之中,而非飘渺的天国,“神圣性”因而是强力意志敦促超越的一大动力,是用来在竞赛当中被打破的、被否定的东西,这样才能换来“肯定”。神圣的肯定应当是“对神圣的应当被打破”的肯定。
二
如果说尼采命运的“神圣与肯定”是他“不愿放弃意义和目标”,同时又需“忠于大地”,关注“此岸世界”,那么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让“此在”在失去上帝“救赎”和“庇佑”的前提下,亲身承担苦难与死亡。如同狮子变幻成婴儿一般,尼采用自己的独特思考和肉体亲历的巨大痛苦第二次施展了魔变的力量,让苦难幻化为快乐。
在《瞧!这个人》当中,尼采说:“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对于某个阴森惊人的东西的回忆将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关于从未有过的危机的回忆、对最深的良知冲突的回忆,对一种引发反对被信仰、被要求、被神圣化了的一切东西的裁决的回忆。”[4]248尼采很明确地将自己遭遇的不幸即“可怕的事物的回忆”与命运连在了一起。萨佛兰斯基那里有着一致的结论:“青年尼采首先遭遇的可怕事物,是他自己的生命……他先写自己的生命,然后用身体和生命写作,而最后他为自己的生命写作。”[3]13青年尼采命运多舛,根据其自传回忆,父亲在其4岁时就不幸死去了,悲伤使得尼采在梦中又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梦到父亲在教室里抱着一个孩子,很快就消失了。在随后不多的日子里,尼采的弟弟也莫名其妙地去世了。这让年轻的尼采伤痛之余深信自己的梦境居然得以成真。1876年前后,尼采似乎完全掉入了命运编织的罗网,他的精神世界一次又一次遭受着来自现实生活的巨大冲击:“在1879年……他估计他失去了四个月的时间,并经常遭受各种各样的消化道疾病带来的痛苦以及19世纪的治疗技术给他带来的痛苦。”[5]令人欣慰的是,在经过长期的治疗之后,尼采居然在1881年神奇地康复了。据《朝霞》记载:“在这篇本来也许会变成一篇诔词、一篇葬礼演说的迟到的前言中,我就要对你们讲述我在地下做什么:我已复来,且伴随着安全。”[6]在之后十年的光景里,这位天才的思想者继续挥洒着他生命的炽热光辉,《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等传世著作更是层出不穷。是什么让一个垂死的病人获得了生命的希望呢?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无厘头:求生的意志和对康复的渴望!在《快乐的科学》的前言中,尼采描述了伤痛和疾病如何走向康复的巨大反转:“末了,最重要的话不可不说:人从如是的深渊、沉疴、多疑症中返回,重获新生,脱了皮,比以前更敏感、更狡黠,对欢乐的鉴赏更精细,对美好的事物更微妙……”[7]317“同时也更具稚气,也比之前尖刻百倍”[7]40。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有对疾病的体验升华的意味,他强调道:“我需要将无法忍受的疼痛,和苦熬通过愈加强力的情感上的激愤来进行自我麻痹,即便是多少在一个瞬间,能够将苦熬遗忘在意识之外。为了‘寻衅’于这种情绪,我们需要一种尽可能野蛮的情绪”[4]472。
许内曼将尼采此处所做之“臆想”理解为“是病态者所共有的性格癔症”。值得我们回味的是,我们不能把疾病的痊愈看作是向健康状态的简单回归,正如同我们的身体在经历过某些疾病之后就会获得抵御此种疾病的抗体一样。我们的肉体在遭受疾病的侵袭并重获健康之后,实际上收获的是比之前更伟大的健康。那么“忠于大地”的超人是否也是在类似身体这样的康复当中汲取超越的力量,让精神不断地飞升直到永恒的回环之中。尼采似乎是想告诉我们,但欲言又止。如果疾病是一种需要且不可避免的“承担”,斗争是为了重夺自由呼喊出来的“我要”,那么唯有更加强大的健康归复才应该说强力意志所寻找的具有魔变力量的超越的东西。尼采的疾病同康复的阐释在他的文字中常有体现,在他眼里,像自己这样经历过某次重大疾病而能够得到治愈的人是同命运博弈的强者:“说到我常年重病,难道我不是要多多的感谢它,远远的超过我的健康吗?我要感谢它给我的一种更高的健康,它不能扼杀的一切东西都具有的这样一种变得更强壮的健康。”[4]460而瓦格纳和叔本华之辈在他看来就是被疾病侵染无法痊愈之辈:“叔本华和瓦格纳满足了此类贫乏者的双重需要,他们否定生命,他们诽谤生命,因此他们是我的对跖者。”[4]461
通过疾病的考验过程实际上就是身体之死与精神之生相互较量的超越博弈。不论生或死,苏醒或者永远的沉睡都意味着对之前生命的”超越”,尼采强调的是前者,因为只有能够从疾病当中获得重生,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超越,而因畏惧疾病而陷入怨恨,最终导致死亡则意味着软弱和虚无。而若要获得前一种超越,就必须从自身之中寻找力量。萨弗兰斯基将其理解为把自己当做“可分割之物”来体验。这对理解尼采命运、超越以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都大有裨益。萨弗兰斯基说:“一个强大的传统谈论‘个体’,如同谈论一种人的不可分割的内核。可尼采很早就对个体的内核分割做了试验。即使对区分我与自身还心存疑虑,但依旧对‘自身’进行续写。”[3]267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中说:“你应该成为自己的主宰,也应该成为自己德行的主宰……你该学会理解在任何赞同和反对中都必然有之的不公,学会理解不公与生命是不可分割的,连生命本身也是由透视及其不公决定的……生命的发展最渺小最逼仄,最贫穷最原始……生命还是不得不亲自充当万物的目的和尺度。”[8]10试问在最痛苦之时如果不将渺小和贫穷与原始祛除,生命如何还能有所充当?永恒轮回的目的就是要“为了内在性而保持超越的力量……对大地保持忠诚”。尼采从“旋转的时间活动的表象当中”取走了“给人负担和折磨人的东西”,让我们快乐的经历着永恒轮回,认为“人类此在的勇气和轻松愉快,能够进入总是同样的世界游戏中的人,才是一个超人”[3]329。这与查拉图斯特拉最终通过自己的“复返”来承担起救赎与治愈的使命,放弃由他的追随者们去完成,并在最终走向命运的超越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三
在《精神之三变》中,从狮子到婴孩的转变体现了命运超越的“神圣性”及其肯定模式,致使此在面对的死亡和痛苦刹那间变为快乐与祝福。由此,尼采进一步阐述了超越的经过,即“我自身”在承担生命的苦难之中实现价值重估。
尼采在《我为什么如此智慧》里说:“我的此在生命的幸福及其独一无二性,也许就在于它的厄运。”这是因为同样的轮回再次出现在了尼采自己的身上,“在我父亲生命衰落的那同一个年纪里,我的生命也开始衰落了……我还活着,但却看不到离我三步遥远的东西……”尼采认为从怨恨之中逃生并且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涤荡,虽苦熬,此疾病却“应当多么值得感谢啊!”因为尼采所秉持的观点是:“疾病本就是一种怨恨”,但大多数患者的摆脱方式只有一种,“我称之为俄罗斯式的宿命论,那种毫无反抗的宿命论”,尼采强调命运的使然“把自身当做一种天命(Fatum)”[4]576,而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宿命论”是致命而且危险的,对它的克服才是重回健康的保证;另一件治愈的本能就是“战斗的本能”,即强壮天性所独有的反抗的天性,属于强者,它从敌人那里获得自身强壮的尺度。尼采注明这两种本能,来给自己的康复辅以一种解释。在这两种本能的作用下,“由一种血液和肌肉上的极度贫乏,带来的欢愉畅快、超凡脱俗。精神的完全明亮和喜悦乃至于精神的繁茂兴旺(Exyberanz),它不仅与最深刻的生理虚弱相一致,而且甚至于一种极端的痛苦相一致。”[4]552尼采引用苏格拉底作为例证,说明这种苦熬带给他的清醒及不值一提的苦熬。此间苦难是他坚持自己思想静土的清静剂,如他所言:“从病人的透镜出发看比较健康的概念和价值,反过来根据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探视颓废的本能的隐秘工作,或将是我最长久的训练,是我最本真的经验……我有能力转换视角:说明何以也许唯有对我来说,一种价值的重估竟是可能的。”[4]442
一种价值重估竟是怎样的可能?萨弗兰斯基通过对比《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解释道:“同从夜之歌经过舞之歌舞之歌一直到坟茔之歌的顺序一样,(权力意志)也有着一次从窒息生命的意气消沉中的新生。对此最重要的协助手段是对创造性力量的回忆。”“倘若存在一种闵希豪森效果,那么它在这里可以找到:一种自己想要的生命,可以把自己从阴郁淤泥中扯出……在这样的创造中自我克服多于自我保存,这是自我升华。”[3]330他认为,如果人们只是在自我克服当中理解到了保存而忽略了尼采更为重要的“扩张”和“升华”,就是对生命的轻视之举。这里,萨弗兰斯基还发现查拉图斯特拉宣布了“达尔文等其他自我保存理论家谈论的那种存在意志,根本就不存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化论的能量在达尔文之后的西方世界日益显现,《物种起源》从实证科学的维度回应了“人是从哪里来的”之古老诘难;天文学以抽象的数学模型演算来发现地外天体而著称。但二者皆未能进入哲学范畴思考其背后的动机,而只是在行使对具体科学工具与范式的剖析和应用。这也就不难理解《偶像的黄昏》中“反对达尔文‘生存竞争’的解释,认为其倒不如说只是一种断言”,因为“达尔文忘记了精神”[9]。
何为精神?《瞧,这个人》里尼采同样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有一番说辞。尼采举出“夜之歌”“夜来了,现在一切跳跃的喷泉都更加高声地说话,而我的灵魂也是一汪跳跃的喷泉……这是夜里了,现在一切爱者的歌声醒起,我的灵魂也是一位爱者的歌曲;我是光明,但愿我是黑夜!然则我被光明所萦系;但愿我是昏暗的和黑夜般的!我要怎样吮吸光明之乳!”[1]104这里明显地看出黑夜与光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完全对立,更像是正在进行着某种互换的前奏,在《漫游者和他的影子》当中尼采说道:“夜幕一降临……黑夜劝人进入死亡的安息,如果人类没有太阳,必须以月光和油灯来与黑夜交战……从人类精神和灵魂本质上不难看出,那一半笼罩生命的黑暗和日光的缺乏,已经使它彻底变得阴暗了。”[8]601黑夜与光明显然并未从彼此之中走向对方,就好像疾病与健康互相分离的状态一样。而尼采将“夜之歌”当作“酒神颂歌的标志”,恰有表明光明为日神之意。疾病—健康,酒神—日神,黑夜—光明,每一组概念都在先历经痛苦之后获得了命运的释放和超越:“查拉图斯特拉……是进行否定的人如何仍然可能成为一种说‘不’的精神的对立面;肩负命运之重荷,却如何仍然可能成为最轻盈和最超然的精神:查拉图斯特拉是一个舞者……思考最为幽深的思想的人……还把自己祝福的肯定带进一切深渊之中”[4]442。命运之重荷以最轻盈的方式被“我自身”所承担,在畏惧过深渊的无底之虚无,尼采抛出了“我自身”作为命运超越的基石,而飞升的方式竟是不借用其他任何外来之力,仅凭借自身的超越本能作为上升的阶梯,以踩着自身的方式去实现精神的自我超越!并最终在生命的回环当中重新积蓄力量,回归自身。“我自身”发生在超越之维的这一举动,再一次重申了相同者永恒轮回的生命超越的承担者:“我”,是为超人的象征,立足于大地。“‘人’被克服了,超人在此成了最高的实在性,即人类身上被诩为伟大的一切东西都处于超人之下,宁静轻快的脚步、无所不在的恶毒和放纵,以及其他对查拉图斯特拉类型来说典型的一切,从来就没有当做伟大性之本质而被梦想过。”[4]441
四
对于尼采的命运和超越之思可以概括为:命运在于承担生命之重负并通过摆脱疾病的本能而重新恢复健康、吸纳伤害并最终恢复健康的最大生命之界限;超越在于与命运的交手之后依然能够具有选择生活,并且将痛苦幻化为快乐的生命超拔。然而,所谓“命运经历的究竟是何种超越”的问题该如何作答呢?
尼采首先反对的是将命运当作一成不变的真理去接受。命运是用来创造他物并被他物所创造的对象,以及其自身也是一个可以时刻被创造的对象。尼采对命运的解读有时是明确的,有时却仍需要进行考察,但是尼采关于“创造”和“命运”的同时使用这一点确实是较为明朗的。在中后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到《瞧,这个人》等著作中,尼采都谈到了命运和创造,他将二者同死亡与超人联系在一起,以展开对耶稣基督受难而复活的一套价值体系进行批判:“基督教道德之发现乃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大事,一场真正的灾难。谁弄清了基督教道德,那他就是一种天灾,一种命运,他把人类历史破碎成两段了。人们活在他之前,人们也活在他之后。”[4]484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意义何在?A.彼珀根据《自由的死》解释说:“死的最好方式是一场好像为超人庆贺而演出的死亡……他们围绕着正在死去的人并示意,他们把在这死亡的完成中最后一次实践的自我超越作为他们自己生活的原则”;“第二好的死是在斗争中死去同时浪费一个未带的灵魂”。这种死亡由于“随着每一次超越自己去创造尝试,用生命冒险”,所以“并非会失去它,而是在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赢回它”;“斗争中失去生命的人……完成了他的死亡,但他不是在适当的时候死去的”;“一个伟大的、也许能够发展出不可预料力量的灵魂提前结束其创造欲……这是一个还能向上的力量潜能的令人遗憾的浪费”[10]315。由死亡的“好坏”来引出对于生命力量的尊重或是浪费,从而拿来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做比较:“与耶稣不同,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死亡时刻,那就是力量不再能够去创造意义的时刻……死亡并不由于生命劣质的不堪受性,出于厌倦而被扔掉,而恰恰因为人们希望生命应该有一个意义。”[10]321
查拉图斯特拉并没有继续说明究竟什么样的死亡才算得上是“第一好”的,而是引入“自我超越”来进行下一篇的内容。如果说疾病是距死亡最近的东西,那么为了康复而超越疾病,就不失为生命自主选择“活下去”的一个“创造”!选择“活下去”的同时也就等于拨动了生命倒计时的指针,不论生死,皆是运数,即查拉图的“第一好”的死。但唯有超越生死,才可能是尼采的真实意愿。不过,尼采似乎对“人类”的超越不抱有十足的把握。对此,萨弗兰斯基解读为:“这个‘自身’成了他的一片完全没有探究过的他想发现的新大陆,而所有的探究总是不断把他引向那创造性的力量……到了最后,那创造性的原则吞噬所有那些反抗的事实性。那个替代尼采自身的形象守住了舞台,而所有其他的人物在这幻想的自我创造的轰动效果前退却。”[3]359
尼采选择“超越”“生成”来破解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回应人之自由的问题。超越是为“无时间性”,尼采的时间没有发生与终结,生命因而摒弃了出生与死亡,一切只有命运朝向自身的回归与竞赛。尼采极力反对用基督教教义和所谓“普世道德”来充当救赎的良医,因为那是放弃肉身而取“灵体”,放弃超越而求“永恒”的思维业障,是真正的致死的疾病。
综上所述,尼采超越的含义有三点:首先,“超越”指意志本身的力且等同于主动向上的东西,它凭借意志运动肯定主体即生命本身,旨在冲破理性的架构,生命的意志应该是在自身被否定的时候仍然可以凭借精神的升华,借此来克服抽象自我意识的局限。其次,超越的力作为生命上升的强力超越了造物主的神迹和奇迹,他不是假想出来的奴役与主人的关系,而天然的就是主人,主导个体的一切运动与生成,这样的超越之力是主导自然万物的生成力量,它本身也是自然的且与自然同质化。如果说时空和因果性可以对人的身体活动产生限制,那只不过是因为时空本就是同人一起的与生俱来的观念,因而也是在自然之内的。作为认识先天形式的,实际上是个体无法突破自己的局限(比如道德领域里的限制)而出现的固有的自我意识。最后,因为超人本身就是在强力意志簇生之中生命努力向上变为意志的个体代表,它具有自我愈合、自我审视的能力,且包含了逻辑的理性,而不受理性知识的束缚。超人代表着最好的知识和道德,不啻如此,他也是尼采在以身体之感,生命主体为准绳立足此岸世界,取代心灵,超验实体为主导的彼岸世界视域下浇灌出的全新的、生成的形而上学之花。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尼采没有给我们一个较为明晰的答案,究竟何以为命运的超越?并非他不愿意告诉我们,因为“超越生死”是此在无法实现的夙愿,只有神才能做到,而我们必须无条件地面对死亡,尼采自己同样没有获得他所说的那种“永远的健康”,因为他看到了在这背后隐藏的人类巨大的命运危机,如同现代技术所日夜渴求的“永恒不死”,人们都在渴求“超越生死”,而把自己看作神灵一般,如此的永恒的健康需要付出代价。如果像斯特劳斯学派所奉行的那样,哲学家都信奉高明的“隐微术”,伟大的哲人都不免要说谎、需要必要的说谎,尼采也许最后会说:死亡是对生命纷扰之赎还,这才是最好的健康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