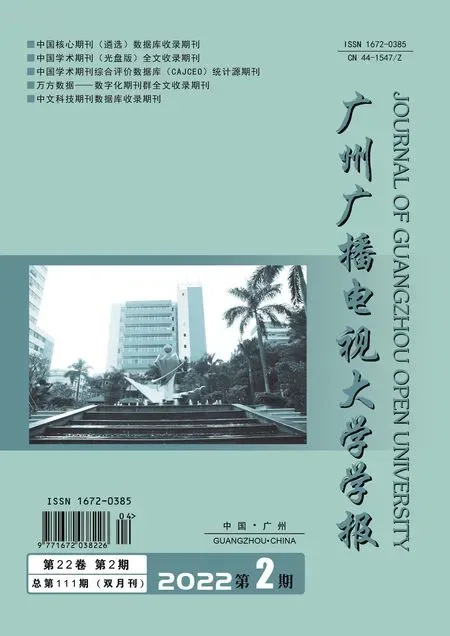汤沈之争中的“案头”与“场上”概念新解*
孙向荣
(广州大学 期刊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汤沈之争是中国戏曲史上著名的争论。众所周知,这场争论在明代两位戏曲家汤显祖与沈璟之间展开。尽管这场争论并未表现出面对面争执的形式,但其间两种截然不同的戏曲观念的碰撞不仅表现在二人的著述之中,而且引发同时代圈内人的关注与参与,更引起后代戏曲界的长期讨论,至今未息。一般认为,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戏曲的文本创作究竟应以“案头”还是“场上”为准绳,如此,似乎主张“案头”的汤显祖以今日之戏剧标准看就处于不利位置,而主张“场上”的沈璟则显然占有观念优势。但问题恰恰在这里:“案头”的汤显祖戏曲却在“场上”盛演不衰,而“场上”的沈璟戏曲反倒沦为“案头”的读物。显然,是人们误读了汤沈之争背后各自所代表的观念。问题是,人们是如何误读这场争论背后的观念的?本文所阐释的观点是:汤沈之际“案头”与“场上”两个概念具有与今日完全不同的内涵。
一、汤沈之争所提出的问题
汤沈之争的关键在于文人的戏曲创作标准究竟以阅读还是以场上演出为准。沈璟指责汤显祖的文本乃案头阅读之本,汤显祖对此批评不以为然,认为为了获得阅读美感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这场公案见诸于明人王骥德的《曲律》:
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齚舌。吴江尝谓:“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中之之巧。”曾为临川改易《还魂》字句之不协者,吕吏部玉绳(郁蓝生尊人)以致临川,临川不怿,复书吏部曰:“彼恶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其志趣不同如此。郁蓝生谓临川近狂,而吴江近狷,信然哉![1]
表面上看来,汤显祖对沈璟批评的反驳,其潜台词乃是主张案头的:为了案头阅读可以牺牲场上演唱的需要。如此,汤显祖就成了文人剧本创作的代表,而沈璟则为场上文本的守护者。
但吊诡的是,被沈璟指责为案头的汤显祖戏曲反倒在场上盛演不衰,而沈璟的场上本却很少被后人搬演。其实,明人对沈璟的剧作就颇有微词,凌濛初《谭曲杂札》就认为:
沈伯英审于律而短于才,亦知用故实、用套词之非宜,欲作当家本色俊语,却又不能,直以浅言俚句,(掤)拽牵凑,自谓独得其宗,号称词隐。而越中一二少年,学慕吴趋,遂以伯英开山,私自服膺,纷纭竞作。非不东钟、江阳,韵韵不犯,一秉德清。而以鄙俚可叹为不施脂粉,以生梗雉率为出之天然,较之套词、故实一派,反觉雅俗悬殊,使伯龙、禹金辈见之,益当千金自享家帚矣。[2]
而明人张岱则对汤显祖的剧作推崇备至:“汤海若初作《紫钗》,尚多痕迹;及作《还魂》,灵奇高妙,已到极处。”事实上,明人就有不少家班搬演汤显祖的戏曲,例如邹迪光、王锡爵、钱岱等著名的家班。
对于这个有趣的悖论,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有赞同沈璟观点的,更多的则是替汤显祖打抱不平。
本文看法略有不同,我认为之所以言人人殊的关键在于未能厘清汤沈之际“案头”与“场上”两个概念的内涵。
二、汤沈之争历史语境中的“案头”与“场上”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需要先做点文献考据,以明晰“案头”与“场上”这一对立的文本概念形成的历史语境与语义。“案头”文本这一概念,明人多有使用,例如明人王骥德就多次使用:
词藻工,句意妙,如不谐里耳,为案头之书。[3]
以是知过施文彩,以供案头之积。[4]
“场上”文本这一概念同样出自明人,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玉杵》杨文炯
文彩翩翩,是词坛流美之笔;惜尚少伐肤见髓语,而用韵亦杂。若与郁蓝之《蓝桥》较才情,此曲当退三舍;然律以场上之体裁,吾未敢尽为《蓝桥》许也。[5]
《合衫》周继鲁
作此专以供之场上,故走笔成曲,不暇修词。其事绝与《芙蓉屏》相肖,但此罗衫会合处,关目稍繁耳。[6]
从以上数例中,可知当时的所谓“案头”文本的特征是注重文采,在文辞上过于雕琢,不太合曲律——“不谐里耳”。而“场上”文本则“走笔成曲,不暇修词”。由此可以得出明代“案头”与“场上”概念的基本内涵:决定“案头”还是“场上”文本之标准的,指的是“曲词”是否合律,而不涉及文本的其他舞台呈现方式,包括剧情设计、叙事形式、表演方式、舞台调度等等。
正因为如此,明代的“案头”往往与“台上之曲”对言,可见当时“场上”概念指谓的乃是“曲”。沈际飞《独深居本紫钗记》引汤显祖自题《紫钗记》的自我评价“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沈际飞亦谓:“《紫钗》之能,在笔不在舌……案头书与台上曲果二。”明人柳浪馆刊本《紫钗记总评》称:“一部《紫钗》都无关目,实实填词,呆呆度曲……余谓《紫钗》犹然案头之书也,可为台上之曲乎?”[7]
明乎此,我们就知道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场上”与“案头”这对概念来评价汤显祖与沈璟的了。
更重要的是,作为当事人的沈璟自己对“案头”与“场上”这对概念的理解。事实上,沈璟并没有使用“场上”这一概念指谓戏曲文本,他是在强调曲律的同时批评“案头”之作时阐释自己关于“场上”观点的。沈璟非常精通并特别强调曲律,他在《二郎神》套曲中通过赞赏何元朗而表达了自己的主张:“道欲度新声休走样,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8]沈璟还著有《词隐先生论曲》《唱曲当知》等曲论著作,可惜未能传世,但沈璟的曲论观点明人王骥德在《曲律》中每每引用。例如沈璟特别强调宫调的整饬,韵律的严整:“须教合律依腔”[9]。“南曲自《玉玦记》出,而宫调之饬,与押韵之严,始为反正之祖。迩词隐大扬其澜,世之赴的以趋者比比矣。”[10]盛赞“词白工整”“音律精严”之作[11]。而这种强调旨在使得词人的音律符合曲唱的实践:“怎得词人当行,歌客守腔,大家细把音律讲。”[12]
需要指出的是,沈璟此处的“歌客”不仅指戏曲演员,而且往往指清唱的歌者。至于场上表演,则可灵活处理,“或稍损益之,不可为法”:
词隐于板眼,一以反古为事。其言谓:清唱则板之长、短,任意按之,试以鼓板夹定,则锱铢可辨。又言:古腔古板,必不可增损,歌之善否,正不在增损腔板间。又言:板必依清唱,而后为可守;至于搬演,或稍损益之,不可为法。[13]
可见,沈璟的“场上”不仅指戏曲演唱,更多的应该指“清唱”的演出。明人臧懋循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责难汤显祖的“案头”文本的,他在《玉茗堂传奇引》中称:“临川汤义仍《牡丹亭》四记,论者曰:‘此案头之书,非筵上之曲。’”所谓“筵上之曲”往往是宴席上佐酒的“清唱”。正因为如此,王骥德就称沈璟之“词曲一道,词隐专厘平仄”[14],也即只注重文本中的“曲词”,并非真正的场上搬演。沈璟为曲词的创作设立了诸多清规戒律,要求“尺尺寸寸守其矩矱”,但其自身的创作却“大都法胜于词”。相反,汤显祖由于不守此律法——“临川汤奉常之曲,当置‘法’字无论”,而被指责为“尽是案头异书”[15]。
由此可见,汤沈二人的分歧仅仅在于曲词的创作是否需要按照沈璟的标准严守音律的法则。尽管曲词与唱腔的配合也是场上表演的要求之一,但“场上”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远比此丰富得多。而且,即便曲词与唱腔不够协调,也可通过唱腔的改造,例如依字行腔的方式加以修正。仅仅据此称汤显祖为“案头”、沈璟为“场上”,不仅有失公允,而且戴错了帽子。
三、汤沈之争传统观点的批判与新绎
根据上述对汤沈之际“案头”与“场上”概念的清理,二者的区分标准指的是“曲词”合律与否,与今天我们理解的“场上”——舞台演出本相去甚远。由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汤沈之争传统观点的症结所在,并据新观点进行以下阐发:
第一,尽管当时及后人对沈璟戴上了“场上”文本的桂冠,但实际上沈璟所谓的“场上”仅仅限于曲词的音乐合律与否①;而汤显祖的“案头”文本之诬,乃是指其曲词过于注重文采,而不惜以牺牲某种既定的曲律为代价。事实上,以“重文采”来概括汤显祖的曲论是不准确的,甚至是以偏概全,汤显祖曾阐述说,自己注重的是“意趣神色”:“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16]那么,沈璟的曲律指的是何种“曲”之“律”呢?是昆山腔,还是弋阳腔抑或宜黄腔?徐扶明认为沈璟的曲律主要指“依《中原音韵》,制定曲韵”[17]。但事实上,判断曲词合律与否,需要依据曲腔,也就是不同的曲腔旋律,具有不同的韵律要求。
第二,沈璟的音律主要针对的是“清曲”,而“剧曲”则稍可灵活;因为剧曲不仅有昆曲,还有当时更为流行的“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并且有取代昆腔之势②,此腔“拗折嗓子”并不意味着所有曲腔都是如此。
第三,从曲词与曲腔的配合上,并非只能让曲词被动地适应曲律,还有“依字行腔”的方式。事实上,即便是明代的昆曲,也并非都是先有曲腔然后进行填词,正如明人潘之恒指出的,昆曲应“曲先正字,而后取音”[18]。所谓“正字”就是定准字音与声调,然后据此转化为旋律——“取音”。这种正字取音的方式即“依字行腔”,洛地对“依字行腔”的解释是,按照字读的四声调值走向化为旋律[19]。此外,根据刘崇德的《再论昆曲中元杂剧音乐的昆腔化》中的看法,明代还盛行的北曲南唱、北曲昆唱的演唱方式,也表明声腔对曲词具有灵活的适应性。
第四,剧曲的音律并非由作剧者毕其功于一役,最终合律与否,往往由演员根据需要自行修正。徐凌霄指出:“文词为案头人所擅长,不论是否能唱,只要会填词,则词有词之音节,只要会作诗,则诗有之音节,词也诗也,有入唱者有不入唱者,然即使不能直接入唱而一经曲家或伶工之实地烹炼——抽衬托补——则词曲可以成为剧曲,诗歌可以合于场上之腔调。词曲及诗歌既不离乎音乐的原理,则其与剧曲关系之密切为常识所易知,而案头人与场上人互相发明,当然为应有之一义。近来新剧盛兴,诸名流率多躬任写剧之事,虽不善唱者,只要能写出词句,即可付之名伶自为斟酌,奏于场上,亦未注意到音律唱法,事实上亦无先明歌术而后写剧之必要。盖皮黄本与昆腔不同,词句不外乎七字格十字格,此固词人所能为,至于临场如何抽衬充补变换,则名伶自能为之。”[20]这表明,作为“词人”的文人所强调的格律,并不完全适合“场上”的演出,表演者往往需要根据“场上”的要求进行修改变换,主张格律的严整并不能代表“场上”的要求。何以如此?其中的道理,汤显祖当年就讲得很明确:“唱曲当知,作曲不尽当知也。”所谓“作曲”乃指曲词创作者,作为案头创作的文人,并不尽知场上的“唱曲”者,当然不能以曲律来包办场上的演出需求。叶长海对沈璟曲律论评价说:“他注意并强调的剧作与演唱的联系,多局限于‘唱’的规律,对‘演’的规律在理论上无甚建树”[21]是十分允当的。更何况,曲律仅仅就“场上”词曲配合的立说,而舞台呈现则是全方位的。
第五,从文本的舞台实践来看,汤显祖的“案头”文本远远比沈璟的“场上”文本更受到舞台的欢迎,尤其是《牡丹亭》,历代盛演不衰。有趣的是,沈璟认为《牡丹亭》不合律,而改写曲词,将其重新命名为《同梦记》,以期更适合舞台需要,岂知人们不买账,早已失传。事实上,沈璟本人的剧作也并非严守律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徐扶明通过考察沈璟的《义侠记》发现:“有些出确实是更调更韵,如第八出《叱邪》,用的是中吕、南吕两个不同声调的宫调,萧豪、家麻、支思三韵。但也有些出,则用的是一调一韵,如第十出《委嘱》,全出均用双调,先天韵。这是因为,在这些出里,武松、武大、潘金莲各自有着不同的感情,因此也就需要运用相适应的宫调和韵脚,借以富有变化地表达出各个人物不同的思想感情和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决不能死守‘每折一调,每调一韵’的格律,却不管剧中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可见,沈璟的曲论与其创作实践就发生了背离。这也说明,沈璟在理论上强调严守律法,乃是沿用文人词曲创作的传统,这恰恰乃是“案头”的规定,并非真正的“场上”要求。
四、结论
综上所述,汤沈之争语境中的“案头”与“场上”,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阅读文本”与“场上文本”,乃是以文本中的“曲词”是否合律为分野。尤其是当年的“场上”文本与今日的舞台呈现文本相差甚远,除了曲唱外,基本未涉及文本的舞台呈现方式。这种所谓的“场上”仍然是一种“案头”的“场上”。
注释:
①我们在讨论汤沈之争时,针对的是沈璟“不欲令一字乖律”的观点,并不涉及对他作品的全面评价。因为实际上,沈璟自己的作品在追求“本色”之际有不少破律之处,正如王骥德指出其矛盾之处云:“生平于声韵、宫调,言之甚毖,顾于己作,更韵、更调,每折而是,良多自恕,殆不可晓耳。”——《曲律·杂论三十九》
②明·王骥德:《曲律·论腔调第十》:然其(昆山)腔调,故是南曲正声。数十年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出。今则“石台”“太平”梨园,几遍天下,苏州不能与角什之二三。其声淫哇妖靡,不分调名,亦无板眼,又有错出其间,流而为“两头蛮”者,皆郑声之最,而世争膻趋痂好,靡然和之,甘为大雅罪人,世道江河,不知变之所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