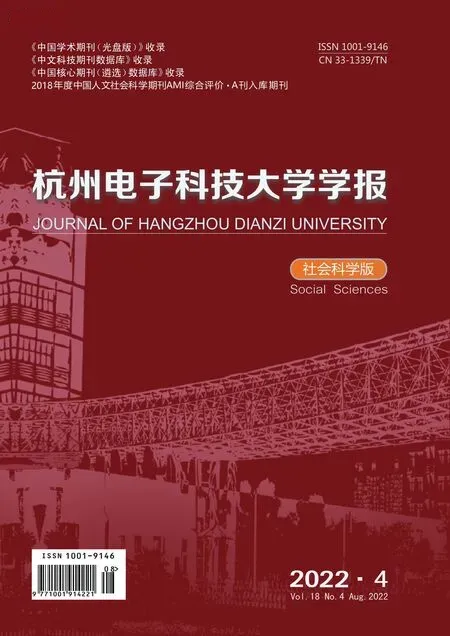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研究
尚长风,李云霞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由于人们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和适应能力有限,人类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各种程度不同的灾难。1942—1943年间,河南自然灾害频发。这一时期也是抗日战争当中较为艰苦的年代。在此期间,中国军队在中原大地与日本侵略军激战。一方面河南人民要为国军供应大量军需,另一方面,穷凶极恶的日军对河南进行了残酷的破坏掠夺。关于这场饥荒,以往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自然灾害、国民政府对灾荒的应对等,研究视角较为孤立,尤其对日本侵华与饥荒的联系有所忽视。本文从自然灾害、日本入侵,以及国民政府对灾荒的应对三个维度,综合探讨上述三个因素对饥荒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一、1942—1943年河南灾情
在人类农业生产的历史上,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粮食生产有丰有歉。如果仅一年遭受灾害,并不容易导致大饥荒,因为一般年份社会上总是留有一部分粮食备荒。但如果连年遭遇灾害,由于上年的余粮已被消耗,则极易导致大饥荒。1942—1943年,由于一系列的天灾人祸,河南人民处于惨烈的饥荒当中,河南省3 000万同胞中,“受灾1 500万以上,饿死300万,流落他省的200万”(1)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4月4日.。
早在1941年,处于战乱中的河南就发生了严重的旱灾。1941年夏,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河南的大旱就成了定局。当时洛阳农村的许多老太太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纷纷赶到城里的庙中烧香,祈求老天爷保佑。河南全省大部分地区除了夏秋之交稍沾雨泽外,自春至夏,自夏至秋,赤日炎炎,滴雨未下,夏、秋两季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据调查,仅在国统区的72个受灾县中,就有1 600余万人食不自给,占全省人口的二分之一以上,其中非赈不活的又有数百万人[1]。
不幸的是,1942年河南的自然灾害更为严重。据《大公报》报道,八九月间临泛各县黄河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严重(2)大公报,1943年2月1日.。1942年11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报道了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对灾情的描述:“豫省本年麦季,干旱为灾,以致二麦欠收。原冀秋收丰稔,以补麦收之不足,不意入秋以来,雨水失调,晚秋复告绝望,豫省安全区内之六十余县,几无县无灾,无灾不重。”(3)新华日报,1942年11月30日.据统计,1942年,国统区96个县的耕地面积约为6 400万亩,夏收麦田受灾约5 100万亩,秋收受灾约5 500万亩。国统区夏秋两季的粮食收成仅占全年所需的25%左右,另外75%则没有着落[2]。
继1941、1942连续两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43年河南又先后遭遇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的袭击。经济更加凋敝,饥荒持续发展。1941—1943年河南灾害的突出特点是连续性。即1941、1942、1943连续三年发生自然灾害,其后果必然极其严重。因为,农耕社会一直有积谷防饥的传统。对于偶发灾害,即使农作物歉收,由于农民、商家以及政府都留存有后备粮食,一般不致于出现大饥荒。但是,如果灾害延续发生,农作物连年减产,储备粮食消耗殆尽,大饥荒就很容易发生。由于当时日寇入侵,加之国民政府应对失当,惨烈的大饥荒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当时的河南国统区可以说是成了人间地狱,灾民死得路断人稀。河南国统区出现成片的荒地,饥民成群结队逃荒,饿殍载道。百姓被迫吃草根树皮,卖儿卖女,“人相食”的惨象不断发生。
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与饥荒形成的联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正面战场迅速溃败,河南便成为华北抗战的后方、西北的门户、武汉的屏障、南北战场的枢纽、中国抗战的最前线,形势极为严峻。1937年10月以后,日军即侵入河南境内。
日本侵略军先后向豫北、豫东和豫南进行了三次大的军事进攻。第一次是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侵犯豫北。到1938年2月底,豫北大好河山几乎全部沦入敌手。第二次是1938年5月至6月侵犯豫东。国民党军事当局为阻止日军西犯,炸开郑州黄河花园口大堤。黄河的洪水固然迟滞了日军攻占郑州再沿平汉路南下武汉的计划,但却淹没了豫东、皖北、苏北40余县的广大土地,给广大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第三次是1938年9月至l0月日军侵犯豫东南。到10月12日,日军占领信阳。至此,包括豫北、豫东、豫东南的河南半壁河山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退守黄河以南、新黄河(中牟、尉氏、扶沟、西华一线)以西、淮河以北地区与日军对峙。
至此,日军在河南的第一轮大规模进攻暂时告一段落。之后,直到1944年4月,河南形势基本稳定。期间日军控制的沦陷区和国民党控制的国统区区域基本稳定。
日军入侵是此次饥荒发生的元凶。正如《解放日报》所指出的:“在华北前线,在黄河的彼岸,侵华日军更是用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制造了这饥饿的大悲剧”(4)解放日报,1944年8月29日.。具体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这一时期抗日战争已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充分暴露,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全民族的反抗,必然带来支出激增。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被迫卷入为战争服务的轨道,包括统治者在内的社会主流的首要关注点在于如何抵抗日寇,粮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不得不被主要用于战争,民生被放到次要位置。
第二,由于日寇全面入侵,我国山河破碎,大一统格局不复存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沦陷区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河南国统区与其他地区被战争人为割裂。灾民向北、东、南三个方向的逃亡路线受阻。战争使铁路中断,救灾物资难以抵达灾区。常态年份救灾,一个主要手段是依靠灾区外部粮食进入,但由于日寇的封锁,外部粮食难以进入饥荒中的河南国统区。此外,河南国统区周边不少地区粮食收成尚好,正常年份,灾民可向这些地区逃荒保命,但由于日军封锁,灾民逃荒的路也被限制了。
第三,日本帝国主义对河南进行了直接的摧残和掠夺。河南国统区多地遭受战争蹂躏。据统计,到1943年底,河南全省的111县中,有48县经历过战争,其中经过多次战役且有大战者有13县。河南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17 312.6万公亩耕田遭破坏,伤亡者123 952人,死亡94 132人[3]。因战争影响,农业播种面积和产量也是急剧下降。日军还频繁地对非沦陷区进行“扫荡”,摧毁田地里的庄稼,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掠夺粮食、牲畜等物资,使国统区的灾情雪上加霜。
第四,在对日战争中,河南国统区的负担大增。河南是抵抗日军的重要战场,常驻国民政府军队50—100万。1941年7月1日前,这些部队的粮食由地方供应。由此,1941年上半年全省田赋征收额较1937年提高了一倍[4]。军粮供应与饥荒的关系,正如经历者所说:“1942年秋,当灾情严重人民在死亡线挣扎之际,正军方向省方索粮火急之时,人民旧存余粮,悉数充军犹不足,死亡惨重,此为一最大原因。”[5]此外,抗战以后,河南出兵役数量占全国最多,这大大减少了农业生产劳动力。河南人民还为抗战做出过其他贡献,如修路、架线、运输等。这些都严重削弱了河南抗灾能力。
第五,黄河花园口掘堤后果惨重。为了阻止日军西进,早在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下令在郑州的黄河花园口掘堤放水淹日军。黄河泥沙涌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没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运。每年汛期时,黄河水会回流倒灌,淹没农田,土地无法耕种,对农业造成严重破坏。河南大地惨遭蹂躏。据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河南、安徽和江苏3省44个县,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洪水,390多万人外逃。自此至1947年黄河归道,黄河水在泛区泛滥长达9年。持续多年的黄河改道后果严重,黄泛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条件严重恶化,各种灾荒频发。
三、国民政府当局对饥荒的消极应对
无疑,日寇入侵和自然灾害给河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这一时期国统区总体上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时间处于和平状态,国统区人民遭受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与国民政府对饥荒的反应有关。
自1927年北伐战争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彻底沦为没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反动势力的代表。由于其所代表的阶级与人民利益根本对立,这就决定了这一政权把维护其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利益作为其根本使命。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国民党当局与人民的敌对性质决定了其对饥荒的消极反应。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政府对百姓疾苦的漠视
人不可一日无粮,时效性对于挽救饥民生命至关重要。“救灾如救火,缓则莫及。”1942年夏收以后,严重的灾荒局面已经形成。这本是遏止河南灾情蔓延的关键时刻。但救灾意味着大幅减少征粮和增加对灾区的财政和粮食投入,这是国民政府所力图避免的。所以当饥荒发生以后,当局仍然漠视人民疾苦,没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阻止饥荒的发展。
20世纪40年代初,蒋介石的主要目标是抗击日本军队,同时准备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内战。为此,必须征购到足够多粮食以维持其财政和军粮之需。为了确保粮食征购,国民政府规定虚报灾况的要予以重惩、征粮有功的予以嘉勉。另一方面,在国民党政权的专制体制下,官员的升迁一般由更高级官员决定。
人的行为是由其所受到的激励所决定的。出于上述原因,各级官员为了向上邀功,普遍瞒灾不报,反而着力征粮。例如,当1942年河南大灾已成定局之后,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呈送的报告称“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1942年10月下旬,中央派张继等到河南查灾、赈济。在灾情汇报会召开前,李培基还嘱各地方代表:“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6]318
直到1943年3月底,在宋庆龄的力促下,曾到灾区做过调查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瑞德得以面见蒋介石,向其汇报灾情并出示灾区照片,才引起中央对饥荒的重视。
1943年4月以后,国民政府的救灾大规模地展开,但已经贻误救荒时机约半年。灾荒已造成惨重损失。正如当时的报刊所报道:“省政府一再急如星火地下令,把救灾运动作为目前行政的中心工作……可惜这个救灾运动开展得太晚,如果能早几个月成立,不知能多救活几千条人命呢。”[6]28
各基层政权也普遍漠视人民疾苦。特别是湖北、陕西等地政府冷酷地对待河南逃荒灾民,使得灾民生活雪上加霜。其景象正如当时的报章所刊:“豫省灾民逃荒到邻省的,多被拒绝入境,甚至武力驱逐。最惨的是壮男送壮丁,妇女强成婚,老弱则驱之出境,转死道途。”[6]177
1942年10月,在粮食大幅减产的背景下,蒋介石将1942年河南粮食征购额确定为250万石(事后,粮食部长徐堪改为250万包,约合280万石)(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开封文史资料(第5辑)[M].开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64.。1942年河南省的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7]。
以上的征收额远远超过河南人民的负担能力。于是,各地强力从灾民口中夺取粮食。例如,许昌县麦的收成大都是一成许,而当时的县长王桓武为了保住官职,强令人们按照他预报的八成收成缴粮。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逼着农民被迫卖掉所有的东西去纳粮(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许昌市魏都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魏都文史资料(第4辑)[M].许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许昌市魏都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4:55.。
(二)官吏普遍贪腐
吏治状况根本上由社会制度决定,是这一制度生命力的体现之一。在灾荒时期,各项临时性的举措较多,监管一般都较为薄弱,贪腐行为容易发生,这就能够比较明显地暴露一个社会的吏治状况。
由于历史原因,国民党先天具有“弱质性”,其中吏治不良是这一特性的重要方面。在1942—1943年的河南救荒过程中,国民党当局进一步暴露了其腐朽。突出的表现是,大批官员乘机发“国难财”,使得各项救灾举措乏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国民政府政权机构贪腐。例如,1943年3月,重庆中央政府拨给河南8 000万救济款,河南省当局“把这笔钱存入银行,让它生息增值”[8]。又因这些钱“都是面值100元的钞票”,需在银行兑成小票,才能在市场流通,而“一张100元的大票只能兑换回83元的小票——1元的,5元的和10元的”[9]。巨额救济款被盘剥。
其次,各级官吏贪污。例如,第1战区副总司令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爱将,驻扎河南期间,被称为“中原王”,是河南国统区实际最高统治者。大灾中,汤恩伯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深受其害的河南老百姓把汤恩伯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上行下效,基层官吏普遍参与各种腐败行为。如邓县田管处的黄剑峰,1942年“浮收征实征购为数至巨”,盗卖净尽(7)河南民国日报,1944年3月1日.。该县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私自将公仓小麦盗卖59 000斤[10]。
由于官员贪腐严重,一边是饿殍载道、尸骨遍野;一边是灯红酒绿、穷奢极欲。饥荒发生期间,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宴请英国访华团时,公开夸耀统治阶级的生活:“中国地大物博,抗战数年还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要吃什么,就有什么。”(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开封文史资料(第5辑)[M].开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74.
尽管国民党当局处理了若干贪腐官员,但受其统治基础和执政能力决定,这种处理仅仅是象征性的。如当巨贪汤恩伯受到指控时,蒋介石便公然为其辩护、开脱,并继续重用。正如当时报刊所指出的“中央近来已不讳言贪污,但伏法的多是末官微秩,尚不足以涤荡污垢、震慑贪官。”[6]269
(三)救荒举措失误连连
不可否认,日寇侵略对于国民政府救荒工作的开展有显著的不利影响。但是,当时救荒仍存在着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其一,饥荒主要发生在河南,而河南周边省份,如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份国统区的粮食收成尚好;其二,当时中原战局相对稳定,河南国统区与大后方的交通联系基本维持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是有可能避免饥荒的进一步发展的。
国民政府在根本上漠视人民疾苦,但在海内外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采取一些措施,救济灾民,但由于国民政府执政能力低下,这些救灾措施收效甚微。
1.从周边调粮情况
历代救荒的一个主要办法是从周边调粮。1942年9、10月间,河南省政府曾下拨垫平粜基金2 000多万元,派员分赴陕、皖、鄂等省采购粮食。1943年1月,根据行政院令,河南省组设省平粜委员会,由中国农民银行贷给平粜基金1亿元,分别从安徽、湖北、陕西等地购来粮食。同时,河南省当局另令各县成立县平粜委员会,自行筹集平粜基金,每县最少以100万元为限,共购进粮食1.7万石[11]。这些粮食与灾区的需要相比,是远远不足的。
当时,河南周边省份的粮食收成尚可。因此,通过从邻省购进粮食以缓解河南饥荒,本应成为一个有力的救荒举措。但实际上,相对于惨烈的灾情,购运来的粮食数量只能称得上杯水车薪,没有对缓解饥荒发挥明显作用。
究其原因,第一,国民政府对于救荒的投入有限,以及大批官员在平粜过程中营私舞弊,挪用贪污救灾粮和救灾款。第二,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有限,外地军阀们宁愿在本省多积粮食,而不愿救济河南灾民。正如时人所论:“邻封遏粜,无异关死豫民。”(9)前锋报,1943年3月27日.第三,为了遏制粮价的猛涨,当局曾经实行粮食限价政策,为此,还枪毙过黑市卖粮的商人。但由于这一政策,河南粮食的官价不比邻省高,致使一般商人不再把粮食从外省运进河南(10)前锋报,1943年2月18日.。
2.对灾民减赋、配拨种籽贷款情况
历代救灾的主要举措除了从周边调粮,就是减少粮赋。尽管灾情严重,但国民党当局仍在继续残酷地剥削人民,主要的形式是征粮。1942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将1942年度河南省粮食征实征购数额由原来的500万石减为380万石,后又核减为280万石,合200万大包(每大包为200斤)[6]15。同时,国民政府准许河南省在1943年4月以前先交140万包,其余60万包,30万包借作省级公粮及灾民口粮,另外30万包缓至1943年7、8月麦收后再补交(11)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A].河南省档案馆藏,M8-49-1407.。
由于灾荒歉收,粮种奇缺,1942年,由中国农民银行拨给麦种贷款500万元。另外,给予灾民晚秋种籽贷款85万元(12)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A].河南省档案馆藏,M8-49-1407.。这一举措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灾民在逃荒之前,普遍地把冬麦种上。这样,1943年夏季的收成有了可能。
但是,由于当局对百姓疾苦关注不足,粮食征收数量仍远远超过灾民承受能力,减赋对于缓解惨烈的饥荒没有发挥明显作用。
3.节约度荒情况
据研究,灾民吃普通人一半之食粮,即可勉保性命,不致饿死。这样,两个饱食人每人节省四分之一的食粮,即可养活一个灾民[6]232。因此,节约度荒可以成为应对灾荒的一个重要举措。宋庆龄、冯玉祥等爱国人士也力所能及地开展了一些募捐救灾工作。
但由于国民政府的腐朽,统治阶级与人民严重对立,整个国家甚至河南省基本上没有开展节约度荒工作。突出的表现是,粮食消费的极端不均衡。当全省处于严重饥荒之中时,一些官员富商则在正常地消费,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在享受奢靡的生活。据1943年3月7日河南《前锋报》记载,在灾区宛城,可以发现“包办酒席的饭庄餐馆,依然是珍羞纷罗,酒绿灯红,一席之费,动辄千金;洋广货肆,百物陈杂,价值上千上万的贵物,随到随即售去。”[6]23
此外,尽管国民政府还采取了设立粥厂、接济流民等救荒措施,但由于河南粮食不足,这些措施必然力度很弱,只能是象征性的。
总之,考虑到当时中原战局较为稳定,而且河南周边,如湖北、陕西、安徽等省的国统区粮食收成较好,国民党当局如采取有力措施就有可能避免大饥荒的形成。例如,迅速、大规模地将周边粮食运往河南;及时减少河南粮食征购额;整肃吏治等。但是,当局并没有有效地推行上述举措。各种救荒举措迟缓且虚弱乏力,只起到装点门面的作用,惨烈的饥荒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四、结语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究其原因,尽管天灾是饥荒的直接诱因,但更主要的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当局的腐朽。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战争对河南生产和生活设施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方面不得不把主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抗战。因此,日本侵华是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