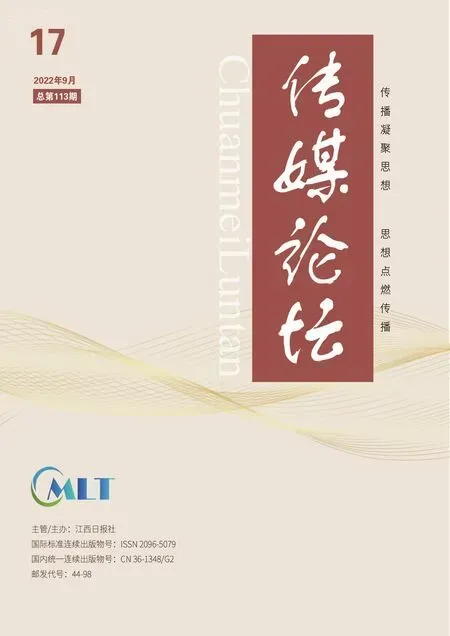娱乐心理:理解娱乐理论的起点
——读《娱乐心理学》有感
何丽敏
尼尔·波兹曼将电子媒介时代比喻为“娱乐业时代”。他认为, 娱乐本身没有错,但想住在我们筑起的空中楼阁里时,问题就出现了。[1]即当所有消息都以娱乐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就要提高警惕。[2]波兹曼基于电报、摄影术、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娱乐性批评而定下了“娱乐至死”的基调,娱乐、泛娱乐化被视为“荼毒”社会发展的“鸦片”。数字时代“泛娱乐化”现象在日常生活蔓延,批判甚嚣尘上。批判娱乐、鞭挞娱乐的笔墨,无不细数娱乐“陈罪”。
但随着“娱乐”的方法论作用越来越受重视,“娱乐”逐渐撕掉“一无是处”的标签。娱乐修辞以故事化、感官化、视觉化等形式在快乐传播中实现嵌入意识形态,彰显娱乐存在的价值。[3]娱乐社会价值与意义生产力的出现使娱乐传播与研究具备了合法性。[4]不过,其余的心理机制、概念化和解释性尚不充分,娱乐过程与信息、教育或劝服相关行为的区分并不明晰,“娱乐”越来越成为需要投以关注的领域。简宁斯·布莱恩特、彼得·沃德勒主编的《娱乐心理学》(晏青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2年)一书出版,有助于大众加深理解娱乐的基本心理过程和机制。
理性剖析“娱乐”,了解其作用机制、思考如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找寻娱乐的正向效果和存在价值,能让我们客观理解“娱乐”存在的必然和娱乐进化发展的价值。《娱乐心理学》以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心理学视角,围绕娱乐信息的接收、反应以及相关的心理学理论、模型三大部分内容,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娱乐现象”案例,以“为何娱乐、如何娱乐、娱乐何为”为线索,阐释娱乐信息如何通过影响心理、情绪、感知继而塑造行为,形成新的社会关系;通过娱乐我们能够获得什么、娱乐愉悦我们的心理机制等,为理解“泛娱乐化”趋势、我们为何需要娱乐等提供理论根据,描摹数字时代主体的娱乐化生存样貌。
为了深度阐释娱乐与心理学的关系与发展现状,《娱乐心理学》从心理学视角观察娱乐,呈现“娱乐的内涵与外延、娱乐形态、心理机制、劝服功能”等成果,将“娱乐”作为探析现实生活的入口,分析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现状、心理现状及其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分析娱乐背后的心理机制;对娱乐研究中与信息传播、教育或劝服、情感与认知、伦理等有关的讨论给予心理学层面的学理性解释。
一、娱乐:作为一种情感结果
在讨论娱乐如何影响并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前,首先要明确我们关注的“娱乐”到底是什么。娱乐的本质,并非对立的“善恶”二元论能轻易盖棺定论。《娱乐心理学》认为,娱乐是一项被人类追求且享受的体验,是一项有益的活动,通常被定义为对电影、电视、音乐、书本等娱乐产品的情感反应,也可以通过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相关学科对娱乐进行定义。[5]《说文解字》对此释义为,“娱,乐也”,指明追求娱乐是人的天性使然。大众文化携带的娱乐基因借力媒介技术疯狂生长、扩张,渗透到每一种文化肌理,日渐成为“一个流行语、一种风行一时的玩意、一套框架性工具、一个跨越不同学科的概念”甚或“是一个研究领域、一种研究方式、一种理论、一种视角”。[6]
关于我们为何追求娱乐的动机,本书提供了答案,其中一个便是享乐的目的。因为娱乐是一项被人类追求且享受的体验。[7]大部分动机心理学将人类活动的潜在原因区分为源于个人内部或外部的资源。内在激励行为的目的源于自身。内在激励驱动下的个体动作或行为是为了从其动作中获得满足感。我们通常因娱乐而娱乐,也是为了体验如愉快、悬疑、消遣、宁静等积极的感受。[8]这些源自我们自身的驱动因素提示了我们需要娱乐的动机,所以“人们认为娱乐是一项有益的活动”[9],身处不同环境中的个体都想娱乐自己且认为值得,正因为“娱乐是一种由内在激励驱动的体验”[10]。
那么,娱乐如何产生影响?书中第一部分是娱乐的“准备与接收过程”,讨论我们对娱乐内容的意向与选择,以及在接收和处理中所涉及的基本机制和过程。研究者们思考“为何娱乐”的问题,通过探究选择性接触理论的发展过程和结果,预测和解释信息时代的选择有效性。
在泛娱乐化媒介环境下,接触娱乐产品有助于满足权限、自治和归属需求。按照瑞恩和德西的“自决理论”,我们在娱乐中追求的“能力、自主、关系”需求可以理解为受到了内在激励的驱使。其中,“能力”将娱乐视为挑战性较小的活动,即在媒介用户可控范围内,并可让人获取一定成就感的行为。“自主”是为了表达我们按需选择娱乐内容的目的,但事实是这些行为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仍然受到了他人影响。“关系”展示了我们试图通过娱乐活动与他人保持联系的感觉,即所谓的拟社会交往或拟社会关系。有些人进行媒介消费的目的就是为了与名人产生联系。[11]
此外,与电视相关的研究展示了注意力如何为娱乐提供必要但不够充分的条件;发现了娱乐媒介“注意力与屏幕尺寸有关”的特征,以及注意力与娱乐相关的理论尚有较大发展空间的研究现状。借助概述认知心理学的感知观,介绍感知及其潜在过程的研究,为理解感知与娱乐媒介之间的关系提供基础,一方面呈现个体如何感知娱乐媒介,另一方面呈现娱乐媒介的频繁消费如何影响构念。
二、娱中寻乐:共情机制
面对娱乐,受众如何反应,其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什么?第二部分聚焦“反应过程”,解释我们如何从媒介信息中选择和接收娱乐的心理机制和过程。这部分的理论涉及幻想与想象、归因理论、倾向理论、共情反应、情绪管理、拟社会关系理论、个性娱乐等,为我们理解媒介娱乐的心理反应机制提供了视角。
媒介娱乐接触过程中,我们对于幻想和想象的心理反应有所变化。比如,我们通常怀有逃避糟糕现状的心态接触娱乐,试图借助观看更多娱乐节目转移注意力、寻求心理慰藉等。接触娱乐之后产生的刺激假说表明,我们会受到娱乐内容中出现的创意影响幻想和想象,尤其契合当下处境或想法时,很可能影响我们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不过,这种变化未必都能带来积极影响。折扣假说中的可视化假说、快节奏假说、被动假说和唤醒假说分别介绍视听娱乐负面效应,告知我们娱乐内容也可能对现实认知产生阻碍影响,如部分视听内容可能削弱孩童的想象力、暴力内容激发模仿行为等。[12]
那么,接触娱乐是否为诱导我们产生行为和情感反应的根本原因?归因与娱乐从考虑归因过程在娱乐媒介的处理中如何发挥作用的角度,介绍了参与娱乐体验中的第三人效果,以及通过娱乐调节情绪的享受娱乐体验等研究。[13]不过,归因思维作为娱乐体验的一个新论点,有助于让我们理解行为与认知的关系。
媒介娱乐体验中,娱乐共情是尤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所谓共情,即娱乐内容引发的对他人情绪体验的情感反应。书中介绍了共情的定义及其概念化过程,即产生共情的类别与方式,进一步阐述了包括进化路径、作为自反性反应的共情、作为习得性反应的共情、作为认知调节反应的共情、面向一个整体性的共情理论等问题。以共情反应过程为切点,可以理解短视频作为主流娱乐方式之一的关键在于依靠故事化共情内容引人入胜。可以说,短视频内容在短时间内抓住用户注意力,“共情”是让用户“欲罢不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即率先呈现扣人心弦的情节,配以气氛恰好的背景音乐,短小精悍的文案直击重点,在用户观看之际制造悬念捕捉要点,调动感官体验产生“共情”,愈刷愈停不下来。“共情理论”的反应机制表明,娱乐媒介根据媒介特性调整故事的叙事方式,才能在“娱”中寻“乐”。
三、娱乐有为:融入媒介叙事
第三部分通过介绍娱乐理论中的心理学理论和模型,主要内容包括:从感觉寻求的一般性人格维度的形成,基于不同人格维度分析其不同的娱乐偏好;以娱乐的享乐心理学为视点,探讨娱乐媒介使用和幸福感之间的联系;梳理并概述“净化”概念及其思想史,批判性审视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和复杂的情感重塑观点,为扩展娱乐理论提供新的可能性;借用进化生物学原理,从休闲时光取向、娱乐作为性选择、娱乐作为游戏等三种取向揭示娱乐进化的发展现状,供未来的娱乐研究方向作参考。
正如书中所言,我们试图从娱乐中进行感觉找寻。所谓感觉找寻,源自“感官剥夺实验”,是指我们“对各式各样新奇、复杂以及集中刺激和经历的找寻”[14]。在媒介娱乐中,高感觉找寻者热衷于现场娱乐活动,受动作、暴力等刺激性情节的娱乐内容吸引;低感觉找寻者也会满足于娱乐游戏、情景喜剧等内容。感觉找寻与娱乐内容性质的关联程度,表明娱乐活动新奇性、刺激强度、媒介喜好等能够满足我们在不同感官层面的需求。其中,具有视听多重感官和体验即时性的电视、电影等娱乐活动,比单一的视觉或听觉感官的文本娱乐更吸引人参与,更能带来独立的娱乐体验。这种感觉找寻行为,被视为一种媒介使用行为。其与我们试图在娱乐媒介中实现的“主观幸福”相关,即从“享乐主义”或“实现主义”出发,找寻能够提供激励或唤醒效应的外界因素,实现情感和心理上的幸福。受此主观因素诱导,我们在交互式娱乐媒介制造的愉悦体验中进行“拟社会交往”,形成“拟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媒介性质主导的娱乐方式改变传统媒介的娱乐形式和叙事方式,生成新的娱乐效果、娱乐价值和影响。
我们的娱乐行为往往也是情绪管理的需要。从齐尔曼的情绪管理理论论述来看,娱乐的体验是复杂的。我们为了改善自身的感觉状态,而有方向地选择某种媒介内容。[15]从这也可以发现,娱乐之于个体的积极作用,体现娱乐存在的正当性,发挥“娱乐有为”的价值。除此,跨媒介、互动式的娱乐能提供更多复杂的情感体验,可以创造时代性的正向娱乐影响,创新娱乐的内涵和丰富其“寓教于乐”效果。
四、结语
《娱乐心理学》一书解释了娱乐使用的动机、如何实现娱乐、娱乐的作用机制等内容,从心理反应、情感体验、行为认知等维度提供理解娱乐的专业视角,也为数字时代“娱乐至死”说辞合理与否留下反思:全盘否定的姿态难以正视娱乐化生存的正当性,融合视角挖掘深嵌新媒体技术的娱乐基因,通过掌握娱乐的作用机制,为文化产业的正向发展提供以“娱”活“娱”的疏导和管理路径,或是我们面对数字时代泛娱乐化现象与进行娱乐传播研究时可选择的批判态度。如书中所言,“只要我们注意屏幕之外的世界,娱乐会给我们的主观和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16],也许,当娱乐基因融入媒介“日常化”时,娱乐的正向效应将为我们实现有意义的生活一种方式,而娱乐本身也成为媒介文化、时代现状的一种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