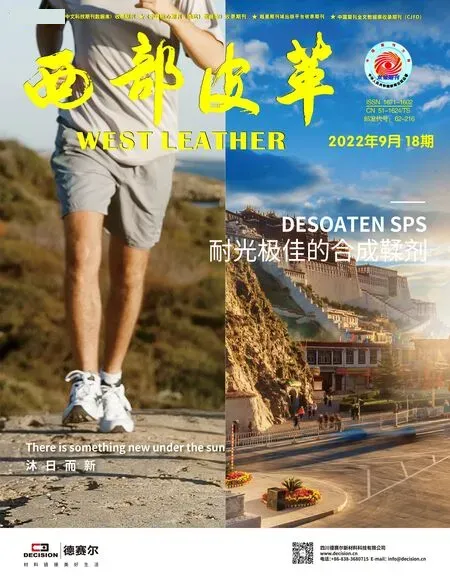西双版纳景洪市傣族织锦技艺变迁动因探究
郭朝义,王焱
(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051)
云南少数民族织锦技艺绚烂多姿,有独特的民族性和多彩的艺术性,其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傣族织锦技艺历史悠久,做工精细,承载着傣族特有的精神追求、思维方式、物质生活等民族底蕴,体现着傣族人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傣锦最初是古代流传在傣族民间的一种手工纺织品,是傣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是傣族造型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经历了从实用性为主到实用性与文化性并存,在傣族人民衣食住行的社会物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与傣族的原始崇拜、宗教信仰等精神生活息息相关。
自1949 年以来,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景洪市的傣族人民创造了一整套完整的傣族织锦技艺流程,其变迁过程对傣锦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织锦材质、纺织工具和图案设计方面都发生显著的变化,使景洪市傣族织锦技艺进入现代历史时期,实现由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的过渡和转化。
1 市场效应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少数民族亦无法置身其外,在被经济支配的社会现代化体系中,当经济发展全球化与民族多元文化间冲突愈发尖锐,作为民族文化代表的传统手工技艺同样面临着技术的局限性与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之间的矛盾。
傣族织锦作为傣族特有的文化符号虽有悠久历史,但民族手工技艺的发展无法游离于民族经济而独立存在,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是相互“嵌合”的。以傣族织锦现有的生产体系和分配方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傣族织锦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商品产生较大利润也难以实现。傣族织锦的作品在市场效应下很难获得较大利润的原因首先是:傣族人民对财产的欲望,尚停滞于原始的意识中未曾扩大[1]。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生产资料易获取,以及宗教中关于节欲的信仰,使傣族人民容易满足于较低的物质生活要求。傣锦织锦技艺一直停留在古老的生产模式,未有较大更新,传统的生产模式周期长、效率低、以及投入成本高,产出效益低。据了解,一个普通手挎包的制作,熟练的手艺人大约需要三天的时间,价格只有20—30 元不等;一个长2 米,宽20 厘米的围巾生产,需要15 天左右,售价在200 元左右,过低的收益使得人们现如今不愿投入太多的精力进行技术的革新。传统乡村农业以人力的手工劳动为主,属于一种劳动集约型经济,劳动的时间越长,劳动的人员越多,劳动的产量和产值增加,这就需要人们具有勤劳的道德品质,乐意在同一劳动对象上付出长时间的劳动[2]。然而由于傣族织锦技艺的学习相对复杂,经济效益较低,使得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主动为之付出较长的劳动时间,导致织锦很难适应现如今的市场需求。
其次是傣族织锦仍旧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并未上升到商品的层面。“商品本身是中性的,但它们的用途却是社会性的,既可成为篱笆,也可以成为桥梁。”[3]不同民族对于商品的理解有所不同,傣族人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绝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下,他们到街上去进行商品的买卖,只是把自己田里剩余的农产品或者自己劳动所得产品用来售卖,然后把售卖的钱转而购买所需的产品,这种交易的类型,就其本身性质而言,实含有“以有易无”的意义,是把自己生产的剩余,去交换消费的不足,双方都不从其中牟利,本来是种“物物交换”的举动,所不同于“以物易物”者,仅只是在方式上多一种货币来作为交易的媒介和价值的标准而已。在这里的商人均为远道而来的内地汉人,他们以当地人民需求较多的物品作为商品与傣族人民交易,从中获取高额利润。纵然当地的手工业较发达,但鲜有人愿意舍弃农业而从事商业,纺织品仅作为生活的必需品,并未上升至商品层面,使傣族织锦传统手工技艺的革新速度缓慢,技术改良空间小。
最后是低效的生产模式难以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经济是一种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性的存在,作为商品它也并非纯物质的对象,它是含有社会观念在其中的。傣族织锦作为傣族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现象,节日符号能影响、带动经济的发展。从形式上说,新的节日符号的创立或者对旧有的节日符号注入新的内容是一种外力强加于人的文化,但在实质上,这些符号的创立和改变,由于正好符合了活动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中的人们的利益而具有了存在的意义[4]。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景洪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民族旅游资源,傣锦作为文化符号是傣族对外展示的一种渠道,其资本化运作的市场潜力巨大。人们在有意识地改变传统符号的能指层面和所指层面,改变傣锦原有款式类型,加上现代化元素,即使是新酒装旧瓶的行为也表明人们在有意识地进行一些资本化运作,但由于低效的生产模式,导致手工技艺品无法满足如今大市场运作的需要。
傣族人民自身较少的社会需求与寡欲的宗教信仰,使傣锦传统纺织技艺的生产方式落后,革新速度慢,导致傣锦款式较为单一,“传统手工+手工工具”的生产模式,较大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投入,经济杠杆系数较低,无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品更多的是具有民族特色,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大,对产品的数量以及款式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而傣锦技艺生产效率低、时间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高以及样式相对较为单一的局限性,无法适应市场的需求。
2 政策制度
2005 年3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文中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与此同时,同年12 月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通知》,再次强调,再把握“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依法和科学保护”,更重要的是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同时,云南省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为了加强对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傣族织锦技艺”项目的保护,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化馆制定了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 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通知》(云财教〔2021〕165 号)等文件,2021 年度财政部下达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国家重点“非遗”项目“傣族织锦技艺”补助资金52 万元,为切实提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傣族织锦技艺”保护传承工作。
该项目的预期效果是通过举办传承人培训班壮大传承人队伍,提高传承人技艺水平,促进有序传承,有效促进傣族织锦产业化发展。在国家出台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的政策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化馆、景洪市文化馆以及文博馆积极响应号召,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傣族织锦技艺传承的制度,促进傣族织锦技艺的发展。
3 民间交流
关于傣锦的织造方法,首先是将花纹组织有一根根细绳系在“纹板”上,用手提脚蹬的方式使经线上下两层后开始投纬,如此循环往复,便可编织出精美的傣锦,傣锦的起花部分利用挑花方式起纹,所以表面会出现大量的纬浮纹起花,整经后的经纱均绕于木辊上,然后穿入分经棍、线综,而纬纱卷于小纡管上,织时可以将攸卷有经线之木辊挂与架上,展开经纱[5]。从工艺而言,傣锦的手工纺织过程是极其复杂、要求也极为严格。在傣族地区会传统纺织手工技艺的手艺人大多是年迈的老者,如今会手工纺织的年轻女性较少,这些手艺人都是经历多年练习,方才掌握这门手艺,在岁月的磨砺下,技艺愈发纯熟,所织傣锦亦愈发完善。
传统的纺织技艺更多的是需要日复一日地磨炼、积累,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劳动成本,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庞大的市场需求。现如今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尤其是具有民族特色,制作精良的商品,不得不对原有的传统手工织造进行改造。在此项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民族旅游村里的织锦商店中已经出现了缝纫机等一些半自动化的机器,出现的手工织造的改进,随着机器的不断改良和完善,机器会慢慢地取代手工操作,直至不再使用手工操作。机器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肌肉的过度疲劳,更减少了织工原本机械式工作的单调。罗雪尔强调,比工作的枯燥更严重的是生活的枯燥。当工人在工作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之后,他们下班后就不会有精力去从事其他的事情了[6]。传统纺织技艺多耗费的时间、精力、重复的动作,使得她们的工作生活相对枯燥,导致如今很少有傣族年轻女子学习织锦这门古老的传统手工技艺。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先生曾表示“为了生产,引进新的社会组织,变革力量也必须传授新的社会规则,在组织新工业中选择社会原则也与变革力量的利益相关。”[7]在傣族织锦密集的村落,政府组织成立了傣锦纺织协会,还有傣锦展览的场所,希望通过这种集中性的展示来提高傣锦的知名度,加上集中展示可以提供更多的产品供游客选购,商品多样化和潮流的迅速变化对于独自纺织者尤其不利,因为其没有足够的库存来供消费者挑选。相对于各自纺织,形成专门的组织或者场所,可以提供更大的商品规模供消费者选择;另外,创办协会为纺织技术交流提供平台,拥有更为强大的技术经济,传统纺织艺人不用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考虑销路问题,只需将精力投入到纺织生产上。如果一个地区只依赖产品单一的工业,那如果市场上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减少,或者是生产的原料供应不足,就容易出现经营惨淡的局面。换言之,当傣族地区个人的纺织产品无法有效地供应市场的需求,就会导致该地区的经营惨淡,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而当以协会或展览馆供游客参观选购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品的供应不足,形成一定的规模效益,市场经济。
傣族织锦作为一种传统的手工技艺,实质上是属于一种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市场在市场经济中是处于劣势地位的。比如当一个穷困潦倒、食不果腹的人对于货币的需求很大,也就是货币的边际效用对他而言很大,当他与雇主进行协商雇佣时,他是处于劣势地位,且当雇主以一种低于市场价格雇佣他时,货币给他带来的边际效用同样具有巨大吸引力,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双方本来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存在,买方处于优势,而卖方则处于劣势,所以受雇佣的工人明知自身处于劣势也会受雇于人。但是,在商品经济市场上,买方与卖方所进行协商价格时所处的地位是平等的。另外,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还有个区别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商品出售只有他自己。
因此,手工织造和技艺体系的突破与发展所带来的学习与交流,促进了技术的革新,使得傣锦上升到商品的层次,出现市场效应,改变原有依靠手工织造来满足家庭需求的处境,顺应时代的发展,出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提高生产效率进行机器化生产;同时,在国家加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背景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各级政府积极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傣族织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使得景洪市的傣族织锦技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发展。将原来一家一户单独经营转变为成立协会、开设展览馆等方式,突破原有的技艺体系,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将劳动力市场向商品市场进行转变,由此构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版纳景洪市傣族织锦技艺变迁的动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