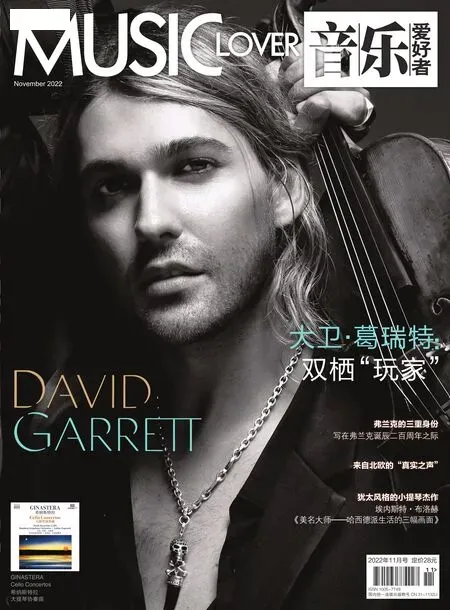戏曲要素与当代戏剧发展的共生性关联及其对戏剧音乐创作的影响
文字_缪薇薇
起源于古希腊悲剧的西方戏剧和孕育于东方文化土壤的中国戏曲,几世纪以来一直在各自独立的平行轨道发展。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东西方戏剧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一些西方戏剧家逐渐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开始试图找寻能够丰富西方文化的思想元素。他们以东方戏剧美学思想为参照,不断推动戏剧革新,丰富西方现代戏剧的艺术表现形式。
在这一浪潮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的“假定性戏剧理论”和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以“间离效果”理论为核心的“史诗剧”。虽然梅耶荷德、布莱希特的戏剧理念与中国戏曲的艺术追求、审美目标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些创新性的戏剧理论均是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审美形式,而后以此为基础,逐步实现了戏剧艺术的现代性转变。然后,这些更具前沿性的戏剧理论又反向推进了中国戏曲现代化的发展,形成了双向互动。
戏曲要素与当代戏剧的共生性关联
放眼当下,西方现代主义戏剧在观念和实践上不断创新、更迭,形成了多元化的戏剧艺术形式。这些戏剧艺术形式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了避免以生活的本来面目作为艺术描摹对象,试图去建构一种无法通过正常行为系统实现的作品或时间空间。为了让戏剧不再具有任何传统意味,连贯性的线性叙事被打破,戏剧的美学原则与组织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传统的故事讲述转变为演员为表情达意而运用的所有身体、动作和声音的语汇。

梅耶荷德
而相较对于传统写实性西方戏剧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中国戏曲则以虚拟象征性的手法摆脱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抽象的符号性的动作也与西方戏剧生活化的表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都成了导演和戏剧理论家们尝试反抗当时的自然主义风格戏剧所借鉴的重要形式之一。梅耶荷德就深受戏曲“写意性”审美观和赋予动作巨大意义的影响,认为戏剧的创作需要提炼并使用夸张的手法,他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假定性戏剧理论”,让时空在西方戏剧的舞台上变得更为灵活。他还提出了“有机造型术”这一概念,强调演员在舞台动作上的“形体造型”,以给人无限的视觉美感与心灵愉悦。

瓦格纳
另一方面,由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瓦格纳在《艺术与革命》《未来艺术作品》《歌剧与戏剧》这三部著作中提出了他所构想的理想化戏剧形式,认为音乐戏剧应该仿照古希腊时期“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导致戏剧、舞蹈、音乐和艺术之间的传统界限开始崩溃,形成不同文化领域、艺术门类之间的互相渗透。歌剧、话剧(传统的戏剧)也自古希腊悲剧衰败后开始分化,再次相互吸收各自不同的特征后又逐渐交融。
瓦格纳对“未来的戏剧”的设想启发了对当时很多戏剧理论家和导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对综合戏剧理想的追求,不仅仅只是像瓦格纳所提倡的那样对古希腊戏剧进行重建。伴随着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尤其是梅兰芳先生在莫斯科交流访问演出后,中国戏曲让西方人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戏剧语汇——“现实主义与假定性的有机结合”,而这正是他们所追求的综合性戏剧。在对于西方而言完全陌生的审美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戏曲这种通过“唱”“念”“做”“打”等多种手段与表演进行结合的具有高度综合性、象征性和程式性特征的复合式艺术形式,为西方戏剧所吸纳与效仿,这不仅推动了新的戏剧理论的创立,也为中西方戏剧找到了交汇点。
戏曲要素影响下的当代戏剧与音乐关系的变革
中国传统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在其戏剧化的音乐结构的制约下,剧诗、唱腔音乐、舞蹈化的行为动作等各种表现手段被综合在一起。这种音乐结构的制约在戏曲中被外化为音乐的节奏,表演中的各种节奏因素被规范成各种高度程式化的节奏形态。具有现实生活内在节奏感的身段、唱腔,在打击乐程式性节奏的调节和控制下被组织起来,使得多种表现手段在音乐节奏上达到统一。节奏形式的变化往往与人物情感的层次以及心理活动的展开相关联,以体现出更深的心里层面的节奏,强化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呈现。而舞台节奏往往是由戏剧冲突和戏剧行动决定的。因此,节奏不仅具有使多种艺术手段达到有机综合的作用,还能够赋予作品更大的戏剧张力。
受到戏曲形式节奏性的影响,音乐在西方戏剧舞台上开始逐步成为戏剧的“共同结构”,被纳入到西方戏剧导演的构思中。导演开始强调舞台时间、空间规则与音乐感之间的联系,使节奏作为贯穿整个戏剧演出过程中的基本结构元素,存在于戏剧行为、舞台调度的画面和演员的台词之中。梅耶荷德不但借鉴了戏曲中的念白和舞蹈化动作,还将台词的朗诵变为一种具有一定韵律的接近于吟诵的方式,让每个动作都与某种音乐形态相结合,使音乐的节奏贯穿于整个戏剧行为,并与之高度统一。这一方式让剧中的音乐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空间的音乐”,即“不仅通过时间表现,而且还通过空间形象表现出来的音乐”。布莱希特也借鉴了戏曲音乐强节奏性的特征,他认识到,鲜明的节奏感是使戏剧中的各种表现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协调、统一的核心因素。于是,布莱希特开始尝试在作品中以多种方式去强调作品的节奏感,如持续使用打击乐、块状化敲击性的和声进行、让演员在表演中用脚踏的方式打节拍等。音乐被用来指引演员所饰角色的动作、行为的表现,并被赋予了强烈的动作性。如同中国戏曲中舞蹈化了的“做”和“打”,演员在舞台上的行为动作经由音乐节奏被有机地组织起来。

布莱希特
在戏曲中,无论是“唱”“念”的声调变化、音乐的节奏运动、舞蹈的动作还是人物的扮相,都有非常严格的形式规范。它们以各自鲜明的形式特征影响着戏曲的综合形态,包括诗、音乐、表演、舞美在内的各种程式性表达。布莱希特认为这样的表演形式能够让演员将事件的原貌更真实地呈现给观众,而戏曲中程式化的形体动作所带来的优雅、力量和妩媚感会使现实的行为举止变得不自然,从而产生“间离效果”,使观众与舞台人物之间产生距离感,减少彼此情感上的共鸣。虽然,布莱希特对戏曲程式性表现手法意义的理解有所偏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表演手法对布莱希特史诗剧所强调的“间离效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主题演释方式的变化导致戏剧节奏改变,戏剧元素独立性的增加使得史诗剧的剧本结构、舞台美术、表演方法以及音乐的运用理念发生了变革。音乐在传统西方戏剧中通常起到深化戏剧内容、表现人物情感和心理状态、推动情节的展开、渲染情景氛围等作用,能让观众更快地代入舞台人物的表演,快速进入戏剧所构建的空间与时间。但在布莱希特的作品中,音乐则是其创造“间离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音乐的协助下,一些现实主义的场景被升华成典型性和历史性的意义,以达成事件历史化的目的。史诗剧的音乐与传统戏剧音乐在功能上有所转变,主要从原先音乐对剧本的强化、渲染心理状态转变为独立性地表达对戏剧主题的某种态度。音乐不仅能插入并打断戏剧的行为与情绪,阐明观点、立场与态度,也对舞台上所进行的戏剧行为起说明、评价甚至嘲讽的作用。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演员甚至需要一反音乐所制造的气氛来进行表演,使音乐在叙事性、动作性等方面都形成一定的“间离性”,以表达对事件批判性的理性态度。
戏曲的现代化对戏曲音乐革新的推动
戏剧通过中国戏曲写意性与西方戏剧写实性的结合,在多重文化的交互作用下产生了实质性的变革,在丰富戏剧表现形式与内容的同时,也扩大了戏剧的边界。而这种探索在对西方戏剧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又反过来推动了对中国戏剧本身的革新,实现了中西方戏剧的双向互动和观念的融通。
随着西方当代戏剧理论的引进,中国传统戏曲也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方向。在当代新戏剧运动的背景下,业界人士纷纷探索话剧与传统戏曲的多元发展路径,一系列具有先锋性质的戏剧形态应运而生。这类实验性的戏剧,其语言及动作介于戏曲与话剧之间。话剧道白、表演和戏曲念白、身段之间的自由切换增加了戏剧的间离性与假定性,呈现出了现实与虚拟的尖锐对比。例如,导演李六乙与作曲家郭文景共同创作的“巾帼英雄战争三部曲”——《穆桂英》《花木兰》《梁红玉》,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对李六乙所提出的“纯粹戏剧”理论的实践。该系列作品在剧场空间中探索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契合点。舞台视觉元素包含了传统戏曲的写意风格,其中简洁而隐晦的光影、涂上脸谱的人偶、古色古香的座椅,令观众赏心悦目。但其绝不仅是戏曲元素的简单堆砌,而是在创造中运用戏曲美学重构程式化表现形式,在文本、舞台、表演、导演、音乐等方面全方位进行革新,并以一种“新的综合形式”介入到传统戏曲当中,从理念上打破中西方戏剧以及各艺术表现方式之间的壁垒,获得一种全新的戏剧形态。
“巾帼英雄战争三部曲”虽是古代题材,但却并没有保留原有戏曲的叙事模式,李六乙导演通过全新的诠释与表现对传统进行了解构与重组。以观众所熟悉的三位巾帼英雄——穆桂英、花木兰、梁红玉为媒介,探索她们身为女性的内心世界以及作为女性英雄的悲剧命运。

01 李六乙

02 郭文景
在表演方面,其看似沿用了传统戏曲中的演唱与念白,配以舞蹈性的工架以及水袖、髯口等程式,但因其文本唱词具有现代性,为了适应内容的变化,演唱与念白在形式上也随之做出了相应的改变。
在戏剧处理手法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李六乙导演受到了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影响,演员会跳出角色之外,发表自己对战争和生死的看法,并自由进出人物内在与外在层次,通过肢体语言以及与他人的对话将其内心活动外化。以他人的不同意见隐喻主角自身的心理挣扎和矛盾,在塑造出多元化人物形象的同时深化戏剧主题。
在音乐的创作方面,作曲家郭文景在继承传统戏曲音乐功能的基础上,为契合具有现代精神及哲理化思想的主题内核,深度挖掘了人物角色的内心世界,并就戏曲音乐中乐器的选择与组合、乐器音色可能性的挖掘、唱腔和音高材料的丰富等几个方面做出了创新与改变,其创作观念也从以唱段为核心结构的表现手法转变成了更具戏剧统一性的整体性音乐设计。
音乐对戏剧舞台组织形式的改变应与戏剧语言、戏剧结构形态的变化同步,否则势必会造成内容和形式的不统一以及戏剧与音乐节奏的脱节。正如布莱希特的史诗剧中的音乐一般,完全以独立的元素参与对戏剧事件的评判,表明自己的态度,音乐在其中的作用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戏剧形式的变革也会推动戏曲音乐创作的发展,而如何通过现代作曲技法对戏曲音乐的变革做出新的探索,使其具有符合中国新戏剧形态所需要的现代音乐语汇,在戏曲的改革道路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巾帼英雄战争三部曲”中,郭文景并没有选择常见的以吸收西方管弦乐队的音响为其音色革新的手段,反而将乐器限定在传统京剧“四大件”中,通过非传统的演奏方法,结合丰富的民族打击乐器编配与组合,赋予了作品全新的音响色彩,其实验性体现在对每一件乐器自身音色表现力的个性化表达。一直以来,声乐都在传统戏曲中占据主要地位,在这部作品当中,作为伴奏存在的乐器第一次超越了其原本“拖腔保调”的传统功能,有了作为京剧唱腔、身段动作的辅助衬托之外的独立表达。这些乐器时而通过特殊的演奏法制造出戏剧中环境的模拟声,时而以其对戏曲韵白的“音色模拟”分离于角色,在对声乐、念白的音色与节奏模仿中,使人声与器乐音色的交替自然衔接,并完成戏剧性的表达。
除此之外,作曲家还使用特定的音色、织体在进行角色性描绘的同时,与角色的肢体动作及表情相结合,以承载人物内心空间的展现、强调人物情感的纵深化表达,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在唱腔、音高材料及节奏的运用上,作曲家则选择以对置或并置的方式与传统的程式化相结合进行表现,如在运用西皮、二黄时与人物持续的舞蹈化动作、表情相匹配,以锣鼓经烘托氛围,以及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具有个性化的音乐语言等。作曲家在保留传统戏曲核心音响特征的同时,突破了以往的戏曲旋律、音色、节奏创作理念,以丰富且多层次的音乐语言和音响效果来突显人物内心的多重变化,深化戏剧矛盾冲突,体现了戏曲音乐在现代审美、创作技法发展趋势下的创新和探索。
中国戏曲音乐如何在结合戏曲抒情性传统与西方戏剧现实主义精神追求的中国新戏剧形态中,找到贴近中国当代戏剧性表达的、融合性的平衡点,是当代作曲家在创作戏曲音乐创作时需要思考的。我们应坚持守正创新,在继承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写意化、虚拟化、程式化的本质,并积极借鉴西方当代戏剧理论,广泛结合现代作曲技术,将其现代作曲技术在音色音响、结构、音高材料、节奏上所寻求的实验性和创新性的突破运用到当代新戏剧形态中,以适应新的叙事和戏剧行为的节奏及其所承载的戏剧结构,充分运用能够体现出文本中现代性的戏曲音乐形态,将其与演员舞台行动轨迹相结合与介于生活化的念白和戏曲化的韵白之间的表演形式所体现出的节奏、韵律达成高度统一,其所呈现出的创作价值亦会促进戏曲的持续性演变与发展。